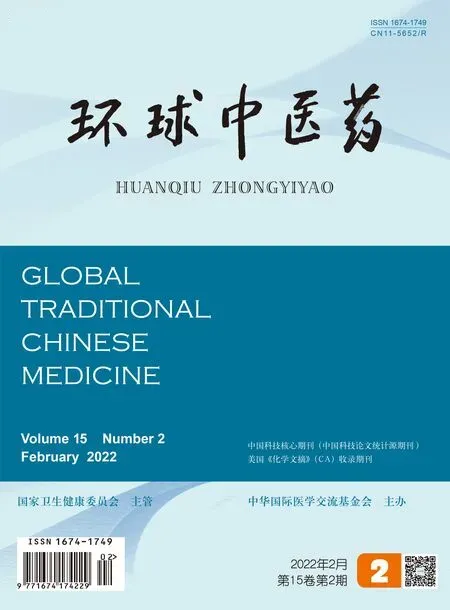基于“有故无殒,亦无殒”思想谈有毒中药在防治类风湿关节炎中的应用
王文炎 黄裳 李勇 阮崇洁 熊源胤 王进军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发[2016]42号);武汉市卫生健康科研基金资助项目(WZ20C11)
作者单位: 430014 武汉市中医医院针灸科(王文炎、黄裳、李勇、阮崇洁、熊源胤、王进军)
作者简介: 王文炎(1984- ),博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风湿病的研究。E-mail:282810054@qq.com
通信作者: 王进军(1975- ),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风湿病的研究。E-mail:wjj2003210@163.com
“有故无殒,亦无殒”出自《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妇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帝曰:愿闻其故何谓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中医名词术语精华辞典》将其解释为:“系一种用药法则……指临床用药时,虽药性峻猛,只要有相应病证,药证相符,就不会出现危险。”[1]“有故无殒,亦无殒”的核心思想是药证相符——“有是证用是药”,理论实质是“以毒攻毒”的治疗原则及其所衍生出具体化的治疗方法和手段[2]。“有故无殒,亦无殒”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目前主要用于妇科疾病、肿瘤的临床用药指导和临床药物毒性评价[3]。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多种免疫细胞参与,以慢性对称性、侵蚀性关节炎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自身免疫疾病,病情顽缠,迁延不愈[4-5]。本病病因病机复杂,“伏毒学说”[6]和“双毒学说”[7-8]认为,毒邪是RA的重要病因,是其发生、发展及转归的重要影响因素[9],而以毒攻毒法是防治RA的主要方法,并贯穿于始终。因此,“有故无殒,亦无殒”思想应用于防治RA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指导价值。
1 有“故”,故“无殒”——大胆、尽早以毒攻之,阻止病情进展
RA的病程长,反复发作,活动期与缓解期交替出现。活动期病情严重,进展快速,若不及时控制病情,则出现多系统损害,尤其骨关节的侵蚀和破坏,关节功能丧失,致残率高。慢性期病情顽固、缠绵难愈。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对RA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强调早期诊断、早期干预。RA确诊后应尽快使用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 DMARDs),可加用生物制剂或激素快速控制病情,阻止病情的进展,使疾病缓解或处于低活动度[10]。这些药物均会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属于毒性药物的范畴。即使毒性药物,大多数RA患者长期使用后并无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往往获益更多,这正是“有故无殒,亦无殒”核心思想——有是故用是药的具体运用。
中医认为毒邪是RA发病的先决条件,毒力强弱决定其发展、转归及预后。在“有故无殒,亦无殒”思想的指导下,一旦RA诊断明确,辨证准确,应大胆、尽早运用具有攻毒或解毒作用的药物或毒性药物进行治疗,以防止毒邪对人体的破坏,阻止或逆转RA的进展,不应畏惧药物的毒副作用,错失遏制毒邪蔓延的势头,造成对人体不可逆转的损害。
2 坚持以毒攻毒的治疗原则,分期分“故”论治
无论是RA活动期还是缓解期,毒邪一直存在。RA的伏毒学说认为,伏毒作为RA的病理产物及致病因素,是RA发生发展、迁延不愈的一个重要因素。避免诱发因素,控制伏毒外发,可提高临床疗效,并将扶正袪毒法做为防治RA的基本原则,贯穿始终[6]。从目前现代医学的治疗和研究现状来看,RA仍是一种不可治愈的慢性疾病,需要长期使用DMARDs控制病情。这正是“有故无殒,亦无殒”理论实质——以毒攻毒治疗原则的运用。根据不同时期RA毒邪来源、性质的不同,实行分期分“故”治之。
2.1 活动期权衡伏毒、外毒多寡论治
从病因角度来看,RA活动期之“故”包括伏毒、外毒及两者兼存三种。不同类型毒邪的来源、性质及其病机、治疗方法亦不同。根据RA活动期“故”的不同,分而治之。
2.1.1 内生伏毒 伏毒来源于体内的痰浊、瘀血、湿热蕴集胶结而成,毒性暴戾险恶,毒力强盛,病性为邪实,病情较重,病势凶险,不仅损害形体脏腑,而且耗伤正气。这相当于现代医学RA活动期的免疫失调所致的病理表现,即免疫细胞过度增殖、活化,产生一系列的细胞因子、抗体、免疫复合物,形成关节滑膜炎、血管翳,侵蚀关节软骨及骨组织,造成不可逆的骨关节破坏。临床表现为多关节的肿胀疼痛,关节功能障碍,常伴有肺、眼、血管、皮肤等关节外损害,以及发热、贫血、白细胞减少、乏力等全身症状。湿、热、瘀之毒是活动期类风湿关节炎的核心病机,分别与脂质代谢、微生物,炎症,血流变学等指标密切相关[11]。
治疗方面,针对伏毒及其蔓延所导致的病理损害,运用以毒攻毒的治疗原则,大胆使用毒性药物治疗,非一般解毒药物所能奏效。非雷公藤、马钱子、昆明山海棠、蜂房等毒性药物不能遏制毒邪,同时应强调辨证论治,配伍非毒性或毒性较小且具有解毒作用的中药,如热毒甚者,加石膏、知母、蚤休、土大黄、黄柏、白花蛇舌草等以清解热毒;湿毒甚者,加土茯苓、萆薢、泽泻等以利解湿毒;痰毒甚者,加土贝母、白芥子、苏子等以化解痰毒;瘀毒甚者,加土牛膝、三棱、莪术、蜈蚣、全蝎等以化瘀毒、通经络;寒毒甚者,加乌头、桂枝等以温散寒毒。现代医学强调RA活动期在尽早使用DMARDs药物的基础上,使用生物制剂或糖皮质激素快速减轻或消除炎症反应,控制病情,以防止病情进展,减轻不可逆的损害。“清解伏毒法”可有效延缓RA患者停用生物制剂后病情复发,降低复发率[12]。解毒凉血化瘀法能够缓解活动期热毒痹阻型RA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患者关节生理功能和降低实验室指标,远期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良好[13]。以笔者愚见,临床实践过程中宜中西医结合,采取最适合患者的方案治疗以快速遏制毒邪蔓延,减轻不可逆的脏腑形体损害,保存正气。
2.1.2 外感邪毒 外毒来源于外界环境中直接感受的邪毒,包括中医学的六淫邪气和现代医学的物理、化学、生物、环境等因素。伏毒本已控制或基本控制,但由于长期使用DMARDs药物或邪盛伤正,导致正气亏虚,则外毒侵袭诱发伏毒而形成以外毒为主的毒邪。相对于伏毒而言,外感邪毒的毒力较轻,病性邪实为主,兼以正虚。这相当于现代医学中RA患者体内的免疫失调得到基本控制,无或低度的炎性反应的基础上,感染(病毒或细菌)诱发低度的异常免疫活动,再次出现低度的滑膜炎症,伴或不伴其他系统炎症反应。临床表现为关节轻中度肿胀疼痛,活动受限,伴或不伴发热恶寒、乏力、肌肉酸痛、咽痛咽痒、咳嗽咳痰、尿频尿急、腹泻等临床症状。
治疗方面,维持原有的治疗方案控制伏毒,针对外感之毒辨证选用不具毒性的解毒药物治疗,兼顾扶正。如外感风、寒、热毒导致上呼吸道感染者,选用银翘散加减以疏风散寒、清热解毒;外感之毒入肺出现咳嗽咳痰、呼吸困难者,可选用清金化痰汤加土贝母、土大黄、土茯苓等以清热解毒、化痰止咳;外感之毒入膀胱出现尿频尿急尿痛者,可选用八正散加土茯苓、土牛膝、土大黄、金银花等以清热解毒、利尿通淋;外感之毒入胃肠出现腹泻者,葛根芩连汤加土茯苓、土大黄等以清热解毒、渗湿止泻。现代医学对此种活动期RA的治疗方案为维持原有的抗风湿治疗方案,常使用抗生素治疗。以笔者愚见,这种活动期RA的治疗,在原有抗风湿方案的基础上,采取中医辨证施治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2.1.3 伏毒、外毒兼存 伏毒、外毒两者兼存者,其毒来源于未控制好的伏毒和外感之毒。毒性、毒力介于以上二者之间,病性多为正虚邪实,病情病势与伏毒与外毒之比成正比。比值越大,病情病势越重,比值越小,病情病势越轻。临床上多由于伏毒控制不佳,加上外感邪毒,二者相互影响,级联放大异常的免疫反应。治疗上,权衡伏毒与外毒的多少,内外双解,立清解邪毒之法[14],选用毒性药物和辨证选用非毒性解毒药物治疗。对于此种活动期RA,现代医学调整抗风湿方案和使用抗生素联合治疗。
2.2 缓解期控制伏毒,兼防外感之毒
陈广峰等认为伏毒是RA缓解期的重要致病因素,其隐伏、缠绵、暗耗、杂合、多变等特点与RA缓解期慢性、进行性、侵袭性、易复发性、致残性的病理特点相吻合,运用伏毒理论指导RA缓解期的治疗,以扶正为本,从补气化毒、清解伏毒、调养结合等三个方面进行治疗[15]。
内生伏毒以解毒、祛伏、补虚为法,选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加蜂房、忍冬藤、炒白术、土茯苓、土牛膝、土贝母、萆薢等药物祛除伏毒,兼以补虚,祛邪而不留寇、补虚而不恋邪[7]。黄芪桂枝五物汤单用或联合应用治疗RA,其作用机制可能涉及抑制血清炎症细胞因子表达,抑制滑膜脂质过氧化和促进细胞凋亡等[16]。通过网络药理学法分析,黄芪桂枝五物汤通过多成分、多靶点及多途径的方式治疗RA,涉及对脂多糖、细菌来源分子、脂筏的反应,膜微区、核受体及类固醇激素受体活性,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及其受体、肿瘤坏死因子及白细胞介素-17的信号通路等[17]。
虽然处于缓解期,毒邪仍然伏藏于内,仍需要使用毒性药物控制伏毒,防止伏毒内发。同时,由于活动期毒邪亢盛耗伤,或长期使用毒性药物损伤脏腑功能,导致正气亏虚,治疗应以扶正解毒,一方面既要控制伏毒以防内发,另一方面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防止外感之毒侵袭诱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亏虚则百病由生,故缓解期的治疗尤应顾护脾胃,常配以黄芪、山药、薏苡仁、麦芽、谷芽、生姜、大枣等药物扶正补虚、顾护脾胃。现代医学认为RA缓解期患者体内异常免疫活动引起的炎性反应较轻,疾病活动度较低,且无感染因素,只需根据患者体质、年龄、病情活动度等因素,综合制定抗风湿方案控制病情,兼以预防感染因素。笔者愚见,RA缓解期若无明显气血、阴阳失调、脏腑功能失调等,采用治防结合的方式治疗,以雷公藤制剂或DMARDs等毒性药物控制伏毒,以饮食、起居、情志、摄生等方面的调摄增强体质,预防外感之毒。
3 “衰其大半而止”——把握量—效—毒之度
毒邪是RA之“故”,以毒攻毒的治疗原则贯穿防治RA始终。毒性药物用之得当则病受之,不当则体受之,造成身体的损害。故RA的临床实践使用毒性药物时,应遵循“有故无殒”的度——“衰其大半而止”,即准确把握其中药量—效—毒的关系,做到药到即止,勿过量或长时间使用,否则病邪去而伤及身体。《程杏轩医案》曰:“用之当不当,不必问其毒不毒。苟用之不当,即无毒亦转为大毒,用之得当,即有毒亦化为无毒。”[18]现代动物实验研究显示,熟大黄对正常动物具有一定的肝毒性,但对于肝损伤动物具有治疗作用[19];何首乌肝毒性与不同证候存在一定关联性,对证使用较为安全,而不对证会导致肝损伤的风险增高[20];低剂量雷公藤提取物在模型大鼠上可改善肾功能,减轻肾脏病理改变,起到肾保护作用,但高剂量则加重大鼠肾损伤[21]。
4 小结
“有故无殒,亦无殒”的核心思想是药证相符——“有是证用是药”,理论实质是“以毒攻毒”的治疗原则,使用之度是“衰其大半而止”。根据RA的临床特点,“有故无殒,亦无殒”思想应用于防治RA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指导价值。临床实践中,一旦确诊,大胆、尽早运用具有解毒作用的药物或毒性药物治疗,阻止病情进展,坚持以毒攻毒的治疗原则,分期分“故”治之,同时还应把握毒性药物的量—效—毒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