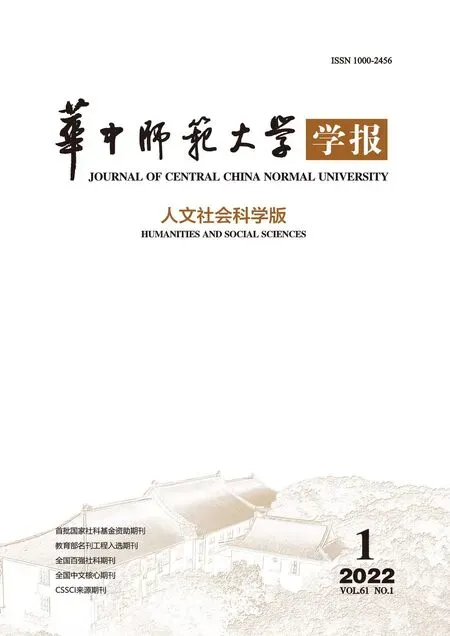五四新文学与国语建设新论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国语是国家通用语言,代表国家的语言水平和语言标准。中国古代也有事实上的“国语”,即“古文”或“文言文”,亦即古代汉语,今天的“国语”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建立起来的新白话文,现代时期称为“国语”,1949年之后则称为“现代汉语”,也叫“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国语在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新文学运动,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建立国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国语在五四之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其中文学对其巩固、稳定和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为什么文学语言对国语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一、新文学运动与国语的建立
历史层面上,现代“国语”是由现代文学建立起来的。在具体原因和具体过程上,“国语”的形成首先要归功于“文学改良”。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文学语言改良“八事”(1)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八事”的根本就是提倡白话文,其实提倡白话文学也就是提倡“新文学”(2)胡适:《胡适留学日记》,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年,第292页。。白话文学的主张得到陈独秀的积极响应,紧接着《新青年》第6号就发表《文学革命论》,新文学运动迅速由“改良”上升为“革命”,《新青年》杂志的主体语言也随之改为白话文,《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了胡适的《白话诗八首》,还有其他白话诗歌以及白话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观察,胡适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发表更具革命意义的长文《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了最具有建设意义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的基本思路:首先用白话文创作出成功的文学范本,然后再根据这成功的文学范本确立“国语”,这其实也是胡适新文学运动的步骤,最初只是提倡白话文学,为白话文学争取“权力”,在语言上最初只是提倡白话文,和文言文争平等的地位,但随着白话文的流行以及白话文学的兴盛,胡适在文学和语言上从“改良”走向“革命”,不再只是提倡白话文,而是提出废除文言文主流地位,主张白话文“独尊”,新文学“独尊”。《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表明,胡适对中国文学、文化和语言等已经不满足于最初的新诗“尝试”,而有了更大的理想,那就是从建立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始继而提升到建立更深层的中国语言类型,改变语言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思想文化,建立真正的现代文明。所以,《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比他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更具有“建设论”意义,是新文学、新文化、国语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的真正经典性文献。笔者认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通过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语言来建立新的通用语言即“国语”。
胡适反复强调,“国语的标准决不是教育部定得出来的,也决不是少数研究国语的团体定得出来的,更不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定得出来的”(3)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165页。,“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48页。。又说:“标准国语不是靠国音字母或国音字典定出来的。凡标准国语必须是‘文学的国语’,就是那有文学价值的国语。国语的标准是伟大的文学家定出来的,决不是教育部的公文定得出来的。国语有了文学价值,自然受文人学士的欣赏使用,然后可以用来做教育的工具,然后可以用来做统一全国语言的工具。”(5)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国语是在语言实践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但在形成的过程中,人的主观努力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其中作家和文学的作用是最大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优秀文学作品的语言在品质上是最好的,也是最能够为民众所接受的,所以胡适说国语都是文学家造成的,国语的标准出自伟大的文学作品。胡适说:“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50页。又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45页。“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8)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47页。这不是先有鸡或先有蛋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先有白话文学的实践,有了成功的文学作品之后再选择这种成功文学的语言作为标准来建立“国语”,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白话文学实践其实也就是“国语”实践,文学实践与国语建构之间可以说是双向互动关系,在相互促进、循环往复的过程最后既成就了文学,也成就了语言。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刚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发表,随后的《新青年》第5号就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这在时间和逻辑上也有某种“隐喻”性。事实上,“国语”正是因《狂人日记》这样一批新文学经典的产生而确立的,新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确立了,现代汉语即国语作为一种新的语言体系就确立了。成仿吾说:“我们的新文学运动,自从爆发以来,即是一个国语的运动。”(9)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见《成仿吾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92页。为什么要通过“文学”实践建立国语,根本原因就在于文学的语言是最优质的语言,胡适曾对“文学”的语言特质做过论述:“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又说:“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10)胡适:《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149页。胡适所说的“文学”语言的标准其实也是国语的标准,既包括思想上的比如概念准确、词语意义清楚明白、逻辑性、表情达意等,也包括语言形式上的诸如优美、典雅、精致、简洁、纯粹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成功其实就是“国语”建构的成功,以后“国语”还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但基本上不脱五四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文学语言的范围。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对“普通话”是这样定义的:“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11)《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见王均主编:《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这里所谓“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主要就是指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的文章这样广义的散文作品。
“国语”确立之后,不断有人对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起来的新白话即“国语”提出质疑,不断有人从语言学的角度对“国语”提出新的设想。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兴起“大众语运动”,展开大众语论战,一方面批判语言复古主义,但同时也批判五四时期形成的国语,认为它过于“欧化”,比如黎锦熙概括说:“现在的‘普通话’里头,却也因东西‘交通’,译语盛行,早已羼入了一些外来语的分子。……现在的作家或译者,未免欧化得过分一点儿,由欧化而艰涩化,乖僻化,却还要站在‘大众语’的立场来骂第一派是官僚式的国语。”(12)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5页。“大众语运动”除了理论主张以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实践,希望建立一种真正的大众能够理解和掌握的语言作为国语,但20世纪30年代大众语文学实践并没有产生真正的伟大的作家,也没有产生为国人所认同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国人所接受的还是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创作为代表的五四白话文的现代文学,这种对典范的现代文学作品的认同就决定了“国语”在标准上的不可动摇。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之所以无法取代五四时所建立起来的国语成为新的“国语”,除了理论上的问题以外,显然与缺乏充分的成功的文学实践支撑有关。
其实,五四之前有很多类型的白话文:一是古白话,即近代汉语,一般认为其代表文学作品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是一种以口语为基础适当吸收古汉语而形成的白话。二是纯粹的民间日常生活中的口语的白话,这种白话本来主要限于日常生活的口语交流,但清末民初报纸兴起之后,为了让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懂,一些报纸特别是地方小报也使用这种多方言、俚语的白话,这些报纸被称为“白话报”,这类白话没有产生经典性的文学作品。三是半文半白的白话,也即雅化的白话,主要是正规刊物和书籍使用的白话,由精通或粗通古汉语的文人创造出来,《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等是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其写作目的既有商业的原因,也有文化普及的原因。上述三种白话在五四之前都广泛地流行,但都无法上升到“国语”的地位和层次,都无法撼动古代汉语的“国语”地位。
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起来的白话是一种全新的白话,从词语构成上来说,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既充分继承了古代汉语和古代白话的合理因素,又充分吸收西方语言的各种因素,是中西两种语言交流、融合而产生的第三种语言,既能够有效地言说中国,也能够有效地言说西方。在品性上,五四白话具有通俗性,因而有广泛的群众性,同时它又充分吸收和继承文言文的古雅与严正,最重要的是它学习西方语言,大量吸纳西方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因而具有现代性,并保持着对西方语言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以根据五四新文学建立起来的五四白话是最好的白话,因而成为标准汉语也即“国语”。瞿秋白说:“旧式白话小说,建立了相当意义之中的‘新的文学’,但是并非国语文学。”(13)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45页。这是非常正确的,新文学白话具有独特的内涵,包括现代思想、综合性的词语体系等,五四白话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是古代白话,胡适重视古代白话的意义和价值,强调五四白话的古代来源,这是正确的,但他说“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14)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集》(第2卷),第46页。,这明显又是片面的。首先,文言也有好的文学作品,这是明显的事实,白话中有大量的平庸之作,这更是明显的事实。其次,白话并不是语言是否有“生命”的标准,也不是“国语”的实质,更不是新文学的实质,现代思想用白话形式才是国语的实质。朱希祖说:“若从文字上来讲,以为做了白话文,就是新文学,则宋元以来的白话文很多,在今日看来,难道就是新文学吗?”(15)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6页。这是非常有道理的。白话文学不是新文学,古代白话和后来的国语白话即现代汉语是两回事,当时胡适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二、为什么晚清的白话文不能作为国语?
“国语”表面的特征是白话,但白话文早在五四之前就有了,先秦就有白话,唐以后产生了很多白话文学,包括白话小说、白话散文、白话诗等(16)参见徐时仪:《汉语白话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清末民初就有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白话文运动,产生了很多白话报纸、白话期刊、白话图书。中国最早的白话报据说是1876年在上海出版的《申报》附刊《民报》,1897年10月创刊的《演义白话报》是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的。1898年之后,白话报大量创刊,比如《无锡白话报》《广州白话报》《白话报》(有多种)《常州白话报》《京话报》《官话报》《杭州白话报》《苏州白话报》《芜湖白话报》《通俗白话报》《湖南白话报》等(17)参见《中国早期白话报汇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9年。,此时的陈独秀和胡适都主编过白话报,这些都是文化白话报,此外还有科技白话报。有人统计,清末民初出现了370种以上白话报刊(18)胡全章:《清末民初白话报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白话期刊有著名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等。此外,还出现了白话课本比如吴遁生、郑次川编辑,王岫庐、朱经农校订的《古白话文选》上下册(19)参见吴遁生、郑次川编:《古白话文选》,王岫庐、朱经农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年。、《近人白话文选》上下册(20)参见吴遁生、郑次川编:《近人白话文选》,王岫庐、朱经农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1924年。。早在胡适提倡白话文之前就有人提倡白话文,比如著名的陈子褒、裘廷梁和刘师培,他们分别写作了著名的《论报章宜改用浅说》(21)陈子褒:《论报章宜改用浅说》,见《陈子褒教育遗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论白话为维新之本》(22)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国官音白话报》第19、20期(合刊),见《无锡文库》第二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23)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见万士国辑校:《刘申叔遗书补遗》上,扬州:广陵书社,2008年。等文章,都明确提倡白话文。既有理论倡导,又有非常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实践包括文学实践,产生了大量的白话文学作品以及白话文章,白话也被知识阶层认同,被人民大众所接受,但晚清白话文运动却没有建立起国语,晚清的白话文也不能作为“国语”,为什么?
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晚清的白话文没有达到“国语”的标准,不具备“国语”的品质,包括外在的形式与内在的思想表达的能力。白话报中的白话过于“原生态”,存在大量的方言俚语,过于口语化,同时又缺乏提炼、融合以及改造,加上通行范围非常有限,因为混杂、差异性而不能作为“共同语”通行。白话期刊中的白话其实是“古白话”和“近代白话”,在口语层面上主要是“官话”,但“古白话”也好,“近代白话”也好,“官话”也好,白话词汇和表达都不具有完整性,所以五四之前的白话写作必须大量借用文言文才能完成。清末期刊白话文在今天看来其实是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或者说文言化的白话,虽然产生了一些作家,产生了一些成功的文学作品,但这种文学主要是通俗文学作品,读者主要是中下层市民,作家也是通俗文学作家,其语言修养和艺术修养以及思想高度在当时不是最好的,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也不是优秀的,所以这种白话语言虽然有它的优越性以及存在的理由,但总体上是粗糙的,即傅斯年所说的“粗率”(24)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这种白话语言不论是从思想表达上还是从外在形式与构成上看都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的语言水平,其词语的完整性和风雅都不能和文言文相提并论,更不要说取而代之了,所以它也不能作为国语。
从语言的品质和思想的表达等方面来说,清末民初的白话文和五四白话文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五四白话文是一批最优秀的作家创作出来的,这些作家不仅是当时最好的作家,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也是优秀的作家,这些作家大都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回来,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又精通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他们代表了当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顺应了世界和中国的潮流与方向。他们所使用的白话形式上是中国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的白话,但在思想的层面上,它是一种新的语言,它在内容表达上不仅大量吸收文言词语,而且大量吸收和使用西方的词语,特别是思想文化术语、概念和范畴。当然这些词语都是以翻译即汉语的形态存在,是经过了由中国文化语境过滤性的选择、改造并附加和融进新内容的词语,它们已经不是纯西方词语而是中国现代语词,这样,五四白话即后来的国语也即再后来的现代汉语就是一种新的语言体系,不同于文言文、古代白话、现代口语白话、西方语言但又包容文言文、古代白话、现代口语白话、西方语言并且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当时把这种白话称作“欧化”的白话,“欧化”主要是现代化,不是贬义词而是褒义词,但“欧化”只是一方面,还有其他特征。这种语言更具有现代性、开放性、大众性,更易于为普通民众所接受并使用,再加上经过大作家们的雅化、精致化、诗性化进而标准化、书面化,所以,它很快就取代文言文而上升到国语的地位和高度。
五四白话文即国语是对各种语言的吸收、改造、融合,集各种语言之精华创新而成,包括口语白话书面化、文言词语现代化、西方词语中国化,当然还包括把中国的文言文、口语白话西方化即“欧化”等。傅斯年在《怎样做白话文》一文中提出“国语欧化”的主张并设计具体措施:“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 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25)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32页。胡适转述时表达更准确:“欧化的白话文就是充分吸收西洋语言的细密的结构,使我们的文字能够传达复杂的思想、曲折的理论。”(26)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0页。五四白话与古代白话以及作为民间口语的白话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更是思想内涵上的。胡适虽然强调“历史进化的文学观”,“用历史的文学观来做打倒古文文学的武器”(27)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文集》(第1卷),第126页。,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学的白话传统来论证五四白话的合法性,但他实际上也认识到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他说:“旧小说的白话实在太简单了,在实际应用上,大家早已感觉有改变的必要了。初期的白话作家,有些是受过西洋语言文字的训练的,他们的作风早已带有不少的‘欧化’成分。虽然欧化的程度有多少的不同,技术也有巧拙的不同,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出,凡具有充分吸收西洋文学的法度的技巧的作家,他们的成绩往往特别好,他们的作风往往特别可爱。所以欧化白话文的趋势可以说是在白话文学的初期已开始了。”(28)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文集》(第1卷),第131页。过去,我们对“欧化”的解释主要是强调语法,但实际上,“欧化”的实质是思想上的,主要是词语上的,大量西方术语、概念和范畴输入中国进入汉语,汉语增加了大量的新词,实质性地改变了汉语的构成,汉语在表达上大大拓展了,这才是“欧化”的实质,“欧化”白话是五四白话即国语与传统白话以及作为民间口语的白话的本质区别。
1922年,周作人写了长文《国语改造的意见》,对五四白话的性质以及未来国语建设的方向作了精辟的论述。周作人认为,国语不是简单的白话,它的构成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方言、欧化词语、古语等,它是对白话的“改造”,并且这种改造就是国语建设的方向和途径,“现在中国需要一种国语,尽他能力的范围内,容纳古今中外的分子,成为言词充足、语法精密的言文,可以应现代的实用”(29)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9页。。“现代民间的言语当然是国语的基本,但也不能就此满足,必须更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现在的白话文诚然是不能满足,但其缺点乃是在于还未完善,还欠高深复杂,而并非过于高深复杂。我们对于国语的希望,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的使他化为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与思想,作艺术学问的工具,一方面再依这个标准去教,使最大多数的国民能够理解及运用这国语,作他们各自相当的事业。”(30)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754-755页。这里,周作人强调五四白话即国语在来源上的“古今中外”性,强调国语建设的“改造”性,强调国语在表达高深思想以及精微情感的“精密”性,这是他对五四白话认识的深刻之处。周作人认为当时口语的白话不能直接作为国语,“我们决不看轻民间的言语,以为粗俗,但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这是无可讳言的”(31)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755页。,“久被蔑视的俗语,未经文艺上的运用,便缺乏细腻的表现力……以致变成那个幼稚的文体,而且将意思也连累了”(32)周作人:《〈江阴船歌〉序》,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172页。。强调国语的雅致、丰富和复杂,并且这种雅致、丰富和复杂是通过文学创作实践来实现的,这同样是非常深刻的思想,超出当时大多数文学家、语言学家的见识。建设国语,充分利用和吸收民间口语,这是绝对必要的,但另一方面,这些语言因为粗俗、词语贫乏和表达简单,需要改造和丰富。
同样,胡适也明确说过清末白话小说中的白话不能直接作为国语,“明清小说里原有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又是国语运动以前的国语著作,特别觉得有价值,然而他们毕竟只是我们所需要的国语的资料,不能作为标准”(33)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754页。。其原因同样是因为这些白话过于粗糙,不能表现现代思想,需要改造和丰富。正是在思想上,白话在改造的同时需要大量借鉴、引进西方词语和借用文言文的词语,需要欧化和雅化,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的理由,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并废除文言文主体地位的理由,“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为他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与理解力都不发达,但别一方面,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34)周作人:《思想革命》,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132页。。吸收文言文在思想表达上的有益成分和废除文言文作为国语,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语言革命也是思想革命。
如何改造传统白话即古白话?如何改造作为民间口语的白话?如何把西方语言的词语和文言文中有益的词语融进白话?途径很多,但新文学创作无疑是最好的方式,“文学的国语”是最符合周作人所说的精微的包容古今中外的能够表达复杂和深刻且现代思想的语言,“从文学家方面,独立的开拓,使国语因文艺的运用而渐臻完善,足供语法字典的资料,且因此而国语的价值与势力也始能增重”(35)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第758页。。纵观五四那一代文学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除了大多有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经历从而接受了西方语言、日语以及相信现代思想以外,他们的古文、古代文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也非常好,他们具有创立国语的优越条件。胡适认为,国语的成立需要两个重要条件:“第一须流行最广,第二已产生了有价值的文学。”(36)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见《胡适文集》(第1卷),第132页。这是精要的概括。事实上,国语也正是在文学的层面上才得以建立起来的,或者说,国语正是在成功的新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国语本质上是文学的国语。
三、其他语言变革为什么没有导致“国语”转型?
中国一百多年来,不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汉语变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外,其他变革都没有导致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转型”,为什么?根本原因还是与文学有关。
汉语求变以及事实上的变革并不是在五四时才开始的,清末随着外来事物及思想文化的输入导致社会本身的巨大发展变化,产生了很多新事物、新思想,传统的文言文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特别是教育普及和文化“下移”之后,文言文的局限和缺点越来越明显。清末有识之士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有人主张白话和文言文并行,知识分子用文言,普通民众用白话;有人主张把白话和文言融合起来,建立一种半文半白的语言;有人主张改革汉字或者废除汉字,用“简字”或用拼音文字,语言上用各地方言也即民间口语。实践上也进行了各种尝试,尤其白话文尝试,产生了各种白话报、白话期刊、白话书籍,有白话新闻、白话文学、白话文章,形成了一个非常广泛的“白话文运动”,但晚清并没有建立起新的国语,当时的“国语”还是文言文,白话只是文言文的辅助性语言。马西尼说:“在各种文学白话中,没有一种白话可以直接拿来当作正式语言,因为它们仍然没有全社会所必须的词语。”(37)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141页。不仅是各种文学白话不能直接拿来当作正式语言,各种新闻白话、文章白话等都不能直接拿来当作正式语言,主要原因同样是因为这些白话词语欠缺,表达不足,当然形式上的粗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晚清各种白话文缺乏对白话的充分改造,也缺乏对西方语言和古文的吸纳,直接表现就是缺乏成功的文学作品,也即没有成功的文学语言,因而没有语言典范。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建立了新文学,产生了大量的堪称典范的文学作品,在文学语言的基础上也建立了新的国语,并且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相互成就。
五四之后,国语还在发展,语言学界以及政府机构、各种组织都为国语的完善与规范做了很多工作,比如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193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写入宪法。这些于“国语”建设来说当然也很重要,但它们都不能和五四新文学的贡献相提并论。笔者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成功了,新文学的经典文本产生了,新文学的正宗地位确定了,国语也就基本确定了,语言学界和国家机构主要是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细节化、规范化,还有学术研究等,对国语建构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五四之后,文学界、文化界以及语言学界和其他学术界对于五四所建立起来的“国语”有一些否定和批评的意见,对于如何改进五四白话,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瞿秋白把白话区分为“旧式白话”和“新式白话”(38)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54页。,所谓“旧式白话”即古白话,“新式白话”即近代以来的白话包括五四白话,瞿秋白把五四白话称作“五四式白话”(39)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65页。,说它是“不人不鬼的话”(40)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54页。,“半人话半鬼话”,是“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腔”(41)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38页。,因为欧化和吸收文言文,所以是“‘非驴非马的’一种言语”(42)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47页。,或者“非驴非马的‘骡子话’”(43)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7页。,是“新式文言”(44)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62页。。从文学上来说,这种语言需要继续“革命”,瞿秋白称之为“俗话文学革命运动”(45)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6页。,“革命的对象是新式文言的假白话和旧小说的死白话”(46)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境》,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8页。,从而建立一种“普洛大众文艺”,语言上则是“现代的中国普通话”(47)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8页。,“读出来可以听得的话”(48)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9页。,也就是大众语,即所谓“真正的中国白话文”(49)瞿秋白:《欧化文艺》,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94页。。与瞿秋白一样主张“大众语文”的人很多,包括胡愈之、陈子展、陈望道、王任叔等,比如有人说:“五四下来的白话文,只是为了上层的资产阶级与一般智识阶级的所有物,而且它那么一下子就停下来,甚至早就回向‘妥协’与‘投降’的路上,而造成了一种全不能为一般的大众所能懂的,充满了欧化气与八股气的‘买办文字’。”(50)转引自文逸编:《语文论战的现阶段》,香港:天马书店,1934年,第69页。所以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大众语文运动(51)可参见宣浩平编:《大众语文论战》(包括《大众语文论战续二》),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丁易编:《大众文艺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51年。,但这次运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语的性质、方式和构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语范本还是五四新文学,大众语文运动并没有产生成功的不同于五四的新文学,也没有产生被普遍认同的可以取代五四白话的大众语。五四新文学的地位不变,国语的地位就不可能变,这就胡适所说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真正含义。
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学的语言有一些变化,特别是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和五四新文学经典作家相比,明显“通俗化”、“大众化”,但笔者认为,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只是风格上的创新,它是五四白话在风格上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一种表现,并没有偏离五四白话的本质,不论是从形式上还是思想表达上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延安文学除了赵树理以外,还有丁玲、孙犁、艾青等人,他们的文学是正宗的五四文学,其语言也是正宗的五四白话。所以,延安文学虽然走“工农兵方向”,更强调文学的“普及”,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其语言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没有超出五四白话的范围或范畴。赵树理虽然被称为“农民作家”,但他的语言却是非常标准的知识分子的语言,而非“大众语”,更非“农民语言”,与鲁迅、茅盾、沈从文这些作家相比,他的小说通俗易懂,利用了很多传统小说的形式以及民间文学的形式,但语言上仍是非常规范的五四白话。赵树理并没有改变五四白话,只是丰富了五四白话,激发了五四白话在吸收民间语言从而增强国语表现力方面的潜力,把五四白话在通俗性方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赵树理小说本质上是五四新文学的产物,是新文学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的演化衍生,是五四新文学的新经典,不出五四新文学的范畴。
中国文学进入“当代”之后仍然是遵循或沿着五四新文学向前发展,虽然文学内容有巨大的变化,政治上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但在文学类型上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却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新文学”,所以也被合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它们具有一体性,差异在于内容上的时代性以及文学自身的合理发展,而不是文学类型的不同。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语言上严格地以五四新文学经典作为范本,即使六七十年代也是这样,这一时期的文学虽然大多数思想层次很低、形式和艺术技巧粗糙,但这不是“方向”和文学观念问题,而是水平问题,是文学内容上出了问题,文学的外部制约条件出了问题,文学类型和语言规范并没有出问题。六七十年代的文学虽然内容上不堪卒读,但稍微严肃一点的作品其语言大都文从字顺,不偏离五四白话文。当时规范的汉语是毛泽东著作的语言,而毛泽东的语言则是标准的五四白话,毛泽东的散文是典范的现代文。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优秀的文学一直制约并规范国语(现代汉语)的发展,只要是以典范的现代文学语言作为国语(现代汉语)的标准,只要文学在语言上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汉民族共同语言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文学对于语言的价值,由此也可见胡适所提出的“文学的国语”的伟大意义。
今天,现代汉语作为国语却不断脱离文学规范,混乱、低俗、粗鄙、歧义丛生的现象随处可见,于语言、于文学、于思想文化都带来负面影响。如何解决语言的粗陋化等问题?笔者觉得五四时期“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的双向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以优秀的文学作品为标准,通过文学语言提高现代汉语的品质,这是语言建设非常重要的原则和途径。当代文学需要自觉地遵守现代汉语的语言规则,自觉地维护“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的标准,这既有利于当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利于汉语的完善、规范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