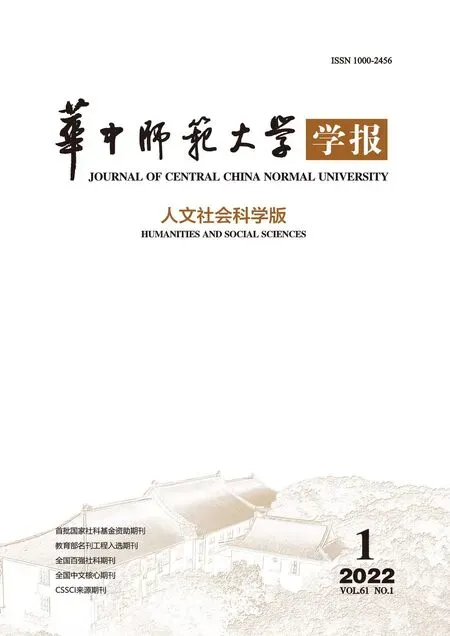日本“修宪”思潮的历史演变
孙宝坤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和平宪法”即《日本国宪法》的颁行,意味着战前天皇制国体和军国主义上层建筑在国家根本大法层面被彻底否定,不但为战后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并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制度基础,而且为维护亚太地区安宁提供了政治保障。然而,自和平宪法问世以来,尤其是进入世纪之交,日本保守势力对这部给日本和亚太地区带来和平发展“红利”的宪法不但不去维护,反而一直在处心积虑予以修改乃至废除;而一旦其“修宪”图谋随着日本政治和社会右倾化加剧以及日美捆绑日紧而得逞,那么挣脱和平宪法束缚的日本将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迅速向战前回归,故为日本国内外热爱和平的人们所关注和警惕。迄今为止,关于日本国内“修宪”思潮的“个案”研究已有学者涉猎(1)如赵阶琦:《评当前日本改宪运动》,《和平与发展》2000年第4期;金一南:《3场战争 3次突破——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环球军事》2003年第8期;包霞琴:《90年代后日本修宪论及其特点分析》,《日本研究》2004年第2期;高岚:《从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看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中华魂》2005年第11期;姚来燕:《论日本宪法第9条》,《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陈卓武:《战后日本修宪的态势及其背后的美国因素》,《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6期;何晓松:《试析安倍的国家战略——修改和平宪法为中心》,《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2期;田香兰:《战后日本宪法斗争的思考》,《日本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卓南生:《安倍修宪:势在必得?》,《世界知识》2013年第17期;渡边三洋:《日本国宪法的精神》,魏晓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等等。不难看出,以往相关成果均系微观、零散或“个案”探讨,尚无关于战后70多年来日本保守势力“修宪”思潮的宏观、长时段或整体性研究成果问世,因此也就难以清晰掌握其来龙去脉、正确预测其未来走势和准确评估其政治危害。,但有关这一思潮的长时段和整体性探讨尚无人问津。因此,就战后70多年来日本“修宪”思潮的演变轨迹进行纵向梳理并就其驱动因素予以横向剖析,不仅对弥补该课题宏观研究之不足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且对预判日本未来政治走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战后初期:日本“修宪”思潮的缘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美国随即对其实行单独占领和管制。为确保日本今后不再对世界尤其是美国构成威胁,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推行了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改造政策,旨在将日本由实质天皇制国家改造成为象征天皇制国家、由封建军事色彩浓厚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改造成为具有鲜明现代民主色彩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国家。而这一宗旨能否实现,将取决于美国占领当局能否敦促或帮助日本政府颁布一部新宪法,以取代战前将日本引上侵略战争不归路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占领当局将日本新宪法的拟制工作提上议事日程。
1945年10月4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告知时任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希望日本政府对“明治宪法”进行修改,并强调要将自由、民主、和平元素融入新宪法。身为前陆军大将和皇族并接受了裕仁天皇“维护国体”训示的东久迩宫,对美国占领当局的这一要求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次日便以内阁总辞职的方式表达了对美方的不合作态度。但修改宪法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既能有效维护国体,又不因激怒麦克阿瑟而蒙受损害,新诞生的币原内阁在10月13日紧急成立了以国务大臣松本丞治为首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展现出有别于前内阁的合作态度。12月8日,松本制定的“宪法修改四原则”(即“松本四原则”)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其主要内容是:天皇总揽统治权的大原则不变;扩大议会权限,缩小天皇大权;国务大臣对议会负责;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对受到侵害的民众予以救济。1946年1月,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遂依据“松本四原则”拟制出新宪法草案(即“松本草案”),并于2月呈给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盟总”)。如果说“松本四原则”完全贯彻了裕仁天皇“维护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体”之训示,那么“松本草案”几乎就是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翻版,因为除了用“自由”“民主”等漂亮词句装点门面外,仅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修改为“最高不可侵犯”、将“天皇统帅陆海军”修改为“天皇统帅军队”等。“松本草案”让美国占领当局看清了日本保守势力阳奉阴违的嘴脸和阴谋原封不动保留天皇制的险恶用心。麦克阿瑟愤怒之余,决定撇开日本政府而由美国占领当局代为制定新宪法。奉命行事的“盟总”民政局长惠特尼组织几名美国宪法专家,很快就拟制出一份真正贯彻“主权在民”原则和充分体现“和平主义”精神、忠实反映美国战略意图的新宪法草案(即“麦克阿瑟草案”),并施压日本当局以此为蓝本尽快制定和颁布新宪法。3月6日,币原内阁向日本国民公布了以“麦克阿瑟草案”为蓝本制定的《宪法修改草案纲要》,以征询各方面意见并继续加以完善。6月20日,《宪法修改草案纲要》被提交给第90届帝国议会审议。10月7日,经众议院和贵族院历时近四个月的反复审议和修改,终于以超过三分之二议员赞成获得通过,并正式更名为《日本国宪法》(即“昭和宪法”)。这部由美国占领当局主导制定的新宪法,最后于1946年11月3日颁布,翌年5月3日生效。
这部新宪法之所以被称为“和平宪法”,不仅仅因为其载明“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第一条)而将天皇从“神”变回了人,也不仅仅因为其载明“主权属于国民”(序言)(2)参见赫赤等:《日本政治概况》(附录《日本国宪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90页。而忠实贯彻了麦克阿瑟的“主权在民”原则(3)参见保阪正康:《昭和时代见证录》,冯玮等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338页。,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第二章第九条彻底贯彻了“和平主义”精神,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4)赫赤等:《日本政治概况》(附录《日本国宪法》),第391页。这才是这部新宪法最大的亮点和价值所在。换言之,和平宪法作为人类历史上首部自动放弃国家交战权、自我否定拥有军队、将日本拉回到和平民主正确轨道上来的一部国家根本大法,其重大理论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难怪麦克阿瑟将和平宪法视为“占领(期间)惟一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成果”(5)島津一夫:《マッカーサー回想記》(上巻),東京:朝日新聞社,1964年,第163頁。,也难怪日本学者坂本义和评价说日本由此“迎来了第二次开国”(6)坂本義和、R·E·ウォード編:《日本占領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第3頁。;而和平宪法颁布之初日本国内有85%的人对象征天皇制表示赞成,有70%的人对放弃战争条款表示支持(7)参见樋口陽一、大須賀明:《日本国憲法資料集》,東京:三省堂,1988年,第10頁。,也就更是顺理成章了。然而,由于和平宪法是由美国占领当局主导制定并施压日本政府颁布的,加之“芦田修正”又潜伏下对和平宪法第九条解释上的歧义即埋下了争议的种子,这就为日本保守势力日后掀起一波又一波“修宪”恶浪提供了口实。
所谓“芦田修正”,是指1946年10月7日日本帝国议会在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纲要》之前,时任“帝国宪法改正案小委员会”委员长芦田均对该“草案纲要”第九条所做之修正,即在“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之前,塞进了“为达到前项目的”之字样。仅此寥寥数字之补充,就使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之承诺有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日本是为了“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才承诺“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二是,只要日本不主动发动战争,就可以保有武装力量和国家交战权。芦田本人曾在“宪法调查会”会议上解释说:“修改之后的条款意味着我们仅仅不能拥有进行侵略战争的武力,从而为自卫队另当别论留下了解释的余地。”(8)魏晓阳:《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宪政的百年历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芦田修正”不但为战后日本保守势力“修宪”浊浪的掀起尤其是“解释修宪”的启动制造了借口,而且为日本政府建立从警察预备队到自卫队的武装力量提供了法律依据。可见,早在日本战败之初即新宪法颁布前后,即已埋下保守势力“修宪”与革新势力护宪之争的引线。此乃日本“修宪”思潮之滥觞。
二、冷战前期:日本“修宪”思潮的发轫
冷战前期(1948—1960),日本政坛从吉田茂内阁到岸信介内阁历时12年。一方面,和平宪法的颁行既是确保此间日本社会稳定和经济迅速恢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是推动未来日本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繁荣以及与邻国共享和平发展“红利”的政治保障,可谓美国占领当局送给战败国日本最大的“礼物”;另一方面,随着美苏冷战开启并愈演愈烈,美国很快将对日政策由最初的“惩罚”改为“扶植”,导致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出现颠覆性逆转。诸如,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恢复其公职(如鸠山一郎),提前释放战犯使其得以重返政坛、军界掌控国家大权(如岸信介)等。这些人不但成为冷战前期日本保守势力的核心,而且充当了日本“修宪”思潮的始作俑者。
冷战伊始即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自由党、民主党、绿风会中的保守派议员就组成了“自由宪法期成议员联盟”,首先发出“修宪”杂音(9)参见肖季文等:《日本: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页。。由于战败初期和平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共产党和社会党等革新势力迅速壮大,故尚处于蛰伏与整合中的日本保守势力的最初“修宪”主张和活动,未能在日本政坛和社会上引起太大反响。
1954年12月,被解除“整肃”的战时高官、时任民主党总裁的鸠山一郎上台组阁。鸠山出任首相后公开宣称,“修改宪法是需要的。纠正(美国)占领政策首先要从修改宪法做起,特别要修改宪法第九条”;“保留现行宪法会延迟日本重建。因此,要为(‘修宪’)这一大目标作出努力”(10)参见赵阶琦:《评当前日本改宪运动》,《和平与发展》2000年第4期。;“修改宪法的重点是第九条”,为了自卫可以保持军队(11)参见姜孝若、宋绍英:《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大事纪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5页。。鸠山还将“修宪”写进1955年2月和1956年7月众参两院议员竞选纲领。凡此表明,鸠山内阁已将“修宪”纳入政府议事日程并开始营造“修宪”氛围。1955年,鸠山斡旋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后,不但直接将“修宪”写进党纲,而且因自民党在国会中拥有绝对多数席位而为 “修宪”创造了便利的政治条件;同年,鸠山内阁和自民党又操控国会通过了《宪法调查会法令》,进一步为修改和平宪法提供了法理条件。这位因战时出任过文部大臣等高官并出版过吹捧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世界之面貌》一书而被美国占领当局开除公职的鸠山一郎,是战后首位抛出修改宪法主张即打开“修宪”潘多拉魔盒的日本首相。
1957年2月,岸信介接替因病辞职的石桥湛山上台组阁。这位集“满洲之妖”(曾是伪满洲国五大头目之一)与“昭和之妖”(曾出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大臣)绰号于一身的甲级战犯嫌疑人,一经重操权柄便将“修宪”列入政府议事日程。其实早在被提前释放、恢复公职之初,岸信介就创立了以“亲美”“反共”“修宪”为纲领的“日本再建同盟”。其组阁后,不但主张彻底摒弃“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而且力主修改和平宪法和《日美安保条约》;不但声称日本拥有自卫性武装力量不违反宪法,而且叫嚣为自卫而拥有核武器也是允许的;不但推出大幅提升军力的《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试图架空和平宪法第九条,而且立即成立“宪法调查会”将《宪法调查会法令》付诸实施。尤需指出的是,岸信介操控的“宪法调查会”发表的《宪法调查会报告书》提出,现行宪法是在盟军占领的情况下颁布的,随着占领结束应就宪法是否需要修改展开调查,实际在为“修宪”寻找突破口。正是在战后右翼总头目岸信介担任首相期间,日本保守势力不但通过强行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实现了“亲美”目标,通过百般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达成了“反共”目的,而且通过舆论鼓噪和政策推动在日本朝野掀起了第一次“修宪”恶浪。
冷战前期“修宪”浊浪的出现,主要缘于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国内右翼保守势力的推动。随着冷战过早到来和两大阵营矛盾激化,日本政府在美国占领当局的默许下,提前释放了在押战犯和解除了对战时军职人员的“整肃”。这些重返政坛、军界当上首相或大臣的军国遗臣,遂成为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中坚”,也就自然成了“修宪”逆流的急先锋。正是在此背景下,两种“修宪”论调随之产生:一种是“宪法强加论”即“修宪论”,认为和平宪法并非日本政府和国民自主制定的,而是美国“为了削弱日本”“按自己的意愿强加”的,因此必须加以修改;另一种是“宪法无效论”即“废宪论”,认为和平宪法将天皇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贬低了整个日本民族”,而放弃战争权利又损害了日本国家的“基本主权”,所以必须予以废除(12)参见刘杰:《战后日本“修宪”思潮论》,《外国问题研究》1995年第1期。。然而,无论“修宪”还是“废宪”都是对和平宪法开刀,都是旨在将日本拉回到战前军国主义老路上去。其次,是国际冷战格局的影响。和平宪法颁行时美苏对立尚不尖锐,随着冷战开启,尤其是中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美国的远东政策遭遇失败。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崛起,美国很快将自己的东亚政策由“扶蒋反共”改为“扶日反华”,着手将日本打造成为远东地区反苏、反华、反共的“桥头堡”或“防波堤”。加之美国的对日占领随着《旧金山和约》签订宣告结束,美国当局不但敦促日本重新武装、重整军备,而且对日本国内的“修宪”言行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不难看出,上述国内外因素均与当初主导制定和平宪法的美国当局密不可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
三、冷战后期:日本“修宪”思潮的蔓延
冷战后期(1960—1991),日本政坛从池田勇人内阁到海部俊树内阁历时31年。此间,日本保守势力的“修宪”主张和活动主要集中在池田勇人和中曾根康弘主政期间,尤其是在“鹰派”政治强人中曾根出任首相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保守势力掀起了第二次“修宪”浊浪。
池田内阁时期(1960—1964),“修宪”派的领军人物仍然是岸信介。尽管其首相生涯在1960年7月戛然而止,但并未因为卸任或年事已高而停止“修宪”活动,可以说此间的“修宪”主张和活动均直接或间接同岸信介有关。岸信介在首相任上时下令成立的“宪法调查会”,此时继续对“修宪”活动施加思想影响和进行组织领导。1963年9月,岸信介授意“宪法调查会”抛出《修改宪法的方向》报告书,明确主张废除和平宪法第九条、实行征兵制。1965年1月,“宪法调查会”又秉承岸信介旨意制订了《宪法修改纲要》,试图将“修宪”活动合法化和“修宪”舆论扩大化。与冷战前期的“宪法强加论”“宪法无效论”等论调有所不同,这时的“修宪”主张以“社会变迁论”为主调。岸信介声称:“日本废除宪法第九条条款的时代已经到来了。自日本从美国那里接受了现行宪法以来,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3)富森睿儿:《战后日本保守党史》,吴晓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21页。这一论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国内颇有市场和影响力,助长了日本保守势力的“修宪”气焰。
时至中曾根内阁时期(1982—1987),日本“修宪”思潮进入了新老结合、朝野呼应的新阶段。一方面,以岸信介为代表的传统保守势力在经过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间的暂时蛰伏后重新抬头和蠢动,欲乘中曾根内阁推行右倾化政策之机再掀“修宪”浊浪;另一方面,作为日本新保守势力的核心人物,中曾根欲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谋做政治和军事大国。此间,尽管日本新老保守势力的“修宪”主张有所不同,但均以重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三位一体的所谓“正常国家”为目标。换言之,由于和平宪法被日本新老保守势力一致视为达成上述政治诉求的最大障碍,所以必欲铲除而后快。这样,日本新老保守势力相互策应掀起第二次“修宪”浊浪也就“顺理成章”了。
首先,第二次“修宪”浊浪的始作俑者是岸信介主导的“宪法调查会”。1981年10月,沉寂十余年的“宪法调查会”再度开会部署“修宪”事宜,并于翌年8月提出删除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不保持战力和否认交战权”之规定(14)参见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75页。。同年10月、12月,调查会先后发表了《第一次宪法改正草案》《第一次宪法改正草案追加案》两个“修宪”方案,为修改宪法大造舆论。
其次,掀起第二次“修宪”浊浪的主角是日本新保守主义“奠基人”中曾根康弘。出任首相前,作为“促进修改宪法的头号热心人”(15)岩见隆夫等:《新总理中曾根康弘》,伍兴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25页。,中曾根不但指责和平宪法是“麦克阿瑟宪法”“强制宪法”(16)斎藤栄三郎:《宰相:中曽根康弘の思想と行動》,東京:上野印刷所,1983年,第128 頁。,而且在防卫厅长官任上时对力主“修宪”的三岛由纪夫的自杀行为表示赞赏,为他所领导的右翼团体“盾会”的暴力倾向进行辩护。担任首相期间,中曾根不但通过抛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1982年)、首开首相八一五“公职”参拜靖国神社恶例(1985年)、制造第二次历史教科书风波(1986年)、突破防卫费不超过GNP 1%限额(1987年)等一系列实际行动冲击和架空和平宪法,而且对“修宪”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一面宣称修改宪法“是本人的一贯理念”(17)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一面又表示出任总理之前和之后立场会有所“不同”(18)斎藤栄三郎:《宰相:中曽根康弘の思想と行動》,第199頁。,言外之意任内暂不“修宪”并非本意(19)参见孙岩帝:《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卸任首相后,再无顾忌的中曾根康弘不但老调重弹“强加论”(20)中曽根康弘:《新しい保守の理論》,東京:講談社,1978年,第251頁。“缺陷论”(21)中曽根康弘:《新しい保守の理論》,第21頁。,而且一再强调日本拥有武力“并不违背宪法第九条之规定”(22)中曽根康弘:《新しい保守の理論》,第246頁。。要而言之,中曾根“修宪”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解释修改”架空和平宪法,使其有名无实,不再成为走向“正常国家”的羁绊。这一“解释修宪”虽然看上去比“全面修改”略显温和,但更具隐蔽性和可操作性,为保守势力的“修宪”思潮和活动指明了方向。
20世纪80年代中叶即中曾根内阁期间出现第二次“修宪”浊浪,同样是由国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的。就国内因素而言,日本在和平宪法庇护下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以至一度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实力增强,日本国内狭隘民族主义重新膨胀,“大和民族优秀论”沉渣泛起,加之中曾根康弘启动了日本政治右倾化进程,这就为日本新老保守势力联手掀起第二次“修宪”浊浪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从国际形势来看,随着冷战格局从“美攻苏守”向“美苏均势”、再向“苏攻美守”态势发展,里根总统一改以往对苏软弱姿态,决定推行对苏强硬政策。为此,美国一面增强自身军事力量,一面要求盟国配合自己的全球战略行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作为美国远东地区最重要的盟国和苏联东方边境线上的主要邻国,由于处于美苏对峙的最“前沿”而越发重要起来。为了获得日本的战略配合与军事支持,美国当局甚至表示可以满足日本保守势力的“修宪”诉求。例如,不但驻日美军司令向媒体表示日本也许需要修改宪法和法律,而且里根总统公开宣称:“虽然日本在军事上受到宪法限制,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看到日本在军事上变得强大。”(23)肖伟:《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可见,日本国内第二次“修宪”浊浪的掀起,与美国政府采取默认乃至纵容的现实主义态度密不可分。
四、后冷战前期:日本“修宪”思潮的泛滥
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步入后冷战时代。后冷战前期(1992—2006),日本政坛从宫泽喜一内阁到小泉纯一郎内阁历时14年。此间,日本保守势力掀起了第三次“修宪”浊浪。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日本保守势力已从“明文修宪”“解释修宪”转向“事实修宪”,即试图通过外围立法架空和平宪法,进而达到“曲线修宪”之目的。此乃世纪之交日本保守势力“修宪”的主要路数和突出特征,为日后安倍内阁加快“修宪”步伐奠定了基础。
宫泽内阁是后冷战前期第三次“修宪”浊浪的始作俑者。1992年初,宫泽政府大肆制造海外派兵“合法”舆论,竭力贩卖“集体安全保障”概念,百般狡辩“集体安全保障”包括海外派兵。诸如,宫泽内阁将“修宪”写入《外交姿态报告》,明确列为20世纪90年代日本三大政治任务之一;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发表演讲说,如果现行宪法成为日本海外派兵的障碍,那就光明正大地讨论和修改;自民党政调会会长三冢博宣称,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的前提是修改现行宪法第九条(24)参见余金成:《冷战后两制关系演变及发达国家共产党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等。到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日本国内的第三次“修宪”浊浪进一步升级。1996年,自民党“自主宪法制定国民会议”推出所谓“平成新宪法”,迅速扩大了“修宪”派的社会基础。1997年,自民党等保守政党成立“国会议员推进宪法调查同盟”,旨在敦促国会加快“修宪”进程。同年9月,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签订,为保守势力“修宪”提供了新的口实和依据。1998年,民主党也成立了“宪法调查委员会”,使“修宪”势力进一步壮大。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国会法修正案》,决定成立国会宪法咨询机构“宪法调查会”。至于桥本龙太郎本人,早在出任首相前就宣称,“如果宪法连包括自卫队人员做贡献都不允许,那我看还是修改宪法好”(25)《橋本龍太郎が〈普通の国〉の確立を目指す》,《現代週刊》1995年第1號。;担任首相期间,则极力为“修宪”提供宽松的政治环境。不过,后冷战前期最具代表性的“修宪”政治人物要数小泽一郎。
小泽一郎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旗手,因此其“修宪”主张主要反映了日本新保守势力的政治诉求。早在海湾战争期间,时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就主张对和平宪法进行“解释修改”,认为现行宪法所标榜的和平主义是死守“一国和平”的和平主义。小泽基于日本欲做“国际贡献”就必须先成为“国际国家”、欲成为“国际国家”就必须先恢复成“普通国家”、欲成为“普通国家”就必须先修改现行宪法这一错误认知逻辑(26)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東京:講談社,1993年,第104頁。,提出通过在和平宪法第九条中增加不妨碍自卫队“维和”之“第三款”、在和平宪法之外另订一部“和平安全保障基本法”,以此消除邻国对日本充实军力的“误解”和解除和平宪法对日本“普通国家”化的束缚(27)参见孙岩帝:《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1999年9月,小泽又撰文提出日本应该拥有自卫权,应当在和平宪法第九条后增加日本保有自卫权和自卫力量之条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小泽不仅嘴上说而且实际做。1990年出任自民党竹下派代理会长后,如日中天的小泽竟迫使三位总裁(即首相)候选人在“派兵法案”问题上做出“同意”的承诺。在小泽一郎的政治运作下,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周边事态法》(1999年)、《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修正案)》(2001年)、《反恐怖特别措施法》(2001年)等,实现了海外派兵范围扩大、自卫队武器携带和使用标准放宽等多个“突破”。可见,小泽一郎不但“修宪”主张极具诱惑力和可操作性,而且通过推动“普通国家”化相关法案的出台,基本达到了“事实修宪”之目的和为最后“明文修宪”创造条件之政治意图。
如果说与“首相”高位擦肩而过的小泽一郎主要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理论旗手,那么手握“总裁”“首相”权柄的小泉纯一郎则是日本新保守势力即“修宪”派的行动领袖。2001年就任首相伊始,小泉就表明了“修宪强军”意愿,宣称:现行宪法禁止维持军力和使用武力,“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必须结束”(28)参见余金成:《冷战后两制关系演变及发达国家共产党研究》,第115页。。尤需指出的是,小泉纯一郞及其内阁在2003年对内对外采取的两大行动,可谓将第三次“修宪”浊浪推向高潮。如果说小泉内阁于年底悍然批准海外派兵计划并迅速付诸实施之行动,在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突破了和平宪法的约束,那么日本国会在小泉的运作下于同年6月一揽子通过的“有事三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修正案》《应对武力攻击事态法案》,则使和平宪法几近名存实亡(29)参见孙岩帝:《小泽一郎的新保守主义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至此,日本保守势力在“事实修宪”即通过外围立法架空和平宪法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换言之,上述背离和平宪法精神的一系列法案的出台,阶段性地实现了日本保守势力的“修宪”目标。对此,日本宪法学者水岛朝穗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事’二字的定义既暧昧又难缠。它可解释为三:一是‘已经发生了被攻击的事态’,二是‘预测可能受到攻击的事态’,三是‘预测之后果真被攻击的事态’。……这种多重定义的‘有事’可将无事都变成‘有事’。”(30)金一南:《3场战争 3次突破——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环球军事》2003年第16期。
日本保守势力此间掀起第三次“修宪”浊浪,主要缘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政治右倾化是战后日本政治演变的总趋势和鲜明特征,进入世纪之交,这一演进趋势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而明显加快,从而为“修宪”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具体反映在:(1)日本政治右倾化终结了“保革对立”的“五五年体制”,使日本多数政党在分化组合中日趋保守化,为保守势力“修宪”提供了组织保障。(2)日本政治右倾化推动了新闻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右转,为保守势力“修宪”营造了舆论氛围和提供了理论支撑。诸如,媒体中不但《读卖新闻》先后在1992年成立“宪法调查委员会”、在1994年抛出包括降低“修宪”门槛内容的“修宪”方案(31)参见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第179页。,就连原本属于护宪阵营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也纷纷转而赞成“修宪”;文化教育界中,不但中西辉政等右翼人士的“修宪”论调甚嚣尘上,就连“中道”学者、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北冈伸一亦撰文称:“宪法中的许多条款不切实际,应修改或删除第九条的后半部分。”(32)北岡伸一:《憲法九条の呪縛から抜け出すとき》,《This is読売》1999年第12號。(3)日本政治右倾化诱导了日本国民意识的保守化,为保守势力“修宪”提供了社会土壤。《读卖新闻》的一份问卷调查显示,此间赞成与反对“修宪”的日本国民各占44%(33)読売新聞社編:《憲法改正:読売試案2004年》,読売新聞社、中央公論新社,2004年,第281頁。,仅此足以反映这一点。
其次,是来自美国的纵容。在日本保守势力看来,美国要求日本自卫队参加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2001年爆发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为日本“修宪”即摆脱和平宪法束缚提供了天赐良机;而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对日本高官所说“日本宪法第九条已经成为美日联盟进一步加强的羁绊”(34)Steven C. Clemons, “The Armitage Report: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Japa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ccasional Paper, No.20, Feb. 2001, p.23.,美国驻日大使贝克对日本当局所说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研究“不得不根据需要……对宪法第九条做出修改”(35)参见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第34页。等,则是对日本“修宪”诉求的直接鼓励和最大支持。
再次,是来自德国和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1990年11月11日,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德国国会将尽快着手修改基本法(宪法)的工作,以便德国可能为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作出军事贡献……我认为日本也能作出贡献。”(36)《魏茨泽克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披露:德将修改宪法作出“军事贡献”》,《参考消息》1990年11月20日,第1版。德国的这一修宪动议及其实践,被日本保守势力视为“修宪”的样板而欲乘机达成。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德国修宪是建立在朝野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基础上,所以不曾引起国内外反对而获顺利实施;而日本“修宪”是在朝野右翼势力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前提下展开的,故理所当然会受到国内外尤其是亚洲邻国的质疑和反对。另外,1993年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竟对日本共同社记者说:“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国家,日本应当为联合国的所有活动承担更大的作用……哪怕是修改宪法。”(37)《加利希望日本发挥更大军事作用》,《参考消息》1993年2月6日,第1版。来自最权威国际组织最高领导人的这一支持态度,令日本保守势力欢欣鼓舞,误以为日本“修宪”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遂肆无忌惮掀起第三次“修宪”浊浪。
五、后冷战后期:日本“修宪”思潮的践行
后冷战后期(2006—2021),日本政坛从安倍晋三内阁到菅义伟内阁历时15年。需要指出的是,其间尽管民主党执政三年又三个月,但日本保守势力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而是继续掀起了第四次“修宪”浊浪;此间尽管只有短短15年,但由于新生代政治家安倍晋三系“鹰派”右翼政客,又先后四次出任日本首相,因此日本国内第四次“修宪”逆流的始作俑者和关键人物均非其莫属。事实上,安倍晋三及其内阁在“修宪”的歧路上越走越远。
安倍晋三出身于政治豪门家庭,1993年开启政治家生涯后,虽然一度“经历过重大挫折”(38)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東京:文藝春秋,1986年,第5頁。,但他不仅只用十余年时间就入主永田町首相官邸,而且创下连续在位时间最长(7年又8个月)和史上累计在任时间最长(8年又8个月)的执政纪录(39)安倍晋三四次出任首相时间:2006年9月26日—2007年9月25日,出任第90任首相;2012年12月26日—2014年12月24日,出任第96任首相;2014年12月24日—2017年11月1日,出任第97任首相; 2017年11月1日—2020年9月16日,出任第98任首相。。尤需强调的是,由于当年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外祖父岸信介是最令其“感到骄傲”的政治家(40)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第28頁。,由于外祖父留下的“修改宪法”“这把火是不能熄灭的”(41)田尻育三等:《岸信介》,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8页。政治遗训被其牢记,所以安倍晋三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42)参见王柯、王智新:《安倍晋三传》,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6页。。这样,安倍成为日本国内第四次“修宪”逆流的始作俑者和关键政治人物也就不令人费解了。
安倍晋三及其内阁的“修宪”目标非常明确:删除和平宪法第九条,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补充“积极的和平主义”条款,为日本“入常”提供政治资本即创造条件(43)参见孙岩帝:《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为达此目标,安倍及其内阁将“修宪”思潮付诸行动。
一是再三说明“修宪”的必要性,刻意营造“修宪”氛围。安倍晋三在首相任上频频发表“修宪”言论,反复表明“修宪”立场,誓以“修宪”为毕生政治夙愿,认为和平宪法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其所谓理由有三:(1)现行宪法是解禁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的法律障碍,因此应制定一部新宪法取而代之,以便有法可依。(2)现行宪法所确定的战后体制是造成当下日本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源,因此应修改宪法第九条及扩大首相权限,以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3)现行宪法不是日本民意的真正体现,而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产物,因此应制定一部新宪法来顺应社会变迁和时代潮流。
二是定出“修宪”时间表,明确“修宪”重点。安倍晋三在2006年9月竞选首相时表示,应将“修宪”提上议事议程,一旦当选将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修宪”,并为在国会中获得三分之二以上议员的支持而努力。2012年9月,安倍再次在竞选纲领中承诺,一旦当选首相将修改现行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向钓鱼岛派驻公务员等。2014年1月,安倍不但在全国党代会上致辞说,2014年的主要工作是经济问题和宪法问题,而且将“修改宪法”写进《自民党2014年运动方针》。关于“修宪”重点,安倍在2012年9月再度当选首相后,立即抛出《日本国宪法修正草案》,删除了和平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战争”中的“永远”二字,并阐明放弃战争的行为不包括行使自卫权。2013年初,安倍在参议院抛出修改和平宪法第96条之意见,要求将“修宪”条件降低为在国会获二分之一议员赞同即可。2014年5月16日,日本内阁法制局召开会议,决定通过“解释性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7月1日,日本内阁会议接受了安倍关于变更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之提议,使自卫队海外参战“名正言顺”。
三是通过颁布相关法案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是否解禁集体自卫权关乎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存废,也是“修宪”派与护宪派斗争的焦点之一。安倍晋三作为“修宪”派的总头目,试图用外围立法和强军举措架空和平宪法。2013年12月6日,日本国会悍然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内容涉及防卫、外交、反恐、间谍四个方面,为政府隐瞒信息和侵犯人权提供了法律依据,完全背离了和平宪法所蕴含的“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两大原则。2015年5月14日,安倍内阁会议通过了《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彻底抛弃了战后以来一直奉行的“专守防卫”政策,为日本对外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法理依据。安倍内阁还修订了多个防卫计划大纲以架空和平宪法。安倍晋三不仅在2007年1月9日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而且在“梅开二度”的2012年底下达了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等指令,旨在逐年增加防卫经费和扩大防卫力量(44)李大光等:《一门三首相:安倍晋三家族与日本世袭政治》,北京:台海出版社,2013年,第195页。。2013年12月17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又通过了被称为“安保三箭”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4—2018)》《防卫计划大纲》《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防卫文件,全面规划了日本国家安全战略、防卫政策及今后战略指向等。
四是颁布《国民投票法》等法案,为“修宪”降低法律门槛。为了尽快达成“修宪”目标,安倍内阁在2007年推出《国民投票法》,规定:在众参两院获得通过的宪法修正案,需在两到三个月内提交给国民投票,过半数赞成即属于通过,大大降低了“修宪”过关门槛。2014年5月9日,在安倍晋三及其内阁的运作下,日本国会众议院又通过了《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将“修宪”公投的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意在扩大“修宪”支持率。
安倍晋三及其内阁的上述“修宪”行径,遭到日本正义人士的尖锐批判和顽强抵制。诸如,由知名宪法学者成立的“国民安保法制垦”指出,安倍当局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对日本国家存亡的威胁;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村越进批判说,安倍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是对日本和平国家国体的一种挑战;自民党政治理论审查会会长村上诚一郎批评说,首相违背民意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是让和平宪法名存实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九条会”领导人大江健三郎也对安倍晋三的“修宪”说辞痛加批判,并呼吁护宪派团结起来共同粉碎右翼“修宪”图谋(45)九条の会編:《九条の会全国交流報告集》,東京:九条の会出版,2006年,第115頁。。
安倍晋三及其内阁之所以掀起第四次“修宪”恶浪,主要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所致。一是,缘于安倍晋三家庭出身、成长环境和从政经历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一门三相”的显赫家族背景(46)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外叔祖父佐藤荣作均系右翼政客,战后都出任过日本首相;祖父安倍宽系战时众议院议员,因反对东条英机而被视为有骨气的政治家;父亲安倍晋太郎政治立场中性,战后出任过日本外相,若非突然去世亦有望成为首相。,使其产生了舍我其谁的政治自负;外祖父岸信介的“修宪”遗训,规定了其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深得小泉纯一郎等政坛右翼大佬提携的从政经历,进一步使其“修宪”思想固化。二是,缘于经济大国地位的重新确立。安倍一直对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这一国际形象不满,更对剥夺了国家交战权和拥有国防军权利的和平宪法第九条耿耿于怀,必欲铲除而后快。三是,缘于美国的默认和纵容。为发挥同盟国日本在遏制中国崛起中的作用,美国当局对日本“修宪”逆流采取了放任乃至纵容的态度,为安倍内阁加快“修宪”步伐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四是,缘于安倍本人的政治谋略。他深知,通过振兴经济赢得选票短期内难以奏效,唯有祭起“修宪”大旗才能迅速树立“伟人”形象,进而实现长期执政的夙愿(47)参见孙岩帝:《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历史演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结 语
通过对日本“修宪”思潮演变轨迹的纵向梳理和驱动因素的横向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四个基本结论。
第一,须认清日本保守势力“修宪”的政治图谋和精神实质,不被其欺骗性言词所迷惑。宪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持久性,又需要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而适时修改,此乃修改宪法的题中应有之意。换言之,修改宪法之本意是向“好”、向“善”改进,而绝非向“坏”、向“恶”改变。只是何为“好”与“善”、何为“坏”与“恶”,常因修改者政治立场有别、修改目的迥异而有所不同甚或截然相反。日本保守势力显然是在将本来“好”与“善”的和平宪法向“坏”与“恶”的方向修改,完全背离了宪法修改之本意,这也是笔者将“修宪”二字标注引号(以示所谓之意)的原因所在。然而,无论日本保守势力如何鼓噪和平宪法“强加论”“过时论”“阻碍贡献论”等,都掩盖不了其向战前回归即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图谋和本质。因此,对日本保守势力旨在扭转国家政治走向的“修宪”思潮要提高辨识力和警惕性。
第二,日本国民是决定和平宪法存亡的关键因素,应推动他们更多更快地走向觉醒。日本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战后以来日本保守势力能够不时掀起“修宪”浊浪,当与日本国内一部分不觉悟国民的存在并不断增多密不可分;日本保守势力之所以迄今未能达成“明文修宪”目标,又与日本国内一部分觉醒国民的存在并持续开展护宪运动息息相关。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日本的未来尤其是和平宪法的命运终究要靠日本国民自己来把握。唯有推动不觉悟的日本国民认清“修宪”本质及其极端危害性,进而在护宪还是“修宪”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正确抉择,才能捍卫和平宪法以确保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因此,对推动日本国民更多更快走向觉醒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有充分的认识。
第三,日本政要是决定和平宪法命运的重要因素,应努力壮大日本政坛护宪政治力量。政治家是国家的舵手和民族的领航员,是一国大政方针、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和变与不变的操盘手。一方面,我们要正视在日本政治右倾化背景下,日本政坛护宪派逐渐式微、“修宪”派迅速走强乃至进入“新的危险阶段”(日共语)(48)参见余金成:《冷战后两制关系演变及发达国家共产党研究》,第116页。之堪忧现实,做好同日本保守势力长期斗争的准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部分觉醒国民和进步学者的支持下,日本政界仍有共产党人和其他正直政治家在坚守和平理念和捍卫和平宪法。因此,如何分化瓦解“修宪”派、团结壮大护宪派,不但是当代日本史研究不应忽视的重要课题,而且是阻止日本向战前回归刻不容缓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第四,应充分发挥国际因素的制约作用,有效遏制日本“修宪”思潮的继续蔓延。在全球化背景下,日本国内的“修宪”思潮难免受到国际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只是这些因素对日本“修宪”有直接与间接、主要与次要、促进与牵制之分而已。首先,要谴责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日本“修宪”思潮所采取的默认和纵容态度,善意提醒和忠告美国当局放任抑或支持日本“修宪”可能给自身带来的潜在威胁和严重后果,使之成为维护而非葬送和平宪法的一支重要制约力量,避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历史结局的真正发生。其次,要推动东亚各国结成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平宪法的国际统一战线,联手应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修宪”逆流,避免日本法西斯侵略和奴役的历史惨剧再现。再次,作为当年日本侵略扩张的最大受害国,中国更应懂得捍卫和平宪法的重要性,更应密切关注日本国内的“修宪”动向,尤需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各项准备,以避免中日战争悲剧的重演。凡此,正是本文撰著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