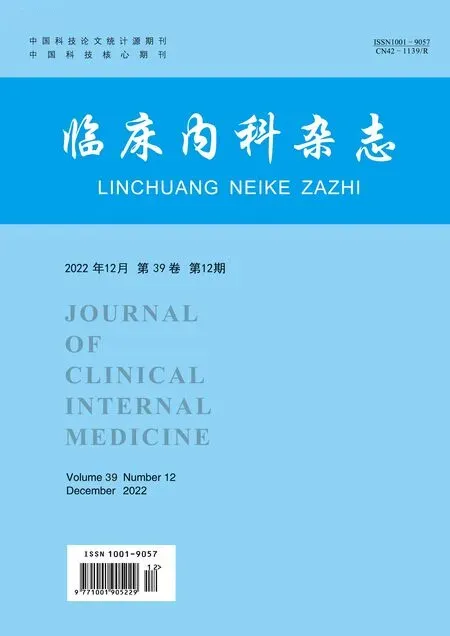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相关肝细胞肝癌的研究进展
杨荣 范建高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遗传易感个体由于营养过剩和缺乏运动引起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随着肥胖、代谢综合征、2型糖尿病(T2DM)的流行,NAFLD现已成为全球慢性肝脏疾病最为常见的病因。亚洲NAFLD患病率在全球处于中上水平,NAFLD累及亚洲1/3以上的成年人口[1]。与北美和西欧患者相比,亚洲NAFLD患者病程短、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进展期肝纤维化在NAFLD中的比例均可能偏低,合并慢性HBV感染的比例较高。HBV至今仍是亚洲原发性肝癌高发的主要原因,75%~85%的原发性肝癌病例是肝细胞肝癌(HCC),NAFLD相关HCC的发生率在亚洲地区同样呈上升趋势[2]。为此,本文综述亚洲成人NAFLD相关HCC的流行趋势、危险因素及其筛查和防治对策。
一、NAFLD和HCC的流行现状
原发性肝癌是全球第六大恶性肿瘤、第三大最常见恶性肿瘤死亡原因,东亚和东南亚是全球原发性肝癌的高发区,高达73%的原发性肝癌死亡病例发生在亚洲。在亚洲,HCC的主要危险因素仍然是慢性病毒性肝炎,特别是HBV感染。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性HBV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的流行率逐渐下降,HBV和HCV感染的发病率下降则更为显著,由此导致的HCC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亦呈下降趋势。然而,亚洲仍是慢性肝脏疾病的高发地区,主要是因为NAFLD在亚洲的患病率增长迅速且不断攀高,从2000年初的25%上升至近年来的34%。随着亚洲肥胖和糖尿病的大流行,预计2030年NAFLD病例总数将较2016年增加30%。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国NAFLD发病人数增加最快,而韩国和日本由于人口减少其NAFLD的增长最慢[3]。
虽然大多数患者的NAFLD处于单纯性脂肪肝的早期阶段,但确有10%~30%的NAFLD患者为NASH,有研究预测2030年中国和日本NASH患病率将分别较2016年增长48%和14%[3]。除非早期发现并积极治疗,否则NASH可通过肝纤维化进展至肝硬化和HCC。约38%~50%的NAFLD相关HCC患者并未经历肝硬化过程。NASH和肝硬化并非肥胖、T2DM患者发生NAFLD相关HCC的必备条件。
近20年来,亚洲HCC的病因正由病毒因素(慢性HBV和HCV感染)向非病毒因素转变,后者主要是酒精性肝病和NAFLD。在日本,非病毒因素所致HCC比例从1991年的10.0%上升至2015年的32.5%;在韩国,NAFLD相关HCC的比例从2001~2005年的3.8%上升至2006~2010年的12.2%[4]。有数据模型预测,从2016年到2030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HCC病例将分别增加82%、85%和65%,日本、新加坡和韩国HCC病例将分别增加44%、80%和80%,为此,NAFLD有可能成为2030年亚洲HCC的首要病因[3]。此外,由于亚洲许多地区慢性HBV感染和乙型肝炎患者同样面临肥胖、代谢综合征和糖尿病的流行,现症或既往感染HBV个体发生NAFLD越来越常见,而合并HBV感染的NAFLD患者更易发生肝硬化和HCC。
二、NAFLD相关HCC的危险因素
高龄、男性、饮酒、进展期肝纤维化特别是肝硬化是NAFLD患者发生HCC的重要危险因素。不良生活方式、遗传易感与表观遗传改变、代谢危险因素及肠道微生态失衡是NAFLD群体发生HCC的潜在危险因素。
1.不良生活方式
NAFLD是营养过剩和长期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能量失衡的结果,并由于遗传易感性而加剧。尽管富裕的代谢性疾病在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存在城乡差距,NAFLD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至今仍不普遍,但近20年随着广大农村地区居民BMI的不断增高,超重和肥胖及其相关NAFLD患病率的城乡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一项针对亚洲5个地区NAFLD患者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发现,NAFLD患者常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其中吸烟占3.8%~22.6%;软饮料摄入占22.6%~62.2%;70%以上未满足体育活动指南的运动建议;仅不足50%的患者进行了高强度或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患者每周平均坐位时间达42小时[5]。一项针对香港NAFLD患者的研究表明,其饮食质量指数-国际得分较低,食用的蔬菜、水果和维生素C含量偏低[6]。一项对14项前瞻性研究(包括4项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研究)进行的Meta分析表明,体育活动与原发性肝癌风险呈负相关,高强度体育锻炼与低强度体育锻炼者HCC的风险比为0.75[7]。然而,由于个人生活方式因素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很难剖析各种生活方式因素在NAFLD及其相关HCC发生中的具体作用。
2.遗传与表观遗传因素
基因组学是研究疾病遗传因素的重要手段,目前基因组学研究已确定一些基因在NAFLD发生发展甚至HCC中的作用,如PNPLA3和TM6SF2促进NAFLD和NASH的进展,而HSD17B13则可预防NAFLD的进展[8]。在这些因素中,PNPLA3 rs738409 I148M变异在亚洲人群中最为多见,且PNPLA3突变在东亚黄种人患者中比白种人和黑人患者更常见。一些队列研究发现,这些基因多态性不仅与NAFLD及其肝脏组织病理学严重程度相关,而且与HCC风险增加密切相关。一项来自香港的肝脏活检证实的慢性乙型肝炎队列研究表明,肝脏脂肪变性和APOC3 rs2854116突变均与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随访中发生HCC相关,而APOC3早已被证实是印度人NAFLD的易感基因[9]。一项来自欧洲的多中心队列研究基于PNPLA3、TM6SF2、GCKR、MBOAT7和HSD17B13建立了NAFLD患者和普通人群HCC预测的多基因风险评分的判别模型[8]。尽管这些遗传标记大多数在亚洲人群中也已进行了探索,但至今鲜见关于NAFLD相关HCC的研究数据[2]。
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和非编码RNA在HCC领域的研究广泛,这些表观遗传过程也参与了NAFLD的进展。如衰老有利于DNA甲基化,进而促进NAFLD相关HCC的进展[8]。未来应进一步研究表观遗传修饰在NAFLD相关HCC中的具体作用。
3.代谢危险因素
肥胖、T2DM、代谢综合征不但是NAFLD及其伴发的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且与HCC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与其他原因所致的HCC患者相比,NAFLD相关HCC患者更容易出现代谢和心血管合并症[10]。二甲双胍、阿司匹林、他汀类药物、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等有可能降低各种类型的慢性肝病患者HCC的发病风险[11]。控制代谢和心血管危险因素本身及应用的这些药物在NAFLD伴或不伴其他肝病患者HCC预防及HCC根治术后复发预防中的作用及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阐明。
(1)T2DM:近来亚洲T2DM患病率正在上升,且发展中国家上升趋势大于发达国家,而糖尿病是HCC的独立危险因素。一项来自中国台湾的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HCC发病率高于无糖尿病患者(分别为21.0和10.4/10 000人年);与糖尿病持续时间为2~5年的患者相比,糖尿病持续时间6~10年和超过10年的患者HCC调整后的优势比分别为1.8(95%CI0.8~4.1)和2.2(95%CI1.2~4.8)[12]。使用二甲双胍、噻唑烷二酮类药物、磺酰脲类药物、胰岛素和仅仅饮食对照治疗的糖尿病患者的HCC调整优势比分别为0.3(95%CI0.2~0.6)、0.3(95%CI0.1~0.7)、7.1(95%CI2.9~16.9)、1.9(95%CI0.8~4.6)和7.8(95%CI1.5~40.0)[12],提示血糖控制不佳及应用磺酰脲类药物和胰岛素降糖治疗均可能增加HCC的发病风险[11]。
(2)肥胖症:肥胖通过增加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IL-6等促炎细胞因子水平来促进代谢性炎症和HCC的发生。一项对普通人群和慢性肝病患者的Meta分析表明,BMI≥25 kg/m2和BMI≥30 kg/m2与原发性肝癌风险增加相关(相对风险分别为1.48和1.83)[13]。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人和高加索人的体脂组成不同,在相同BMI的情况下,亚洲人体脂和内脏脂肪含量高于高加索人,而中心性肥胖与NAFLD相关HCC风险又密切相关。因此,亚洲人能够在较低的BMI和较小的腹围时发生代谢功能障碍、NAFLD甚至HCC,内脏脂肪组织过多和中心性肥胖是酒精性肝病和NAFLD患者HCC的危险因素。
(3)代谢综合征:代谢综合征是慢性肝病患者HCC的独立危险因素,其重要组分血脂紊乱和高血压本身也可能增加HCC的发病风险。一项1993~2005年的研究显示,血脂紊乱和高血压分别增加HCC的发病风险1.35倍(95%CI1.26~2.45)和2.22倍(95%CI2.04~2.42)[14]。并且,高脂血症患者可能更易发生无肝硬化的HCC[15]。具有降脂功能的他汀类药物不但可安全用于NAFLD和NASH患者,还可预防HCC的发生。韩国的一项研究发现,他汀类药物显著降低慢性HBV感染患者HCC的发生风险[16]。一项来自挪威、瑞典和奥地利的纳入578 700例受试者的研究发现,高血压在HCC发展过程中的相对风险为2.08(95%CI0.95~4.73)[14]。目前亚洲国家鲜见血脂紊乱、高血压队列人群HCC发病风险的数据。
4.肠道微生态失衡
肠肝轴是目前研究的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肠道菌群在NAFLD相关HCC中发挥重要作用。肠道菌群多样性减少、革兰阴性菌(主要是变形菌门)丰度增加而革兰阳性菌(主要是厚壁菌门)丰度减少等均是NAFLD发生和发展中常见的肠菌紊乱。膳食胆固醇通过诱导小鼠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的改变(包括双歧杆菌和拟杆菌水平下降,而Mucispirillum水平增高),可促进NAFLD相关HCC的发生[17]。来自米兰的一项研究发现,与NASH肝硬化患者相比,NAFLD相关HCC患者肠道Akkermansia和双歧杆菌水平均较低[18]。
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参与微生物驱动的NAFLD相关HCC的发病。一旦肠道屏障被破坏,包括脂多糖在内的细菌和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可通过肠道转运至肝脏,通过激活病原体识别受体和诱导免疫反应诱发HCC。此外,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后,肠道微生物可易位至肝脏,可能进一步导致肝脏损伤[19]。
氨基酸、短链脂肪酸和次级胆汁酸等微生物代谢产物是肠道微生物组和NAFLD相关HCC之间的另一个重要联系。例如,肠道微生物酵解三甲基赖氨酸的代谢产物N,N,N-三甲基-5-氨基戊酸,可减少肉碱合成和脂肪酸氧化,进而加剧NAFLD相关HCC的发病。肝脏中次级胆汁酸脱氧胆酸的增加可能引发衰老相关的分泌表型,促进各种炎症和促癌因子的分泌,进而诱发HCC。因此,靶向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有可能起到预防或治疗NAFLD相关HCC的作用。然而至今有关短链脂肪酸在NAFLD及其相关并发症中丰度和功能的报道仍有争议[19]。
三、NAFLD相关HCC的管理
尽管无肝硬化的NAFLD患者也可发生HCC,但绝对风险较低(每年<0.1%),现有指南均不建议在广大NAFLD患者中筛查HCC。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NAFLD和肝纤维化程度轻的患者HCC发病率为0.03/100人每年,而肝硬化患者HCC的发病率为3.78/100人每年[13]。肝脏活检确诊的NASH相关肝硬化患者应考虑每半年使用超声监测HCC,可考虑联合血清甲胎蛋白检测。对于重度肥胖、不均质性脂肪肝患者,超声筛查HCC的质量受限,必要时需考虑通过增强CT或MRI筛查HCC。然而,常规的血液和影像学检查难以敏感诊断NAFLD相关肝硬化,与慢性病毒性肝炎导致的肝硬化患者相比,NAFLD相关肝硬化人群通常未有效进行HCC的筛查。使用简单且基于现成参数的肝纤维化评分有助于发现进展期肝纤维化或肝硬化患者,从而提高NAFLD患者HCC的筛查和监测效果[20]。瞬时弹性检查的肝脏硬度值>15 kpa伴或不伴血小板计数减少,高度提示NAFLD患者存在进展期肝纤维化和肝硬化,这些患者应该筛查和定期监测HCC[21]。
与其他病因所致的HCC相比,NAFLD相关HCC患者接受治疗的可能性更小,因为这类患者常在中晚期发现,往往年龄大、合并症较多、心肺功能差。相比于西方国家,亚洲在通过肝叶段切除、肝移植和射频消融等方式治疗HCC方面更为积极,然而亚洲国家并没有报道NAFLD相关和非NAFLD相关HCC在手术时间、围手术期失血量和输血需求等方面的差异,且部分亚洲国家原发性肝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于西方国家[22]。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和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抑制剂]、化学治疗等系统治疗通常用于进展期或晚期或复发性HCC患者。基础和临床研究报道,NAFLD相关HCC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效果不如病毒性肝炎相关HCC,且可能更易出现不良反应。一项纳入334例不能切除的亚洲晚期HCC患者(其中21%与HBV、HCV、酒精滥用无关)的研究结果显示,口服多激酶抑制剂Lenvatinib的总体生存率高于索拉非尼[23]。一项针对133例不能切除的亚洲HCC患者(30%与HBV、HCV无关)的研究发现,联合使用阿替利珠单抗(PD-L1抑制剂)和贝伐珠单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的总体和无进展生存率也高于索拉非尼[24]。我国一项针对34例未接受过系统治疗的晚期HCC患者的Ⅱ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给予卡瑞利珠单抗联合FOLFOX4方案或GEMOX方案治疗后,患者的客观缓解率为26.5%,疾病控制率高达79.4%[25]。遗憾的是,后两项研究并未对有无NAFLD相关HCC进行区分或分层分析,目前的证据表明并存的脂肪肝对慢性乙型肝炎及其相关HCC患者有明显的不良影响,而有效防治代谢紊乱和脂肪肝有可能降低HBV相关HCC的发病和复发风险[2]。
总之,随着亚洲NAFLD相关HCC发病率的上升,未来几年NAFLD相关HCC病例的绝对数量将超过西方。由于亚洲地区同时流行慢性病毒性肝炎和代谢性疾病,NAFLD成为该地区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又因肿瘤通常在晚期发现且合并多种基础疾病,NAFLD相关HCC的根治面临巨大挑战。基于成熟的临床、遗传风险因素及肝纤维化特征可指导NAFLD患者HCC的筛查和监测,有望早期发现HCC,而减肥、戒酒、有效防治代谢性疾病则可降低各种类型肝病患者HCC风险,现有的针对NASH治疗的新药研发需关注有无降低HCC和肝外恶性肿瘤的潜在获益,当前需要加强NAFLD相关HCC治疗和预防复发的临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