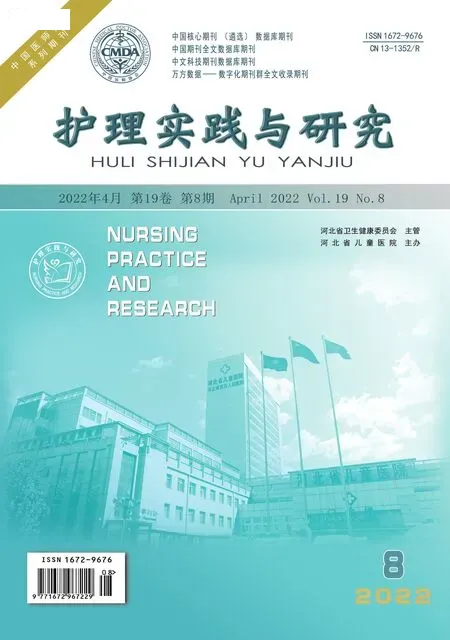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相关评估工具的研究进展
魏其秀 钱自华
脑卒中是脑血管阻塞或突然破裂造成脑组织损伤的急性脑血管病[1]。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2019指出,我国居民脑卒中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由于脑卒中难以治愈,容易复发,疾病管理对患者有较高要求,比如按时服药、改变生活方式、定期随访等,给患者带来了较为沉重的治疗负担[3]。治疗负担是指患者为疾病管理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及其对幸福感的影响[4]。较重的治疗负担会导致患者治疗和自我护理的依从性下降,从而造成不好的临床结局[5]。因此,了解脑卒中患者的治疗负担成为急待解决的临床问题,对促进脑卒中患者疾病恢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国外学者对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研究较多,我国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相关评估工具文献则鲜有报道,本文主要对其进行综述,旨在为医务人员选择合理的评估工具、构建适合我国脑卒中患者的治疗负担评估工具提供参考和借鉴。
1 治疗负担的概念及主要内容
1.1 概念
治疗负担是卫生保健领域提及的一个新兴概念,不同于以往的药物负担、医疗保健负担、自我照护负担、疾病负担等,还包括所有类型的卫生保健干预以及患者的观点[6]。最早是Vijan 等[7]观察到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任务相当繁重,于是开始研究患者的治疗负担。近年来,有关治疗负担的研究逐渐增多,不同学者对治疗负担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见解。Gallacher 等[8]通过对29 位脑卒中患者进行访谈,采用标准化过程理论为基础进行框架分析,总结出治疗负担的概念模型,提出治疗负担是医疗保健工作量或护理不足导致的结果。为了找出治疗负担的概念,Alsadah 等[6]对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基于质量评估标准筛选出了2 个质量较高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指长期疾病患者的医疗工作量及其对功能和福祉的影响;第二个概念是患者为自己的医疗保健投入的行动和资源,包括就医困难、协调时间、药物管理、自我监控及饮食改变等。第二个概念比第一个更简洁明了,且适用范围更广。
1.2 主要内容
关于治疗负担的内容目前还没有确切统一的标准,国外学者大多通过质性访谈从患者的角度进行研究。Gallacher 等[8]检索了2000 年1 月—2013 年2 月发表的与治疗负担相关的文章,并进行系统评价,认为治疗负担应包括4 个方面:①花时间了解脑卒中管理和计划护理,包括疾病随访、药物管理等;②与他人沟通交流,包括医务人员、家庭照护者等;③制订管理策略,包括住院管理、社区管理、脑卒中后生活适应等;④管理反思,脑卒中患者需要定期对疾病管理效果进行评估。Sav 等[9]对97位患者及其照护者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深入分析后总结出治疗负担包括:经济负担、时间和行程负担、药物负担、获取医疗保健负担。其中,经济负担是最重要的负担,不但影响患者的用药情况而且会加剧其他类型负担。治疗负担不仅受客观因素影响,同时也受患者主观影响,因此,医务人员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减轻患者治疗负担,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Eton 等[10]对32 位慢性病患者进行质性访谈,采用概念框架进行评估,提出治疗负担包括3 个主题:①患者为了健康必须做的工作,比如用药管理、自我检测、预约复查等;②加重负担的因素,如经济负担、药物副作用、家庭冲突;③负担的影响,影响生活方式、情绪困扰等。这与Sav 等[9]提出的治疗负担部分相似。我国学者郑琛等[11]对10 名内科医生进行了质性访谈,从医师的角度探讨治疗负担的内容,总结出治疗负担包括经济负担、用药负担、获得健康照护负担、时间负担、心理负担5 个方面。从医生和患者的角度分别对治疗负担进行探讨,虽然结果不完全一致,但大都包括了经济负担、心理负担、医疗保健负担等。
2 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相关评估工具
2.1 治疗负担问卷(TBQ)
法国学者Tran 等[12]为了测量慢性疾病患者的治疗负担,在2012 年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患者编制了TBQ 问卷。TBQ 有13 个条目,采用Likert 10级评分法,最高得分130 分,得分越高治疗负担越重。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重测信度0.76,内部一致性良好。由于法国慢性疾病患者拥有免费医疗保健服务,所以问卷编制过程中舍弃了经济负担这一条目,因此TBQ 较难被借鉴。2014 年,Tran 等[13]对问卷进行了修订,增加了治疗费用、医患沟通困难2 个条目,TBQ 总条目变为15 个,Cronbach’s α 系数为0.90,重测信度0.77,修订后的问卷符合较多国家的医疗现状,并且Tran 等将法语版的TBQ 问卷翻译为了英文版。问卷被较多研究者引用,我国学者也对TBQ 进行了汉化,在香港和大陆地区都进行了验证,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80[14-16]。因此,可以结合研究目的及临床情况,利用TBQ 测量我国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水平。TBQ 作为测量慢性病患者治疗负担的普适性量表,得到了广泛学者认可,是目前测量治疗负担应用最多的一个问卷。
2.2 多病疾病感知量表(Multiples)
英国学者Gibbons 等[17]在2013 年对1500 名患有2 种及2 种以上慢性病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其中490 名患者完成了问卷,编制了Multiples 量表,用于测量患者对疾病的感知。量表共22 个条目,有5 个分量表,分别为情绪表现、治疗负担、优先考虑、因果关系、活动受限。所有条目均采用Likert 6 级评分法,从0~5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所有分量表均与Rasch 模型拟合良好,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Multiples 量表优势在于通过因子分析对各维度进行初步探索之后,又使用Rasch 模型对量表信效度进行了分析,保证量表的科学性。但量表只有部分内容是关于治疗负担的,对患者治疗负担的评估并不全面,且量表研发的时候,纳入的研究对象为患有抑郁症、骨关节炎、冠心病、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没有将脑卒中患者纳入其中,虽然纳入研究的5 种慢性疾病较具代表性,但对脑卒中患者适不适用,还需进一步检验。
2.3 健康照护任务困难量表(HCTD)
2014 年,美国学者Boyd 等[18]通过查阅文献、专家咨询、访谈患者,形成了11 个条目的HCTD量表,邀请904 名65 岁以上老年多病患者及其308名照顾者参与研究,删除了3 个多余条目,最终形成7 个条目的HCTD 量表,用于测量患者的健康照护困难程度。7 个条目分别为获得药物困难、难以计划用药时间表、难以决定换药、难以处理医疗账单、很难安排医疗设备、安排运输困难、获取信息困难。采用Likert 3 级评分法,0 表示没有困难,1 表示有点困难,2 表示极大困难。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疾病数量、较差的身心状况、不良的护理质量与HCTD 增加有关。对接受调查患者中的419 名患者进行纵向分析,发现对患者采取激励措施可以降低 HCTD 得分。该量表优势是进行了纵向分析,可有效减少偏倚,但HCTD量表只包括了治疗负担的部分内容,对治疗负担的评估较局限,目前没有中文版本的HCTD 量表。
2.4 Chao 感知连续性量表(Chao PC)
Chao PC 量表是患者自评量表,由研究者[19]基于Banahans[20]的连续性概念编制而成,包含23 个条目,分为两个部分,第1 部分评估护理过程,第2 部分是连续性的关系维度。采用Likert 5 级评分法,评分为1~5 分,第1 部分条目可评为“绝对是真的;大部分是真的、不确定、大部分是假的、绝对是假的”;第2 部分的条目在同样的评分量表上从“强烈同意”到“强烈反对”进行评分,评分越高感知的连续性越高。Chao PC 量表在美国147 名患者中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可靠性报告。2014 年,英国学者Hill 等[21]对310 名急性卒中后在社区生活了约1 年的卒中幸存者进行Chao PC 量表的问卷调查,确定其是否适合用来衡量初级保健环境中脑卒中患者的护理连续性,并将23 个条目进行主成分分析,探索性分析的新兴因素有3 个:①人际信任,即关系连续性;②人际知识和信息,即信息和关系的连续性;③护理过程,即管理的连续性。其中人际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部分,会影响患者参与护理过程和患者对护理的满意度。通过调查,Hill 等[21]发现Chao PC 量表对患者情绪、功能状态不敏感,可能会影响患者护理连续性体验。由于量表问题设置的形式,量表中特定于上下文的条目患者表示难以理解,导致数据缺失及患者回复率低。因此,除非对原始量表进行修改,否则不能广泛应用。Chao PC 量表23 个条目均侧重于护理的连续性,虽然其中有17 个条目测量了治疗负担,但仍不全面,量表的使用并不广泛,是否能推广使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2.5 患者关于治疗和自我管理体验量表(PETS)
PETS 量表是美国学者Eton 等[22]在2016 年通过医护人员、卫生服务研究员以及患者共同讨论而研制出的,用于测量慢病共存患者,即同时患有2种及以上慢性病[23]患者的治疗负担状况和自我管理经验。量表包括医疗信息、就医预约、医疗花费、医疗服务利用困难、药物、健康监控、人际关系困扰、角色和社交活动受限、身体或心理疲乏9 个维度共48 个条目。除了医疗服务利用困难维度使用Likert 4 级评分法,其余均使用Likert 5 级评分法,得分越高,表示患者治疗负担、抑郁程度越重,用药满意度越低,自我效能感、身心状况及医疗保健便利性越差。Eton 等[22]使用PETS 对332 名慢病共存患者进行了测试,结果显示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0.79~0.95,各维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1~0.95,信效度良好。但PETS 量表研发出来的时间还不太长,且条目数偏多,患者完成量表填写需要耗费较多时间,导致问卷完成率低[23],因此,量表的实用性还需进一步考量,进一步研究可以探讨是否能对量表进行简化。
2.6 慢性病共存治疗负担问卷(MTBQ)
MTBQ 是英国学者Duncan 等[24]于2018 年编制,用于测量慢病共存患者的治疗负担。问卷共1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0~4 分表示“不适用或没有困难”到“极度困难”,得分越高患者治疗负担越重。治疗负担严重程度分为4 个等级:0 分无治疗负担、<10 分低治疗负担、10~21 分中治疗负担、≥22 分高治疗负担。MTBQ 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重测信度0.76,说明MTBQ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MTBQ 条目简洁,实用性强,得到了普遍认可,现已被丹麦学者翻译[25]。我国学者豆丽园等[26]也对MTBQ 进行了汉化,并在220 名慢性病患者中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8,信效度较好,可以用于我国慢病患者治疗负担水平的测量。
2.7 脑卒中护理满意度问卷(SASC)
1994 年Gompertz 等[27]为了测量住院脑卒中患者和社区脑卒中患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编制了SASC 问卷。问卷由2 部分组成,即住院护理(Hospsat)满意度和患者出院后护理(Homesat)满意度。SASC 有13 个条目,其中12 个条目衡量了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采用Likert 3 级评分法,0分代表非常不同意,3 分代表非常同意,分数越高,患者满意度越高。问卷在脑卒中幸存者中进行了信效度检验,Hospsat 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Homesat 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7,两个部分的内部一致性都较好。2003 年,Boter 等[28]将其引入荷兰,并增加到了19 个条目,扩展问卷(SASC-19)的信度和效度在166 例脑卒中出院患者中进行了验证,Cronbach’s α 系数和类内相关系数均大于0.80,两份分量表均具有良好的同质性和重测信度。此后,SASC 又被不同国家的学者翻译为多种文字[29-31],广泛用于评价脑卒中患者护理满意度。SASC 是专门针对脑卒中患者护理满意度开发的,属于脑卒中患者特异性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了治疗负担的大多数,但仍有缺失的方面,且问卷开发时间较久远,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研发全面测量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的评估工具。
2.8 脑卒中后体力活动障碍量表(BAPAS)
Drigny 等[32]为了测量脑卒中患者的体力活动障碍,对脑卒中幸存者进行访谈和问卷调查,通过专家小组讨论于2019 年开发了BAPAS。BAPAS 最初版本有27 个条目,为了节省填写时间,研究者邀请了109 例患者对量表进行简化,删去了13 个多余条目,最终留下14 个条目,构建了由BAPAS I(7 个条目)和BAPAS II(7 个条目)两部分组成的BAPAS 量表,BAPAS I 探索患者行为障碍,比如患者的情绪、动机等;BAPAS II 探索患者身体障碍,比如存在运动方面的问题或身体患有多种疾病。采用Likert 6 级评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赋值0~5 分,总量表最高得分70 分,得分越高活动障碍越多。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但量表主要是测量轻度残疾的脑卒中患者的活动障碍,而中重度残疾的患者会面临更多的障碍,所以量表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脑卒中患者,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去检测不同严重程度和不同地区的患者,并评估量表与其他行为、幸福感、生活质量等的标准效度。BAPAS 量表14 个条目中有7 个条目与治疗负担相关,是评估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的特异性条目,但只是治疗负担中的一小部分,不能广泛地用于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的测量。
3 小结
目前,临床上还没有可以治愈脑卒中患者的医疗方法,只能尽量控制延缓疾病的发展,除了疾病急性期在医院治疗外,大部分时间需要患者自我管理,这势必会给患者带来治疗负担。通过治疗负担评估工具对患者进行调查,能及时了解患者治疗负担水平,对负担重的患者应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同时评估工具还可以测量干预的效果。虽然现有的治疗负担评估工具已经经过了信效度检验,但仍存在问题:①大部分评估工具仅包含了治疗负担的部分内容,不能全面反应患者的治疗负担;②评估工具主要基于文献回顾、经典理论、访谈患者和专家咨询编制而成,大都未采用现代心理测量技术如Rasch 模型等,科学性受到一定限制;③治疗负担评估工具主要为国外学者研发,由于存在地域、文化差异,不能精确地反映我国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的严重程度,且普适性评估工具居多,脑卒中患者特异性治疗负担评估工具很少,目前未见可全面测量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水平的评估工具。
因此,建议在接下来的研究中:①基于已有研究,采取质性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深入探讨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包括哪些内容,为研发全面测量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水平的评估工具提供基础;②我国暂时还没有评估脑卒中患者治疗负担的测量工具,可参考国外研究,基于系统方法学,编制适合我国国情、可操作性强的评估工具,采用现代心理测量技术,保障评估工具的科学性;③通过评估工具的测量,结合临床,为脑卒中患者制订切实可行、个性化的干预方案,减轻患者的治疗负担,改善患者临床结局。
DOI:10.1186/s12916-014-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