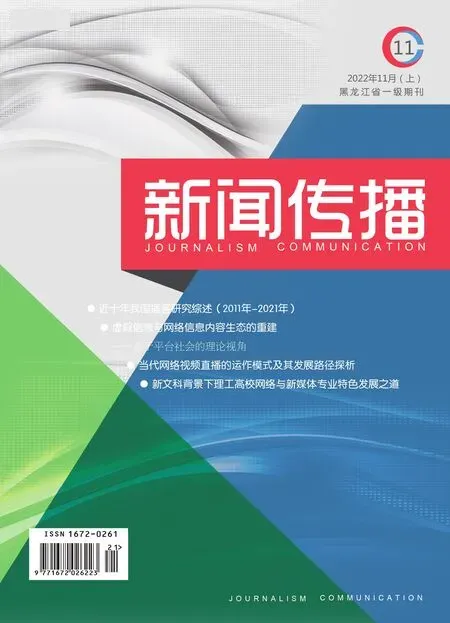近十年我国播客研究综述(2011年-2021年)
买尔哈巴·吐达洪
(新疆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6)
随着Web2.0 技术的普及,移动播客逐渐成为市场宠儿,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本研究针对2011-2021 年我国播客研究展开文献梳理,以“播客”为检索条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共得到中文文献共969篇;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文献436 篇,学位论文168 篇。笔者试图梳理出10 年来播客研究的知识版图,为探寻新的研究视角提供启示。国内关于播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一、播客的特点及其发展研究
近十年,关于播客特点及其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播客属性及定义的界定、播客特点分析以及播客发展三个方面。
播客属性及定义的界定,相关研究各有侧重,汤莉萍(2012)从网络传播方式和信息分享途径对播客进行狭义和广义界定,认为狭义播客侧重自动订阅,广义的播客侧重分享。谢瑜瑶认为播客是给受众创造独立与自主制作,发布和传播相关音视频的新媒体平台。刘滢、胡洁(2017)则从词源界定播客:播客的英文Podcasting,源自于“Ipod”和“Broadcast”的合成词,是一种向互联网分发视频和音频的方法,区别于早期在网上直接发布视频和音频节目。[1]童云和毕丹认为,从内涵上看,播客是在网络环境中由网民自发生产、传播与存储,可供个性化订阅和信息交互的音视频数字媒体;从外延上看,播客逐渐从小众化、个人化媒体演变为社会化媒体,构建了新的音视频网络传播体系。[2]
播客经历早期的播客网站发展到现在基于web2.0的音频播客平台的发展,对播客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成为学者的关注点。陈刚认为早期的播客是以土豆网、优酷网等众多以娱乐消遣为主的播客网站,其内容主要是单纯音频和综合听说书写视频。陆美兰分析了早期博客和播客(有声播客)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为播客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博客的升级及继承。王慧敏认为播客经历了终端移动化、用户私密化、使用场景化等三种阶段,播客在发展中面临市场格局不清晰、话语权漂移、个体与社会脱离等问题,应借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支撑推进移动音频的发展。熊辉梳理了中国网络音频从早期萌芽状态的商业化过程到后来智能化发展的历程,指出网络跟广播的实验性结合,音频产业链的形成再到互联网和移动智能设备的结合完成了声音收听,录音和传播的使命。王子健认为播客从以往复杂的设备发展到移动客户端,其便携性得以增强,节目内容与形式更加多样,播客平台的开发将形成“受众群”,制作形式呈现平民化向众媒时代的转型。史安斌、薛瑾梳理传统广播发展到播客的演进历程,指出随着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普及,播客的复兴使全球新闻传媒业经历音频转向。王长潇、刘瑞一(2019)分析了播客兴起、衰落到再次兴起的原因,认为由于播客对信息传播方式以及所衍生的信息传播权利的变革,一度被视为是传统广播的颠覆者;而“图像革命”的规制及支撑播客发展的客观条件不足,使播客陷入低潮;移动音频媒体崛起使播客再度进入公众视野,播客具备了移动化、智能化和场景化的特征。[3]周利娟以小宇宙APP为例分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中文播客平台的发展,认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中文播客打破了早期中文播客平台中心化、互动单一的局限,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兴中文平台针对中文播客主打造了更便捷的制作运营方式和合理的盈利模式。
播客特点的研究与播客属性与播客发展研究同时展开。如前文提到的学者陈刚认为播客为网络新媒体具有四个特点:即播客是一种多媒体传播媒介,传者和受众可以实现互动,其传播模式是一种多线性传播模式,其内容可以实现自由订阅和下载以便受众利用多种接收终端接收。王恒分析了播客传播主体,认为其传播主体具有草根色彩,多元形式存在的主体给个体充分表达的机会,使受众拥有了双重角色;由此多元主体使播客内容呈现灵活而自由的特点;传播符号跨界与多种符号结合的特点增强了播客的表现力;直观的口语化形式则提高播客的传播力,实现播客传播的平民化。田园认为传统广播具有“信息媒介”的胜利,智媒时代中文音频传播则实现了“生活媒介”的胜利。从广播发展到音频传播,是时空和功能的“转场”与“转向”。
二、播客与广播媒体关系研究
由于同属于音频传播,十年来播客与广播媒体关系研究也成为播客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播客对传统广播的影响研究及播客与传统广播的比较研究,实际上这两方面的研究是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能够勾勒研究脉络,本部分从上述两个方面展开。
从影响研究来看,施国龙认为播客对传统广播电视的影响体现在播客为传统广播提供了全新的传播模式,传统广播还可以从播客中汲取丰富的内容,播客节目中插入的广告与付费订阅模式也为传统广播电视媒体提供了盈利思路。贺艳、林怡婷(2015)分析了播客的传播内容、传播特性以及传播模式给传统广播发展带来的启示,认为传统广播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路径应该是以播客为方法,以移动应用为载体。[4]栾轶玫认为播客彻底改变了传统广播的线性传播与不易保存的属性,短音频的发展、移动终端的出现以及车联网技术的普及迫使传播广播必须转型。王卫明、马晓纯(2018)指出广播+移动网络、广播+社交网络等音频播客形式是传统广播转型的方向,就两者关系来看,音频播客使传统广播具备了盈利前景可观、创设成本低廉、用户黏度较高等新优势,但也存在着用户需求模糊、音频变现困难、音频内容同质化等问题。[5]
播客与广播媒体比较研究方面,张璇分析了播客与广播电视的关系,认为播客与广播相比具有交互式传播、平等受众、把关人弱化及强大的搜索引擎等优势,同时也有版权纠纷、质量不佳及管理复杂等劣势,播客是传统广播电视的衍生,两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金姗姗指出,播客因准入门槛低,以往复杂的设备操作逐步简单化,其便携性得以增强等特征区别于传统电视与广播。任珍分析了播客与传统广播的差异,认为播客以传者为本位,其内容生产集中于互联网和自动订阅系统,是草根生产者通过简单设计与制作输出内容的新型数字广播。而传统广播以受众为本位,运用数字传输技术,通过大设计生产具有权威性与原创性的新闻内容。吴思哲(2020)认为播客与广播的不同之处在于播客的沙龙属性,又因受众的自主性,播客具备了较强的用户黏度,因其低门槛的生产成本拓展了私人交谈与公共言说的边界,促进了思想的碰撞与文化的传播。[6]
三、播客的传播学研究
龙平研究了播客的社会娱乐功能,指出播客传播具有社会进程的纪实性,娱乐功能的后现代性等独特表现形式,其促进了播客传播的娱乐功能发展。刘天祥认为播客的主体是以互动形式存在,传播者和信息生产者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其传播模式的特殊性在于双向的互动过程与普通人能够掌握一定的媒体力量。季君在新媒体、商业与文化领域的传播语境下分析播客的传播现状与特点,指出播客具有后现代文化的多元化与去中心化,大众化与娱乐性,复制粘贴组合等特征。李静从内容生产和广告营销两个方面分析,认为播客生产呈现跨媒介、跨平台的趋势;播客规模快速增长引发广告商的关注,定制播客成为品牌推广的重要工具。宋青将播客置于声音媒介环境,结合听觉文化和声音媒介理论厘清播客发展历程,解读播客“新听觉文化”理念,介绍国外播客的媒介融合属性,探讨了播客所迎来的“新听觉文化”中受众的交互行为,提出声音媒体的市场可能。孙鹿童(2021)以中文播客小宇宙为个案展开分析,认为中文播客对谈聊天的主旨是热点社会话题;在播客主与用户构建的交流空间中,用户依靠单一传播元素交流,彰显播客的“文化沙龙”特质,并在消费中获得社交临场感的收听体验,结合自身感悟展开次级交流,实现社会化媒体逻辑与音频传播的功能互补。[7]许苗苗认为播客平台的公共性使播客成为一种新媒介口语文化现象,其兼具电子媒体次生口语和日常原生口语的特色。作为一种新媒介口语文化现象,播客以趋同的话题预设知识背景,在碎片信息环境中吸引听觉注意力。
四、新闻播客研究
史安斌、刘长宇(2020)对普利策新闻奖增设“音频报道”奖项展开分析,总结了音频新闻的历史发展、途径的演变与实践特征;指出播客的出现提升了新闻报道内容体系结构的构建,声控智媒在内的各种技术飞跃推进了播客复兴与扩展音频新闻的传播渠道。[8]刘艳青基于5G 技术,从新闻播客在全球范围内的数量变化,全球化跨语言发行趋势,受众的年轻化,新闻内容的叙事性,广告盈利的增长与收听平台的多元化等方面对新闻播客在全球的发展进行了分析与归纳。辜晓进以纽约时报的新闻播客为例,探讨了报业播客兴盛的演进,指出新闻播客具备多任务同时执行,受众规模最大化与增强受众黏性度的能力。史安斌、叶倩提到,智能音响与车载广播等类似于声控智能设备性能的大幅提升将会使新闻播客的潜能充分发挥。王雨笋指出播客平台聚合巨大流量给音频新闻传播提供载体,听觉逻辑的复归与传播渠道进一步推进着音频新闻的发展。彭碧萍(2021)在口语文化理论背景下,探讨新闻播客借助于情景化声音景观的建构增强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也介绍了新闻播客在新闻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9]
五、播客产业与经济研究
播客产业和经济研究主要集中在播客营销和播客作为耳朵经济的探索。徐迪认为播客已成为一种具有极大盈利空间的营销工具,未来中国播客的盈利模式有网站与用户共赢模式、个性差异化定制模式及合理化增值服务模式。谢啸轩认为,播客产业发展需要应对平台和创作者探索如何扩展新用户,如何创新内容与形式,如何把握好商业化度等方面的挑战。史安斌、童桐指出新冠疫情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播客的场景价值,提高了用户消费能力与意愿来增加商业收入。赵航(2021)基于4I 理论分析播客的营销策略,指出播客精准营销应该坚持选题的创意和主播表述的趣味性,借力内容付费、播客带货与品牌节目定制实现利益共赢,利用音频社交的优势,丰富互动形式留存用户,节目内容与品牌广告和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相对接。[10]章睿探讨耳朵经济市场,指出音频播客行业成功“破圈”,扩展原有的商业模式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主要的收入来源变为吸引各行企业投放广告,内容付费模式,出版有声读物与智能设备合作而分成等。技术的发展与场景的扩展使得听众对播客的消费更便捷,播客听众的年轻化是播客市场放量增长的重要元素之一。
结语
总体而言,2011-2021 年十年来我国播客研究在研究范式、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随着播客业自身的快速发展,播客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研究呈现范围广、数量逐年增多的趋势;值得一提的是,播客研究仍有许多维度需深入探讨,如互联网视角下的移动播客研究、作为听觉文化的播客研究、播客用户研究、播客伦理研究、播客媒介史研究等;再推进一步,“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1]如我们把播客看作是一种新媒介的话,将播客置于数字化媒介生态或无边界重构的智能化生态中展开研究的话,那么关于播客的研究理应形成更多的学术想象和学术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