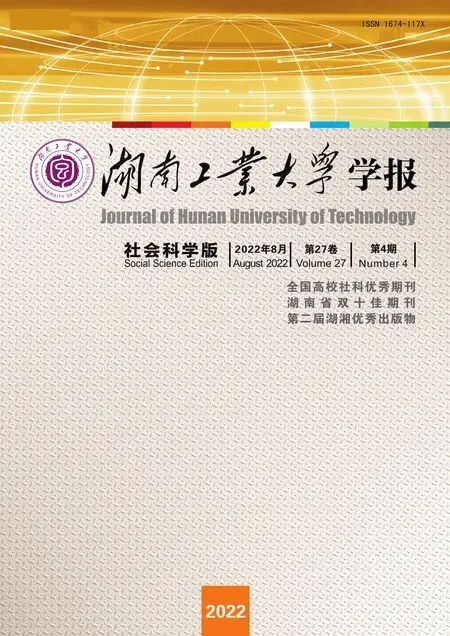《国语》中“美”的概念论析
陈望衡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国语》是先秦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其思想的基本倾向应是儒家。现在流行的《国语》版本共21 卷,计《周语》3 卷,《鲁语》2 卷,《齐语》1 卷,《晋语》9 卷,《楚语》2 卷,《郑语》《吴语》各1 卷,《越语》2 卷。据《汉书·艺文志》载,刘向编定的《新国语》为54 篇,可惜这一本子没有流传下来。《国语》记事,始于西周穆王(约公元前976 年—前922 年),迄于鲁悼公(约公元前967—前453 年)。《国语》的重要价值,一是记载了数百年的周朝的历史,二是彰扬了周朝的礼制。正是因为其所持的是周礼之立场,所以,从理论体系上看,它归属于儒家。此书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经典的地位,一些经学大家如郑众、王肃、贾逵曾为其做注,可惜这些注本均未流传下来。现在最流行的本子是三国时韦昭的注本。《国语》虽为史书,但其重在立论,书中不少论述关涉美学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美”本体相关的几个概念——文、章、和、美、貌等。
一、“文”论
“文”在中国文化理论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人们熟知的是《论语》中对文的论述。《八佾》篇云:“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8此处的“文”应该是“文明”义。《子罕》篇云:“博我以文,约我以礼。”[1]90这里的“文”,应是“文献”义。《颜渊》篇云:“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1]126此处的“文”,应是“文采”义。又,此篇有句:“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1]132此处的“文”,其义应是学术或者艺术。这些关于“文”的用法,都含有美化的意义。
事实上,文,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是一个美学概念。文,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意义,有侧重于内容的,也有侧重于形式的。侧重于内容的,并不忽略形式;侧重于形式的,也并不指纯形式。
文,与之相对立的概念是野,而与之同义的是雅。可以说,古代的文相当于今天说的美。只是较之于今天说的美,它更重视内容的真与善,更强调对世俗对功利的超越。
文,在《国语•周语》中有着深入的阐述。缘由是周室的单襄公对晋襄公的孙子公子周很有好感,在他病重之时,叫来儿子顷公,让他善待公子周。单襄公在对公子周的评论中,多处用到了“文”:
其行也文,能文能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后国。夫教,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2]75。
这段文字显然是对公子周的赞赏,核心是一个字——文。文之内涵的不同方面,各对应一个优秀的品德:
教,文之恭;
忠,文之实;
信,文之孚;
仁,文之爱;
义,文之制;
智,文之舆;
勇,文之帅;
教,文之施;
孝,文之本;
惠,文之慈;
让,文之材。
一共十一项。按单襄公的看法,这十一项优秀品德,公子周都具备了。让我们惊讶的是,《国语》将这么多优秀品德都归之于文,而且导出了文的诸多方面的性质:本-体,实-虚,帅-师,品-质,内-外,静-动,等等。
也就在此篇中,还将文用于评价周文王:“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质文,故天有胙之以天下。”[2]75
于是,文,就不只是人的优秀德行的荟萃,还是永恒天道的体现。
文,从诸多方面通向美学:
第一,“文”通向中华民族最具广义的美。在中华民族的语汇中,“文”的内涵极为丰富,但无一不见出美善,且无一不见出至尊。如果将“文”理解成中华民族所崇尚的“美”,这美就达于“神”与“圣”的境界了。
第二,“文”即艺术创作。《山海经•海外北经》中的“使两文虎也”,郝懿行注曰:“文虎,雕虎也。”[3]976《左传•宣公二年》中的“文马百驷”,杜预注:“文马,画马为文。”[3]976
第三,“文”通文饰——形式上的加工。《孝经•丧亲》“言不文”中的“文”,陆德明释曰:“文,文饰也。”[3]976文饰当其得当,有助于内容的彰显;而如其不当,则可能损害内容。
第四,“文”为文采即形式美。《孟子•告子上》中的“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朱熹注曰:“文绣,衣之美者也。”[3]977
“文”在汉语中,具有极强的构词能力,它所构成的词,均在突出主题意义时,又从不同方面传达出审美的意味,从而使中国文化弥漫着浓重的审美情调。
二、“章”论
“章”,也是重要的美学范畴。
《周易》最早从美学意义上运用“章”。《周易》坤卦六三爻辞云:“含章可贞。”孔颖达疏:“章,美也。”[3]1657
《国语•周语》中《定王论不用全烝之故》篇,比较详尽地说到了“章”:
夫王公诸侯之有饫也,将以讲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服物昭庸,采饰显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顺,容貌有崇,威仪有则。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饮食可飨,和同可观,财用可嘉,则顺而德建[2]52。
这段文章的背景是议论王公诸侯宴饮的礼仪,提出“讲事成章”。“讲事”是议论礼仪之事,而“成章”,即要求将礼做成可以观赏的“章”。据《说文解字》:“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4]58原来,章本是一阙音乐作品。当“章”借用指称他物时,“章”原本具有的审美性并没有消除。当一件事,要求其“成章”,就意味着,它应该像一章乐曲那样完整与美好。
上段引文中,谈到诸多的“章”。有服饰,有行为,有容貌,有饮食等。从它的具体描述,可以概括出“章”的几个要点:
第一,“章”须有象。“文章比象”,指可以让人感受到——或视,或听,或触,或闻。
第二,“章”须显明。“采饰显明”,指具有一定的感官冲击力。
第三,“章”须有法度。指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均“周旋序顺”,法度分明。
第四,“章”须具有礼的庄严。指其体现在人的修饰上,则“容貌有崇,威仪有则”。
第五,“章”的法则须有哲学的高度。具体来说,就是要达到阴阳五行哲学的高度,做到“五味实气,五色精心,五声昭德,五义纪宜”。
第六,“章”的总体性质为完善。此完善称之为“可”,具体可分为:(1)功能上的“可”,如是“饮食”则“可飨”,如是“财用”则“可嘉”。(2)审美上的“可”:“和同可观”。“和同”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可观”指感性上的愉悦。(3)品位上的“可”。合乎礼制,“顺而德建”。
以上这六点,几乎概括了“章”的基本性质与特征。
在中国美学中,“章”与“文”都能作为“美”的代名词,但在具体语境中,它们对于美的表述则会有所不同。
三、“和”论(上)
“和”是中国美学的重要范畴,它在诸多意义上与美学相关。其一,它是乐的基本性质;其二,它也是美的基本性质。《国语》中有诸多关于和的论述。
《国语•周语》中《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钟》一篇着重论述乐之和。
(一)乐从和平
此篇中,乐官伶州鸠对周景王说:
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诗以道之,歌以咏之,匏以宣之,瓦以赞之,革木以节之。物得其常曰极,极之所集曰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逾曰平[2]94。
这是对“乐从和”最全面的阐述。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和,二是平。和为和谐。乐是多种艺术手段包括丝竹、诗、歌、匏、瓦、革、木共同配合的产物。平,是和的升华。和,只需“声应相保”就可以了。所谓“声应相保”,就是彼此配合,即丝竹、诗、歌、匏、瓦、革、木等艺术手段相互配合,它无需考虑到欣赏主体。而平,则需要考虑到乐与主体的关系,只有能够让主体很好地接受、感到快乐的乐才是平,即所谓“细大不逾曰平”。
和乐的产生来自客体内部诸因素的和谐,平声则不仅如此,还需加上和乐与主体的和谐。调控这个过程的重要手段是“律”。
(二)和通阴阳
乐是人工制作的声音,当其为和平之声时,它与自然、社会的和道是相通的。伶州鸠接着说:
如是,而铸之金,磨之石,系之丝木,越之匏竹,节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风。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2]94。
古人将乐器分成八类,名之为“八音”。和乐演奏起来,八音就与大自然的“八风”相应和。这虽是古人的一种感受,却又寓有天人合一的哲理。在古人看来,八音和平是阴阳和谐的体现,自然界以阴阳和谐为常,而“物得其常曰乐极”。物得其常,就是四季分明,风调雨顺,万物兴盛 (《国语•郑语》中有句“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虞幕”,舜的祖先,“协风”即和风。“成乐物生”,成就快乐也成就万物)。于人来说,无灾无祸,生产丰收,万事顺心,那就是福,称得上“乐极”。于人曰乐,于物则曰备。“物备”,“乐成”(快乐的乐与音乐的乐是相通的,乐成既是乐音的成就也是快乐的成就)。自然与人、生态与文明双赢。这就是古人所梦想的美好世界吗?
(三)和通治国
中国古代文化道德意识很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会联系到道德,而道德问题的最高指向则是治国平天下,伶州鸠论和也不例外。他说:
夫政象乐……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于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宁,民是以听。若夫匮财用、罢民力以逞淫心,听之不和,比之不度,无益于教而离民怒神,非臣之所闻也[2]94。
和平之声,表达的是中德的思想,吟咏的是中正的音乐。中德,纯正的道德。中德之声就是德音。德音自然不会有任何差池,必然合于神人。在中国文化中,神与天命往往是一个概念。神根据君主的作为,或赐福祉,或降灾殃,由此决定着政权的更迭。
这里,它强调和平之声不仅“合神人”,而且“神是以宁”。神是不是宁,与声是不是和,有着直接联系。神宁,民也宁,国也宁;神怒,民就离,国也散了。
(四)和通审美
关于和与审美的关系,在伶州鸠发表高论之前,大臣单穆公已经发表了重要的观点。他说:
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明则德昭。听言昭德,则能思虑纯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归心焉。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然则能乐。夫耳内和声,而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乐之至也[2]93。
“乐不过以听耳”,“美不过以观目”,这里说的是审美,而且注意到了感觉在审美中的作用。单穆公是从正反两面来谈音乐的审美的。
从正面来说,可以见出三个层次:其一,悦耳悦目。听到和声,耳朵舒服;看到美色,眼睛舒服。其二,增智昭德。“耳目,心之枢机也”,因此“听和则聪”,“视正则明”,“聪则言听”,“听言昭德”。到这阶段,就不只是感觉舒服,还能得到智慧与德行的提升。其三,忠君爱民。听到这样的音乐,国君“以言德于民”,“口出美言,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做到爱民。其 “民歆而德之”,归心朝廷,而且“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做到忠君爱国。
从反面来说,“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2]93-94即如果出现反面的情况,音乐审美就不仅没有感官的愉悦可言,而且会令人头脑晕眩,精气焕散,言语狂悖,行为乖讹,进而影响国家:“出令不信,刑政放纷”,“民无据依”“上失其民”。社会因此而动荡。
四、“和”论(下)
在《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中,史伯在与郑恒公纵论天下大势之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观点:
公曰:“周其敝乎?”对曰:殆于必弊者也。……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488。
史伯从政治入手,认为周王室必衰,原因是周王专喜好与他一样的小人(“谗慝暗昧”“顽童”),而拒绝与他不一样的正人君子(“高明昭显”“角犀”)。对此,史伯归结为“去和而取同”。然后,他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观点。“和”与“同”,在中国先秦文化中是区分得很清楚的两个概念。《左传•昭公二十年》云:“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也……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5]4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141
史伯关于“和”的论述,突出了这样一些要点。
(一)和的生物功能
一物生一物是不可能的,和之所以能生物,是因为它是由多元素组成的,是杂。上段引文后,有这样的话:“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物之生,是多种元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和”能生物,因为和是质变,质变才生物;同不能生物,因为同是量变,量变不生物。
(二)和的创美功能
史伯在他的论述中,有这样的句子:
是以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2]488-489。
“以五味以调口”,说的是味觉的美感;“刚四支以卫体”,说的是身体的美感;“和六律以聪耳”,说的是音乐的美感;“正七体以役心”,说的是全部感官的美感。
由和所创造的美,史伯表述为“和乐如一”。和乐如一,就是和乐统一。和,侧重于说审美对象,它是多元的统一;乐,侧重于审美主体,他的感受是乐——愉悦。和乐统一,就是审美中主客体的统一。“和乐如一”也是“和之至”。之所以是和之至,是因为它不只是客体的多元统一的和,而且还是主客体相统一的和。基于这种和的突出特征是乐,因此,它是审美的。在这里,史伯实际上表达了他的一个重要观点:审美的和才是最高的和。
“同”不具审美效果:“声-无听”——声不中听;“物-无文”——物不中看;“味-无果”——食不中吃;物-不讲——物就根本没有办法去评说它的审美品位。
(三)和为天地功能
史伯关于和的论述涉及到自然。他说的“和实生物”,是指天地的功能。天地间,物与物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生态关系,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生死灭绝的各种战争,既循环不息,又绝不重复。新陈代谢,万千变化。事物之间的关系有时残酷,有时又不乏温馨。而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这种生态大战的最高原则是“和”,不是空空洞洞的和,而是实实在在的和。“和”的极致是“平”。“平”不是整齐,而是生态的公正、生态的平等、生态的平衡。史伯的表述是“以他平他”。这里所谓以他“平”他,是指按照公正的生态原则,事物在相互关系中实现着生态的平衡,其最终的成果是 “丰长物归之”。一方面,万千世界,兴旺发达;另一方面,则九九归一,规律了然。这就是宇宙的美、最高的美。
(四)和为政治功能
史伯论和,立足于政治。他追溯历史,认为虞、夏、商、先周之所以能创造政治上的辉煌,是因为他们坚持了“和”的治国理政原则:“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2]488再联系到当时的情况,他认为当时周王室的治国理政,已经完全抛弃了和的原则。于是,他对郑桓公应该如何治国理政进行了切实的指导,试图让郑桓公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五、“美”论
中国古代文化中,论美的言论并不多,对美的论述,多附属于对伦理、自然、器具等问题的论述之中。不过,在先秦《国语•楚语》中记录的楚国大臣伍举有关美的议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相当于给美下了定义:
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2]512。
虽然此语相当于给美下定义,但伍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论美。上引的类似为美下定义的句子,相当于逻辑学三段论式中的大前提,小前提是章华台,结论是章华台“胡美之为”?尽管如此,从伍举的论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对美有相当系统的认识。
(一)美的基本性质——无害
无害,当然是无害于人。是哪些方面的无害?伍举提出四个方面:上下、内外、小大、远近。这四个方面,囊括了美的基本性质。
无害可以作两个维度的理解。其一是最低线,美不应有害于人;其二是最上线,美具有超功利性。超功利,似是无功利,实是有功利,然而此功利不局限于物并超越了物,进入了精神境界因而高于物;而在精神境界中它也超越了真,也超越了善,因而高于真善。
(二)美与观
伍举论章华台,也谈到了美与观的关系。“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2]512他没有完全否定观,只是否定唯观。事实上,审美是离不开观的,但如果观超出一定的限度,它就会妨害乃至破坏物的审美性质。伍举说:
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2]512。
伍举肯定了四种正面价值:服宠(受到国民的尊崇)、安民、听德、致远,而否定与之相对的四种负面的价值,这四种负面的价值都涉及观(广义的观包括所有的感知及心观)。伍举所谓四观,具体而言就是:“土木之崇高、彤镂”之“美”——视观;“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之“乐”——听观;“观大、视侈、淫色”之“明”——视观兼心观;“察清浊”之“聪”——视观兼心观。
从伍举的这些论述来看,他否定的是超出一定限度的观。而这,也是对的。审美固然离不开观,但不能唯观。唯观必伤人,伤人即有害,有害就说不上美了。《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5]29在这点上,《国语》与《老子》是一致的。
(三)美与利
美要不要讲利?伍举对此有分析。
美的事物,它本有功利。这里,涉及艺术物与实用物的区别。
1.实用物:美在真实功能的完善体现。实用物不论是生产实用物,还是生活实用物,都是有功利的,只有以功能为本,才谈得上美。对于实用物来说,美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实用物的美,根本的,在于其功能。功能由它的形式(内在结构、外在形象)来实现。功能与结构与形象完全一致。伍举说:“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讲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2]513这是以先王例。伍举说,先王建造台榭,榭不过是用来讲习军事,台不过是用来观望气象吉凶,因此,榭只要能在上面检阅士卒,台只要能登临观望气吉凶就行了。这说得没错。因为对于实用物来说,装饰可有可无。可有,是指如果财力无问题,又希望增加审美,可以增加装饰;可无,是指如果财力有问题,就无须增加装饰。
对于实用物来说,第一选择是无装饰,这种情况下,功能与形式完全统一,功能即形式(广义的形式)。这样的美通常用“简单”来表述,简单是最高的美。在这个意义上,美即功能的完善实现。伍举推崇的就是这种美。
2.艺术物:美是虚拟功能的真实体现。艺术物情况有些不同。艺术作为虚构,它是没有现实功能的,就这点而言,它无功利性,但是,艺术物也需要以功能为依托,只是这依托是虚拟的。没有功能为依托的艺术物,它首先就是不真实的,不真实就谈不上美。伍举没有谈到这种美,他不试图全面地论美,因此,这种忽略也可以理解。
(四)美与德
伍举反对造章华台。他真实的想法,是因为章华台建得太奢华了。在他看来,作为君王的宫室,不必要建得这样豪华、这样高峻、这样气派,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君王实用的功能。按他的审美标准,章华台不是功能的完善体现,而是形式大于功能,故不美。而按善的评价标准,章华台浪费了大量的财用,是为不善。伍举说:“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百官烦焉。”这是典型的劳民伤财工程、败家子工程。
这种豪华的工程虽然具有一种炫目的形式美,但这种美不是善的体现,而是恶的体现。最直接的,它体现君王无德。这种无德之形式美,还是不是美?当然不是了。伍举否定了这种美。这种否定,基于美的本质。这本质就是上面所引:“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当然,如果不是基于美的本质,而是将美就看成形式美,这种否定就不成立了。但必须强调的是,自古以来,无论中外,对于美的认识,均兼顾内容之善,而且将善看成美的内核,仅以形式论美者少之又少。
《国语•周语》“密康公母论小丑备物终必亡”一篇也谈到美与德的关系。文中说,密康公(西周一个小诸侯国的国君,属地在今河南密县)跟从周恭王去泾水边游玩。有三位美丽的女子私奔密康公,密康公的母亲劝道:“女三为粲……夫粲,美之物也。从以美物归女,而何德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2]5这里说的也是美与德的关系,但不是形式美与内在德行的关系,而是指美物与占有者品德的关系。在《国语》作者看来,有德者方可持美物,美归属于德。密康公的母亲认为,三女为粲,粲为美物,这样的美物只配有德之人,连周王都不配,你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君,无德缺才,是小人物,又哪配享受这样的美物呢?密康公不听,将三女纳了,结果一年后,周王将密国灭掉了。
(五)美与礼
美与善的关系,不仅涉及德,而且涉及礼。礼虽以德为依据,但更多地注重国家的利益。德与礼对人都有约束作用,德在心理自律,礼在制度他律。《周礼》中对诸侯宫殿的大小有着严格的规定,章华台的规模严重地破坏了这种规制,它超标了。《国语•楚语上》中说,楚灵王为了显示国家的强大,慑服他国,在灭掉陈国、蔡国、不羹(楚地名)国之后,加修了城墙,城墙很有气派。他派人去询问楚国大夫范无宇,这样做好不好。范无宇说:“国为大城,未有利者。”[2]516范无宇之所以如此回答,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章华台不合礼制。
在春秋战国年代,破坏礼制的事太多,时人谓之“礼崩乐坏”,孔子对此痛心疾首,曾狠狠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伍举的议论中,没有明确地提到礼,大概也是基于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他对章华台的批评,实际上也是以礼制为基准的。他说:“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而以伯子男为师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望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2]512-513这里说到天子之贵,在于“以公侯为官长,而以伯子男为师旅”,说的就是礼制。“施令德”让百姓安居,说的更是礼制。
先秦是一个讲礼制的时代,以礼为善,以礼为美,这是社会的共识。
在先秦,论美的言论不少,但真正能作为定义用的,除了《国语》中的伍举论美,还有就是《孟子》的论美。《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6]334这里说了“善”“信”“美”“大”“圣”“神”等若干相关的概念。“美”之前有“善”“信”,大概“美”以“善”“信”为基础;“美”之后有“大”“圣”“神”,大概“美”的升华则为“大”“圣”“神”。将这段话与伍举论美比较,不难发现,它们有共同点,也有相异点。共同点是,它们都重视美的基础或内涵,这基础或内涵是“善”(包括德、礼、利)、“真”(信);他们都没有忽略美在形式上的特点——可观。不同点在于伍举论美,基于美的底线——“无害”;而孟子论美,则追求“美”的上线——“大”以及“美”之上的“圣”和“神”。孟子说“充实之谓美”。他认为,充实是善与信的充实,善与信的充实既有内容又有形式。“大”是“美”的升华,其突出特点是不仅充实,而且“有光辉”。这“有光辉”为美升为“圣”“神”奠定了基础。“圣”虽然伟大至极,但还可知;到神时,就是更伟大而不可知了。
伍举论美,比较平实,没有孟子的思辨深度,也没有孟子这样的准宗教意识。他的基本立场是,美应该无害有利。无害有利,既是对民而言,也是对国而言,对君而言。应该说,伍举论美,具有最大的可接受度,是中国人最为朴素的审美观。
六、“貌”论
中华文化中,评论人物外貌美的言论不是很多,《国语•晋语》中“宁嬴氏论貌与言”一篇算是少见的论貌有深度的文章。
这有一个故事。晋国大夫阳处父出差卫国,返回路上,经过宁这个地方,住进宁嬴氏客栈。宁嬴氏对他的妻子说:“我一直在寻找有德行的君子,今日算找到了。”于是,就跟阳处父上路了。在路上,他与阳处父有过交谈;但走到温山后,他就不再跟从阳处父了。回到家后,妻子说:“你找到了心仪的人,还不跟从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呀?”宁嬴氏就说了下面这番话:
吾见其貌而欲之,闻其言而恶之。夫貌,情之华也;言,貌之机也。身为情,成于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也。若内外类,而言反之,渎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机,历时而发之,胡可渎也!今阳子之情譓矣,以济盖也,且刚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惧未获其利而及其难,是故去之[2]353。
这段文字主题词是“貌”,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词是“言”。宁嬴氏的总体意思是清楚的:貌与言是两回事。阳处父面貌好,让人喜欢,而言语糟糕,让人厌恶。
这涉及怎样对人进行审美评价的问题。《国语•晋语》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有层次的分析。
(一)外貌美的价值
1.外貌美的吸引力。“貌,情之华也。”情,人的内在情性。内在情性,通过身体展露于外,这之中,面貌最重要,它是“情之华”。华者,花也,比喻为精萃,即通常说的精华。面貌既然是情性之精华,其重要性可以想见。因此,面貌是否让人看着舒服,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从这看,《国语》给予面貌美以最大的肯定。事实上,宁嬴氏开初就是因为阳处父长得相貌堂堂,从而决定跟随阳处父的。
2.外貌美的独立性。肯定外貌美的价值,显示出先秦时代的人们对外在形式美有了初步的觉醒。具体为二:外在形式美有其构成规律,也有其评定标准,这种规律、这种标准独立于德之外;外在形式美有其独立的价值,它可以让人悦耳悦目、让人舒心。
(二)外貌美的局限
虽然外在形式美具有独立性,但这独立性,是有一定的限度的,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1.外貌美受到言的控制。宁嬴氏向他妻子说了“貌,情之华也”之后,紧接着说:“言,貌之机也”。机,枢也。说言是貌的机枢,就无异于说,言能够控制貌。言为何能控制貌?这涉及对貌的认识。貌有自然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自然性的一面来自先天,它是无法更改的,具有客观性;社会性的一面,来自后天,它是可以调控的。貌的社会性,为整个社会文明所决定,社会文明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外貌美的基本标准,而个人文明修养又决定着其外貌在什么层次上接近外貌的社会标准。人的社会性内在于心理,外在于言行。容貌的先天性,构成人的容貌的基础,容貌的美一部分来自于这种先天性。宁嬴氏初见阳处父,为其貌所吸引而决定跟从他,这里的貌即是先天性的丽质。但是,在跟随阳处父一段时间后,通过与他对话,宁嬴氏发现他的言语粗恶。这粗恶的言语,一方面反映出他内心的黑暗与肮脏,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的容貌。换言之,他话语中的粗恶让他天生美好的容貌受到扭曲,使得这张脸变得难看了。这就是“言,貌之机也”的内涵。
2.外貌美受到行的控制。外貌美不仅受到言的控制,而且受到行的控制。这方面,宁嬴氏没有多谈,但是,也涉及到了。因为言与行是密切相关的。他说阳处父“刚而主能,不本而犯,怨之所聚”,意思是说阳处父做事刚决,但没有能力,没有底线,总是犯规,集怨甚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阳处父正是因为做事不慎,最后被晋国的中军统帅狐射姑杀了。
(三)人美的综合性
问题归结到如何看待人的美,从宁赢氏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的美具有综合性。
1.身与心的统一性。身可以看见,是人美之外在方面;心不可以看见,它是人美的内在方面。宁嬴氏说:“身为情,成于中”,意思是身体为情状,此情状能不能够“成”,即为人所肯定,决定于“中”,即心中。只有心中有善有慧,方能让身展现出良好的情状。
2.言与身的统一性。宁嬴氏说:“言,身之文也。言文而发之,合而后行,离则有衅。”这里的“身”不只是指身体存在,还包括身体的行动,可以概括为“行”。说言是身之文,可以理解为,言不只是行的表达,还是行的修饰。“言文”即漂亮的话,当其表现为行动之时,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言文”与行为“合”,这种情况下,它是好的;另一种情况是“言文”与行为“离”,这种情况下,它就“衅”——出问题了。
3.貌与言的统一性。关于貌与言的统一性,宁嬴氏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内心与外表的统一性。宁嬴氏说:“若中不济,而外强之,其卒将复。中以外易也。”意思是,如果心中不够强大,而外表显得强大,那么这个人最终要覆灭。二是貌与言的统一性。他说:“若内外类,而言反之,渎其信也。”如果中情和外貌相类,而言辞却与之相反,那就会使诚信受到亵渎。阳处父就是这种情况。宁嬴氏说:“今阳子之貌济,其言匮,非其实也。”即阳子相貌堂堂,但言语跟不上,不副其实。这里说的就是貌与言不具统一性。
统观宁嬴氏之“貌”论,概括起来有三个要点:其一,貌是重要的,貌美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其二,言比貌更重要,言可以克服貌的吸引力;其三,言的重要是因为它是心之声。归根结蒂,心才是决定性的。
与《晋语五》宁嬴氏论貌相呼应的有《晋语八》智果论智瑶。晋的卿大夫智宣子想立他的儿子智瑶为继承人,向晋大夫智果征求意见。智果说:“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2]480智瑶比别人强的有五点:“美鬓长大”,相貌好;“射御足力”,武艺好;“伎艺毕给”,技艺好;“巧文辩慧”,言语好。“四贤”中,“美鬓长大”摆在第一位,足见智果对貌的重视。智瑶优点很多,但有一不好,就是“不仁”。因为不仁,他必不能取信于人。如果他继承智氏的禄位,智氏宗庙必灭。 “不仁”就是心坏。论人,最根本的是论心,心若坏,貌再好也没用,一切都谈不上。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关于貌的问题,数《国语》论述得最为充分。《国语》的“美”论,几乎集先秦儒家“美”论之大成,只可惜诸多美学史只是摘引其片言只语,对其整体没有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