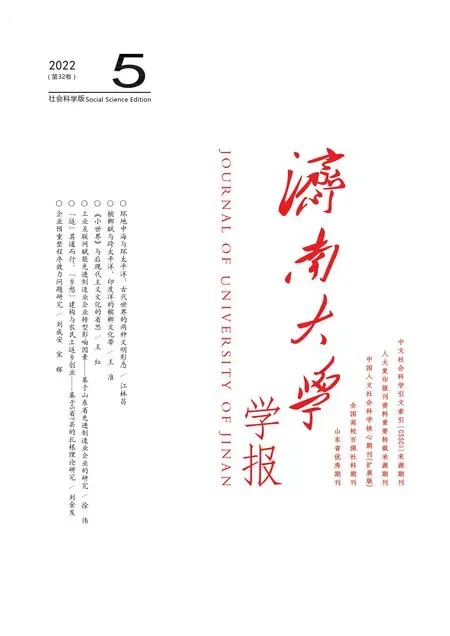槟榔赋与跨太平洋、印度洋的槟榔文化带
王 准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在众多描写槟榔的辞赋作品中,明林鸿《槟榔赋》,明黎遂球《槟榔赋》,清张汉《滇槟榔赋》和清王必昌《台湾赋》等辞赋中涉及槟榔的部分都反映了槟榔这一植物的生长习性和文化内涵。将这些辞赋作品与文献记载相比较可知,槟榔文化是一种与槟榔有关的,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嚼食槟榔的习俗亦是一种具有显著地域特征的饮食民俗。而与这一民俗文化相对应的是一个地域广大的槟榔文化带。槟榔食俗持续、深入的影响辞赋创作,不断充实着赋体文学的文化内涵。
一、赋体文学对槟榔的早期记载
槟榔是棕榈科常绿乔木,原产于东南亚,在我国广东、云南、福建、台湾均有栽培。其果实有食用价值。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对槟榔的记载与描写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司马相如《上林赋》。该赋在描写上林苑植物时有:“留落胥邪,仁频并闾”(1)萧统编:《文选》,李善等注,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0页。之句。李善注云:“孟康曰:‘仁频,椶也。’《仙药录》曰:‘槟榔,一名椶。’然仁频即槟榔也。”(2)萧统编:《文选》,李善等注,卷八,第160页。又《史记· 司马相如列传》裴骃《集解》:“频,一作‘宾’。”司马贞《索隐》:“姚氏云:槟,一名椶,即仁频也。”(3)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9册,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卷一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30页。《索隐》又曰:“《林邑记》云:‘树叶似甘蔗’,频音宾。”《辞源·人部》解释“仁频”为槟榔的别名。结合古今各种注释可知槟榔在古代有“仁频”、“椶”等不同名称。
关于槟榔的记载首见于《上林赋》,与汉王朝平定南越国的军事行动有关。《三辅黄图》载:“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甘蔗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4)佚名:《三辅黄图》,卷三,(清)毕沅校注,《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26页。古代南越国统领区域涵盖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中、北部,临近槟榔原产地东南亚,使槟榔等物种得以输入中原。
而汉王朝平定南越并设郡管辖的历史无疑使南越地区与汉王朝之间的人员、物资往来日益密切,食用槟榔的习俗也开始传播。有学者指出:“汉武以来,交趾、日南成为中国郡县者数百年,汉人官吏商旅客居其地者渐多,亦渐习于嚼槟榔之俗,并渐传其俗入于乡土。”(5)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附二·蜀蒟酱入番禺考》,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有学者认为:“很多植物虽然未出现于正式的历史或产业文献,但汉赋、汉诗中却有引述,显示这类植物在汉代或汉代之前就已引进中国,并且已普遍栽植”,槟榔即是其中之一(6)潘富俊:《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483页。。由以上记载、研究可以确定槟榔大约在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开始引入中国,中国人食用槟榔亦或由此时开始。
西汉后则有西晋左思《三都赋·吴都赋》曰:“其果则丹橘、余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叶无荫。”(《文选·三都赋》)刘良注曰:“槟榔树高六七丈,正直无枝。叶从心生,大如楯。其实作房,从心中出。一房数百实,实如鸡子,皆有壳肉满。壳中正白,味苦涩,得扶留藤与石贲灰合食之,则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文选·三都赋》)《三都赋·吴都赋》注释较详细,涉及槟榔之形貌、口味、食用方法、产地等信息。
此外,东汉以来的方志、类书、史料笔记等对槟榔亦多有记载,东汉杨孚《异物志》:“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若桂。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瘣木焉……剖其上皮,熟(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7)杨孚著,曾钊辑:《异物志》,卷下,《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载食用槟榔之习俗曰:“(槟榔)叶下系数房,房缀数十实,实大如桃李。天生棘重垂其下,所以御卫其实也。味苦涩,剖其皮,鬻其肤。熟如贯之,坚如干枣。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则滑美,下气消谷。出林邑,彼人以为贵。婚,族客必先进。若邂逅不设,用相嫌恨,一名宾门药”(8)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下,《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从这两段记载来看,东汉时人们对槟榔的药用价值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唐宋史籍亦有对槟榔的记载,唐樊绰《蛮书·云南管内物产》载:“荔枝、槟榔、诃黎勒、椰子、桄榔等诸树,永昌(今云南保山、腾冲、缅甸北部等地)、丽水(今缅甸打罗)、长傍(今缅甸拖角)、金山(地名待考)并有之。”(9)樊绰撰:《蛮书》,向达原校、木芹补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又《太平御览》引唐韦齐休《云南行记》云:“云南有大腹槟榔,在枝朵上色尤青,每一朵有二三百颗。又有剖之为四片者,以竹串穿之,阴干则可久伫。其青者亦剖之,以一片蒌叶及蛤粉卷和嚼,咽其汁,即似咸涩味。云南每食讫,则下之。”(10)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合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云南行记》又曰:“云南有槟榔,花糁极美。”(11)王叔武:《云南古佚书钞合集》,第27页。又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的记载凸显了槟榔的药用价值,为《本草纲目》所转录。该书提到槟榔首要的功效是“御瘴”,其次又有提神、醒酒和助消化之效。而岭南人“以槟榔代茶”的特点,则说明槟榔可用于日常交际并开始逐渐融入士大夫日常生活,他们以物比德,为槟榔赋予一种中正仁厚的君子人格(12)参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47页。。又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槟榔。生黎峒。上春取为软槟榔,夏秋采干为米槟榔。小而尖为鸡心槟榔,扁者为大腹子,悉能下气,盐渍为盐槟榔。琼管取其征,居岁计之半,广州亦数万緡。自闽至广,以蚬灰、蒌叶嚼之,先吐赤水如血,而后嚥其余汁。广州加丁香、桂花、三赖子,为香药槟榔。”(13)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不分卷,孔凡礼点校:《范成大笔记六种》,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6页。由此可知槟榔因为采摘季节、后期加工方法等的不同而品种各异,其食用方法在同一地区更是有所差别,同时槟榔在南宋时不仅是人们的日常所需,还是一种税收来源。
明清两代关于槟榔的记载除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外,更有清番禺(今广州)人赵古农《槟榔谱》这一关于槟榔的专书出现。而随着清王朝收复台湾和对台湾岛的开发,台湾出产、嚼食槟榔的习俗也同样见诸清代文献,清周玺《彰化县志·物产志》载:“槟榔,树直无枝,高三四丈。皮类青铜,节似筠竹。叶皆上竖,临风旖旎。叶脱一片,内现一包。数日包绽,即开花。淡黄白色,朵朵连珠,香芬袭人。实附花下,形圆而光,宛若枣形。一穟数百粒。秋末采食,至三、四月乃尽。和荖叶灰夹食之,能醉人,可祛瘴。”(14)周玺:《彰化县志》,清道光十六年(1836)本,卷十,台北:大通书局,1977年版,第322页。这些记载在前代基础上大大丰富了有关槟榔的史料。
虽然《上林赋》最早记载并描写了槟榔,但仅寥寥数语,两汉、魏晋辞赋对槟榔也只是偶有涉及,唐以前的文人更多关注槟榔的植物属性而非将其视为带有某种寓意的文学意象。有学者认为槟榔在唐以后被视为文学意象,主要受到晋宋之交刘穆之食槟榔之事的影响。指出:“唐代诗人李白率先将此事写入诗中,为槟榔典故在古典文学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代文人则在创作中从多个角度去阐发刘穆之求食槟榔这一历史事件,将槟榔与人生观、功名观和亲情观等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槟榔这一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蕴藉更为丰富。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槟榔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植物学意义到文学意义上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在明代基本完成。”(15)吴春秋:《试论古典文学中的槟榔》,《海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而这种转型不仅影响了诗歌,也影响了辞赋,明清两代槟榔赋的大量出现足以证明槟榔作文学典故与文学意象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其所涵盖的文化内蕴也得到了更多发掘。
总之,原产东南亚的槟榔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后传入中国,司马相如《上林赋》首次记载槟榔。随着槟榔的传入,食用槟榔的习俗也在一些人群、一些地区开始出现并逐渐推广开来。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槟榔的药用价值首先被先民们发现,进而成为日常食用之物。这种特点,符合中国食药同源之传统。而在药用价值之外,人们也将槟榔与其他物品混合嚼食达到促成爱情、增进友谊等效果,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而槟榔也经历了一个从植物逐渐转变为文学典故、意象的过程,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浓厚兴趣,形成了包括《槟榔赋》在内的文学创作。
二、槟榔赋的地域文化特色
华南、西南、华东等地为槟榔在中国的主要产地,食用槟榔的习俗在这些地区普遍存在。明清两代出现了专门描写槟榔的辞赋、诗歌等文学作品。目前已知的辞赋创作中,明林鸿《槟榔赋》、明黎遂球《槟榔赋》、清张汉《滇槟榔赋》和清王必昌《台湾赋》等辞赋中有关槟榔的描写较有代表性,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林鸿、黎遂球《槟榔赋》与岭南槟榔文化
以广东、海南和广西部分地区为代表的岭南地区,是槟榔文化较为典型的区域。历史上出现了不少以槟榔为题的诗作,如北宋苏轼流放岭南时,作《食槟榔》一诗云:“中虚畏泻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妩媚。”(16)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卷三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52页。南宋杨万里《小泊英州》诗云:“人人藤叶嚼槟榔,户户茅檐覆土床。”(17)杨万里:《南海集》,卷一五,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768页。而在辞赋中,明黄佐《粤会赋》叙广州之槟榔曰:“椰浆醉客,侑以槟榔”(18)陈元龙:《历代赋汇》,卷三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又明邱濬《南溟奇甸赋》述海南岛之槟榔曰:“椰一物而十用其宜,榔三合而四德可取。”(19)陈元龙:《历代赋汇》,卷三八,第166页。而明林鸿《槟榔赋》则是明代辞赋中专门描写岭南槟榔的佳作之一。其文曰:
世有异物,产于炎方。既坚且实,名曰槟榔。挺根株之特达,抽枝干之芬芳。披烟云于海岛,霑雨露于遐荒。体团圆而如玉,质文采而成章。落冰刀之雪白,起柔壳之丹黄。味兼灰蒌之美,液凝齿颊之香。岂中华之所尚,实南海而见尝。乃椰子之是类,与豆蔻而同乡。其生也,匪桃李之礧磈。其熟也,若橘柚之焜煌。嚼之则吐红而点地,吞之则汗流而成浆。无琳无琅,非璧非璋。花先月桂,叶似桄榔。
狼蛮以之而为礼,珠崖以之而为良。至若瘴烟乍敛,海天微凉。雕题黑齿,蜑髻黎裳。莫不奔走兴贩,摘曝盈仓。或肩挑而背负,或舟载而车装。于以订婚礼,于以献庙堂。是皆风土之夸羡,日日喜啖而不可忘也。乃拜手嵇首,复为之歌曰:“琼山高歌兮如屏,琼海流兮有声。槟榔生兮满林,妙结实兮为祥为祯。”再歌曰:“琼山青兮峨峨,琼海流兮波波。槟榔生兮孔多,为祯为祥兮千秋不磨。”(20)马积高:《历代辞赋总汇·明代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4—4815页。
林鸿《槟榔赋》整体上四六相对,短小简洁而又凝炼雅致,文体属于骈赋一类。作者首先描写槟榔树形挺拔、枝繁叶茂的总体特征,继之以槟榔的生长环境,而槟榔果实特征和口感则是描写重点。赋中的“南海”“珠崖”“琼海”等地名显示《槟榔赋》所写为海南岛之槟榔。该赋不仅详实反映琼人嚼食槟榔的习俗,而且生动刻画琼人售卖槟榔的情况。在作者笔下,海南岛槟榔产量之大,用途之广为其它地方所不及。说明海南槟榔在古代即是美名远扬,众人皆知的特产,通篇洋溢着作者对地方风土物产的礼赞。
而林鸿《槟榔赋》的描写与古代文献记载多有相似之处,比如南宋赵汝适《诸蕃志》对海南槟榔的记载:
槟榔,产琼州。以会同为上,乐会次之。儋、崖、万、文昌、澄迈、安定、临高、陵水又次之。若琼山则未熟而先采矣。会同田腴瘠相半,多种槟榔以资输纳,诸州县皆以槟榔为业。岁售于东西两粤者十之三。于交趾、扶南十之七。以白心者为贵……三四月开花绝香,一穗有数千百朵,色白味甜,杂扶留叶、椰片食之,亦醉人。实未熟者曰槟榔青,青,皮壳也。以槟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芬芳,琼人最嗜之。熟者曰槟榔肉,亦曰玉子。则廉、钦、新会及西粤、交趾人嗜之。熟而干焦连壳者曰枣子槟榔。则高、雷、阳江、阳春人嗜之。日曝既干,心小如香附者曰干槟榔、则惠、潮、东莞、顺德人嗜之。(21)赵汝适:《诸藩志》,卷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29页。
上述记载与林鸿《槟榔赋》的描写有共同之处。《诸蕃志》中槟榔在海南各地大量种植的记载印证了林鸿《槟榔赋》关于海南盛产槟榔的描写,而《槟榔赋》重在描写有关海南当地人售卖槟榔的场面,与《诸蕃志》中海南槟榔售于两广以及域外国家的情形有一致之处,证明海南槟榔在古代是地区贸易中的重要产品而备受重视。也说明槟榔之所以在海南岛、两广以及海外畅销,与其自身独特的口味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起到的促进感情(订婚礼)、沟通人神(献庙堂)的作用大有关系。
而林鸿《槟榔赋》提到以槟榔为礼的“狼蛮”,和贩卖槟榔的“蜑髻黎裳”等居民。“狼蛮”是明清时分布在广西、广东一带的独有民族,而“蜑髻”与“黎裳”则是海南岛的两类主要居民,“蜑”又作“疍”,泛指生活在今福建、广东沿海的水上居民,源于古代百越民族,后逐渐融入汉族。“黎裳”则是海南之黎族。从《槟榔赋》的具体描写来看,海南岛的黎族等居民既是槟榔的贩卖者,又是消费者,槟榔在海南人特别是黎族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且影响了海南、广东等地的其他民族。《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海南卷》一书指出:“种槟榔,吃槟榔,送槟榔,原为古越人、黎人的习俗,明清时期逐渐为汉人所接受。此时期,送槟榔、吃槟榔已融入汉文化内涵,据考究,‘槟榔’乃‘宾郎’的谐音词,宾与郎均为对客人的尊称,以槟榔待客或彩礼,象征礼貌和吉庆。”(22)袁行霈、陈进玉、符和积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海南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0—311页。今人的相关研究无疑可以印证林鸿《槟榔赋》中海南各地、各民族广泛存在的槟榔食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阔的文化根基。
除林鸿《槟榔赋》外,明末清初岭南文人黎遂球亦有《槟榔赋》。在部分内容上较林鸿《槟榔赋》更为详细:
美嘉实之贞烈,含文采于炎方。干亭亭而直上,枝扶举而疏张。涉南海以流望,见团盖之彷徉。摘鲛人之明珠,犹什袭而锦装。牵异卉而荐叶,朋翡翠于越裳。准削瓜以成瓣,或如钱而掷筐。疑獭髓与玉屑,并资嚼而得浆。拟漱石而砺齿,胜含脂以为容。
于是集良耦,邀上宾。进鲤尾,献猩唇。调甘选脆,嘉澹雪醇。龙华代烛,鸡人迟更。觞羽倦而既醉,德味饱乎大烹。却易牙而不顾,视杜康以逡巡。并牵裾与捧袂,见微诚于华巾。结方胜以象物,翅则蜨而首螓。香俨含乎鸡舌,液半饮而霞蒸。酌腑脏之损益,导元气以降升。是以靡俗不珍,无时不宜。托吉士以为友,比白茅而包之。指摽梅以兴感,伫斯焉之相遗。陈瓜果以穿针,悬艾虎而续丝。匪一端以调笑,即怀袖以寄怡。在凝寒而拥背,或立月而露滋。忽温霭而如醺,惟丹丸之馥颐。彼啮唇与唼舌,药并枕于低帷。畅同心之兰言,相吞吐而气佳。笑贞士之苦节,采松实而缘阿。分藜藿之我安,适晚食而婆娑。咏素餐而不怍,歌无酒而可酡。纵乐饥于衡门,亦回味以旨多。况鼎养之罗列,侑退食而委蛇。(23)陈元龙:《历代赋汇》,卷一二七,第511页。
该赋前有小序,涉及晋刘孝绰食槟榔之事,以此化解人们对粤人嚼食槟榔之俗的误解,并盛赞槟榔之美。黎遂球《槟榔赋》除描写槟榔生长特征、制作方法之外,主要描述槟榔之效用及其与粤人之日常生活之关联。作者笔下的槟榔形貌和口感兼备,其对健康的裨益更是许多山珍海味所不能比拟,而槟榔还是沟通友情的媒介,象征着纯洁的友谊。从地方文化的视角观之,《槟榔赋》在极短的篇幅中涵盖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涉及粤地槟榔的来源、形貌以及槟榔与婚姻、待客习俗等的关联,可印证众多古籍的记载,比如明王士性《广志绎》载广东地区“俗好蒌叶嚼槟榔,盖无时无地,无尊无长,亦无宾客,亦无官府在前,皆任意食之。”(24)王士性:《广志绎》,卷四,周振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92页。而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述及广东各地区人们所食的槟榔青、槟榔肉、枣子槟榔以及干槟榔等不同类别(2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赵元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29页。。对槟榔的嚼食方法、效用等方面则尤为重视:
当食时,咸者直削成瓣,干者横剪为钱。包以扶留,结为方胜。或如芙蕖之并跗,或效蛱蜨之交翾。内置乌爹泥、石灰或古贲粉,盛之巾盘,出于怀袖,以相献酬。入口则甘浆洋溢,香气熏蒸。在寒而暖,方醉而醒。既红潮以晕颊,亦珠汗而微滋。真可以洗炎天之烟瘴,除远道之饥渴。虽有朱樱、紫梨,皆无以尚之矣。
若夫灰少则涩,叶多则辣,故贵酌其中。大嚼则味不回,细嚥则甘乃永,故贵得其节。善者以为口实,一息不离。不善者汁少而渣青,立唾之矣。
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敬。聘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子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而琼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有关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至持以享鬼神,陈于二伏波将军之前以为敬。(2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第629页。
从以上记载来看,在广东、海南大部分地区,人们嗜食槟榔,且吃法极为讲究,调料的多少、咀嚼的程度都能影响槟榔的口感。《广东新语》所载槟榔的产地、食用方法等诸多方面与《槟榔赋》中的描写多有吻合,足见嚼食槟榔自古就广泛流行于岭南地区。而今人的研究亦可佐证《槟榔赋》的描写及古代史书记载。有学者指出:“自古以来,食槟榔在广东蔚为风气,世代相传。槟榔不但作为口果,而且可以代茶敬客,作为礼果互相馈赠,亦作为婚嫁聘礼,以及用以拜祀鬼神等,文化内涵有所扩大。”(27)袁行霈、陈进玉、司徒尚纪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广东卷》,第311—312页。
而除了叙写嚼食槟榔的习俗之外,黎遂球《槟榔赋》和屈大均《广东新语》中的有关记载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岭南人以“方胜”即“两个菱形压角相叠组成的图案或花样”(28)《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48页。包裹槟榔及其配料的做法。这种包裹方法在明代以后的史料笔记中有详细记载,清李调元《南越笔记》载广东人制作槟榔盒、槟榔包贮藏槟榔的情况曰:“居者用盒,行者用包。包以龙须草,织成大小相函,广三寸许,四物(槟榔、蒌叶等物)悉贮其中,随身不离。是曰:‘槟榔包’,以富川所织者为贵,金渡村织者次之,其草有精粗故也。”(29)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六,《丛书集成初编》,第98页。槟榔包的存在,说明广东人由嚼食槟榔的习俗而衍生出了诸如槟榔包这类民间艺术,在岭南地方文化中独具特色。
(二)张汉《滇槟榔赋》与云南槟榔文化
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是槟榔文化广泛流传的又一区域。明代以来,槟榔在辞赋等文体中时有提及。明俞纬《滇南赋》在述及云南之果类时有“槟榔无柯,南枣刺棘”(30)袁文揆、张登瀛辑:《滇南文略》,卷四一,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编:《云南丛书》,第38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20039页。之句。清李汝相《滇南赋》有:“槟榔芦茶之络绎兮,入五都而绣错。”(31)金廷献纂裁,李汝相等修辑:《路南州志》,卷四,民国十六年(1927)刻印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0页。清柯树勋《西双版纳竹枝词》诗云:“下车身到罗槃甸,只要槟榔树不枯。”(32)李孝友:《清代云南民族竹枝词诗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页。清李坤《滇中草木颂·槟榔》云:“银生异产,厥号槟榔。春华秋实,负阴抱阳。丽质凝紫,奇葩吐黄。益期不见,怛焉用伤。”(33)秦光玉:《滇文丛录》,卷二〇,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编:《云南丛书》,第41册,第22644页。足见槟榔作为云南特产之一久负盛名。而清张汉《滇槟榔赋》则是反映云南槟榔文化的代表作。
《滇槟榔赋》开篇即指出云南槟榔之产区在:“罗盘之甸,礼社之江。玉台诸峰之侧,银生节度之邦。距羲叔南郊之宅,邻《禹贡》黑水之邦。”(34)袁文揆、张登瀛辑:《滇南文略》,卷四二,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编:《云南丛书》,第38册,第20073页。赋中自注曰:“槟榔产元江府。江名礼社,宋为罗盘甸。”(《滇南文略·滇槟榔赋》)又曰:“唐属银生府节度使”,“南距交趾甚近”且“西瞰澜沧江即黑水”。(《滇南文略·滇槟榔赋》)据唐樊绰《蛮书》的记载以及今人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等的考证,上述地区约在今红河州、普洱市、西双版纳等地。这些地区是云南槟榔的主要产区,嚼食槟榔的习俗亦是自古流传。《滇槟榔赋》的主体部分就着重描写云南特产槟榔并艺术化的再现嚼食槟榔的习俗:
爰生嘉种,厥号槟榔。宜蛮烟与瘴雨,亦负阴与抱阳。彼其劲节参天,亭亭独立;不蔓不枝,春华秋实。黄英韦华韦华兮,穗结云垂;香雾噀人兮,众香之国。丹枫江上夕阳红,朱树蟠根同一色。紫气氤氲丽质凝,累累绿珠纷可摘。
尔乃登之绮席,盛以琼盂。手劈混沌之窍,中含太极之图;既同条而共贯,亦外枯而中腴。砺金错以平分,宛鱼符兮半璧;抵摩尼之一串,复蚌甲兮衔珠。佐以扶留之实,采诸哀牢之墟。夺炎帝司天之色,借娲皇炼石之余。白应受采,赤岂近朱。饵丹砂与白石,比勾漏以何殊。邓郁细餐云母屑,季伦怒击珊瑚裂。吐吞绛雪咀流霞,喷成石壁桃花赤。晕红粉兮云英,宛琼浆兮载啜。燕支未点绛唇赤,玳瑁微斑纤指涅。唾珠满地赤水凝,咳玉九天红冰结。吐袖遥添莱彩斑,舐毫淡染江花馞。赤瑛盘里,比樱桃以犹鲜;探春宴中,薄杏花兮红雪……试傅粉之何晏,汗淰然以潮生;近含香之荀令。载齿颊以尤馨。祛青草黄梅之瘴,回冰天雪窖之春。其沉醉也,入醉乡而非酿,顿逊国可以无花。其解醒也,起玉山之既颓,兴庆池可以无草。其破闷也,似卢仝之茗战,腋底风生。其疗饥也,似王质之窥枰,山中得枣。(35)袁文揆、张登瀛辑:《滇南文略》,卷四二,赵藩、陈荣昌、袁嘉谷编:《云南丛书》,第38册,第20073—22274页。
《滇槟榔赋》对云南地区嚼食槟榔的描写细致入微,极富想象力。在作者笔下,初采的槟榔如剖开后如鱼符、如蚌甲,完美无缺。而为食用槟榔而配制的扶留、丹砂等佐料更非寻常之物。咀嚼时能令人脸颊红润,神清气爽。而其效果也无比神奇,不仅是除去瘴气的良药,更是解酒提神之佳品。而因为云南所处偏僻,作者在赋末发出了“何滇产之尤僻,乃题咏之独希!”(《滇南文略·槟榔赋》)的感叹,为云南特产槟榔抱不平,亦彰显了云南槟榔之珍稀,嚼食槟榔效用之神奇。一系列夸张的描写,凸显了云南槟榔的独特与名贵,也为云南槟榔赋予了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滇槟榔赋》的相关描写也与居住在云南南部红河、西双版纳等地居民嚼食槟榔的习俗相一致。明陈文《云南图经志书·元江军民府》载:“其地多瘴疠,山谷产槟榔,男女旦暮以蒌叶、蛤灰纳其中而食之,谓可以化食御瘴。凡遇亲友及往来宾客,辄奉啖之,以礼以敬,盖其旧俗也。”(36)陈文修:《云南图经志书》,卷三,李春龙、刘景毛校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6页。明谢肇淛《滇略· 产略》载:“槟榔,树高十余丈,临安、广南诸郡有之。叶如芭蕉,花如金粟,实如桃李,土人四剖其房,并实干而贯之。食者佐以石灰及扶留。扶留,蒌子也,似桑葚而绿,味辛辣,其功消宿食,祛瘴疠,故闽、广人亦啖之。”(37)谢肇淛:《滇略》,卷二,(近代)秦光玉编:《续云南备征志》,李春龙、刘景毛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0页。
而《滇槟榔赋》与云南傣族的日常生活习俗的关系尤为紧密。江应樑《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详述摆夷(傣族)日常嗜好曰:“边民之于槟榔,犹乎汉人之于烟茶,客来用以敬客,闲时放口中嚼之,不单纯嚼槟榔,而是用槟榔、芦子、石灰膏和切碎的草叶,拌入一堆,放口中大嚼,嚼至满口留涎,有如喷血,年老人因吃槟榔太多,嘴唇尽成殷红色,口角有如积满污血,唐樊绰《蛮书》所谓的赤口濮,也许就是指此而言。”(38)江应樑:《摆夷的经济文化生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滇槟榔赋》中的“扶留之实”、“丹砂”、“白石”等物与傣族人嚼食槟榔时用作配料的草烟、芦子、石灰膏等物类似。《滇槟榔赋》中“燕支未点绛唇赤,玳瑁微斑纤指涅。唾珠满地赤水凝,咳玉九天红冰结。”的传神描写更是点出了嚼食槟榔时汁液染红嘴唇,犹如喷血的情形。而《滇槟榔赋》中盛放槟榔的“琼盂”,其原型或为傣族槟榔盒一类的器具,李昆声《云南艺术史》一书指出“槟榔盒有圆形、方形、多角形,盒遍体雕刻孔雀、大象、花卉。”(39)李昆生:《云南艺术史》,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页。造型精美。可见《滇槟榔赋》中的描写信而有征,是汉文化与云南各族民俗文化的完美结合。
不仅是傣族,《滇槟榔赋》的描写也与滇南一带布朗、阿昌、基诺等众多民族嚼食槟榔的习俗有类似之处。布朗族:“男女都喜欢嚼槟榔,即用槟榔叶包上草烟、石灰、槟榔果放入口中嚼食,其味不甜、不苦,略带辣味,吐出的水呈红色。”(40)颜思久:《布朗族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7—104页。阿昌族嚼槟榔:“嚼时先将草烟丝放于口中,再加入芦子、沙基膏、槟榔、熟石灰各少许,混合嚼十多分钟,即开始慢慢吐出,并边嚼边吐出赤红的口水,持续几小时不等……闲暇之余,大家互相传递,像传烟一样也是一种礼节。”(41)刘江:《阿昌族文化史》,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27—228页。此外,槟榔还与云南少数民族的其他民俗文化存在交叉,如饰齿习俗,基诺族在举行婚礼时“喜欢用槟榔、石灰放在嘴里嚼,时间久了牙齿逐渐变黑,并经久不退。”(42)程德祺:《解放前基诺族的婚姻、宗教和其他习俗》,《民间文学》,1981年。饮茶习俗,被誉为“古老的茶农”的德昂族:“会制作酸茶,是在竹筒中放茶,并加入少许槟榔,将竹筒压实,密封筒口存放一个月余发酵而成。此茶放入口中咀嚼,有生津止渴,清热解暑之力。”(43)施维达、段炳昌等编著:《云南民族文化概说》,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由此可知,在以云南为代表的西南地区,槟榔与傣族等少数民族息息相关,在这些民族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三)王必昌《台湾赋》等辞赋中的槟榔书写与台湾槟榔文化
以台湾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除云南、广东等地之外,槟榔文化较为突出的区域。在南明政权及清王朝统治台湾近200多年时间里,台湾岛的地理地貌、名物特产、风土人情等也渐受重视,关于台湾槟榔及有关习俗的描写在台湾不同时期的辞赋中时有出现。明末至清代,台湾辞赋中涉及槟榔及有关习俗的篇目包括:1.明沈光文《台湾赋》:“槟榔木直干参天,筼筜竹到根生刺。”(44)许俊雅、吴福助主编:《全台赋》,台南:“国家台湾文学馆筹备处”,2006年版,第532页。;2.清王必昌《台湾赋》:“厥有槟榔,生此遐方。杂椰子而间栽,夹扶留以代粮。饥餐饱嚼,分咀共享。婚姻饰之以成礼节,诟谇得之而辄忘。为领略其滋味,殆恍惚夫醉乡。”(《全台赋·台湾赋》);3.清屠继善《游瑯桥赋》写瑯桥(今台湾恒春)之民俗曰:“冠婚则惟酒、布、槟榔之属。”(《全台赋·游瑯桥赋》)4.清康作铭《瑯桥民番风俗赋》:“口满槟榔,掀唇涅紫。”(《全台赋·瑯桥民番风俗赋》)
从以上篇目来看,台湾地区古代辞赋对槟榔只有零星描写,目前还未发现专门描写台湾槟榔的辞赋作品。但结合清代台湾地方志来看,这些赋作也通过一些细节体现了台湾槟榔的产地、习性和台湾人嚼食槟榔的民俗。王必昌《台湾赋》的描写与清高拱乾《台湾府志·风土志》“槟榔”条所载:“槟榔,向阳曰槟榔,向阴曰大腹,实可入药,实如鸡心,和荖藤食之,能醉人,可以祛瘴。人有故,则奉以为礼。”(45)高拱乾:《台湾府志》,卷七,清康熙三十三年(1692)本,台北:大通书局,1977年版,第199—200页。的内容相吻合,也同清陈朝龙、郑鹏云《新竹县志稿·风俗》:“至槟榔一物,嗜食者齿常黑,谓可以避烟瘴,嘉、彰尤盛。每诣人,则献以示敬。遇小诟谇,一盘呼来,彼此释憾。”(46)陈朝龙、郑鹏云:《新竹县志稿》,卷五,清光绪十九年(1893)本,台北:大通书局,1977年版,第608页。的记述相一致。而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台湾人也将槟榔与扶留混合嚼食,且多用于日常交往;屠继善《游瑯桥赋》和康作铭《瑯桥民番风俗赋》与清屠继善《恒春县志·风俗》云:“恒邑产于番社者多,形如黑枣。裹以荖叶、石灰,男妇皆喜啖之,不绝于口,婚姻大事,及平时客至,皆以槟榔为礼。”(47)屠继善:《恒春县志》,卷八,清光绪20年(1894)本,台北:大通书局,1977年版,第155页。的记载较为相似,表明槟榔在台湾人的婚姻等活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沈光文《台湾赋》等辞赋中有关槟榔的描写也与台湾岛内各少数民族嚼食槟榔的习俗极其相似。有学者指出:“槟榔是阿美、排湾、鲁凯、卑南和雅美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卑南人以槟榔为重要祭品或婚事的主要聘礼,其村落多环植槟榔树,在阿美族各庐的庭院中也可见到结着累累果实的槟榔树。将这些槟榔种子切开后,加荖叶和石灰,便成了人们喜爱的食品。”(48)袁行霈、陈进玉、林仁川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台湾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52页。因而台湾的槟榔文化亦是中国槟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辞赋的描写、古代文献的记载以及今人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中国华南、西南、华东等地槟榔文化的风貌。从调料、嚼食方式等方面观之,华南、西南、华东三地嚼食槟榔的方法大同小异,而槟榔在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中所发挥的功用也比较接近,包括药用价值,婚丧嫁娶,成年礼仪,日常交往等多个方面。而林鸿《槟榔赋》、黎遂球《槟榔赋》、张汉《滇槟榔赋》和王必昌《台湾赋》所涉地区既有汉族,又有其他少数民族,这些赋的描写都多少涉及汉族和少数民族,就汉族而言,赋体文学中的槟榔更多地具有传统文人以物比德的寓意,象征着敦睦亲族,以礼待人的儒家伦理道德。就各少数民族而言,赋体文学中的槟榔更贴近各民族日常生活,是各民族生活习惯,审美习尚等内容的生动呈现。
就文学属性言之,槟榔赋应属于辞赋中咏物赋的一个门类,可归入花果或饮食类题材。与中国古代其他咏物赋相比,槟榔属于比较新颖且地域特征鲜明的题材。林鸿《槟榔赋》、黎遂球《槟榔赋》和张汉《滇槟榔赋》均有摹写细腻,工于体物这一赋体文学的基本特点,也都有地域特色鲜明、生活气息浓郁之特征。在具体细节描写上则各有侧重。林鸿之赋着眼于槟榔本身的形貌和琼人贩卖槟榔之事的详实记录。黎遂球和张汉的创作虽重在叙写嚼食槟榔这一习俗本身,但旨趣各异。黎遂球之赋,有解疑释惑之意;张汉之赋,有发掘地方特产,显扬美名以广身价之旨,均为明清时期咏物赋的佳作。
而槟榔赋的存在反映了赋体文学题材世俗化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在汉以后十分明显,明清两代尤其突出。槟榔成为咏物赋中的新题材,与明清两代植物种植技术提高,商品经济繁荣,各民族之间往来融合等因素有莫大关系。而作为一种饮食民俗和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槟榔文化在进入赋家的创作视野后无疑强化了辞赋的世俗化特征,使得辞赋的文化内涵向着更为广阔的领域发展。槟榔赋对槟榔文化的描写也同样使赋体文学的审美趣味发生了变化,明清文人在辞赋创作中更加关注辞赋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使得这一古老文体在关怀时事,寄托个人情怀的同时也拉近了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传统文人对于民间文化的认可与接受,不仅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强化了辞赋雅俗共赏的审美特色。
三、槟榔赋与槟榔文化带之关联
林鸿《槟榔赋》、黎遂球《槟榔赋》、张汉《滇槟榔赋》以及王必昌《台湾赋》等赋作对槟榔的描写和各种古代文献关于槟榔的记载。反映了中国华南、西南、华东等地富有地域特色的槟榔文化。而从地理空间言之,上述区域不仅涉及中国,也连接着域外国家,处在一个包含中国两广、海南、云南、台湾以及东南亚、南亚多国,跨太平洋、印度洋的槟榔文化带上。槟榔文化带的存在,说明槟榔赋有其文化属性,是槟榔文化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除中国外,槟榔文化带上有关国家出产、食用槟榔的情况亦见诸文献记载,比如越南,成书于越南阮朝嗣德三十五年(1882)的《大南一统志》载:“承天府(今顺化),产槟榔,俗名果槔。”(49)(越南阮朝)国史馆编:《大南一统志》,第一册,越南阮朝嗣德三十五年版(1882),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24页。“果槔”之“槔”音“高”,与越南语中槟榔的发音“cau”类似(50)林明华:《越南语言文化漫谈》,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5页。。而“果”则道出了槟榔作为树木果实的特性。《大南一统志》又记越南山西省槟榔出产情况曰:“槟榔子,出福寿县早下社,有四季槟榔,肥美稍胜。”(51)(越南阮朝)国史馆编:《大南一统志》,第一册,第424页。而有越南学者据考古资料指出,在距今约一千多年前的雄王时代,“(越南先民)食品中除了谷米一定还有水果、蔬菜,如瓜类、菊、豆、橄榄、番荔枝、槟榔。”(52)(越)文新等著:《雄王时代》,梁红奋译,河内:越南科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94页。而在越南人的日常生活中,槟榔同样扮演着一种维系宗亲关系,婚姻关系和沟通友情的作用,林明华《越南语言文化漫谈》一书指出:“越南俗语曰:‘吃片槟榔,成人家娘。’男婚女嫁时,槟榔是必不可少的聘礼之一;红喜之日,前来庆贺的朋友皆得赠尝槟榔。平时,朋友造访,槟榔又是各家常备的待客之物,正如另一越南俗语所说:‘先用槟榔后叙谈。’如此等等。”(53)林明华:《越南语言文化漫谈》,第33页。
越南之外,其他国家食用槟榔的情况亦见诸各类文献记载,如明马欢《瀛涯胜览》载占城国(今越南南部沿海地区)人:“槟榔、荖叶,人不绝口而食。”(54)马欢:《瀛涯胜览》,万明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爪哇国(今印尼爪哇):“男女以槟榔、荖叶裹蜊灰不绝于口……宾客往来无茶,止以槟榔待之。”(《瀛涯胜览·爪洼国》)暹罗(今泰国)男子在成亲后:“请诸亲友分槟榔、彩红等迎女归。”(《瀛涯胜览·暹罗国》)锡兰(今斯里兰卡)人亦是:“槟榔、荖叶不绝于口。”(《瀛涯胜览·锡兰国》)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邦):“人家无茶,客至以槟榔啖之。”(《瀛涯胜览·榜葛剌国》)又明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载缅甸之事曰:“芭蕉、槟榔实如碗而尖。味皆香美,取以供佛。”(55)朱孟震:《西南夷风土记》,《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由这些记载记载可推知,从中国华南、西南、华东等地,再到东南亚、南亚诸国。嚼食槟榔的习俗分布甚广,且在嚼食方法和日常使用等方面存在相似性。将槟榔文化的分布区域连接起来,就是一个槟榔文化带,其形状大致如同小写英文字母“m”。从右到左来看,m最右边的弧线代表两广、海南、云南、台湾以及国内其它相临地区的槟榔文化,在地理上靠近南中国海和太平洋;m中间的弧线代表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等地区的槟榔文化,紧靠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等区域;而m最左边的竖线代表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的槟榔文化,临近印度洋、安达曼海、孟加拉湾等地。这个呈小写英文字母“m”形的槟榔文化带彼此之间并非各自孤立,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稳定而又有所差异。
跨太平洋、印度洋的槟榔文化带是伴随着嚼食槟榔的习俗而逐渐形成的。从《上林赋》的描写、有关文献记载和今人研究可以推知,中国人嚼食槟榔的习俗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后开始形成,发展于魏晋、唐宋,至明清及近代渐趋成熟。综合古今中外各类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而言,槟榔文化经历了一个发源于东南亚并最终传播到中国的过程。槟榔文化带长期存在且从古至今不断发展,其成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在自然、地理因素方面,从有关史料来看,槟榔生长的区域均在中国南方、东南亚、南亚地区。这些地区靠近印度洋、太平洋等地,属热带、亚热带地区。炎热潮湿的气候特征为槟榔的自然生长和人工种植提供了优越的地理环境,也为槟榔文化的形成创造了必备的自然条件。
在身体、心理因素方面,就身体因素而言,由于槟榔文化带所在区域炎热潮湿,这些地区的人们常常受到与气候有关的各种疾病的困扰。而槟榔所具有的清热解暑、去瘴消食等效用在各地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被发现,嚼食槟榔成为人们免除疾病困扰的一种有效方法被普遍采用且广泛传播。
就心理因素而言,槟榔结果甚多且与荖叶、石灰等物混合食用等特点给各地区先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槟榔因此被寄寓了多子多福,夫妇和睦等吉祥含义。比如林鸿《槟榔赋》中“槟榔生兮满林,妙结实兮为祥为祯”和“槟榔生兮孔多,为祯为祥兮千秋不磨”的描写就可能含有祈求子孙兴旺的祝福寓意,而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也认为与槟榔与荖叶共同嚼食,有“夫妇相须之相”(56)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五,第629页。足以说明槟榔一物在祈求多子与夫妇和睦方面给人以很大的心理安慰,从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一物品的崇敬之心,各地区的人们将槟榔视若神物,使之随着历史变化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
在民族因素方面,槟榔文化以及槟榔文化带的形成,也与各民族的迁徙,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密不可分。以傣族为例。有研究表明云南傣族与海南之黎族,泰国之泰族以及缅甸之掸族等均源于古代之“百越”。(57)云南历史研究所编:《云南少数民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而在云南傣族、海南黎族以及泰国泰族、缅甸掸族中均存在嚼食槟榔的习俗。又以台湾境内各族为例,有学者指出:“台湾高山族和大陆的侗壮语族都同源于古代百越人。台湾的高山族与古越人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古越人是构成台湾高山族的主要成分。”(58)吴文明,许良国主编:《台湾高山族与祖国之渊源》,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57页。又有研究显示:“台湾少数民族中的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等族等是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而鲁凯族、雅美族、阿美族、卑南族等民族则源于马来人,是从菲律宾群岛以及印度尼西亚各岛屿迁入的。前者由大陆,后者由海洋进入台湾。”(59)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页。因此,无论是云南傣族、海南黎族、泰国泰族、缅甸掸族还是台湾岛内的一些民族都是百越民族的分支,体现了中国东南沿海各地民族多元一脉的特征。
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指出:“中国南方各民族很早就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共同生活,并在漫长的岁月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结成了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关系,体现着南方民族历史生动、丰富的内容。”(60)王文光:《中国南方民族史》,第1页。按照包括百越民族在内的中国南方各民族的分布与融合特点可以大胆假设:嚼食槟榔的习俗在古代百越民族那里可能早已出现并世代传承,随着这一民族的迁徙广泛传播并影响到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最终成为中国东南、华南乃至东南亚、南亚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共有习俗,随历史发展而形成内涵丰富的槟榔文化。
在政治、经济因素方面,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活跃朝贡活动和民间贸易也对槟榔文化带的形成起到了稳定和推动作用。就朝贡而言,《新唐书·地理志》载安南中都督府(今越南)土贡:“蕉、槟榔、鲛革、蚺蛇胆、翠羽。”(61)欧阳修:《新唐书》第4册,卷四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111—1112页。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交州(今越南)于唐开元八年(720)贡槟榔(62)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八,《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2页。。另有学者据《大清会典》统计出清代贡自安南的物品中有砂仁、槟榔各90斤。(63)李云泉:《万邦来朝—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页。民间贸易方面,宋赵汝适《诸蕃志》载产自中国和海外的槟榔销路广泛,并成为中国泉州、广州的税收来源之一(64)赵汝适:《诸藩志》,卷下,第186页。。《诸蕃志》和《广东新语》均记载了槟榔产自琼州(海南岛),售于中国广东,海外交趾(越南)、扶南(柬埔寨)等地的情况。这些史料,均可视为槟榔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依据。
民俗学有关理论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由外在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的影响与内在的基本心理过程相互关联的关系所规定的。”(65)乌丙安:《民俗学原理》,长春:长春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页。槟榔文化带的形成亦是如此。在构成跨太平洋、印度洋的槟榔文化带的四个要素中,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心理因素的影响均有体现。自然、地理因素是构成槟榔文化的基础,而身体、心理因素、民族因素及政治、经济因素则促进了槟榔文化带的形成和扩展。槟榔文化带的存在不仅体现了槟榔文化本身,也反映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悠久的交往历史和多元文化。
因此,槟榔赋的创作正是槟榔文化带久已存在的一个表征,也说明槟榔对不同地区、民族的生活均有影响。从文献记载和文学作品的描写来看,槟榔在槟榔文化带上各地区、各民族之婚姻习俗(傣族结婚用槟榔)、节日习俗(清代云南建水过年备槟榔)、待客习俗(傣族等民族、中国广东。海外越南等地以槟榔待客)、民间工艺(傣族槟榔盒、广东槟榔合、槟榔包等)、宗教信仰(广东以槟榔祭拜先贤,缅甸以槟榔供佛)等领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代代相传,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槟榔赋的创作和槟榔文化带的存在也足以证明槟榔成为了一种跨区域、跨民族的文化符号。
而除了辞赋这样的作家文学,在地域广阔的槟榔文化带上,民间文学中也同样有槟榔的影子,比如关于越南人在婚礼时嚼食槟榔习俗之起源的民间故事“阿宾与阿郎”,就有明显地劝诫、规讽之意,表达夫妇和睦、长幼有序之意。而越南传说《槟榔》,更是移植中国“黄粱梦”的情节和叙事结构,表现文人对于功名的渴望以及官场的黑暗险恶等内容(66)(越)阮董之:《越南民间文化库藏》,河内:社会科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58—261页。转引自林明华:《越南语言文化漫谈》,第37页。。是越南人成功改造中国有关传说的范例之一。除越南外,中南半岛东南部的古国占婆(今越南南部等地)亦流传着占婆国王浦克龙降生于槟榔果中的神话,属于典型的卵生神话,但卵已经变为东南亚广泛存在的槟榔,这一改变或可探知槟榔在古代占婆文化中的神圣地位。而这则传说中的槟榔又与作为印度教的圣物之一的牛发生了紧密联系,是槟榔文化带上文化交流的又一鲜活事例(67)常任侠:《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以上民间故事、传说的存在足见在区域广大的槟榔文化带上,槟榔不仅是辞赋等作家文学中的题材,更是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中的重要情节。而辞赋、民间故事、传说又与槟榔文化带上的儒、释、道、印度教等发生了联系,反映出文化交流中存在的要素移植、同源异流、多元汇融、共同创造等诸种形态(68)傅光宇:《云南民族文学与东南亚》,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不断丰富着槟榔文化的内涵。
因此,无论是《槟榔赋》等辞赋创作还是与槟榔有关的民间故事、传说等。都反映出槟榔文化悠久的历史和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种植槟榔和食用槟榔的习俗使得槟榔文化逐渐形成,并产生了若干槟榔文化区。而受到民族迁徙、融合等因素的作用,槟榔文化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地域广大的槟榔文化带。而在槟榔文化带上,槟榔及其嚼食习俗进入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中,形成了包括《槟榔赋》在内的众多文学作品,使槟榔文化的内涵得以不断扩展,也为《槟榔赋》等文学作品赋予了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呈现出一个自然与人文,文学与文化交融共生的统一体。显示出槟榔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魅力,而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流互鉴,共同发展的特征也籍此得以展现。
《槟榔赋》等辞赋作品与槟榔文化这一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的广泛存在密不可分,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因素为槟榔的生长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槟榔的药用价值在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被逐渐认识,形成了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并广泛传播,最终发展成为跨太平洋、印度洋等广大地区的槟榔文化带。在这个文化带上,槟榔及槟榔文化进入文学创作,形成包括《槟榔赋》在内的一批优秀作品,不断充实着槟榔的地域文化特色,使其作为文化符号的特征愈发明显。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论认为:“人类最初的需要就是衣食住,而三者之中,以食物为第一位。因为人类也像动物或植物一样,不进食就无法维持生命。不但如此,食物还能影响于个人的性情、品行、团体的幸福和种族的繁殖等。”(69)林惠祥:《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食槟榔作为饮食民俗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显而易见,它不仅祛除疾病,还成为了连接有关地区人们亲情、爱情、友情的纽带,亦是影响文学创作,促进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