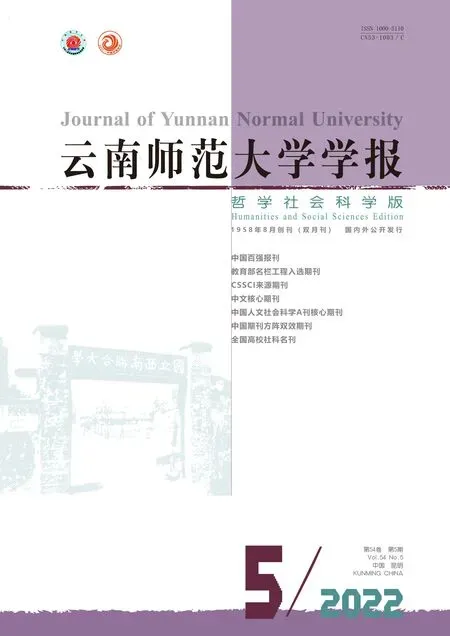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西方边疆观演变与边疆治理转变
——兼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转型*
何修良, 罗柳宁
(1. 中央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81; 2. 广西民族研究中心,广西 南宁530028)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综述
全球化浪潮打破了民族与国家、主权与领土、群体与个人等多重界限与领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交流交往,进而促使了边疆不断成为流动的节点而不再是阻碍民族国家交流交往的起点,对边疆内涵的理解逐步从民族国家“主权性”的框定走向了边疆区域多样权力的实践关系阐释,这构成了理解全球化时代西方边疆观演变的前提。
相较于传统意义国家所特有的那种模糊的“边疆(frontiers)”,(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4.现代经典意义的民族国家认知是与边疆相互隐喻互证而存在,通过给国家政治空间设立一个清晰的界限,(2)Holdich T.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y Making[M].London:Macmillan,1916:38.实现民族国家“行政范围正好与领土边界相对应”(3)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13.。民族国家的边疆必须是清晰的、确定的,以此来确保国家之间交往发展。作为具有清晰界限的边疆社会,边疆治理始终遵循传统“地缘政治路径”模式,边疆观呈现出向心性、稳定性、静止性与结构化特征,进而导致“边疆的边缘性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4)刘雪莲,刘际昕.从边疆治理到边境治理:全球治理视角下的边境治理议题[J].教学与研究,2017,(2).,边疆的“边缘性”与“屏障性”功能不断地被强化。在此背景下,边疆被动地嵌套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话语叙事中,对边疆的认识很少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与文化层面的理解,甚至缺乏将其视为表述主体来看待,自然也就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边疆社会整全性观念的认知。
随着全球化兴起和地缘政治变迁,人们逐渐认识到,边疆作为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因流动性不再是与“中心”相匀质的静止性区域,国家层面意义的边界和其他边界也并非完全重合,边疆是一个混杂性空间,里面包含着不同类型的边界现象。(5)Minghi J.Boundary Studi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63,(2).伴着信息技术与交通能力的提升,经济全球化所塑造的“全球是平”景观促进资金流、物质流与信息流等在全球范围无界流动,“流的空间”(6)Castells M.The Informational City[M].Cambridge,MA:Blackwell,1989:5.使产生社会关系与地点(places)、领域(territories)相互脱嵌带来了“去领域化”现象。同时随着国际社会组织对边疆区域发展的投资以及所催生的跨国企业、边境双子城市出现,物质与人口、信息与技术大量地流入边疆区域,边疆地方性逐步融合外部力量,甚至随着生物计量技术与网络信息的发展,边疆传统功能出现了“弥散化”现象,涌现在非边疆地区,比如飞机场、车站甚至是网络登录端口处(7)Benjamin J.Muller.Risking it All at the Biometric Border:Mobility,Limits,and the Persistence of Securitisation[J].Geopolitics,2011,(1).乃至在远离边疆的中心地带,从而使“国家之间的公共性、跨越国家界限的个体之间的公共性开始日益为人们所重视”(8)沈湘平.论公共性的四个典型层面[J].教学与研究,2007,(4).。随着流动与边疆区域变化加剧,两者之间关系也呈现出新的解读,“流动不再是边界的对立面,反而是边界不断再生产的动力,甚至是边界得以‘批判’的关键”(9)赵萱,刘玺鸿.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9,(1).。在流动性世界里,边疆不再被视为民族国家需要治理的依附性产物,也不仅仅是由多种政治理念与权力实践所设置出来的“对象性”区域,边疆社会逐步成为“一种主体性的而非客体性的东西”(10)Ladis K.D.Kristof.The Nature of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1959,(3).,边疆开始以主动性因素影响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与民族国家政治变迁,并在有些区域扮演着关键性角色。
总之,全球化的到来带来了边疆内涵、功能与地位的巨大变化,边疆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悄然改变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边疆认知,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边疆内涵发生了变化。在民族国家视野中,“边疆是什么”有着简单而固定的回答,全球化时代这一诘问很难给予明确的答案。全球化时代,边疆不能仅仅从民族国家一侧的单一向度理解而是需要从国家间交往交流的关系向度来理解,边疆充满奇点(singularities)(11)Rumford,Chris.Rethinking European Spaces:Territory,Borders,Governance[J].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2006,(3).缝合起了国家间的正式或非正式交往联络,边疆地方性与世界性逐步对接与融合,在那些流动发生的地方就可能成为边疆。(12)Rumford,Chris,Does Europe Have Cosmopolitan Borders[J].Globalizations,2007,(3).以往民族国家视角下所理解的边疆内涵所内在的“主权性”特征也在发生转变,边疆内涵理解长期蜷缩在民族国家主权界定下以及所形成的稳定边疆观开始松动,继而推动了全球化流动性视角中动态性边疆观塑造,边疆呈现出流动的、面状的、可渗透(13)刘一.欧洲边境的重筑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24.的面向与特征,并不断影响着民族国家权力关系形态与运行逻辑。另一方面边疆功能的变动带动了边疆治理模式变迁。边疆功能转变是流动本身的效果。在空间层面,边疆不再预设为先天存在的地理边缘,而是产生于领土边界内外的多个区域,其与建构因流动主体及治理理念上的差异性而表现出复杂性,比如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边疆安全议题的变化促成了“离岸边疆”(off-shore border)治理(14)Mark B.Salter.Passports,Mobility,and Security:How Smart Can the Border Be?[J].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2014,(1).的出现,显然这远远超过了传统民族国家边疆治理理解的范畴。与传统影响治理的“领土主义”的管控性因素不同,学者开始探索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政治异质性程度以及族群与文化认同(15)Anderson M.The Political Problems of Frontier Regions[J].West European Politics,1982,(4).等互动性因素对边疆治理影响,传统上企图通过加固边界来隔离彼此分歧的“高政治”议题行为难以为继,“政治家需要通过对话与协调实现国家系统与边疆系统的良性互动”(16)Stoddard E.Local and Regional Incongruities in Binational Diplomacy:Policy for the U.S.-Mexico Border[J].Policy Perspectives,1982,(1).。因此,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要实现边疆善治效果,需要走向新的治理模式以适应流动性边疆社会需求。那么,深层次地看,依照笔者理解,需要追问与解答的是:什么样的主体在怎么样的空间中以何种流动方式生产出不同边疆以及如何构成影响民族国家变化的因素。
近些年国内学术界开始关注与探索从全球化视角认识与理解边疆内涵的转变与特征。在宏观研究上,伴随全球化推进,非民族国家化似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利益边疆”(17)于沛.经济全球化和现代西方边疆理论[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理论应运而生。利益边疆是一个有着多层次复杂结构的整体系统,它体现为高边疆、深边疆、信息边疆等等,(18)王西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利益边疆与积极防御战略的转换[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1,(3).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对地理边疆的理解。在中观研究层面,全球化时代边疆社会面临着“我者”与“他者”之间、“开放”与“封闭”之间的协调问题(19)曹亚斌.全球化时代边疆社会中的世界主义文化[J].教学与研究,2020,(2).以及边疆重塑(20)刘一.西方边境安全治理研究:现有方式、问题与可能路径[J].东北亚论坛,2021,(5).对边疆治理的影响,对边疆观的理解与边疆治理理念始终处于像钟摆一样在“去边境化”与“再边境化”之间选择,(21)刘一.欧洲边境的重筑及其对欧洲一体化的影响[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20.进而突出了边疆安全议题研究的重要性和日益的学术聚焦。还有学者评述了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综合性地讨论了近些年兴起的批判边界研究在“流动”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生命政治边界”的理论取向以及对中国边疆研究的启示。(22)赵萱,刘玺鸿.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9,(1).在微观研究层面,学者集中讨论了西方“边境区”概念的提出与发展,(23)曹亚斌.全球化时代边疆政治思维困境及应对之道[J].教学研究,2017,(2).这既意味着对传统边疆空间理念的理论重构,也意味着新的权力结构对边疆影响的学术关注。还有学者从人类学视角探索了全球化时代政治边疆观、文化边疆观、社会边疆观(24)何修良,牟晓燕.斑斓多彩的边疆图景: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观描述与型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所形成了斑斓多彩的边疆图景,进而反思了“流动性现代化”背景下“世界边疆”与“边疆世界”之间的联系与走向,(25)何修良.边疆人类学发凡:全球化时代边疆观的叙述与重构[J].广西民族研究,2021,(6).在描述边疆观原有内涵流变以及在演化过程中的内在性张力的同时,更深层次地阐释了如何通过将政治边界从一个消极的地理标志物转向积极的过程和制度以及对全球化流动冲击下的民族国家转型(26)赵萱.全球流动视野下的民族国家转型——基于海外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的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在更为微观研究层面,从民族志视角探索全球化时代边疆观的变迁和边疆治理的变化构成了另一鲜明特色。比如对耶路撒冷土地争夺的民族志材料的解读,考察巴以边疆区域的社会秩序形成,进而强调巴以领土冲突理解为秩序之争而非简单的领土争夺,(27)赵萱.重建领土观:东耶路撒冷的领土/土地争夺——批判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巴以冲突[J].世界民族,2019,(5).还有通过对以色列巴勒斯坦人的日常生活与个体生命的民族志书写,阐释了边疆地区的地缘政治与生命政治的交互性特征(28)赵萱.隔离墙、土地与房屋:地缘政治与生命政治的交互——一项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志研究[J].开放时代,2018,(5).。这些研究,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本文立足边疆“空间重塑”与“主体转向”视角,沿着多学科视野理解全球化流动视野下边疆内涵所指与边疆治理转变,同时以边疆为方法对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转型做一个尝试。
二、研究路径:“空间性”与“主体性”的交互分析
随着全球化加速与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国家之间联系更加紧密,跨界行为频繁,边疆区域受到了更多关注与研究。纵观在新地缘政治学、边疆人类学、批判边界研究(critical border study)等政治研究领域以及新安全主义、新领土观、新自由主义等政治思想影响下,与之相伴的“后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等后现代化研究方法的兴起与影响,逐步形成了边疆概念内涵的“实践转向”——一种超越传统固有的区域主义转而围绕权力实践在多空间性和多主体性上构建新的边疆观正在悄然兴起,边疆区域完成了“空间重塑”(29)Henk Van Houtum.Prologue:Bordering Space[A].Henk Van Houtum,Olivier Kramsch and Wolfgang Zierhofer.Bordering Space[M].London:Routledge,2017:1~6.与“主体转向”(30)Scott,James W,Borders.Border Studies and EU Enlargement[A].Wastl-Walter,Doris.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M].Burlington:Ashgate Publishing,Ltd.,2012:123~142.并在理论层面上建构起了更为丰富的边疆认知框架,进而推动了反思全球化视野中边疆治理以及民族国家变迁的学术路径上进一步拓展。
(一)流动即生产:“空间性”
全球化的急剧变化直接促进了边疆区域变迁,进而引起了边疆“空间重塑”,带动了学者开始关注传统地缘政治视野中边疆时空层面上的改变及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在全球化“时空压缩”的流动世界中,各种物质与文化在边疆区域相融、交汇与共生,边疆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延展性和扩散性”(31)Mountz,Alison and Hiemstra Nancy.Spatial Strategies for Rebordering Human Migration at Sea[A].T.Wilson and H.Donnan.A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M].New Jersey:Wiley-Blackwell,2012:455~472.的特征。边疆开始以“边疆化”(bordering)的状态出现,学者开始对边疆空间塑造的流动过程分析,边疆也被比作“一个动词,标志着边疆生产过程”(32)Nicholas De Genova.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Border Regime:Towards a Marxist Theory of Borders[J].International Socialism,2016,(4).。在这一演化逻辑中,场域形塑、政治资源整合以及治理策略行为体博弈重塑的边疆空间具有了新的叙事意义,逐步淡化了民族国家治理场域的“物理/自在空间”的内在演化叙事,而不断转向了“政治/社会空间”的功能主义研究,集中体现在通过时间、空间以及活动三重维度来分析边疆社会变化的动力,(33)Zartman I W.Understanding life in the borderlands:boundaries in depth and in motion[M].Georgia: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2010:8~20.全面阐释了边疆内涵所呈现出的客观化(objectification)、民族化(nationalizing)和秩序化(ordering)的过程,(34)赵萱,刘玺鸿.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9,(1).民族国家的权力实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不同的边疆地区表现出多样的内容与特征。
在全球化“以功能性、功利性为特征的‘流动型空间’(spaces of flows)”(35)Blatter J.From “spaces of place” to “spaces of flows”? Territorial and functional governance in cross-border regions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2004,(3).中,边疆区域开启了形式多样的政治性复杂重构,边疆研究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围绕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疆议题,还包括如何理解边疆区域多空间、多关系的重塑以及所带来的新地缘关系的讨论。美墨边疆作为世界“第一热边”,是理解边疆空间与边疆社会行为变化的样板。(36)Alvarez,Robert.Borders and Bridges:Exploring a New Conceptual Architecture for(US-Mexico) BorderStudies[J].The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Anthropology,2012,(1).近些年由于美墨之间巨大悬殊的经济发展地位,相伴着资本、市场与技术的合谋,美墨边疆成了一道“旋转门”,在不同的层面展示出不同的边疆内涵,在实践层面保障了美国廉价劳动力(墨西哥移民)的获得,在象征层面又显现出美墨边疆相关的安全性,(37)Rosas,Gilberto.The Managed Violences of the Borderlands:Treacherous Geographies[J].Policeability,and the Politicsof Race.Latino Studies,2006,(4).边疆不再是“桥”(开放与联系)与“墙”(封闭与隔绝)的矛盾对立问题,而是成为在频繁的流动性中如何实现各自利益的同时又动态性地维持相对的安全问题。在实践中,比如在美墨边疆日常检查分析中,充斥着大量“自由裁量”现象,在边疆口岸、边疆区域的检查点和机场以及远离边疆区域的广阔区域地带,边疆检查越发随意性和简单化,其检查结果更多依赖于某个巡逻人员的判断,(38)Heyman,Josiah Mc C.Trust,Privilege,and Discretion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US Borderlands with Mexico[J].Canadian Journal of Law & Society/La Revue Canadienne Droit et Société,2009,(3).边疆管理权力从过去“集中化”规范行使转向了情境化的“个体性”判断继而使得权力处于一种“弥散化”状态。这些年,随着非国家主体的不断参与而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多重博弈关系特征,比如美墨边疆中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参与,质疑、批判和反抗移民非法化行动,促成了“人道主义边疆”(39)William Walters.Foucault and Frontiers:Notes on the Birth of the Humanitarian Border[A].Brockling Ulrich,Susanne Krasmann and Thomas Lemke.Governmentality: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Challenges[M].London:Routledge,2011:138~164.的出现。美墨边疆内涵的多层次展现以及多主体权力以不同的方式和内容在塑造边疆空间中发挥着自身作用,边疆治理的具体实践也无法归结为国家权力运行的投射,而是折射出特定具体空间的场域逻辑,其实效是多主体参与下边疆空间不断博弈的结果以及所形成的飘忽不定的政策理念,民族国家边疆治理自上而下的可持续性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式微。在欧洲,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和《申根协定》实施,则表现出渗透性的“电子边疆”(40)Rumford,Chris.Rethinking European Spaces:Territory,Borders,Governance[J].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2006,(3).(Iborder)特征,欧洲最能凸显边疆的地方,并不是在申根区域的地理边疆位置上,而是在边疆警察的便携式电脑上,(41)Tsianos,Vassilis,and Serhat Karakayali.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European Border Regime:An Ethnographic Analysis[J].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10,(3).边疆生产性随着管理信息系统的完善与实施最终完成了欧洲民族国家边疆空间的独特性塑造。边疆治理过程也就转换为对不同群体的筛选、区分和治理的过程,(42)赵萱,刘玺鸿.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9,(1).对其进行拘留或驱逐,既可以发生在欧盟的边境检查站点上,也可以在欧盟的任何地方发生继而实现欧洲边疆安全。实质上,欧洲数字边疆强调技术的“算法”而非正式“制度”促使了边疆治理技术的新面向:不再是“应付”性的结果处理而是根据现有数据预测未来,聚焦边疆在时间上的前后延展性。(43)Bonnie Sheehey.Algorithmic Paranoia:The Temporal Governmentality of Predictive Policing[J].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2018,(2).边疆空间安全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某一个特定区域,在同一时间某一地方的边疆安全问题可以呈现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也带来了离岸式的边疆安全治理模式。在全新的欧洲边疆安全治理观念中,民族国家主权与领土固化的认知发生了改变,甚至出现了“主权企业家”概念所指向的“共享主权”(44)Andrijasevic,Rutvica:From Exception to Excess: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s Across the Mediterranean Space[A].De Genova,Nicholas and Nathalie Peutzeds.The Deportation Regime[M].Duk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10:67.,这种欧洲边疆治理在时空上变化则构成了民族国家转型的新特征。在非洲,边疆空间的情况更为复杂,比如在加纳海关治理中,海关职能外包给私人公司而引发了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加纳海关边疆区域在海关产业的私人力量和国际力量影响下被不同主体所分享(45)Brenda Chalfin.Global Customs Regimes and the Traffic in Sovereignty Enlarging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J].Current Anthropology,2006,(2).从而形成了一种边疆管理制度外包化(out-source)模式,这在以往民族国家权力实践中是不可想象的。次国家主体和非国家主体等介入边疆治理在增加了对边疆区域变迁多样性理解的同时,也显示出了边疆区域及其边疆治理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当然这种不稳定状态也会随时因被民族国家收紧或收回权力外放而回归原样,毕竟“国家同样有能力通过增加边疆社会封闭性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46)Hutnyk.J.Hybridity[J].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05,(1).。进而言之,权力外包的边疆治理实践成功与否的重点转移到了边疆治理能力建设及持续推进边疆空间实践的创新动力,而能力建设,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了外部知识的引进使用和边疆地方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
综上,全球化流动促进边疆空间权力组织形态和运行逻辑发生了变化,逐步孕育了由边疆区域经济和社会因素所催生的“从边缘到中心”的新政治地缘思维,带动了边疆区域由传统等级性政治结构向新的平面性政治结构的转型。(47)Jessop B.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cale//Perkmann M,Sum N.Globalization,Regionalization and Cross-Border Regions[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2:37~42.边疆外部因素影响不断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以及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形成的结构关联,使得边疆区域不仅表现出是一个功能性单位,还逐步具有制度空间(48)参见按照国内学者赵萱的理解,边界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由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编织而成的,包括国家针对边界的安全和流动有着一整套法律规范,也包括非国家的行动者围绕边界展开的每日实践,其中既有经济活动也有政治和文化行为,边界观念本身就是制度运行的结果。赵萱.全球流动视野下的民族国家转型——基于海外边界人类学政治路径的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1).的特征,推动了边疆区域内部治理结构的形成,形成了变动的新地缘政治秩序。民族国家的主权、公民、组织权力、领土等内涵也扩大了到了民族国家之外去理解,即这些国家要素从边疆空间生产性的前提背景转换为引致边疆观演化的不同变量,而边疆也不再是固化的划分权力清晰界线,而是可以发生移动与分化、消失与涌现,甚至超越民族国家权力约束的一系列日常在地化实践。
由此看出,全球化时代,边疆与民族国家之间并非单一向度的影响,而恰恰是双向性建构。传统民族国家在影响边疆发展的同时,在边疆区域公共秩序反复重塑中,(49)边疆区域公共性与公共秩序塑造既有弱化的时候,也有强化的时候,伴随着“去边界化”和“再边界化”的动态过程,这种“潮标”式波动过程构成了边疆秩序再造的逻辑,其移动所留下来的痕迹,可以是反复的也可以是突然改变的。可能会产生长时间的效应,也可能会瞬间就消失。但不管怎样,其依旧体现或者制造了差异。Green,Sarah.A Sense of Border[A].T.Wilson and H.Donnan.A Companion to Border Studies[M].New Jersey:Wiley-Blackwell,2012:573~592.由行动者话语、身份以及福柯所提倡的国家“治理化”(governmentalization)边疆知识体系,反过来重释了所惯常认识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不再是思考问题的原点反而成了被思考问题的本身。(50)Nick Megoran.For Ethnography in Political Geography:Experiencing and Re-imagining Ferghana Valley Boundary Closures[J].Political Geography,2006,(6).在此,民族国家边疆政治权力运行完成了一次较为彻底的空间重构,极大地促使民族国家发生了深刻转型,原来由不同色彩的国家所拼接而成的“马赛克式”世界地图正在被“重叠式”“互嵌式”地图所取代。(51)曹亚斌.区分即融合:西方“边境区”概念的学术史梳理[J].广西民族研究,2019,(3).在这一过程,民族国家不断进行调整与重组,其利益被外溢、拆解与输送甚至交换,进而嵌入其他民族国家之中并互相竞争与共生,民族国家要保证国家安全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和谋划实现“利益边疆”。申言之,相较于传统民族国家分析视角,边疆分析从“定点性”走向了“弥散性”,由“保护性”走向了“生产性”,边疆空间重塑过程分析采取了将“边疆地区之间、国家以及政府之间的双边关系优先于将国家视为背景的地方文化”(52)黑斯廷斯·唐南.边疆人类学概述[J].袁剑,刘玺鸿,译.民族学刊,2018,(1).而具有了方法论的优越性,多层空间的权力实践和话语建构最终使具体化的边疆成为不断被话语阐释和治理对象。同时对边疆治理的理解不再仅仅被视为民族国家权力运行逻辑的线性结果,而是那些对流动进行管控的地方,边疆空间也无法被化略为“规训/惩罚、服从/反抗”的权力二元对立思维的科层体系,而是日益彰显出具有非平衡性、非线性、开放性的多中心治理的网络特征。
(二)身份即政治:“主体性”
20世纪后期,全球化时代兴起了“生命政治边疆”的理论取向,边疆研究内容也开始从“地缘政治”分析向“生命政治”(bio-politics)分析(53)Nick Vaughan-Williams,Border Politics:The Limits of Sovereign Power[M].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156~158.转变,学者开始通过边疆主体实践和主体性塑造角度来分析边疆区域,这构成了全球化认识边疆的另一种叙事。通过阐述边疆是如何“在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弹性、冲突和角逐的生产性过程”(54)Josh Watkins.Bordering Borderscapes:Australia’s Use of Humanitarian Aid and Border Security Support to Immobilise Asylum Seekers[J].Geopolitics,2017,(4).,并描述了不同人群在边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主体性”变化以及相应身份认同的选择,进而展示了全球化对边疆不同政治文化和不同族群的影响及相应的边疆治理策略。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边疆主体形塑的“过程性”以及阐释边疆主体行为如何影响边疆观建构的“总体性”,即“从关注边疆包含什么转向边疆本身以及他们所参与其中的边疆过程”进而“通过那些在边疆生活并跨越边境的行动者的能动性去追问边疆如何、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被塑造、维持和消逝。”(55)黑斯廷斯·唐南.边疆人类学概述[J].袁剑,刘玺鸿,译.民族学刊,2018,(1).随着研究深入,西方学者形成了“人/人”“人/地”和“地/地”3种分析模式,诠释了边疆空间主体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以及民族国家权力结构的实践变化。
首先,“人/人”分析模式。“浮动群体”(population flottante)(流动人群)是边疆流动空间层次变得更为丰富的关键因素,边疆区域中人与人的关系依然可视为边疆空间不断生产的结果,只不过所展演的空间延展到了个人类型层面以及所显现出的政治内容。边疆开启了地方日常生活权力运行,认为“公民的角色都在设想、建构、维持以及清除边疆”(56)Rumford,Chris.Introduction:Citizens and Borderwork in Europe[J].Space and Polity,2008,(1).。但针对某个个体而言,身份又表现出多面向,他们不是以一个固定身份或面目出现在边疆过滤机制中,而是在不同的空间情景中的理性抉择,“他们在对权力和服从的闪展腾挪中,不但变换和重建身份认同,并且往往运用多重身份”(57)Gupta A,Ferguson J.Beyond culture:space,identity,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J].Cult.Anthropol,1992,(7).,于是流动性本身也被看作是一种生计(58)沈海梅,陈晓艺.跨边界生计研究的国际人类学新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边疆民众身份在政治意义进程得到了个人化的展现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主体之间各种企图和行为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不稳定的、个体化的边疆体制”(59)Julian Hollstegge and Martin Doevenspeck.“Sovereignty Entrepreneurs” and the Production of State Power in Two Central African Borderlands[J].Geopolitics,2017,(4).。边疆区域治理过程中主体生产所凸显的一种政治策略,国家很难再用单方面的权力意志分析,而是寓意了不同主体权力关系交互影响的可能性,边疆区域中主体更多是以复杂性多元博弈主体参与实践过程中。比如阿瓦拉兹(Robert R.Alvarez)认为美墨边疆区域是由3种不同意图的关系网络共同交错而成,(60)Robert R.Alvarez,Jr.The Mexican-US Border:The Making of an 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5,(124).形成了由公司与官僚企业家以及国会代表的关系网络、反移民理论家关系网络、企业和政府精英关系网络的复杂博弈格局,不同利益诉求与利益争夺在边疆时空实现。总之,边疆空间不再是领地争夺的对象,而是一个空间意义不断变幻的政治性场域,不同身份转化或重塑所展现的是一种个人层面的政治技艺,边疆治理也就成了民族国家对不同群体的差异性政策体现,遵循着策略、语境以及竞争性的身份认同构成了边疆再造的过程(61)Tali Hatuka.Civilian Consciousness of the Mutable Nature of Borders:The Power of Appearance along a Fragmented Bborder in Israel/Palestine[J].Political Geography,2012,(6).进而形成边疆内涵演变的主体间性思维,开始以动态眼光看待边疆不同人群的互动与身份塑造,其内在治理逻辑表明,边疆治理议题研究逐步从领土安全向人的安全转变。
其次,“人-地”分析模式。边疆内涵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边界流动得以整合,进而与领土边疆弥合成一条整齐的边疆。作为一种情势化和混合性的方式,其逻辑为,在以边疆“之人”为对象的治理需求下,对于边疆“之地”的认知依附在对生活在当地人群认知的基础之上。比如人类学学者试图突破宏大叙事的边疆研究进路,开始转向对地方语境中边疆日常生活实践的讨论,进而推动了不同主体参与的边疆分析。比如在非洲沙贝边疆中,世代生活在这里的边民认为“我们自己就是边界”,自己有权决定进行自由跨界贸易,不需要政府的边境审查,更不用交税。他们认为“边疆身份”不再简单地由民族或者国籍确定,而是根据人们在该地区居住的时间与社会融入程度来裁定。(62)施琳.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J].广西民族研究,2017,(2).换句话理解,他们具有自主性的行为可以作为国家的代表行使权力意志并保护或方便自己而不是受到国家内部更多权力的规训与压抑。身份认定类型的多样性显示出了边疆区域是如何形成了一种多方向的流动和相对比较松散的“融而未合”空间,同时也表明边疆区域内部的人群并非内部同质化的群体,表现出差异性理念与行为的理性选择。同时大量民族志显示跨越边疆的人员流动不断形成的跨境地方性关系,通过不同的机制被不同的社会组织吸纳而得到“集体感”与“成员感”,“在边疆地区,移民既是界定边界的外国人,也是默认的(尽管处于阶级结构的底层)内部人士”(63)Heyman,Josiah.The Mexico-United States Border in Anthropology: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1994,(1).,从而利用跨界地方性政策网络、象征性机制以及地方性制度形成了超越边疆区域的跨界政治共同体。相反,那些由社会机构、资本、地方官僚利益所利用法律作为治理之术对移民“非法性”再生产,“人”与“地”相分离而陷入了“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成为“小写人民”(the people),(64)阿甘本认为,“小写人民”是指在具体的司法—政治结构中,又始终特指在共同体中被征服的、受压迫的底层人口,即“被从政治中排除出去的阶层”。运用在到边疆群体描述中,这部分被征用和压迫的移动群体,无法扭转生命政治的结果而陷入“例外状态”之中。Agamben.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trans.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M].Minneapoli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29.这部分群体也因而成为边疆区域所要过滤与治理对象,比如在美墨边疆,已经成为一条实质性的“生命政治边疆”(bio-political border),大量的移民识别与规训,成为美国后福特制时代所亟需的低成本劳动力储备库。(65)Vaughan-Williams,Nick.The Generalised Bio-Political Border? Re-conceptualising the Limits of Sovereign Power[J].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09,(4).在人与地的互动与权力关系网络实践中,边疆表现出某种“制度化”的稳定性特征,“这一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人们的互动建立稳定的结构,并且因此减少不确定性以及提高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性”(66)Paasi,Anssi.Boundaries as Social Processes:Territoriality in the World of Flows[J].Geopolitics,1998,(1).。其中,地缘政治与生命政治交互存在与影响,而民族国家主权作为一个权力的顶层,逐步开始俯身面对边疆底层生活问题并给予回应。
再者,“地/地”分析模式。随着“边疆区”(border regions)概念的提出与成熟,边疆区域内部以及由内部所延伸的不同地点构成了主体性分析的另一视点。最为典型的是马丁斯(Oscar Martinez)提出的“边疆类型学”,边疆区特有的地缘政治优势促进了不同群体的观念和文化交流,这有利于民主制度模式的构建,但也存在族群歧视与冲突等特定问题。他按照跨境交流领域与交流频度,由低到高把边疆分为分离化边疆、共存化边疆、共享化边疆以及交融化边疆,(67)Martinez O.The Dynamics of Border Interaction:New Approaches to Border Analysis[A]. Schofield H C.World Boundaries[M].London:Routledge,1994:1~14.表面上是边疆类型参差多样最终形成了不同主体所认可的边疆类型划分,实质上则是全球化边疆区域受影响程度不同的边疆群体权变的在地选择,边疆继而具有了“建构主义”所呈现的后现代研究方法生成的过程特征。更为微观层面上,这种关系模式分析围绕着人群的流动痕迹进行,比如有学者质疑美国社会的影响和劳动力市场对墨西哥移民群体的同化带来的移民与家乡存在“弱关系”的判断,他们研究发现移民身份具有“黏着性”特征,墨西哥移民与墨西哥家乡的社群之间具有持续性的联系,(68)Robert R.Alvarez,Jr.The Mexican-US Border:The Making of an Anthropology of Borderlands[J].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5,(124).身份意义的政治边疆可以在“故地”,亦可同时在“他乡”,流出与流入之地“内外交织”连带性的“强关系”所带来的身份性关联构成用来定位和确认美国边疆移民政策问题建构的关键指标,边疆在此可视为一个身份可以转换和交叠的地方。边疆主体在动态化的外部反复影响中形成了一套内在化的自我认知,认识自身能力有限性并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重塑我者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进而通过多样认同、社会化网络、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合法与非法的关系网络把边疆线两边人们联系在了一起,(69)Martinez O.The Dynamics of Border Interaction:New Approaches to Border Analysis[A].Schofield H C.World Boundaries[M].London:Routledge,1994:1~14;Oscar J.Martinez.Border People:Life and Society in the U.S-Mexico Borderlands[M].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94:6~10.最终形成了一种依据群体区分而非空间融合的全球“流动体制”(mobility regime)(70)Ronen Shamir.Without Borders? Notes on Globalization as a Mobility Regime[J].Sociological Theory,2005,(2).,同时也加大了边疆治理难度。
总之,3种分析模式表明,民族国家在边疆区域的单一空间范围的“主权”问题不断转换为多主体空间范围的“人”的问题。通过“边疆人群”的视角研究边疆区域的社会结构、民众身份认同以及边疆文化式样等,(71)Van Houtum H.An overview of European geographical research on borders and border regions[J].Journal of BorderlandsStudies,2000,(1).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族群、社群及个体之间的复杂性关系在边疆区域的不同层次、不同维度展现开来,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结构与外部政治结构之间的界限在边疆区域相互交错叠加而变得日益模糊。边疆区域的权力格局和治理性质发生了很大改变,一方面在边疆多元主体参与的场域中,政治权力关系不断调整与反复重组,以往民族国家的边疆区域等级分明的官僚体制演化为了错杂交叉、多样分布的立体性权力结构。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陌生、不确定已成为边疆社会日常生活的常态……人们的时空感和身份认同都变得模糊、随意、碎片化与摇摆化”(72)Michel Agier.Borderlands: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he Cosmopolitan Condition[J].Polity,2016,(7).,不同主体的参与使得边疆化过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从而使风险变得不可预测和难以控制,其治理成效需要考虑特定的时空情境而被认为是一种“权变治理”(governing through contingency)(73)Chris Perkins and Chris Rumford.The Politics of(Un)fixity and the Vernacularisation of Borders[J].Global Society,2013,(3).。也有学者通过分析边疆与领土之间的复杂关系将这种变化的过程特征描述为民族国家从马克斯·韦伯所理解的“主权国家”向福柯所称谓的“治理国家”转变。(74)Rumford,Chris.Rethinking European Spaces:Territory,Borders,Governance[J].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2006,(3).
深层次分析,“空间重塑”和“主体转向”两者在此有了逻辑交汇,既有暗合的部分,也有分殊的内容,两者都是全球流动的结果,但流动性的理性化过程也往往伴随着问题产生,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多表现为流动要素的释放以及带来的空间张力变化的影响,后者表现为主体因流动能力的差异性而带来不同的际遇以及治理政策的摇摆。在后者,部分群体获得全球化流动带来的福利,其他群体却遭遇“锁定”(enclosed),这种流动迫切需要明确是,什么样的主体又通过什么样流动行为塑造了边疆社会?人类学家拉杜(C.Radu)强调了个体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互动,他认为“边疆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边疆地区人们的动态与互动中产生变动,边疆具备一定的施事(agentive)能力,能够成为行为体(actant)”(75)Heyman,Josiah.The Mexico-United States Border in Anthropology: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1994,(1).。换言之,边疆区域具有互动能力的群体和个体都是可能性的行为体,比如一部分没有被剥夺感和无分离倾向的跨境族群,他们的共同文化认同就有可能生成跨境共生意识,也可能为边疆政治稳定注入自身的力量。(76)Henrikson K A.Facing Across Borders:The Diplomacy of Bon Voisinage[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0,(2).很显然,这种现实与现象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政治框架下人口以及所对应的“公民”这一政治概念的认识,反映在边疆治理中,使得“边境化”和“再边境化”的治理之策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可以同时在一个边疆地区出现进而形成了一种边疆化动态的混合情境,(77)Lawrence A.Herzog and Christophe Sohn.The Co-mingling of Bordering Dynamics in the San Diego-Tijuana Cross-Border Metropolis[J]. Luxembourg Institute of Socio-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s,January,2015,(2).甚至很多时候需要民族国家之间“协调边疆化(co-bordering)”(78)Matthew Longo.A “21st Century Border”? Cooperative Border Controls in the US and EU After 9/11[J].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2016,(2).实施协同合作治理。在价值层面上,学者对不同主体差异性行为进行分类与反思,那些流动能力受限者可能会遭受国家与资本捆绑的“污名化”的非法再生产,(79)Galemba,Rebecca B.Illegality and Invisibility at Margins and Borders[J].Po LAR:Political and Legal Anthropology Review,2013,(2).甚至成为某些大国受剥削的劳动力群体。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全球化中同样存在着与“图绘”(mapping)相对的“反图绘”(anti-mapping)博弈与竞争,(80)Marina Tazzioli.Which Europe? Migrants’ Uneven Geographies and counter-mapping at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Movements[J].Journal for Critical Migration and Border Regime Studies,2015,(2).边疆区域民众并非完全被动卷入全球化,而是表现出了自身的主体性。由此可以看出,民族国家对边疆民众单一向度的压制性难以奏效,边疆民众以生产性的面向构建他们的世界并带来了某种自身逻辑亦可以感知的生命政治格局。
三、余论与展望
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边疆实践增添了民族国家转型理解的新途径。当“国家再一次拥有边疆而不是边界……乃是因为边疆与其他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且,它们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与各种跨国集团的交往之中”(81)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4.。边疆内涵以全球化相适应的新政治观念与思维方式展现,“边疆、民族国家与全球”的整体性认知构成了边疆观理解的定位与民族国家转型的参照。一方面是以现实的空间政治格局和复杂的权力结构来考量边疆社会的关系与秩序,进而理解以边疆为对象的外围联系并阐释其与民族国家内部区域的结构性关联,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更具普遍性和解释力的民族国家的变迁框架与动力机制。从这层意义看,对全球化时代边疆观的追寻与探索为认识“民族国家/边疆”之间长期紧张状态的缓解带来了一个新视角。另一方面也清晰地看到,西方学者从边疆内涵的反思与批判入手,强调在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元素之外,边疆主体力量开始在非民族国家层面上展开,权力对象与关系开始面向边疆日常生活实践重构,边疆社会存在的冲突与合作得到了新的解释,所形成的与“民族国家”分析视角迥然不同的“边疆视角”(seeing like a border)(82)Chris Rumford.Towards a Multiperspectival Study of Borders[J].Geopolitics,2012,(4).。正是从边疆“空间重塑”与“主体转向”相互生成与促进的视角出发,边疆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内部地方性治理范畴,透过边疆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治理在理念、思维、方式与具体途径上的转变与效果。
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边疆空间重塑,还是边疆治理主体转变,边疆并非民族国家主权所指向的消极化状态,而恰恰相反,在边疆在地日常实践中,民族国家主权在不断调试、重组与转型进而通过边疆变迁展演了民族国家主权在时空上的延伸、改变与重构。通过边疆观演变的阐释,使得边疆成为一种从边缘和具体场景中展开的分析策略,既跳出了边疆与民族国家“削弱-强化”的二元性论调,也摆脱了叙事分析上的“方法论上的国家中心主义”(83)赵萱,刘玺鸿.当代西方批判边界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19,(1).,形成了一种观察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权力与组织转型的新视角。那些对构成民族国家的标识性要素进而赋予了诸如领土、人口、边界、权力等固定性概念以全球化式的内涵与意义。
我们从民族国家边疆在全球化时代时空演变入手,阐述了边疆空间如何被重构,边疆治理如何发生转型继而揭示了边疆在民族国家主权实践中的多歧性面相。全球化流动性世界里,把传统边疆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转化为以边疆作为一种分析方法,通过日常生活和在地实践观察边疆,分析其内涵如何在不同空间与主体话语中型构及如何不断被塑造以发挥差异性功能,进而把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多样的边疆实践纳入到观察视野中,有助于认识全球化时代边疆治理理念的变迁和背后民族国家转型以及内在逻辑。“以边疆为方法”的方法论层面的普遍性意义在于,一方面能够消解民族国家的“国家中心主义”带来的对底层社会(比如边缘区域或人群的利益)主体性、能动性与相关利益的忽视或遮蔽,重视或重拾这一部分人群的关注,或许能够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转型以及民族国家需要多方位地维护自身的整体性利益;另一方面也能够缓解民族国家与国内某一特定空间公共事物治理的理念与目标之间的紧张与冲突,理解这一张力有助于认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内外关系以及探寻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纾解之道。但随着全球公共事务治理增多和全球权力格局不平衡加剧,尤其是风险社会加剧(比如新冠肺炎的世界性传播带来的影响)以及伴随的所称谓“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民族国家重新扎紧了交流与交往的口袋,直接导致了边疆传统“闭合性”的阻断与障碍属性出现了回潮,至于边疆社会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边疆治理又将如何转变以及民族国家主权实践如何演变,期待更多学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