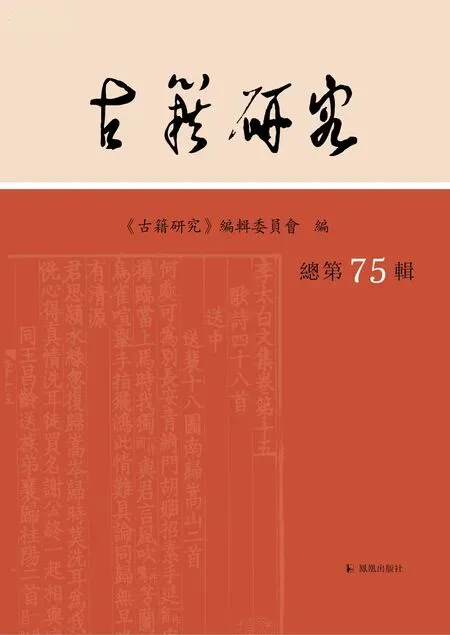《世説新語·企羡》王導“洛水邊談道”疏證*
——兼論王導在東晋詩歌史上的意義
孫銀莎 蔡彦峰
關鍵詞:王導;洛水邊談道;玄學;言盡意;詩歌
王導是東晋前期政壇上重要的人物,歷史上對其評價也主要在政治方面,陳寅恪《述東晋王導之功業》即指出:“王導之籠絡江東士族,統一内部,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獨立,文化因得以續延,不謂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論也。”(1)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77頁。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段評論中陳寅恪還提到王導對東晋文化的功勞。陳寅恪、錢穆等學者都曾指出士族在魏晋南北朝文化學術發展中的重要意義。(2)如陳寅恪:《崔浩與寇謙之》,《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147—148頁。錢穆:《略論魏晋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作爲高門士族的代表,又是東晋政治中舉足輕重的人物,王導對東晋文化學術上的發展也有重要的影響,但這在有關王導的研究中極少得到關注。本文將從《世説新語·企羡》所載王導過江前在洛水邊談道這一條材料出發,分析王導的玄學清談的内涵及其對東晋學風和文學的影響,從一個側面揭示王導在東晋學術和文學上的意義。
一、 王導“洛水談道”所談何道?
《世説新語·文學》:“舊云:王丞相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3)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1頁。歷來講到王導的清談都會引此條爲據,這是瞭解王導乃至整個東晋清談的重要材料,劉孝標注認爲“三理”分别出自嵇康《聲無哀樂論》《養生》及歐陽建《言盡意》,但是王導所談的内容是什麽則無從得知。《世説新語·企羡》中還有一條材料:
王丞相過江,自説昔在洛水邊,數與裴成公、阮千里諸賢共談道。羊曼曰:“人久以此許卿,何須複爾?”王曰:“亦不言我須此,但欲爾時不可得耳!”(4)《世説新語箋疏》,第630頁。
這條材料一直没有得到重視,却是瞭解王導玄學思想的重要記載,因此有必要對這段材料進行相應的闡釋。與王導“談道”的裴頠、阮瞻都是玄學家,但兩人的玄學思想有質的區别。阮瞻是竹林七賢之一的阮咸的兒子,《晋書·阮瞻傳》載:“(阮瞻)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5)(唐)房玄齡:《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1363頁。《世説新語·文學》將此事歸爲阮修與王衍,據學者考證,當以《晋書》所載爲是。(6)莊亦樂、閆新春:《“將無同”考》,《許昌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第9—11頁。這是現在所能看到的,阮瞻在玄學上的主要事迹,因此對“將無同”的解釋,關係到對阮瞻玄學思想的理解。歷來大多將“將無同”解釋爲:大概没什麽不同吧。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阮宣子(修)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衍)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7)王仲犖:《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04頁。把“將無同”斷句爲“將‘無’同”,“無”就是何晏、王弼所説的萬物之本體,所以“將無同”的涵義是聖人與老莊、名教與自然,皆統一於“無”,在“無”這一本體上是相同的。《世説新語·文學》載:“王輔嗣弱冠詣裴徽,徽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於有,恒訓其所不足。’”(8)《世説新語箋疏》,第199頁。王弼即認爲聖人體無,老莊言無,歸根到底都可以通過“無”而溝通,阮瞻的“將無同”正是對王弼玄學思想的言約旨遠的表述,故得到王戎的咨嗟歎賞。由此可見阮瞻是玄學中的“貴無”論一派。
《世説新語·文學》“袁彦伯作《名士傳》成”,劉孝標注云:“(袁)宏以裴叔則、樂彦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爲中朝名士。”(9)《世説新語箋疏》,第272頁。中朝名士多任性縱情,《世説新語·德行》:“王平子、胡毋彦國諸人,皆以任放爲達,或有裸體者。”劉孝標注:“王隱《晋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遊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脱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爲通,次者名之爲達也。’”(10)《世説新語箋疏》,第24頁。這是由“貴無”玄學發展而來的虚無放廢之風,可見阮瞻等人皆屬於“貴無”玄學一派。裴頠則對“貴無”一派的思想作風極爲不滿,臧榮緒《晋書》記載:“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魏末以來,轉更增甚。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虚,不尊禮法。屍禄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甚,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頠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藪。世雖知其言之益治,而莫能革也。朝廷之士,皆以遺事爲高,四海尚寧,而有識者知其將亂矣。”(11)《世説新語箋疏》引,第202頁。《崇有論》中對當時的“貴無”之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遊之業,埤經實之賢。……是以立言藉於虚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12)《晋書》,第1045頁。。可見裴頠與阮瞻等元康放達派名士,在思想行爲上極爲不同,因此王導與裴頠、阮瞻的“談道”應該關涉的是玄學上一場“崇有”與“貴無”的論辯。
在這場“談道”中,王導是基於什麽樣的立場呢?這是此前在探討王導清談“三理”所没有注意的問題,却又關係到對王導清談的準確理解。《世説新語·品藻》:“王丞相云:‘頃下論我比安期、千里。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余嘉錫案云:“《御覽》四百四十七引《郭子》,‘頃下’作‘洛下’,‘亦推此二人’作‘我亦不推此二人’,皆於義爲長,《世説》傳寫誤耳。”(13)《世説新語箋疏》,第514頁。其説可從,王導不推阮瞻、王承二人,大概與二人皆屬於放達的中朝名士有關。王導較崇實幹,與“貴無”玄學士人口談虚無不同,《晋書·王導傳》載南渡之後王導對晋元帝分析西晋以來的社會風氣説:“自魏氏以來,訖於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厭於安息,遂使奸人乘釁,有虧至道。”(14)《晋書》,第1746頁。這與裴頠《崇有論》對當時社會的看法相同,正是對“貴無”影響下的社會風氣的批評,説明這場“洛水談道”中,王導的思想主張應當是與裴頠相近的。
《崇有論》載於《晋書·裴頠傳》中,全文共分五段,二、三、四段旨在破“貴無”,第一、五段則旨在立“有”,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自生”的思想:
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爲已分,則虚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虚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
裴頠提出了與貴無玄學“有生於無”“以無爲本”針鋒相對的“自生”思想。“自生”這一概念並非裴頠首創,王充《論衡》即多言“自生”,如《論衡·自然》:“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又《言毒篇》:“萬物自生,皆察元氣。”向秀《莊子注》也言“自生”,張湛《列子·天瑞》注云:“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15)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頁。王充講的“自生”是在反對“天地故生物”這種神學目的論時提出來的,其意思是萬物由元氣自然而然産生,仍屬於宇宙生成論。向秀雖然有意地以“自生”來揚棄貴無論玄學“有生於無”的生成命題,但他又講“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這種“不生不化者”就是“無”,可見向秀仍然偏向於貴無論玄學的“以無爲本”。裴頠則賦以“自生”新的内涵,不僅否定“有生於無”,而且他進一步説“自生必體有”,這正是針對貴無論“以無爲體”而提出的,意謂“萬有”的“自生”是以其自身的存在爲根據的,“有”是其自身存在的根據,這一包含了“以有爲體”的命題否定了“無”的本體意義(16)湯一介:《郭象與魏晋玄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17—218頁。,某種程度上摧毁了貴無論玄學的理論基礎。(17)余敦康:《魏晋玄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41頁。因此《崇有論》提出後即引起很大的論争,《世説新語·文學》注引《惠帝起居注》曰:“頠著二論(《崇有論》《貴無論》(18)《世説新語·文學》注引《晋諸公贊》云:“頠疾世俗尚虚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第201頁)余嘉錫先生認爲:“頠《貴無論》即附《崇有論》後。此引無‘貴無’二字,蓋宋人不考《晋書》,以爲頠既‘崇有’不應複‘貴無’,遂妄行删去。不知《崇有》只一篇,安得謂之二論乎?”而馮友蘭先生則認爲《崇有》二論的“二”乃“之”字之誤。但《三國志·魏志·裴潜傳》注引陸機《惠帝起居注》説:“頠理具淵足,贍於論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虚誕之弊。”這裏則明確説裴頠作了《崇有》《貴無》兩篇,馮友蘭先生認爲“貴無”二字是後人妄加上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四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111頁)。余、馮兩位先生的意見正好相反。許抗生《魏晋玄學史》(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79頁)、湯一介《裴頠是否著有〈貴無論〉》(《學人》第十輯,1996年第6期)都引晋人孫盛《老聃非大賢論》:“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二論。”認爲裴頠著《貴無論》是有可能的。我們認爲不管裴頠是否作過《貴無論》,都不會影響其《崇有論》的哲學性質,從裴頠的哲學出發點來看《貴無論》很可能是從否定的角度提出來的,即對貴無説加以批判;從寫作體制上看,《崇有》《貴無》二論就如班固《東都賦》《西都賦》合稱《兩都賦》,故有時又直接稱爲“《崇有》二論”。)以規虚誕之弊。文詞精富,爲世名論。”又説:“裴成公作《崇有論》,時人攻難之,莫能折。唯王夷甫來,如小屈。時人即以王理難裴,理還複申。”(19)《世説新語箋疏》,第201頁。《文心雕龍·論説》云:“夷甫裴頠,交辯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20)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327頁。這些説明在貴無之風盛行的西晋,裴頠《崇有論》的提出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成爲當時清談的焦點。
瞭解了這一學術背景,我們再來看王導與裴頠、阮瞻等人的“洛水談道”,雖然文獻中没有記載他們“談道”的具體内容,但在分析當時的學術語境下,還是可以認爲這是一場崇有與貴無之間的論争。前文分析指出王導的思想立場與裴頠相近,也就是説王導在這場“洛水談道”中是接受了裴頠的“崇有論”玄學的。裴頠《崇有論》的目的是糾正當時的虚誕之風。南渡之後,東晋士風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總體上否定了西晋虚無放廢的作風,並且對這種士風的思想根源進行了反思,如戴逵《放達爲非道論》、王坦之《廢莊論》、孫盛《老聃非大賢論》、江淳《通道崇儉論》等,這正是裴頠、郭象等人對“貴無”玄學思想的糾正的繼承。王導與裴頠等人對“崇有”的探討,對兩晋玄學思想從“貴無”到“獨化”的發展,及東晋崇實士風的形成皆有重要意義,所以王導對這個經歷頗感自豪,而時人也認識到王導在玄學的這一發展進程中的作用,故羊曼謂之“人久以此許卿”(21)參見蔡彦峰:《從“得意忘言”到“言盡意”——言意之辨的發展及其詩史意義》,《國學研究》,第31卷,第238頁。。《羊曼别傳》載:“曼頽縱宏任,飲酒誕節,與陳留阮放等號爲兖州八達。”(22)《世説新語·雅量》劉孝標注引,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第363頁。這是典型的元康名士的放達做派,而渡江後他又與庾亮、温嶠、桓彝等並稱爲“中興名士”(23)《晋書》,第1382頁。,所謂的“中興”指的就是東晋時期,其時間從東晋建立到中期。庾亮、温嶠、桓彝等人皆是頗重實幹的東晋名臣,《晋書·羊曼傳》載其過江後代阮孚爲丹陽尹:“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云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24)《晋書》,第1383頁。其留意事功、注重名節,已非西晋放達名士可比擬,可見就是像羊曼這樣的西晋名士,渡江後也經歷了思想、風格的轉變,這是兩晋思想和士風發展的一個大勢。可以説羊曼以親身的經歷瞭解了王導在這場轉變中的意義,因此有“人久以此許卿”的回答,這裏的“人”正是以羊曼本身爲代表的士人。這些都説明王導在“洛水談道”中與崇有論玄學所建立的内在關係,這實在是東晋思想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
二、 從“貴無”到“崇有”:王導與東晋玄學思想的轉變
王導與裴頠等人的“洛水談道”,説明他在過江前就深受玄學的影響,因此過江後仍熱衷於清談。《世説新語·文學》説王導過江後清談的内容是“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然宛轉關生,無所不入”,即能曲盡其妙、剖析毫微,可見他對這幾個論題是相當精熟的。這些清談論題與王導“洛水談道”有什麽關聯或變化?這也是王導研究中一個缺乏關注和深入探讨的問題。“聲無哀樂”“養生”源自嵇康歷來幾無異議,這都是玄學關注的論題,而“言盡意”則與當時的玄學思想相悖,因此有必要對其内涵進行深入分析,以期進一步理清王導清談的内涵及其在東晋思想文化上的意義。
《世説新語·文學》劉孝標注認爲王導“言盡意”來自歐陽建《言盡意》。“言意”關係是玄學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湯用彤先生認爲玄學思想體系就是以“言意之辨”爲方法而建構起來的。(25)湯用彤:《魏晋玄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0頁。魏晋以來荀粲、王弼、嵇康等人或主“言不盡意”或謂“得意忘言”(26)參見蔡彦峰《玄學“言意之辨”與《文賦》的理論建構》,《文藝理論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4—129頁;《從“得意忘言”到“言盡意”—— 玄學“言意之辨”的發展及其詩史意義》,《國學研究》,第31卷,第235—236頁。,兩説雖有所區别,但“均終主得意廢言也”(27)湯用彤《魏晋玄學論稿》,第22頁。。歐陽建《言盡意》開篇説:“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即針對當時玄學普遍主張“得意忘言”而發的,歐陽建在分析名的來源、作用和意義之後説:“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回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矣。苟其不二,則言無不盡矣。”(28)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2084頁。雖然在先秦《墨子·經説上》中有所謂“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吕氏春秋·審應覽·離謂》也説:“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其中都包含有言盡意的意思。(29)參見樓宇烈:《〈言盡意論〉正讀》,《人民政協報》,1998年2月16日,第3版。但是歐陽建將批評的矛頭對準當時的言不盡意説,特别是那種認爲語言在傳達事物根本道理時毫無作用,因而主張不用語言的觀點,如張韓的《不用舌論》,因此其《言盡意論》有其現實及思想史的意義。玄學是思辨性很强的哲學,求新意識濃厚,在理論上常追求推陳出新,如聖人有情、聲無哀樂、言盡意、逍遥遊等論題上,都體現了玄學士人求新的意識。《世説新語·假譎》云:“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傖道人爲侣,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30)《世説新語箋疏》,第859頁。這條材料雖説的是般若學心無宗創立的緣起,却體現了東晋對新思想、新理論的熱衷。王導對歐陽建《言盡意論》的接受,自然也有這種求新意識的緣故。但是歐陽建《言盡意論》所探討的是形而下的名實問題,屬於形名之學的範疇,其哲學理論價值不高。(31)康中乾:《魏晋玄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8頁。在東晋玄學求新意識的背景下,我們認爲王導所談“言盡意”不是僅述歐陽建之義,毋寧説歐陽建之説只是王導“言盡意”的第一層次,王導對這一論題還有更進一步的發展,所以時人才會謂之“宛轉關生,無所不入”。
從思想學術淵源上來講,王導之所以能對“言盡意”論有新的發展,與他和裴頠等人的“洛水談道”的經歷有重要的關係。裴頠“崇有論”講“自生”,主張“自生必體有”,這是玄學思想上的一個進步,但是裴頠在批判“貴無論”時,認爲“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在他看來“無”就是“虚無”,是没有用的,他説:“濟有者皆有也,虚無奚益於已有之群生哉。”這説明裴頠對玄學“有”“無”缺乏綜合,這一任務由郭象“獨化論”玄學來完成。但“崇有論”講“自生”,這與郭象“獨化論”玄學的邏輯起點是相同的,並爲郭象“獨化論”做了必要的思想準備,因此,王導在與裴頠等人的“洛水談道”中接受了“崇有論”的玄學思想,有助於他理解和接受郭象的“獨化論”玄學。郭象《齊物論注》云:“是以涉有物之域,雖複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之境者也。”這是郭象“獨化”論玄學的基本思想,湯用彤即指出:“懂得此語即懂得向郭之學説。”(32)《魏晋玄學論稿》,第163頁。其内涵是指萬物在本質上都是自生、自爾、自爲、自然的,並在其自身的發展變化中體現爲一種微妙幽深的玄冥之境。這是對莊子“道”的“境界形態”之義的發展。“玄冥”是一種境界,如何進入這種境界,郭象提出了“無心”,《齊物論注》云:“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要進入玄冥之境,“作爲認識活動之主體的‘心’就不能處在通常意義下的主客二分的狀態中,而必須處在主客合一或‘天人合一’的‘齊物我’狀態中,即‘心’的掘然自得、塊然自生、芚然無知、窅然無爲的狀態中,這就是‘無心’”(33)《魏晋玄學》,第224頁。。在這種主客合一的“無心”狀態下,“主體的‘心’本身就將自己境界化、意境化,實際上這時的主體‘心’就由原來的認識活動轉入到了審美活動,也就處於‘獨化’的狀態中了,達到了心、物在存在性上的同構”(34)《魏晋玄學》,第226—227頁。。即郭象説的“無心而自得”(《莊子齊物論注》),認識活動由“有心”到“無心”的這種轉變,可以稱之爲玄學的審美進程。而如何做到“無心”?郭象提出了“忘”,《大宗師注》云:“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郭象的“忘”來自莊子,《莊子·大宗師》説“相忘乎道術”,《外物》講“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莊子講的“忘”與王弼的“得意忘言”之“忘”不一樣,王弼的“忘”是遺忘、遺棄之意,而莊子的“忘”則是心物合一的得意、體道之法。(35)參見蔡彦峰《從“得意忘言”到“言盡意”—— 玄學“言意之辨”的發展及其詩史意義》,《國學研究》,第31卷,第234—236頁。在“言意”問題上,郭象提出“寄言出意”,這既是他注《莊子》的方法,又是一種認識論,從認識論的性質來説,“寄言出意”與《莊子》的“得意忘言”本質上是相近的(36)⑤ 《郭象與魏晋玄學》,第255頁。,但是王弼也講“得意忘言”,爲了與貴無玄學相區别,郭象特提出“寄言出意”。《説文解字》:“寄,托也。”(37)段玉裁:《説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41頁。孫綽有“莊子多寄言”(38)李善:《文選注》,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注》,蕭統撰、李善注:《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19頁。。“寄言”在於“出意”,與莊子的“忘”一樣,“寄”是“得意”之法,可見郭象的“寄言出意”是以“即用是體”爲言的⑤,由“寄”以體道,只能通過審美而實現,因此,郭象的“寄”也具有審美方法的性質。從審美的角度來講,郭象説的“寄”與魏晋文學中的“興寄”實有關聯,“興寄”的基本方法即將情感寄托於審美意象之中,這是郭象玄學與文學重要的内在關聯之處。
郭象“自生”“獨化論”的玄學是對裴頠“崇有論”玄學的發展和系統化,代表了玄學理論發展的最高水準,因此東晋以來玄風雖然極盛,但玄學理論本身已無法進一步發展,玄學由正始、西晋時期抽象思辨的理論探索,發展爲士人的生命體驗和生活方式。王導“言盡意”就是在玄學的這一轉型中提出來的,從上文的分析來看,王導與裴頠等人的“洛水談道”使他對玄學從“貴無”到“崇有”再到“獨化”的發展極爲熟知,甚至可以説王導是參與到玄學的這一發展進程中的。因此,其“言盡意”也就帶有明顯的時代學術特點,也就是從“言”“意”的抽象思辨中轉化爲以審美爲體道的方法。王導“言盡意”可以説就是“獨化”的思想方法的運用而得。郭象認爲萬物皆“獨化於玄冥之境”,即自我顯現於本體之境,也可以説自我顯現即本體之境,“獨化”與“玄冥之境”的關係是,“‘獨化’是‘玄冥之境’工夫進徑,即工夫即本體,‘玄冥’即本體即工夫,是郭象玄學的最高境界”(39)黄金榔:《玄學言意之辨與後代詩學理論之關系》,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88頁。。由獨化工夫進入的玄冥之境,就是道的境界。既然萬物都藴涵玄冥之境,語言自然也包括在内,從“獨化”論角度來講,“言盡意”就是語言的“獨化”進程,“意”是“言”之“獨化”而成的境界,在語言的藝術之境中體悟“意”,所以“言意”是二而合一的即體即用,並不局限於作爲認識論的“言意”的主客對立。王導運用郭象“獨化”論發展出“言盡意”之説,可以説把握住了莊子“得意忘言”論。莊子講的“忘”是一種獨特的體道之法,王導“言盡意”之“盡”與莊子的“忘”内涵相近,也就是在審美中使“道”自我顯現,這是王導“言盡意”的本質。
三、 王導“言盡意”與東晋詩歌的發展
共同的文化心理是塑造和團結一個群體的重要因素,作爲思想和實幹兩者兼長的政治家,王導深諳此道,因此渡江之後王導在政治上推行“鎮之以静”的策略,文化上則提倡清談以引導士人的精神生活。他所談“三理”不僅出於玄學理論上的興趣,也是一種以身作則的示範,在王導的宣導下,東晋玄風重新興盛起來,培養了一批清淡名士,如謝尚、劉惔、王濛等,這些輩分稍晚的名士都曾預王導組織的清談,形成了“中興名士”群,這個“中興”既是政治上的,也有玄學復興之意。正是從這一點來講,王導在東晋思想文化上也有重要的影響。
前文指出王導“言盡意”有兩個層次,一是來自歐陽建的形而下的名實問題;二是由莊子和郭象發展而來的關於本體境界的表現問題。王導“言盡意”的這兩個層次對東晋文學産生了重要的影響。
王導《重議周札贈謚》云“原情盡意”(40)《晋書·周札傳》,第1577頁。,這裏的“盡意”就是名實層次上的“言盡意”,也就是主張語言能够表現意義。貴無玄學“得意忘言”的言意觀,以及清談中追求“言約旨遠”的風格,都有忽視語言價值的傾向,與作爲語言藝術的文學背道而馳,因此“貴無”論者往往不具有文學創作的才能和實績,如《世説新語·文學》載樂廣“善於清言,而不長於手筆”(41)《世説新語箋疏》,第252頁。。這其實是西晋清談名士的普遍特點,西晋的清談家幾乎都没有文學作品留世,與“得意忘言”的語言觀是有重要關係的。與此相對的是,主“崇有”論的玄學士人則體現出截然不同的語言觀,如《世説新語·文學》劉孝標注:“(裴)頠疾世俗尚虚無之理,故著《崇有》二論以折之。才博喻廣,學者不能究。後樂廣與頠清閑欲説理,而頠辭喻豐博,廣自以體虚無,笑而不復言。”(42)《世説新語箋疏》,第201頁。裴頠的“辭喻豐博”與樂廣的“辭約旨遠”,體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觀。與裴頠同時的郭象,其清談亦以辭藻豐富爲特點,王衍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43)《世説新語箋疏》,第438頁。王導“言盡意”即是對“崇有”一派語言觀的總結,對語言的作用和價值的推崇,對東晋時期清談與文學走向融合具有積極的促進意義。
西晋大亂之後,東晋清談能够重新興盛起來,與王導等人的積極倡導有很重要的關系(44)《世説新語·品藻》載:“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第517頁)劉孝標注云:“或清言析理,何不逮謝故邪?”(第517頁)可見王導對清談的重視。,东晋人对王导之功是很清楚的,孫綽《丞相王導碑》即特别點出王導“雅好談咏,恂然善誘。”(45)《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1813頁。東晋前中期最重要的清談名士,如殷浩、衛玠、謝尚、劉惔、王濛、王羲之、謝安等人,都與王導關係密切,常參加王導組織的清談,所以王導“言盡意”對東晋士人的影響極爲顯著,可以説是東晋玄學的新方法,這是東晋清談能開創新局面的重要原因。“言盡意”重視語言之美的價值,《世説新語》中這類記載極多,如《文學篇》:
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遥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46)余嘉錫《世説新語箋疏》,第223頁。
崇尚辭藻豐富的語言之美,是東晋清談普遍的特點。吕思勉《兩晋南北朝史》指出:“玄學初興,重在明悟,不在多聞。及其抗辭求勝,則不得不炫博衿奇。”(47)吕思勉:《兩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46頁。兩晋清談風格之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王導“言盡意”影響下語言觀的轉變有直接的關係。東晋人在清談之前甚至需要事先構思、撰寫清談的語言,《世説新語·文學》載:“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並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别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48)《世説新語箋疏》,第228頁。所謂的“義言”即談義理的語言,這與文學創作已極爲接近。從這一點來講,王導“言盡意”也具有重要的文學意義。
與西晋清談士人相比,東晋清談士人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即清談與創作並重。(49)彭玉平:《魏晋清談與論體文之關係》,《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2期,第143—154頁。認爲曹魏時期 “清談與著論同擅名聲”,但是何晏、阮籍、嵇康等人本身都是文學家,事實上曹魏西晋時期,清談與作論已比較明顯分爲兩途了。王衍、樂廣等西晋清談領袖,幾乎没有作品傳世,東晋清談家則在口談之外還擅長創作,《世説新語·文學》“江左殷太常父子”條注引《中興書》稱殷融“理義精微,談者稱焉。兄子浩亦能清言,每與浩談,有時而屈,退而著論,融更居長”。可見殷融、殷浩在清談之外都還作論。此外如王坦之的《廢莊論》、李充的《釋莊論》、孫盛的《老聃非大賢論》、支遁《逍遥論》《即色論》,謝萬《八賢論》、孫綽《名德沙門論目》《道賢論》等,從嚴可均《全晋文》所載來看,東晋清談士人論體文的寫作遠遠超過正始、西晋清談家,這與清談士人自身的寫作才能有關,但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還在於兩晋清談語言觀的轉變。如果從文學創作實踐來看,這種區别就更加明顯,西晋清談士人幾乎都無文學創作實績,而東晋清談名士如庾亮(50)鍾嶸《詩品序》説:“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頁)可見桓温、庾亮等人也進行詩歌創作。、桓温、謝安、王羲之、支遁、孫綽、許詢等皆是兼具清談家與作家兩種身份的(51)參見蔡彦峰:《東晋清談與吴聲歌的流行及其詩史意義》,《文學遺産》,2016年第2期,第55—64頁。,劉躍進先生指出兩晋名士清談上的區别“東晋名士又增加了詩的成分”(52)劉躍進:《蘭亭雅集與魏晋風度》,《安徽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第8頁。。東晋清談名士的聚會,除了談名理之外,也常常進行文學創作,如《晋書·謝安傳》載謝安隱居東山與支遁、許詢、孫綽、王羲之等人“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咏屬文。”而永和九年的蘭亭雅集更是清談賦詩的盛會。所以東晋這些重要的清談家都有文學作品傳世,孫綽、許詢更是一代文宗,支遁、王羲之也取得頗高的文學成就。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説:“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鍾嶸《詩品序》也説:“永嘉時,貴黄老,稍尚虚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這種清談影響於文學創作,至東晋才成爲一種潮流。雖然鍾嶸批評玄學影響下的創作爲“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但是東晋玄言作家其實是非常重視語言之美的,與東晋清談一樣追求“辭條豐蔚”,如簡文帝贊美許詢詩:“玄度五言詩,妙絶時人。”檀道鸞《續晋陽秋》説許詢“有才藻,善屬文”,孫綽《蘭亭詩》贊美蘭亭雅集的清談、創作是“攜筆落云藻”,其《天臺山賦》辭藻富麗,支遁的五言詩也以辭藻之美著稱(53)參見蔡彦峰:《支遁的五言詩創作及其詩史意義》,《文藝理論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3—114頁。。總體上看,東晋人的詩歌創作比較自覺地追求品鑒式的語言,這是其審美方式的體現,却也説明東晋清談士人對語言之美的自覺追求,正是這種語言觀,才使東晋的清談和創作走向融合,一改西晋清談、文學分爲兩途的作風。兩晋清談士人與文學關係上的這種轉變,與王導“言盡意”的普遍影響有密切的關係。
從語言表現本體境界這一層次來看,王導“言盡意”對東晋人的審美及詩歌的寫作方法也有顯著的影響。與莊子“得意忘言”、郭象“寄言出意”一樣,王導“言盡意”也具有普遍的認識論的性質,它探討的不僅是語言和意義的關係,也涉及對如何把握本體的思考,將形而下的名實提高到語言與本體關係的層次上。王導之所以能推進“言意之辨”的發展,與他在“崇有”玄學的基礎上接受郭象“獨化論”玄學思想密切相關,是從“獨化論”玄學發展而來的認識論。如何實現對本體之境的認識,郭象提出了“無心”,“無心”就使主客對立的認識活動轉化爲審美活動,從這一點來講,郭象的“寄言出意”之“寄”就與詩歌藝術的“興寄”有相通之處。王導“言盡意”之“盡”與郭象的“寄”性質相同,也就是通過審美實現、進入物我合一之“境”,在這個“盡”的過程中,“言”和“意”不是邏輯關係,而是審美關係,“言盡意”就是“獨化於玄冥之境”。
“言盡意”的審美性質,對東晋玄言山水詩産生了顯著的影響,可以説是以審美表現義理或謂之爲寄玄理於審美之中。這也是王導“言盡意”與詩歌的“興寄”的相通之處。東晋人常言“寄”“興”“想”,如孫綽回答支遁説:“然以不才,時複托懷玄勝,遠咏老、莊,蕭條高寄。”(54)《世説新語箋疏》,第520頁。所謂“高寄”即寄其玄勝之情。又如《三月三日蘭亭詩序》:“情因所習而遷移,物觸所遇而興感。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遼落之志興。”在山水中寄托“遼落之志”,其内涵即後文説的“齊以達觀,决然兀矣,焉複覺鵬鷃之二物哉。”(55)《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1808頁。又如《世説新語·言語》:“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56)《世説新語箋疏》,第120頁。其所“想”的就是《莊子·秋水》悠然自得的理趣。可見東晋人有意識地通過山水審美實現對義理的領悟的,這就是“以玄對山水”的内涵,也是玄學士人普遍的思維特點。雷次宗《與子侄書》説在廬山慧遠門下:“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57)(南朝梁)沈約:《宋書》卷九十三《隱逸傳》,第2293頁。“山水之好”可以“通理輔性”,也就是在山水審美中達到對義理的體悟,這就是王導“言盡意”之“盡”的内涵。這種以山水的審美體玄悟理的方法運用於文學創作之中,可稱之爲山水興寄法。(58)參見蔡彦峰:《玄學與魏晋南朝詩學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年,第205頁。
王羲之、謝安、孫綽等名士組織的蘭亭雅集所作的《蘭亭詩》,即集中地體現了山水賞悟興寄法。如王羲之《蘭亭詩二首》其二:
三春啓群品,寄暢在所因。仰望碧天際,俯瞰緑水濱。廖朗無崖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新。
詩中山水名理結合,所謂的“寄暢”即在山水審美中寄其悟理而得的朗暢之境,可謂是王導“言盡意”以審美表現本體的認識論在詩歌藝術上的落實。王羲之《答許詢詩》也説:“取歡仁志樂,寄暢山水陰。”説明以山水悟理確實是東晋玄言山水詩普遍的方法。《蘭亭》組詩集中體現了這一詩學思想方法,詩中大量出現的“寄”“暢”“興”“想”“散”,如:
望岩懷逸許,臨流想奇莊。(孫嗣《蘭停詩》)
契兹言執,寄傲林丘。(謝安《蘭亭詩二首》其二)
時來誰不懷,寄散山林間。(曹茂之《蘭亭詩》)
端坐興遠想,薄言遊近郊。(郗曇《蘭亭詩》)
駕言興時遊,逍遥映通津。(王凝之《蘭亭詩二首》其二)
消散肆情志,酣暢豁滯憂。(王玄之《蘭亭詩》
散懷山水,蕭然忘羈。(王徽之《蘭亭詩二首》其二)
散豁情志暢,塵纓忽已捐。(王藴之《蘭亭詩》)
肆盼岩岫,臨泉濯趾。感興魚鳥,安居幽峙。(王豐之《蘭亭詩》)
蘭亭諸人在山水欣賞中寄托對玄理的領悟及由此獲得的心境,從本質上講審美和悟理不是邏輯的關係,而是合二爲一的,這正是王導“言盡意”之意。東晋玄言詩人也説“情志”,如“散豁情志暢”“消散肆情志”等,但這種“情志”是與玄理的體悟融合在一起的。
從晋宋詩歌史來看,玄言詩的意義在於,它將抒情言志的興寄藝術運用於體玄悟理的詩歌之中,以興寄法表現哲理,發展了興寄藝術,給湛方生、謝靈運等人很大的啓發。湛方生等人的詩歌用力於寫景,即是對這種山水賞悟的興寄法的發展。謝靈運等人注重體物寫景的山水詩,其藝術淵源與東晋玄言詩不同,但寫景言理結合、寄理於景的寫作方法,應該説也是進一步發展了東晋玄言詩以興寄法言理的藝術,而其思想方法則直接來自郭象“寄言出意”、王導“言盡意”所建構的以審美爲“盡意”之法,這是王導在東晋詩歌史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