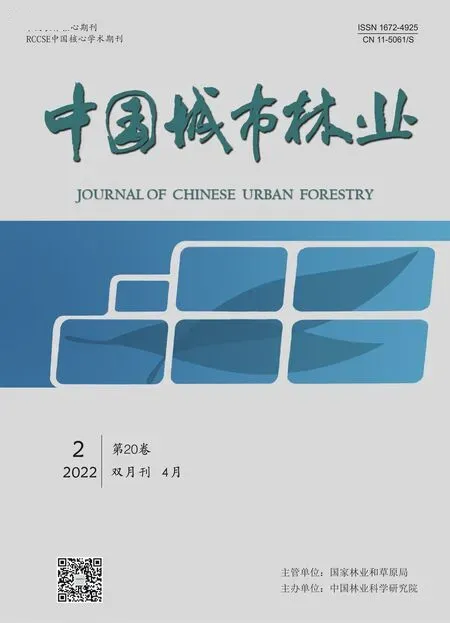公共健康需求对近代欧洲城市绿地发展的影响
关艺蕾 朱春阳
华中农业大学 武汉 430070
城市绿地在城市园林基础上发展起来, 是东西方园林文化、 人类精神健康得以发展的重要社会载体, 具有构成城市骨架、 营造城市景观、 承载城市文化、 保护生态环境、 维持环境卫生健康、提供游乐场所等多种功能[1-2]。 19 世纪以后近代工业的产生、 城市规模的扩大, 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影响城市健康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绿地内涵在追求精神健康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了对公共环境健康的需求。 19 世纪以来, 欧洲城市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之间呈现阶段性作用关系, 大致经历了4 个阶段, 即私有花园公共化阶段、 开放空间多元化阶段、 城市绿地增量化阶段、 城市绿地系统化阶段, 从最初的公共健康需求为城市绿地发展提供契机, 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绿地发展主动回馈公共健康需求, 两者之间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 本文从欧洲代表性城市伦敦、巴黎、 圣彼得堡和斯德哥尔摩的城市绿地发展与公共健康的阶段性需求关系进行论述, 旨在通过历史溯源, 明确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的互促关系及阶段性特征, 为我国未来城市空间的公共健康质量提升提供参考。
1 城市公共健康需求对私有花园公共化阶段的影响
19 世纪工业革命使社会经济高速发展, 各种社会问题随之产生, 如城市基础设施缺乏, 居住环境拥挤, 城市卫生状况急剧恶化[3], 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成为当时主要的健康危机等。 为解决“瘴气” 威胁而出现的“城市之肺” 理念贯穿19世纪伦敦城市绿地的建设与发展, 推动伦敦城市私有花园向满足公众休闲活动的开放空间转变。
1.1 19 世纪初期英国“瘴气致病” 理论引发的公共环境思考
第一次工业革命后, 城市扩张和人口涌入破坏了伦敦的宜人环境, 造成住房拥挤、 居住环境恶劣等问题, 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居住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1818—1848 年, 霍乱三次席卷英国[4], 当时人们普遍接受 “瘴气致病” 理论(Miasma Theory), 认为腐烂动植物释放的毒气(瘴气) 是传染病的致病之源[5], 导致流行性疾病快速蔓延, 居民体质逐渐下降。 “瘴气” 引起的危害受到社会改革家和公共卫生学家的关注,完善排水系统、 治理生活垃圾、 引入开放空间成为缓解城市拥挤所带来的公共健康问题的重要手段。 19 世纪城市公共卫生改革就此展开, 直至1943 年城乡规划部成立[6]。 对公共健康的关注,是推动公众开放空间发展的核心动力。
1.2 “城市之肺” 与伦敦皇家花园的公众开放
19 世纪以前伦敦的城市绿地以皇家花园或修道院花园等私人封闭花园为主, 仅定时向公众开放[7], 而伦敦近郊的绿地因受到圈地运动的影响,公众无权进入。 19 世纪以后, 为数不多的花园难以满足人们对开放空间的需求。 1829 年约翰·娄登提出“城市之肺” (Lungs of London) 理念, 将公园和公地 (Commons) 视为伦敦的 “城市之肺”, 并提出在伦敦城市周边设立 “呼吸区域(Breathing spaces) ” 的建议[8]。 在“城市之肺”理念的倡导下, 1833 年, 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市民对开放空间的需求[9], 首次向当局提议建设开放空间以改善不断恶化的城市环境, 为工人阶级提供休闲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场所。 1838 年英国议会要求在未来所有的圈地中, 必须留出足够的开放空间作为居民锻炼和娱乐之地[10]。 迫于压力, 皇家财产管理委员会管理下的摄政公园(Regent' s Park)、 邱园(Kew Gardens) 和维多利亚公园(Victoria Park) 相继开放, 伦敦摄政街区域城市公园群形成未来公园系统的雏形, 影响了后来城市空间的结构发展[11]。
2 城市公共健康需求对开放空间多元化阶段的影响
19 世纪中叶以后, 细菌理论(Germ Theory)出现, 城市公共卫生问题逐渐从一项工程性事务转向专注于征服病原体的工作[3]。 但改善居住环境、 控制和预防疾病仍是社会关注的重点, 长期紧张疲惫的工作带给人们精神压力, 居民迫切需要可作为休闲活动场地的绿色开放空间。 开放空间运动的支持者和社会志愿团体通过对市政当局施压, 将城市郊外公地、 墓地等绿地纳入城市开放空间[12], 多元化开放空间成为增加伦敦市内开放空间数量的一大途径, 推动伦敦开放空间向城市绿地的转变及立法保护, 大量保留下来的城郊公地为之后城市绿地系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1 “呼吸场所” 与伦敦公地保护运动
19 世纪60 年代的伦敦处于城市扩张时期,大量市民被迫迁到城郊, 而交通网络向郊区延伸,又导致大量郊区公地被建筑物取代, 伦敦“最有价值的呼吸场所” 汉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 面临被圈占的威胁。 1865 年, 特别委员会对伦敦城内和外围的森林、 公地与闲置空地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伦敦城市外围的多数公地已因圈占而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 1866 年, 公地保护协会成立, 议会通过《首都公地法》 保护首都管辖内的公地, 公地作为重要开放空间为城市居民创造“呼吸场所”[12]。 公地保护协会的成立是人们对公地认知的转折, 公地成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开放空间, 此后的二十年间, 自然保护主义者筹集捐款, 购买伦敦郊区房产以对抗圈地活动, 保留下来的大量城郊公地成为当今城市绿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伦敦开放空间内涵的扩展
伦敦最早开放的公园是皇室和贵族们的居住地, 大部分位于伦敦西区, 城内开放空间呈现阶级性分布的特征。 1875 年成立的凯尔协会(Kyrle Society) 致力于保护城市绿地和建设公园, 主张为工人居住区提供公共花园, 以遏制恶劣居住环境引起的流行性传染病, 提升工人们的健康水平;开放空间的支持者也积极为工人阶级的健康需求发声, 批评伦敦公园和开放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呼吁在伦敦内城中提供更小、 更便捷的绿地[12]。受到伦敦市内昂贵地价及绿地数量的制约, 凯尔协会试图对墓园、 荒地进行公园化改造, 1875—1900 年, 伦敦市内近百个墓园被改造成公园[13]。1887 年, 《开放空间法》 通过, 改造后的墓园移交市政府进行维护, 志愿机构和市政机构接管城市内现有的开放空间, 建造成专门绿地, 或改造成公共花园和游乐场, 开放空间的类型逐步多元化。
3 城市公共健康需求对城市绿地增量化阶段的影响
工业城市在带给人们就业机会和高收入的同时, 繁重的劳动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也给人们带来精神危机[14], 物质健康的进步愈发凸现精神健康的贫乏。 随着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成熟, 城市绿地作为规划的主要因素纳入城市规划范畴, 增强城市绿地在城市中的功能性、 改善公共健康状况成为19 世纪奥斯曼巴黎改造的目标。 伦敦绿带法案和圣彼得堡十年绿化计划均对城内和外围绿地数量进行整体提升, 增加城市绿地成为缓解公共健康问题的一种途径, 为居民提供更多与自然接触的可能性, 丰富居民的休闲文化需求。
3.1 霍乱疫情与奥斯曼巴黎公共空间改造
1832 年和1848 年, 霍乱疫情席卷整个巴黎,密集的住房、 狭窄的街道以及尚不完善的输水系统导致疫情迅速传播。 改善公共健康状况、 增强城市绿地在城市中的功能性成为1853—1870 年奥斯曼巴黎改造的主要目标, 城市公园第一次被纳入公共设施建设范畴, 在巴黎城内和近郊改造及兴建一大批公园[9], 城市边缘的布洛涅林苑(le bois de Boulogne) 和梵塞纳林苑 (Bois de Vincennes) 两座森林公园形成巴黎东西呼应的“首都绿肺”。 奥斯曼巴黎改造中还出现林荫道系统的概念[15], 用宽广的街道和林荫道连接公园。17 年间, 巴黎增加2000 hm2的绿地, 构成点、线、 面结合的绿地布局雏形[16]。 1859 年的议会报告显示, 城市绿地的增加带来空气、 光线和健康,疾病的流行得到控制, 巴黎市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3.2 大气污染与伦敦绿带的建设
20 世纪初期, 伦敦烟雾事件反复出现, 人们对阳光与新鲜空气的渴望愈发强烈。 霍华德认为大自然是生理、 心理和社会的健康之源[17], 于1898 年阐述了最初的田园城市构想, 提出建立伦敦大都会绿化带, 公园、 林荫道等开放空间的建设被推到城市规划尺度[18], 其规划思想因对人的身心健康给予积极考虑, 得到英国卫生部门的好评[13]。 一战期间, 伦敦学会同样意识到应将公众对开放空间的需求纳入伦敦中心城区规划[12], 并有效控制城市外围地区的土地利用。 1927 年, 恩温提出在城市外围建立3 ~4 km 宽的绿带以“保持大气的纯净”, 同时将人口分散至伦敦周边卫星城, 弥补城内开放空间不足的问题。 1935 年,大伦敦规划委员会提出增加开放空间和建立绿带的建议, 1938 年, 议会通过《绿带法案》, 由城郊森林、 大型公园、 运动场、 自然保护地、 墓地、果园、 苗圃、 农田等开放空间构成的绿带体系初步形成。
3.3 列宁格勒(圣彼得堡) 绿化十年计划
19 世纪后期, 城市化与工业发展导致圣彼得堡环境状况恶化, 引起政府和建筑师的广泛关注。1917 年, 圣彼得堡城市中由63 个公园和花园、 6个自然森林转变而来的森林公园成为“人民共有财产” 并被市政当局接管[12]。 1927 年, 城市绿地仍严重缺乏, 城市建筑师和园丁认为由绿地和水域产生的新鲜空气有利于改善人们健康, 并制定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于1924 年更名为列宁格勒, 1991 年又恢复原名) 绿化十年计划, 规定最高和最低的人均绿地指标, 提出切实可行的城市绿地增加计划[12]。 1935 年, 《大列宁格勒总体规划》 制定城市、 市政经济、 绿地的总体发展战略, 在城市绿地快速建设的热潮下, 叶拉金岛的基洛夫公园(Kirov Park) 建设完成[19], 成为公众参与娱乐和休闲活动的场所。
4 城市公共健康需求对城市绿地系统化阶段的影响
随着公共健康关注点的扩展, 人们更加重视城市绿地改善市民生活、 有益身心健康的功能,更注重个人预防和治疗性干预, 构建公共健康的理想城市空间。 战后重建成为欧洲城市规划、 建设健康城市的契机, 在斯德哥尔摩林德哈根城市规划及之后的花园郊区规划、 伦敦战后规划中,城市绿地成为城市规划的主要元素, 系统考虑城市绿色空间的整体功能。 城市绿地系统被视为有利于公共健康、 环境改善及经济增长的主要规划因素, 在协调城市人口密度、 解决拥挤的内城公共健康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1 斯德哥尔摩林德哈根城市规划
19 世纪中叶, 由于供水和废弃物的不当管理导致严重的卫生问题, 霍乱反复发生致使斯德哥尔摩城市的人口死亡率持续上升。 受奥斯曼巴黎改造的影响, 林德哈根在1866 年新的城市规划中提出建立滨海大道和林荫道的设想, 以改善市民健康状况。 其规划强调公园等绿色公共设施的重要性, 并提出将城市不同区域内大小不一的公园构成一个连续的公园系统[12]。 城市公园、 广场、开敞空间、 林荫道联合形成城市绿地系统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纳入规划。 林德哈根计划在街道网络设计方面为1868 年、 1874 年的城市宪章工作提供了灵感, 计划中强调的文化、 社会因素在1900 年之后同样影响斯德哥尔摩城市外围绿色空间的建设和发展, 越来越多的城郊绿地成为体育运动、 社区农业和户外运动的场所。
4.2 伦敦战后规划
1943 年的伦敦郡规划提出将伦敦城市及周边新城的开放空间作为一个整体, 采用公园道(Parkway) 相联系, 形成居民区—开放空间、 城市公园—楔形绿地—外围绿带的网络化绿地系统[14]。 规划后的私人休憩用地尽可能向公众开放, 开放空间面积总体增加50%; 重组后的泰晤士河两岸开放空间从9%提升至30%[12]; 城市外围的环城绿带作为解决城市问题的“有效解毒剂” 发挥重要作用。 1944 年, 在阿伯克龙比编制的大伦敦规划中, 开放空间被视为有利于健康、环境及经济增长的主要规划因素, 在伦敦行政区设置4 个环形地带, 并提出将绿带纳入到城市结构中成为城市的第3 个圈层[15], 环绕城市外围建设9.6 km 宽的绿带作为重要的开放空间类型[20-21], 包括受1938 年《绿带法》 保护在内的森林、 公园、 农业用地等, 形成伦敦环带状网络化的开放空间体系。
5 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的互促关系
近代工业化大生产导致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在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 城市的卫生条件与健康环境严重恶化, 19 世纪以来, 欧洲城市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间具有阶段性的作用链接关系与历史渊源(表1), 公共健康需求在私有花园开放化、 开放空间多元化、 城市绿地增量化、城市绿地系统化4 个阶段均对城市绿地发展产生影响。 在此基础上, 公共健康需求与城市绿地发展的互促关系可归纳为: 1) 公共健康需求为最初城市绿地的发展提供契机; 2) 城市绿地纳入城市规划范畴之前, 公共健康需求推动城市绿地发展; 3) 城市绿地广泛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之后, 城市绿地发展主动回馈公众健康需求。
纵观城市公共健康需求与绿地发展间的历史关系, 不同团体在引导城市绿地回应公共健康需求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立场。 伦敦开放空间运动时期, 同样是支持工人居住区开放空间的增加, 议员巴布列松的考量是基于维持国家生命力, 认为环境的退化将引起个体的堕落[22],将不利于工业和帝国权力的发展。 而凯尔协会则是秉持“将美景带到穷人家” 的理念, 强调开放空间的民主价值, 为工人提供呼吸场所,为孩子创造游乐场地。
19 世纪城市绿地很大程度是应公共健康的需求产生[22], 但公共健康需求并非是影响城市绿地发展的唯一因素。 除改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外,苏联政府希望城市绿地展示对工人阶级休闲活动组织的关注, 政府认为公园和花园不仅是娱乐的场地, 还具有政治宣传作用[12], 此后出现的文化休闲公园和胜利公园再次证明官方意识形态对城市绿地规划的影响。 同时, 最初以满足公共健康需求为目的而建设的城市绿地, 其主导功能也不断发生变化。 烟雾事件导致国民体质下降的威胁及户外活动的需求合力推动了伦敦绿带的形成,大伦敦规划之后绿带受到了严格的开发管控[23],但在战后经济衰退时期, 因新城和住房建设的压力, 绿带的主导功能也逐渐转化为一种限制城市扩张的战略规划工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