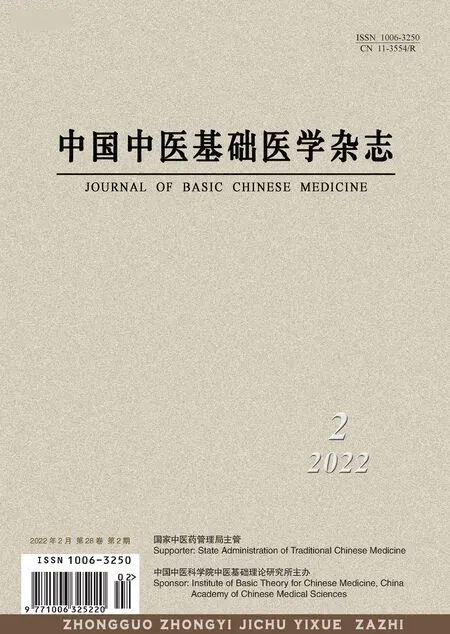岭南医家吕安卿医疗经验述略❋
林振坤, 宋文集, 李乙根
(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广州 510130;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广州 510360)
吕安卿(1876~1950)祖籍广东鹤山,出身世医,为近现代岭南医派早期代表性医家。岭南医史学者吴粤昌(1915~1989)曾将其与杨鹤龄(1875~1954)、郭梅峰(1879~1970)、吕楚白(1869~1942)并称近代“岭南四大家”,指出此四家影响很大,堪与岭南伤寒“四大金刚”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谭星缘相媲美,而杨、郭、二吕四家“形成了岭南医派的奠基人”“开创了岭南医家的新风气”[1]。
吕安卿以妇儿科见长,其祖父吕德基、父亲吕元照均以医为业,堂兄吕楚白亦以妇儿科闻名广州,家学深厚。1913年,已行医羊城的吕安卿加入广州医学卫生社,成为该社第二期社员[2]。广州医学卫生社是近代广东中医影响深远的学术社团,吕安卿广泛参与社团的学术与社务活动,与当时广东医界翘楚有着密切的交集。吕安卿无专著存世,医案、医话由门人辑录,收载于《广州近代老中医医案医话选编》,以及亲传弟子雷仁生(1904~1990)所撰《中医妇科医疗经验》中。此外,还有一些医案以“仁普医庐治验录”之名连载于1931年之《光汉医药月刊》。一直以来罕有对吕安卿医疗经验之系统介绍,兹试做一初步探讨。
1 辨治温病杂病,独创松、通、清法
松、通、清法是吕安卿学术体系中颇具特色的内容,并独步岭南医林[3]100。其理论与实践展示了吕安卿对清代以来叶、吴温病学术的深刻理解,为叶、吴温病学术在近代岭南传播“在地化”之体现。
1.1 松、通、清法之内涵
吕氏松、通、清法亦称“松解”之法、“松透解郁”之法,是吕安卿辨治温病传里、邪困心包并与温病、杂病郁热内伏之证的用药法度。
吕安卿认为温病传里多因失治、误治,致温邪郁遏,传入营分,困伏心包,不得透泄,“其病每似实似虛,脉沉而四肢微冷,外表不甚感热,而心里觉烦躁灼热,若加上夹痰夹湿,则不作渴,但觉胸膈翳似疼”[4]7-8。此等病证“医者如不明察,一见脉沉而又困倦,且外表又不甚热便误用补剂,则愈治而病愈剧,愈补而邪更困,致病日益加深。或误认为困热在内,用猛烈药如犀角、石膏、生地、大黄意图解救心热,但屡进而热不退,热更郁闭,是由寒性药压伏,不独不能清其热,反令热益不能退”[4]8,其时“发表则汗不易出,过凉则致肢冷呕恶,直攻伤脾而致溏泄,辛散则伤津液而致唇齿燥裂,均于病不利”[4]5。故宜“松、通、清之法开其郁闭,透其伏热,使由表入里之邪透引从表而解”[4]5,恰如“热水在保暖壶中,一定要拔其栓塞,使热有出路,热水才可以徐徐转冷”[4]8。
温病、杂病邪热郁伏者,“就是病邪在体内固结、匿闭状态”[3]103,多因夹痰、滞、瘀、湿等,或因失治误治如过用寒凉、温补、滋腻等导致气机不畅,邪热胶结。其表现见之于温病则发热不退,其病未入营分,而在卫、气阶段;见之于杂病则多有神机受扰之机象,如“胸中烦热”“烦躁”“晕厥不语”“胸翳口苦”等。按吕安卿门人雷仁生所言:“此类病证,关键在于疏达郁伏之邪”“只有设法使之疏松,向外透达,才能有效地清泄”[3]103。
1.2 松、通、清法之运用
温病邪入营分,叶天士提出“透热转气”的辨治理论,并阐述了不同情况下的具体用药法度。如“从风热陷入者,用犀角、竹叶之属;如从湿热陷入者,犀角、花露之品,参入凉血清热方中”[5]。赵绍琴认为[6],营分证之所以“入营尤可透热转气”,在于其多因失治误治,或夹痰、滞、瘀、湿等阻滞,使气机不畅,邪热郁遏,耗伤营阴,内扰心包,故当依据邪气郁遏之不同病因,去除壅塞,疏达郁遏之气机,使邪有出路,则入营之邪即可透出气分而解。在叶天士“透热转气”法中,凉血清热为法中基础,再依据郁遏营分气机病因之不同,参入疏透之品。吕安卿松、通、清法深合叶天士理法,以“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不寐”,多神机受扰之象,故所用皆心肝两经之品而偏于疏透。郁金、菖蒲清心豁痰、开窍通闭;莲梗通气宽中,“开郁结以通淋”“泻火清心”[7];蝉花清肝透表;木通清心除烦利尿;川楝子解郁泄热,主“大热烦狂”“利小便水道”[8]。此6味为松、通、清法之“松”“通”环节。各经清热药如连翘、赤芍、黄连、紫草等皆为清心凉血之品,则为松、通、清法之“清”环节。其诸药一则去除壅塞、疏达郁遏之气机,为邪开路;一则清泄郁伏营分之邪热,使心营恢复清宁,邪热透出气分而解。故吕安卿松、通、清法实为对叶天士“透热转气”理论之发挥。
而温病、杂病邪热郁伏之证,病因与温病传里入营一致,疏达气机、清泄郁热亦为必由之法,故为松、通、清法运用之扩展。然而因证未及营分,故吕安卿多不用开窍之石菖蒲而重在清透,着眼心肝二经,务使气机不受遏,郁热得以清泄。如治小儿外感发热,以蝉蜕、连翘、银花、赤芍、莲子心、木通等清透之品清心凉肝退热。夹咳嗽痰滞者加浙贝、茵陈、麦芽、瓜蒌仁等;兼呕者加左金丸、厚朴花、竹茹等[4]13-14。小儿疳积“肝有郁火,脾滞有痰”,以郁金解郁,赤芍清肝,川楝子、莲梗、木通、灯芯疏肝凉肝清心,加入化滞消积之品,如海螵蛸、瓦楞子、水仙子、使君子肉、鸡内金、浙贝、山楂核、谷芽。伴潮热者加独脚金、胡黄连;痰滞化热者加布渣叶、珍珠草;兼有脾虚不足者以参须、白芍、甘草益气生津;心肝火盛者黄连、珍珠草主之;气滞不行参用大腹皮、厚朴、木香、槟榔一二味行气之品[4]67-68。再如治“产后痉搐”,病妇“产后服姜醋过多,内积热滞,外束风寒”,抖然痉搐,厥后“高热烦躁”“渴饮骨痛”“腹胀”,吕安卿用石膏清泄阳明浮热,郁金、赤芍解郁清肝,辅以蒺藜、连翘、钩藤、紫草等清心透泄,竹黄、山楂、枳壳、布渣叶清化痰滞,为邪热透达扫清障碍[4]101。
应用松、通、清法后往往会先有热势升高之象,但此为“郁伏之邪已得疏松向外透达的表现”[3]103“是使用松通清法有效的先兆”[4]5-6,且郁热外透之后,病者神机受扰之象如胸中烦热、烦躁等多得到改善,为正常现象。
2 辨治女科,重调气理血
妇科为吕氏家学,调气理血是吕氏妇科的核心内容之一,贯穿于吕氏妇科诊治之方方面面,反映了吕安卿于妇科丰富的临床经验与独到的经验,其内容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2.1 重视解郁调气,喜用花类药。
《灵枢·五音五味》云:“妇女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女子善郁,有余之气郁结,肝之疏泄失常妇科诸疾随之产生。《素问·阴阳别论篇》即言:“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吕安卿将解郁调气的思想贯穿于妇科诸疾的诊治中,如倒经、经闭、赤白带、妊娠呕吐、妊娠胎动不安、妊娠腹痛、产后乳汁不通等,强调气调则血活,常用合欢花、玫瑰花、素馨花、香附、郁金、杉寄生等,少用柴胡尤喜用花类药,以“芳香、轻清之花类,有疏肝解郁之功效,善解妇人之郁”[9]。吕安卿尤对素馨花情有独钟。素馨花本产自西域,却在广州有着悠久的栽培、观赏史。其入药大概在清末民初,性味甘平,归肝、胃、大肠经,能舒肝郁、醒脾化滞,用于肝郁气痛、胸肋不舒、胃气痛和下利腹痛等,吕安卿以之为疏肝解郁之专药。
2.2 妇科血病,慎用芎归,重益气固摄
吕安卿认为,“女子多患血分病,一切月经不调,无不与血分病有关。故历代治妇科病多以四物汤为主,但在临床实有许多妇科病人不适合使用四物汤,如月经过多、胎期预兆流产之出血、经逆上行而致吐衄,皆不宜使用川芎、当归,犯之每使病情加剧甚至气血双脱而死。因当归之性能走而不守,动血通络,在月经崩漏及妊娠期中有流产先兆、阴户出血等病者,应慎用当归;川芎性升,燥血动血,血因热而上行吐衄者,用之则引血上涌,势必盈盆盈盂,不可收拾”[4]129。因此,对于诸如月经崩漏、妊娠先兆流产等妇科血病,吕安卿以益气固摄为根本大法,正如门人雷仁生所言:“胎动不安,兼见阴道流血的病证……纵便是血热动胎,治宜清热养血,但也勿忘益气固摄……益气固脾肾实为安胎的根本要法。[3]67”益气多用四君子汤加黄芪,重用黄芪以复摄血之权[4]76-77,91-92;若出血过多阴损及阳,阳气衰微,则以四逆汤加黄芪,重用芪、附温壮阳元[4]75。固摄多以温肾固摄之品,如菟丝子、煨肉蔻、金樱子、续断、吴茱萸、桑螵蛸、补骨脂、杜仲等,或用四神丸[4]75-77,91-92,[3]26-27,89-90。四神丸本治脾肾虚寒之五更泻,然方中五味子、补骨脂、肉豆蔻、吴茱萸皆为温肾固摄之品,吕安卿将之用于崩漏、小产,可对四神丸应用之拓展。
2.3 经闭未有不涉血虚
吕安卿认为,“妇科经闭原因虽不一端,但未有不涉及血虚者。血虚则冲任不满,血海空虚,经血何来?是以欲通其经,必先养其血,血足自然经行。苟非腹有瘀块,攻冲作痛,不可妄用攻破之药”[4]129,强调先调心脾,养血以资化源,常用当归、白芍、丹参、乌豆衣、桑寄生、柏子仁[4]80-86。此为四物汤去滋腻碍脾之熟地,辛燥走窜之川芎,加丹参、乌豆衣、桑寄生、柏子仁补而不腻、平润不燥之品,可谓四物汤之变法,较之四物汤更为平稳。吕安卿尤喜用乌豆衣,乌豆衣性味甘平,归肝、肾经,养血补肾,用于血虚头痛眩晕、肾虚耳鸣、自汗。同时注意疏肝,常加入素馨花、玫瑰花、合欢花、香附之类,以使“血足怀舒”。待气血充足则经血自行,或加活血通经之剂,自然经行血畅。
(1)活性材料筛选。取3号样品加入 AP 2.0%、水泥20.0%、CA5.0%及相应添加剂,不同活性材料投加量相同,考察固化改良后浸出液主要指标,试验结果见表8。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活性材料其对水泥水化作用不同,活性越高,作用效果越好,固化后各项指标越好,采用混合的活性材料比单一的活性材料效果好,因此选择混合型活性材料HHJ。
吕安卿还强调“有形之血不易骤生,当从缓图”[4]80-81“草木之药,功力缓弱,还须藉肉食营养,气血才易恢复”[4]83-84。门人雷仁生亦言:“病延日久,虚损较甚,不能速固,医者要谨守病机,病者要耐心调治,相互配合。精血亏损严重,草木之药仍嫌不力,须得血肉有情之品,如胎盘、龟板、龟鹿胶之属,尤以胎盘能养血益精、填补精血之虚损”[3]38,可谓深得其师之传。吕安卿除用血肉有情之物,常教病人用鹿茸炖老毛鸡,或用老母鸡炖汁调服祖传培坤丸[4]80-84。
3 幼科外感,以风热痰滞为提纲
吕安卿认为,风、热、痰、滞是小儿外感病最常见的致病病邪与兼夹病证[4]137-138。这是由小儿的体质特点所决定的。小儿体质稚嫩,藩篱疏弱,易为六淫所感,而风为百病之长,常兼其余五气为病。正如《临证指南医案》所言:“盖六气之中,惟风能全兼五气,如兼寒则曰风寒,兼暑则曰暑风,兼湿则曰风湿,兼燥曰风燥,兼火曰风火……由是观之,病之因乎风而起者自多也”[10],其于小儿为病亦最为常见。同时小儿为稚阳之体,外邪致病多易从阳化热,故风热之证多见。小儿肝常有余,心火常炎,外感六淫化热入里易有内陷心包、引动肝风之虞,而见惊风、抽搐诸证。是以风之为病于幼科有内风外风。小儿脾常不足,胃气薄弱,饥饱失宜,脾胃受损,运化失司,则“胃常停滞,腻滞生痰”,故在外感病中常兼夹痰、滞为患,而见咳嗽、哮喘、纳差、泄泻等症,甚则痰蒙心窍、引动肝风等。总之,风、热、痰、滞是儿科外感病中当时时留意之病邪与病程中之兼夹证。
基于此,对于小儿外感热病吕安卿强调“清心平肝”,特别是对于左手脉搏“浮急搏指”者[4]137-138。用药常以蝉蜕、连翘、黄连、赤芍、郁金、莲子心、钩藤、菊花,甚则牛黄、羚羊角、象牙丝等入心肝两经之品,合入松、通、清法中,视乎夹痰夹滞而参入清痰化滞之品,如布渣叶、绵茵陈、浙贝母、谷麦芽、竹茹等疏风清热,开郁达邪,时时留意风热炽盛窜入心肝两经而生惊风抽搐之变,使肝风息于未成已成。
吕安卿小儿外感四证理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小儿外感病的常见病邪与兼夹病证,对临证有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体现了岭南医家临证理论注重简练实用而非耽求体系完备的风格。
4 用药善于融合岭南经验与经典方药
岭南本土医药于晋唐时期已展示出鲜明的岭南特色,对民间医药经验的持续吸纳,并将之与经典中医理论熔为一炉,不断推动着岭南医学的发展,逐渐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岭南方药体系。这一特点在清代、民国都得到充分展现[11]。清初何克谏的《岭南生草药性备要》,即是对清以前岭南医家运用本土草药经验的一次总结,其中记载的岭南草药及其药物学知识,极大地丰富了传统药物学知识,对后世岭南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吕安卿临证用药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与个人风格,既善用岭南本土药材,又对经典方药应用经验独到,展示出成熟、深厚的岭南本土用药经验与药物学知识之积淀。此用药风格之形成即得之家学师承,更是岭南本土经验之涵育,兹举述如下。
4.1 喜用、善用岭南草药
如于小儿麻痘热毒未清、咳嗽不止之用膨鱼鳃。膨鱼鳃味咸、性寒,入脾、肺能清热解毒、透发痘疹,岭南民间以之煲汤或煮粥用于小儿麻疹,以促使麻疹及时发齐并除痘疹毒[12]。吕安卿以之配腊梅花、柚树寄生、银花、连翘等以清解余毒,杏仁、瓜蒌、浙贝等宣肺化痰。腊梅花清热解毒、润肺止咳,亦为吕安卿治疗小儿麻疹余毒未清、肺热咳嗽之要药[4]58-60。
又如龙脷叶,其味甘淡、性平,入肺、胃经,能润肺止咳,吕安卿以之配桑叶、雪梨干、北杏、瓜蒌皮用于肺燥咳嗽[4]15,或配仙鹤草、鹿衔草、藕节等用于痰火咯血[13],且本品性润兼能通便以利肺气肃降。
再如金橘干,金橘干入药岭南独有,其味甘、微酸、辛、性温,入肝、脾、胃经,能理气、解郁、化痰、醒酒,为其调理中焦之常品,或配砂仁以醒脾和中[4]80-81,或配厚朴、木香、青皮以治腹满不舒[4]78-79,或配乌药、香附、刀豆干、石菖蒲以治胸膈不利[4]90-91,94,或参入二陈汤中以理气化痰[4]101。
还有天香炉、锦地罗药物,天香炉清热利湿、行气止痛、解毒消肿,锦地罗清热解毒、利湿消积,岭南医家常以此药味配伍用于治疗湿热痢疾、腹泻[4]42,[14]。
另外寄生类草药于岭南也有着丰富的资源与运用经验[15]。吕安卿善用寄生类草药,所用寄生主要有桑寄生、柚树寄生(椂柚寄生)、松树寄生(松寄生)、杉寄生4种,4种寄生均可祛风除湿又各具特性。桑寄生养血平肝、固肾安胎,并常配蒺藜、甘菊、天麻用于风阳上扰之头痛头晕[4]90-91,或配当归、阿胶、杞子、柏子仁等以养血固肾安胎[4]75-76。柚树寄生性味辛平,有化痰止咳、解毒之功,用于麻疹余毒未清兼咳嗽咯痰者[4]58-59;松寄生有活血止血、化痰止咳之功,可用于肺结核之咳血,用之于逆经倒经之咯血吐血[4]78-79;杉寄生功同松寄生,偏于理气解郁,除用之于逆经咯血吐血[4]79,[13]外,常用于胸肋气滞不舒之证[17,18]。
4.2 经典方药的独特运用
如柿蒂传统多用于降逆止呃,主治呃逆反胃,吕安卿则以之敛肺降逆、止咳平喘,用于新感咳嗽、喘促气逆[3]91-92,[4]5-6,且用量偏大,多在12~30 g。
又如牵牛子多畏其性有毒,吕安卿则取其泄肺逐痰消饮,气雄烈、性急疾,通利三焦,用之于痰涎壅盛、喘逆气促之肺胀咳喘可收捷效,即便小儿亦不避讳[4]25。
刀豆干传统多用于温中降逆止呕,吕安卿则常以之行气宽中,配石菖蒲、枳壳、青皮、金橘干等以治胸闷胸痛不舒之证[4]99,[17]。
又如吴茱萸、肉豆蔻、五味子、补骨脂即四神丸,一般用于脾肾虚寒之五更泻,吕安卿取其温脾固肾之功加入益气固肾方中,用于肾火衰微、脾肾虚寒、阳虚气弱之崩漏经多[3]26-27,89-90,[4]75,是于四神丸应用之扩展。
再如当归、川芎两者相配即为《删补名医方论》之佛手散,是吕安卿治疗妇科经闭、产后心腹痛属血分瘀阻者常用方药。原注云:“当归、川芎为血分之主药,性温而味甘、辛,以温能和血,甘能补血,辛能散血也。古人俱必以当归君川芎,或一倍或再倍者,盖以川芎辛窜,捷于升散,过则伤气,故寇宗奭曰∶不可单服、久服,亦此义也。然施之于气郁血凝,无不奏效,故用以佐当归而收血病之功,使瘀去新生,血各有所归也。血既有所归,则血安其部,而诸血病愈矣。[19]”吕安卿灵活调节当归、川芎的比例,或重用当归至六钱、八钱,而川芎用三钱,配党参、黄芪、杞子、首乌、乌豆衣以治血虚经闭[4]83-84,或当归、川芎等量配桃仁、丹参、穿破石、益母草、穿山甲等以活血通经[4]81-82。
此外,还有用蒺藜、菊花、蜂房、苍耳子相配,以治肝阳上亢之头痛[4]50-51;以及治小儿疳积于消导药如鸡内金、使君子、五谷虫、山楂核等外,加海螵蛸、瓦楞子以化湿消积[4]67-68等。
5 结语
由于现存吕安卿医籍数量有限,加之此类经由门人整理的医案、医话不注时间背景,故无从借此了解吕氏各时期学术思想、临证风格之变迁,也就不免有无以全窥吕氏医疗学术之遗憾。基于此些文本的分析,难免有拾一漏万之嫌。然而吕安卿特色鲜明的学术思想与医疗经验,堪称岭南医家融合本土民间经验与经典中医理论方药之典范,值得深入探讨与发掘,以进一步丰富岭南医学流派之学术内涵,发扬岭南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