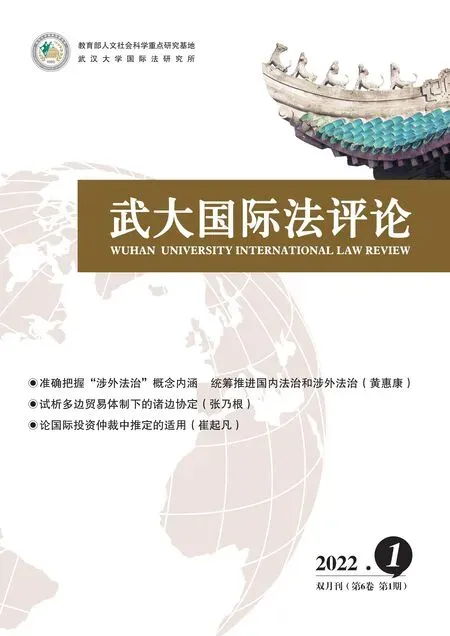数字平台国际反垄断监管冲突下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条款之困
赵泽宇
数字平台的跨国经营使得市场竞争呈现国际化态势。大型的数字平台,例如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为了维持垄断地位,可以利用其算法和大数据的优势,在多个司法辖区内的市场中采用不正当手段挤占市场以及剥削消费者剩余。这遭到了多个司法辖区的反垄断调查与执法。①例如,在著名的欧盟谷歌安卓案中,谷歌公司采取的与该案相同的在安卓手机中预安装谷歌自身app的行为受到了包括俄罗斯、土耳其与印度等多个国家的反垄断调查和执法。See Case AT 40099—Google Android C(2018)4761.See also Jurgita Malinauskaite&Fatih B.Erdem,Digital Antitrust:The Google(Android)Decisions in Russia,Turkey and India,42 Business Law Review 183(2021).例如,在苹果税案中,苹果应用商店的用户购买应用时遭到限制,只能通过“苹果支付”(apple pay)进行支付,而且苹果公司对于支付的费用抽成30%,该行为虽然由美国的苹果总公司作出,但影响到了中国市场,法院裁定该行为受我国法院管辖。①参见〔2021〕沪73知民初220号民事裁定书、〔2021〕最高法知民辖终303号民事裁定书。同时,苹果公司的行为并未区分不同国家和地区而作出,该行为引发了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多个司法辖区的竞争关注。②See Epic Games,Inc.v.Apple Inc.Case Number:4:20-cv-05640-YGR from USDistrict Court for the Nor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2021).See also European Parliament,Official Complaint by Spotify against Apple for Discrimination and Apple Music’s Unfair Advantage over Spotify:The Power of Digital Platforms,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E-9-2019-002996_EN.html,visited on 6 October 2021.不仅是苹果公司,我国自身的数字平台,例如腾讯和阿里巴巴等,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也可能会遭受其他司法辖区的反垄断调查。③我国企业.包括数字平台企业有可能被无理地遭到反垄断执法,此处可以参见维生素C案。实际上,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该案的判决背后包藏了采用“反倾销”措施的祸心,以在中美经贸摩擦中取得优势,减小对于中国进口的维生素C药物的依赖,意图限制外国主权参与的出口卡特尔的实施以达到认定“低价倾销”的效果。See Angela Huyue Zhang,Chinese Antitrust Exceptionalism:How the Rise of China Challenges Global Regulation 168-169(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虽然各国都意识到需要对平台企业加强反垄断监管,但是各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路径进行监管;而且就平台本身所在的国家而言,其是否真的有强力规制平台巨头的态度仍然存疑。而发展中国家缺乏执法资源,且其市场对于平台巨头来说可能欠缺重要性,即使其大力对平台巨头进行反垄断规制,该规制效果也存在疑问。另外,如果大多数国家都采取较为激进的规制模式而且采取基于“效果”的管辖规则,那么由于平台企业跨境经营的特性,必然会产生管辖权冲突。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形成数字平台的国际反垄断协调与合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现有的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RTA)试图就各国的竞争立法和执法达成一定的协调,创造双边或多边之间的协调方式,消除对于同一反竞争行为在不同国家的规制差异,并就管辖权冲突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为企业的跨国经营创造公平和自由的市场环境。但是,从总体来看,各国仅在相对较浅的层面上就竞争政策的协调达成一致。而且,数字平台利用算法和大数据进行经营,与数据流动、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标准等议题无法割裂;同时,许多平台具有跨境网络外部性,④网络外部性指的是企业对于新用户的吸引度取决于同一种类或者不同种类旧用户的数量,同一种类的情况被称为直接网络外部性,不同种类的情况被称为间接网络外部性。跨境网络外部性则指的是一国用户是否被吸引取决于另一国的旧用户数量。这种外部性如果反映在平台上,即是平台一边的某国消费者购买意愿取决于另一国商家数量或同类消费者数量。See Maximilian Stallkamp&Andreas P.J.Schotter,Platforms without Borders?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of Digital Platform Firms,11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65-66(2021).例如,爱彼迎(Airbnb)平台上某一热门目的地的民宿越多,其平台上的国际消费者也越多,这样,Airbnb(无论是否设立营业实体)即可以通过互联网与不同国家国内的同类旅游服务企业展开竞争,作出的行为也可能在多个国家产生竞争损害。因此,现有简单的国际竞争规则可能难以解决数字平台带来的跨境反竞争问题与法律适用冲突。①See Oliver Budzinski&Annika Stöhr,Competition Policy Reform in Europe and German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Light of Digitization,15 European Competition Journal 15-17(2019)See also Robert D.Anderson,et al.,Competition Policy,Trade and the Global Economy:An Overview of Existing WTO Elements,Commitment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Som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Issues for Reflection,OECD DAF/COMP/GF(2019)11,5 November 2019,paras.71-73.本文以RTA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协定中的竞争政策条款在面对数字市场的冲击下引发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这些竞争规则本身浮于表面,缺乏深入的立法和执法标准的协调,这可能会促使企业客观或主观地逃避规制;其次,这些规则并未考虑到数字市场的特殊性,而个人信息保护、数字行业监管与新型执法工具的应用却是数字市场反垄断必然涉足的方面。本文认为,在某一区域内的深化合作能够形成较为深入的竞争实体规则和较紧密的执法合作,而通过数字贸易协定(digital trade agreement,DTA)的方式则能够规定与数字平台特性有关的竞争政策条款或数字行业监管标准和规则,使得上述困境得到缓解。
一、各国对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的冲突与不足
(一)各国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态度与路径的冲突
尽管各国意识到了数字平台跨境竞争与行为跨境反垄断影响的趋势,纷纷呼吁加强竞争法律制度的实施,但各国的实施态度与方法并不一致。在欧洲,对于数字巨头企业的反垄断规制模式也主要分为三个流派:一种是以欧盟《数字市场法》草案为代表的数字行业规制模式;一种是以英国数字市场部(DMU)为代表的设立专门机构的数字行业规制模式;第三种是以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十次修正案为代表的、设立专门的垄断标准的反垄断法规制模式。②See Marco Botta,Sector Regul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Europe,12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Practice 501(2021).而就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而言,尽管总体上美国执法机关采取了主动的市场调查,也出台了一些针对数字平台巨头的反垄断法,③这些反垄断法分别为《终止平台垄断法》(Ending Platform Monopolies Act)、《美国选择与创新在线法》(American Choice and Innovation Online Act)、《平台竞争和机会法》(Platform Competition and Opportunity Act)、《通过启用服务交换法》[Augmenting Compatibility and Competition by Enabling Service Switching(ACCESS)Act]、《合并申报费现代化法》(Merger Filing Fee Modernization Act)、《州反垄断执法场所法》(State Antitrust Enforcement Venue Act)。See Lauren Feiner,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form Odd Alliances During Tech Antitrust Debate,CNBC,https://www.cnbc.com/2021/06/24/-big-tech-antitrust-debate-odd-alliances-form-and-party-fractures-show.html,visited on 3 November 2021.但相较于欧盟而言,其对于数字平台巨头的反垄断态度更为保守。例如,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欧盟谷歌搜索案放到美国,谷歌很有可能不会构成违反《谢尔曼法》第2条的反竞争滥用行为,因为尽管谷歌的广告前置策略对于消费者产生了一定的损害,但与竞争最关切的价格、质量等要素并没有显著变化,而且谷歌有充足的理由,例如,其提出纵向搜索是一般搜索的替代品等理由,以反驳执法机关对于一般搜索市场这一相关市场的认定以及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这些美国法院在反垄断案件审理中的关注点在美国运通案中有所体现,美国最高法院在运通案中对于双边平台的垄断力量滥用仍然秉持保守态度,其对于美国运通公司双边市场的较为开放的市场界定分析导致垄断力量的认定和垄断行为的认定难以实现。①See Eleanor M.Fox,Platforms,Power,and the Antitrust Challenge:A Modest Proposal to Narrow the U.S.-Europe Divide,98 Nebraska Law Review 308-309(2019).因此,尽管美国有如此多的对于数字平台加强反垄断的呼吁,但付诸实践者却寥寥无几,这不仅是因为美国是“数字巨头”的输出国,这些巨头是其数字霸权、文化霸权输出的重要途径之一,②这些数字巨头自身也有能力进行政治游说,或者以脱离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相威胁,进而使执法机构放弃强硬的反垄断执法。See Jeffrey Bone,Antitrust Reform:Implications of Prospective Threats by Digital Platforms to Relocate Abroad,8 Belmont Law Review 170-171(2020).同时也与其根深蒂固的反垄断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不无关系。③芝加哥学派的反垄断理念长期被美国反垄断实践所接纳,其倡导的是以消费者福利与经济效益分析为中心的反垄断规制模式,崇尚自由放任与减少干预,倾向放任反垄断执法产生的“假阴性”成本。然而按照其观点,平台巨头的许多行为有可能因为其结果能够增进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剩余而逃脱反垄断监管,但在此期间却忽视了该行为对于整体市场竞争结构造成了破坏。参见吴汉洪、王申:《数字经济的反垄断:近期美国反垄断领域争论的启示》,《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2期,第48页。See also William E.Kovacic,The Chicago Obsess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USAntitrust History,87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487-489(2020).
(二)发展中国家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效果不足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数字市场反垄断规制的问题集中在执法资源和执法效力之上。根据UNCTAD的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如何利用一般的反垄断工具应对数字市场带来的挑战表达了担忧,这包括了识别数字市场的特殊性、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力量等的要素。④See UNCTAD,Competition Law,Policy and Regulation in the Digital Era:Note 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TD/B/C.I/CLP/57,28 April 2021,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ciclpd57_en.pdf,visited on 11 October 2021.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反垄断执法部门在缺乏有效的与美欧反垄断执法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的前提下,也很难获取跨国数字平台巨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相关信息以及美欧国家对于这些案件较为成熟的执法经验。这使得发展中国家难以对跨国数字平台巨头进行合适的反垄断处置。⑤See UNCTAD,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uiding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under Section F of the Set of Multilaterally Agreed Equitable Principles and Rules for the Control of Restrictive Business Practices for the Nineteenth Sess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Experts on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Noteby the UNCTAD Secretariat,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information-document/ccpb_IGE COMP2021_Implementation_GPP_final_en.pdf,visited on 11 October 2021.另外,就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执法部门而言,无论是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人员配备、财力资源和根植的竞争文化,都有可能难以制止数字平台巨头的垄断行为,特别是在执法和司法调查中涉及复杂的数字市场竞争损害分析与开展全面的市场竞争状况调查时。①Se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Network Vice-Chair for Young Agencies and Regional Diversity,Lessons to Be Learn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Young Competition Agencies:An Update to the 2006 Report,46-48, https://www.internationalcompetition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SGVC_YoungerAgenciesReport2019.pdf,visited on 11 October 2021.例如,有学者就对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这三个国家对于谷歌案的处理展开了批评,认为它们对于“反事实”(counterfactual)的分析欠缺,且对于谷歌收集个人信息的剥削性效果判断不足等。当然,各个国家也需要基于自身的产业发展要求与国家政策需要对于一个案件作出不同的处理。②See Jurgita Malinauskaite&Fatih B.Erdem,Digital Antitrust:The Google(Android)Decisions in Russia,Turkey and India,42 Business Law Review 193-194(2021).同样,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对于数字平台巨头来说似乎过于弱小,如果处罚力度过大,数字平台巨头,特别是对于不在这些国家设立实体的巨头企业而言,退出该市场也轻而易举,但本国的数字产业却可能会面临巨大灾难。③See Thembalethu Buthelezi&James Hodge,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Digital Economy:A Developing Country Perspective,15 Competition Law International 202(2019).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处理数字平台巨头反垄断的案件时仍然与发达国家合作或者参照发达国家的执法实践,化解执法和司法上的冲突,起到真正的威慑作用。
(三)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的管辖权冲突
与传统市场一样,确定反垄断管辖权与处理反垄断管辖权的冲突仍然是国际社会面对数字平台带来的反垄断挑战的重要一环。
美国铝业案与《外国贸易反垄断促进法案》采取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效果原则”代表着一定程度的“长臂管辖”,一直以来被许多国家所反对与批判。④参见刘宁元:《反垄断法域外管辖冲突及国际协调机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8页。See also USv.Aluminium Co.of America 148 F.2d 416(2d Cir.1945)(“Alcoa”).Foreign Trade Antitrust Improvements Act(“FTAIA”),15 U.S.C.§6a.而欧盟则保持较为拘谨的域外适用原则,除了在并购控制这一领域采用的是“效果原则”之外(因为该行为是由欧盟委员会处置,欧盟委员会的立场与美国一致,都主张积极的域外管辖),在卡特尔与滥用行为中都是采用严格的行为发生地原则。在英特尔案中,欧盟法院一再坚持反垄断法的域内适用,反对过度扩张。⑤See Case C-413/14 P Intel Corp.v.European Commission[2017]ECR I-632,para.42.See also OECD Working Party No.3 on Co-operation and Enforcement,Roundtable on the Extraterritorial Reach of Competition Remedies-Note by the European Union,(DAF/COMP/WP3/WD(2017)35,December 2017,paras.3-7.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称《反垄断法》)第2条也主张适用“效果原则”实行域外管辖。然而,在数据流动和算法应用如此广泛的数字市场中,对数字平台企业的某些行为如何界定行为地,特别是大型科技公司采用算法共谋的形式形成国际卡特尔时,如何界定行为地尚须考量。①例如,在算法默示共谋的场景中,由于算法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自动化和隐蔽性,很难对默示共谋的意思联络进行识别,而在缺乏意思联络的情况下,默式共谋在许多国家的竞争执法中有可能被认定为正当的单边价格调整,但在有些国家有可能被认定为卡特尔协议。另外,发展中国家缺乏强有力的数字化执法工具也会成为识别该种类型的共谋行为与搜集相应证据的一大障碍,这导致和加剧了各国之间的执法冲突。See Philippe Brusick,Competition Concerns in Cross-border E-Commerce: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36(CUTSInternational 2018).然而,正如上述的谷歌安卓案一样,这些行为对于各国数字市场竞争的影响却是普遍存在的,那么各国都会对这些案件适用反垄断管辖。同时,鉴于该案将谷歌应用商店相关地域市场界定为全球市场,那么在调查执法的过程中,必然要对平台在辖区外的市场力量和行为进行评估,在调查取证甚至计算处罚数额的过程中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其他辖区执法机关的管辖权。②See Case 40099—Google Android C(2018)4761,para.402.作为协调各国反垄断规则与形成执法合作与交流机制,尊重他国司法或行政执法的效力或者他国的数字行业政策(如何国际礼让规则等)③事实上,许多国家目前的数字产业发展还不完全,亟须数字企业的发展壮大来发展自身的数字行业,我国也需要数字企业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国家也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推动数字平台“走出去”。不过,与河北维尔康药业的维生素C案一样,我国数字企业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反垄断调查,如何避免这种反垄断执法与司法损害我国数字企业发展的正当利益成为了一个需要重视的议题。参见金美蓉:《中国企业在美国反垄断诉讼中的挑战与应对:基于对相关判决的质疑》,《法学家》2020年第2期,第162页。的重要机制之一,RTA似乎能够缓解以上冲突与不足,但其在数字平台跨境经营的大潮中也有自身的问题。
二、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条款的路径阐释与评价
近年来,涵盖竞争政策的RTA的数量呈上升趋势,因而RTA逐渐成为了解决各国反垄断规制冲突的重要路径。④截至2021年10月,WTO已经收到568份RTA的通报,相对应已经生效的RTA有350个(包括其他国家正式加入现有RTA的通报)。在这350个已经生效的RTA中,涉及226个FTA(不含EIA和CU)中具有竞争政策条款或者章节,占已生效RTA总数的64.57%,其中包含竞争实体规则的RTA有124个,占到具有竞争政策条款或章节的RTA的54.87%。与2018年相比,包含竞争政策条款的贸易协定的数量有所增加。参见闻韬:《区域贸易协定中的竞争章节研究》,《法学论坛》2018年第4期,第46页。数据来源于WTO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Database,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visited on 12 October 2021。各国在RTA中就竞争实体规则、执法程序和如何进行合作上达成一致意见,以共同应对跨境反竞争行为带来的挑战。RTA中的竞争政策条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体现在其竞争政策条款只要求成员建立国内竞争法律制度或者简略地规定了某些反竞争行为;另一类体现在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区域(包括某些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等)签订的要求成员国竞争法完全遵守协定内容,并且建立区域性竞争执法机构的“区域竞争协定”(regional competition agreement,RCA)。①See G.Deniz Both,Driver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38 World Competition 305(2015).See also Franćois-Charles Laprévote,Competition Policy within the Contex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DAF/COMP/GF(2019)5,para.6.尽管合作形式还包括了国际组织(OECD和UNCTAD)与非正式制度安排(ICN)制定的多边非约束性的竞争规则、司法互助协定(MLATs)与各国执法机构之间互相签订的执法合作协议与备忘录,但RTA始终是各国寻求经济合作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一般性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条款的三种模式
就上述的第一类竞争政策条款而言,有学者将其又分为了三种模式,分别是欧盟模式、美国模式和大洋洲模式。
1.欧盟模式
欧盟模式以《欧盟运行条约》第101、102、106、107条为范本,倾向于较为细化的实体性规定,将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三大行为一览无余地呈现,同时也包括限制政府补贴条款。但各欧盟模式协定对于执法合作机制的规定实则参差不齐,尽管总体上欧盟也希望其执法合作能够遵循一定的原则,但缺乏在文本上对执法合作机制的进一步细化。②See Franćois-Charles Laprévote,Competition Policy within the Context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 DAF/COMP/GF(2019)5,paras.58-60.例如,在欧盟—加拿大CETA中,其在实体上定义了反竞争行为,包括要求双方禁止垄断协议、协同行为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等的内容,但在执法上,仅仅明确双方对于国内的反竞争行为有执法权,开展合作以及双方执法措施应当遵循透明、非歧视以及正当程序原则,并没有其他的执法合作条款。③See CETA,Articles 17.1 and 17.2.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也体现出上述特点,该协定径直将《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和第102条、《欧盟合并条例》(139/2004 EC)以及2002年英国企业法第三章中对于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英国称并购)的定义进行了复述,并且允许双方明确基于公共政策豁免适用竞争政策的情况。然而在执法合作上,该协定仅简要地要求在上述三大原则下双方应当致力于竞争执法合作,并仅列出了信息交换这一种合作机制。④See The EU-UK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Articles 359-361.
2.美国模式
美国模式下的竞争政策条款几乎不涉及任何规定反竞争行为的实体法内容,对各国国内竞争法中反竞争行为的规定给予尊重,但其执法合作机制的规定则比欧盟模式更加丰富和细化。例如,美墨加协定(USMCA)中对执法中的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规定,但是与欧盟模式不同的是,其对于何为“正当程序”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该原则包括立法与执法透明度、调查执法期限要求、当事人有权聘请法律顾问等的规定,而前述欧盟模式的两个协定只单纯列举了“正当程序”原则。但是,USMCA并未列举规定反竞争行为,其只要求各国制定明确的禁止性条款以及将经济效益与保护消费者权益作为目标。①See USMCA,Articles 21.1 and 21.2.同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之后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与USMCA的规定较为接近,要求各成员执法机构在调查和执法时遵守一定的原则和程序,其中包括了较为细化的“正当程序”原则(例如,当事人有权获取案件信息、聘请法律顾问与在辩护时提出证据的权利)以及当事人私人提请执行的诉权等。在各国执法机关的合作上并非如同欧盟模式一般仅简要规定各国执法机构应致力于加强互相合作,而是规定了立法和执法的信息交换、通报、磋商、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合作机制。②See TPP,Cha.16.2.1,16.3-16.5;CPTPP,Cha.16.2.1,16.3-16.5.由此可见,与美国模式下的竞争政策条款而言,欧盟模式着重于竞争法实体规定的契合,而对于具体执行机制则并无许多规定,因而该模式被称为“实体法协调模式”,而美国模式则正与之相反,被称为“软机制合作模式”。③参见骆旭旭:《区域贸易协定的竞争条款研究》,《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82-83页。
3.大洋洲模式
大洋洲模式指的主要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的《澳新紧密经贸关系贸易协定》(ANZCERTA)实行的模式。在该协定中,由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意欲达成“无条件自由贸易”的目标,双方之间取消了“两反一保”的贸易救济措施,要求双方之间的竞争实体法律包括反竞争标准、技术规范、效果测试程序等的趋同。在执法合作上,大洋洲模式也向美国模式看齐,要求各执法机关在作出决定前和作出决定后及时通报对方执法机关等。④See ANZCERTA,Article 12(1);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Australian 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and the New Zealand Commerce Commission;Protocol to the Australia New Zealand Closer Economic Relations-Trade Agreement on Acceleration of Free Trade in Goods,1988,Article 4(4).然而,到目前为止,大洋洲模式的竞争规则只见于ANZCERTA这一协定中,而且还是因为澳新之间紧密的合作关系而促成的。但该种模式和竞争合作一般只能在经济交往较为深入的国家之间达成,其适用范围有限,而且并未就数字平台企业的竞争法作出协调深入规定。因此这种竞争立法与执法合作模式并非主流,下文不再进行深入分析。
(二)对欧盟模式与美国模式的竞争政策条款的评价
欧盟模式和美国模式对于竞争政策条款的处理方式各有优劣。美国模式的做法在尊重各国反垄断立法与执法主权的前提下,避免了各国实体法上对于不同行为认定合法性的冲突,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对跨境反竞争行为的反垄断执法效率。不过,由于各成员的实体法不一样,而执法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因此缺乏实体规则的协调很可能导致执法漏洞的出现。①参见钟立国:《自由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条款研究》,《武大国际法评论》2020年第6期,第46页。欧盟模式的优劣则正与美国模式相反,尽管协定各方能够就规制何种行为达成共识,但由于约束性执法程序与合作机制的缺乏(尽管欧盟委员会与许多国家竞争执法机构都签订了大量的执法合作协定及备忘录,但如下文所述其效力仍然饱受质疑),各国的执法随意性并不能受到约束。在仅规定“三大支柱”行为应当受到规制的情况下(即解释了“三大支柱”行为的含义),如果成员方的国内竞争法规定的不一样,那么对于具体案件而言,在双方之间缺乏执法协调机制的情况下,该国可能会怠于执法或者造成成员之间的执法差异。实际上,欧盟模式和美国模式的差异也代表着两地多边贸易态度的差异。欧盟模式对于反竞争行为的列举反映了其重视协定各方的“市场准入”(代表了欧盟出口方利益),而不是保护自身市场免受国际反竞争行为的冲击(代表了进口方和国内消费者利益)。同时其代表着欧盟为了维护统一市场的需要,想要确保与其开展贸易的国家都适用与欧盟相同或相似的竞争政策准则。这类似于欧盟在跨境数据传输方面的实践,即其将个人信息保护的高标准落实到与其他国家的数字贸易之中。②参见许多奇:《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应对》,《法学论坛》2018年第3期,第130-131页。
而美国则并非如此,受到芝加哥学派自由贸易理念的影响,美式竞争政策条款更突出经济效率与消费者福利的重要性,但美国并不认为贸易协定能够解决国际反竞争行为的问题,其更倾向于执法机构在执法过程中的合作,且认为这样的做法更有效率,更有利于保护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与其他国家竞争执法机关难以达成合作或者该国竞争法并不完善,美国更愿意采用单边行为,通过其反垄断法的“长臂管辖”解决问题。③See Anu Bradford,et al.,The Global Dominance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Over American Antitrust Law,16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738-739(2019).此外,欧盟的竞争法实施模式中,大部分反垄断执法由欧盟委员会进行,其强调制定一系列的明线规则(bright-line rules),为执法提供可靠的制度遵循,使得行政权力更为有效地实施。④See A.Douglas Melamed,Antitrust Law is Not that Complicated,130 Harvard Law Review Forum 169(2017).而美国则充斥着反垄断私人诉讼和司法裁判,重视诉讼程序的正当性与当事人的表达自由,法院似乎才是终局的反垄断实施部门,其具备相当的自由裁量权。⑤See Anu Bradford,et al.,The Global Dominance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 Over American Antitrust Law,16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738-739(2019).
总而言之,大多数贸易协定中的竞争政策条款要么“重实体、轻程序”要么“轻实体、重程序”,即便是实体和程序都重视的RTA,但其数量也较少,这一切都与各国在贸易与竞争政策议题上的核心利益息息相关。但是,无论是执法合作机制的缺乏还是实体规范的缺乏,都会降低合作规制跨国反竞争行为的有效性。
(三)区域竞争协定
经济一体化更高的区域竞争立法和执法情形又如何呢?许多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在其本身的RTA中设计了专门针对竞争政策的区域竞争协定,在区域内设立统一竞争法实体规则(要求各国国内竞争法予以遵循),同时还设立统一的竞争执法机关。①See OECD,Regional Competition Agreements:Benefits and Challenges,Note by the Secretariat,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DAF/COMP/GF(2018)5,29 September 2018,para.6.目前为止,OECD归纳了11个能够达到以上统一标准的RCA,分别是安第斯共同体(CAN)、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中非经贸共同体(CEMAC)、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共同体(EAC)、欧亚经济联盟(EAEU)、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欧盟(EU)、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以及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WAEMU)中的RCA。②See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Regional Competition Agreements-Inventory of Provisions in Regional Competition Agreements,Annex to the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DAF/COMP/GF(2018)12,29 November 2018,Table 1.有学者指出,虽然东盟(ASEAN)采取的是软协定模式,也即出台了东盟区域竞争政策指南等的相关文件来形成统一的竞争立法和竞争执法框架,但是东盟在2025年远景规划中指出:东盟各国要确保各国所签订的FTA中的所有竞争章节相结合(alignment),以实现区域内竞争政策和法律的协调。③Se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para.27(iv).另外,随着近年来东盟愈发强调建立统一市场的目标,东盟竞争执行计划(2016—2025)要求包括建立竞争执法的共同合作原则,在2019年之前建立与欧盟竞争网络(ECN)相类似的东盟竞争执法者网络(ASEAN competition enforcers’network)等的区域竞争统一计划。④See An ASEAN Competition Action Plan(2016-2025),Strategic Goal 3.所以,尽管没有确定的RCA,东盟也能算是积极促进区域竞争统一化的地区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RCA的标准。⑤See Huong Ly LUU,Regional Harmonization of 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An ASEAN Approach,2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09-310(2012).然而,下文也会指出,尽管一些RCA在表面上规定得较为全面和深入,但其实施效果与实体规定却大相径庭,这也是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条款困境的一个方面。
三、区域贸易协定竞争政策条款困境的具体表现
尽管有如上的路径选择,但RTA中的竞争政策条款在实体文本和执法合作上并不深入,这可能会导致监管逃避和套利现象。另外,将这些规定的机制放在需要新的损害判定、监管模式与监管方法的背景下,其会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难以形成对数字平台竞争监管的有效协调与合作。
(一)简略的实体规范与合作机制诱发监管逃逸
1.规制反竞争行为的实体规范不够完善
在RTA框架内,尽管各国都开始重视竞争政策的协调与合作,但这种合作形式和程度各有不同;同时,总体上这些规范仍然较为粗浅。首先是关于反竞争行为规制的实体规范,有研究指出,在138个具有规制反竞争行为的实体规定的特惠贸易协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PTA)中,有113个协定涵盖了垄断协议行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但只有28个协定只涵盖了经营者集中行为,三者都包括在内的协定只有24个。①根据文献来源,其所称特惠贸易协定应当也包括了基于GATT第24条的FTA和CU,因为在该文章附录中不仅列举了CETA(欧盟—加拿大)和中国—智利FTA,甚至包含了南部非洲关税同盟这样的CU,因此一定程度上该文献中特惠贸易协定的特性也能反映RTA的特点。See Martha Licetti,et al.,Competition Policy,in Aaditya Mattoo,et al.(eds.),Handbook of Deep Trade Agreements 524-525(World Bank Publication 2020).具体而言,关于反垄断法这三大支柱行为的具体规定中,除了某些贸易协定对垄断协议行为采取了“目的或效果违法”的评价标准,或者对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采取了基于行为效果的评价方法或滥用行为类型化的规制范式以外,大多数的双边和多边协定都未能在对三大支柱行为列举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欧盟似乎乐见于将其较为完善的《欧盟运行条约》中的竞争法实体规定通过协定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但仅仅实现了对于《欧盟运行条约》中反竞争行为定义的转述。②See Martha Licetti,et al.,Competition Policy,in Aaditya Mattoo,et al.(eds.),Handbook of Deep Trade Agreements 524-525(World Bank Publication 2020).欧盟外的RTA仅注重各国竞争法实体规则以及执法机构的独立性,连规制何种行为以及如何划定竞争执法的范围都未达成一致,仅规定了反垄断例外适用的透明度要求、无歧视原则、合理抗辩、程序正当性等的要求。③例如,RCEP未对具体规制何种行为加以规定,而是在具体执法合作与程序规则上有许多规定。再如,USMCA虽然着重强调程序正当性与透明度要求,但其并不禁止本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发生在国外的商业行为的调查和规制,无法弥合管辖权的冲突。See RCEP,Article 13.2-13.7;USMCA,Article 21.1(2).此外,RCA中规定的竞争实体规则较为全面,在以上提到的所有RCA中都包含了具体的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但是,当前RCA的数量并不多,有许多RCA都不包含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统一规则;④以上提到的RCA中,不含经营者集中审查统一规则的RCA有CAN,CARICOM,EAEU与MERCOSUR,WAEMU,它们采用的是非强制性的统一审查规则。See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Regional Competition Agreements-Inventory of Provisions in Regional Competition Agreements,Annex to the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DAF/COMP/GF(2018)12,29 November 2018,Table 4.其次,达成RCA的国家一般都形成了较为深入的经贸合作,这一点难以具有复制性。因此,除了少数RCA外,大多数的RTA中规定的反垄断实体规则都较为简单。
2.竞争执法合作机制效果不佳
就竞争执法合作而言,RTA中的规定较为松散,这使得执法合作机制的效力存疑。首先,有研究指出,就FTA和PTA中形成的竞争执法合作模式来看,大致能够分为四种合作机制:执法机关的协调;信息交换;通报;技术协作。当然,并不是每个协定中都包含这四种合作机制,甚至某一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协定中包含的合作机制条款也不尽相同,例如,中国—韩国FTA规定了较为详细的通报、磋商、信息交换、技术合作的具体要求;中国—格鲁吉亚FTA中也提到了上述四点合作形式,但通过列举的形式阐释了前三种机制,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和要求;而在中国—瑞士FTA和中国—冰岛FTA中则仅仅提到了双方可以协商和信息交换的形式展开合作。当然,其他国家的FTA也是如此,尽管某些协定中还规定了更深入的执法合作机制,例如对于发生在某一缔约方的反竞争行为由多个缔约方展开共同调查的合作机制,①See Turkey-Montenegro FTA,Article 24.5;Turkey-Serbia FTA,Article 25.5.但能够达到如此高度合作机制的FTA较为少见。因此,大部分的FTA或PTA都体现出较为简单的竞争执法合作,这既是因为各国可能在很多细节性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也可能是因为许多国家尚未有成熟的竞争执法体系和经验所造成的。
就RCA中的执法机制而言,虽然某些协定设立了统一的竞争执法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执法效果却受到广泛质疑。例如,加勒比共同体竞争委员会只有6位委员和5位职员,每年的预算也极少,这导致了其成立以来没有发起过一起竞争执法案件;南方共同市场也是如此,其竞争执法机构自成立以来也没有发起过任何一项跨境反竞争行为调查。②See Mario A.Umaña,Regional Competition Arrangements: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n and the Caribbean,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DAF/COMP/GF(2018)6,paras.14,15,22.到目前为止,仅有欧盟的统一执法机构与欧盟法院这一竞争执法与司法合作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欧盟的统一模式也并未排除各成员国自身对于本国反竞争行为的管辖权。在《欧盟运行条约》以外的RCA中,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法律制度的差异,各国执法机构为了本国利益不愿意遵从区域执法机构的决定与要求,各国政府阻挠区域竞争立法和执法在本国的转化和实施等原因,③See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Regional Competition Agreements:Benefits and Challenges-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DAF/COMP/GF(2018)5,29 September 2018,Cha.4.2.区域内的统一执法名存实亡,各国仍然各自为政。
即便许多国家的竞争执法机构之间签订了能够补充RTA的竞争执法合作协议或备忘录,但大多数国家皆选择备忘录的形式,缺乏法律约束力,④根据OECD在2016年的统计显示,在OECD成员国签订的执法合作协议中,仅有15份协议属于政府间合作协议,而超过140份协议属于执法机关间签署的备忘录。See OECD Working Party No.3 on Co-operation and Enforcement,Inventory of Provisions in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Agreements(MoUs)-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nd Inventory,DAF/COMP/WP3(2016)1/REV2,July 2016,paras.3,5.无法确定各执法机关之间是否能依照备忘录执行。此外,能够达成共识的具体执法合作也较少,例如,第二代协议/备忘录(second-generation agreement)较少①第一代协议是指禁止涉密信息交换或者对于涉密信息交换采取非常严格限制的国际竞争合作协议;而第二代协议指的是能够进行涉密信息交换的竞争合作协议。See Patrik Ducrey,The Agreement between Switzerland and the EU Conce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ir Competition Laws,4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Practice 441-442(2013).See also Valerie Demedts,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aw Enforcement:An Assessment of the EU’s Cooperation Efforts 163-164(Koninklijke Brill NV 2019).,而这种协议或备忘录下执法机关可以进行涉密信息交换。但是,如果执法涉及数字平台巨头的数据、算法等因素,不可避免会涉及信息保密的问题,这样使得他国竞争执法更加困难。
3.实体规范与执法合作的低效引发监管困局
上述问题会为各国之间协调规制数字平台巨头的反竞争行为带来难题。由于跨境网络外部性的影响,数字平台巨头在本国一系列的反竞争行为同样也会对他国的消费者以及市场竞争环境产生影响。在该国缺乏反垄断执法的情况下,他国很难获取充分的证据,例如,如果需要准确识别竞争损害,实际上不仅需要考虑消费者与竞争者遭受了多少损害,行为的正当性与因果关系仍然是需要界定的要件。在经营者集中控制的场景中,这显得尤其重要,因为经营者集中体现的是对反竞争行为的预防,在分析单边竞争损害效应时,往往会分析经营者在集中后是否会作出该行为,同时要比较集中后作出行为与反事实分析情况下的竞争损害差异,②所谓反事实分析,即是对现有事实的某一因素进行改变的因果关系分析方式,在假定这一因素发生变化时对于其产生的效果进行分析。在经营者集中的场景下,其体现为合并后的竞争状态与同时期不发生合并时竞争状态的对比。See Cento Veljanovski,Credit Cards,Counterfactuals and Antitrust Damages:The UK Master Card Litigations,9 Journal of European Competition Law&Practice148(2018).如果不对企业行为的动机与可能性进行研究,则难以准确判断集中后市场竞争的影响。在无法对平台巨头特别是实体在他国的数字平台巨头进行调查的情况下,难以从行为的角度对于竞争损害的程度进行量度。即使在没有对行为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径直执法,也可能会导致管辖权冲突的情况。因为行为地在另一国家,该国仅发生了竞争损害效果。对于那些没有在该国设立实体的企业来说,这样的处罚不仅难以实施,即使实施,也难以对其造成实质惩戒。这样,该巨头企业的反竞争行为实质上并未得到真正的处罚,即造成了监管逃逸。再者,由于数据跨境流动的便利化,平台可以随时转换利用数据作出反竞争行为的地点,即使某一国进行高度严格的反垄断执法,数字平台也会如许多金融机构一般作出跨国性监管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的选择,将行为发生地放在弱监管的区域以达到规避执法的效果。③参见王兰:《全球数字金融监管异化的软法治理归正》,《现代法学》2021年第3期,第111-112页。实际上,这种规避监管的方式屡见不鲜,例如,许多数字平台巨头采用VIE股权架构以规避境外上市限制以及将注册地设在免税天堂地区以规避税收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就体现了监管套利。由此,并不能排除其为了逃避国内反垄断监管而采取的监管套利措施。然而,无论如何,缺乏实体与程序上的协调不仅不利于遭受损害国家对于其市场运行机制的救济,同时还会对双边贸易的公平性与自由度造成负面影响。
本文并非认为粗略的实体规则和低效的合作机制本身不应该出现,它们是因为各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形成的。不过,如果以这种程度的竞争立法与执法合作应对数字平台跨境的反竞争行为,不仅会忽视这些行为带来的许多方面的损害,也难以真正制止数字平台广泛在各国实施的反竞争行为。
(二)与数字平台规制的新特点结合不足
1.疏于考量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与竞争政策的结合
随着数据的跨境流动,平台经营者跨境收集消费者和竞争敏感数据(例如价格、产量等),通过算法实现商业决策的制定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平台经营者可能会滥用其市场力量,在各国消费者不知情的状态下收集其个人信息,或者在掌控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例如自我优待、降低数据互操作性与可携带性等方式排除本土的中小型竞争对手。①See OECD Global Forum on Competition,Competition Provisions in Trade Agreements,Contribution from TUAC,DAF/COMP/GF/WD(2019)18,December 2019,para.30.德国Facebook案与法国GDFSuez案反映了执法机关开始采用反垄断法的方式保护个人信息免受数字平台巨头不合理收集和使用,进而防止以上反竞争行为的发生。②在GDF Suez(现为ENGIE)案中,法国竞争执法局将“赋予竞争对手接入垄断者数据的权限”仅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而最终竞争执法局将隐私保护救济措施的制定转引至法国数据保护执法机构(CNIL),由该机构制定具体的针对该数据保护方案隐私保护方案,与竞争执法局的数据开放方案共同实施。See L’Autoritéde la concurrence,Decision 17-D-06 of 21 March 2017 Regarding Practices Implemented in the Gas,Electricity and Electricity Services,paras.289-294(Direct Energie/ENGIE).See also Bundeskartellamt(German Federal Cartel Office),Decision 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under Section 32(1)German Competition Act(GWB)on Facebook Inc.et al.B6-22-16,6 February 2019,paras.522-523.学界也在热议个人信息是否或者如何成为反垄断法的保护对象,假如其成为反垄断法的保护对象,由于监管积极溢出(positive spill-over)与消极溢出(negative spill-over)的影响,某国对于平台经营者收集和利用个人信息的竞争法处理都会正面或负面地影响到另一国家的市场竞争状况与竞争法的实施。③消极溢出是指某一国的执法对于他国的企业和市场竞争产生负面影响,而积极溢出指的是该国的竞争执法对于他国的竞争状况与消费者保护有正面影响。See Robert D.Anderson,et al.,Competition Policy,Trade and the Global Economy:An Overview of Existing WTO Elements,Commitment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Some Current Challenges and Issues for Reflection,OECD DAF/COMP/GF(2019)11,5 November 2019,para.73.因此,这需要各国竞争执法机构与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紧密合作,也需要数据跨境传输中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与上述协定竞争规则的协调。但是,过度地保护个人信息,对于跨国数字平台企业的数据收集行为进行严格限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跨境的竞争损害后果,但其却阻碍了平台经营者的跨国经营,反过来可能对国外平台经营者造成不合理的差别待遇,违反了在许多RTA中已经确立的非歧视性原则。尽管许多RTA中包含了数据跨境流动中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但其并未与竞争政策规则相结合,而两者在目前的环境下恰恰难以分离。①例如,数据可携带权有着双重含义:一是其在个人信息自决上的独立性,属于个人信息权利的范畴;二是其是维护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See Erika M.Douglas,The New Antitrust/Data Privacy Law Interface,130 The Yale Law Journal 656-657(2021).大多数RTA也未提到各国竞争执法机关是否能在他国竞争执法机关的协调下与他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关合作,这可能是由于各国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差异过大,也可能是因为本国竞争执法机构与数据规制机构的合作也尚未建立。
2.未能囊括数字行业监管层面的竞争促进机制
不过,光靠竞争规则上的合作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还需要数字行业监管框架下的进一步协调。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数字行业规制的框架,为数字平台巨头施加不得自我优待、平台互联互通、数据互操作等义务。然而这些义务或责任是基于每个国家不同的市场环境与监管措施所产生的,因此跨国数字平台巨头也许在不同国家要承担不同甚至冲突的竞争性义务。由于数字行业监管并没有国际化的标准,因此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解决这方面的冲突以及设立国际化的平台合规标准至关重要。就多边合作而言,《七国集团数字与技术部长宣言》(G7 Digital and Technology-Ministerial Declaration)表示,要共同努力,通过现有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协调与互补的方式促进数字市场的竞争和创新。②See Ministerial Declaration G7 Digital and Technology Ministers’Meeting,28 April 2021,4-5.欧盟和美国甚至还计划设立贸易与技术委员会,设立相应的技术标准在数字行业的监管上展开合作。③See European Commission,EU-USTrad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Inaugural Joint Statement,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1_4951,visited on 30 October 2021.行业监管上维持市场竞争的协调并不少见,例如,CPTPP就在金融服务、电信与政府采购行业设置了一些共识性义务,通过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防止垄断协议的形成等方式促进区域内的市场竞争。④实质上,在TPP中行业规制内的竞争政策已经体现,CPTPP并未对这些条款进行修正。See CPTPP,Articles 11.5,13.8,15.10,15.12,15.17 etc.See also Martha Martinez Licetti,et al.,Deep versus Shallow PTAs:Rules Affecting Competition Dynamics Antitrust,Competitive Neutrality and Pro-Competition Economic Regulation,World Bank Group Report,17-18,2020.但是,在电子商务领域或者USMCA所提出的数字贸易领域,尽管新近的RTA中在电子商务(数字贸易)专章中都设置了一定的线上消费者保护与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但对于平台接入、数据互操作的标准等问题则并未涉及。同样,对于行业监管机关与竞争执法机关的合作形式与程序也未能涉及,这一点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合作。
3.未能融入反垄断监管科技的合作路径
此外,就竞争执法合作而言,由于大数据、算法等的科技不断运用于数字平台的商业决策,各国执法机关也开始创新执法工具,或者通过进行市场调查的方式识别并处理竞争损害。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CMA)借鉴了其金融行为管理局(FCA)的经验,在其新设的数字市场部的反垄断监管中部署“监管沙盒”工具,测试新的算法行为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各种影响。①See Competition and Market Authority,Algorithms:How They Can Reduce Competition and Harm Consumers,January 2021,para.4.25.有学者也指出,应用程序接口与机器学习等技术能够成为监测算法引发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监管科技”。②See Rob Nicholls,Regtech as an Antitrust Enforcement Tool,9 Journal of Antitrust Enforcement 146(2021).同时,许多国家都对整体的数字市场或者某一方面的市场展开市场调查,对于本国或本区域的市场竞争状况进行评估,并预测与采取措施降低反竞争风险。③See e.g.,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Online Platforms and Digital Advertising Market Study:Final Report,July 2020;Australian Competition&Consumer Commission,Digital Advertising Services Inquiry-Final Report,September 2021;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 of Singapore,E-commerce Platforms Market Study: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September 2020;Japan Fair Trade Commission,Final Report Regarding Digital Advertising,February 2021.在目前的竞争执法合作模式下,就信息交换、通报等事宜而言,由于新的执法工具更多地采取了数字化的模式,较一般而言更加难以区分一般信息与商业秘密信息,因此为了保密的需要,执法机关可能会选择不进行信息交换和通报,而执法机关的“监管科技”的运作本身也可能是技术秘密,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也不能与其他国家共享。另外,这些数字化信息如何在执法机关之间传输也尚未可知,这同样需要遵守数据跨境流动的相关规范。大部分RTA在竞争执法合作机制方面规定过于简单且缺少约束力,难以有效应对竞争执法科技与频繁的市场调查带来的挑战。另外,仅就市场调查而言,除了少数RTA中的竞争条款有涉及之外,其他RTA均无此规定。尽管在某些执法合作协议的补充下,双方可以互相提供调查援助,但这仅是针对个案的调查,并非整体的事前性市场调查,即便是这种个案调查,其也没有规定具体调查援助的程序和准则。④See OECD Working Party No.3 on Co-operation and Enforcement,Inventory of Provisions in Inter-Agency Co-Operation Agreements(MoUs)-Note by the Secretariat and Inventory,DAF/COMP/WP3(2016)1/REV2,July 2016,para.26.
一国市场中的数字平台巨头的商业行为往往也会在另一国市场中出现,其竞争损害效果往往也具有相似性,市场调查方面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协定双方的相互借鉴,也有利于降低各国的反竞争风险。
四、可能出路:区域内的深化合作与数字贸易协定
(一)区域内竞争政策实体规则与执法合作机制的强化
有研究表明,数字贸易协定或竞争政策条款签订除了与地缘位置、经贸往来密切相关之外,还与商业文化与竞争文化认识的趋近性有关。①参见韩剑、蔡继伟、许亚云:《数字贸易谈判与规则竞争——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量化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11期,第133页。See Thomas K.Cheng,Convergence and Its Discontents: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erits of Convergence of Global Competition Law,12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84-485(2012).因此,在某一区域内国家或者邻国之间的RTA中,更容易就数字市场竞争条款的细化达成共识。此外,虽然上文中提到的区域内国家达成的RCA的效果有限,但是相较于一般的RTA而言,其都展现出更细致的实体规则与更深入的执法合作机制。就我国而言,也可以积极采取区域战略,先行与邻近国家在RTA中或与“一带一路”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体深化数字市场的竞争政策。
1.“趋近”区域内竞争政策实体规则
例如,就实体规则的趋近而言,同为东亚国家,中韩可以就数字市场的反垄断规则进一步的协商。因为我国《反垄断法》和韩国《垄断规制与公平交易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反限制竞争法》或《欧盟运行条约》的体例进行了借鉴,例如,不仅采用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方式,并且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中都参考了欧盟的严重阻碍实质竞争测试(SIEC测试)的标准。②相反,美国《谢尔曼法》第2条并非采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方式规制具有市场力量的单边反竞争行为,而是将其规定为“垄断行为”,而在《克莱顿法》项下对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而言,美国采用的是“实质减少竞争”(significant lessening of competition,SLC)的标准。这在我国《反垄断法》上体现为“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而在韩国《垄断规制与公平交易法》中体现为“实际抑制了竞争”。③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17、28条。See South Korean Monopoly Regulation and Fair-Trade Act,Article 7.5(4).See also Yo Sop Choi&Andreas Heinemann,Competition and Trade:The Rise of Competition Law in Trade Agreement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43 World Competition 532-533(2020).日本《反垄断法》虽然有着强烈的美国色彩,但在评价“市场支配地位”的时候,其也采用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市场份额”或“集中比例”(concentration ratio)测试,通过设定一定的市场份额标准推定“市场支配地位”;同样,中韩的国内竞争法也都采用此种基于市场份额的推定方式。④See Yo Sop Choi,The Choice of Competition La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nforcement in Asia:A Road Map towards Convergence,22 Asian Pacific Law Review 142(2014).因此,随着东北亚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中日韩自贸区框架谈判的不断推进,最起码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一项行为上,未来中日韩自贸协定竞争政策条款可以将其阐述得更为深入,而这一行为也在数字市场的背景下较为常见。实际上,竞争实体规则已经在中国—韩国FTA中的竞争政策条款中有所体现,其不仅涵盖了单独或共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也在经营者集中的条款中加入了“显著妨碍有效竞争,特别是形成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这一中国、韩国国内法所共同认可的判断标准。中国—韩国FTA也是我国签订的FTA中竞争条款最为完善的协定。
2.强化区域内竞争执法合作机制
另外,即使有国内法文本差异形成的阻碍,导致实体条款上的合作难以实现,区域内国家的竞争执法合作也可以深化。实现执法合作的深化无疑较实体规定而言更为容易。有学者认为,即便“一带一路”国家对于许多反竞争行为的实体规定和法律适用标准完全不一致,“一带一路”框架也可以建立起诉与证据分享机制,这不仅更有利于执法机关调查取证,而且还有利于增强各国竞争执法的互信,这一点还可以通过建立共同的执法程序规则加以体现。①See Kelvin Hiu Fai Kwok,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ooperation in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 Antitrust Enforcement,in Yun Zhao(ed.),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125-12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而且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都有国内的竞争立法,为此提供了充足的制度准备,有利于区域内竞争执法合作的形成。这种深化的合作实际上也不仅限于“行政执法合作”,还包括人员培训、资金支持以及通过互联网等手段开设竞争执法国际论坛,以便各国的学者与执法机关在论坛上互相交流,这一点在中国与欧盟或者金砖国家的竞争执法合作机制上有所体现。②See Jörg Philipp Terhechte,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Enforcement Law between Cooperation and Convergence 67-68(Springer 2011).这些合作措施也许在平台经济的反垄断上更为重要,因为其涉及许多新型的反竞争行为,只有少数大国拥有调查和执法资源和经验,那么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区域内较为弱小的国家提供执法协助,贯彻统一的执法理念无疑较为重要。
(二)数字贸易协定下竞争政策与数字平台特性的结合
为了应对数字贸易带来的革新,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一些国家开始在数字贸易领域寻求签订合作协定,例如,新加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美日数字贸易协定》(USJTA)、《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SADEA)、《韩国—新加坡数字伙伴关系协定》(KSDPA)以及《英国—新加坡数字经济协定》(UKSDEA)等。这些协定旨在就许多数字贸易的技术性问题达成一致,例如,新加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规定了从无纸化贸易、电子化货物的传输与物流、电子支付到个人信息保护、线上消费者保护、数字身份,再到金融科技与人工智能领域中各国需要遵循的义务。③See Marta Soprana,The 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DEPA):A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Trade Agreement on the Block,13 Trade,Law and Development 153-161(2021).See also Mira Burri,Towards a New Treaty on Digital Trade,55 Journal of World Trade 92-93(2021).不过,许多的DTA中也开始纳入竞争政策条款,意图通过更为专业化的方式解决数字平台竞争政策的国际合作问题。
1.参照数字贸易协定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实际上,就上文提出的三点RTA中尚未涵盖的、与数字平台特性有关的议题而言,采用DTA竞争政策条款的方式加以规定似乎更佳。当然,如果无法达成专门的DTA,在新近具备丰富数字贸易关联条款的RTA(例如USMCA)中处理也可行。就数字市场竞争维护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联系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机关与竞争执法机关的合作机制问题而言,依照德国Facebook案和法国Suez案来看,识别竞争损害同时需要对个人信息损害进行界定。而许多DTA对于在跨境数据流动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措施进行了列举,要求数字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采取这些措施并增加成员国之间个人信息保护机制的互操作性。①See DEPA,Article 4.2(3),(4),(5)and(6).在识别个人信息损害时,新加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各国执法机关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指引,例如,没有采取新加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所列的保护措施,则构成个人信息的损害,进而也会构成竞争损害。
2.融合数字贸易协定的数字行业监管规则与标准
在数据开放标准以及数字行业监管标准的议题上,DTA也可成为较好的实现路径。例如,澳大利亚与新加坡在签订《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前委托机构对于这些标准进行了研究,其涵盖了金融信息和支付标准、应用程序接口(API)开放标准、二维码标准、跨境物流平台标准、数据可携带标准等项目,同时还涉及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金融科技等的标准。这些标准为平台反垄断中的竞争损害认定和救济措施设计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参照。②《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一定程度上将协定签订前关于数字贸易标准的研究成果转化为了实体规定。See TRPC Pte Ltd,Australia-Singapore Digital Economy Cooperation on Standards-Research Report,September 2020,34-41.《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中还含有竞争政策条款,在该协定中,成员国被要求分享数字市场的竞争执法经验以及发展数字市场的竞争执法工具和政策,其中包括了信息交换与技术性的合作措施等的机制。③See SADEA,Article 16.那么根据协定内部体系的理解,这些信息和技术性措施当然也包括了这些数字行业标准的取用,自然可以包括该DTA中所共同商议确定的标准。
3.通过数字贸易协定展开反垄断监管科技的合作
就监管科技而言,在金融领域,《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也提到了各国在金融科技与监管科技领域的合作,例如,各国通过监管沙盒等的机制发现并监管新的数字跨境金融科技形式,以及在开放银行领域的合作。④See SADEA,Article 32(c).当然,监管科技目前在金融行业较多适用,尚未广泛延伸到其他领域,但采用科技手段实行反垄断监管已然成为趋势,我国市场监管总局不久前也建立了竞争政策与大数据中心。⑤参见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竞争政策与大数据中心组建成立》,https://www.samr.gov.cn/xw/zj/202112/t20211217_338179.html,2022年1月19日访问。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数字贸易中监管科技将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无论是对于反垄断监管还是其他行业的监管而言,皆是如此。
不过,不同的DTA中的标准和竞争政策条款也有差异,新加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竞争政策条款被置于“新兴趋势和技术”(emerging trends and technologies)模块中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和政府采购的合作并列,并未独立成为一个模块。①See DEPA,Article 8.4.这似乎反映了新加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数字经济中的竞争问题仅作为技术性问题加以考量,并未从全局加以把控,有着独立竞争政策条款的《新加坡—澳大利亚数字经济协定》则与此不同。这体现了不同的DTA对于竞争政策的设计方式和重视程度不一样,较为疏浅的DTA也许在竞争政策的趋同与合作上仍有不足,使得条款效力有所缺乏。不过,总而言之,无论DTA中的竞争条款深化的程度如何,DTA都是能够建立并深化平台竞争规制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之一。我国在提出加入新加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基础之上,也可以顺势为进一步深化新加坡《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的竞争条款提供我国的方案,站在整个数字贸易全局的基础上创设更加公平与开放的数字市场环境,为巨头企业设立更细致的竞争性义务,更为我国数字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结 语
数字平台反垄断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国内竞争规制议题的重点之一,其预示着传统反垄断法行为判断与救济标准的变革,这在我国也不例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数据跨境流动、跨境网络外部性等因素的影响,数字平台巨头的跨国经营已经不再是阻碍。事实上,以GAFA为首的美国数字平台巨头们已经在许多国家的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市场力量,不仅相互之间进行排除,更会排斥本土中小型数字市场经营者,美国本身却疏于对这些巨头进行强力的反垄断规制。然而,无论是FTA还是RCA中的竞争条款,即使有机构间的执法合作协议的补充,还是难以形成较为统一的数字平台反垄断规制谱系,大多数的贸易协定文本仍然浮于表面,缺乏对于数字市场规制模式的深入理解,各国在数字市场竞争规制方面的利益冲突也难以协调。因此,先行探索具有趋近性竞争政策目标与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区域内的深化竞争规则,同时通过DTA的途径探索数字竞争规则较为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