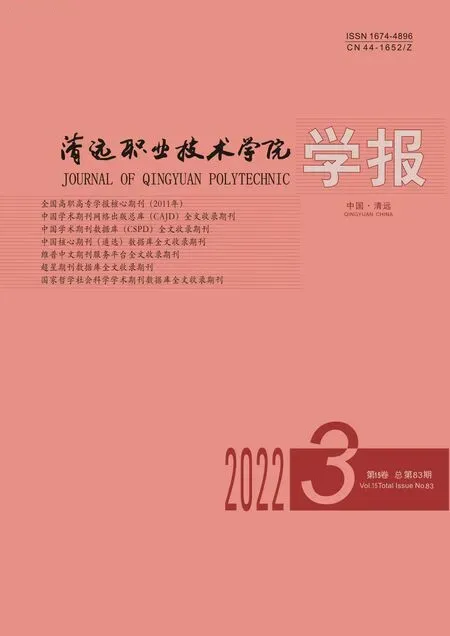地方金融资产交易所融资理财产品风险分析及防范应对措施
张梦娇
(肇庆学院计算机科学与软件学院、大数据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1 地方金交所的法定内涵及融资理财产品模式的分析
1.1 地方金交所的法定内涵
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 号,以下简称38 号文)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 号,以下简称37 号文)有关内容,地方金交所为地方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综合性金融资产交易服务平台,主要为各类投资、融资主体提供金融资产相关的转让交易、撮合登记等服务。主要特点如下:一是经政府审批设立。凡使用“交易所”字样的交易场所,除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外,必须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前,应取得国家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的书面反馈意见。由于经国务院或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交易所服务范围覆盖全国,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等全国性交易所,此类不属于地方金交所。此外,37 号文明确,从事权益类交易、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以及其他标准化合约交易的交易场所,原则上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经营活动,因此地方金交所不应设立分机构跨区域经营。二是地方金交所产品的购买者需拥有合格投资者资格。根据《关于印发〈关于稳妥处置地方交易场所遗留问题和风险的意见〉的通知》(清整联办〔2018〕2 号)要求,“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应制定投资者(包括交易类业务的买方)适当性制度,且投资者适当性标准不低于《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 号,即《资管新规》)要求的合格投资者标准”。《资管新规》将投资者分为不特定社会公众和合格投资者两大类,合格投资者包括自然人合格投资者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格投资者。其中,自然人合格投资者需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 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 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 万元。法人单位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1000 万元。因此,地方金交所融资理财产品的购买门槛较高,投资者须对投资风险有一定认识,能够并愿意承担一定的投资损失。三是产品交易的其他限制规定。地方金交所不得将任何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不得采取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不得将权益按照标准化交易单位持续挂牌交易,权益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 人,不得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不得从事保险、信贷、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
1.2 地方金交所融资理财产品模式的剖析
经查询公开信息和查看部分地方金交所合同协议,地方金交所融资理财产品一般存在挂牌方、摘牌方、担保方、地方金交所等四个交易主体,和以下五个交易环节:第一步,产品打包。挂牌方将其应收账款、收益权等权益类资产进行打包,形成以打包资产作为底层资产的拟挂牌产品。拟发布产品一般会折价发行,即挂牌价格低于应收账款、收益权等的票面价值。第二步,兑付担保。挂牌方请担保方对拟挂牌产品的兑付进行担保。一般在交易协议中予以明确,担保方对挂牌产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步,产品发布。挂牌方向地方金交所提出融资需求并申请挂牌,地方金交所在其网站上发布有关信息,重点面向地方金交所的会员进行宣传推介。第四步,撮合摘牌。地方金交所协调有意愿的会员通过竞价等方式来确定最终摘牌方,摘牌方向挂牌方支付挂牌价格,挂牌方分别向地方金交所、担保方支付服务费、担保费。挂牌方提前回笼资金,可投入到下一轮再生产中,以获得更多生产利润。第五步,到期结算。产品正常到期后,摘牌方能获得挂牌价格和票面价值的差额回报。
2 当前我国地方金交所融资理财产品面临的主要风险
经分析,地方金交所的融资理财产品存在合法性风险、真实性风险、涉众性风险,须予以高度重视。
2.1 合法性风险
仵永恒认为,地方金交所部分产品和业务不合规[1]。实践中,38 号文、37 号文有关风险防范措施的规定基本上能够应对文件出台时的风险现状,即存在交易场所未经批准开展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管理人员侵吞客户资金、经营者卷款跑路等问题。根据38 号文、37 号文有关规定,权益类产品不能够拆分为均等份额,并公开发行,其实际持有人累计不得超过200 人;而且,地方金交所原则上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经营活动。在2020年举行的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部际联席会议第五次会议明确提出,地方金交所登记备案、挂牌交易的非标债务工具总体风险较高,要求各地督促辖内金交所依法合规经营、严守法律边界,不得向个人销售产品、不得跨区域展业。然而,随着地方金交所理财产品不断创新发展,在新交易模式下部分挂牌方、摘牌方的有关行为突破了或绕开了监管,导致有关措施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效果削弱,地方金交所理财产品的合法性风险抬头。第一,新交易模式绕开了对实际持有人数的限制。摘牌方在摘牌之后,将应收账款等资产包装成理财产品,切割为均等份额向不特定群众公开销售,实际持有人数可突破200 人的限制,变相突破了38、37 号文的规定,产生较大的涉众风险。第二,新交易模式突破了对经营地域的限制。新交易模式下,地方金交所业务仍然仅在本地开展,但摘牌方企业可在多地设立分公司开展地方金交所理财产品销售业务,变相突破了地方金交所有关业务不得设立分支机构在异地开展经营活动的监管措施,加大了跨区域协同监管难度,容易出现监管盲区。第三,容易产生摘牌方的监管缺位问题。根据目前金融监管体系,投资公司的监管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进行,但目前各地对投资公司的定义尚不明确,行业监管办法尚未完善,容易产生监管空白。如投资公司不仅以自有资金,还吸收群众资金来进行对外投资活动,就具有公共性和外部性,对经济和社会安全稳定产生影响,不符合“金融特许经营”原则。同时,投资公司发布的理财产品也未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管,理财产品的合法性真实性存疑,容易成为非法集资的工具。
2.2 真实性风险
蓝翔等人指出,部分地方金交所产品存在信息透明度不高、信息披露不充分、对资金流向的监控不足等风险问题,隐藏了较大的法律和道德风险[2]。实践中,由于地方金交所不对底层资产、挂牌方、担保方有关情况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核查,仅对有关交易进行登记备案,常出现以下风险问题。
一是底层资产真实性问题。如底层资产为应收账款类权益,有关上下游交易是否真实;如底层资产为车位租金收入等权益,有关车位数量和用户数量描述是否真实;底层资产是否会重复挂牌、随意分割,从而一标多融。
二是担保方是否有能力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问题。较多协议合同中均有类似“担保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表述”,有关表述似乎能增强投资者投资信心。但由于地方金交所并未对担保方担保资质能力开展实质性调查,且担保方一般同时承担多个挂牌产品的担保责任,一旦兑付风险爆发,担保方流动性将受到严重影响,无限连带责任只能流于纸面。
三是挂牌方与担保方、有关企业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问题。经查看有关合同协议,部分挂牌方与担保方、底层资产涉及上下游相关企业经穿透后存在关联关系,如同一集团的母子公司、兄弟公司等,因地方金交所并不对资金流向进行监测,可能会产生挂牌方自融自用问题。
四是摘牌方的资质问题。如摘牌方为自然人投资者,则自然人投资者需满足合格投资者资格。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银发〔2018〕106 号)规定,合格自然人投资者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资产管理产品最低不低于30 万元(固定收益类),具有2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300 万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500 万元,或者近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40 万元。上述投资的门槛条件并不低,根据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2020年平均工资水平为97379 元,40 万元个人年均收入约等于2020年平均工资水平的4.1 倍。但据了解,部分地方金交所采用由自然人投资者签署合格投资者承诺书的方式,来确认自然人投资者是否具有合格投资者资格,而不对自然人投资者家庭财产情况或收入情况进行核查。因此,可能出现部分自然人投资者因不了解合格投资者意义和自身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而盲目签署承诺书的情况,也可能出现自然人投资者虚假承诺情况,无形中降低了地方金交所产品的投资门槛,提高了产品涉众性。
2.3 涉众性风险
吴晋科认为,地方金交所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不足,降低了投资者门槛,同时地方金交所涉嫌发行标的或转让对象违规[3]。地方金交所的理财产品向广大投资者发售,如出现违法违约,容易引发众多投资者关注。第一,有关产品的自然人投资者数量较大,涉众风险较大。根据上述分析,鉴于实际运作中存在摘牌方投资公司将资产包装为理财产品向不特定群众公开销售的情形,以及部分地方金交所并未充分验证自然人摘牌方是否具有合格投资者资质的情形,使得有关融资理财产品的实际投资人数超过200人的监管上限。第二,融资理财产品超出部分自然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易引发社会矛盾。同样地,由于投资公司和部分地方金交所并未对自然人投资者的家庭财产情况和投资经验情况进行实质性检验,部分自然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容忍度与融资理财产品不匹配,导致部分自然人投资者承担了难以接受的投资损失风险,一旦产品逾期,将严重影响生活。第三,刚性兑付预期未打破,容易引发集体维权。在自然人投资者角度来看,因为融资理财产品在地方金交所挂牌交易,且多有国内知名的大集团大企业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担保方,所以认为此类融资理财产品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较低的投资风险,普遍存在刚性兑付预期,因此投入较多的资金购买。一旦产品“爆雷”,产品逾期的实际和刚性兑付预期冲突,将引发大面积维权诉求。
3 防范化解地方金交所融资理财产品风险的对策建议
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地方金交所产品作为中小企业资金融通的重要补充渠道,应当从源头上予以规范,防范化解风险。
3.1 强化地方金交所的审核和管理责任
就目前地方金交所的交易模式来看,风险主要集中在挂牌方和摘牌方两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对挂牌方的监督。通过对地方金交所业务的指导,督促地方金交所完善对挂牌方资质的核实登记备案规范要求,落实对挂牌方和其挂牌底层资产真实性的核查;建设全国统一的地方金交所备案产品底层资产信息库,将经核实的底层资产有关信息上传信息库,并向地方金交所开放查询,降低虚假挂牌、多地重复挂牌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摘牌方资质的认定和管理。如摘牌方为自然人合格投资者,要严格测试客户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采用如要求提供存款证明、流水收入证明、投资经历证明等方式核查检验其是否具备合格投资者资质,确保不同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的客户能与融资理财产品互相匹配。如摘牌方为投资公司,要加强会员管理,强调会员纪律,不得将融资理财产品向不特定公众转售;如发现有关违法违规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和金融监管部门反映,并将该投资公司和其法人、董事、监事、高管列入黑名单。
3.2 规范整治投资公司涉地方金交所业务
如前文所述,目前各地对投资公司有关监管办法尚未完善,大部分投资公司仅需要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即可开展业务,同时没有像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受到日常监管,因此投资公司长期游离于监管之外,风险底数不清。为逐步化解投资公司风险,要组织各地对投资公司进行风险排查。一是把好市场准入关,严禁企业工商注册或信息变更时,其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投资”“财富”“理财”等有关字样,严控新增风险。二是明确风险排查整治对象。需要根据各地实际,将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含“投资”“财富”“理财”等有关字样的企业纳入风险排查范围,列出排查整治名单,对实质开展的业务进行现场检查和宣传教育;如发现有投资公司开展地方金交所融资理财产品业务,要列为重点整治对象,融资理财产品的挂牌方、融资方、待兑付余额、投资者人数等产品明细需要定期报送给当地金融监管部门。三是压降风险规模。压实有存量融资理财产品的投资公司主体责任,严控新产品的发售,兑付出清存量产品,逐步压降待偿余额和投资者人数,减轻社会面影响。四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如整治过程中发现投资公司存在虚假标的、设立资金池、关联公司挂牌摘牌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侦办。五是加快出台投资公司监管规则。要坚持“金融特许经营”原则,尽快研究出台投资公司监管规则,填补监管盲区,规范经营业务,定期报送经营数据。
3.3 坚持源头治理
一方面,要多渠道多层次开展投资者宣传教育。不断提升群众金融素养,掌握基本金融常识,了解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对个人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偏好类型有一定认识。打破刚性兑付预期,自觉承担投资失败损失。提高群众防范非法集资的意识和能力,开展监测预警和举报奖励,及时作出风险提示,铲除问题投资公司的生存土壤。另一方面,要拓宽合规融资投资渠道。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引导资本流向中小微企业,打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症结。坚持“金融特许经营”原则,全面将投资公司纳入地方金融监管,鼓励开展风险可控的金融创新,新业务模式产品须经备案后运营,且匹配具有一定投资经验和适当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者,确保发展可持续、风险不外溢。丰富群众可投资金融产品,支持金融基层服务点和投资咨询服务发展,指引群众配置期限不同、标的各异的投资组合,形成合理的投资结构,推动财富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