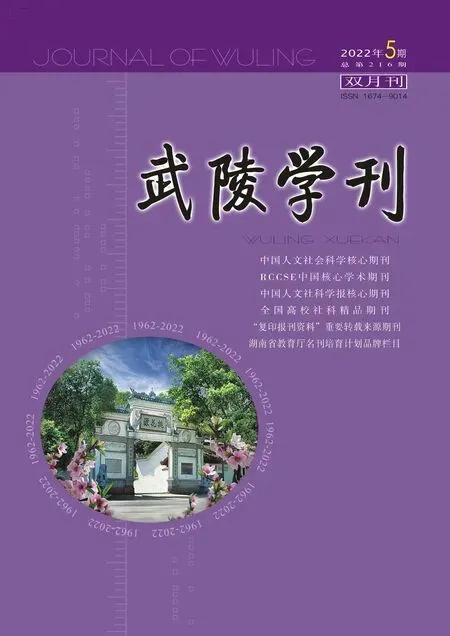晚清社会学与章太炎文论观的建构
余 莉
(湖南文理学院 文法学院,湖南 常德 415000)
晚清民初,由严复引领的社会学逐渐形成了一股学术思潮。在这股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正积极寻找革命思想武器的章太炎也将学术视野拓展到社会学领域,他不仅在1898年与曾广铨合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部分理论并以《斯宾塞尔文集》在《昌言报》上连载,还在1902年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完整的社会学译著。章太炎在该书序言中认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理念“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1]45,更胜于斯宾塞学说。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代表,章太炎在阐述西方社会学说时与严复等人一样喜欢将其与中国传统学术会通,以致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与学术理念逐渐渗透到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体系中。1902年夏,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就提到社会学对其史学研究的影响:“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2]61其实,章太炎不只是史学思想受到晚清社会学说的激发,其文论思想也同样被晚清社会学研究视野和学术理念所影响,尤其体现在文学溯源、论体审美以及文学风格论这三方面。
一、社会进化与章太炎的文学溯源
关于文学起源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论著作中一直含混而神秘。《文心雕龙》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又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将文学起源与宇宙起源结合,并引导至征圣宗经,唯心主义倾向比较明显,所以鲁迅曾批评刘勰的文学起源论“其说汗漫,不可审理”[3]。然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刘勰的文学起源论影响甚广,后世鲜有别出心裁者。晚清社会学勃兴之后,进化论指引文学研究向历史深处挖掘,翻开了文学起源研究的新篇章。章太炎的文学起源研究以社会学视野下的语言文字进化为基础,涉及到文学与言语、文学与文字、文学与图像三个层面的构建。
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章太炎认为文学最初权舆于言语。1902年4月,章太炎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第五号(续第九号、十五号)发表了《文学说例》一文(此文内容与《訄书》重订本《订文》篇所附《正名杂义》基本相同),在该文中,章太炎提出了自己的文学起源观,曰“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这种观念与其社会学译著中的观念如出一辙。1898年,章太炎与曾广铨合译的《斯宾塞尔文集》中讲到语言变迁与社会进化之关系时说“人之初言,喜怒哀乐,皆作一声。……然始以唇吻达意者,亦仅有动静与名物二语耳。其后支流余裔,日以繁赜,记动静者,析动静为二;记名物者,分虚实为二。其气之缓急,时之先后,事之等级,物之盈歉,又各为标识,则又有以连语譬况者,有定其形势审其位次者,有助动静附动静代名物者。辞气既备,人始得以言道意”[1]9-10。所以,章太炎认为言语是文学的最初来源。
章太炎还提出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文字。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言语的局限越发明显,社会交流出现障碍,文字应运而生。于是,文字成为文学的又一来源。在1902年《文学说例》中,章太炎曾从社会进化角度提到这一观点,在提出“文学之始,盖权舆于言语”之后接着说“自书契既作,递有接构,则二者殊流,尚矣”[4]403。强调言语与文字分离的观点也可以在章太炎的社会学译作中找到相应的学理。如其《论进化之境》译文中说:“人初有语言也,固不能遍包众有,其形色志念之相近者,则引申假借,归之一语。俄而聆其言者,眩惑如射覆矣。乃不得不为之分其涂畛,而文字以之孳乳。”[1]10人类最初的言语并不能包罗社会万象,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引申假借成为常态,语义越来越复杂,听者常有猜谜之惑。当言语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交流的需要,于是文字就派生了,并成为文学的又一重要源头。1906年9月,章太炎印行了《国学讲习会略说》,其中《讲文学》一篇以论文学起源开篇,正式提出了文字是文学之源的观点:“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5]32这里所谓的“文”就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学”,而其所谓“文学”,则相当于文论。在这篇文章中,章太炎明确了“著于竹帛”的文字就叫文学。与1902年的《文学说例》相比,此时的章太炎显然更坚定了以文字为文的文学观念,而且这种坚信到1910年出版《国故论衡》时也未曾改变,成为了他一生的坚持。
章太炎认为文学“权舆于言语”,又坚持“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这并不矛盾,恰恰证明他的文学起源观受到社会进化理念的影响。他在《文学说例》中说:“夫炎、蚩而上,结绳以治,则吐言为章可也。既有符号,斯淆杂异语,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绝言者,无能往来,况夫审别流变耶?”[4]403章太炎认为,人类社会在“结绳以治”的年代,社会交往靠口耳相传,此时文学表现在言语中。有了文字之后,言语与文字分离,文字就成了文学的重要来源。中国古代的文字学被称为“小学”,因此他说“世有精炼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4]403章太炎的这种观点看似是经学家的,其实有很多社会学理念的参与,且《文学说例》一文中对社会学说的引用与论析也不胜枚举。此外,社会学还扩展了章太炎对“小学”的认知。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之演讲》中谈到中西语言文字观差异时说:“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每一个字,有他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那欧洲比较语言的学,范围不同,性质也有数分相近。但是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专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余此类,一时不能尽说。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5]8-9这些社会学研究思路的加持,使章太炎的文学起源研究更具近代科学精神。
除言语与文字之外,章太炎的文学起源研究还注意到了图像与文学的关系。在其所译《论进化之境》中就有关于文学与图像方面的论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皆昉乎营造宫室而有斯制。”[1]10因为注意到了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所以在文学分类上,章太炎的标准也不同于常规分类。在《讲文学》中,章太炎将“图书”“表谱”“簿录”“算草”归类为无句读文,与诗词歌赋、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等有句读文一起收入文学囊中。这种分类意识也受到其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学起源研究的影响,是其文学起源研究的一种延伸。我们可以从其列表分类前的一段论述找到印证:“文字初兴,本以代言为职,而其功用,有胜于言者。盖言语之用,仅可成线,喻若空中鸟迹,甫见而形已逝。故一事一义,得相联贯者,言语司之。及夫万类坌集,棼不可理,言语之用,有所不周,于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谱图画之术兴焉。凡排比铺张,不可口说者,文字司之。及夫立体建形,向背同现,文字之用,又有不周,于是委之仪象。仪象之用,可以成体,故铸铜雕木之术兴焉,凡望高测深,不可图表者,仪象司之。然则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则有独至,凡无句读文,皆文字所专属者也。”[5]39将这一段话与《论进境之理》《订文》及《文学说例》中的观念相比,可知章太炎的文学分类以及其对图像的重视,也与其社会学研究一脉相承。
社会学视野使章太炎的文学起源观跳出了传统文论的神秘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科学精神,但传统学术依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以文字训诂为基础的小学给章太炎的文论起源研究作了详细注脚。可以说,章太炎的文学起源观是晚清社会学与传统小学相会通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章太炎的文学起源研究虽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然而当时文坛正在向纯文学转向,所以这种杂文学理论就显得脱离了文学创作实践,故被视为保守或复古。章太炎文论以社会进程立论,又被社会进程碾压。这大概是他没想到的。
二、社会意识与章太炎的论体审美
晚清社会学不仅影响了章太炎的文学起源研究,还影响到他的文章审美观,其中论体审美研究更是章太炎对文章学史的一大贡献。在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文学七篇中,有《论式》篇专门讨论论体文的审美问题。在章太炎看来,论体文要以周秦诸子为正宗,以汉魏六朝论体文为表率。这种审美观的形成与晚清社会学热潮挟带而来的社会革新意识有密切关系,章太炎发现了周秦诸子和汉魏论体文在革新社会意识方面的价值,故而将之推举为论体文的典范。
晚清社会学的传播与发展激发了求新求变的社会意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文学变革作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认为在社会革命之前,有必要先通过文学变革来开启民智,于是发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中以“小说界革命”影响最大。1898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在《清议报》第1册发表文学评论——《〈佳人奇遇〉序》,该文将小说的社会功用提高到六经、正史、律例均不及的高度。梁启超又在1902年撰写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进一步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6]246-249此后,小说成为“改良群治”的有效武器,而改造民族文化心理、开启民智也成了当时文坛的时髦话题。在开启民智、塑造国民精神等社会意识层面,章太炎与梁启超目标一致,所不同的是,梁启超倾向于用西方文学的成功经验,用俗语文学(即新小说)去宣扬新思想、塑造新国民,而章太炎则主张文学复古,在传统学术中寻找合适的资源。章太炎的思路是以诸子为途径,试图用诸子学理(如名实关系探讨)来拨乱反正。他早年从俞樾学,对诸子学用力颇深,接触社会学后发现诸子学说与社会学有会通之处,故而对诸子学越发看重。1902年,章太炎在《致吴君遂书》中说:“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2]118这份进化之理正是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视周秦诸子为论体文之正宗的重要基础。
以周秦诸子为参照,章太炎发掘了过去一直不为文坛看重的汉魏六朝论体文。在《国故论衡·论式》中,章太炎将魏晋之文与周秦诸子对比,将魏晋论体文提到周秦诸子的高度:“魏晋之文,大抵皆埤于汉,独持论仿佛晚周。气体虽异,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矣。”[7]453这是章太炎文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并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为何章太炎会对汉魏六朝论体文有如此高的评价呢?细究其中缘故,其实与章太炎1902年前后的社会学研究有密切关系。在文章写作上,章太炎一开始追从韩愈,后又在谭献的引导下推重汪中,并未太重视汉魏六朝论体文。对汉魏六朝论体文的重视是1902年前后的事,标志性事件是《訄书》的修订。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其《自述学术次第》和《自定年谱》中找到印证。章氏在《自述学术次第》中说:“余少已好文辞,本治小学,故慕退之造词之则。为文奥衍不驯,非为慕古,亦欲使雅言故训,复用于常文耳。……三十四岁以后,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读三国两晋文辞,以为至美,由是体裁初变。”[8]500又其《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中说:“余始著‘訄书’,意多不称。自日本归,里居多暇,复为删革传于世。初为文辞,刻意追蹑秦汉,然正得唐文意度。虽精治‘通典’,以所录仪礼之文为至,然未能学也。及是,知东京文学不可薄,而崔实、仲长统尤善。既复综核名理,乃悟三国两晋间文诚有秦汉所未逮者,于是文章渐变。”[9]在《訄书》修订本的《学变》篇中,也可以找到章太炎看重“东京之文”的痕迹:“王符之为《潜夫论》也,仲长统之造《昌言》也,崔寰之述《政论》也,皆辨章功实,而深嫉淫靡靡,比于‘五蠹’;又恶夫以宽缓之政,治衰敝之俗。《昌言》最恢广。上视扬雄诸家,牵制儒术,奢阔无旋,而三子闳达矣。”[10]147可见,章太炎在1902年突然看重汉魏六朝论体文,与其社会学研究有密切关系,是其社会意识和学术思维发生变化后在文章审美上的一种反映。
在外部学术环境的影响之外,章太炎看重周秦诸子和汉魏六朝论体文的内在理路,在于他认为周秦诸子、汉魏六朝论体文所体现出来的革命意识与学术精神,能在一定程度上契合晚清社会所需要的社会变革意识和个性解放。随着章太炎对社会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斯宾塞社会学说已经不能继续满足他的学术追求。1902年,章太炎翻译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在该书的出版序言中,章太炎评价斯宾塞的社会学说虽善于“藏往”,但“匮于知来”。在对斯宾塞社会学说的反思过程中,章太炎后来又陆续写作了《俱分进化论》和《四惑论》等文章。在《俱分进化论》中,章太炎引用赫胥黎等人的观点来反对斯宾塞,认为进化只是自然规律,而非社会原理;在《四惑论》中,章太炎提出另有不同于自然进化的社会意识和大道规则,并认为社会意识才是社会发生和进步的动力。于是,周秦诸子和汉魏六朝论体文在晚清社会学说的激荡下成为了革新社会意识的传统资源。在《国故论衡·论式》篇中,这种社会变革意识和独立个性精神暗含于“仑者,思也”的审美定位中[7]436,章太炎举庄子《齐物论》、公孙龙《坚白》《白马》、孙卿《礼》《乐》、吕不韦《开春》为例,说“前世著论在诸子,未有率尔持辩者也”[7]437。从这四个释例来看,《齐物论》旨在解决诸子学派纷争,《坚白》讨论名实关系问题,荀子以《礼》《乐》论治国之本,《开春》由自然现象思考社会现象,均体现了对社会现象和社会意识的深刻思考,表现出极具个性的学术精神。虽然重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中国文论自古以来的主论调,对学术性的看重,也是清代经学家的一贯选择与坚守,似乎与晚清社会学没有关系,但从《论式》后续的相关论述来看,又实与晚清社会学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意识紧密相连,比如“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此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也”[7]438-439。章太炎所列举的这三篇论著在当时都极具改革性。以《昌言》为例来说,作者仲长统是东汉末法家的代表人物,他在《昌言》中公开挑战儒家,针对儒家所提出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提出“三代不足慕,圣人未可师”的观点,主张以法家的精神对儒家进行清理。这种批儒的倾向与1902年的《訄书》修订高度一致。可见,章太炎对论体文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看重,实带有社会变革意识和追求个性精神的倾向。
这种倾向也可以在章太炎当时的一些文章中找到例证。作为近代提倡个性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太炎早在1894年的《独居记》一文中就批判“入世则以独为大邮”的偏见,主张个性解放才是孕育新“大群”的母体。接触社会学说以后,受社会学理念的影响,章太炎的社会变革意识更加激进,著书立说常常大胆挑战传统意识,不断爆出惊人之语。如其《读〈管子〉书后》,大胆挑战“重农抑商”传统观念,认为《管子·侈靡》中所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观念,“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之本,亦泰西商务所自出矣。”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了《〈革命军〉序》,盛赞邹容此书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8]233。又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大骂光绪皇帝“载湉小儿,不辨菽麦”。章太炎自己的文章写作也充满了社会革命意识和对个性精神的追求,真正实践了其论体文审美标准。
这里要同时提出的是,章太炎论体文的思想精神虽然走在革命前列,但文辞形式偏又格外保守,比如《訄书》文辞刻意古奥。章太炎自己的解释是在“提倡国粹”,或说“文学复古”。后人也据此视章太炎为保守派代表人物。惟朱维铮在《〈訄书〉发微》一文中认为,章太炎所谓的“文学复古”并不是大众所理解的复古,而是“文艺复兴”的意思。“我以为清末出现的‘文学复古’主义,倒不可与‘复古主义’等量齐观。‘文学复古’是外来语,后来被通译为‘文艺复兴’。章炳麟何时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史发生兴趣?尚待考证。但他被清末最热衷于在中国实现意大利式‘文艺复兴’的一派学者,视作精神领袖,则由一九〇五年二月在上海创刊的《国粹学报》,提供了明证。那以后章炳麟一再把他‘提倡国粹’,与意大利的‘文学复古’相比拟,更是直接证明。”[11]从论体文审美这一视角来看,章太炎对社会变革的希冀,对个性精神的追求,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与文艺复兴有相通之处。
要之,随着章太炎社会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开始重视社会意识建设,追求个性解放,他对周秦诸子的审美推崇,尤其对汉魏论体文的发掘,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晚清社会学说的影响。这种论体审美观,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而言,亦未免不是一副苦口良药。
三、环境、体格与章太炎的文学风格论
晚清社会学还影响了章太炎的文学风格论,他认为自然环境与人体体格影响了文学风格。关于环境与文学风格的关系,中国传统文论主要重视的是政治环境,如《礼记·乐记》中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2]。刘勰《文心雕龙》中有《时序》篇全面研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中有“八音与政通,而文章与时高下”[13]等等。与传统文论相比,章太炎的立论基础略有不同,他不仅关注政治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如“国势论”),而且将自然环境与人的精神、体格、道德勾连起来,构成一个文学风格论系统。
晚清进化论兴起后,自然环境对艺术风格的影响逐渐被重视。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丹纳《艺术哲学》中说,“气候与自然形势仿佛在各种树木中做着‘选择’,只允许某一种树木生存繁殖,而多多少少排斥其余的。自然界的气候起着清算与取消的作用,就是所谓‘自然淘汰’。各种生物的起源与结构,现在就是用这个重要的规律解释的;而且对于精神与物质,历史学与动物学植物学,才具与性格,草木与禽兽,这个规律都能适用”[14]。在《訄书》重订本的《原学》篇中,章太炎详细解析了自然环境对学术的影响,“寒冰之地言齐箫,暑湿之地言舒绰,瀛坞之地言恢诡,感也。故正名隆礼兴于赵,并耕自楚,九州五胜怪迂之变在齐稷下。地齐然也”[10]136。虽然文章末尾处章太炎认为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自然环境的影响会逐渐减弱,“夫地齐阻于不通之世,一术足以柁量其国民。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10]136,但是,当《原学》后来编入《国故论衡》时,章太炎就删除了这一观点。可见,章太炎最终还是认为自然环境对学术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学影响下,章太炎认为自然环境对民族文化精神有重要影响。在1903年《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针对康有为《论印度亡国书》中所述印度“文学工艺远过中国”的相关论点,章太炎从地理环境论予以反驳:“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著故。此社会学家所证明,势无可遁者也。……夫欲自强其国种,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2]52通过运用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认为印度地处热带,其地理环境促使他们精神慵懒,而中国的自然环境与印度不同,民族精神也因此而不同,绝不会像印度那样。在当时学界,这种社会学原理的运用并非是章太炎一人的偏执,在其他学者的文章中也可以找到类似观念的表述。如汤调鼎《论中国当兴地理教育》中引用社会学说中“所处之地,湿气既多,勇气亦随之消失”的理念来论述环境与文化精神之关系[15]。
如果仅仅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对社会文化的影响,那与《汉书·地理志》中的“风俗”论以及《隋书·文学传论》中的“南北词人”论也差别不大,晚清社会学给章太炎的文学风格论更大的助力在于,由此内转发掘了体气体格与文学风格的内在关系。在《文学略说》中,章太炎通过比较周秦以来文章之盛衰,提出了文章风格与“体气”相关的联想,并从人类体格进化的视角对这一联想进行了阐释。如在总结两汉赋文写作风格时,章太炎认为西汉之赋与东汉之赋风格差异明显,“《七发》气势浩汗,无堆垛之迹,拟作者《七启》《七命》,即大有径庭。相如、子云之赋,往往用同偏旁数字堆垛以成一句,然堆垛而不觉其重。何也?有气行乎其间,自然骨力开张也。降及东汉,气骨即有不逮。然《两都》《两京》,以及《三都》,犹粗具规模,后此则无能为之者矣”[5]1042。而造成风格差异的原因,章氏以为大抵不在情理,而在体格与体气。“此类文字不关情之深理之邃。以余度之,殆与体气有关。汉人之强健,恐什佰于今人,故其词气之盛,亦非后世所及。”[5]1042“体气”说在中国传统文论中也有相关叙述,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有“孔融体气高妙”之说,但其所谓“体气”指向根基在于音律,而章太炎所谓“体气”的指向根基则明显在于“体格”之强健。以体格论精神,正是晚清社会学的副产品。在甲午海战后的集体反思中,受进化论影响,人们对强身健体有了新的认识。1895年,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形神相资,志气相动”的观点,说:“顾今人或谓自火器盛行,懦夫执靶,其效如壮士惟均,此真无所识知之论也。不知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体气强健者不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杰之姿。”[16]在该文中,严复一方面以近代科学为依据,认为形神一体,故劳心者与劳力者一样,均需要强健的体格,另一方面以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为例,力证射御之教的重要性,并以孔、孟二人体格魁梧为释例,将体格、精神与智略关联起来。这种观念得到了其他学者的呼应。如梁启超《新民说》中说:“体魄者,与精神有切密之关系者也。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是以古之伟人,其能负荷艰巨、开拓世界者,类皆负绝人之异质,耐非常之艰苦。”[17]章太炎也是这一理念的认同者,他在论述汉朝文章气盛与体格的关系后,说明了二层理由:一是考古发现古人体格壮于今人。“今人发古墓,往往见古人尸骨大于今人,此一证也。武梁祠画像,其面貌虽不可细辨,然鼻准隆起,有如犹太、回回人,此又一证也。”[5]1042二是汉代尚武之风盛行,歌诗不道行军之苦。“汉世尚武之风未替,文人为将帅者,往往而有。又汉行征兵制,而其时歌谣,无道行军之苦者。唐代即不然,杜诗《兵车行》《石壕吏》之属可征也。由此可见唐人之体气,已不逮汉人,此又一证也。”[5]1043故而得出汉人体格与其文章之关系的结论:“以汉人坚强好勇,故发为文章,举重若轻,任意堆垛,而不见堆垛之迹,此真古今人不相及矣。”[5]1043此外,章太炎还曾牵引“体气”与道德的关系以佐证其与文学的关系,如“道德非尽出于礼,亦生于情。情即有关于体气。体气强,则情重,德行则厚;体气弱,情亦薄,德行亦衰”[5]1043,并举《吕氏春秋》和《史记》中关于孔子为勇力之辈的例证。这与严复《原强》中所述可谓如出一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晚清社会学说的辐射与延伸。彭春凌在《进化之调律:斯宾塞与清末的种群竞争论述》一文中认为:“严复、章太炎正面译介赫胥黎、斯宾塞著作之后,趋新学界才逐渐接受由具有哲学性质的进化论所缀合的一整套对人体生理以及生物历史的新认知。”[18]也正是这套从进化论哲学到人体生理、生物历史的认知,使章太炎将人类的自然环境、精神、体格与文学风格联系在一起。
所以说,与传统文论中的相关论述相比,章太炎的文学风格论终究是不一样了。因为时代的不同和学术体系的差异,现代科学观念已经开始渗透到了文学研究领域。
在晚清民初文学批评的革新过程中,采合中西是一种被广泛认同的途径。即使西化程度较高的梁启超,也在《饮冰室诗话》中说过:“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6]46章太炎的文论建构,诚然是以中国的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子学为基础[19],并与扬州学派的文论有一脉相承之处,其文章写作也多是古奥的旧形式,但晚清社会学热潮所带来的学术精神和学术视野还是渗透到了他的文学研究之中,在文学溯源研究、论体文审美研究以及文学风格研究方面引导章太炎在传统文论基础上开辟了新方向,这具有一定的现代学术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