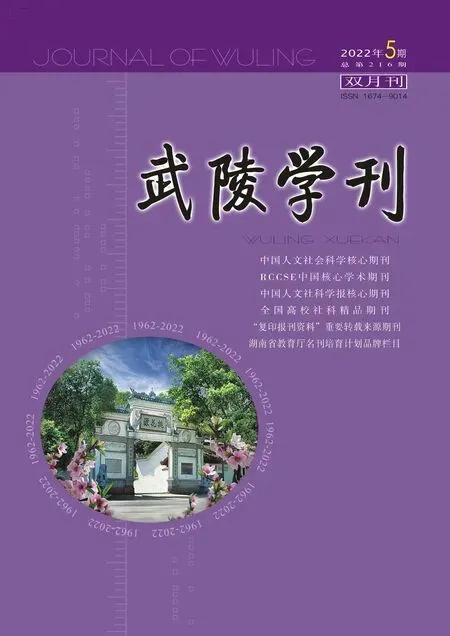《庄子》论“命”探微
黄圣平
(上海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444)
“命”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说文解字·口部》曰:“命:使也。从口从令。”[1]32“命”与“令”相关,是后者的派生字,具有“命令”“教令”“指令”“使命”等义。查《庄子》一书,涉及“命”的用例共有八十余处①,其中除了“命令”“寿命”“命名”“司命”“教命”“任命”等日常意义上的用例外,主要是在“天命”“生命”“性命”和“遇命”等哲学意义上的用例,且以“遇命”为主,兼及“命”的其他含义,围绕“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从人生困境出发,主张“知命”与“安命”,从“知命”“安命”到“逍遥”与“超越”,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思想逻辑,而作为其中枢纽与关键的是从受“命”主体向授“命”主体的视域变换,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己之精神超越。分析研究《庄子》之由体“道”而“安命”,并进而“逍遥”与“超越”的运思理路,目的在于理解以“道”观“命”中的视域变换及其内在含义,从而把握《庄子》“安命”论区别于一般前定论和宿命论思想的超越性理论特征,在“安命”与“逍遥”思想的对比中体认《庄子》逍遥思想的进路与特征。
一、“命”的含义与特征
庄子人生哲学的出发点在于解决人生困境,相应地其“命”论思想的出发点也在于反思人生困境,故“命”之初始,其适用范围与所指对象一般是具有困境性的人生之所“遇”[2]。《大宗师》篇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3]286这里的“命”是指“霖雨十日”“子桑殆病矣”的病殆困境。在《德充符》篇中,“鲁有兀者王骀”[3]187,“申徒嘉者,兀者也”[3]196,“鲁有兀者叔山无趾,踵见仲尼”[3]202,“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3]206,“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灵公说之”[3]216,此篇中的异人均为“安命”者,而且他们所安之“命”均为身形上的残疾与骇恶之体状。另,“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3]679“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3]595其所言者均为圣人所处“匡陈”之地的外困险境。当身处顺境、志得意满时,人之目的、力量和意志在对象世界中得以流畅展现,获得的是人之存在的证实和肯定,是很难有限制性与无奈性的人生感叹的。惟当身处困境时,外在处境的限制和强制性力量才得以凸显,人的存在和力量也被压制和否定,则易起命运之叹,此乃人之常情常理。同样,在面对困厄、人力的无可奈何与无从逃避时,人之所思总会在运命的追因和不公的时遇中兴起激愤与哀怨之情。《大宗师》中子桑子“若歌若哭”,“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3]286;《德充符》中兀者申徒嘉“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3]199;《达生》篇中“有孙休者,踵门而诧子扁庆子曰:‘休居乡不见谓不修,临难不见谓不勇;然而田原不遇岁,事君不遇世,宾于乡里,逐于州部,则胡罪乎天哉?休恶遇此命也?’”[3]663《徐无鬼》篇中子綦面对其子梱“将与国君同食以终其身”的命运,“索然出涕曰:‘吾子何以至于是极也!’”[3]857《则阳》篇中老聃弟子柏矩“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号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灾,子独先离之……”[3]901等等,都呈现了在困境初始时人之不知命、不安命的激荡心态。此亦人心中的常情常理之一端也。
从不知命、不安命走向知命、安命,其关节点在于对此外在之命的含义与特性的体认。孔子言“唯天为大”[4]83,“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4]177,又言“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4]157,又子夏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4]125之语,在孔圣人处,所谓“命”与“天”相连,“天命”的涵义较重,但也较多地指谓命运、命数,是人力所无可奈何的一种必然性存在。墨子“非命”,曰:“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5]71又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5]77其所“非”之“命”也主要是指一种与人力相对的,决定着人之贫富、众寡、治乱、寿夭等诸种生命情态的外在力量。张岱年先生指出:“孔子所谓命,是何意谓?大致说来,可以说命是人力所无可奈何者。……总而言之,可以说命是环境对于人为的裁断。”[6]309又说:“道家讲命,比儒家更甚。儒家虽讲命,而仍不废人事,实以尽人事为基本;道家则不谈人事,专言天命。道家所谓命,也是人力所不能及,人力所不可奈何的意思。”[6]307刘笑敢先生认为:“我们可以将庄子所讲的‘命’理解为‘既定境遇’。这种‘既定境遇’只描述已经发生的、无可奈何的状况。”[7]179可见,与孔子、墨子之所言相类,《庄子》所谓“命”也主要是指一种外在性的强制力量及其对人之存在的限制。《养生主》曰: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3]124
“介”,郭象注曰“偏刖之名”[3]124;“刖”是把脚砍掉的意思,是古代的一种酷刑。“偏刖”,是指砍掉了一只脚。触犯法网而遭受刑罚,一般会被认为是人为原因(“其人与?”)造成的,但对这种人为原因的追问会引发对原因链接的无穷追溯,最终就会落在“天”等终极存在上(“天与?”)。以因偏刖而独足为“天生之”,庄子强调了它的外在必然性,而将它与“有与”即两足并存的状态相提并论,认为二者均是“天生之”,更凸显了人力所无从选择和改变的方面。“天也表示人所不能参与或者决定的事物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人所不能决定的,因此叫做天,……它就是造化本身。”[8]160遭受偏刖之刑与两足并存类同,都是“天生之”的结果,具有自然变化的意思。庄子说“知天之所为者,天而生也”[3]224,“道与之貌,天与之形”[3]221,“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3]241,“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3]260,可见“天”是一种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超越性力量,它决定人的各个方面,而对于天,以及由天而来的落于己身的任何事态及其变化,由于其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人只能接受和顺应,不能抗拒与改变。“天之生是使独也”,对于己之“独”的结果,只有承受、认同和顺应。
《庄子》所论“命”具有强制必然性,是从其与受“命”主体之间的关系来说的。对于受“命”主体来说,其所“受”之“命”,作为一种客观事实,它为己所“遇”,已然发生而落于己身,不可改易,也无从逃避。由此而言,“命”具有不可移易的必然性,《庄子》中所言之“不得已”“无奈何”“知其不可奈何”等,均含这一道理。显然,在此意义上的必然性,主要是一种外在的限制与强制性,是主体存在的被动性表征。由于这种限制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就主体心态来讲,无论他认可还是不认可,对其所“遇”之“命”的事实本身没有影响。“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也”[3]692,“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3]241“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3]596等,所言均是“命”的外在强制性和不可改易的必然性特征。显然,由于所“遇”之“命”具有的这种必然性与因果和逻辑无关,也不具备重复实现的规律性,所以它只是一种具有盲目性的、超越于人力之外和之上的强制性力量。作为规律、因果或逻辑上的必然性,可以为人力所认知和把握,进而可以利用和闪避,而《庄子》所言之“命”,却是无法加以认知和把握的。“命”的这种外在强制性和必然性,由于它不接受因果、规律和逻辑的范囿,不能重复发生和实现出来,所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又是一种偶然性。
《庄子》中的“命”具有随机偶然性,指的是所“遇”之“命”具有随机性。何以是此“遇”而非彼“遇”落于己身,因无法给出理由来说明,故只好付诸于“命”。《德充符》有言“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3]199,置身于神箭手后羿的射程范围之内,一般说来是一定要中箭的。然而“游于羿之彀中”,居然不被百发百中的后羿射中,这是无法解释的意外,也是无法预测的偶然。《外物》篇中说“鱼不畏网而畏鹈鹕”[3]934,盖因“网”是固定不移的,所以能预先加以回避,而“鹈鹕”是突然而至的,因此是猝不及防的。申徒嘉丧其足,但是他对子产说“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是说他把丧足的事实作为偶然的“命”之所“遇”加以承受了。子桑子困病欲殆,他或歌或哭:“父邪!母邪!天乎!人乎!”但是思乎至此极者而不得,而其所归因之“命也夫”,亦即是将其归因于所“遇”之“命”的偶然性,故不可究责,也难以进一步追问。又如,《外物》篇载:“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策,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3]934这里以寓言的形式指出了人之知力的界限和不及。盖人生在世,其外在之境遇中总是难免各种无法预料的遭际。时世芜杂,人事变换,个体的人生遭际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它们为人之知力所不能事先预测,也难以主动回避,故纵使有至知之神,又何能抵挡得了万人之谋?总之,从偶然性角度看,庄子所谓个体之“命”,就是由无限多的“遇”之随机性所构成的无序的生命轨迹与人生曲线;从这些偶然性的人生际遇为己所“遇”,从而不可改易,也无从逃避的角度说,它们都是个体“命”运的必然。但是为何“遇”此“命”而非彼“命”,实在给不出一个有力的解释而只好归之于随机性和偶然性。可以说,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庄子》之“命”中是内在统一的,它们不过是同一个事实在不同视域下的不同呈现而已,不需要将二者对立起来。
《庄子》所论之“命”具有无为自然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统一于自然性。从“命”为个体所“遇”而“受”之的角度看,它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和必然性;而从“命”之来源而“授”予之的角度看,无论“遇命”“性命”还是“生命”,其所“授”最终来源于自然性之“天”,或是总体性的超越之“道”,它们都不具有意志性和人格性,其运行和流转也没有安排、计划与目的,而是随机的,是无为和自然的,并由此决定了个体所“遇”之“命”的偶然性和自然性特征。《德充符》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以正众生。”②松柏的“性命”“受命于地”,而“地”之授予“性命”于万物,本来无为无心,没有任何有意与偏私,故它“授”松柏以“冬夏青青”之“正”性,实乃自然为之,没有必然性而实具有偶然性,故谓之“独”。就松柏自身而言,它“接承”和“禀受”其作为松柏的“性命”,却是具有必然性的,它不能选择和逃避,也不能推脱和改变,而只能被动地“接收”和“承受”之。同理,尧舜之“性命”“受命于天”,唯“独”有其“正”,故“幸能正生,以正众生”,但是“天”的“命”具有自然性和偶然性,尧舜“受”之则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可见,即使在“性命”的禀赋上,自然性、偶然性和必然性也是合为一体的,是同一个事实本身。“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3]241,“死生为昼夜”[3]616,“死生终始将为昼夜”[3]714等,是说个体的“死生”之“命”犹如“昼夜”“夜旦之常”,是自然而然的,其来源则是“天也”。《至乐》篇言:“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3]612又言:“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夏秋冬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噭噭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3]615庄子妻死,他鼓盆而歌,是因为他看到了生死变化犹如四季变换,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王叔岷先生辑录《庄子》佚文,有“天既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自然”[9]两条,而《达生》篇中亦曰“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3]658,可见“天”“命”之“自然”义是庄子的深切体认。
在《庄子》中,“命”具有至上权威性。就字源而论,在甲骨文中“命”“令”同源,后者的基本字形为,其意象为“”+“”。对于“”,学界较有共识,即“人”,“古文象人跽形”[10]。《说文》曰:“跽,长跪也。从足,忌声。”[1]46可见其身姿中的恭承之意。“”之含义,争议颇多,罗振玉和孙海波说,即古“集”字,集众人而令之;林义光和高田忠周说,卩即“人”字。从口在人上,象口发号;李孝定说,象倒口篆文,乃由口传令;徐中舒说,象木铎形,为铎身,其下之短横为铃舌;古人振铎以发号令;丁佛言说,象屋宇形,朝庙受命者[11]105-106。尽管学者所解的具体含义或有不同,但是受“命”者居于下位而以跪姿恭承外在指令的基本含义是贯通一致的。也就是说,表示一个人以恭顺的姿态接受外来的指令,由此产生命令的含义,引申表示指示、使得、受人尊敬,再引申为官名,从而具有权威性。金文中再加“口”另造“命”,基本字形为,亦在强调开口发令,“在事为令,在言为命”[11],从而与“令”的其他含义区分开来,引申表示给予、指派。由于命令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和生命,亦由此产生命运和生命的含义[12]。在《庄子》中,外在的至高者乃“天”“道”等超越性的形上存在,将“命”的来源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使得“命”的权威性更为凸显。“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3]691,“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3]262,“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为父,而身犹爱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而身犹死之,而况其真乎”[3]241,“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3]155等,都是以“天”(“阴阳”“道”)之“命”与“君王”“父母”之“命”相对而论,以凸显前者的至上权威性,并因此彰显了生之“安命”的绝对性。“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3]155,“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3]630,所言均是指由于“命”的至上权威性而要绝对“安命”。
在《庄子》中,“命”具有泛化全面性。“命”之所指主要是困境性的外在境遇,也可以推扩开来,适用于个体一身所“遇”之任何性质的内外境遇、性命,以至于生命本身,从而使得《庄子》之“命”因为泛化式的理解而具有了全面性特征。《德充符》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其中“死生、存亡”和“饥渴”属于生命问题,“穷达、贫富”,“毁誉、寒暑”属于外在境遇问题,而“贤与不肖”则属于内在性命问题。可见,在《庄子》中,“命”所包含的不只是外在境遇,也包含内在的性命和生命。另外,在“命行”“事变”中不仅包含“死、亡、穷、贫、不肖、毁”,也包含“生、存、达、富、贤、誉”,以及“饥渴、寒暑”,所以“命”的性质不只是消极否定及对人之存在和努力构成限制、制约的方面,也可以是积极肯定及对人之存在和努力构成助益、实现的方面。至于“饥渴、寒暑”,则是中性的,它们之为“命行”“事变”,原因在于它们为个体之所“遇”。《至乐》也曰:“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3]620小口袋不能装进大物件,短汲绳不能提取深井水,这都是由其先天条件决定的,而且,这种先天的限制,后天也不能随意改变,故曰:“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夫不可损益。”此处之“命”受之于“天”,实由其先天秉赋所铸成,故为“天命”,亦为“性命”。《人间世》中“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其中的“命”就既为“性命”,亦为“天命”。总之,依照《庄子》,个体一身的任何所“遇”都可以用“命”来涵括,从而成为其“命”所指的对象与内容。徐复观先生说:“庄子之所谓命,乃与他所说的德,所说的性,属于同一范围的东西,即是把德在具体化中所显露出来的‘事之变’,即是把各种人生中人事中的不同现象,如寿夭贫富等,称之为命;命即是德在实现历程中对于某人某物所分得的限度;这种限度称之为命,在庄子乃说明这是命令而应当服从,不可改易的意思。”[13]要之,“命”的含义主要指一种外在境遇,但是也可以扩充开来而包含人生、人事中的所有内容。
二、以“道”观“命”中的视域变换
如上所论,所谓“命”,就是人之“知不能规乎其始”,却又时刻左右着人的那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的潜在力量。在庄子看来,人生中的一切落于己身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都可归之为“命”,而从“命”的角度思考和把握之,就是“知命”。显然,这是一种对“命”的泛化式认识。进而,在对“命”之来源的追问中,“天”(“道”)作为造物者,其运行是自然无为的,也是变易不息的。由此,“天命”也具有了随时变易的特征。《山木》篇曰:
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仲尼恐其广己而造大也,爱己而造哀也,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谁乎?”回曰:“敢问无受天损易。”仲尼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谓无受人益难?”仲尼曰:“始用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窃。吾若取之,何哉!……”“何谓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谓天与人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3]691
仲尼困于陈蔡,其所“遇”之“命”具有外在强制性特征(“吾命其在外者也”)。孔子称他在陈蔡的困厄为“天损”,表明这种困厄(“损”“穷桎不行”)的来源是无为自然(“天”)的,其运行宛如饥渴寒暑一般,是“天地之行也,运物之泄也”,所以不可改变,也不可抗拒,只能因顺,故曰“与之偕逝之谓也”。进一步,对于这种所“遇”的外在之物的变化,《庄子》强调了其中随时变易的绝对性,所谓“无始而非卒”“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就是说由于变易的绝对性,万物每时每刻都处在变易之中(“始”即是“卒”),而且这种变易是连绵不绝的,所以也无法知道它们接下来是什么样子。因为万物不可知其始,也不可知其终,而且又是无时不为始,亦无时不为终(“卒”),故唯有“正而待之而已”,“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这是针对“天损”性质的困厄之“命”。而“人益”性质的“始用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等“物之所利”,由于它们是外来性质的,是“非己”性的“吾命其在外者”,也具有外在强制性,所以对待它们也只有采取因顺的态度,非“盗”非“窃”,“取之”而已矣。无论“天损”或是“人益”,都是自然的,因此可以说“有人(益),天也;有天(损),亦天也”。对于任何外在性的所“遇”之“天”(“命”),人主体上都是无能为力,无法改变,不可抗拒的,因此说“人之不能有天,性也”,“为人臣者,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安命”是庄子对待“天命”的基本态度,因为“不敢去之”,所以只能“安”而顺之。孔子身处困厄而歌猋氏之风,所呈现的就是“安命”者不为外境所动的超然心态。
因为“命”具有外在性、强制性和必然性特征,庄子的“命”论思想有朝前定论和宿命论方向发展的可能。如《徐无鬼》篇中言九方歅相子綦之八子,言梱也为祥,而其后梱亦终为盗人所刖而鬻之,适当渠公之街,然终身食肉而终,与九方歅所相正同。又,《则阳》中记载:“夫灵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数仞,得石椁焉,洗而视之,有铭焉,曰:‘不冯其子,灵公夺而里之。’”③可见灵公葬时所“遇”之“命”也是早勒刻于石椁之铭,其中预先给定的色彩是很强烈的。因为命运的前定化和宿命化,容易带来情感上的悲抑与绝望,如子綦之泣梱。但是,在《庄子》中,这一前定或宿命论色彩被自然变易之道有力地消解掉了。盖根据自然之道,任何境遇均无时不变,无处不变,故终究没有任何“前定”“宿命”存在的余地。“化其万物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天有历数,地有人据,吾恶乎求之?莫知其所终,若之何其无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3]958何为始,何为终,一切均在未定之变易中,不可前知亦不可后定,唯有正而待之,“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庄子》中的前定论乃至宿命论思想倾向,被自然之道化解和消弭了。
《大宗师》曰: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3]275
死生困境是困境之巨,死生之来去,均为己力之所无奈何,所谓“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孟孙才“以善处丧盖鲁国”,原因在于他简择生死之异而不得,从而能以屯然无知之心超越死生、先后之别,故“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孟孙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明白生死之道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是变易之道,变易之道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它涵括死生、先后,不可预知,无从把握,只能随顺、因任,并安顿己心于其中,所谓“若化为物,以待其不知之化已乎”,此即“知命”“安命”。显然,尽管变易不可预知,但是它所具有的绝对性决定了这种变易之“命”无法给定化,更不可能宿命化,因为任何定命和宿命都是板结和凝滞的,都是经不住绝对化的变易之道的荡涤与冲击的,由此,面对命运,人是不可避免、无从逃开的。但是《庄子》中少有如俄狄浦斯般,在面对杀父娶母之宿命时刺瞎双眼的惨烈与绝望,而是在与化俱往中的因顺与平静。“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反正化与不化、化为何物,均属于未知之数,且自身不可预知,不可改变,故投身大化之中的安命之心是安静的,是随运任化、与化为一的,这样,面对悲剧处境的己心,无论惨烈或绝望,它们也应在大化流行中与化偕逝,又哪里值得执滞与固守,从而沉沦其中,为其囿限,坚执而不化呢?在与化为一的生死流变中,“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④,虽有身体上的死生之变,却没有心神上的真正损、丧,原因在于己心对于形体上的任何先后、变化均能“相与吾之耳”,也就是说己心可视己身在形体上的一切变化如梦境,而予之以己心作为超越之心贯而统摄。盖无论化为鸟而厉乎天,或是梦为鱼而没于渊,鸟之为鸟有其鸟之“吾”,鱼之为鱼也有其鱼之“吾”,而“言者乎,觉者乎,梦者乎”,亦各自有其作为言者、觉者和梦者之“吾”存乎其中。由此,形体所化之各物之一“吾”,又是同一个己心之大“吾”,在与化流变中给诸形、诸身和诸“吾”以形式上的统摄。这当然是一种因为“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而来的超越的、大我的精神境界[14]。在此境界中,其适其笑均不待安排,一切均是自然的化境。
关于造物者,及其对人之“命”的决定作用,《庄子》中曾多处言及: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3]244
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3]262
成玄英疏曰:“大块,自然也。”[3]243又言:“大块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称也。”[3]46“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其乃“善吾生者”,亦“乃所以善吾死也”。所谓万物之形、生、老、死,均是自然、造化流行于天地之间的命行、事变,但是若下落于己身,则成为一己之“命”运所在,故若从个体之“命”而论,所谓“造物者”亦即是造“命”者。《大宗师》句“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3]268,也是将个体之形体的变化纳入“天地之一气”的大化流行之中,而其来源与动力则在于自然性的造物者。个体与造物者合一,“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此即所谓“藏天下于天下”,其实质是指通过己心与造物者合一,“安命”者能实现一己视域的转换。换句话说,他不再是作为受“命”者来被动接受各种“命行、事变”的外落和下落,而是能从造物者的超越性视域审视大化流行中天地万物之诸种形体和生死的不绝流转,并超然于所有的“命行、事变”之上。这种视域的转换,其实就是《秋水》篇中所谓“以道观之”:
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3]585
《秋水》篇还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3]577《天地》篇亦曰:“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之应备。”[3]404在《庄子》中,“道”是造物者,亦是造“命”者。《大宗师》曰:“夫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生天生地。”[3]246又曰:“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3]252《知北游》亦曰:“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3]741这是说有形物中的粗大者从有形物中的精微者中产生,万物彼此都有生成关系,但最终是来自于无形之道,道生天生地,是一个永不间断的变化过程,故《大宗师》中又将道称为“造化者”[3]262“造物者”[3]258。《渔父》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3]1035《知北游》曰:“运量万物而不匮,……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3]743可见在生成万物之后,道作为支配者同时还存在于万物之中,是万物的根据,决定着万物的命运。在以“道”观“物”的视域下,“道无终始,物有死生”,它兼怀万物,而无所畛域,是“无穷”亦“无方”的总体性存在。此总体之“道”同时也是自然之道和变易之道,故“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万物无动不变,“若骤若驰”,其或死或生,均“不恃其成”,而是自然性的自生亦自死的过程(“夫固将自化”)。进一步,在物、物关系问题上,在“以道观之”的视域下,“何贵何贱”“何少何多”,“万物一齐,孰短孰长”?所谓贵贱、多少、长短等物、物之间的任何分别,均在“万物一齐”的均平化中泯合为一,是谓“反衍”,是谓“谢施”⑤,其实质在于“心”“道”合一中的、由“小我”“私我”之心向超越性的“大我”之“心”的转变。因为“以道观之”的缘故,心与“道”一,所以“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其“心”既然“无私德”“无私福”“无所畛域”,其实就是对“有私德”“有私福”“有所畛域”之“私我”“小我”之“心”的超越。与超越性的“大我”之心相对,“私我”“小我”之“心”者“与道大蹇”“与道参差”,他们“拘其志”而“一而行”,是对个我性行为与志欲的坚执和拘滞,从而无法与“道”合一,无法从己身的困境中摆脱出来。这样的“私我”“小我”之“心”,当然不可能“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不可能“兼怀万物,其孰承翼?是谓无方”⑥,也就不可能在心、物关系中获得对物我、彼此间更新式的、共振性的理解和实践,也就是说,只有付诸具有超越性的“大我”之心的至人或曰圣人才能与道合一。
进一步,若将此以“道”观“物”的视域应用于“命”上,也就是说以“道”观“命”的话,则可获得对一己之形躯、死生,还有得丧、祸福之超越性的理解。《庄子·外篇·田子方》说:
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3]714
“已为道者解乎此”,故“此”实为以“道”观“命”的超越性视域。成玄英疏曰:“疾,患也。易,移也。食草之兽,不患移易薮泽;水生之虫,不患移易池沼;但有草有水,则不失大常,从东从西,盖小变耳。亦犹人处于大道之中,随变任化,未始非我,此则不失大常,生死之变,盖亦小耳。”[3]715显然,这是身、心分途,而以四支百体为尘垢,形躯、得丧、祸福上的任何变化均不足以患心,盖心合大道,而大道乃“大常”所在,“万物之所一也”,故“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而“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也”。之所以“安命”,不只是因为所“受”之“命”的外在强制性使然,而是因为“道”之“授”予己身之“命”在大化流行中的自然。盖“命”之为“命”,正如其字源之所示,有“授”命与“受”命之两端。理解己“命”,若仅仅从一己之“受”命的视域观之,以“命”之外在强制的必然性与随机的偶然性为依据,则“安命”者心中总难避免逆来顺受式的冷漠、迟钝与麻木,从而也就难以避免阿Q式精神胜利法与自我欺瞒、混世主义、鸵鸟哲学的指责[15]。但是,若从“授”命者的角度,尤其是在道生万物的视域下观之,以个体之“命”在所谓“事之变,命之行也”中的大化流行及其自然流转为依据,则“安命”者心中自然会渗透着对“道”“命”透彻性“觉解”之后的超然与恬淡。《庄子·外篇·至乐》说: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恶之。支离叔曰:“子恶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恶!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昼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3]616
成玄英疏曰:“支离,谓支体离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犹骨稽也,谓骨稽挺特,以遗忘智也。”[3]616《大宗师》云“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可见“支离伯”和“滑介叔”正是“同于大通”的“坐忘”之人。又,《刻意》曰:“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⑦“黄帝之所休”的“冥伯之丘”与“昆仑之虚”,实即与“道德”(“天地”)合一的窈冥与超越之域,惟此方能“平易恬淡”而无所忧患,方能“柳(瘤)生其左肘”而曰“亡,予何恶”,而没有任何因为己“命”之所“遇”引发心境上的波荡,此谓“德全而神不亏”。能够如此,当然是以“道”观“命”带来的心境上的超越。《大宗师》曰: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俄而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曰:“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项,句赘指天。”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跰跹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恶之乎?”曰:“亡,予何恶!……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悬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3]260
这里所说的仍然是心、形分途。在心、形分途的运思模式下,心之超越和形之淡漠双维并立,相因互成。《德充符》中兀者申徒嘉斥责子产曰:“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3]199所谓“形骸之内”是人之心灵,人之所以为人者,而“形骸之外”是形体以及与形体有关的一切,它们属于命运,是人之所无能为力的领域[8]64。《德充符》又曰“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3]216,其所“长”之“德”即是心与“道”一,以及由此而来的超越心境,故“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知生死存亡之一体”,故能“阴阳之气有沴,其心闲而无事”,亦能“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至于形体以及属于形体的一切,既然属于命运,就应该被“忘”掉,也就是应该从心灵之域驱逐出去,所谓“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3]212,如此才可以把自己的心灵从形体与有形世界中解放出来,进而臻于与“道”合一的无形之域。能如此者,谓之“悬解”,喻心灵从被束缚的倒悬状态中解脱出来;不能如此者,则是心灵为形体及有形的东西所束缚,谓“物有结之”。世俗之心为形体所支配,心随形动,“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3]56,从这种小我的、有“结”之心中超脱出来,“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16]145,从而与造物为一,则能以“道”观“命”。此时,其心闲而无事,丧足若遗土,视己之形体变化无所相关,故能恬淡寂漠,安时处顺,而一无所恶也。要之,在以“道”观“命”的视域之下,己形之“拘拘”已经摆脱了它们对人之存在的否定性、负面性的价值特征,一转而为自然造化。由此,“命”之为“命”,就不再是人生困境式的外在压迫和异己性存在,而是因为无所非“命”,从而无所非“吾”的形式统一性的本己性存在;也不再是人之“不知其所始”,亦“不知其所终”,从而具有不可知不可变特征的盲目性力量,而是既来源于、亦回归于“道”“天”等造物者,从而既是造物之所“授”,亦为己身之所“受”的产物,其中自有其“大义之方”和“万物之理”,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人能知其所始亦能知其所终,并能在与化流行中随化而变的可知可变性存在。“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对于大化之自然流行,人既然无从胜之,当然只有淡然受之。恬静、淡漠与安任、因顺,是庄子对待一己之形体变化的基本态度,它建立在“一气流行”的自然变易之道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暗含着庄子对宇宙终极存在之真实性和价值性的信赖与认同。从《人间世》《大宗师》等篇中有关“心斋”“坐忘”“见独”等体道方法和修持功夫的思想看,庄子对“道”之作为形上存在的超越性和价值性是有真实和真切的体认的。
三、“安命”与“逍遥”的对比
如上所论,在《庄子》中,“命”的基本含义是一切外在境遇对个人存在的限制,相应地,“命”具有异己强制性、随机偶然性、自然变易性、外在权威性、不可认知性和泛化全面性等诸种特质。所谓“安命”,就是“安”于“命”对己身的限制,并肯认和接受之。换句话说,所谓“安命”,实质上是站在“受命”主体的维度,通过对下落于己身之“命”的“知之”和“安之”,达到对落于己之任何命运的接受和肯认。“安命”就是心命合一,心随着命运波荡而波荡。但是,在对“命”之来源和根据的追问中,庄子将一己之“命”与超越性的“天”“道”结合起来,进而在以“道”观“命”的超越视域与精神境界中对己身之“命”有了新的觉解和把握,表明庄子从“安命”走向“逍遥”的枢机在于一己体“道”而来的视域和心灵上的根本性转换,并体现在对己命关系、己世关系、己物关系和己身关系的思考。由此,“逍遥”若与“安命”对比,则它实质上是站在“授命”主体的维度,通过在己“命”关系上的视域变换和精神超越,实现对己“命”之限制性及相应拘囿困境的突破与超越。因而“安命”与“逍遥”的对比,是把握庄子逍遥思想的重要进路,有助于理解庄子逍遥观的诸多特质。
其一,异己强制性与内在本己性。“安命”首先是安于己“命”之异己强制性。这种由“命”而来的强制无可逃避,具有强烈的外在压迫性和异己性特征。与此不同的是,“逍遥”中任何存在、状态、过程等都是内在化和本己化的,具有内在本己性特征。因为“授命”者是“造物者”,它造物的过程是大化流行;大化流行是整体性的存在,或是世界作为整体性的存在本身。在以“道”观“命”的视域下,人心与造物者合一,与大化流行合一。在“授命”主体的维度,万物之间均可以平等而视,均可以作为流变的部分而纳入到整体领域之中,成为其内在化和本己化的组成要素,从而使外在压迫性和异己性的己物和己命关系一转成为超越视域下本己内在性的浑然一体和相入自得。《德充符》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3]190肝胆相异相抵,原因在于“自其异者视之”的个我化立场,而“万物皆一也”中的浑然境界则是“自其同者视之”之整体化视域的结果。“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3]79,“官天地,府万物”[3]193,“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豪为小,待之成体”[3]735,说的是无论天地六合之大,抑或万物秋毫之细,它们都内在于“造物者”的本根性作用之下,是大化流行中的部分性存在。总之,在超越性的逍遥境界中,天地万物以及任何己身之所“遇”,都是作为内在本己性存在被含纳于其中的。
其二,随机偶然性与客观普遍性。“安命”需要“安”于“命”之随机偶然性。《庄子》之“命”不具备逻辑性和规律性,从而不可重复,由此就无法对此进行普遍化和客观化的分析和把握。但是,与“命”之随机偶然性相反,在对“天”“道”的体认中,“天”“道”所具有的超越性特质同时也成为“授命”者之浑然境界的固有特质,而这些特质却是普遍的,具有理性化的客观与必然性质。《天道》曰:“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3]457《刻意》曰:“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焉)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⑦对于“帝王圣人休焉”中的“道德之质”,《知北游》称其为“狶韦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汤武之室”[3]765,《大宗师》更是以夸张句式推崇之:“狶韦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戏得之,以袭气母;……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3]247可见,先古帝王圣人具有同一的、共通的超越特质。这些特质,以“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道德之质”为核心,且具有客观普遍性。
其三,自然变易性与超越“不化”性。在《庄子》中,“安命”就是“安”于己“命”之自然随机性和无穷变易性,否弃“命”之来源的人格化和宿命论、前定论。但是,追因“命”之来源,自然性的“天”“道”之超越性特征凸显了,并具有“不化”、不可变易的特征。在“逍遥”中,这种“天”“道”的“不化”特征得到了人格化的呈现。《庄子》中的理想人格具有“不化”的重要特质:“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3]634“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3]765“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3]885可见“无所化”“内不化”“一不化”式的内在心境是体道者的重要特质。《德充符》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3]189其中“命物之化”,陈鼓应解释为“顺任事物的变化”[16]146,也就是“外化”“与物化”的意思,但是这需要建立在“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的基础上,而后者正是“止乎无所化”“内不化”“一不化者”的意思。在圣人处,虽死生之变,天地覆坠,而其心却“不得与之变”“亦将不与之遗”。《大宗师》曰:“杀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3]253体道者的“逍遥”(“撄宁”)境界具有“不生不死”的超越性特质。
其四,外在权威性与自在逍遥性。站在“受命”的角度,所“安”之“命”来源于超越性的天、道,天、道具有超越于父母、君王之上的权威性,它们所“授”之“命”具有绝对性。因此,对于“受命”主体而言,《庄子》之“命”不仅具有外在强制性,而且是由上而下之凌压式的绝对命令。与此不同,在“逍遥”中,因为“授命”主体与“天”“道”合一的缘故,《庄子》中的理想人格超然凌驾于万物之上、“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3]668,不受任何外物的限制、制约和凌压,具有与众不同的自在逍遥性特质。《逍遥游》曰:“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3]17“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3]28《齐物论》也曰:“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3]96《大宗师》曰:“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3]264“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途。”[3]279这些论述中的“乘”“御”“骑”表明了“逍遥”者不受万物制约和压制,而凌驾和超然乎任何外物之上的自在形姿;“登天游雾,挠挑无极”“彼且恶乎待哉”“游乎四海之外”“以游无穷者”等,则是以形象化的方式表达了“逍遥”之无待、无穷、无极的特质。
其五,落于己“身”与落于己“心”。《孟子·万章上》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17]揭示了“天”“命”共有的非目的、自然性特征,其中“命”的“莫之致而至者”,即是此“命”的作用和影响之落实于己“身”。依据《庄子》,在“安命”状态下,任何落于己身之上的事实,无论它们具有或正面、或负面、或中性的价值,都可以被纳入到“命”之范囿,这即是“命”的泛化式全面性特征。庄子,作为动乱年代中失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18],他改变不了世界的任何外在部分和世界之落于己身的任何作用和影响,但是,作为一个超越化的哲人,他可以在一己的心灵领域完全地自作主宰、改变自身。在《庄子》的“心”之领域,也存在着一种泛化的全面性,但是与“安命”中的全面被动性不同,“心”的“逍遥”却是全面的主动性。《德充符》中兀者申徒嘉批判子产:“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3]199“形骸之外”是外在的功名爵位,“形骸之内”是内在的超然心境。外在的功名爵位是命运之域,外在于人身,同时将其作用和影响下落于人身之上;内在的超然心境是精神之域,内在于人心,能在自作主宰中将一切外来命运的作用和影响予以遗落和荡涤,故有“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的感慨。“逍遥”在本质上是境界之事,是心之事,而“形骸”与“身”则本质上属于命运之域。
其六,不可认知性与可知可变性。与儒、墨等论“命”不同,庄子之“命”具有不可知和不可改变的特征⑧。庄子之所以强调要“安命”,这与他对“命”的理解有关,他认为“命”具有自然性特征,从而随机偶然,不可预知,也不可改变⑨。但是,在“逍遥”中,以“心”之转化为枢纽,全面的被动性却转化为全面的主动性。在逍遥境界下,己“身”通过以“道”观“身”,更通过“坐忘”“心斋”“见独”的修养过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3]147的“气”化使得它不再是被动的命运之域,而是上通“天”“道”,成为“天”“道”的象征与图式[19]。要之,“身”“心”在工夫论维度的纯粹化和净化,“逍遥”不只是局限在纯粹的境界之域,而是由“游心”而“游形”,二者自然合一,进而由“内圣”而“外王”,由一己之转变带来整个世界的扭转和变易。在《庄子》外杂篇中,就论述了万物各有其“性命之情”的思想。就万物的存在以及物物关系而言,“性命之情”是常态化和稳定的,也是平衡和协调的。这样,在自然状态下的己身、己物、己世和己命关系,就都是可以预知和把握的。在《庄子》中,万物的“性命之情”始源于“天”“道”,它们的失落导致了现实世界的动荡,也带来了个体之己“命”的困局。体“道”圣王以无为之治在宥天下,引领万物复归于“至德之世”,由此可以消解群品、众庶之时“命”困局。
最后,关于由“安命”向“逍遥”的转变,《德充符》曰:
仲尼曰:“……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3]215
对于“才全”,孔子将其直接解读为“知命”与“安命”,并由“知命”“安命”进而“超越”与“逍遥”。至人“安”于所遇之任何人生境遇,无论其性质为何,均视之为“事之变”“命之行”,也就是将其自然化、变易化和命运化,“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这是“知命”。因为“知命”,知其不可知亦不可易,同时亦知其为大化流行的自然发显,所以“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从而不因命运的任何流转而干扰内心的虚静与恬淡,这就是“安命”。在“知命”“安命”的基础上,“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也就是使心安逸自得,与物通畅而不失怡悦,可见《庄子》的“命”论思想不只是停留于对时世与己身变迁的无动于衷,而是落于时事的实践而尽己成物。换句话说,在《庄子》的“命”论思想中确实存在着从“知命”“安命”向“超越”“逍遥”的转变与提升[7]182。这种“超越”和“逍遥”建立在“灵府”之超越性的德性与心境之上,其实质在于对“道”“天”等“造物者”的体认。因为体道的缘故,“才全”者以“道”观“命”,使落于己身之上的任何“事之变,命之行”,均是“造化”之流本身的自然性波荡,是“道”在当下的发显和流衍;不是外在强制性、否定性和限制性的命定存在,而是具有随时变易性特征的、无所不“命”从而亦无所不“吾”的自然性和肯定性的价值呈现。由此,方有“才全”者与外物、外境的“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才有“不形”之“德”中的“内保之而外不荡也”。总之,圣人由“安命”而体道,其体道之心的超越与逍遥并不仅限于“灵府”之“和豫”“通兑”,而是由“灵府”而下落在“身”“形”之上,也就是说进一步落实在“才全”者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中。这种“接时于心”“与物为春”的日常生活与行动,因为“平者,水停之盛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所以最终落实在圣王的无为式治世活动中。综上所述,《庄子》的“命”论思想重在强调以“道”观“命”的视域变换和超越精神,而“逍遥”与“安命”的对比,对于理解《庄子》的纵向的、立体性思想结构亦将不无助益[7]169-182。
注 释:
①查《庄子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篡处编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15-316页),录得“命”字共61条(但是其中没有录入涉及“司命”“性命”“大命”“小命”“寿命”等相关材料),读者可参考之。另外,应用“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网站的检索功能,查得《庄子》全书中涉及到“命”字的使用共50段落81处。
②王孝鱼点校,《阙误》引张君房本下有正字,据以补之,见郭庆藩著《庄子集释》第193-196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灵公夺而里之”之“里”,王孝鱼点校,赵谏议本作“埋”。参见郭庆藩《庄子集释》第909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④“人有形体的变化而没有心神的损伤,有躯体的转化而没有精神的死亡。”见陈鼓应著《庄子今注今译》第20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⑤成玄英疏曰:“反衍,谓反覆也。夫贵贱者,生乎妄执也。今以虚通之理照之,则贵者反贱,而贱者复贵。故谓之反衍也。又曰:谢,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为少,故施用代谢,无常定也。”参见郭庆藩著《庄子集释》第585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⑥成玄英疏曰:“怀,藏也。孰,谁也。言大圣慈悲,兼怀庶品,平往而已,终无偏爱,谁复有心拯赦而接承扶翼者也!”参见郭庆藩著庄子集释》第586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⑦依照王孝鱼校“《阙误》引张君房本‘休休焉’作‘休焉休’”,参见郭庆藩著《庄子集释》第538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⑧关于“命”之是否可以预知和能否改变的问题,可以参考陈宁著《中国古代命运观的现代诠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版)之第二章《命运观的形成与发展》中的相关分析。
⑨当然,一方面,这种“不可知不可变”是就己“命”之具体内容而言的,是指何以此“命”而非彼“命”之落于己身,何以身“遇”此“命”而非彼“命”等,这在内容上不可解释,也无法加以改造,只能接受和承负之。另一方面,如前所论,“安命”却需要对“命”之为“命”有其体认,要“知命”方可“安命”。但是,这是在“命”之为“命”的形式维度上来说的。这种形式和内容上的区别是需要予以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