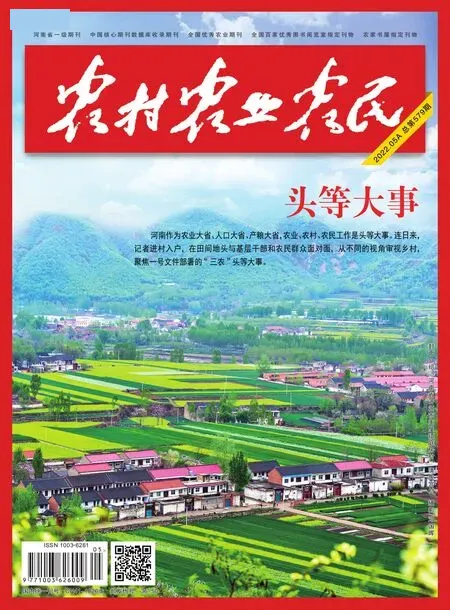打 场
曾庆棠
在我的学生时代,老家杨家寨生产队连年获得小麦丰收。一夜南风起,小麦满冲黄,社员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作为一个农家孩子,每当放学归来,我最喜欢跑到小麦田间,一边看着金灿灿的麦浪随风翻涌,一边吮吸着那成熟麦穗散发出的清甜如饴的气息,内心顿时充盈起一种无比的甘美。
那时候队里夏收夏种、加上养柞蚕等,是最繁忙的时节,社员们不舍昼夜地与时间赛跑。时令不等人,天气也不等人,一切都处在不可预测的变化之中。也许昨天还是朗日高照,可能明天就会大雨落下。麦子熟了,割了,还得尽快收捆,挑运到麦场上,将其晒干打出来。男女老少一齐忙得连轴转,人都累得黑瘦黑瘦的。特别是趁晴天打场,那简直是争分夺秒呢!
一吃过早饭,生产队队长就吆喝社员们到塆子东南侧的麦场上,打开一个又一个麦捆,均匀有致地平铺在经过碾压平整的场子上,让5月火辣辣的太阳曝晒着。赶到午饭将熟时分,青壮年男社员纷纷背着连笳来到麦场,井然有序地分为上下手,排成相对两列。我的力气小些,父亲便有意站在我的上手,即对面。
烈日的光辉闪耀在麦芒上,饱满的麦穗泛着金红色,沉静安详地躺在那儿,凝视着。恍惚间,它们熠熠生辉,金碧辉煌,欣喜的泉流在打场人的眸子里与心底间涌动……
随着队长一声“打呀”的话音落下,“噼啪、噼啪”的连笳打麦声倏然间在麦场的上空响起。打场也讲究配合,你一噼,我一啪,对方的连笳刚落下来,我这边的连笳恰好扬到空中,依此反复,绝不会交叉碰撞,以使每一啪连笳都有一定的留空时间。一时里,“噼啪、噼啪”的打场声汇在一起,浑然一体,节律齐整,响遏行云,真的是激动人心。这时,我似乎也不觉得累了,只感到我们村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乡间,热烈的打场情景则是天界飘落的一幅画笺。
打场时刻,风很少说话,说出的话都是热浪,一味张扬着夏阳的猛烈和热辣。打场的男社员们一个个汗流浃背,竟无一人停下来擦把汗的。
头场打罢,社员们当即翻过场,就把第一遍打下的麦粒收拢到一堆儿。这一道的麦子都是颗颗饱满的上等粮食,一般情况下是专门留下来扬净后交公粮用的。那时全国人民一家亲,社员们喊的口号是“向工人阶级学习”,好的粮食自然是要交公粮。
晌午觉后,不用招呼,大家都主动过来,开打复场。社员们被火燎燎的毒日头炙烤得汗流浃背的,但大家好像跟老天爷抗争似的,都默默地攒足劲儿,一气儿之下,很快就把打复场完成了。
傍晚时分,有扬场经验的生产队队长和万益哥便非常默契地干起了扬场的技术活儿。说是技术活,是因为扬场的确需要有力气、有经验,又要有些技巧。只见他们仰首望望天,脸往一边试试风,然后前腿微躬,后腿直蹬,一木锨扬出去,将麦子抛撒成一个弧形。动作持续起来,一个个的弧形连缀到一起,恰若一幅美丽的彩笔画图。这时候,双手把握大扫帚的万益哥利索地转过一边专职打溜儿,即把麦粒堆上的麦稳子等杂物用大扫帚前端有弹性的梢子轻轻扫出来。由于麦粒重,麦稳子轻,只要把握好力度,用扫帚梢来回拂动轻扫,就能将麦稳子等杂物及时分离开来。那边扬场的人不停地扬,这底下打溜儿的人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马虎,务必及时轻快地把麦堆上的麦稳子等杂物扫出来,以免被不时落下的麦粒覆盖住。细一看,这扬场和打溜儿正是一对好搭档,是一种相生相伴、相辅相成的统一体,缺一不可。原来,这庄稼活里也是有着一种哲学意味的。
夕阳慢慢西下,麦场上的麦堆渐渐隆起,金色的晚霞映照在生产队队长和万益哥两个人那有些黑黝黝的脸庞上,有一种敦实的、自信的光感,与麦场上的景物特别匹配。麦堆随晚风散发出一缕缕土性的香味儿,也弥散着一种丰收的喜气和甜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