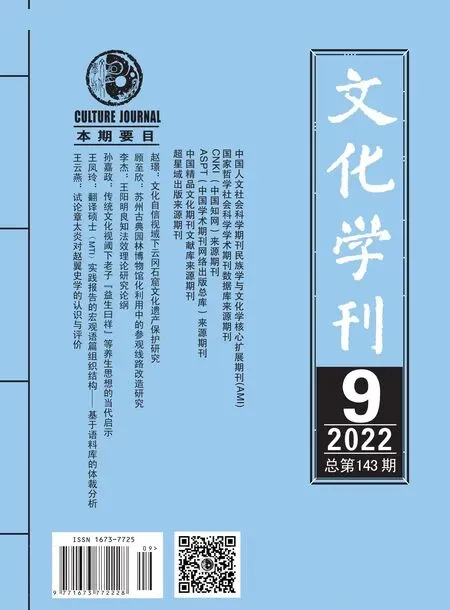试论章太炎对赵翼史学的认识与评价
王云燕
在清末民初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于乾嘉史学谱系中声名不显的赵翼获得新的关注,一时间其代表作《廿二史札记》广为流传,引起诸多学人重视。总体看来,民国学人对待赵翼史学的态度主要呈现两种取向:一派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家引入新学理,高度颂扬其进步性;另一派以章太炎为代表,承袭乾嘉汉学家的路径,继续以“经师”的眼光审视之,带有贬低意味。两者形成鲜明反差。关于梁启超对赵翼史学的认知,笔者已有专文探讨[1],现就章太炎对赵翼史学的评判略作阐述。
一、章太炎对赵翼史学价值的否定
20世纪初年,在史学上能与梁启超比肩而立者,大概只有章太炎(1869—1936)一人。[2]章太炎虽不是史学名家,但作为学术通人,史学在其学术研究中仍占有重要一席。朱希祖称:“先师学术,虽极广博,然史学实占其大部分,不特史之本身,即经学、文学,亦包括史学之内,所撰文章,亦多以史为根柢也。”[3]作为清代朴学的殿军,章太炎经学功底深厚,对清代学者的治学理路、优缺点了如指掌,被称作20世纪国内对清代学术史进行系统总结的第一人。[4]大约在梁启超关注赵翼的同时,章氏也开始注意到他。
章太炎最早一次提及赵翼史学是在20世纪初年撰写的《中国通史略例》一文中。该文系统阐述了关于新编中国通史的设想和主张,“必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5]335是他倡导的作史要则之一,他强调经史的互通性,认为治经为治史之基础,必要的经学素养是成就良史的重要前提,并借助以往史籍之得失来验证此说:
魏、晋以来,神话绝少,律历、五行,特沿袭旧名,不欲变革,其义则既与迁、固绝异。然上比前哲,精采黯黕,其高下相距则远……后世经说,古义既失其真,凡百典常,莫知所始,徒欲屏绝神话,而无新理以敹彻之。宜矣!其肤末茸陋也。要其素知经术者,则作史为犹愈。允南《古史》,昔传过于子长,今不可见。颜、孔《隋书》,亦迁、固以后之惇史。君卿《通典》,事核辞练,绝异于贵与之伧陋者。故以数子皆知经训也。[5]335
在章太炎看来,司马迁、班固、谯周(字允南)、颜师古、孔颖达、杜佑(字君卿)等之所以能够成为良史皆在于通晓经训。相反,不通经而治史者所得必浅薄。随后,将赵翼作为近人中治史不通经的典型单列出来,加以批判:“近世如赵翼辈之治史,戋戋鄙言,弗能钩深致远,由其所得素浅尔。”[5]335“经史同源”是经学中古文一派的重要治学理念,章氏身为晚清经学古文派的领军人物自觉秉承这一理念,一再强调治古史者必通经,将经学素养作为制约史学文野高下的关键。这与清儒普遍认可的“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6]的学术观念有一定契合之处。依此基准,经学根基不深的赵翼,自然是不符合其所谓的良史标准。
学人金毓黻曾就这一观点作如下解释:“盖章氏邃于经术,以其余力治史,故喜以治经之法治史,其称君卿而抑贵与,则以知经训与否别之耳。《瓯北札记》,时有善言,讥其浅鄙,亦以此故。”[7]如其所言,章太炎对赵翼(字瓯北)史学之贬低确有出于经学因素的考量,但若就此断言他“喜以治经之法治史”则不免有失武断。众所周知,与赵翼齐名的钱大昕、王鸣盛是清儒中擅以治经之法治史的典范,但评论二人史学时却说:“王(鸣盛)、钱(大昕) 诸彦, 昧其本干, 攻其条末,岂无识大, 犹愧贤者”[5]333。由经入史的钱、王两人亦不被章太炎认可,金氏所言有待商榷。通经虽然是章氏追求的良史标准,却并非唯一标准。钱大昕、王鸣盛虽具备了通经的条件,但治史又有“昧其本干, 攻其条末”之弊。章氏拟修撰的《中国通史》旨在“镕冶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5]333以今日眼光视之,意在强调历史研究不应仅限于追求史实的真确,更重要者在于把握历史变化“之所原”这一基本线索,作“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5]333的哲理阐述。在致梁启超的信中也强调:“所贵乎通史者,因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8]由此观之,以钱、王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似乎只能满足对“求真”的需要,却不能满足对历史进化思想和经世目的的追求,故亦不为章太炎推重。
章太炎对“乾嘉史学三大家”的评论是否得当暂且不论,但可推断出以下两点结论:其一,三大家的史学与章太炎所追求的新史学皆存在一定距离;其二,与梁启超一样,章氏亦觉察到赵翼与钱、王两人治学风格的差异。在他看来,赵翼的缺陷在于经学素养不高,对赵翼史学的否定建立在其经史观的基础上。此外,他对钱、王之学的评判则不涉及经学方面的影响,纯粹是出于史学层面的考虑。由于三家的史学思想与章氏此时的新史学主张皆存在一定偏差,故一律予以批评,尚未表露出孰优孰劣的意向。
二、“钱优赵劣”的学术取向
1924年,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问世。据其介绍,撰述此书时曾就体例、人选等问题向章太炎请教。章氏提出的多条建议中,有一条涉及清代史学派别的划分,他认为:“史学分‘浙派’‘别派’,尚非允惬。代嬗之间,知明代旧事者,自以浙人为多,然所重则在作史耳。‘作史’‘考史’二者才本不同。今宜将‘作史’‘考史’分列,不必以‘浙派’‘别派’分列。”[9]3虽提倡作“考史”“作史”之分,却无优劣之别。按照“考史”“作史”的分类标准,赵、钱、王三家皆被归入“考史”一派,声称:“若王鸣盛、赵翼,则‘考史’者也。钱之《廿二史考异》,虽较王、赵为精,亦‘考史’者也。”[9]3在他看来,“考史”“作史”两派之间虽无优劣之分,但同一派内部却有高下之别。三家虽同属“考史”一派,但在考证方面,钱氏比赵、王两家更精,表现出明显的“尊钱抑赵”倾向。对照前文可知,章太炎此时评判三家史著的立场和态度较先前已有很大转变。当他从考据的视角重新审视三家史学时,得出与一般清代学者相同的认识,与梁启超从新史学视角得出的判断截然相反。(1)按:在清代一般学者眼中,三人的学术成就,以钱最尊,王次之,赵为下。然以梁启超的新史学标准看来,代表清学正宗的钱大昕距离新史学最远,而不为清人所重的赵翼却距新史学最近。
1932年,章太炎在北平师范大学作《清代学术之系统》的演讲时再次论及这一问题,谓:
考史者清代特多,最早为万斯同的《历代史表》……其余零考琐录者尚多,以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最佳。三书之中,钱书当为第一,钱、王是一路,赵则将正史归类,其材料不出正史;钱、王功力较深,其实亦不免琐碎。[10]93
这段文字包含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就章氏对待赵翼的态度而言,明显温和许多,不再一味批判赵翼,而是能够正视其与钱、王并称的事实并承认他在清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尽管如此,对比三家史著优劣时,仍然坚持“钱优赵劣”的主张,称“钱书当为第一”“钱、王功力较深”。
其次,章氏不再纠结赵翼经学素养上的缺陷,而是从史学的视角重新衡定得失。他认为赵书不及钱、王两书不仅是因为考证功力的欠缺,还由于史料来源单一,“材料不出正史”。诚然,与钱、王两书相较,赵书在史料的征引和使用上确有以正史为主的特点,但绝非“材料不出正史”。章太炎对赵翼的误解可能是由于《廿二史札记·小引》中的一段自叙:
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11]1
据学人考证,赵翼的实际做法与言辞上的声明并非一致。《札记》一书述史、治史,虽以援引借鉴正史为主,还相当广泛地引用野史杂书、稗乘脞说的史料。[12]正是这种表达与实践上的不同,致使不少学者就赵翼对待正史料和外史料的态度问题产生歧异,章太炎也是其中之一。对赵翼的批评从侧面也反映出章氏并不欣赏这种以正史为主的治史范式。他本人注重史料的广泛搜罗,具有博大的史料观。在《中国通史略例》中曾言:
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5]335-336
章太炎主张治史不要局限于常见文献,应尽量扩充史料范围。举凡域外典籍、地下实物、历史遗迹等皆囊括在内。与钱、王两书相较,史料来源相对单一的《札记》显然不能引起他的兴趣。
第三,指明三家考史著作存在“零考琐录”的缺陷。章太炎发表该演说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在国难的刺激下,其治学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时他认为,“今日切要之学只有两条道路:(一)求是,(二)致用。求是之学不见得完全可以致用,致用之学也不必完全能够求是。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10]93他追求的治学境界是求是与致用的完美结合,按此标准评定清代学术,则“清之学者考证经史详搜博引,虽为前古所无,惜不谙当代制度,治事的时候,辄来请教于幕僚”“虽欲致用亦不能也”。[10]95也就是说,清代学者通古而不知今,只能“求是”而不能“致用”。批评三家史著流于琐碎,主要是因为缺乏“致用”精神。尽管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不局限于狭义的考证,书中诸多内容涉及“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11]1,却并不能令其满意。
三、章太炎贬低赵翼史学的缘由
总体看来,章太炎后来评判赵翼史学时虽不像先前一般言辞激烈,却依然表现出不满。在他心中,赵翼的史学成就始终不能与钱、王两人相比肩,为何梁启超一再推介的赵翼史学不被章氏认可?除上文提到的经学素养、史料采择方面的因素外,似乎还与清人固有之成见有关。
追溯赵翼史学传播的历程,可以发现嘉庆以后,赵、钱、王三家著作齐名并称发展为一种风尚。囿于当时的考据风气,时人往往从考据的标准评定三书优劣,不以考据见长的赵书,只得沦为末座。梁启超所谓“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13]的说法,正是由此而发。深受清代考证学影响的章太炎,不自觉地延续了清儒的观点,展示了赵翼史学接受的另一种取向。
与章太炎同属国粹学派的刘师培(1884—1919)亦不重视赵翼的史学,批判程度较之更甚。他在1905年发表的《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一文中,仅提到钱大昕、王鸣盛两家的史著,与之齐名的赵翼全然不见踪影。按说撰写此文时,“乾嘉三大考史名著”一说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学识渊博的刘师培不可能不知,之所以避而不谈,自有深意。同一文中,谈及赵翼的学问时,称:“若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若袁枚、赵翼之流,不习经典,惟寻章摘句,自诩淹通,远出孙、洪之下。[14]结合前文可推测,不以三家并提或是基于身份和学问上的差异。刘师培对钱、王两人的定位是汉学家,对赵翼则以文士视之,显然是有意区别其身份。即使是文士内部,学问亦有高下之分,在他看来,孙星衍、洪亮吉治经尚有所成就,赵翼、袁枚之流则只是寻章摘句,毫无创获,与孙、洪两人相差甚远。同章太炎一样,刘师培也出身古文经学,尊崇清学正统派的治学路径,经学功底不深的赵翼,自然不是他服膺的对象。
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新旧杂糅、中西交汇,史学界再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基于学术路径和治学旨趣的差异,学人关于赵翼史学的评价毁誉不一。章太炎与梁启超学术根底不同,学论、政见往往针锋相对,二人对赵翼史学的一抑一扬,特别是籍评点其著作彰显的学术旨趣,其实异中有同,不乏相通之处。章氏借批判赵翼的“素浅”,意在强调新通史应具备“钩深致远”的格调,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批判旧史学“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的弊病,有一定契合之处。对赵翼史学的不同诠释反映出民国学术的纷繁面相,也昭示着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多元并存的治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