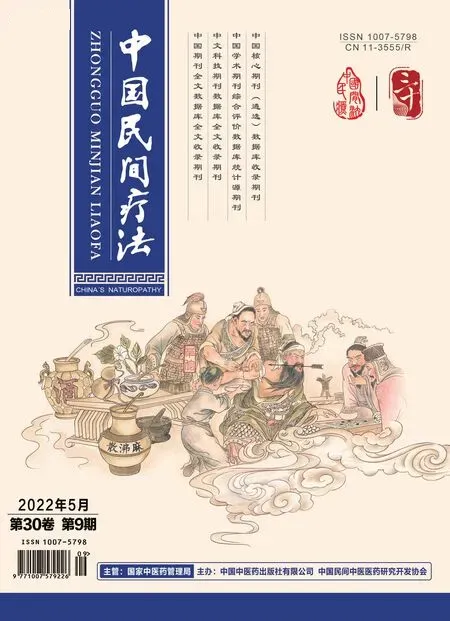基于心肺相关理论浅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
张文潇,张 艳
(1.辽宁中医药大学,辽宁 沈阳 110847;2.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辽宁 沈阳 110032)
2019年12月,湖北省武汉市暴发了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以发热、咳嗽、周身疼痛、疲乏无力及呼吸困难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且具有强烈传染性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采用中医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的诊疗模式展开治疗,使国内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在对COVID-19的研究中,诸多医者发现COVID-19可能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损伤,且患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患者与健康人相比更容易感染COVID-19,合并有心血管系统基础疾病的COVID-19患者的临床症状多较重,预后明显较差。本文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基于心肺相关理论探讨COVID-19与心血管疾病的相互作用,旨在为后续的临床诊疗提供思路与依据。
1 COVID-19对心血管疾病的影响
根据临床资料显示,COVID-19的临床表现以呼吸系统症状为主,亦有大部分患者出现心脏系统损伤的临床症状[1-2]。临床研究发现,在138例COVID-19患者中,发生心律失常的患者占16.7%,发生急性心脏损伤的患者占7.2%[3]。
目前COVID-19对心血管的损伤机制还待进一步阐明,当前研究认为可能有5种相关机制:一是病毒的直接损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7版)》提出,心肌细胞间质内可见有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浸润,可见心肌细胞变性与坏死[4]。二是炎症因子与细胞因子风暴,HUANG C L等[5]研究指出,COVID-19患者体内的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可能存在Th1、Th2反应失衡,因此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导致心肌损伤。炎症细胞浸润和细胞因子的释放也会影响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的斑块稳定性,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6]。三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与进入体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结合,而ACE2具有高度的组织特异性,其在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病和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中发挥重要的作用[7]。四是缺氧,因COVID-19患者肺部感染,造成气体交换障碍,通气量明显下降,诱发低氧血症、休克等,使心肌氧供不足,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机体代谢旺盛,心肌代谢增强,心肌耗氧量增加,而氧供又不足,故诱发心肌损伤[8]。五是凝血功能亢进,在对99例COVID-19患者的研究中发现,36%的COVID-19患者中有D-二聚体升高,30%凝血酶原时间缩短,故感染COVID-19后可能使凝血活性增加,易形成血栓,诱发心肌梗死[9]。
2 心血管疾病对COVID-19的影响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发现,患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相对于正常健康人群更易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且合并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预后多较差。在对COVID-19死亡病例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有22.7%的死亡病例合并心脏系统疾病,合并高血压病者占39.7%[10]。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心血管系统疾病患者对COVID-19的易感性明显高于糖尿病等其他的慢性疾病患者[11]。彭昱东等[12]研究112例有心血管疾病又感染COVID-19的患者的临床表现及预后转归,结果显示COVID-19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病情较重且死亡率较高,由此得出心血管疾病可能会加剧COVID-19的发展,是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有学者分析1 099例重症、非重症COVID-19患者的临床资料后发现,重症COVID-19患者合并冠心病、高血压病、脑血管疾病的比例明显高于非重症患者[13]。
3 心肺相关的中医认识
3.1 心肺生理相关 从中医整体观念角度分析,人体脏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心肺之间亦存在紧密联系。心、肺皆居于胸膈之上,位置相邻,经脉相连,气血相通,生理上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共同调节人体生命活动。《黄帝内经》中有“心肺相关”的相关描述,《素问·痿论》云:“肺者……为心之盖也。”《类经》云:“肺与心皆居膈上,位高近君,犹之宰辅,故称相傅之官。肺主气,气调则营卫脏腑无所不治,故曰治节出焉。”认为肺可辅助心调节全身气、血、津液及脏腑生理功能,故言肺为相傅之官而主治节。人体各脏腑组织能维持规律的生命活动,也有赖于心、肺的协调与配合。此外,经脉在心肺间也形成各种信息网络,成为联络心肺、运行气血的重要通道。如“心手少阴之脉,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络小肠……其直者,复从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下循臑内后廉,行太阴心主之后”。手少阴心经起于胸中,与心系和肺系联系,从腋下发出,行于上肢的内侧后缘,是沟通心、肺的重要通路,为心、肺功能的联系奠定一定的基础。
心主血脉,上朝于肺,肺主宗气,贯通心脉,心与肺相辅相成,维持气血的正常运行和各脏腑组织的正常功能。《素问·经脉别论》曰:“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输精于毛皮。毛脉合精,行气于府,府精神明,留于四脏。”水谷精微上注于心,化为血液,流行于血脉,血气渗透至经脉,产生经气,在十二经脉周流循行,又回归于肺。百脉血气流向肺,从肺获得清气,使阴血与天阳之气相合,既可濡养周身,又可产生能量,供应周身脏腑组织功能活动,由此可见,心与肺在血脉上相通。宗气具有贯心脉、司呼吸的生理功能,加强了血液循环和呼吸之间的协调平衡。刘玉金等[14]认为宗气是心肺相关的功能基础。《灵枢·邪客》曰:“宗气积于胸中……以贯心脉,而行呼吸焉。”因此,宗气是联结心、肺的中心环节,是心肺功能联系的纽带。
3.2 心肺病理相关 五行决定五脏之间的生克关系,肺属金行,心属火行,火克金,金亦可侮火,故心克肺,肺亦可侮心,心病可及肺,肺病亦可逆传心包。《诸病源候论·五脏六腑病诸候》云:“肺之乘心,金之凌火,为微邪,虽病不死……心之乘肺,火之克金,为大逆,十死不治也。”《全生指迷方》亦有心火乘肺金的论述:“肺母火也,性惯受温而恶寒,心火更炎,上蒸其肺,肺金被火伤,则叶萎。”认为心火过盛,上蒸于肺,乘克肺金而致肺痿,故心病及肺。《灵枢·病传》曰:“大气入脏……病先发于心,一日而之肺。”此为心病传肺。《温热论》曰:“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此为肺病传心。
心主血脉,生成的血液在脉管中流动,营养全身;肺主气,生成宗气为血液提供物质基础,推动血液在脉管中正常运行,心与肺相互为用。若血无气的推动,则血瘀滞不行;气无血的运载,则气涣散不收。因此,在病理上,肺的宣肃功能失调,可影响心主行血的功能,使血液运行失常。如《灵枢·本脏》曰:“肺大则多饮,善病胸痹。”《灵枢·经脉》曰:“肺所生病者,咳,上气喘喝,烦心胸满。”同理,心功能失调,也会影响肺的宣发肃降。如《素问·痹论》曰:“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心合脉,心气闭阻,则脉气不通。心之脉气不通,加以郁火扰动,故心下悸动不安;手少阴心经之直者,从心系却上肺,心火上炎扰动肺气,故表现为突然发作的上气和喘息。
4 COVID-19与心系疾病关系的中医认识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关于COVID-19病因病机的认识众多医家学者各持己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沈燕平等[15]提出疫毒夹痰、痰瘀互结为COVID-19的核心病机。诸多医家提出COVID-19多由湿邪致病,湿性重浊黏滞,湿聚成痰,《杂病源流犀烛》谓:“痰之为物,流动不测,故其为害,上至颠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脏六腑具有。”痰浊流动至心,阻遏心中气血的正常运行,形成血瘀,心脉痹阻而致胸痹[16]。尧忠柳等[17]认为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失衡是COVID-19和心血管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RAS经典轴和ACE2分别介导痰湿和燥热的产生。感染COVID-19后导致RAS系统过度激活,使痰湿内生;ACE2活性增加,使燥邪内伏,这种痰湿蕴结、燥热内生的状态使心血管疾病亦缠绵难愈。王玉光等[18]认为COVID-19属于“瘟疫”范畴,病机特点为湿、毒、瘀、闭。《温热论》有“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之说,《温病条辨》云:“温病由口鼻而入,鼻气通于肺,口气通于胃,肺病逆传则为心包。”瘟疫之邪多由口鼻进入机体,肺为五脏之华盖,邪必先伤,心与肺同居上焦,肺卫邪热不传中焦,则可横逆而内陷心包。《诸病源候论》云:“热毒入深,结在五脏,内有瘀血积。”湿热毒邪,久郁于内,逐渐入里化热,蕴结于心,乃成瘀血,瘀血阻滞,气机运行不畅,血脉痹阻不通,发为胸痹。《素问·痹论》曰:“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温热论》曰:“平素心虚有痰,外热一陷,里络就闭。”邪热灼液成痰,或素痰盛,又有邪热内陷,痰热酿成。《景岳全书》云:“气全则神旺……血盛则形强。”素体气血不足,又疫毒入侵,是COVID-19发病的关键因素;若病者素体心阴不足,心气虚弱,邪气更易乘虚而入,加之邪气太盛,而机体无抵御之功,使病情愈发加重。
5 讨论
心肺相关理论基础源自《黄帝内经》,国外学者对心血管系统与呼吸系统进行大量研究后,发现心脏疾病与肺系疾病具有相关性。有学者提出“心肺一体”假说[19],与中医的“心肺相关”一致。研究发现,COVID-19可能会损伤心血管系统,而合并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的重病率和死亡率更高,且预后较差。从中医角度分析,心与肺生理功能及病理机制的联系极为密切,心血管疾病和COVID-19在中医病机上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目前,临床治疗COVID-19更多是着眼于对肺病的治疗,而忽略了对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心与肺生理或病理上均存在密切联系,因此,以后临床治疗COVID-19时,特别是合并心血管基础疾病的COVID-19患者时,可从心肺相关理论出发,采用心肺同治的治疗方法或可取得更为理想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