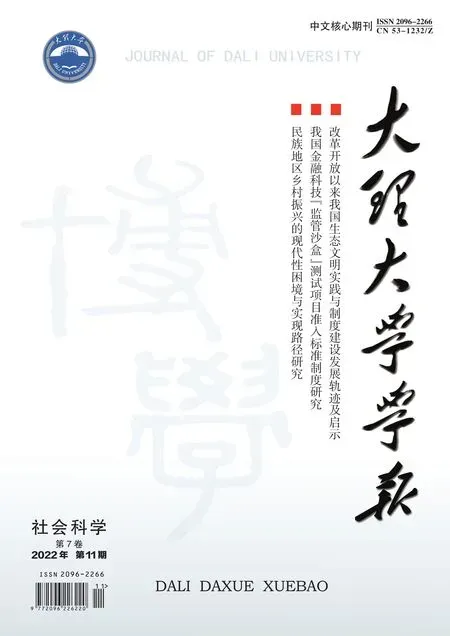论纳张元散文中“彝山”的精神内涵
马绍玺,张 睿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昆明 650500)
彝族作家纳张元的创作始终关注着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彝山文化构成了他作品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纳张元走出彝山,走进城市生活与现代文明,由此开始重新思考彝山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因而现代文明和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冲突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在纳张元的小说中,当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发生冲突时,民族传统文化总是处于劣势地位,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中一一逝去。然而,在散文创作中这一观念却发生了改变。对于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他不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来将问题做简单化处理,而是重新审视文化的复杂多样性,以更加开阔的文化观念,来看待和讨论民族传统文化。本文以纳张元散文文本分析为主,探讨纳张元散文对彝山的精神皈依和文化思考,从中发现作者的文化和情感价值取向。
一、坚毅淡泊的彝山性格
人生长于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并深受其影响。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对人的生理产生影响,而且对人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的形成也产生重要影响。外界环境与作者内在精神的互动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外界环境对作者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为其提供了丰富的表象世界,而且还在无形中浸染着他们的精神气质。群山森林的生存环境背景,使得纳张元散文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同时,群山森林还为他的创作注入一种原始健壮的活力,影响着作品的艺术风格和精神气质,显示出作者独特的山地气质。
“彝人的祖先从不穿裤子和野兽赛跑,直到在窝棚里定居下来,刀耕火种,数千年来一直是在寻找森林,并不断向偏远的高山峡谷中迁移。”〔1〕181彝族人世代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群山森林融在他们的生命和血液里,形成了他们坚毅淡泊的彝山性格。野兽出没的险峻高山,陡峭的盘山小路,艰难的日常生活,练就了彝山人面对人生的勇气和韧性。在《父亲》中,纳张元写父亲年轻时凭借着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棍与大公熊搏斗,从黄昏厮打到黑夜。《山道悠悠》中写自己到山外小镇艰难求学的经历。由于学校没有集体食堂,为了一日三餐,学生需每周背着食物和柴火往返于崎岖的山道上。夏季毒辣的太阳烤得人硕大的汗珠从脸上坠落,多雨的秋季则需要脱下衣服盖住食物以防淋雨发霉,冬季常常又因衣裳单薄冻得手脚麻木,走在结冰的土地上稍有不慎就会摔得鼻青脸肿。作者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谈到,虽然这些在山道上奔波的日子已经远去,但是“它已潜移默化地教会了我,在风雨兼程的人生路途中怎样走好每一步”〔1〕146。这种具有极大挑战性的彝山环境和生活,造就了纳张元坚韧的品质,使他即使离开彝山来到城市也能从容面对各种困难和挫折。
开阔的山岭,深邃的山谷,使彝山人养成了乐观开朗、淳朴厚道的性格。彝山人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唱山歌。纳张元在《梦里,我在唱山歌》中写道:“家乡的人非常喜欢唱山歌。砍柴时唱,种地时也唱,放羊时更爱唱。”〔1〕129开阔的山野还给彝山人提供了直接表达情感的空间,塑造了他们乐观开朗的性格。年轻人在其中大胆表达爱慕之情,妇女诉说着自己的生活苦闷,放羊老汉们的歌声则是古朴苍凉。在《山坡上的羊群》中,纳张元写爷爷一辈子都在牧羊,幼年时给土司牧羊,青年时给生产队牧羊,老了给自己牧羊。爷爷把羊当作孩子看待,悉心照料,根据季节的变化来调整放牧的区域,夏季把羊群赶到嫩草多的高山上,冬季赶下暖和的河谷区,使得羊个个长得油光水滑。爷爷淳朴厚道而无私,不含任何功利目的地放牧羊群,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来认真对待,所以一生悠然地放牧着生活。纳张元从记事起就赤着脚丫在山沟野箐里飞奔,跟着大人们放牛牧羊,目之所及是碧绿的山坡和悠游的羊群,耳之所闻是质朴豪爽的山歌。这样的环境培养了他一生淳朴厚道、淡泊名利的品格,即使当他面对复杂喧嚣的城市时,仍然可以以“宁静祥和的心态放牧生活”〔1〕180。在纳张元看来,彝山的自然风物和民族文化是一种独特的馈赠和重要的精神财富。这样的环境所塑造的性格相异于城市生活所塑造的功利猜忌的性格,他因具备这样的性格而傲于在城市中做一棵独特而有意义的“歪脖子树”〔1〕183。
二、精神回归彝山故乡
纳张元离开彝山走进城市,满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想象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但是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投入城市之中,蓦然发现自己与城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与鸿沟。城市生活和现代文明指向的竟是精神家园的失落和幻灭,而不是理想的驿站。他身居城市,但是精神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都市边缘人”的角色,灵魂深处时常充满着孤独。他常称自己为“山里人”,而把自己的城市生活称为“客居”。“城市不是我的家。我的民族造就了我一副土头土脑的农民模样,我固执的农民脾气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1〕181
城市生活常常让纳张元感到茫然。在他看来,充满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都是被异化了的。在《城市情怀》中,纳张元在城乡对比中多样地描写了异化了的城市生活:自然生长的猪鸡牛羊才是美味佳肴,这是彝山人用数千年验证了的生活知识,城市里却违背自然生长周期,使用大量的生长剂催熟家畜,导致食物寡淡无味;城市里川流不息的汽车让人处处提防,缺少了山里羊肠小道的温馨自由;城里人的装束也是千变万化,“男人们的裤脚宽了又窄,窄了又宽,后来干脆让裤裆坠到脚老弯以下,形同马笼头”,“女人们的裙子短了又长,长了又短,最近好像又在开口上打主意”;甚至还出现了专门教走路姿势的公司,于是城里人走路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走路,其中的刻意修饰充满着暗示;在被异化的城市中生活的人,人格也变得猥琐卑微,一方面笑脸相迎,一方面暗地里尔虞我诈。在另一篇散文《城市蛙声》中,纳张元用尖锐刺耳的蛙声来形容城市里嘈杂的人声。作者觉得与城里人的交谈是件极其困难吃力的事,城里人的话语闪烁其词,含义扑朔迷离:“他们说‘是’的时候,表情分明告诉我‘不’;他们说‘不’的时候,表情明显是‘是’”。城市喧嚣嘈杂、虚假功利的生存环境与彝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生活环境常常使作者感到精神疲软,无所适从。
在与现代城市的对照中,纳张元开始游离于城市寻找精神家园。寻找的结果是对故乡彝山的回归。纳张元是在彝山的山沟野箐中跟着大人放牛牧羊成长起来的,牧羊和唱山歌是他重要的“童年经验”。童年总是与纯粹、纯真相连,当人们对现实产生不满,而现实又难以改变,皈依纯正的童年就成为他们的一种选择〔2〕。与故乡连接的童年经验引发了纳张元对故乡的回归,于是,放羊和唱山歌成为他的散文反复吟唱的对象。在《梦里,我在唱山歌》中,纳张元写自己的梦中经常出现在家乡唱山歌的情景:“进城已经多年了,但我总梦见自己还在家乡的崇山峻岭之中牧羊。梦里我总在尽情地唱山歌”;在家乡牧羊放牛的日子也是他在城市生活中常追忆的对象,他在《山坡上的羊群》中写道:“我羡慕那些山坡上悠游自在的羊群,我更羡慕爷爷这样淳朴厚道的、心底无私的牧羊人,他们淡泊名利,心境透明宁静,所以,他们放牧生活。”山地上牧羊追牛的日子是纳张元自由自在欢乐的时光,唱山歌是其中排遣寂寞、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牧羊和唱山歌是纳张元重要的家园符号,每次对它们的吟唱,都是一次“归乡之旅”,带给他精神的慰藉和情感的归属。
同时,此时的回归并不仅是意味着回归童年的乡土生活,而是对故乡的一种精神皈依。正如鲁枢元在论述故乡的意义时说道:“故乡又是一个现下已经不再在场的,被记忆虚拟的,被情感熏染的,被想象幻化的心灵境域。”〔3〕牧羊和唱山歌是纳张元重要的精神意象,其内蕴指向的是他的心灵家园。对牧羊追牛、尽情地唱山歌的彝山生活的追忆,代表的是纳张元对于真挚纯粹、自由自在生命状态的向往和皈依,是在他曾经生活、生长的乡土之中寻找精神力量的支撑,坚定自己的精神人格。他在《城市情怀》中写道:“我很清楚,我已成了这个经常刮大风的城市里的一棵歪脖子树,一种怪异的人文风景。会有许多好奇的人把我当作某种标本,用放大镜来反复鉴赏研究。他们将不会失望,作为标本的一种,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纳张元在对故乡的频频回首中,寻找着自己精神气质的根基,以便傲立于城市之中。
纳张元的还乡,不仅是对现实和物质之乡的怀念与向往,更是一种对精神故乡的回归。这一精神故乡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和精神诉求,这一精神故乡是他对淳朴真挚、自由自在人生的向往,也是他坚持自我精神人格的依据。
三、对彝山文化的反思
纳张元是接受了现代知识并有自觉文化反思意识的现代作家。他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但他同时也意识到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所处的滞后地位。所以,他一方面在写作中尽力呈现自己的民族与故乡,另一方面,又以自省的态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思考。他在谈自己的文学创作时说道:“我在创作上一直朝两个方向努力:一是在语言上找到自己的个性,二是不简单流于风情描写,而致力于文化反思。”〔4〕
纳张元凭借自己的奋斗走出彝山,接受现代文明与现代教育,最终成为大学教授,定居于都市。当他重新回望或回到故乡彝山时,他的感受已经大异于从前。此时他除了看到故乡诗意存在的一面,也看到了彝山封闭落后的一面。火塘、酒和唱山歌是彝山独特的风俗。纳张元在散文中写道:“酒是男人的性格,没有了酒,也就没有了彝家汉子。”〔1〕143彝族喜欢用狂欢纵饮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清淡人生》中,在小镇教书的“我”到山里家访时,憨厚淳朴、不善言辞的家长对老师表达信赖和崇敬之情的方式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给我斟酒,把我的酒碗倒得很满很满”。借酒咏歌,以酒传情,体现了彝族人淳朴豪爽的性格特征。但是在这种豪爽与洒脱中,纳张元感受到了酒对彝山人的侵蚀,也由此思考到了民族发展滞后的原因。《秋天的困惑》集中写了彝山人饮酒后不良的生活习惯。秋天一年收成换来的钱先去买酒喝,不管房子有没有破,孩子有没有衣服穿,发了酒疯还要打媳妇。纳张元深感彝山男人的懒惰、暴力,文章最后发出疑问:“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山里人收获了什么?”这一沉重的疑问的发出,既是作者对彝山文化的沉重反思,也是作者向自己的同胞发出的沉重的文化警示。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即使千百年来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种一片坡,收一土锅”〔1〕157生活的彝山,也正在被匆匆向前的现代时间惊醒。作者看到了在这一前进过程中彝山的落后状态,而他应对这一危机的办法是放弃传统中过时的文化因素,以自省的态度来整理自身文化中不合时代的落后因素,并将其舍掉。纳张元说道:“外面人看我们,更多看到一些美好的方面,我倒觉得许多东西值得反思。”“自己写自己的民族,可以如实描写,没有顾忌。”〔4〕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自省也是其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纳张元对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批判,是其对故乡和民族产生的忧患表达,其中包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这体现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和使命感。同时,纳张元对民族传统文化也不是全盘否定。他努力开掘彝山特定的地域文化,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民族文化的对比中,思考民族文化的优异之处,发掘民族文化来启示新的现代文化。
纳张元在许多作品中都表达着他的生态意识,而这些生态观正是来自彝族古老先民的生态智慧。彝族世代生活在崇山峻岭之中,人与自然关系密切。他们深信万物有灵,认为自然万物不仅具有生物生命的特征,还具有精神生命的特征,于是便产生了自然崇拜。彝族的自然崇拜强调人与自然生命一体的生态关系,人仅是自然中的一个因素,因此人要尊重自然,对自然充满善意,这样人与自然才能和谐相处。
鹰和蛇是彝山常见的两种动物,彝山有许多关于鹰和蛇的神话传说。彝族崇拜鹰,认为鹰是百鸟之王,有能够预知自然、预测未来变化的能力,是能够战胜一切邪恶的神鸟,是族人的保护神〔5〕。在《远去的鹰影》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鹰的敬畏之情:“穿梭在彝山上空的鸟类很多,但绝大多数雀鸟都只是匆匆过客,只有鹰才是永驻天空的主人”,“如果说虎是大山的灵魂,鹰就是天空的思想”,“自从天空中没有了鹰,风调雨顺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他认为鹰身上富有勇敢高贵的气质,同时还是自然的保护神。在彝族的神话里,蛇被认为与人有亲缘关系,因此不能随意杀害,更不能食用,如果违反了则会受到祖先的惩罚,引发大自然的灾害。所以,当听说“城里人连蛇都吃时”〔1〕160,彝山人感到惊异不已。同时在与蛇长期的共处中,彝山人发现“蛇是一种善良的动物,它们从来不会主动攻击人类,除非人类首先对它构成了威胁或伤害”〔1〕159。
在生态环境遭到人类严重破坏的现代化进程中,纳张元在自己古老的彝山文化中寻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办法,并在自己的散文中将彝族在自然崇拜中保有的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精神进行了很好的文学表达。
纳张元是从彝山走出的作家,从乡村到城市的生活空间的变化,构成了他现代文化和传统民族文化交融的双重文化背景。彝山的自然风物、传统文化浸润着他,塑造了他坚毅淡泊的性格,也成为他漂泊异乡时可供寻找的精神家园。同时,纳张元又是接受了现代知识并具有自觉反思意识的现代作家。他以双重的文化视野来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在两种文化的关照中思考彝山文化的滞后和优异之处。他的文学创作关注的是彝山的文化和生活,作为作者的他虽然身居城市,但是他的文化和精神皈依仍然与他的故土相关,他的文学思考也是他探索民族文化发展之可能性的具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