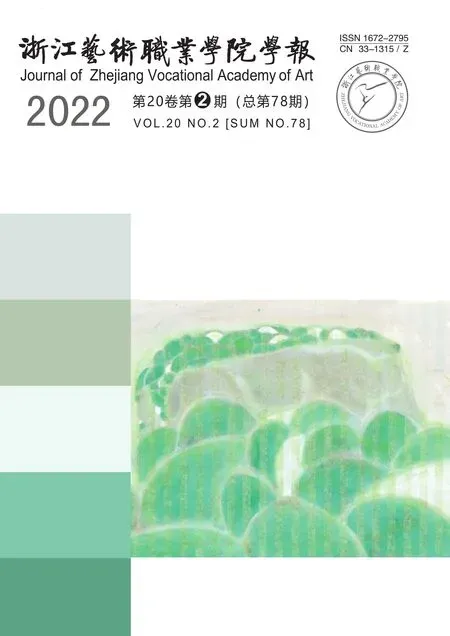《西游记》杂剧世情笔墨研究
马小玉 高益荣
一、神魔世界的世情色彩
“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1]。看似魔幻的《西游记》 杂剧,呈现的依旧是人间的世情伦理。世情笔墨最突出的体现,便是本应与人天差地别的神魔,都浸足了世情的色彩——用市井言语交谈,依世俗规矩做事,循尊卑等级自处。
(一)典型神魔的凡俗特质
《西游记》 杂剧中的孙行者,兄弟姐妹俱全,七情六欲皆存。与小说中“受天真地秀,日精月华”[2],明心见性的心猿大有不同。他有家庭,有血亲,处于血缘纽带、人伦关系中。
小说中,“只有孙悟空有完整的童年”[3]7。杂剧中的行者没有童年,却有童趣。寻常人有的,他要有,强抢金鼎国女子为妻;寻常人没有的,玉露琼浆、仙衣仙桃,只要喜欢,或偷或盗,总得收入囊中。既像不懂事的孩童,见了好的就不松手,又像小偷,贪心又胆小。偷回仙衣又生怕:“左右的,与我照管前后门,休放闲神上来”[4]439。李天王下界拿他,他与天王捉迷藏:“上树化作个焦螟虫,看他鸟闹。把我媳妇还于本国,我依旧入洞,顶上洞门。任君门外叫,只是不开门”[4]422。即便出家也静不下心:丈量金鼎国山高、和另一个“小孩”哪吒逞胜争强。西行取经,他像顽童一般,调皮捣蛋,却也不失率真可爱。
又像个不讲理的“游民”。唐僧不顾山神劝告拼力救他,这厮却想着:“好个胖和尚,到前面吃得我一顿饱,依旧回花果山,那里来寻我!”[4]445-446还有一股好勇斗狠、不甘人下的傲气。山神好心提醒“流沙河妖怪能伤人”[4]447,行者却道,“说道他要吃人,我着他先吃我一吃”[4]447。与人争斗先夸口:“我是紫云罗洞主,通天大圣。我盗了老子金丹,炼得铜筋铁骨,火眼金睛,石屁眼,摆锡鸡巴。我怕甚钢刀剁下我鸟来?”[4]483分毫不像出家人,浑一个市井混混。身至佛国,与贫婆说经也出言不逊,问道有心也无,回道:“我原有心来,屁眼宽阿掉了也”[4]490。不过,杂剧中的行者自有其发光之处。裴海棠称其“仗义师兄”便十分准确。西行一路,也是行者行侠正义的一路。路遇被劫的裴海棠,主动请缨“我与你寄一个信”[4]462。给裴老带回女儿,纵不知是何妖怪、能否战得,即便寻求他助,也要好人做到底:“我降得,便自降他;降不得,直至普陀,告观世音,差二郎来收他,绝了你两家后患”[4]468。对刘大姐也是如此:“老儿,你管待着俺师父。俺弟兄三个,拿那妖怪,夺的孩儿还你”[4]450。
一面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师兄,一面是劣迹斑斑的腌臜猢狲。两个看似悖谬的特质在他身上合作一处,使之成为杂剧中最复杂、立体的神魔形象。而他的生动活泼,恰来自于其“俗子”身份——处于凡俗社会关系、血缘纽带之中。
行者顽皮、粗俗、放肆,自然有一分真。与之相对,唐僧与观音属于成人的世界,他们更懂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也添了一分伪。小说中“人物来历日趋神异化与精神世界日趋世俗化”[5]的唐僧在杂剧中已见身影。对行者的称呼是唐僧态度的晴雨表。态度的变化取决于他认为行者是给他惹事还是排忧。路遇裴朱吵嚷,行者自告奋勇“要你的女儿,当来问我”[4]465。玄奘对徒弟这般出风头甚不满意,道“你这胡孙,又惹事了”。等行者不差毫厘地讲完,玄奘瞬间改了口风:“行者,你如何得知来?”[4]465待行者出发去寻裴海棠时,惹事的猢狲,变成了“吾弟用心”[4]465。自玄奘登场,其言行就很难与“大得玄妙之机”相联系。听闻身世,气得晕了过去;擒贼雪仇看似是他的功劳,实际工作却大多是丹霞禅师和虞世南所做。路遇红孩儿,不辨善恶、不听劝阻,定要行者背着,导致自己身陷魔爪。但闻魔障祸患,只会问如何是好,全不知自己才是师父,取经队伍的带头人。西行多难,虽不能苛求唐僧一力踏平荆棘,但作为西行队伍的灵魂,取经重担真正的背负者,唐僧的意志堪称软弱。
杂剧中的观音会算计,懂经营。西行艰难,观音看中通天大圣本领高强,想让他随行取经,可他凡心未退,于是就面临两个问题:一、怎么让通天大圣答应西行;二、如何保证他不伤害唐僧。通天大圣本领高强,家门显赫,自是一身傲气。观音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便是“哄”。这局棋,她从山压行者便开始布置了。杂剧中,无论神魔还是人,都遵循善恶有报的思想观念。所以观音抄化了行者并没有即刻送到唐僧身边,而是把他压在山下,由唐僧亲手救出。如此,唐僧就是行者的救命恩人。照常理,行者应对救命恩人感激涕零。但这位通天大圣并不能以常理忖度。于是观音另有高招: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一面是胡萝卜,交予行者。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相诱:“好生跟师父去,便唤作孙行者。疾便取经,着你也求正果”[4]446。另一面是大棒,交给唐僧:“这畜生凡心不退,但欲伤你,你念紧箍儿咒,他头上便紧。若不告饶,须臾之间,便刺死这厮”[4]446。杂剧中的铁戒箍与小说中的紧箍咒,都是菩萨用来帮助唐僧束缚行者的,但两者大有分殊。紧箍咒也唤“定心真言”,由如来赠予观音,将神通广大的妖魔收入佛门,目的在于教化。所以小说中观音赐给唐僧紧箍咒,除了保护唐僧外,还有教化悟空、助成正果之意。杂剧中却是“须臾之间,便刺死这厮”。紧箍咒是一把戒尺,而铁戒箍是可以取人性命的匕首。杂剧中的观音全无小说里的半点慈悲为怀,她在意的只有取经,所有人都是棋子。本应心静神闲、无所欲求的菩萨,却为实用功利羁绊,可谓世间实用功利的代表。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乍看之下引不起我们的留意,是因为他们遵循的本就是世俗规则。“神魔”,不过是一纸标签,活跃着的尽是世间活生生的普通人。鬼子母失去爱奴儿,与殷温娇送走江流儿一样肝肠寸断;面对 “上级”旨令,天王龙王和尉迟恭虞世南一样都得服从。光怪陆离的神魔世界,实际就是凡俗世界的戏剧化演绎。
(二)神魔世界的人间秩序
《西游记》 杂剧中,诸天神介绍自己时,都会将自己归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已出家学艺的,自报师门:“西天我佛如来座下上足徒弟”[4]405观世音;“观音佛上足徒弟木叉”[4]432。还没从师的,自报家门:“毗沙天王第三子哪吒”[4]440;姓沙的回回水怪沙僧等。通过归属,人们在社会这张大地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再像水的波纹那样,一圈一圈地推出去,形成相应的社会关系,逐渐产生社会序列与等级秩序。
木分花梨紫檀,人分三六九等。《西游记》 杂剧在“奉”“领”“令”“着”等字眼中,春秋笔法般道出神界的严明秩序。南海小龙领观音法旨:救陈光蕊入水晶殿,护江流儿一路周全。华光天王面对“观音佛相请”也得“须索走一遭”[4]435;李天王要“奉玉帝敕令”。风雷雨电四位天神,要听从李天王调派,护送凡间女子回乡;奉观音法旨,为唐僧灭火消灾。天神,并不因飞升成仙就能逍遥自在,而是被安排进等级严明的神界秩序,同凡人一样有高低尊卑。
与人间相同,有等级秩序就必然有相应的法度,具体表现为奖惩手段。无论是依律当斩的龙王,还是合该毁形灭性的行者,比起小说,他们犯的罪并不重。小说中的龙王悖逆了玉帝旨意,杂剧中只是由于疏忽。弼马温大闹天宫引得压身五指山,通天大圣受困是因为盗了王母的仙衣仙帽仙桃。可他们最终都没有身首异处。观音为他们留了一条生路,但不是因为我佛慈悲,只是因为他们还“有用”:南海火龙可以化身坐骑给唐僧当脚力;通天大圣则可以用胡萝卜加大棒逼他就范,保护唐僧西行。正应了人间的俗话: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龙王与行者并没有脱罪,活下来是因为他们可以将功折罪。与其说这是神佛体系,不如说这是世俗世界在神界的映射。
二、人间世界的世俗情味
《西游记》 杂剧塑造了洋溢着人情味的神魔世界,也没有忽视充满烟火气的人间。他们在舞台上来来往往,欢歌笑骂,爱恨别离。
(一)人间的情
“世总为情”[6]。《西游记》 杂剧围绕取经展开,着墨最多的自然是西行的情节推进。但在推进中,我们能感受到一些停顿。停顿发生时,矛盾被暂时搁置,剧情发展逐渐变缓,进入到某种人所共有情感之中,与角色发生共情。
第二出《逼母弃儿》,单看剧情,这只是唐僧的身世背景,无须过多笔墨就能交代,但作者用了整整一出。一连十二支曲,将读者代入一种愁情,以至于我们忘记要报仇,要西行。“诉苍天不能搭救”[4]412,她能做的微乎其微:“将这乳食儿再三滴入口”[4]412“将匣缝儿塞,匣盖儿缚,包袱儿紧扣”[4]412。使出浑身解数也无可奈何时,只能将希望寄托于渺茫的天地神明:“天地祚,祖宗扶,神明相祐”[4]412。“言出至情,自然刺心,自然动人,自然令人痛哭”[7]。殷温娇的唱词令人肠断,是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对亲情的记忆与感受。母亲的不舍、痛苦、绝望被掰开揉碎,母子亲情奔涌而出,令读者感同身受。
情有亲疏远近,《西游记》 杂剧中亦如是。丹霞禅师的话便是最好的印证:“先报了生身的慈亲,却来报养身的师父”[4]416。除却亲情,作品中还穿插了其他情谊,比如:恩情。《行者除妖》 中,行者请缨搭救刘大姐,刘太公便要“宰一个耕牛儿亲自接”[4]450作为答谢。女儿得救后,更是将恩情久久挂怀,万望报答。无独有偶,重获自由的裴海棠感叹:“来、来、来,我亲自礼拜你三千万”[4]467。有恩,自然衍生出报恩。这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观念。当然,有恩就有恨,报恩也报仇。陈光蕊一遇害,殷温娇便考虑日后谁人能为丈夫报仇,也因此才委身刘洪。
世间之情,有母子亲情,就必然有男女之情。西行之于唐僧,最难的不是妖魔拦路,而是世间温柔乡。《女王逼配》 中,她以嫦娥“孤眠居乐窟”自比,丝毫不掩饰、否认男女之情,直白表露自己对男子的渴望:“见一幅画来的也情动,见一个泥塑的也心伤”[4]474。不但不否定欲望,还认为是十分合理的伦常:“听得说天地阴阳,自有纲常,人伦上下,不可孤孀。俺这里天生阴地无阳长,你何辜不近好婆娘? 浮屠尽把三纲丧。”[4]475认为佛家教义破坏了人间伦常。她的态度非常坚决,若唐僧坚持不肯,她已做好“霸王硬上弓”的准备:“你若不肯呵,锁你在冷房子里,枉熬煎得你镜中白发三千丈。成就了一宵恩爱,索强似百世流芳。”[4]476这位国王的情感流露可谓直勾勾、赤裸裸。“大得玄机之妙”的玄奘,最后只剩一句软绵绵的“我还要取经咧”[4]476。没有天尊护持,老和尚能不能守住真元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见难过美人关不只有英雄,还有和尚。
(二)人间的理
《西游记》 杂剧不仅“书情”,而且“说理”。其世情笔墨不止于表象描绘与情感描摹,唱词念白下还潜藏着世俗观念——世间人等磨合多年的处事之理。首先是天命观。事态发展似乎皆是命中注定,整本杂剧都仿佛是在注定的框架中按部就班。自第一出开始,陈光蕊就注定有十八年水灾。所以无论王安寻得怎样的船夫,刘洪是不是谋财害命之徒,一切偶然都会走向一个必然——十八年的水灾。自毗卢迦尊者转世,诸天神就像传话筒一般,奔波于仙凡两界,提险示难。江流儿被抛之江上,伽蓝报丹霞禅师 “有西天毗卢迦尊者,今日早至”[4]414;玄奘年满十八,伽蓝如时钟一般:“此子时节到也,当报仇雪恨去”[4]415。取经路上更是如此,但凡劫难灾殃,没有不知、不报的。二郎神、韦陀天尊,哪怕是观世音,言语之中都无甚个人意志,尽皆传达天命安排。于是一切偶然又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必然。小到一股金钗,龙王许诺要“金赠有恩人”[4]411,后金钗出自殷温娇之手,经江流儿一路飘零,到丹霞禅师门下,最后归入救起江流儿的渔夫囊中。辗转多回,黄金终要赠予有恩人。“大官司输与小孩儿,小孩儿亏杀老禅师”,陈玄奘大报仇的关键都在于“老禅师慧眼识天时”[4]423。
一切天命,寻常百姓虽不可知,却会有异样之感。殷温娇抛弃孩儿十八年,不曾有过任何异样,独玄奘将来那日,“耳热眼跳,神思不安”[4]416。雪恨之日“夜来灯花爆,今日灵鹊噪”[4]421。行者去救刘大姐时,银额将军 “耳热眼跳,不知为何”[4]450。取经完成,东回大唐,更是一片“祥云叆叆,瑞气腾腾”[4]499。
其次,善恶要报的朴实观念与善恶有报的心理期待。《西游记》 杂剧中,无论神魔还是凡人,善恶要报,镌骨铭心。龙王醉酒化鱼,险些“公厨银镂刀”[4]411,幸得陈光蕊买而放之,保全性命。贵为龙王,也一直惦念着“此恩未尝报得”[4]411。但得报恩机会,便将陈光蕊养在水晶宫内十八年。取经作为整本故事的核心,也是由唐僧报恩开始:“小僧性命,也是佛天相保……我舍了性命,务要西天取得经来,平生愿足”[4]425。善是如此,恶亦如是。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是无须多言的常理。自陈光蕊遇害,殷温娇就在考虑为夫报仇,也才委身刘洪,蛰伏多年。善恶要报不仅在主要情节中表现深刻,在一些“细枝末节”处,仍有关照。被李天王救了的金鼎国女子感叹:“得见双亲,实感天王之大恩……将天王众多神将来雕,摆列着香案,供养着容貌。每日逐朝,记在心苗。办着一片虔心把香烧,将您那恩来报”[4]441。还有要等取经一众回来“重酬谢”的刘太公,要“亲自礼拜三千万”[4]467的裴海棠等。看似无关紧要,实是作品中重要的思想观念,或详或简,贯穿整本杂剧。
如果说善恶要报是能通过主观能动性实现的朴实观念,那么善恶有报就是他们最渴望的心理期待。“为善,天降之百祥;为恶,天降之百殃”[8]。这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动力。害人性命的刘洪,冒任一年“便动了残疾致仕”[4]415。十八年后,终落得“尖刀剖其腹,俘献陈光蕊”[4]422。受了屈的玄奘一家也得到补偿:“将陈光蕊十八年,都准了月日。授了中书门下平章事,特进楚国公,殷氏封楚国夫人。赐公田四十顷,归老为农”[4]423,恰便是“善和恶在乎方寸,花开枯树再逢春”[4]418。
再次,“有人好办事”的人情观念。江流儿长大成人,是时候为父报仇。师父和母亲多番叮嘱:“那厮在彼处十八年,广有手足”[4]416。处理这一问题时,丹霞禅师请缨“老僧和你去”[4]416;殷温娇让玄奘“星夜回金山寺去,请师父引你来,报仇雪恨”[4]418,可谓不谋而合。丹霞禅师前来作甚呢?“洪州太守虞世南和老僧有一面之交,引着玄奘告状去”[4]420,便是要用人情解决问题。虞世南听了尊师告状,不经调查,不问证人,甚至不假思索,即刻点兵捉拿。
最后,实用功利的考量标准。唐僧决定西行并不是出于对佛法的虔诚,而是 “报皇恩万万千”[4]425。取经途中,借山神之口说出“此一行半为于民,半为报国”[4]444。取经完成,许下的心愿是“愿祝吾皇万万年”[4]499。佛经对皇帝来说,是稳定人心、维护统治的工具;对唐僧来说,是回报皇恩的礼物。所以取经本身就充溢着实用、功利的色彩。世间常人没有高官厚禄可坐享其成,只有勤勤恳恳地“做生活”才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看了社火的胖姑回归家中,还是要自己解决生计。所以在她看来,一天的工夫不如用在 “生活”上。他们的收获是汗水浇灌而来,因而当他们不用付出辛苦,或付出少于获得时,他们会很乐意接受,即所谓的“小便宜”。它也是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深入人心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行为模式。需要获得帮助时,先告知对方能获得的好处,希望这好处能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杂剧中,不仅是人,观音、行者等神魔也深谙这一点:“好生跟师父去,便唤作孙行者。疾便取经,着你也求正果”[4]466;“你放心,随我师父西天取经回来,都得正果朝元,却不好来”[4]4448。
三、世情笔墨的时代内核
神魔架构中的鲜明对比,六本二十四出的精彩演绎,使得市民意趣在《西游记》 杂剧间大放异彩。贪杯的龙王、调皮捣蛋的行者、“处心积虑”的观音。神魔之于人,不过是样貌、属性不同。他们的行事作为,与世人无异,更准确来说,与市民无异。西游故事的发展脉络中,之前的《取经诗话》 宣扬佛教,一句“天王”可在任何境遇下化险为夷。之后的《西游记》 小说,“游戏之中,暗传秘谛”[2]252。处于其间的《西游记》 杂剧,既不宣扬佛法,也鲜有深刻的哲学思考。它的精彩,恰在于亲近市民,痛快、酣畅地演绎出市民性这一时代内核。
“市,买卖所之也”,指古代城内进行商业活动的区域。“市民”,即伴随着商业活动兴起的阶层,以生活在城市中的民众为主体。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市民群体生产生活的内容与形式相对同质,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也相对稳定。但比之此前的文学,此时的杂剧打上了更深的市民烙印。考察客观条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与前代的不同。
此时的统治者全不像中原地区的传统君王。他们像商人一样追求利益、实用,却又不懂商业策略,不善经营,像纨绔的富家子弟,不愿费心,喜好奢靡,需要足够的金银。他们重视商业,给商人减税、免税等优待政策鼓励贸易[9]516。甚至“从政府到蒙古、色目贵族普遍积极参与经商逐利”[9]512。“至于交通的发达,大城市的众多和繁荣,手工业和商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展开,都超过前代……市民阶层在元代较以前壮大。”[10]商业城市兴起,经济繁荣发展,促成了市民阶层进一步崛起,也刺激了元杂剧的蓬勃发展。这一点可以从元杂剧作家群的分布得到佐证:“很多作家由于城市分布的地域影响和作品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固定的群体,如大都作家群(包括马致远、杨显之、纪君祥、张国宾等)杭州作家群(包括鲍天佑、萧德祥、王晔、沈和等),这些地区都是商业活动非常频繁、商业发展繁荣的地区。”[11]同时,元杂剧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与商业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亲和。因此,元杂剧体现出的市民性色彩,与元代蓬勃发展的商业、崛起的市民阶层是分不开的。
世情笔墨表面上呈现为神魔的世俗化与大量涌入的市井角色,深而观之,则是杂剧中暗含的世俗观念与市民审美趣味。城市、商业、经济,这些外部条件并不能直接促使杂剧向市民靠拢,为市民书写。《西游记》 杂剧中的市民性并非个例,而是杂剧这一体裁的常见现象。比之诗词文,元杂剧呈露的气象与审美趣味大有不同。蒙元铁骑挟异族文明猝然踏来,游牧民族成为农耕文明的统治者,一系列举措在有意无意间为华夏文明注入新鲜血液,也促进了审美趣味的转变。元代统治者汉化程度较低,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也较为有限。加之蒙元帝国疆域横跨欧亚,汉人作为被征服的民族之一,其文化对于蒙人没有天然的优越性。蒙古贵族对汉文化的接纳,多是出于维护统治的考虑。对思想的采撷,也带着兼收并蓄、实用为上的粗犷气息:“人类各阶级景仰和崇奉四大先知,基督教把耶稣作为他们的神,穆斯林把穆罕默德看做他们的神,犹太人把摩西当成他们的神,而佛教徒则把释迎牟尼当作他们的偶像中最为杰出的神来崇拜。我对四大先知都表示景仰,恳求他们中间真正在天上的一个尊者给我帮助”[12]。
思想文化领域的宽松政策自然有利也有弊。好的层面来看,这为创作者提供了相对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加之游牧民族“美声文而侈观听”的审美观念,对中原“植纲常而厚风俗”礼乐观念的冲击,许多传统观念被淡化怀疑[13]44。传统的音乐审美观念以孔子诗学精神为内核,“礼”为主,“乐”为附庸;音乐表达应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但这种文化氛围恰不利于戏曲发展。戏曲本是民间艺术,追求大众化的通俗直率,主要功能是娱乐而非“载道”。只有旧有观念被撕裂,审美趣味有所转变,戏曲长期积聚的力量才能喷发[13]41-44。元代思想文化的多元与对儒家正统的冲击,为杂剧勃发扫清障碍,使杂剧得以成为“一代之文学”。坏的层面来看,“中国政治的法统与文化的道统到了元代被割裂了”[14]。统治者不像从前那般重视儒学,对关系文人社会地位的科举不够重视。“自1234年蒙古灭金占领中原并废除科举取士,直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首次恢复御试,中原地区科举取士制度被废时间长达81年。原属南宋统治的南方地区,自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国,直至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南方地区科举取士制度被废时间亦长达36年。”[13]52科举——历代儒生求取功名的捷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谋生之路,不再是通往君王座上客的通途。“学而优则仕”,这对文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然凡事皆有两面,庙堂之路被折断是文人的不幸,却是元杂剧的幸运。从前“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的文人被迫进入市井,为市民性直接带来两方面的促进作用。
一方面,文人进入书会,成为“才人”。书会具有盈利性质,作为观众的市民为杂剧买单。“元杂剧具有票房价值”[15],要想赢得观众的喜爱,就得考虑他们的所思所想。对普通市民而言,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事物更能打动人心。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是创作者,也是观众。人们更希望在戏曲中关照自己的生活与命运。于是,贴近市民,为市民书写便再自然不过。另一方面,文人真正接触到市民,切实了解市民的所想所愿,才能真切地将市民的生活、愿望、观念呈现。“文以载道”失去了现实依靠,只能出入于书会勾栏[16]176。普遍的穷困使他们不得不栖身市井,混迹于长街闹市,与普通市民同处一境。是一批距离世俗生活很近的文人——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心理距离。处于市民之间,抑或本身就是市民的一员。所在的环境、所接触的人事,成为创作时的素材。所以无论是无意识、不自觉地贴近市民,还是考虑到杂剧演出的收益,主动向市民靠拢,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市民性在杂剧中的呈现。
结 语
“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17]。《西游记》 杂剧显然不满足于描绘一个渺远的神魔世界,其真正的关怀始终在凡俗世间。反观西行,虽是神佛的事业,却是人间的旅程。从灞桥烟柳,到娑婆世界,表面上是诗意的出世之旅,实际却一刻也没有离开人间烟火。字里行间,隐藏着作者对彼时世情的观察与书写。神魔浸满了世间色彩,人间充满温情。如果说这些都是表象,那么潜藏着的,是切近市民的创作者对世间热辣鲜活的市民生活的体认,展现的是“世俗却实用的‘生活力’ ”[3]5。
“话语明白如话,而言外有无穷之意”[18]117。念白和曲词由舞台上的角色道出,而让角色发出声音的,是台下的创作者。那一时期“主要的作者,与其说是官僚,不如说是市民”[19]134。他们扎根于人民,出没于市井,与底层人民保持着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联系。“没有前代和后辈文人自视清高的酸腐,比较注重实际和接近平民生活”[19]136。不刻意地追求“雅”,也不刻意避开“俗”,甚至热情洋溢地拥抱 “俗”。以市民之自然,成文章之自然[18]116,贴近世俗情态,呈现世俗生活状貌,才能够写出“反映社会面广阔而生活气息浓厚的元杂剧”[16]169。《西游记》 杂剧正是沾染了浓厚生活气息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