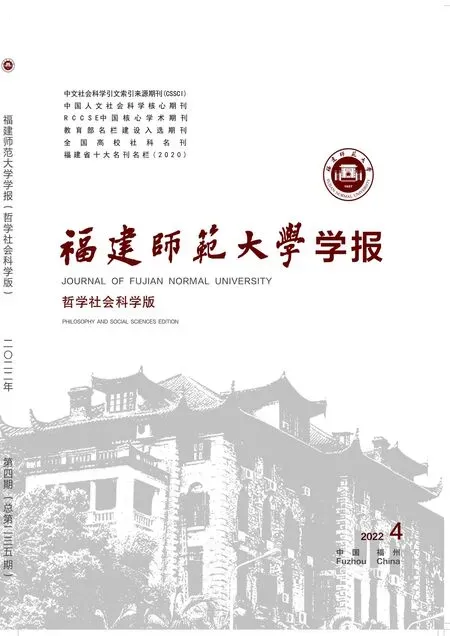智能时代的信息控制、电子人与媒介物质性
——论凯瑟琳·海勒的后人类传播观念
郑 奕,连水兴
(1.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2.福建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随着网络信息、人工智能与虚拟现实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生存主体的“人”本身也成为一种可以根据需求进行改造的对象。在这种背景下,“后人类”这一概念引起了学术研究的普遍重视。其中,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 (N.Katherine Hayles)以其独特的“后人类”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诸多关注。海勒在其后人类理论中,广泛涉及计算机技术、信息网络、人工智能、虚拟符号、媒介物质性等问题,其中的部分观点也逐渐被国内的传播学者所关注和引用。然而,学术界关于海勒后人类理论“只言片语”的引述,不仅无法呈现其理论形态的整体性,而且很容易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和误读。因此,笔者试图从传播学的维度对海勒“后人类”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探究其中所隐含的后人类传播观念,并对这种传播观念形成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与适用性进行分析。
一、人工智能与“后人类”传播时代的到来
海勒在其经典著作《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的序言中,一开始就将阿兰·图灵(Alan Turing)写于1950年的经典论文《计算机与智能》作为介入“后人类”思考的开端。在她看来,“图灵测试”为之后数十年的人工智能研究设定了基本议程,而为了获得能够思考的机器,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围绕“图灵测试”展开了长期的探索。这一切,构成了后人类理论产生的时代语境与知识背景。
海勒在追溯“后人类”研究的学术史过程中,发现所谓的“后人类的观点”往往带有一系列假设性的视角:比如将由生物基质形成的具体形象和意识/观念都视为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人的身体只是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其中,海勒认为最重要的是:“后人类”总是试图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安排和塑造人类,以便能够与智能机器严丝合缝地链接起来。(1)[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在这里,智能机器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后人类产生了密切的关联。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智能机器的出现,才真正导致所谓的“后人类”在身体性存在与计算机仿真之间没有了本质的不同或者绝对的界线。对于后人类与智能机器的内在关联,海勒认为:“我把人类和后人类理解为从各种技术、文化的不同外在形态中显现出来的历史性的特定结构。我对于人类定义的参照点是自由人本主义传统;当计算替代占有性个人主义作为存在/人(being)的基础时,后人类便出现了。这种变化进一步促使后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2)[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5页。原书译为“这种变化这一进步促使后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应为“这种变化进一步促使后人类与智能机器无缝连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能为后人类传播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技术基础。但后人类与智能机器之间是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结合,这种高度的“结合”甚至模糊了生物学的有机智慧与具备生物性的信息机器之间的差异。
从技术层面看,计算机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让机器能够对信息进行符号化处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变成了一个可以协商的问题。海勒将这种新的人机关系界定为“表现的身体”和“再现的身体”,并通过计算机技术勾连起来。她认为,“表现的身体”以血肉之躯出现在电脑屏幕的一侧,“再现的身体”则通过语言和符号学的标记产生于电子环境中。当两者通过灵活变化的机器界面结合起来,主体也就成为所谓的“电子人”。在此,海勒从理论层面将人工智能、虚拟身体与电子人等因素融为一体,建构了一种所谓的后人类感知模式。而这种融合人工智能与人类生物属性的“感知”方式,构成了后人类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
海勒的这种后人类观念对许多传播学研究者产生了影响。比如,英国学者尼古拉斯·盖恩(Nicholas Gane) 和戴维·比尔(David Beer)在讨论网络、信息、交互界面、档案、交互性和仿真等问题时,就直接以海勒的理论分析关于信息的物质性或具身性本质。(3)[英]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刘君、周竞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10页。中国学者张磊在相关研究中,也将“智能媒介”定位为人类社会性传播中的新角色,他从媒介哲学层面追问这样一系列问题:智能媒介与人类有什么相似性和差异性?智能媒介是一种全新的传播主体吗?它将带来何种革命性变化?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张磊援引海勒的观点指出:后人类是反思并超越了人类主体性之后的存在状态,它的核心是人与智能机器的交互。(4)张磊:《拟人、非人与后人类:论人工智能媒介物与人类的相遇》,《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0年第6期,第3-17页。张磊对于海勒观点的引述,说明中国学者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海勒的后人类理论对传播学研究具有的启发意义。但从整体上看,当代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里,依然缺乏对海勒及其“后人类”传播观念的系统考察和深度思考。笔者将在海勒诸多关于“后人类”的论述中,深入挖掘和归纳其中与传播研究相关的部分,并将其作为一种传播观念进行系统化的阐述,以此探讨海勒的后人类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启发意义。
二、信息论与控制论:后人类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
关于何为“后人类”,学界未曾有过一个权威的界定。面对这一难题,海勒从“信息”这一最基本的范畴介入关于“后人类”的研究,以著名的“图灵测试”引出研究者们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答的问题:智能机器如何消除具体形象?在海勒看来,为了获得能够思考的机器,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是“信息形态的控制”(5)③④⑤⑥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4、25、6、19、25页。。而为了更好地论述“信息形态的控制”,海勒选择了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作为“后人类”理论建构的基本框架。
在海勒看来,香农信息理论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将信息定义为一种没有维度、没有物质、与意义没有必然联系的概率函数。它是一种模式 (pattern) ,而不是一种存在(presence)”(6)③④⑤⑥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4、25、6、19、25页。。从某种物质的基质上将信息抽取出来,就意味着信息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不受语境中的变化影响。“这种行动所获得的技术杠杆/优势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对信息进行形式化处理,使之成为一种数学功能,香农就可以在自己强大的理论归纳中开发很多定理,完全不用考虑具现信息的媒介”(7)③④⑤⑥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4、25、6、19、25页。。正是香农对信息的重新理解和定义,使得在“后人类”理论中,“信息(心智)与物质(身体)相分离”具备了可能性。在香农的信息理论基础上,传统的以人本主义为主体的人机关系学被颠覆了。“心智”作为一种信息有可能脱离人的肉身,甚至人本身也被“理解为一套信息程序”(8)③④⑤⑥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4、25、6、19、25页。。因此,海勒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非生物媒介中安置信息——人类的心智,那肉身的存在就显得有点多余了。甚至可以说,在后人类的人机关系观念中,传统作为承载“心智”的肉身已经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被替代,其重要性也就被大大贬低了。在追溯信息论的学术史中,海勒发现,尽管香农的信息理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将信息与语境相分离必然导致信息与意义的切割,这很可能使香农的信息理论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技术条件下使用,而不是普遍适用于一般的传播学领域。海勒清醒地意识到:香农的信息理论对传播的物质基础分析远远不够。“后人类”理论要在传播学中得以适用,首先必须解决“信息与环境分离”的问题,这在20世纪早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技术问题。但海勒认为,“二战”后信息传播技术的高速发展,恰恰可能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自“二战”后到20世纪末期,“从DNA编码到全球性的计算机网络,所有的物质对象都被信息流渗透贯穿,技术与感觉的链接也无处不在”。在这个新的时代,“将信息具体化为自由流动的、去语境化的、可量化的实体(entity)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个实体将成为解开生命与死亡之谜的关键之匙”。(9)③④⑤⑥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24、25、6、19、25页。随着这个“时机”的成熟,香农面对的“信息与环境分离”难题得以破解,而信息理论重新介入传播研究也就具备了可能性。
如果说香农的理论界定了信息的基本概念,那么,维纳的控制论则把人与系统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信息交换。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二战”之后,通讯和传播技术日益发展,不断推进各种控制技术的重组,最终引发了计算机技术革命。在此背景下,维纳于1948年出版了后来影响深远的《控制论: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在这本著作中,维纳把控制论作为研究机器、生命社会中控制和通讯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在维纳看来,信息是控制的基础,一切信息传递都是为了控制,而任何控制又都依赖于信息反馈才能实现。维纳的理论将信息论与控制论深度融为一体,这成为海勒建构“后人类”理论的重要基础。
海勒通过对控制论概念的研究发现,人的肉身作为信息体现(embodiment) 的传统观念正被一步步消除。她不断追溯“天生的自我”与“控制论的后人类”之间存在的连续与断裂,却不是为了恢复“自由的主体”。相反,海勒认为,这是一个可以采取干预行动的关键契机,以免这种“分离”(dieombodiment)再次被改写进各种强势的主体性概念中。因此,海勒把自由人本主义主体的解构视为一种机会,借此重新考察在控制论讨论中将继续被抹灭的主体。(10)④⑥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112、152页。而恰恰是在这种带有批判性的考察过程中,海勒将“后人类”理论与传统的控制论进行重新整合,从而对传播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影响。如果说,控制论“从人与机器对话的角度出发阐释了现代传播的基本作用过程”(11)陈卫星:《传播的观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那么,在智能传播时代,这种新的人机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对话”层面,而是超越了维纳当初所设想的信息控制模式,建构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传播新主体”——电子人。
三、电子人:后人类传播的新主体
海勒关于后人类传播新主体——“电子人”的论述,主要借鉴了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理论。早在1985年,哈拉维就在著名的《赛博格宣言》中,将“赛博格”定义为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赛博格既是虚构的生物体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体,是一种打破了传统物种分类界的“电子人”。(12)Donna Haraway,“A Manifesto for Cyborgs: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Socialist Review 80,1985,pp.65-108.海勒在论述后人类理论时多次引用《赛博格宣言》中的内容,指出“电子人”将控制论装置和生物组织融合在一起,颠覆了人类与机器的区分;用神经系统的反馈代替认知,挑战了人与动物的差异;利用反馈、等级结构和控制等理论解释恒温器和人的行为,消除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区分。(13)④⑥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112、152页。这意味着在后人类时代,一种传播新主体正在产生,这种观念在中国传播学领域也获得了认可。比如孙玮将这种源于后人类思想的“电子人”视为“当前技术与人的融合所塑造出的新型传播主体”,并认为这“昭示一个颠覆性的事实,即传播的主体已经从掌握工具的自然人转变为技术嵌入身体的赛博人。因此,媒介融合不可能仅仅从媒介本身理解,而是进入了重造主体的阶段”。(14)孙玮:《赛博人: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融合》,《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第4-11页。
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指出:就技术性意义而言,在20世纪末大约有百分之十的美国人口堪称“电子人”,比如那些使用电子心脏起搏器、人造关节、药物注射系统、植入角膜晶体和人造皮肤的人;而从隐喻的角度讲,还有更多的人参与了与“电子人”相关的职业,其中包括将电路与屏幕连接起来的计算机操作员、手术时接受光纤显微术引导的神经外科医生,以及各地游戏厅年轻的游戏玩家等等。(15)④⑥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112、152页。当然,以上关于“电子人”的界定,大多是从技术层面——也就是所谓的“科学产品”进行的。对于海勒来说,仅仅从“科学产品”这一层面论证“电子人”的重要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文化产品”显然更为重要,必须重视“电子人如何被创造为一种文化偶像/标志和技术性人工制品”(16)③⑤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257、32页。。为了更好地描述“电子人”这一新主体在后人类时代的表现,海勒将各种科幻作品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描摹。比如,在科幻小说《血色音乐》(BloodMusic) 中,电子人的产生是通过彻底重组人类的身体实现的,变成了一种长生不死的结合体。《终极游戏》 (TerminalGames) 描述的“电子人”则是一种对人体具有控制功能的“智能机器”,对人类产生了致命威胁。在《伽拉忒亚 2.2》 (Galatea2.2) 中,存在着两种具有独立意识的“电子人”,具体表现为“交感神经人工智能”,其中一个是具身化的生物,可以在物质世界中运动;另一个则是某种分布性的软件系统,尽管具有物质载体,但在任何类似于人类的世界中都不具有身体。而《雪崩》 (SnowCrash) 讲述的是人类受到计算机病毒的影响,变成了只能执行被输入的程序而无法拥有其他任何选择的机械化的“电子人”。
海勒这种基于科幻作品进行研究的方法受到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影响。福柯在关于知识“考古学”的论述中,关注的往往并非那些具体事件是否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而是试图追寻这些事件据以发生的基础。在福柯看来:“经验知识在特定的时空也可以是有明确的规则的,谬误与真理都可以遵循某个知识译码的种种法则,非形式化的知识的历史本身也拥有一个系统。”(17)[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译者的法”第5页。显然,海勒将科幻作品中所建构的后人类世界,视为福柯所说的那种关于某个特定时空的“知识译码”或者“非形式化的知识”。恰如海勒自己所言,这种人文学科领域的话语分析,与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将身体视为话语系统的一种游戏”恰恰是一致的,其中隐含着一种后现代的意识形态:“身体的物质性是第二位的,身体编码的逻辑或者符号结构是第一位的。”(18)③⑤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257、32页。
正是由于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构成信息的“数字化符号”有可能脱离它的物质形式,符号技术与人体彼此镶嵌在一起,从而导致作为后人类传播新主体的“电子人”的形成。(19)Hayles,N.K., How We Think:Digital Media and Contemporary Technogenesi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2,p.34.由于这种所谓的“电子人”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因而海勒认为这是物质对象被信息模式贯穿的一种“文化感知”(cultural perception)(20)③⑤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2、257、32页。。通过科幻作品,人们想象和建构了以人工智能和虚拟技术为代表的“电子人”这一新的传播主体,并对其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入的反思。
四、后人类传播与媒介“物质性”的问题
在传统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中,物质与精神、物与人被视作完全不同的范畴。也就是说,物质在本质上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受此观念影响,传播物质性的研究主要针对具有实体的介质,比如书籍、广播电视设备、计算机硬件等。正如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所说,“媒介物质性”指的是媒介系统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资源、支持日常交流活动的设备,以及构建和维护这些基础设施和机器所需的劳动链。(21)[英]格雷厄姆·默多克著,刘宣伯、芮钰雅译:《媒介物质性:机器的道德经济》,刘宣伯、芮钰雅译,《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第97-102页。相较之下,关于媒介内容、文本、意义、隐喻、话语,以及网络空间、虚拟现实等问题的研究,则被视为“非物质性”层面的研究。但在后人类时代,虚拟技术及其造成的“虚拟现实”对信息传播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那么,媒介的“物质性”问题是否也随之发生变化与重构呢?这是传统传播学理论难以回应的问题。
维纳的“控制论”作为早期传播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将世界的“信息性模式” (informational patterns) 与“物质性客体” (material objects) 紧密结合起来,并将其阐释为一种任何有效的物质性理论都必须面对的标准。海勒认为,从纯理论的角度讲,信息在概念上不同于表达信息的符号和标记,比如报纸或者电磁波,“说它是一种存在呈现,毋宁说它是一种模式,取决于传播构成信息的编码元素的可能性”。(22)④⑤⑦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35、3-4、46页。在这里,海勒借鉴了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 (Friedrich Kittler)的理论资源。基特勒将媒介视为广义上的“文化技术”,开创性地将技术、话语和权力等问题结合起来,探索媒介何以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23)张昱辰:《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话语网络”与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期,第76-87页。基特勒还把“话语网络”定义为“技术与机构的网络”,使得一个特定的文化得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24)Kittler, F., 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369.海勒将此观点运用到对“后人类”的研究,认为计算机中的文本作为一种视觉呈现,不论其动态还是其概念,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操控;但是如果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客体,则难以做出任何改变。也就是说,虽然物质性界面发生了改变,但模式/随机的辩证关系并不能消除物质世界,信息的效力依然源于物质性的存在基础。(25)④⑤⑦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35、3-4、46页。在这里,海勒将作为媒介的计算机及其物质性,与人的“经验”建立了内在的关联。
在界定“后人类”时,海勒认为最重要的是将人的身体与智能机器严密地链接起来,这将导致“有关主体性的一些基本假定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26)④⑤⑦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35、3-4、46页。在建构这种后人类的物质与身体关系时,海勒还接受了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的观点。麦克卢汉将工具作为人类的一种技术“假肢”,认为“媒介作为我们身体和神经系统的延伸,构成了一个生物化学性的、相互作用的世界;随着新的延伸的发生,这个世界必须永不停息地谋求新的平衡(27)[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4页。。”这种构想可“清晰地看出电子媒体带来的重新建构甚至可以改变‘人’的本质”(28)④⑤⑦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4、35、3-4、46页。。海勒认为,麦克卢汉的这种思想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后人类的传播观念。
盖恩和比尔在《新媒介:关键概念》中指出,正是在海勒的影响下“当代媒介理论的研究焦点也有了一个微妙变化”,开始聚焦考察“仿真与其物质基础之间的深层联系”,比如硬件和软件、身体和意识、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等的相互关系。(29)[英]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刘君、周竞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8-99页。这种媒介研究焦点的变化,在智能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随着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的行为、活动、身体状态等以多种维度被映射在虚拟世界里,尤其是VR、AR、XR等技术将改变虚拟空间的呈现方式,曾经以“离身性”为主的虚拟空间也越来越多地体现出“具身性”特征。(30)彭兰:《智能时代人的数字化生存——可分离的“虚拟实体”、“数字化元件”与不会消失的“具身性”》,《新闻记者》2019年第12期,第4-12页。而当我们在研究这种现象时,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后人类时代传播的物质性问题。
五、结语
在这个智能技术迅猛发展、人机交互程度前所未有、人造生命不再稀奇的时代,对于所谓的“后人类”,有学者秉持悲观的看法,甚至认为后人类是反人类的和毁灭性的。比如福山就曾认为:“后人类的世界也许更为等级森严,比现在的世界更富有竞争性,结果社会矛盾丛生。它也许是一个任何‘共享的人性’已经消失的世界,因为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结合,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31)[美]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黄立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17页。而海勒则相当宽容,她指出:“人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发明智能机器,而在于如何在全球化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也许还包括碳与硅的公民。”(32)Hayles,N.K.,My Mother Was a Computer: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p.147-148.海勒这种对后人类的乐观和超然态度,在传统的传播批判理论看来无疑是离经叛道的。毕竟,对于传播批判理论而言,后人类更像是一种技术对于人本身的入侵和异化。后人类时代“人机结合”的紧密程度,早已远远超越了早期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前辈学者所能的想象。这意味着随着智能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传播理论体系已然遭到新的挑战,其阐释能力也面临着新的危机。对此,海勒有着清醒的认知,她认为:传统伦理研究关注的主体主要是拥有自由意志的个体,但这样的观点已经不适用于处理自主运行的技术设备,更不适用于处理将认知和决策权分布在整个系统中的复杂的人类技术组合。(33)Hayles,N.K.,Unthought:The Power of the Cognitive Nonconscious,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p.4.海勒运用文学、传播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各个领域的理论,在解剖新兴的“后人类”现象时,也构建出一个更为复杂的“后人类”理论体系。就像海勒自己所描述的:“我被带入了一个迷宫,进而开始了一次长达六年的冒险旅程,在有关人机关系学的历史档案中摸索前进,采访计算机生物学和人工生命学的科学家,阅读关于信息技术的文化和文学资料,拜访研究虚拟现实的实验人员,钻研各种关于控制论、信息理论、自生系统论、计算机仿真和认知科学的技术论文。”(34)[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2页。在此基础上,海勒通过对人工智能、电子人与媒介物质性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探讨,以一种超乎想象的学术视野和理论建构能力,为后人类时代的传播研究建构了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