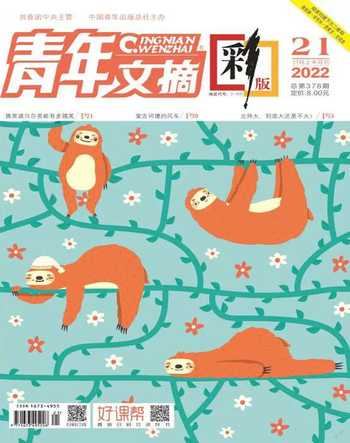长江最后一条白鲟,我们追丢了
陈诗欢

白鲟被称为“中国淡水鱼之王”,迄今已存在一亿五千万年。曾经,白鲟只是长江里的普通鱼类,然而,它们的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起急剧下降。2003年初,宜宾长江段一条白鲟被渔民误捕,经救护后成功放流。这也成了白鲟和人类的最后一次会面。
危起伟全程参与了这次救护,他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鲟鱼专家组成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所研究员,一生都从事长江濒危珍稀鱼类的研究与保护工作。以下是他的讲述。
养了29天,还是死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白鲟是在2003年前后,距离我上一次见到白鲟已经过去整整10年。
2002年12月,我们在南京下关的长江口发现了一条白鲟,当时特别激动。我们开了一辆吊着活鱼运输箱的东风车,一路从荆州开到南京。当时这条白鲟遍体鳞伤,鳍条是卷曲的,一看就是被船打的外伤,而且它的肚子很大,整条鱼翻了过来,说明它鳔里充了气。
按照以往救助鲨鱼的经验,需要拿一根塑料管子捅进鱼肚子里放气。但这可是珍贵的白鲟啊,我们哪敢。后来我们就拿兽医用的针头和注射器插进去,再把注射器拔出来,气一下子排掉,鱼肚子下去了,鱼“唞”地一下就翻正过来了。
这条白鲟有3.3米长、117千克重,我们把它运到昆山一个中华鲟养殖基地,放进一个直径16米、深2米的圆池里,它就游起来了。
每天看着它在池子里打转,伤口一天天愈合,真的特别高兴。但到了12月下旬,气温下降得厉害,池子都冻冰了。我们准备给池子加盖彩钢板保温,可能是敲敲打打的声音和新建材料的油漆味让白鲟很躁动,它在游动的过程中,长长的鼻子不小心插到一个缝里,又拼命地一退,鱼一下子就翻了。

2003年1月,危起伟等研究人员在四川宜宾市抢救被误捕的大白鲟

1994年,邮电部发行《鲟》特种邮票一套4枚,图名分别为“鳇”“中华鲟”“白鲟”和“达氏鲟”
翻了以后怎么也抢救不过来,白鲟最后还是死了。当时团队里所有人都哭了。十几个人又开车又熬夜,拼了命把鱼救活,养了29天,看着它一天天变好,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这条白鲟其实承载着很多人的希望。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养活过这种鱼。新中国成立前,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因为没有救活过这种鱼而遗憾终身。他去世前有个心愿,如果哪一位后人把鱼抓到了养活了,一定要告诉他。我们最开始救活了这条白鲟时,这位老教授的后代辗转联系到我们,把当时的报道拿到老教授坟头上烧了,但没想到最终还是留下遗憾。
最后的白鲟
第二年1月24日,我们在四川宜宾遇到那条“最后的白鲟”。吸取之前的教训,我们没有将它带回去人工驯养,而是标记后放流回长江,然后追踪它找到它们的产卵场,再通过人工繁殖实现物种的延续。遗憾的是,我们追丢了白鲟的信号。
这是一条3.35米长、150.9千克重的雌性白鲟,体内有数十万颗鱼卵。我当时追着信号,发现它先是往下游游了一段,然后加速逆流向上游游。中间有一段,我收到的信号非常强,原来这家伙就在船的旁边跑起来了。它跑起来,真是壮观啊!半个身子在水面上走,“咻——”地跑着,跟着船玩儿。
白鲟是一种很有灵性的动物。它们的吻(突出于面部的嘴鼻部位)很灵敏,布满了神经组织细胞,比我们人类的二维码识别还精确,能通过闻气味,在长江无数支流中,准确无误地找到洄游产卵地和繁殖场。这条白鲟好像知道有人跟踪似的,就在那里跟我们跑着玩儿。
1月29日晚上快10点时,这条白鲟加速游进长江九龙滩激流段,我们的追踪船触礁了。船上三个人都差点没命,也没办法继续追踪了。船修好后,我们又来回了好几趟,但都没有接收到信号,白鲟就这样跟丢了。
那之后10年间,我们还在长江上组织了8次大规模的探测和试捕,都无功而返。原本我还抱着白鲟会回来的希望,哪知道这竟成了我和白鲟的最后一次相遇。
保住了种,就保住了一丝希望
过去的事情很悲伤,回忆起来很傷心。我总是跟别人讲,白鲟的灭绝是一个教训。如果1993年之前,我们就开展主动捕捞、研究习性,并且准备好设施,进行人工繁殖,可能今天白鲟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但直到2003年之前,我们都是在打“无准备之仗”。
我总觉得,2002年、2003年最后接连出现两条白鲟,像是这个物种的回光返照、拼死一搏,让我们意识到长江中这些鱼类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何种危急的程度。好在,现在我们对中华鲟的一系列保护工作和研究课题,都陆续开展起来了。
198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一年后开始接手中华鲟的野外调查。接手时,我只有2万元经费。拿着这2万元,我租了一艘“破木船”,每年有2个月吃、住都在船上,收购渔民捕捞的铜鱼、黄颡鱼等食卵鱼类,看它们的肚子里是否有中华鲟鱼卵,再结合这些鱼类生活的江段,大致推断中华鲟的产卵场。
为了寻找中华鲟鱼卵,我一个人每天要解剖几百斤鱼。最终,1993年我找到了中华鲟的新产卵地,就在湖北宜昌江段,这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中华鲟的稳定产卵场。1996年,湖北省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中华鲟自然保护区。
对我们科研人员而言,保住了种就保住了一丝希望。只要鱼种还在,我们就可以做人工繁殖,野外放流,就有可能重新形成野外种群。这么多年下来,我们基地现在保有92条野生中华鲟,还有800多尾子一代(野生中华鲟经人工繁殖后得到的后代)。
鱼类不会说话,只能靠人替它说话
白鲟灭绝,大家都关注到了,但可能比较少人知道,长江鲟的濒危程度从“极危”被提级成“野外灭绝”,而目前处于“极危”状态的中华鲟事实上也已经连续5年没有发现自然产卵了,中华鲟的自然种群也岌岌可危。
这些年,长江水温升高使得中华鲟性腺发育延迟,自然繁殖窗口进一步被压缩。栖息地的人为破坏,导致鱼类能吃的食物变少。来往船舶带来的震动和噪音,使得中华鲟浮出水面时也更容易被船舶误伤。
很多生物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鱼类不会说话不会喊,只能靠像我们这样的人替它说话才行。
2020年起,长江开始实行十年禁渔,这的确能减少对鱼类的直接捕捞伤害,但对这些鱼类而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生态环境的恢复。现代经济中,鱼和人无可避免地要利用同一个空间,理想化的情况下,我们希望一些鱼适应后,可以做到不怕人,人也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做自己的事。但另一方面,人也不要伤害鱼,人要让鱼走,让鱼能够有地方藏匿,有东西吃,能去繁殖。
其实我们发现,人类只要把水文、河床、地形等这些条件营造好,鱼自然就会来繁殖。理想的情况就是人要给鱼留鱼道,然后船也有自己的航道。船走船道,鱼走鱼道,大家都能自由地畅游在长江上。
栋梁//摘自GQ报道微信公众号,本刊有删节/
——以泉吉河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