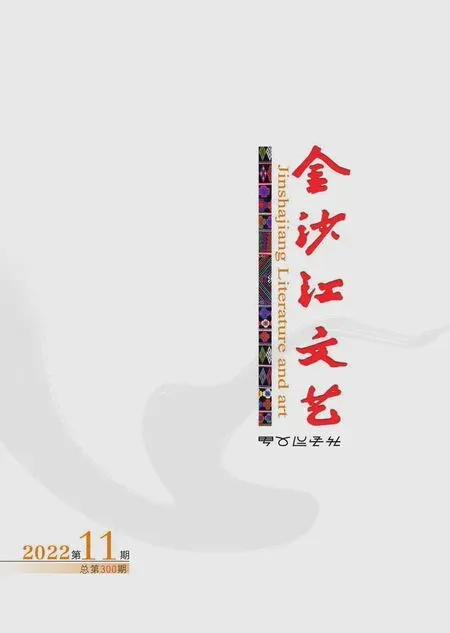谁是小筱
钱会芬
1
我是在那天下午看到那张画的。
那天是正月初六,是我回到老家的第八天。春节已经过完了,离我们寒假结束还有十多天。想到一收假那种忙碌紧张的日子,别说回家看父母,连打个电话都要找时间,我决定再陪父母几天。连续几天阳光灿烂。睡午觉起床后,我打算去看看我家的老房子。我父亲说正月十五过后,我家的老房子就要卖给我大伯家了,价钱比同等条件少近四分之一。我父亲说,少点就少点吧,以前两家人同在一个院子住了几十年了,何况又不是卖给外人。父亲本是不愿意卖老房子的,我家那时日子已经比较宽裕,不缺那点钱,只是大伯家两个儿子没能力另盖新房,于是大伯就找我父亲商量,希望能把我家的老房子买过去,和他家的一起翻修后接着住。这可不好拒绝,就像不愿意成人之美似的,于是我父亲只能答应了。那是我父亲的衣胞之地,他在那间逼窄昏暗的过道里送走了我祖奶奶,迎来了我们姐弟五人的降生,之后又送走了我奶奶。我12岁那年,家里盖了新房,我们就离开了老房子。
幽深的巷子里静悄悄的。我穿过那道门楣上有龙腾云雾凤呈祥云图案依稀可辨的大门,左拐,就进了那间过道。在我记忆中,过道一直是我奶奶住,直到她去世。我奶奶去世前那些年,过道的阁楼上摆着她的棺材,虽然被我父亲用许多草帘子啦草席啦杂七杂八的家什遮盖得严严实实,但还是让我们姐弟几个心惊胆战,一般不敢上楼。这间过道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对那具棺材的恐惧,那种感觉成了我长大后的梦魇。过道的斜对面是一间厢房。这间厢房听我奶奶说,以前是借给一家因为修白鹤水库占了他家的田地,所以搬到我们村里来的迁移户住,到我7岁那年才归还给我家。厢房阁楼采光比较好,我奶奶说我和弟弟读书写字需要有亮光,于是我父亲母亲就带着我们搬进了厢房。厢房房顶装着亮瓦,楼上有一面很大的窗户。那时的房子没有玻璃窗,用几块木板装在凹槽里,需要亮光的时候把木板梭开,不需要时把木板梭拢,就像现在的梭窗。我和弟弟还有我们的伙伴每天放学回家,就在厢房阁楼上的窗户前写作业,看小人书,胡乱涂鸦。我、秀秀和惠惠上学时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放学后我们三人就到我家厢房阁楼上写作业,写完作业后,秀秀和我经常躲在我家厢房阁楼上玩“改股”,我们那时就称那种游戏叫“改股”,知道它另外一个名字叫“翻绳”是后来的事。惠惠不和我们玩,她总说家里有事,收好书包就急匆匆回家了,好像她家永远有做不完的事似的。
2
我顺着楼梯爬上阁楼。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屋顶的亮瓦投进暖黄色的光,楼上的物什还是我熟悉的样子。我把窗户完全梭开,眼前顿时亮堂起来。从楼口往里并排摆着三张床,依次是大姐和二姐的,三姐和我的,隔开一点是我父母亲和弟弟的。床是木板床,很窄,上面铺着草席。搬新房子后,父亲说我们长大了,旧床睡不下了,就没搬走。草席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土砂子,还有很多老鼠屎。父母亲床头上方的木板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语录,原来那种鲜亮的红色底子,现在已经变成了石灰白,但是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楚,我盯着看时,不知不觉就念出了声: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那时我母亲经常在我耳边说的一件事就是我一位远房表叔家的女儿,八岁就能背10多条毛主席语录。我母亲说,不用你背十多条,把这条记住就行。于是我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盯着这张红底白字的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除了床头那面是木板墙外,其余三面都是土墙,墙面用面浆裱了一层报纸,报纸上有几块深黑色的痕迹,那是我们晚上点着煤油灯看小人书熏黑的,很多地方报纸已经剥落,露出深褐色的墙面。
这个不算宽敞的空间里弥漫着我熟悉的气息,我在三姐和我的床前站了一会,掀开草席的一个角落,我想在床上坐一会儿。就在那时,在草席下面,我看到了那张画。
画是用铅笔画的,一张36开的小楷纸上,画着一个人形,从脑后稀疏飘散的头发来看,应该是一个女人。她有着细长的脖颈,头抬得很高,像是努力寻找远处的什么,最让我诧异的是她的小腿以下被密集的弯曲的线条遮挡住,因此看上去这个人就像是从一片什么东西里冒出来的似的。这是谁画的呢?整幅画的内容就是那个三分之二的女人和女人小腿下的线条,除此之外再没别的;笔迹很细,是那种笔芯削得很尖的铅笔留下的;线条没有圆润感,很多地方都画走形了。从这三点来看,我断定这是一个孩子的涂鸦。纸面已经发黄,但线条依然清晰,很显然,这幅画放在草席下面后一直没被挪动过,要不铅笔的笔迹就模糊了。
太阳已经偏西,阁楼的光线变暗了。我把画拿在手里仔细看,发现画的右下角有两个极小的铅笔字,字迹和画中的笔迹一样,极细,颜色极深,猛一看就像两个紧挨在一起的小黑点。这两个字是:小筱。我依稀记得“筱”这个字读xiǎo,好像是小竹子的意思,回家翻《新华字典》一查,我记得没错。很显然,小筱就是画这幅画的人,而且根据这个字的意思,应该是个女孩,谁是“小筱”呢?不可能是我大姐二姐,因为当我们从过道搬到厢房住时,她们都已经到县城读高中去了。我三姐呢,她在离家八九公里的镇上读初中,每个星期日才回家一次,也就在家待两三个小时,所以小筱只能是我的伙伴,她既然把这幅画藏在我们的床上,说明她跟我关系很密切,而且到过我家的阁楼。我想了又想,在我的记忆中,我儿时伙伴中没有名字叫小筱的,那时村子里就那么十来个女孩,到我家玩过的女孩也就只有秀秀和惠惠。
谁是小筱?
3
我突然想起一些事。如果你和我一样经历过那个年代,你就知道那时我们农村孩子的名字都是父母随口取的,名字里带着父母对土地最直接的感知,女孩子的名字如花呀、梅呀、秀呀、香呀,男孩子的如树呀、林呀、石头呀。我们进学校识字后,发现书里那些孩子的名字和自己的迥然不同,如:赵伟红呀、刘东方呀、张振国呀,不同在哪里说不清楚,总之不是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那些尘埃里的花草树木石头,而是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那么美,像天空中飘逸轻盈的云朵,又像绚丽灿烂的彩虹,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心驰神往,于是我们怀着既紧张又甜蜜的心情给自己另外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包含着我们自己的某种愿望或心情,是父母所不知道的。比如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喜欢“勇”这个字,读着响亮,而且能给人一种什么都不怕的胆量,按照辈分,我们女孩子是“会”,于是我就想给自己取名叫“会勇”,当我说给三姐听时,三姐笑弯了腰,说咱们大伯就叫“家勇”呀,亏你一个姑娘家想得出来!村里有一个叫石柱的女孩给自己取的名字叫“璐璐”,和这名字一样,她也确实是一个活泼伶俐的小姑娘。那么,小筱,也应该是一个女孩子给自己取的名字。
我把那张画带回了家。接下来的几天我总在琢磨,她为什么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那么小呢?不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如果不想让别人知道这张画是她画的,她可以不写名字,可她为什么又要把名字写上去呢?难道是她既希望别人知道这张画是她画的,出于某种原因,又不希望别人知道这张画是她画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又让我想起一件事,那年我们村搞包产到户时,我家分到一头一岁多的小母牛。这头牛瘦骨嶙峋,毛皮粗糙,而且还是甲甲蹄。牛蹄饱满呈圆形,形状像螃蟹身体的,我们称为螃蟹蹄。甲甲蹄窄长,蹄尖扭曲,像裹脚老太的三寸金莲,看上去很丑。总之那头牛长得真难看!它还喜欢打背角,常常在吃着草的时候突然转头用角顶脊背,让我们放牛时不能骑在它的背上。最令我和弟弟讨厌的是它太胆小。村里的牛放到山上后,领头的牛带着牛群在山上吃草,孩子们就可以找一块平坦些的地方打扑克,嬉戏打闹,可是我家的牛因为害怕被别的牛欺负,吃草时总是远离牛群,让我和弟弟因为担心它祸害人家的山地而要时时跟着它,不能和伙伴玩耍。回家时,它不敢走在牛群里,而是走在牛群前面五六米的位置,跟在它后面吧,又怕身后的牛群上来顶着,不跟在它后面吧,又怕它去啃庄稼。别人家一个人放几头牛,我家是两个人放一头牛还搞得手忙脚乱,我和弟弟恨死它了。不过,相处久了,我们开始觉得它很可怜,因为它丑,别的牛经常欺负它,它不敢和其它牛一块吃草,于是我们不再和别的孩子一起放牛,而是另外找个地方,让它安心地吃草、晒太阳、甩着尾巴悠闲地赶苍蝇。当它反刍时,它就用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看着我们,眼神温顺而且忧伤,仿佛有话要对我们说似的。好几次,它在山坡上从容地吃草,嘴边发出均匀的唰唰声,阳光照在它的身上,它背上的毛反射着金色的光,我坐在山坡上,吹着习习的清风,有蝴蝶在草帽旁飞来飞去,我和它都那么安详和惬意,仿佛时间都停止下来。在我们的照料下它渐渐长胖起来,也好看起来。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人,父亲说是来买牛的,我和弟弟要读初中了,没时间放牛,要把牛卖了。我大吃一惊,赶紧找弟弟想办法,这牛好容易才长胖一点,如果被卖了,新主人对它不好怎么办?它要受多少罪,吃多少苦头啊!尽管我们都揪着心,可是却不敢对父亲说不愿卖牛,那个时候,父母在我们心里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我父亲,平时不苟言笑,但他让我们感到的威压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和弟弟听到那两个买牛人和我父亲在厨房里吃饭的声音,吃完饭,那两个人就要把牛牵走。巨大的忧伤和绝望包围了我们,我和弟弟互相对视着,那么无助。最后,我找来一截粉笔,在墙上写了一句话:我家不卖小母牛。想了想,又加上一句:不要买我家的牛。我们不敢和我父亲说不卖牛,但我们多么希望他从这间屋前走过时能看到我写的字,知道我们的想法。但那也只是我们小孩子的想法而已,小母牛还是被牵走了。
根据我的经历,很有可能小筱既想向别人表达某种意思,又不敢说出来,所以就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写出来,但又写得非常小,企望别人能发现。
谁是小筱?
这张画要表达什么意思?
4
那天正午,我在院子里晒太阳时看着那张画出了神,忽然,我发现在画正上方的空白处,隐约有半个中指头顶大的一块稍微泛灰的痕迹,我把画放到光线最亮的地方,用干净的布把痕迹轻轻擦拭了一下,发现那个地方有写过字的印迹,我不断变化着角度细细琢磨,从笔画之间的位置关系和印迹的结构来看,应该是“希望”这两个字,那么也就是说,这幅画叫“希望”。根据我的判断,小筱给这张画取名为“希望”,在给画写上名字后,又慌忙把它擦了,字迹是看不出来,但是因为笔芯太尖,笔尖画过的痕迹还在。
当我脑子里蹦出“希望”这两个字时,我怔住了,希望!对于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希望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以至于人们不知什么时候都把它遗忘了,我们的父辈习惯了心安理得地接受眼下缺吃少穿的境况,而我们小孩子呢,也把在父母威压下的凄惶当成了理所当然。然而一个叫小筱的女孩发现了它,在某一天,她小心翼翼地削尖铅笔,认真地把它画下来。我能想象,那是一个午后,那天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多,小筱写完作业,看了看四周,伙伴们不在身边,也许他们写完作业去外面玩耍去了,她迅速拿出一张空白的小楷纸,认真地画了起来,因为那个画面经常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所以她很快就画完了。她在画的正上方写下了“希望”两个字,又极其小心地在画的右下角写上了“小筱”这个名字,然后她想了想,用橡皮把“希望”那两个字擦了,就在这时,她听到有人上阁楼的脚步声,小筱随手把画藏了起来,就这样,这张叫“希望”的铅笔画被压在床角,直到30多年后的那天下午我看到了它。我突然明白,小筱画这幅画,是想表达一个人抬着头看向远处寻找希望,而脚下的那些密集堆叠的线条,是绊住了脚的某种东西。是什么东西绊住了小筱寻找希望的脚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些深奥,也许只有小筱自己才能解释清楚。
可是,谁是小筱?
5
我思来想去,既然已经确定这是一张女孩子的画,而且到过我家阁楼的女孩只有秀秀和惠惠,那小筱就应该是她们俩人中的一个。
我首先想到的是惠惠。
惠惠和我一样,在家排行老四,也和我一样头上三个姐姐,后面一个是弟弟,也就是说我俩的母亲都是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个才是男孩。尽管这样,我的父母对我们姐弟五人虽然管教得极为严格,比如大人说话我们不许插嘴,不许向大人提任何要求等等,但我的父母对我们从不厚此薄彼。惠惠可没有我幸运。那时惠惠的大姐二姐已经出嫁了,三姐不满十五岁就被人贩子拐跑了,惠惠的父亲重男轻女,对她弟弟百般溺爱,对惠惠却横竖不满意。那时大人忙于生产队的活计每天早出晚归,家里的事都是小孩子干,惠惠的弟弟除了读书就是玩,家里喂猪鸡浇菜水、挑水煮饭的事都是惠惠一个人做。惠惠还经常被她父亲打,好几次我们看到惠惠脸颊上有手掌印,或者嘴巴肿着,我们都知道是她父亲打的。当我们问惠惠时,她总是笑笑,放学后在我家阁楼上做完作业,麻利地收好书包就回家了。我听母亲说惠惠的父亲开始连书都不想让惠惠读,说一个瘪丫头读什么书,那是白糟蹋钱,反正以后都是要嫁出去的。后来看到和惠惠同龄的孩子都进学校了,在亲戚三番五次的劝说下,才勉强让惠惠读书。惠惠读书比我和秀秀用心,成绩也比我们好。惠惠有时也对我和秀秀说,她要好好读书,读好书就能离开家,去远处工作和生活,再不被他父亲打。因为惠惠读书很争气,让她父亲觉得脸上有光彩,小学毕业后,他父亲同意让她接着读初中。惠惠初中毕业后考取中专,后来在县城有了工作,离开了老家。我初中毕业又补习一年后,也考取了中专,后来在县城安了家。而秀秀呢,小学读完就被他父亲叫回去了。
既然当时惠惠那么想离开家,正好说明她是最有可能画这张画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判断不错,打算第二天就给惠惠打电话。
也许是太心切了,那晚我躺在床上,想着秀秀和惠惠,童年的一些事在脑海里像放电影似的:立春刚过,一大早我们去山里摘苦刺花,正午我们三人坐在山坡上吃各自带去的午饭:一铁盒米饭和一块腐乳。这时,一辆公共汽车,我们那时叫班车,它顺着半山腰新修的公路爬上来,我们忘了吃饭,大张着嘴巴,看着那辆车朝我们这边开过来,越来越近,它的身子那么长那么高大,洁白的车身上有两道天蓝色的线条。这辆车在明亮的阳光下,就像是从某个未知的地方突然降临的一样,那么神奇,那么漂亮!当班车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我们发现车里竟然坐着一些大人孩子。车子要把他们带到远方,远方是什么样的呢?当这个念头在我的脑海里如电光一闪的瞬间,我丢下饭盒,起身追了过去,秀秀和惠惠也跟在我身后跑。强劲的春风在车后扬起阵阵灰尘,我们三人被裹挟在滚滚灰尘里追啊追啊,直到我们摔倒在浮尘里,那辆车消失在山那边。我们对远方和未知是如此渴望。
夏天的晚上,月亮亮得吓人,村里的孩子汇集在稻场上闲聊,有一个男孩提了一个问题:什么东西最大?有人说汽车最大,有人说飞机最大,接着就有人反驳说汽车飞机都不算大,火车才大呢!飞机和火车我们没见过,但是听大人说过,我们都觉得火车当然比飞机大。这时有一个大一点的男孩说,火车也不算大,十轮大卡最大。十轮大卡什么样,连我们的父母都没见过,但是在我们非常有限的认知中,“十”是一个多么大的数字,“大”又引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十轮大卡这个词就深深根植在我们心里。那晚回家的路上,秀秀、惠惠和我兴奋地谈论着十轮大卡,想着以后如果能去看看十轮大卡到底是什么样,该多好哇!后来才知道,十轮大卡就是有十个轮子的大卡车,在我上下班途中经常能遇到。
一夜恍恍惚惚,醒来已是次日清晨。
我在手机通讯录上翻找了好一阵才找到惠惠的号码。相信你们也一样,有些人让你心里时时记着,但由于某些无法言说的原因,很长时间都不联系,我和惠惠就是这样。那个号码是好几年前就记下的了,不知道现在她还用不用。电话打过去,真巧!号码还在用,而且惠惠在单位值完班,前一天也回老家了。
我在那张画原来的笔迹处写上“希望”两个字后,揣上画到了惠惠家。惠惠变了,原来敦实的身材臃肿了,小巧清秀的脸变得又胖又圆,额头上、嘴角边的皱纹又深又密。我们说起这些年的生活,惠惠说她羡慕我有一个相濡以沫的丈夫和一个和谐的家庭,而她的幸福,早在她童年时就被他父亲毁了。我对她的话感到不解,惠惠说,她工作后,她父亲隔三岔五向她要钱,说当初供她读书的钱可不是白花的,有两次甚至跑到她的单位上,说不给钱就不走。惠惠说她没想到,她离开家了,但命运的绳索还是紧紧牵在她父亲手中,父亲在她心里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她想躲避,想寻求保护,于是她很快就结婚了,丈夫是一位警察。婚后,她才发觉丈夫性情非常暴躁而且喜欢酗酒,夫妻俩也为此经常争吵甚至动手,日子过得磕磕绊绊。不过后来父亲就很少来找她了,或许是被暴脾气的警察吓到了。惠惠说,她父亲去世前几年,她给他买过很多好烟好酒,让他享受了几年女儿对他的孝心。惠惠说,她很感谢父亲,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是父亲把她养大,供她读书,让她有了工作。她的孩子出生后,她丈夫依然酗酒,夜不归宿,孩子经常处于家里剑拔弩张的氛围中,从小性格内向孤僻,高中毕业后放弃高考,远走他乡自学美术,一个大姑娘远在外地,让她这个做妈的操碎了心,好在前年孩子回来了,虽然学无所成,但总算回到她的身边了。惠惠平静地说,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已经对婚姻失望了,前年我离婚了,解脱了,现在女儿和我一起生活,我打算给女儿租个铺面做点小本生意,我的工资也不算低,只要能维持娘俩的生活就行。惠惠如释重负地说。
我拿出那张画给惠惠看,问是不是她画的。惠惠说,小筱,谁是小筱?我那时想离开家去远处寻找希望的愿望确实迫切,因为被我父亲打怕了,不过这张画是不是我画的,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也许这个小筱就是我,你记得吗,上学后,看到课文中那些小孩子的名字真好听,我们都嫌弃父母取的名字太土气了,就想悄悄地给自己另取名字。我记得我给自己取过名字,叫什么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你和秀秀也都给自己另外取过名字啊。说到秀秀,惠惠顿了一下,眼神难以捉摸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秀秀出嫁那天,哭得跟泪人似的。
我蓦地想起秀秀结婚那天的事。那天是元旦,我们单位搞活动,中饭后我和领导请假,但我没说明请假的原因,我无缘由地担心领导知道我为参加一个婚礼请假会拒绝我,不出所料领导没有准假。搞完活动后我又向领导请假,说我家里有事,领导不耐烦地说你家里的事比集体的事重要?并冷冰冰地扔下一句“有没有集体观念”拂袖而去。我望着领导远去的背影默默流泪,我想如果我说明请假原因,告诉他那是我最好的朋友结婚,我必须去,也许他会准我假,但是,童年的经历,让我在日后的生活中总是因为担心被别人拒绝而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这种担心和不安就像一道坎,让我难以逾越。我知道,秀秀结婚那天我没去,惠惠对我心存芥蒂,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些年不联系的原因吧。
面对我的沉默,惠惠的眼神柔和下来,她让我去找秀秀问问。
6
秀秀嫁去的那个村子叫仓东,离我们村子大概六里地。我一路走着,回忆就像脚下的路一样铺展开去。秀秀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到我们读三年级的时候,她哥哥已经娶媳妇成家了,她姐姐也出嫁了。秀秀的父母很疼爱她这个幺女儿,那时生活艰难得很,我们的父母过日子都得精打细算,多数家庭到新年时,都是买黑色或者枣红色的灯芯绒布料给女孩子做新衣服,因为灯芯绒布料耐磨,老大穿不得了老二接着穿,老二长大后缝缝补补老三接着穿,一件衣服能穿七八年十年,也就是说在这件灯芯绒衣服还没破烂到缝补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好几年都穿不上新衣服。像我家有四个女孩,等我大姐二姐三姐穿过轮到我穿时,衣服早已旧得看不出颜色了。我读五年级那年,学校搞合唱比赛,要求每个班出一个合唱节目,音乐老师让我当我们班的合唱指挥。比赛前三天,班主任把我叫去,问我比赛时穿什么衣服。穿什么衣服?我说就穿这件呀,我一直不就穿这件吗?说完我还在班主任面前提了提衣角。班主任眼神复杂地看了看我,瞅了瞅我衣襟前的两大块补丁,好像有点吃力地说,指挥的事我叫别人吧,你跟着唱歌就得了。多年以后,当我面对满衣柜的衣服,却为出门找不到一件自己认为得体的衣服穿犯愁时,我才意识到似乎和这件事有些联系。
那时我们可羡慕秀秀了,秀秀每年都有新衣服穿,薄薄的小花布布料,虽然价钱远不如灯芯绒的贵,而且洗过一次就容易皱,但颜色活泼漂亮,让她整个人看上去清清爽爽的,而我们的衣服颜色又单调又沉闷,而且还不合身。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时,秀秀穿了一件天蓝底子上起白色小雏菊图案的衣服,仿佛晴朗的天空下开满了白色的花朵,那么清新可爱。秀秀那天梳着两条小辫,衬着她那消瘦清秀的脸庞,好看极了,她带着我们在舞台上表演节目,就像一只漂亮的小蝴蝶翩翩起舞,吸引了所有老师同学的目光。秀秀喜欢跳舞,她说跳起舞来,就什么都忘记了,仿佛自己就是那个最快乐的人。秀秀说长大后要去当舞蹈演员,在队长家黑白电视里看到的那种大大的舞台上跳舞。
秀秀也做家务,但是比如挑水呀,浇菜水呀等重一点的活计,她的父母舍不得让她做,说小孩正长个子呢,压矮了以后就长不高了。惠惠经常做各种重活,体型矮小敦实,我自小身体差,身形矮且羸弱,秀秀是我们村的女孩子里个子长得最快的,体型高挑纤细,用我母亲的话说,就像一棵小嫩竹子。嫩竹子,小竹子,小筱……我沉吟着,小筱应该就是她!
我上初三那年的暑假,秀秀来我家找我玩。她个子又长高了一些,身形也渐趋丰满,原来黄瘦的脸颊上竟有了两抹胭脂红。她告诉我,过完霜降,她就要出嫁了,婆家在仓东。我再也不能跳舞了,我以后就是当农民的命了!秀秀说着,深深叹了一口气。等你以后读书读出去了,可不要忘了我。秀秀说完低头就走,我想拉住她,我母亲向我摆了摆手。后来我才听我母亲说,秀秀的父亲给秀秀定下了一门亲事,那个男孩的父亲原来是生产队长,男孩是独生子,家庭条件比秀秀家好,听说那个男孩只读过小学二年级,但是他父亲说了,他家就一个独子,又没有兄弟姊妹分家产,只要秀秀嫁过去,那个家都是秀秀的了,他们两夫妇也会把秀秀当亲闺女对待。秀秀本来不愿意,她嫌弃那个男孩子只读到小学二年级,没文化,可是秀秀的父亲对秀秀说,这是一个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人家,男孩是独子,他爹妈不对你好对谁好?你嫁过去后,那个家就是你的。再说他家比我家条件好,你嫁过去不会吃苦,我也就放心了。
一位老人把我领到一道低矮的铁门前,说那就是秀秀家。门开后,秀秀就出现在我面前,我几乎认不出眼前这个中年女人,身形没变,但是脸颊比小时候更瘦削,使得额头上和眼角处皱纹密布,稀疏枯黄的头发在脑后随便绾成一个发髻。她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紫红色棉衣,黑色的棉裤上蘸了一些泥浆。秀秀带我走进院子,眼前是一字排开的四间只有一层的砖房,被两边的房屋遮住了采光,地面显得潮湿阴暗。进到屋里坐下后,秀秀给我倒了一杯水,说过去了这么多年,你终于来看我了。家里没人喝茶,没有准备茶叶,你将就点喝杯水吧。我没有过多地谈我的情况,都是听她说。秀秀说她那年很想像我和惠惠一样接着读书,可是她父亲说女孩子迟早都是要嫁给人家的,读书有啥用,书读多了,身子骨读软了,以后嫁不出去,还不如回家干活,把身体锻炼硬扎些。秀秀的哥哥姐姐也都只是读到小学毕业,于是秀秀只好回家了。秀秀说那时她并不愿意嫁过来,她自己一个女娃都读到小学毕业,而那个男孩才读过小学二年级,可是她父亲不管这些,他看到的就是男孩的家境比自己家好,男孩是独子,以后可以独享家产。你走的路还没有我过的桥多,你一个小孩子知道啥?他父亲经常这样说。如果你拒绝了这一家,以后我再不会管你的事,他父亲最后又这样说,秀秀只能含着眼泪答应下来。嫁过来后,秀秀确实也过了两年省心的日子,当过生产队长的公公精明能干,婆婆劳动力好又会操持家务。后来,公公婆婆先后去世了,家里家外的大小事情落到了秀秀夫妇俩头上,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的丈夫脑子不好使,所有的事都是秀秀独自操劳。秀秀红着眼圈说,那些年,娘几个经常被人欺负,生活的风风雨雨都是她独自承担,经历过多少艰难困苦啊!秀秀说,她父亲是前年冬天去世的。父亲弥留之际,拉着秀秀的手说,他对不起秀秀,让秀秀这些年吃了很多苦。秀秀叫父亲不用牵挂自己,孩子长大了,能挣钱了,艰难已经过去了。秀秀说着这话的时候眼里有了泪光,她擤了一把鼻涕,接着说,好在两个儿子虽然书没有读成,但是身体好,也还算懂事,这些年一直带着脑子不够用的傻爹在深圳做苦力,挣了不少钱,今年春节爷儿三都没回来,说这个时候加班工资比平时高很多。我让他们明年回来,把房子再加盖三层,给两个儿子的婚事办了,我也了了一桩心事。秀秀说这话的语气很沉着,眼睛里浮现出一层笑意。
我拿出那张画,问她有没有见过。秀秀接过画,嘟囔道:这都是什么呀?是哪个小孩子画的吧。我指着“小筱”两个字给她看,告诉她是这个人画的,她只认识“小”字,问我另外那个是什么字,我告诉了她。秀秀有些难为情地笑了,说当农民这么多年,又不读书写字,把以前认得的字都忘了。我指着“希望”两个字告诉她,这张画的名字叫“希望”。“希望”!秀秀吃惊地说,什么叫希望?希望不就是我想加盖房子,我想明年两个儿子能结婚吗,这有啥好画的!我告诉她,当年我们还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名叫小筱的好朋友,她非常想去看看远方是什么样子,但又因为很多条件限制不能去,所以画了这张画,放在我家老房子里。我的话刚说完,秀秀说,谁是小筱?谁说只是小筱想去远方?那时我们都想去呀!你、我、惠惠我们不都这样想吗?我问,这张画是你画的吗?秀秀惊愕了一下,低头若有所思地说,可是画上写的是“小筱”啊!我急了,说道,你忘了,那时我们都瞒着大人私下给自己另取名字,你想想,想起来了吧?这个“小筱”应该就是你吧?秀秀抬起头,灰黄的脸颊上竟有了一丝红晕,我是给自己取过名字,但是取的什么,那些小孩子时的事,这30多年来早忘了。也许这个小筱就是我,这幅画就是我画的,因为那时我想象过很多美好的生活,我想接着读书,以后当一名舞蹈演员,去看看远处的世界,但是这种想法我能对我父母说吗?我父母亲那么艰难地把我养大,供我读到小学毕业,我怎么敢再对他们提其他要求呢?秀秀的话竟让我心里隐隐痛起来。
从秀秀家回来的路上,我接到领导的电话,领导说上面有紧急通知,要他立刻回单位上报一个数据,他本人倒是在城里,可是他家里有事没时间去,叫我替他跑一趟。我平静地告诉领导,我回老家了,我家里也有事。
聪明的读者,当你读到这里时,想必你已经明白了是什么牵绊了小筱想去远方寻找希望的脚步。
然而,谁是小筱?
7
我决定把那张画放回原处,就让它湮灭在时光里吧。
第二天吃过午饭,我揣着那张画回到我家老房子的阁楼上。我掀开草席,想把那张画放回床角。就在我弯下腰的时候,我瞥见床下有一本覆满灰尘的笔记本,我把笔记本扒拉出来,拍去灰尘翻开一看,发现这是我五年级时的数学笔记,扉页上用稚嫩的笔迹写着:
为人莫做爬地草,
要做青竹节节高。
——自勉
青竹……小筱,小筱……青竹,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一道亮光:在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也有什么联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