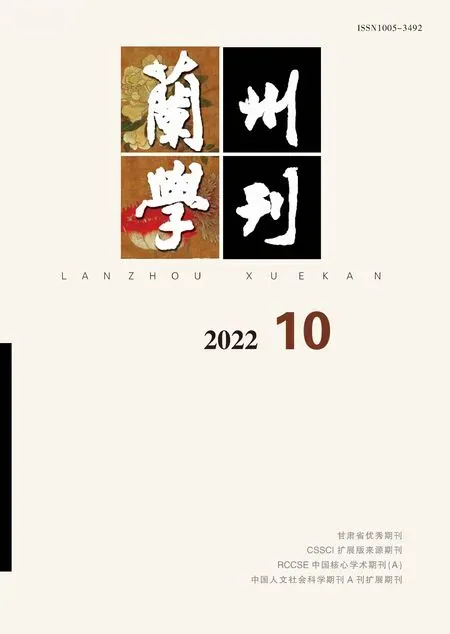持守、识变与应变: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
杨静慧
家庭作为典型的初级社会群体,承担着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功能。对于一个个体的成长,父母是其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其第一个课堂,父母有责任、有义务在这个直接的、面对面的、以情感为基础的课堂中开展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作为父母和家长,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82页。品德是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经由个体内化的产物,是个体社会行为的内部调节机制。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作为文化构成的核心内容,是通过“代”来实现纵向传递和丰富发展的,对于未成年人来说,这种道德社会化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家庭教育中的亲子实践。“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个人对个人的关系,而是代表了一种深层的文化传承与道德教—受的使命”。(2)赵庆杰:《家庭与伦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7页。从理论层面考察,社会学习理论主张个体的社会行为源于人际互动中的观察与模仿,这种学习多以偶然强化作为中介,即凭借他人展示或者生成的信息来获取知识与技能,这一实践促进了个体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形塑与发展,而“绝大部分观察学习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行为偶然或有意的观察的基础之上”(3)[美]班杜拉:《社会学习心理学》,郭占基、周国韬等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39页。。可见,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是最早也是最全面地嵌入其中的,自然充当了子女道德观察和道德模仿的对象,成为了子辈道德价值和道德规范的关键强化者。从实践层面考察,道德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起源于人类的生活世界,而家庭德育的运行载体就是日常的真实生活,其间频繁发生的亲子实践则是家庭德育的最主要方式和最有效方法。“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为道德训练提供了最有效的基地。这种训练尤其在家人之间的血缘亲情方面着力。”(4)樊浩:《道德教育的价值始点及其资源性难题》,《教育研究》2003年第10期,第44页。显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家庭中,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实现路径都是建立在亲子关系基础上的代际互动。因此,社会变迁作用下亲子关系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现代家庭的道德教育,进而影响到未成年人的道德建设。于是,探讨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其价值由此彰显。
一、社会变迁重构亲子关系
传统社会,家庭中亲子两代人的不对称性显著,父慈子孝的权威格局固化,高度的同时代性保障着家庭德育在“由父及子”单一模式中顺畅进行。转型社会里,急剧的社会变迁解构了传统的亲子关系,并朝向平等化、民主化的方向重新建构现代的亲子关系,亲子两代人的不同声音也越来越明显。
(一)不对称性消逝,亲子关系平等化
亲子之间天然存在着成熟差异,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对称性,即相对于子辈,父辈在知识、经验和经历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使得包括德育在内的各类教育具备了必需性和可行性,且固定为前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进行的实践模式,落实在家庭领域就是父母或祖父母对子辈或孙子辈开展的培育及教导。印刷媒介也助推了这种不对称性,并将其进一步地固化,亲代凭借强于子代的读写能力,通过对印刷资料的高度选择来实现对子代的规范引导和限制约束,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同时也加深了代际之间的不对称性。科技助推下的社会变迁带来了以电子媒介为典型的现代传媒,打破了印刷媒介所维护的严格等级层次序列,消逝着亲子之间的不对称性。无孔不入的现代媒介激发着未成年人毫不费力地翻越读写障碍,快速获取大量信息,进而闯入原本对其封闭的成人世界。在这个“没有儿童的时代”,亲代对信息的控制与霸权被推翻,亲子之间的知识鸿沟和资讯差距逐渐弥合,年幼的孩童几乎可以发展到与其父辈相当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机会,亲代与子代共处于同一信息系统,亲子关系日益平等化。
(二)权威格局式微,亲子关系民主化
传统中国,家庭本位、父子主轴、孝亲核心的宗法人伦有效整合了社会。《礼记·大学》云:“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但这里的“孝”与“慈”并非对等,而是偏重于前者,后由“父慈子孝”逐渐演变成了“父为子纲”,其权威结构更为鲜明。传统亲子权威格局的构建基础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在家庭这个基本的经济生活单元里,父辈凭借其性别带来的体力优势和年龄带来的经验优势,位居家庭主导的权威地位。但随着机械化、工业化的推进,家庭的经济功能外移进入各类社会组织,家长的务农收入逐渐低于子女的非农产业收入,家长的农耕经验也远不及社会现代化的知识更新;进城务工使子辈在城乡地理和陈旧家庭关系等多个维度上都实现了“脱域性”流动,年轻一代在增加收入、拓宽视野、革新观念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些变化都锐减了亲代对子代的支配力和控制权。加之平等自由、民主解放、张扬个性等社会潮流对社会个体的思想浸染和行为导向,家庭中代际之间的传统权威格局逐渐式微,亲子关系日趋民主化。当然,现代的亲子实践仍然遵循着“父慈”与“子孝”道德规范,但这与传统社会“尚齿”的尽孝观念和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伦理道德是有本质区别的。
(三)同时代性差异,亲子关系冲突化
亲子的同时代性(contemporaneity)意味着家庭中父辈与子辈所接受的环境作用是相同的,从而使他们拥有相同的生命历程和价值观念,在行为选择和道德规范上归属于同一历史类别。传统社会变迁缓慢,亲代与子代的生活场景、成长历程都是高度复制的,具有明显的同时代性,于是,亲代对教育子代满怀信心,子代对认同亲代心悦诚服,家庭德育理所当然地在亲子实践中顺畅进行。然而,迅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带来了“同时代人的非同时代性”(the non-contemporaneity of the contemporaneous),亲子两代人虽然共同经历着同一时期,实际上却活跃在性质迥异的主观时间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同一时间’却是不同时间——换言之,代表了他自己的不同时段,这种不同时段他仅能与其同一年龄的人们所分享。”(5)[德]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精粹》,徐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也就是说,对于任一时点,人们都能辨识出不同代的各自声音。在这里,代环境可以作为形塑个体道德品行的养成条件和解释框架,“技术、教育、旅行和现代通讯之间的相互作用彻底改变了时间和距离的含义,而且使主观范畴内社会道德标准和客观范畴内社会环境都发生着迅速的变化”(6)[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同时代性的差异导致不同代的人面对同一道德现象会做出不同的解释,因此,亲子两代在道德意识、道德行为方面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局面,进而引发亲子冲突。
二、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持守
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家庭中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实现路径是建立在亲子关系基础上的代际互动。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不对称的、父权独大、同时代性的传统亲子关系,被重构成为平等、民主且冲突频显的现代亲子关系,那么,相应地,亲子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于是,面对这种状况,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第一要义便是要坚持、守护中华民族注重家教、家风的优良传统,通过亲子互动积极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发展起来的优秀家教、家风传统,是中国灿烂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也是现代家庭德育的深厚思想根基。中国传统家教、家风以“仁义礼智信”的五德作为价值指引,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作为核心理念,形成了诸如《颜氏家训》《郑氏家训》《治家格言》《曾国藩家书》等为代表的传承范本。正是这些优秀家教、家风传统在中华子孙的生命中传递、延续着,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所继承、发扬,才凝结成了五千多年的中华灿烂文明史。孔氏后代著书立说、才华横溢,呈现出重教兴学的世家风范;“孟母三迁”“断机之教”表现出求知好学的家教观念;“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彰显出保家卫国的育子理念;欧阳修之母“画荻教子”展示出勤学苦练的家庭教导,等等。类似的经典故事、感人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这些典故中都蕴涵着家教、家风的光辉思想和示范行为,传承着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以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要继续前进,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继承和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特别是包含其中的传统美德。”(7)习近平:《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人民教育》2014年第12期,第6页。对待亲人,要慈孝互敬、相亲相爱;对待朋友,要互助互敬、和睦相处;对待国家,要爱国敬业、甘于奉献;育子要求德才兼备、立德树人;持家讲究勤、检、恭、恕四德治家,等等,这些传统美德至今依旧璀璨夺目、展示出丰富的价值。我们勇于创造未来,必须不忘本心;我们敢于追求创新,必须善于继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8)教育部课题组:《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15页。习近平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理论为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指明了方向,家教为“体”,家风为“用”,体是用的内在依据,用是体的外在表现,两者统一在家庭这个以血缘、亲情为内在逻辑的牢固基石上面,坚持守护中华民族重家教、育家风的优良传统,通过亲子互动积极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三、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识变
建立在亲子关系基础上的代际互动是未成年人家庭德育的实际实现路径。社会变迁重新构建了亲代与子代的互动关系,进而,亲子关系由传统向现代的变化又作用于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在此背景下,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德育一方面要坚定持守中华民族注重家教、家风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还要准确辨识平等化、民主化且冲突频现的亲子关系给家庭德育实践带来的各种变化,从而为有效应对这些变化做好准备。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其一,代际重心下移挑战了家庭德育的权威性;其二,文化反哺颠覆了家庭德育的单向性。
(一)代际重心下移挑战家庭德育的权威性
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男性长辈是一家之主,他们凭借亲子之间天然存在的不对称性,顺应父权至上的习俗礼教,依据同时代性的稳定规律,拥有不可撼动的家庭/家族权威。作为先知和道义的化身,亲代有责任、也有义务将丰富的经验、祖先的智慧和古老的文明传递给下一代;同时,子代对亲代只有顺从的义务,毫无反抗的权利,必须无条件地全面接受家长对自己的教导和灌输,并以此作为自己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前提和基础。显而易见,家庭重心明显偏向父辈,这种家庭传统权威格局强劲有效地保障着家庭德育由亲代向子代顺畅实施。在家庭德育的实际过程中,道德同一性和榜样的关系极大,孩子在接纳榜样价值观的同时就发展形成了自己的道德同一性。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亲子交往、家人互动是其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加之父权独大的传统权威,他们自然且自觉地会将亲代视为自己的榜样,这个榜样便是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 W. Mills)(9)“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这一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赖特·米尔斯在乔治·米德有关“自我发展”的理论基础上首先提出的,是指在个体社会化以及心理人格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具体人物。所强调的“重要他人”。在人类较长的依赖期中,个体会对自己的“重要他人”产生敬畏和热爱这两种特殊的情感,当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时,道德教育的效果就是最显著的。于是,在传统社会的家庭德育中,未成年人与其父母之间发展着强烈的道德认同,这种道德同一性有力地维护着家庭德育的权威性。然而,随着社会变迁,扩大的家庭结构逐渐小型化,生产、分配、消费等经济功能逐步从家庭中外移出去,家庭功能的简单化撼动了父权家长制运行的经济基础。在以核心家庭为主流的现代家庭中,代际重心已呈现出明显的下移趋势,亲子关系里年轻一代的重要性增加,而且由于家庭结构的改变增加了亲子互动的机会,也模塑了亲子间民主的参与和决策模式。同时,社会变迁中的电子媒介凭借形象具体、及时便捷且海量信息的时代特征,顺势挤占了父母的“重要他人”角色,成为影响未成年人道德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维度。通过电子媒介,未成年人提前接触到了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也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多元价值观念的侵染与裹挟。在一定程度上,价值导向的多元化会导致道德认同发生混杂与矛盾,进而引发道德行为选择的模糊和无所适从,给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依据道德认同危机理论,文化或心理上的认同紊乱将会导致道德教育危机,阻碍未成年人实现道德同一性的社会化目标。于是,在家庭代际关系平等化、民主化的发展趋势中,亲代与子代之间必然出现对话,甚至可能发生对抗。父母力求将从上一辈传承下来的规范、习惯继续传递给自己的后代,然而,孩子们却崇尚自由独立和突破创新。在文化冲突和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里,道德权威旁落,未成年人道德教育机制脱离了既有的权威性,家庭德育在困顿中艰难实施,“他们不知道如何教诲这些与自己童年大相径庭的孩子,大多数儿童也无法向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父母或长者学习。”(10)[美]玛格丽特·米德:《代沟》,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81页。社会变迁使家庭代际重心下移,亲代“重要他人”角色的动摇凸显了道德认同与多元价值之间的张力,挑战了未成年人家庭德育的传统权威性。
(二)文化反哺颠覆家庭德育的单向性
在传统社会,未成年人的家庭德育是通过长辈将道德规范口口相传给晚辈、将道德行为榜样示范给晚辈的方式来具体实践的,未成年人学习、内化道德文化的过程就是道德社会化,而这一社会化机制正常运行的前提便是上一代要具有显著的知识优势,且能够依据亲子同时代性来准确解答未成年人的成长困惑,有足够信心地为子代的发展指点迷津。在这种情况下,未成年人家庭德育的实践方式固定表现为由亲代到子代的单一方向性。然而,社会变迁进入到信息化的数字时代,父辈遭遇到“人生滑铁卢”(个人电脑的大普及和互联网络的全覆盖),年龄优势急转直下,很快就演变成了年龄劣势,大量固有经验也因为知识的快速更新而丧失了向后代传递下去的实际价值,父辈的家庭地位迅速下降,对子辈思想和行为的作用力及权威性明显减弱。在论及自己对子女的教育能力和引导作用时,绝大部分家长都感到力不从心,感叹人类掌握计算机的能力与年龄成反比,对于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不仅自己无法指导孩子,反过来还经常要向孩子请教,从孩子那里获取有效信息以跟紧时代的节奏。美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 Mead)(11)[美]玛格丽特·米德:《代沟》,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20页。创新性地提出“后象征”“互象征”和“前象征”这三种文化类型:“当论及‘未来重复过去’型时,我用‘后象征’(Postfigurative)这个词;论及‘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型时,我用‘互象征’(Cofigurative)这个词;在论及年长者不得不向孩子学习他们未曾有过的经验这种文化类型时,我就用‘前象征’(Prefigurative)这个词。现在,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由于年轻人对依然未知的将来具有前象征性的理解,因而他们有了新的权威。”也就是说,社会变迁背景下,新生事物“井喷”式显现,父辈所掌握的传统规范、价值取向、行为选择丧失了原有的解释力和传承价值,家长不再是正确观念、先进知识、前沿信息的唯一代表;同时,子代也第一次拥有了与父母争辩、甚至反过来影响父母继续社会化的机会,于是,文化反哺现象就自然出现了。在未成年人家庭德育的实践过程中,文化反哺切实提升了亲代对新生事物的接触广度和应用深度,但这仅限于技术工具层面上,如果扩展到超越技术工具层面的观念、意识层面,涉及诸如文化认同、生活方式、媒介体验等领域,则亲子之间的“数字鸿沟”异常明显,这种全方位的家庭代际差距可以视为威廉·奥格本(W. F. Ogburn)(12)William Fielding Ogburn,Social Change with Respect to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50,p.200.所提出的“文化堕距(cultural lag)”R的另一种版本。自从1988年周晓虹教授第一次使用“文化反哺”这一概念发展至今,家庭德育中亲子之间在对新观念、新行为的接纳和适应上已经显现出鲜明的快慢差异,年长的一代就如同M.米德(Margaret Mead)所谓的“时间移民”一样,而“各种新兴媒介的出现和使用已经超出纯技术的范畴,对青年群体具有全方位立体渗透式的影响,青年社会化表现出双向互动性、个性化、主动化和虚拟化等特征”(13)袁光亮:《新媒体时代的青年社会化》,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3页。。其实,不仅在家庭德育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传承模式都正在被颠覆,亲子之间的同时代性差异增强,两代人开始平等争论,由亲及子的固有的道德传递方向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给未成年人家庭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应变
亲子关系源于生物体的自然属性,在社会实践中,经由情感和社会角色,提升至伦理层面发展完善为人的社会属性。作为实践家庭德育的现实基础,亲子关系伴随社会变迁而呈现出鲜明的运动变化性,相应地,代际重心下移挑战了家庭德育的权威性,文化反哺颠覆了家庭德育的单向性。应对这些变化,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由单向灌输完善为双向对话,由共依存发展为同成长。
(一)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由单向灌输到双向对话
亲子之间与生俱来的不对称性使教育成为必需,其实,教育的社会功能就是去弥合这种不对称性。传统家庭中,长辈凭借年龄优势和权威地位将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道德文化强行灌输给晚辈,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晚辈只能完全服从、照单全收,这种由父及子的社会化必然是单一方向的,整个过程都忽视了子辈的主体性。伴随工业文明的进程,父辈的经验显得狭窄且落后,亲子关系平等化、民主化的现代转型使得单向灌输的家庭德育模式无以为继,而具备科技禀赋的子辈则不断彰显其信息敏感性、知识更新性和适应灵活性,这些变化反映在家庭德育层面便是教育主客体角色的反转,亲子之间开始对话,呈现出由父及子和由子及父的双向社会化过程。所谓对话,它是发生在两个行动主体之间的沟通实践,并建立在平等、民主的意识之上,对话的各主体相互理解,合作共生,致力于在沟通中实现共享共创。亲子对话表现为一种发生在亲代和子代之间在平等意识基础上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对于不同的道德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选择,两代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子代既可以赞同、支持亲代的观点,也可以将传统观点进行补充、完善,甚至可以推翻既定结论,创新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对话并非个体之间的随意攀谈,而是一种双方相互尊重、理解和欣赏的过程,它如同一座“桥”,承载着代际之间道德文化的双向社会化。家庭德育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对话,是作为行动主体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交流、沟通的创造性实践,亲代和子代在对话的过程中,彼此尊重、平等交流,双方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养成都因对话而得以提升,变得更加充实而丰富。这种亲子间对话式的德育实践创新了教育理念,与传统的单向灌输式相比,显然是一种超越和优化。在急速的社会变迁中,不同代的人成长环境大相径庭,即代环境不同,这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不同代的个体成长环境不同,代环境体现代际差异;二是同一代的个体因成长环境相同而表现出相似的观念思想和行为模式,代环境体现代内同一性。从这两层意义上来说,家庭德育实践中亲代和子代同期不同代,所经历的代环境不同,两代人之间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存在鲜明的代际分化,亲子之间必然存在进行对话、开展沟通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当父母为孩子们解释规则和认真听取孩子们观点时,他们孩子的道德和亲社会行为将会得到加强。”(14)Krevan J, Gibbs J C.,“Parents’ Use of Inductive Discipline: Relations to Children’ S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Child Development,No.67,1996,pp.3263-3277.显然,相互尊重、平等共识、对话沟通已发展成为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亲子实践的时代特征。《圣经》中“巴别塔”的典故早已隐含了沟通的价值,启发我们面对社会变迁中亲子关系的重构,家庭德育必须摒弃传统由父及子的单向式灌输,亲子之间应该接纳不同声音的充分沟通,构建代际共享的话语格局,实现亲代与子代的双向式对话,完善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的亲子实践。
(二)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由共依存到同成长
共依存(co-dependence)原指酗酒者沉溺于酒瘾而无法自拔的生存状态,后拓展为描述个体内在世界失落、依赖外界事物以求生存的病态。在亲子关系层面上,共依存是一种不健全的亲子互动状态,因为它会引发一种他人导向的生活方式。例如一些家庭中父母对子女事事代劳、件件替做就是典型的共依存行为,子女只能丧失独立性地依赖其父母,无法自立自强。数千年来,人们凭借这种依赖性把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道德文化传递给自己的下一代,显然,这种社会化模式只能存在于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中,它落后保守而且毫无反思。社会转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刻变迁正在重构亲子关系,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作用效果日益显著,影响子辈道德社会化的主体也不再仅限于家庭中的长辈,而是呈现出多元化和现代性的特征。作为网络社会原住民的年轻一代,不仅强烈反对全盘复制其父辈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而且还致力于用现代的思维、时尚的观点来质疑陈旧的经验,通过文化反哺去推翻、替代那些陈词滥调,进而推动文化创新和社会进步。博尔诺夫(Otto Friedrieh Bollnow)(15)[德]博尔诺夫:《教育人类学》,李其龙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将人定义为“教育的、受教育的和需要教育的生物”,不仅子代需要接受亲代的教育以传承文化,亲代亦需要认可子代的影响以创新文化。文化反哺的价值不仅表现为家庭内亲子传承和家庭外代际传递的实际方向发生了反转,将道德社会化主体与客体的角色、施教者与受教者的位置进行了重置,更重要的是,文化反哺还展示了社会变迁过程中年轻一代历史角色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彰显了家庭中亲代与子代之间共同成长的新型亲子互动模式。家庭德育中,通过文化反哺,这种亲子共同成长的创新模式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变迁撼动了“父为子纲”的传统权威结构,网络的普及、科技的腾飞使年轻成为优势,父辈已不总是家庭德育中高高在上的施教者,反而经常会受到子辈的质疑和挑战,民主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催生了两代人之间的讨论与合作,亲子互动更多体现为沟通交流、共享共事与共同进步。在这一过程中,亲代的社会适应能力显著提升,“文化反哺甚至成为年长一代接触外来文化和现代性的常规途径之一”(16)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第113页。。实际上,父母“重要他人”的角色并非静止,它是亲子互动的产物,这一角色要求父母应把共同成长视作心灵建构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文化反哺作为社会变迁的重要成果,它不仅为父辈带来了继续社会化的机遇,还为子辈提供了登上社会舞台、强化历史责任的锻炼机会。显然,道德是一个高度自主、自为及自觉的概念,在社会学意义上,德育过程表现为施教与受教双方的相互作用;在教育学意义上,德育过程是施教者主体性的实施以及被教育者主体性的实现。家庭德育过程中实现共同成长要求亲子关系必须具有以下四点特征:第一,亲子之间相互尊重,都将对方视为自主、独立的个体,这是共同成长的前提;第二,亲子之间平等民主,不因辈分而压制对方,这是共同成长的基础;第三,亲子之间充分交流,不同声音相互对话,这是实施共同成长的途径;第四,亲子目标一致,愿意为此共同努力,这是实现共同成长的保障。可见,这样的亲子关系不是泯灭自身、混淆边界,而是滋养新的情感、提升新的自我,这是社会变迁中亲子关系的革命性发展。这种亲子实践在拓宽父母眼界、增强父母社会适应能力的同时,赋予下一代以自信和责任,使亲子两代人之间由共同依存发展为相互促进、共同成长。
五、结论与讨论
广泛且深刻的社会变迁解构了传统亲子关系,重新建构了现代亲子关系,作为家庭德育实践路径的亲子互动随之改变。于是,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应当在持守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准确辨识这些变化,并进行有效应对。其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17)《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3日,第1版。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事关大局,家庭德育以其特有的奠基性、亲密性和深刻性对个体的道德社会化产生深远的影响,是涵养未成年人道德品行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家庭德育的实践路径是建立在亲子关系基础上的亲子互动,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未成年人道德意识的培育、道德行为的塑造具有天然的情感优势和无可替代的社会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已于2022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家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意味着家庭教育已经从“家事”提升到“国事”的重要维度,也对为人父母的教育责任和抚育义务在法律上给予了明确的要求。家庭教育以德育为首,代际秩序变更,“代际平等已成为现代性张力的必然现象”(18)于兰华:《“共生”亦或“契洽”:我国代际资源循环的历史变迁与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反思社会变迁过程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除了“反哺”之外,亦不可缺少“跪乳”。“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19)《中共中央国务院举行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8日,第1版。“三个注重”作为家庭德育的着力点,为转型社会里家庭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路径指明了方向。认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理论的深刻内涵,有助于创新社会变迁中家庭德育的亲子实践,弘扬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家庭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宏观层面的国家治理与微观层面的家庭治理相互促进、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