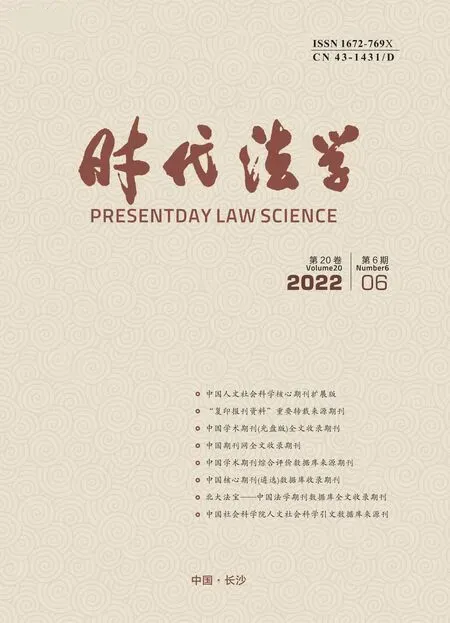论受贿犯罪的法益:职务行为不可交换性说的提倡与检视
郑泽星(中南大学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受贿犯罪的法益保护一直是刑法学研究中被广泛探讨的问题。近年来,学界对于受贿犯罪保护法益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但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统一定论。在我国,受贿犯罪法益学说先后经历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以及目前占据通说地位的“廉洁性说”,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于德日刑法理论的继受,“不可收买性说”和“公正性说”已经形成了对“廉洁性说”的夹击之势。此外,仍有学者提出新的理论主张,如“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不可交易性说”以及“公职不可谋私利说”等等。各种理论学说之间互相辩驳,但究竟应采何种观点,学者们难以形成共识。本文认为,“不可收买性说”存在解释论上的缺陷,应当对其进行修正,具体方法是以职务行为不可交换性的表述代替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表述,从而赋予“不可收买性说”更丰富的内涵,以应对反对论者对于“不可收买性说”的诘难。为厘清受贿犯罪法益之争并提倡“不可交换性说”,本文将梳理受贿犯罪法益的不同学说并分别作出评析,然后尝试从不同学说的相互辩驳中探寻确定某一犯罪法益应当考察的基本要素并据此对不可交换性说进行教义学上的检视。
一、受贿犯罪法益学说梳理
我国学界关于受贿犯罪法益观点始于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说[注]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62.,对于受贿罪法益的真正讨论则始于廉洁性说,之后学者们又提出了“不可收买性说”“公正性说”“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不可交易性说”以及“公职不可谋私利说”等学说。
(一)国家职能正常实现说
“国家职能正常实现说”又称“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说”,持该说的学者们认为,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为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腐败行为对内危及国家的正常秩序,对外损害公众对于公共决策公正性的信赖[注]Loos. Welzel-FS:890.,进而导致国家的正常职能难以实现。德国学者多林(Dölling)将公务人员的义务分为一般义务和特别义务,所谓一般义务是指公务人员依照客观准则无私地履行其职务,公正地实现其任务以服务于国民全体。特别义务则是指禁止公务人员在职权行使范围内谋取私利。一般义务履行只在从正面维持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特别义务的履行,则通过防止职务行为与私人利益的互换,从而避免公务人员违反义务实施职务行为的可能性,进而从反面维持了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注]Dölling.Jus 1981:574.。
(二)廉洁性说
“廉洁性说”发端于法益学说引进之前,“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严惩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上的贪婪,也就是国家设置受贿罪的宗旨所在”[注]郝力挥,刘杰.对受贿罪客体的再认识[J].法学研究,1987,(6):55.。对于何为廉洁性,持该说的学者有不同的阐释:一种观点认为廉洁性即职务行使的合规性,它要求国家工作人员依据法律和有关制度规定承担国家赋予的特定义务,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特定权力[注]孙谦,陈凤超.论贪污罪[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3):36.。另一种观点则从廉洁本身的含义出发阐释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内涵:廉洁的本质含义就是“在金钱方面没有欺诈或者欺骗行为的”“不损公肥私、不贪污”,所以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从其字面含义来理解,应当是兼有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和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注]吕天奇.贿赂罪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120.。又如,有学者指出,除应得的合法报酬之外,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以作为或者不作为为由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否则即构成对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害[注]曲新久.刑法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356.。显然,后一种观点在廉洁性说的支持者内部占绝对多数。虽然对于廉洁性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刑法学者多持“廉洁性说”。
(三)不可收买性说
“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说”(UnkäuflichkeitoderUnentgeltlichkeit der Amtsführung)首先在德国帝国法院的判决中得以确立[注]RGSt 63:369f.,该说认为,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受来自于第三人用作收买利益的“私人利益”的影响,并因此违背了对国家的忠诚义务而损害了公众对于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注]Henkel.JZ 1960:508.。在我国,“不可收买性说”是学者在批判廉洁性说的基础上提出的。在支持的学者内部,存在对于“不可收买性说”基本内涵的不同认识。部分观点认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即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两者之间没有本质区别,甚至可以说是同一的[注]刘艳红.刑法学(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49//叶良芳.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实用主义阐释[J].浙江社会科学,2016,(8):31//李少平.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M].中国法学,2015,(1):16.。有学者则突出了“不可收买性说”与信赖说的关联,认为公众对于职务行为客观公正性的信赖是以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为前提的,“不可收买性说”和信赖说只不过是观察角度不同,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注]孙国祥.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及其实践意义[J].法律科学,2018,(2):133.//王春福.受贿罪法益之展开[J].人民检察,2009,(21):54.。一般认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与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有内在关联,两者存在类似于目的与手段的关联,同时两者又相互区别。受贿犯罪侵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或者说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注]张明楷.刑法学(第5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203.。也有学者提出受贿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易性的观点,其大致主张与“不可收买性说”类似,在此不再分别列述[注]孙国祥.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及其实践意义[J].法律科学,2018,(2):133-136.。
(四)公正性说
“公正性说”又称“纯洁性说”“纯粹性说”,该说最早由德国帝国法院在判决中确立,该说认为受贿罪侵犯了职务行为的纯洁性(Reinheit der Amtsausübung)。早在1938年,德国帝国法院即在判决中确定了“维护职务行为的纯洁性是对公众而言极为重要的法益”[注]RGSt 72:237//BGHSt 10:241f; BGHSt14:131; BGHSt15:96.。该说认为,当职务行为与不被允许的利益相连结时就危及到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并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职务行为的信赖[注]Dölling.Die Neuregelung der Strafvorschriften gegen Korruption.ZStW 112:335.。在我国,有学者认为《刑法》第388条扩张了受贿犯罪的成立范围,因此也波及了对受贿犯罪保护法益的理解,因而主张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应为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按照公正性说,将收受贿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的目的在于:防止在职务行为与贿赂之间建立对价关系,从而使得职务行为被不公正地实施。而贿赂犯罪所处罚的对象,正是收受贿赂这种行为所引起的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侵害及其危险[注]黎宏.受贿犯罪保护法益与刑法第388条的解释[J].法学研究,2017,(1):71.。
(五)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
张明楷教授针对学者们对“不可收买性说”的批评而对其予以修正,部分接受了“公正性说”和“信赖说”的观点,区分受贿犯罪的不同类型而分别确定其保护的法益:“认为普通受贿的保护法益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加重的普通受贿的保护法益则可能还包括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斡旋受贿的保护法益是被斡旋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以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的不可收买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以及国民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注]张明楷.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J].法学研究,2018,(1):148.。
(六)公职不可谋私利说
“公职不可谋私利性说”最早由德国学者多林(Dölling)提出,其最初的表述是“为了确保公职人员对于职务的忠诚,应当将公共职务与私人领域相区隔”[注]Dölling.(Fn.8):C 49 f.。公职与私人利益相区隔是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与社会相区隔的具体化,后者对于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注]Greco.Annährungen an eine Theorie der Korruption. GA2016:251.。在我国,有学者提出了相近的观点,认为在贿赂犯罪中体现了交换关系,但交换并非发生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而是发生在受贿人的职位所蕴含的公权与其所捞取的私利之间的交换。因此,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应当定位为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注]劳东燕.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J].法学研究,2019,(5):118-137.。
二、受贿犯罪法益学说的反思
正如上文所展示的,受贿犯罪的法益学说众说纷纭。上述学说中,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说已经鲜被国内学者提及,对于廉洁性说的批判似乎也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因此本文将重点反思不可收买性说、公正性说、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以及公职不可谋私利说。
(一)“不可收买性说”反思
“不可收买性说”较“廉洁性说”更为具体地揭示了受贿犯罪“钱权交易”的本质,从而将贿赂犯罪法益与贪污罪的侵害法益相区分。但是,对于“不可收买性说”也不乏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无法对我国刑法实定法层面的部分受贿犯罪类型予以合理解释:在斡旋受贿的场合,实际实施的职务行为并不是被收买的对象,因而不可收买性说无法说明其处罚依据问题[注]郑泽善.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及贿赂之范围[J].兰州学刊,2011,(12):65.;在利用影响力受贿和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场合,受贿主体和行贿对象并不一定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可收买性说”无法对贿赂如何能够左右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进行合理解释[注]黎宏.受贿犯罪保护法益与刑法第388条的解释[J].法学研究,2017,(1):71//黎宏.职务行为公正性说与事后受财行为的定性[J].中国法学,2017,(2):234.;在索贿的场合,索贿行为侵害的应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出卖性,这显然无法涵括在不可收买性的语义射程之内[注]孙国祥.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及其实践意义[J].法律科学,2018,(2):133.//劳东燕.受贿犯罪两大法益学说之检讨[J].比较法研究,2019,(5):130.。也有学者从“不可收买性说”的立论基础对其予以反驳,认为职务行为并非当然无酬, “大部分由国家提供的服务和国家行为都是要付出费用或者提供对价的,因此不可收买性说立论的基础即已不存在。”[注]Graupe. Die Systematik und das Rechtsgut der Bestechungsdelikt:95// Henkel, JZ 1960:508; Schröder, GA 1961:290.此外,在德国刑法的视角下,受贿罪的利益包含了非物质利益,因而有德国学者提出,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并不能涵括此一部分非物质利益,因而不能作为受贿罪的适格法益[注]Nazanin Sporer. Die Auswirkungen der Täuschung im Rahmen der §§ 331,332 StGB:36.。
事实上,“不可收买性说”所表达的含义与职务行为的无酬性以及职务行为与财物的不可交换性是一致的,只不过采“不可收买性说”的表述使这一学说无论在语义内涵还是在解释力方面都受到局限,因此本文认为应当以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代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作为受贿犯罪的法益。下文将作进一步的阐释。
(二)“公正性说”反思
相较于“不可收买性说”,“公正性说”从更高的层面描述受贿犯罪的法益,因而从表面上看来解决了“不可收买性说”涵括性不足的问题。但对“公正性说”也不乏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公正性说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因而其法益区分性较弱,将其作为受贿犯罪的法益,不能从本质上对受贿犯罪以及同样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的职务犯罪进行区分[注]Geerds. Über den Unrechtsgehalt der Bestechungsdelikte und seine Konsequenzen für Rechtssprechung und Gesetzgebung:47// Geppert. Jura 1981:46; Graupe, Die Systematik und das Rechtsgut der Bestechungsdelikt:77// Henkel. JZ 1960:508//Schröder.GA 1961:290.;其二,对于特殊形式的受贿犯罪,“公正性说”不能给出合理解释:在没有违反职务义务的情形下,即通常所说的“受财不枉法”情形,公正性说无法准确说明对其予以规制的合理性。正如德国学者所批评的,“德国刑法典第331条和第333条中并没有规定违反义务的职务行为,因此将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作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并无意义”[注]Geppert. Jura, 1981:46.;按照“公正性说”,对于事后受财行为,只能得出无罪的结论,但这一结论无论从司法实践以及形势政策的角度考量,都不具有合理性[注]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 条规定,“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给予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应当认定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第三,从我国刑法的规定上来看,如果采“公正性说”,则受贿犯罪的规定与同样侵犯职务行为公正性的滥用职权罪的规定不相协调[注]张明楷.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J].法学研究,2018,(1):150.。“公正性说”部分揭示了受贿犯罪的特征,即公职人员在收受贿赂之后往往会作出倾向于利益提供者一方的决策从而损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但这种描述并不周延,无法包含受贿犯罪的全部情形。此外,“公正性说”基于将斡旋受贿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纳入受贿罪法益的涵括范围的考量而舍弃了受贿罪“钱权交易”的本质特征,因而不能认为是恰当的受贿犯罪法益。
(三)“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反思
从法教义学的角度来看,“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至少有如下缺陷:其一,在斡旋受贿场合,该说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具体化为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的不可收买性,一方面,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不可收买性的重要性程度要低于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不具有解释的当然性,上述解释则不当地扩大了职务行为概念的内涵,使之缺乏必要的边界[注]劳东燕.受贿犯罪两大法益学说之检讨[J].比较法研究,2019,(5):130.。其二,在利用影响力受贿场合,该说认为国民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也属于受贿罪保护的法益。因此,对于信赖说的批评也就当然适用于对这一修正观点。例如有学者指出,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应当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之类的客观内容,而不应包括对不可收买性的信赖之类的主观内容,将“信赖”这种内容模糊、主观色彩浓厚的要素作为保护法益不具有合理性[注]黎宏.受贿犯罪保护法益与刑法第388 条的解释[J].法学研究,2017,(1):69-70.。此外,也有学者从具体的刑法体系协调性的角度对“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提出质疑:“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不能解释为什么斡旋受贿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要较普通受贿为窄[注]劳东燕.受贿犯罪两大法益学说之检讨[J].比较法研究,2019,(5):130.。。“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实际上只是回应反对者对于不可收买性说的质疑的权宜之策,以之作为受贿犯罪的法益,理论上并不具有优势,实践中则可能使受贿犯罪的法益判断复杂化,因此,如果有更为合理的法益学说,“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并非首选。
(四)“公职不可谋私利说”反思
公职不可谋私利说基于受贿犯罪的不法本质在于“违反不得用公共职位谋取私利的禁止性义务”的认识,而将受贿犯罪的法益确定为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如果严格依照公职不可谋私利性说的语义,基于公用目的的受贿则无法被涵括在受贿罪法益的解释范围内。详言之,当收受或者索取贿赂的公职人员并非基于占为己用的主观意图而是基于公用的目的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在收受财物之后用作公用的,则不能认为符合公职不可谋私利性的法益界定,进而不能认定为构成受贿罪。例如某国土局领导心系乡村教育,一心想为教育落后乡村捐建一所希望小学,无奈公务员工资不高,积蓄甚少,一直未能如愿。后有房地产商向其行贿,请托其在建设用地审批中提供便利,该领导心想:“有了这笔钱,我就可以捐建一所希望小学了”。遂收受房地产商的贿赂款并为请托事项提供便利。后该领导将所得贿赂款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并如愿为落后乡村建起希望小学。依照“公职不可谋私利性说”的立场,本案中的受贿官员并非为私利而收受贿赂,因此没有侵犯受贿犯罪的法益,也就不构成受贿罪。这样的结论,无论从司法实践角度抑或从刑事政策的角度都是不能接受的[注]基于公用目的的受贿仍然成立受贿罪。参见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出于贪污、受贿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收受他人财物之后,将赃款赃物用于单位公务支出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的认定,但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
三、法益确定的考察要素与不可交换性说的提出
(一)法益确定的考察要素
综观受贿犯罪不同法益学说之间的相互辩驳,可以归纳出学者们在考察法益是否适格时主要关注三个方面,即法益的专属性、涵摄性以及协调性。首先,法益应具有专属性,即法益应当能够揭示某一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本质特征,如果某一法益揭示了某类犯罪的共同法益,则不能认为其具有专属性。其次,法益应具有涵摄性,即所确定的法益应当对目标犯罪的所有不同犯罪形态具有解释力,当所确定的法益不能涵括目标犯罪的所有犯罪形态时,则不能认为其是目标犯罪的适格法益。再次,法益应具有协调性,即所确定的法益以及据此得出的解释结论应当与现有的法律体系以及教义学结论相协调,如果两者之间存在抵牾或者明显的不协调,则不能认为其是目标犯罪的适格法益。
1.法益的专属性与受贿犯罪法益的选择
法益专属性的基本内涵是特定的犯罪应具有特定的法益,不能以类法益或者复法益的存在而否定法益的专属性[注]孙国祥.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及其实践意义[J].法律科学,2018,(2):134.,申言之,所确定的法益应当能够揭示目标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本质特征,如果所确定的法益除了揭示目标犯罪的本质特征之外,仍能涵括其他犯罪类型,则不能认为其是目标犯罪的适格法益。刑法规定的每一种犯罪之所以各自拥有不同罪名,原因正在于其与其他犯罪行为具有本质的不同,而确定法益的过程,即是揭示目标犯罪本质特征的过程,也是界分目标犯罪与其他犯罪的过程。贯彻法益的专属性,对于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到法益专属性的确定而言,应当结合法益的位阶性进行判断,下文将结合受贿犯罪的法益进行详细阐述。
2.法益的涵摄性与受贿犯罪法益的选择
确定法益的过程中,仍应考虑涵摄性要素,即所确定的法益应当对目标犯罪罪名之下的所有犯罪形态具有解释力,易言之,目标犯罪罪名之下所有的犯罪形态都应当能够涵括到所确定法益的解释范围之内,否则,则不能称之为适格法益。事实上,所有关于法益的争论,大多是不同学说之间基于法益涵摄性的相互批驳。具体到受贿犯罪而言,如上文所述,反对学说对于“不可收买性说”的批评集中在“不可收买性说”不能对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以及索贿给出合理解释[注]黎宏.受贿犯罪保护法益与刑法第388条的解释[J].法学研究,2017,(1):71.。而意图摆脱“不可收买性说”涵摄性缺陷的公正性说以及“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同样面临涵摄性不足的质疑。易言之,学者们对于受贿犯罪法益的攻守,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法益的涵摄性进行的。因此,涵摄性的检视也是“不可交换性说”教义学检视的重点。
3.法益的协调性与受贿犯罪法益的选择
协调性要素是法益在满足专属性要素、涵摄性要素之后,仍需考察的方面。其判断的内容是所确定的法益以及据此得出的解释结论是否与现有的法律体系以及教义学结论相协调,易言之,所确定的法益应当经受住体系解释的检验并且符合教义学的逻辑[注]劳东燕.受贿犯罪两大法益学说之检讨[J].比较法研究,2019,(5):137.。举例而言,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那么,侵犯相同法益的行为,在侵害程度大致相同时,其法定刑也应当大致相同,这是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得出的当然结论。如果认为受贿犯罪的法益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那么,对比同样侵犯职务行为公正性法益并且以实害犯面貌示人的滥用职权罪,以侵害职务行为公正性法益的危险犯面貌出现的受贿犯罪反而配置了更高的法定刑,这一体系解释的悖论从反面说明公正性说作为受贿犯罪法益并不具有妥适性。张明楷教授在对于“不可收买性说”的修正中,认为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侵害的不再是单一法益,而是复合法益,但从处罚范围上来看,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均规定了“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限制条件,使得其处罚范围较普通受贿犯罪更窄,申言之,依照“修正的不可收买性说”,侵害复合法益的斡旋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要窄于侵害单一法益的普通受贿罪,这在解释论上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二)“不可交换性说”的基本内涵
“不可交换性说”的基本内涵是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应为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其中,职务行为既包含收受利益的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也包含相关的其他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职务行为既可以是已经实施、正在实施的职务行为也可以是将来实施的职务行为;交换的方式就现阶段而言指以财物为对价的交换,同时保留了将其解释为以服务或者其他无形物为对价的可能性;交换的时机可以是实施职务行为之前、实施职务行为之时或者实施职务行为之后;在某些特殊的场合,交换不要求合意,一方存在交换意图并且实施交换行为即可。
(三)“不可交换性说”的界分
“不可交换性说”脱胎于不可收买性说,又与“不可交易性说”具有相似之处,在此有必要对三者进行语义上的界分。“不可交换性说”是对“不可收买性说”的修正,克服了“收买”在语义上单向性的缺陷,兼顾行贿人角度的不可收买和受贿人角度的不可出卖,从而体现了受贿行为的交易性[注]陈伟,汪洁,受贿罪相关问题探析——以受贿罪的交易性本质为视角[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6):119.。此外,相较于“收买”,“交换”在语义上的内涵更为丰富,基于此,“不可交换性说”较“不可收买性说”具有更强的涵摄机能,对于不能涵括在“不可收买性说”语义范围之内的犯罪形态(如事后受财型受贿)具有解释力。不可交换性在语义上与不可交易性类似,两者仍存在差别:交易本指物物交换,后指做买卖[注]夏征农,陈至立.大辞海(第3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1624.,就其语义而言,交易具有正式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当场性,作“做买卖”理解时,双方至少对买卖行为应具有合意,因此,采“交易”的语词表述,不利于将事前没有约定的事后受财纳入到解释范围内。相比较而言,交换意为双方各拿出自己的给对方[注]夏征农,陈至立.大辞海(第3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1621.,不论何时给对方,不论是否有合意,只要双方相互交付,即是交换。因此,相较于交易,交换的表述则更具有随意性,其语义的涵摄范围更广。
综上,“不可交换性说”虽与“不可交易性说”以及“不可收买性说”具有语义上的相似性,细究其意涵,“不可交换说”的涵摄范围更广,因此本文采“不可交换性说”的表述。
四、“不可交换性说”的教义学检视
根据上文的论述,法益的确定应当考察其专属性、涵摄性以及协调性,本文对于“不可交换性说”的教义学检视也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不可交换性说”的专属性检视
通过上文对于受贿犯罪法益不同学说的展示与反思,可以发现,虽然不同法益学说尝试以各种方式描述受贿犯罪的本质特征以使其与其他犯罪相区分,但是基于描述角度的不同,各种学说既表现出相互重叠的特性,也分别表现出了各异的涵摄性,进而展示出了不同的位阶性。具体而言,除贿赂犯罪之外,滥用职权犯罪也可能侵犯职务行为的公正性,贿赂犯罪和贪污犯罪都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受贿犯罪、贪污犯罪以及渎职犯罪都可能影响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而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以及公职不可谋私利性虽然在具体的表述上存在差异,但都揭示了受贿犯罪“钱权交易”的本质,而都只能作为受贿犯罪的专属法益而存在。根据上述法益学说所涵摄的犯罪类型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的位阶:其中,位于第一位阶的是国家职能的正常实现说,其所能涵括的犯罪类型最多;位于第二位阶的是公正性说、廉洁性说,除贿赂犯罪外,它们分别能够涵括其他另一类犯罪类型;位于第三位阶的是“不可收买性说”、“不可交换性说”、“不可交易性说”以及“公职的不可谋私利说”(见表1)。

表1 受贿犯罪法益学说的位阶分析
总体而言,上一位阶的法益具有类法益的性质,基本可以涵摄下一位阶的法益,而作为具体法益的第三位阶的法益,则并不能应用于描述贿赂犯罪之外的其他犯罪类型,因而属于贿赂犯罪的专属法益。在确定某一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时,应当首先考虑专属法益。就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而言,只有位于第三法益位阶的受贿犯罪法益学说(不可收买性说、不可交易性说、不可交换性说、公职不可谋私利说)符合法益确定的专属性要求,能够作为受贿犯罪的适格法益。因此,就专属性的考察而言,“不可交换性说”表现出妥当性。
(二)“不可交换性说”的涵摄性检视
1.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
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法益是不同受贿犯罪法益学说聚讼的焦点,直接决定了学者们对于受贿犯罪法益的基本态度。整体而言,学理上对于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法益之争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上述场合中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即“交易性”。否定“交易性”的观点认为,《刑法》第388条对受贿犯罪保护法益的传统理解形成了挑战,将受贿罪的本质由“权钱交易”扩展至“影响力交易”,这直接导致受贿犯罪的法益不再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注]黎宏.受贿犯罪保护法益与刑法第388条的解释[J].法学研究,2017,(1):67-70.。斡旋受贿场合,处于斡旋地位的行为人并没有利用自身的职权,充其量只能说是利用了自身职位的间接影响,因而并不涉及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的出卖与收买关系[注]劳东燕.受贿犯罪两大法益学说之检讨[J].比较法研究,2019,(5):131.。肯定“交易性”的观点则认为,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并没有否定受贿犯罪的交易性本质,同时认为,其保护法益应当是复法益,即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一方面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其中,不可收买性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身(斡旋受贿);二是国民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利用影响力受贿)[注]张明楷.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J].法学研究,2018,(1):159-163.。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说”脱胎于“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说”,其立论的基础也在于承认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的“交易性”。因此,对于否定“交易性”的观点,应当自觉回应:“交易性”否定说的基本逻辑往往是收受财物的人与实施职务行为的人并不同一,因此难以认定特定的职务行为与给予财物之间形成了对价关系,也就不能肯定职务行为与收受财物之间的“交易性”。在本文看来,仅从此种意义上理解受贿犯罪的“交易性”过于狭隘。“交易性”的基本形态是实施职务行为的公职人员亲自“出卖”其职务行为并取得相应的对价,但利害关系人通过“出卖”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而获得利益所表现出“间接交易性”同样未脱离“交易性”范畴。将职务行为用以交换的行为人所持有的对价虽非其自身的职务行为,但基于其身份、地位或者特定关系,又可以影响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正是基于此,刑法才对此类行为予以规制。当然,刑法也将此类行为的主体明确限定为基于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公职人员(对应斡旋受贿)以及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或者关系密切的人(对应利用影响力受贿)。
“交易性”否定说的观点仍然认为,《刑法》第385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成立受贿罪,并不以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形成对价关系为必要。此外,以“交易性”为基础的法益学说无法说明为什么有关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斡旋受贿行为的立法规定要求成立相应犯罪必须满足“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注]劳东燕.受贿犯罪两大法益学说之检讨[J].比较法研究,2019,(5):131-137.。关于第一个质疑,在本文看来,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规收受的回扣、手续费实际上也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职权)的对价:虽然其可能不存在具体的、直接的职务行为,但是,相应的回扣和手续费是与相关国际工作人员的职权密切相关的。易言之,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相应的职权,相关人员也不会为其提供回扣和手续费,而之所以为其提供回扣和手续费,目的正是获得其在职权行使(职务行为)时的便利。因此,《刑法》第385条第二款规定的受贿罪,仍然没有否定职务行为(职权)与财物之间的对价关系。关于第二个质疑,本文认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条件是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对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要件所作的必要限缩。以斡旋受贿为例,对斡旋受贿的行为人进行处罚的依据是其利用了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但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与职务行为相比,在保护的必要性程度上要低得多,对这一类行为进行规制,则有必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条件进行限缩。
“不可收买性说”和“不可交换性说”同属承认受贿犯罪“交易性”的法益学说,但是其在语义上存在差异:不可收买性说的“收买”对应“出卖”,通常语境下,“出卖”权力者必须拥有权力或者至少拥有对权力的处分权,而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场合,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密切关系人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均不具有“出卖”的权力,因此,对于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不可收买性说”存在语义上的解释困境。而“不可交换性说”的“交换”,对于上述情形则仍具有解释力:国家工作人员以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对价交换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密切关系人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对价交换财物,则存在语义上的合理性。
综合上述,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场合,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与财物之间仍然体现着“交易性”的特性。相较于“不可收买性说”的“出卖”要件,“不可交换性说”的“交换”能够准确地诠释斡旋受贿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交易性”特征,因而体现出更强的涵摄性。
2.事后受财型受贿
事后受财型受贿可以分为事前有约定的事后受财和事前没有约定的事后受财,前者为典型的受贿罪,此处仅讨论后者。“不可收买性说”中,“收买”语境下,实施职务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与财物受特定时空限制,“收买”对应“出卖”,要求行为人在收受财物时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否则不能认为其在“出卖”权力[注]陈兴良.判例刑法学(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642-644.。易言之,收买关系应当在买卖当时已经存在约定,而严格依照“收买”语义,事后受财型受贿中,职务行为实施时并不存在“买卖”的约定。而不可交换性说的“交换”在时空上则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因而其表现出更强的涵摄性:即使是实施职务行为时并不存在约定,而只有事后的受财的行为,也可以将事后收受的财物理解为职务行为的对价,从而肯定两者之间的交换关系。
3.感情投资型受贿
感情投资型受贿是指公职人员收受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财物提供者的财物的行为。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感情投资型受贿因为不满足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而不构成受贿罪。根据本文的立场,“不可交换性说”中用以交换的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可以是已经实施的、正在实施的职务行为,或者将来实施的职务行为,感情投资型受贿即是以现在的财物为对价,交换公职人员将来的职务行为或者对于将来职务行为的期待,从公职人员的角度而言,即将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者将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这一解释路径契合了司法解释关于感情投资型受贿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级关系的下属或者具有行政管理关系的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三万元以上,可能影响职权行使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明确了感情投资型受贿应受刑罚处罚。从比较法角度来看,德国刑法也规定了单纯收受贿赂行为的处罚:《德国刑法典》第331条收受利益罪(Vorteilsannahme)第一款规定:“公务员、欧洲公务员或特别受雇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员,为自己或者第三人而对于职务行使,要求、期约或者收受利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易言之,无论是否实施公务行为,公职人员收受利益的行为均构成犯罪。同样,《德国刑法典》第333条规定的“提供利益罪”(Vorteilsgewährung),对是否实施职务行为,也没有要求[注]StGB§331,§333.。
4.公用型受贿
公用型受贿是指受贿的目的并非为了私利而是出于公用目的或者将所收受的财物用于公共用途。按照刑法理论,受贿的目的为何在所不问,只要公职人员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并且收受了作为对价的财物,行为即已符合受贿犯罪的犯罪构成,至于收受财物的目的以及收受财务之后的用途,只能作为量刑时酌定考量的因素。如上文所述,“公职不可谋私利说”对于公用型受贿不具有解释力。基于本文“职务行为不可交换性说”的立场,只要将职务行为与作为对价的财物互换即已构成对法益的侵害,至于受贿时的目的为何以及收受财物之后的用途,“不可交换性说”再所不问。可见,对于公用型受贿,“不可交换性说”具有解释力。
(三)“不可交换性说”的协调性检视
“不可交换性说”无疑会遭受基于协调性的质疑:如果承认受贿罪的“交易性”本质,那么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就会构成共同正犯的关系,两种行为的不法程度没有明显差别,并且行贿方在贿赂犯罪中属于主动方。基于此,不可交换说立场下行贿罪的法定刑期限至少应当不低于受贿罪的法定刑期限,这与刑法的规定并不协调[注]劳东燕.受贿犯罪两大法益学说之检讨[J].比较法研究,2019,(5):137.。在本文看来,上述质疑忽略了贿赂犯罪在刑法中的体系地位。贿赂犯罪在刑法典中被规定在“贪污贿赂罪”一章中,本章中规定的犯罪都具有明显的身份性特征,或者要求行为人具有特殊身份(如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要求行为对象具有特殊身份。因此身份在本章犯罪中对于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到贿赂犯罪中,行贿者只占据形式上的主动,受贿者则掌握实质上的主导权。详言之,虽然在贿赂犯罪(索贿罪除外)中,行贿者的行贿行为是发动贿赂犯罪的主动因素,但是,是否接受贿赂,是否为他人谋利,决定的主动权却掌握在具有身份的公职人员手中。此外,在贿赂犯罪中受贿者的身份决定了贿赂犯罪的实质,例如,当受贿者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时,行贿者构成行贿罪;当受贿者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时,行贿者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因此在贿赂犯罪中,表面上行贿者占主动地位,实质上则是具有身份的受贿者起决定作用。因此,从法益侵害性的角度而言,受贿罪具有更高的不法性,对其配置更高的法定刑也是合乎教义学逻辑的[注]许恒达.贪污犯罪的刑法抗制[M].中国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6.。因此,对于不可交换性说立场下行贿罪和受贿罪不协调的批评不具有妥当性。
五、结语
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既然信仰法律,就不要随便批判法律,不要随意主张修改法律,应当从更好的角度解释疑点,对抽象的或有疑问的表述应当作出善意的解释或推定,将“不理想”的法律条文解释为理想的法律规定[注]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这便是教义学的使命。关于受贿犯罪的法律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了数量众多的受贿犯罪情形,给教义学的探讨设置了不少障碍,但无论受贿犯罪情形如何驳杂,对于受贿犯罪法益的探讨都不能偏离受贿犯罪“交易性”的本质,否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水中捞月。在承认受贿罪“交易性”本质的法益学说中,本文所主张的“不可交换性说”符合专属性、涵摄性以及协调性的要求,能够经受教义学的检视,是受贿犯罪的适格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