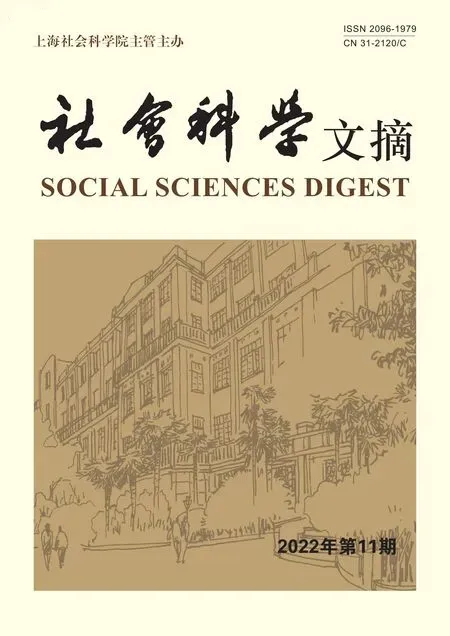论士人画:从苏轼到郑板桥
——“墨石诗意”七百年
文/夏中义
“文人画”“士人画”概念甄别
苏轼(1037—1101,号东坡,下简称“苏”)最早这般言及“士人画”:“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回味再三,拟判苏眼中的“士人画”有两个特点:一曰“意气俊发”;二曰摒弃宫廷气、院体画之工笔毕肖。鉴于“士人画”家“萧然有出尘之姿”,故将此非凡品性诉诸笔墨,当不屑重蹈院体画的精匀线描。这就很难不令后世将“士人画”粗读成是与董其昌(1555—1636,下简称“董”)“文人画”无异。董撰《画旨》,也明确“文人画”须讲“士气”俊爽,化为笔墨即“以书入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甜俗蹊径”,指弥散宫廷气、一味形似的软媚画风。这就与苏说到一路去了。思路若仅止步于此,则“士人画”“文人画”之间也就边界泯然。事实上,中国画学史自明代迄今逾四百年,将“士人画”读成“文人画”的近义词或同义词,已俨然主流。
但事情到2014年生变了,潘公凯、范景中在追认潘天寿(1891—1971,下简称“潘”)为当代中国的“士人画”家时,实已形成如下共识:即与闲情遣兴的“文人画”相比,潘自有更高追求,潘是以奇崛磅礴之笔墨,来表征他对跌宕国史的赤诚感应及道义责任——而这般将“家国情怀”沉凝为“个体道德”的内在律令,在中华文化史上只有儒士方能担当,故其水墨所饱濡的价值自觉,只有尊其为“士夫画”(即“士人画”),才名副其实。于是,在潘公凯敬仰潘天寿为“中国艺术界的最后的‘儒士’”之同时,范景中也说出了“一个自己酝酿已久的观念:潘天寿是学者画家,更是士人画家”。潘公凯、范景中的细微差异则在:若曰前者是从宏观国史、人生履历来对潘“人格自圣”作动态考量;那么,后者是将大画家品性置于“道德的力量与艺术的质量”之微观框架作静态审视,其结果,发觉潘“始终把个人道德修养放在一个比社会伦理更高的位置之上,这正是儒家士人的精义所在”。
精准定义“文人画”“士人画”中的那个“文人”“士人”究竟何谓,无非两种:要么将“文人”“士人”径直读成画家的社会身份;要么将“文人”“士人”含蓄地读作对画面所示的精神级差的隐喻性命名。现代水墨史让笔者选择了后种读法。
现在要问,回溯中华水墨史自宋至清八百年,能否觅得这样一个造型元素,它不仅能微妙隐喻画家的生命样式暨价值意向,并且能像分界石一般精准地标识“士人画”“文人画”之间的异质边界?有,传统花鸟画题材有个元素叫“石头”,不论它是被苏轼、郑板桥涂成皴痕郁馥的“诗意墨石”,还是被米芾、陈洪绶“拜”成青灰嶙峋的太湖石,它在文化心灵史上,确乎早就在深浅不一地代言历代画家的精神生命状态,成了中华君子用笔墨来刷其人生“存在感”的器识性符号。
苏轼《怪石枯木图》的诗画互证
对苏轼《怪石枯木图》作诗画互证,说苏轼是比米芾更具“价值含金量”的“石痴”,有必要先释疑如下:为何“米芾拜石”之传奇,反而比“东坡怪石”之史载更深入人心?
就纵向传播而言,确凿实录的“史载”,往往不如传奇性“史传”更易吸引历代眼球,关键仍在“阳春白雪,和者必寡”,门槛高了,那些不适宜高抬腿的人便会割爱。米芾“拜石”之史传宛若行为艺术的隔世快闪,能轻松地满足后人的猎奇心;而苏轼“墨石”之史载,则若无中华艺文史暨心灵史的深层探询,怕很难估计其价值含金量几何。这不是非专业性猎奇所能耳食且消化的。拜读苏轼诗文,追认苏是不亚于米芾、且有过之无不及的“石痴”,史据有二:一是苏确像石颠一般痴迷“石头”,其于1082年所作《怪石供》和1085年所作《书画壁易石》是典型例证;二是苏在《怪石供》中还像学院派对所谓“怪石”作逻辑定义及分类,这是石颠做不到的。
从《苏轼文集》抠出的“怡性之石”与“米芾拜石”之石无大异,其实苏也曾撰文《法云寺礼拜石记》。然《苏轼诗集》所深藏的两块“安魂之石”却郁结凝重得让石颠没了可比性。这是两首写于不同时段的咏石诗,前后相距八年,却又像苏不经意创编的两台连续剧,分别让两块石头担纲主角:一块是苏于元丰八年(1085年,时48岁)在扬州太守官邸所激赏的、有棱有角的青绿“醉道士石”;另一块是苏于元祐八年(1093年,时56岁)丁忧居蜀时梦见的、本系乌有、却又奇思般灵异的丑石。这两块石头,粗读是一实一虚,一阳一阴,判若霄壤;细读却相信这是苏在对其灵魂作逼迫性叩问。然也有差异:前者是让苏从石头形态痛感自我命运之跌宕多乖;后者则像鬼魂在歌哭诗人须更悲怆地醒悟“我是谁”。
《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是用五言编织了一篇狂猿化石之传奇。苏诗对此石“顽且丑”所生发的天人浩叹,与其说是为了应酬杨太守的青眼相邀,毋宁说更是为了隐喻自身因其独立政见、旷世襟怀、绝代才情而落下的遍体鳞伤与一腔幽愤(勿忘1079年乌台诗案,1080—1084年苏蛰居黄州)。《咏怪石》是用韩愈式五七言混搭的即兴咏叹,此诗是将作者想象为两个已在心灵深处争执得极苦的对手,实是隐喻两种甚难兼容的人格意向。一种是朝野庸众,独尊读书当官、功名利禄,于是也就很难像大丈夫做到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其身心早被朝纲矮化得卑琐不已,还以为头顶乌纱,便高人一等,自欺欺人;另一种是脱俗君子,体认这世上没有比做一个独立、自由的尊严个体更富有诗意,更能像太阳吸引春花、月亮舒卷秋潮一般,劝人以此为终极根基来安顿灵魂,由此,则朝野历代所主导的种种诱迫,也就与己无涉。这若用马克斯·韦伯的词语来转述,也可谓前者属“工具理性”,后者属“价值理性”。看得出《咏怪石》是让诗人屈尊来代言朝野庸众的“工具理性”,让“怪石”来代言脱俗君子的“价值理性”,宛若一出戏,在诗人与“怪石”间诡异地揭幕。
做实了1085—1093年苏咏石诗这篇文章,将有助于解析1080年苏绘制的《怪石枯木图》。不妨说,苏1080年创绘《怪石枯木图》的幽深意念,确可被1085—1093年的咏石诗惟妙惟肖地逐层显影。这就意味着,苏当初画《怪石枯木图》留下的诸多造型密码,不仅今人只睹其形、难识其神,即使让作者现场说明,恐也难说透其底细。悬念至少有三。其一,这幅画在让枯木与怪石配对时,为何将枯枝画作鹿角状?其二,此“怪石”为何被一圈圈墨线缠得郁复不已,紧得透不过气?其三,当整幅构图被设计成蜗牛状时,则其造型元素之视觉效果也就生变:原先鹿角状的枯枝被疑拟蜗牛细脖上的纤柔触角;原先那块苍黑墨石则被化为蜗牛背上卸不掉的沉重硬壳——这又在暗示什么?
或许针对悬念一,苏会脱口道枯枝作鹿角状典出“鹿鸣宴”。唐宋流行科举考试后,皆有州县长官宴请主考官、学政及中试考生之仪式,凡宴必诵诗经“鹿鸣”篇。这是中举者跻身官场之必经门槛,也是苏曾亲历的“金榜题名”时刻。但为何将树杈画作“枯木”?米芾题在此图的五言或许披露一二:“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知世路险,老觉道心微。”苏生于1037年,1077年4月始任徐州太守,恰逢“四十”不惑之年,转眼1079年4月因“乌台诗案”而入狱,这又对上米诗云:“三年不制衣。”唐宋官吏服色颇制度化,不同官品者着衣服色大异,无非是以此来标识朝廷对各级官员的心身制约。但苏是天纵之才极具洁癖,若遇邪恶,便“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当然不屑在朝廷违心腆颜地“追陪新进”(新贵),自然其“谢恩表”又会将此孤傲称为“臣性资顽鄙”。这也就太不给“新贵”面子了,窘得那拨小人非置苏于死罪不可,其大罪状即无礼于朝廷甚至不把今上放在眼中。类似情节若以婉词道出,即米诗云“三年不制衣”。意谓朝廷套在苏身上的朝服冠冕,根本约束不了其洁癖天性,苏无论主掌徐州还是湖州,皆性本丘壑而不拘于官场礼法,这也就形同脱去道袍而赤裸,酷似扒了树皮的苍柏而成“枯木”。
悬念二,那图上“怪石”为何被一圈圈墨线缠得艰于呼吸?其实,苏也未必不知他这“枯木”般赤裸地抵挡歹毒的唇枪不可能不被抹黑;或许他亦曾一次次地劝自己无妨虚伪,但其内心却又一次次地拒绝苟且或沦陷;他也弄不懂其胸中的“怪石”为何这般纠结、坚硬得迹近偏执?1085年苏开始觉知那就是他在杨太守处所震惊的、被凝冻在“醉道士石”里的那种无羁无绊的本真天性;1093年苏更体认那个鬼魅般“怪石”所赠言的“震霆凌霜我不迁”“子盍节概如我坚”,才是自己须臾不可离弃、愿以生命去抵押的人格尊严,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世上没有什么能比将自在“自身”历炼成自由“自我”更值得追求了。
再来看悬念三,图上“蜗牛”背上的“硬壳”,究竟是阻碍仕途晋升的沉重包袱,还是鉴证东坡所以为东坡的灵魂之重、本就该有的秉性叫“生命中无可承受之轻”?从1080年绘《怪石枯木图》到1093年《咏怪石》诗,苏已渐愈体认他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了。所以,当黄庭坚(1045—1105)《题子瞻画竹石》诗云:“风枝两叶瘠土竹,龙蹲虎踞苍藓石。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竟确认图上“怪石”本即师尊酒后呕出的、在内心郁结甚久、甚重的一团浓墨,这是何等眼光、何等气魄。
郑板桥“竹兰石”诗意序列分析
对郑板桥“竹兰石”作诗意序列分析,说此石才是士人画史上直接传承苏轼“墨石”的“安魂之石”,有人不免质疑:从苏轼到郑板桥毕竟契阔七百年,况且其间还有从米芾到陈洪绶(字老莲)的“拜石绘事”,为何独独对郑板桥“竹兰石”别具青眼?这儿先说两点:一是从米芾到老莲“拜石绘事”就其价值取向,属“文人画”史,本文则关注“士人画”史;二是笔者拟撰文《论文人画:从米芾到陈老莲》,以期确认老莲绘石对“米芾拜石”的“峰谷体验”(从峰顶跌落地下),似表明老莲的艺术心灵特点是在“凡庸之深刻”及“深刻之凡庸”。“深刻之凡庸”,是指在“怡性不可替代安魂”一案,老莲远比米芾体悟得深刻,一块太湖出身的“怡性石”曾让米芾揖拜得不亦乐乎,从未反省其“怡性石”能否像东坡“安魂石”一般沉毅恢弘,老莲却痛悔“怡性绝非安魂”。“凡庸之深刻”,则指老莲无论怎样图示“从怡性到安魂”此路不通,但他只能止步于“米芾拜石”之边界,而进不了“东坡怪石”的诗意境界。与“米芾拜石”相比,“老莲绘石”无疑要深刻;然与极天才的“东坡怪石”相比,老莲不免逊色。真能在清代遥接“东坡怪石”诗意之非凡嗣响的,是领衔“扬州八怪”的郑板桥(1693—1766,下简称“郑”)的“竹兰石”。
清代传人对北宋先知的这一“价值认祖”,若落到对彼此“造型元素结构”作逻辑比较,当可鉴其“亲缘性”。此“亲缘”再借化学“同位素”视角来看,则东坡“怪石枯木”与板桥“竹兰石”,又可谓是典型的“同分异构体”。说东坡“怪石枯木”与板桥“竹兰石”的“分子式相同”,是说这两者的“造型元素结构”竟皆与植物学上的“块茎结构”呈(如土豆)“对称”:东坡“怪石”对应“块”,“枯木”对应“茎”;板桥“峭石”也恰对应“块”,“竹兰”对应“茎”。阐释东坡抓住“怪石”“枯木”的交互关系,“两点一线”;阐释板桥则须深入到“竹”“兰”“石”所连成的“三角形”(下简称“△”)去作精微的诗意序列分析。此谓“异构”。
序列一,“竹”的诗意分析。“竹”被公认为“竹兰石”整体构成的第一元素,其理由当是郑在“扬州八怪”中以画竹最多而著名。然郑画“竹”,为何偏与“兰”与“石”绘成一个招牌式“诗意△”?或曰郑“竹”所喻指的诗意,为何只有在“诗意△”才可能被说透?历代花鸟画中“象征文人和君子的文化品格”的梅兰竹菊之“竹”,极容易让后世径直将郑“竹”与“气节和人品”挂钩。但若对郑“竹”读得更专业些,不得不辨“气节”未必等同“人品”:“气节”侧重君子的道德自律或坚贞不阿;“人品”则涵盖君子的济世襟怀与悯民深情。“气节”主内倾,“人品”较外向。这落到郑“竹”的水墨造型来看就一目了然。郑“竹”若真是象征“气节”,郑就不宜将其绝大多数竹竿、竹枝画得这般纤细、一折脆断;相反,郑更应模拟北宋文与可将竹竿画得较粗壮坚韧,不易折断。郑颇具主见,未视文与可为楷模:“文与可、吴仲圭善画竹,吾未尝取为竹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0年版《郑板桥画集》(下简称《画集》)选辑郑“竹”图甚多,稍作功课,便可验证郑“竹”确凿画出了不同于文与可的独特诗意。据统计,这本94页的《画集》辑录郑“竹”图计60幅,除2幅竹竿较粗、不易折断、意在喻指“气节”外,其余58幅皆细竿纤枝肥叶,其所喻指的诗意决非“气节”所能涵盖。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郑在潍坊当七品知县时写的这首题画诗极重要,像金钥匙能一气打开三把密码锁:一是郑为何强调“竹”“祝”谐音?二是郑“以书入画”,融入山谷、东坡笔意来画“竹”的动机究竟何在?三是郑1753年遭黜(时61岁),只身南漂扬州煮字卖“竹”,为何不见卑琐憋屈,反倒愈挫愈奋,名满天下?
先解第一把锁。“竹”“祝”谐音,出于郑1762年(时70岁)绘《华府三祝图》的题款:“写来三祝仍三竹,画出华封是两峰。总是人情真爱戴,大家罗拜主人翁。”“华封三祝”典出《庄子·天地》,是谓古时华州人对上古唐尧的三大祝福即“多富、多寿、多子孙”。郑在潍坊夙夜行役、每每寝卧衙斋之际,也在想如何将他对民间百姓的那份柔美怜悯表达出来;否则,从窗外传入的风竹潇潇,他也会幻听作底层弱者辗转于泥坑的呻吟而不得心安。于是,他想用墨竹“一枝一叶总关情”来劝勉自我,即自己在面对黎民疾苦时终究没冷漠地装睡,相反,其身上的每根神经皆像竹叶会因寒风凄冽而颤栗。
再解第二把锁。郑有两次表白他以东坡、山谷书法入墨“竹”画法,但郑未说为何偏借东坡、山谷笔意来助其画“竹”,或东坡、山谷笔意究竟怎样成全了郑“竹”的“凌云意”。解此锁的密码仍藏在“一枝一叶总关情”里。请细嚼“一枝一叶”四字。当他别具慧眼地用山谷的瘦硬笔锋来支撑竹竿竹枝以彰显其孤高凌云,用东坡的短肥笔触来舒卷竹叶以昭示其悯民情厚,这确是天造地设般的门当户对。
续开第三把锁。郑虽可为民遭罪而无怨悔,然对朝政之不公不义,他当作挑战性宣泄。郑曾说自己不同于清初石涛,石涛画“务博”,自己“务专”,“五十余年不画他物”,仅痴迷于竹,“竹其有知,必能谓余为解人”。历代墨客画墨竹者无数,怕只有郑才有底气这般将咏竹与对自我的英雄式豪迈自嗨融为一体:“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为龙为凤上九天,染遍云霞看新绿”;“一阵狂风倒卷来,竹枝翻回向天开。扫云扫雾真吾事,岂屑区区扫地埃”。
序列二,“兰”的诗意分析。抓两个疑点:一是郑为何强调兰、竹“同根并蒂”?二是郑有否省思兰、竹亦宜“阴阳守衡”?所谓“同根并蒂”,出自郑诗:“兰竹芳馨不等闲,同根并蒂好相攀。”这不是着眼于植物学(兰、竹同属草木类),而纯然是着眼于郑特有的诗意关怀,郑是把竹、兰视作“同”一人格“根”基的“并蒂”喻象来看:“竹”是象征郑的济世性“悯民”之人品;“兰”是象征郑的遗世性“养德”之气节。其圣贤级气象之“芳馨”当非“等闲”之辈所有,故竹兰关系在郑的诗画框架无疑天然高贵,最宜相亲“相攀”。
那么,兰、竹“阴阳守衡”又何谓?这是后学从郑的诗画读出的心得,然不惮说这未必不是郑的潜台词,只是郑不这般概括而已。人心结构的硬道理不离“阴阳守衡”四字。于是不免忧思:像郑这般极高调地张扬其济世性人品,他内心若不同时极低调地静养其遗世性气节,则这位奇才怕很难活到古稀之年,就会悲剧性脆断。西学将此人生悲剧命名为“善的脆弱性”。因为皇权与鄙俗所无形合谋的暧昧现世,想窒息一个独立、自由的天才生命并非难事。至少从郑的平生暨阅历来看,已有两条引发其省思:一是要挡住体制性诱惑;二是要忍住人际性孤独。郑为了能在现实生态中持续其济世性人品的迥拔不群,他在内心道德上务必不懈地涵养其遗世性气节的贞洁不移。前者阳刚如“竹箭”,后者阴柔如“幽兰”。如此“阴阳守衡”被诉诸诗画,也就可解郑为何热衷于让墨兰墨竹同框,且不时咏叹不已:“石上披兰更披竹,美人相伴在幽谷”;“老夫自任是青山,颇长春风竹与兰”;“惟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
序列三,“石”的诗意分析。同样作为史述“文人画”“士人画”分流的那类器识性墨石,东坡“枯木怪石”与板桥“竹兰石”在士人画史上究竟呈何关系?两者皆堪称“安魂石”,为何东坡“怪石”只算“破题”,而板桥“竹兰石”才是“解题”?说墨石“安魂”,那么,“为何安魂?怎样安魂?安魂何果?”这其实也是回应“士人画”何以区别于“文人画”时绕不开的问题。东坡是画“怪石”在前(1080年),《咏怪石》在后(1093年),东坡用墨线来直觉怪石有安魂“意向”,到用诗行来“自觉”怪石有安魂“功能”,隔了十三年,嗣后又因谪迁颠簸丧乱,遽归道山,没时间没心思去回答这串“诗意”之问。这在客观上,亦为近七百年后板桥“竹兰石”之横空出世,腾出了回应如上“诗意之问”的艺术—心灵史空间。说东坡不无自觉的“诗意之问”(破题),到了板桥腕下,才画成不无系统的“诗意之学”(解题),未必夸饰。“诗意之学”宜分三点概述之。
第一,“为何安魂”?那是基于“善的脆弱性”,而对“竹”为喻象的济世性人品之犀利,对“兰”为喻象的遗世性气节之洁白,在画家内心所酿成的“双重忧思”所致:既忧前者“峣峣者易折”,又忧后者“皎皎者易污”——郑胸中焉能不生“安魂”之祈愿?
第二,“怎样安魂”?郑是对症下药,两手抓,两手皆硬:既为“峣峣者易折”之竹提供“靠山”;亦为“皎皎者易污”之兰提供“空山”。“靠山”“空山”不指他物,正指其画上那尊站在竹兰背后永恒给力的坚硬峭石。郑咏叹“安魂石”怎样当竹之“靠山”的词句颇丰。最著名、最脍炙人口的当数这首七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第三,“安魂何果”?郑曾这般自述其生命境况:“板桥最穷最苦,貌又寝陋,故长不合时;然发愤自雄,不与人争,而自以心竞。”“自以心竞”,在此不妨作“独自安顿心灵”解,亦即“安魂”。郑以“安魂石”既替“竹”所隐喻的济世性人品安顿于“靠山”,又将“兰”所隐喻的遗世性气节安顿于“空山”,郑作为一位有诗哲智慧的大画家的生命质量,在其晚境有多优质且迷人,当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