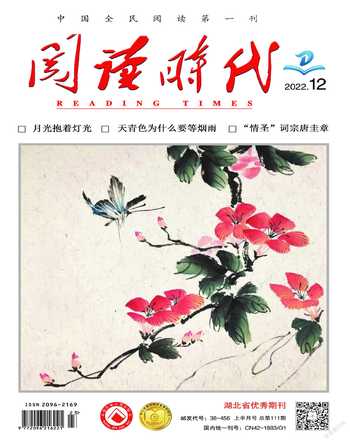古人也跟帖
杨建民

古人读书比我们好,我信。可是,现代印刷术传布,互联网拓展,今人阅读之便捷,相信古人很难企及。
譬如通过网络阅读,虽说碎片化些,可一篇文章流出,后面七言八语跟帖,议论纷纷,说好评差,多少热闹。原以为这是今人独有的优势,哪知在看了清人的《幽梦影》之后,这优势也显得不那么明显了。
读书
《幽梦影》作者系明末清初文学家张潮,有名文化之地徽州(今安徽歙县)人,其著述甚多。此书倘归类,应该是笔记随感一路:天地自然、人生况味、庭院花草、阅书心得……几乎无所不谈,还大都是以人们喜欢的格言、联语形式。作者内在灵动,并不书卷气,故笔下有味,许多还有趣。这些可以引发读者兴趣的因素外,还出现了古书十分少见的“跟帖”:在几乎所有章节之后,有少则三两人,多达四五或更多人加以评说、附和、打趣……这些评说者,从表达看,与张潮性情相近。他们文字大都精粹,也尽量在有趣有味上下功夫,虽为评语,可运笔老到,与原作搁一起,常常有彼此映照、互为生发之效,这让读者观阅时,更加一层感兴之愉悦。
《幽梦影》一小节直名“书”:“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能用不难,能记为难。”此节说的是读书由表入里,层层上升要求。读书一般终于致用,可此节最后却说“能用不难,能记为难”。这里的“记”,笔者以为,是记得读书的基本功用主旨,即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这样一来,就比仅仅能用又高出一层。此节后面三人跟帖,一洪去芜说:“心斋以能记次于能用之后,想亦苦记性不如耳。世固有能记而不能用者。”显然未解此“记”之真谛。另一王端人说:“能记能用方是真藏书人。”再一张竹坡说:“能记故难,能行尤难。”此处之“行”,显然不是用,应该是“践行”书中的精神要求层面。张竹坡是当时著名文人,评点过《金瓶梅》,他的见解,高出他人一筹。
读书所获,也分生命阶段。张潮有一节谈及此:“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所谓“窥”者,当为视野窄、有限;“望月”,似乎全看清楚,认识明白;“玩”就不同,是领略、体会、把玩。人的阅历增加,世事历练,对事物,包括他人文字论说的书,自然不一般。这大约是“破万卷书”还得“行万里路”的深层理由。此节后跟有三贴。一是黄交三对作者说的:“真能知读书痛痒者也。”一是张竹坡:“吾叔此论直置身广寒宫里,下视大千世界皆清光似水矣。”本来是赏月,却说从月宫下视(反观),眼界不凡且清澈,对张潮点赞评价极高。另一毕右万者说:“吾以为学道亦有浅深之别。”此处所谓“道”,应是古人认为的人世及自然规律,这当然比读书更宽广,可认知道理的过程却有相似之处。
境界
相关读书作文说法还很多,可其他妙语也不少。春天了,作者有一节“春听鸟声”:“春听鸟声,夏听蝉声,秋听虫声,冬听雪声;白昼听棋声,月下听箫声,山中听松风声,水际听内乃声,方不虚生此耳。若恶少斥辱,悍妻诟谇,真不若耳聋也。”此节有趣,春夏秋冬、白昼月下、山中水际……这些雅趣声听过之后,又回到现实,拉“恶少”“悍妻”进来,对照鲜明。张潮会写文章。此节大约因为有此一变,后面跟帖者众多,选几个帖子看看。一朱菊山说:“山老所居,乃城市、山林,故其言如此。若我辈日在广陵城市中,求一鸟声,不啻如凤凰之鸣,顾可易言耶。”正是。你张潮有处可听闻,许多城市人,连一声鸟鸣且不易听到,遑论其他。张竹坡也跟帖:“久客者欲听儿辈读书声,了不可得。”竹坡的见识总不寻常。你听到的基本为高雅之音,可人世人情人伦之声,也该考虑进来的,譬如在外者念想家中孩子读书之声。一张迂庵者言:“可见对恶少、悍妻,尚不若日与禽虫周旋也。”随即补充:“读此方知先生耳聋之妙。”这些评语,使得张潮原作得以丰富,跟帖与原文共生了。
還说佳境:“赏花宜对佳人,醉月宜对韵人,映雪宜对高人。”“韵人”该是有韵致之人吧;“高人”者,超脱之人。这般相合的“人”“境”,要求实在太高。不说佳、韵、高人稀少,就算有,对月赏花映雪之时,也难能凑泊呀。后面跟帖者,一位余淡心不甚同意作者说法。以为:“花即佳人,月即韵人,雪即高人。既已赏花、醉月、映雪,即与对佳人、韵人、高人无异也。”此帖跟得不错。不一定非与作者同调,才见出跟帖的自有价值。另有江含征引用苏轼两句诗跟上帖来:“‘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扬州鹤”为故典,指极为美好愿景。此人引苏轼句子,应该是说张潮的境界要求太高了。
缺憾
有佳境便有缺憾。张潮有这样两句:“新月恨其易沉,缺月恨其迟上。”这是看月亮的心情。一孔东塘跟帖:“我唯以月之迟早为睡之迟早耳。”此人说得妙,他是跟随月亮起伏而调整睡觉时间的。一名孙松坪跟帖说:“第勿使浮云点缀,尘滓太清足矣。”观月不使得浮云遮蔽,甚至清空不要一点尘滓,这要求太高。一冒青若者跟帖:“天道忌盈,沉与迟请君勿恨。”此人通达。无论人世、自然,忌讳追逐盈满,“沉”或“迟”其实是常态,遇上,不必深恨。张竹坡跟帖:“易沉迟上,可以卜君子之进退。”这又高了一层。从一个人观察月亮的态度上,可以知道其对待世事的认知,也就大致可以推知此人生活之路的升迁腾伏了。
这缺憾仅仅在观月。下面,张潮小结出“十恨”来:“一恨书囊易蛀,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焦,五恨松多大蚁,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荷易谢,八恨薜萝藏虺,九恨架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把生活太过理想化,不能如意,便无端生出恨来。读到这些,他人也有各自看法。一江菂庵者跟帖:“黄山松并无大蚁,可以不恨。”举出例外,消解恨意。张竹坡跟帖:“安得诸恨物尽有黄山乎?”这么多恨,包含黄山不?问得好。胜过三山五岳的黄山,你总不能“恨”吧。也在说恨多了些。一名石天外人跟帖:“予另有二恨,一曰才人无竹,二曰佳人薄命。”这两条,相比一般了些。
总体看去,《幽梦影》一书多风花雪月,追逐风雅,可偶然,也论到人间贫富:“为浊富不若为清贫,以忧生不若以乐死。”“为富”中间,作者加一“浊”字,似乎希望这“富”来得干净,否则不如“清贫”着。这大约只表现张潮自己的想法,跟帖者却不见得认同。一位李圣许跟帖:“顺理而生,虽忧不忧;逆理而死,虽乐不乐。”此人不论贫富,只在忧乐二字探讨。他的说法心理学上有支持,“顺理”牵涉认知,自己认为合切,便心安自在,所以生活之“忧”也就不算多大事;可如果“逆理”,与理相悖,那无论怎样,也难得快乐。可另一吴野人不同意前面看法,他跟帖说:“我宁愿为浊富。”他应该是友人,所以这般与作者反着来。这也不能过于当真。同是读书人,应有一些基本相近的价值观,可生存世间,也未尝不透露些不忍贫寒的心态。还是张竹坡说得中和些:“我愿太奢,欲为清富,焉能遂愿。”愿意过得好些,可希望这富庶来得干净(清),怎样才能遂愿呢?看来,他对此是有疑问的,这疑问,反而说明他的清醒。
去年读报,看到宗璞先生谈枕边书时,说到《幽梦影》,认为书中表现的是“中国文化的审美情趣”。而从时代看,《幽梦影》描摹的“情趣”,颇为精致,同时单薄,少了《诗经》的质朴,《楚辞》的飞扬华美,汉唐的金戈铁马……它是明清时期的表达,可以成为我们认识此时文人情趣部分。当然,当时居然有“跟帖”风习,更有文字记录下来,这又让我们感觉意外,同时也感佩古人的创获。
(源自《北京晚报》)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