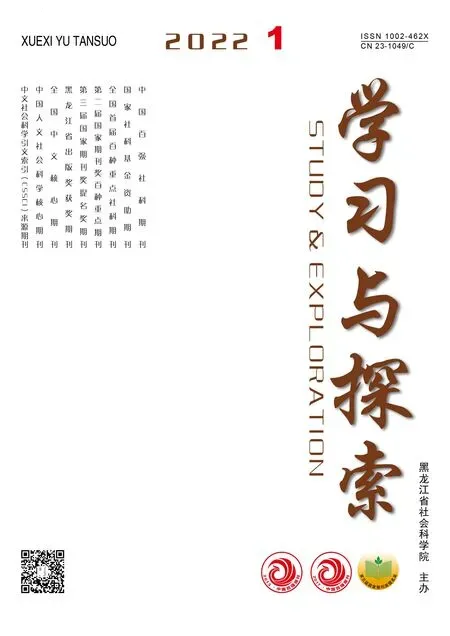“共同体焚毁”之后:论卡夫卡的当代意义
曾艳兵,贾思稷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杰出学者、结构主义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希利斯·米勒在《共同体的焚毁:奥斯维辛前后的小说》一书中指出,研究卡夫卡作品和大屠杀小说责无旁贷。“卡夫卡的作品预示了奥斯维辛,凯尔泰斯的《无命运的人生》回应了卡夫卡,而莫里森的后奥斯维辛小说《宠儿》具有卡夫卡小说的特征(Kafkaesque features)。”[1]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预示了大屠杀,是因为他的小说描绘了共同体的焚毁。卡夫卡的作品不仅预示了大屠杀,还预示了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当代欧洲著名哲学家南希在《无用的共同体》一书中写道:“现代世界最严峻、最痛苦的见证就是对共同体崩解、错位和焚毁的见证(the testimony of the dissolution, the dislocation, or the conflagration of community)。”[2]共同体的焚毁导致诸多人类灾难的出现,因此,重建共同体,或者说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当代中国学者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当今全人类应当思考和关注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阅读卡夫卡,或重新阅读卡夫卡,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一、“不可摧毁之物”
在“共同体焚毁”之后,人类最珍贵的就是共同的信心、信念和信仰了,用卡夫卡的话来说,就是人的内心的“不可摧毁之物”。卡夫卡认为,“人不能没有对自己内心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持久的信赖而活着,而无论是这种不可摧毁之物还是这种信赖也许都长时间地潜藏在他身上。这种潜藏的表达可能性之一是对一个自身上帝的信仰”[3]48。这种对“某种不可摧毁之物的持续不断的信赖”就是对人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信赖。在卡夫卡心中的上帝是存在的,虽然对于这个上帝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卡夫卡的“自身上帝”不能说是什么,但一定是“不可摧毁之物”。
1918年1月18日,卡夫卡在一则笔记中写道:“上帝说,亚当必将在吃知识之树的果子那天死去。按上帝的说法,吃知识之树的果子的结果是当场死亡,按蛇的说法(至少人们至此还能理解它),其结果则是与上帝比肩。二者都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为不正确。人没有死,而是变成有死亡的,他们也没有变得与上帝同等,但却获得了成为同等的不可或缺的能力。二者也以同样的方式表现为正确的。不是人死去,而是天堂的人死去,他们没有成为上帝,但是得到了上帝的智慧。”[3]58在亚当偷食知识之树的果子这件事上,一方面上帝和蛇所说的都不正确:亚当既没立即死去,也没有成为有上帝;另一方面上帝和蛇所说的又都正确,因为从此人必有一死,但人同时得到上帝的智慧。人虽有一死,但又可以思考死。正是因为有了死亡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死亡是所有人都必须思考、关注和面对的问题。
宗教的荒诞并不成为否定它的理由,反倒成为它存在的依据。因为按照卡夫卡的逻辑,上帝的逻辑和人的逻辑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克尔凯郭尔曾特别论述过亚伯拉罕的牺牲:“依世人的标准来看,上帝的要求既蛮横又不公正,而另一方面,世人的责任就是按照这种他无法理解的神的法律来指导自己的生活,哪怕是他从天上得不到丝毫的帮助也得如此——这就是卡夫卡信仰的另一面,而这正是他最伟大的作品《城堡》的戏剧基础。”[4]57-58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方面的胜利就意味人世方面的失败,反之亦然。“卡夫卡所写的全部故事都是关于一个问题的直接的想象的表达,这个问题就是:置身于这个世界的人类怎样才能调节自己的生活以便与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法律保持一致,这种法律的奥秘是人类永远也无法确切地加以解释的,尽管看上去这些奥秘并不是什么奥秘。”[4]565人类怎样与另一个世界的法律保持一致?后者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信仰问题,也就是“不可摧毁之物”的问题。
卡夫卡一生似乎缺乏统一的坚定的宗教信仰,但他始终不缺乏对个人乃至人类命运的关怀,他对“不可摧毁之物”的坚信终其一生。卡夫卡写道:“心理分析学认为宗教的起源也无非在于单个的人的‘疾病’之中。当然今天没有宗教的共同体,分支不计其数,而多半又局限于单个的人。”[3]195在卡夫卡的心中,一方面没有上帝,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上帝。这一点与他被认作具有血亲关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相似。上帝是什么,或者上帝是谁、谁的上帝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必须有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不可摧毁之物”,就是卡夫卡内心坚定的信仰。
就宗教而言,对卡夫卡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犹太教。一直以来,犹太教就存在着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两股对立的潮流。理性主义试图通过哲学思辨来阐明犹太教信仰,而神秘主义则主张消灭自我,进而达到灵魂的飞升,强调的是内心体验。在卡夫卡的宗教观中,这两种潮流此消彼长,从未达到过和谐统一,任何一种潮流或者作为总体的犹太教显然并没有成为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卡夫卡的“不可摧毁之物”应该另有所指。
“不可摧毁性”是卡夫卡思想的核心:“他的信仰观和人正论都是通过这一观念来表达的。人之不可摧毁,乃因为他有神性本质,神性包含在人受造之初的天堂状态即‘原始性’之中,是每个人生命的基质,是人的潜在性和可能性。”[5]卡夫卡认为:“不可摧毁性是一体的;每一个人都是它,同时它又为全体所共有,因此人际间存在着无与伦比的、不可分割的联系。”[3]53这种不可摧毁性,就像一个伟大的作家或者一部伟大的作品,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唯一的,又是整体的。
1918年2月25日,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并不是惰性、恶意,或笨拙……导致了我的失败,或者甚至都谈不上失败:家庭生活、友谊、婚姻、职业和文学。这里缺少的是立足之地、空气和法规。我的任务就是去创造这些,并不是为了补回过去损失,而是为了不失去任何东西,因为这一任务就像其他的任何任务一样有益……我不是像克尔恺郭尔那样被基督教的那只沉重的手指引着去生活,也不是像犹太复国主义者那样抓住了正在飞逝的犹太教袍的最后的衣角。我就是终点或开端。”[3]74-75(1)译文根据英译本略有改动。卡夫卡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犹太教徒,但他也说不上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也总在祈祷。卡夫卡一方面在最大胆地怀疑,另一方面又在最虔诚地祈祷。卡夫卡是一个总在怀疑的祈祷者。他通过写作表现了他的怀疑,又通过写作实现了他的祈祷,因为“写作就是他的祈祷的方式”。
卡夫卡一生都在追求无限和完美,这种无限和完美就是他的终极关怀。“他不是一位宗教作家,但他把写作变成了一种宗教。”[6]写作就是他的终极关怀,就是他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卡夫卡将写作当作自己的唯一财富,为此他甚至排斥生活,更是拒绝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充满罪孽的失误,对生活的亵渎”。一方面,卡夫卡特别害怕死亡,因为卡夫卡都没有好好生活过,而死亡会终结他的创作;另一方面,卡夫卡必须拼命写作,而这种拼命又将他一步步逼向死亡。卡夫卡终其一生都在与他写作的障碍,诸如工作、恋爱、疾病做斗争,这种斗争惨烈异常,卡夫卡最终几乎葬身于此。然而,这种斗争又是卡夫卡创作的主题,他总是从这种斗争中汲取力量和灵感。这种斗争最后便成为了卡夫卡写作的对象和意义。生命、斗争、写作;写作、斗争、死亡,结局就是终点。1922年1月23日,卡夫卡对自己短暂的一生作了概括:“在我这一边,我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了。我好象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有了一个圆心;我也好象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得先走出一条半径来,然后按这条半径,划一个美妙的圆圈。可是我并没有这么做。我总是在刚走完助跑线、开始走半径的时候,就不得不停下脚步来。”卡夫卡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他感到自己一无所获。“我以刚开始走的那条助跑线为半径,划了一个圆圈,以上那些事情在这个圈子里凝固了。我也不可能作任何新的尝试了,我已上了年纪,什么神经衰弱等毛病,我都无所谓了。我也知道,再作任何努力也是白费,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7]卡夫卡一生执念于写作,这就是他的生命之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即便在生命的最后,卡夫卡委托朋友布罗德焚毁他的手稿,但有些已经发表的作品,并不在卡夫卡焚毁计划之列。卡夫卡对他的作品、人类和世界仍然抱有希望。
二、“无限多的希望”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评论家伊格尔顿在2015年出版了《不乐观的希望》(HopewithoutOptimism)一书。伊格尔顿在这本书的书名上借用了卡夫卡的表达方式。卡夫卡的朋友布罗德在卡夫卡去世后撰写的《卡夫卡传》中写道,有一次他问卡夫卡:“还有希望吗?”卡夫卡说:“哦,很有希望,很大希望,但不是对我们来说。”伊格尔顿随后解释道:“卡夫卡的意思很隐晦,但是有很多人认为他指上帝在倒霉的时候创造了宇宙,当时他因消化不良而情绪低落,很容易地,可能确实如此容易地创造了其他宇宙,在别处造了无数宇宙,那里希望明显还在。所以我猜想从那个角度看还是有某种希望的。”[8]关于这段对话,伊格尔顿的引文或者译文还不够准确。关于上帝“因消化不良而情绪低落”说法,并不可靠。这段对话原文见于布罗德撰写的《卡夫卡传》。1920年2月28日,卡夫卡对布罗德说:“我们是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思想。”布罗德随后引证了诺斯替教关于世界的恶创造者德米乌尔根关于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学说。卡夫卡说:“不对,我相信,我们不是上帝急剧的堕落(a radical relapse of God’s),而是他的一次恶劣情绪,一个糟糕的日子。”布罗德问:“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啰?”卡夫卡微笑着说:“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于我们。”[9](2)在这里,“a radical relapse”译成“急剧的堕落”似有不妥,译成“旧病复发”或者如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致命的疾病”,应该更为合适。
有关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我们究竟有无希望?在卡夫卡看来,希望是有的,但与我们无关;上帝是有的,也与我们无关。存在着无限多的希望,但却不在这个世界之内,而在这个世界之外。卡夫卡说:“我仅仅就我自己而言。拿我来说,如果我置身于自由之中,就比如将要到来的拯救会带给我们的那种自由,我将几乎无法忍受,或者说,我真的无法忍受,因为我现在坐在监牢之中。当然,我并非追求监牢生活,而只是笼统地希望离开一切,也许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先到另一个星球上去再说。可是那儿的空气是能够呼吸的吗?我是否会像在这监牢里一样不至于窒息而死呢?这么看来,我即使追求监牢生活也是无可厚非的。”[3]216-217在卡夫卡那里,希望似乎不在这个星球上。逃出地球,流浪地球,或者就是人类最后的希望。卡夫卡的寓言或者预言甚至成为当今科幻小说家创作的源泉。科幻小说家刘慈欣“其实‘不小心’读过卡夫卡的所有中文译作”[10]。当然,有时候希望甚至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绝望,希望就是放弃希望,献身于生活。卡夫卡说:“只要绝望,放弃一切希望就足够了,这不是什么冒险。延续,献身于生活,表面上看似乎无忧无虑地一天一天过日子,这才是冒风险的勇敢行为。”[3]337
希望无限多,但不在人间。卡夫卡的这种说法我们甚至在古希腊神话中也能找到例证。普罗米修斯是一位先知先觉者,是智者的象征。他从奥林波斯山上盗走天火,带给人间。宙斯则命令火匠之神赫淮斯特斯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女人——潘多拉,并派他去找普罗米修斯的弟弟,也就是后知后觉者厄庇墨透斯。弟弟不听哥哥的警告,收下了潘多拉。潘多拉打开了宙斯不怀好意送给厄庇墨透斯的匣子。于是,灾难、疾病,特别是瘟疫以及那些人类闻所未闻的东西顿时飞散人间,待潘多拉急忙关上匣子时,却将人类的希望永远锁在了箱底。希腊神话告诉我们:希望不能说没有,但却与人类无缘。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蔓延,夺走了几百万人的性命,或者就是印证。经历这一灾难,几乎所有人对失望、无望、绝望和希望都有了新的体验和认识。
人类究竟是否还有希望?在卡夫卡看来,这个世界不过是上帝情绪不好时的创造物,是上帝糟糕日子的产物。如此一来,我们不禁要问:上帝也有情绪,也有情绪不好的时候?上帝也有糟糕的日子?那么,这个上帝与普通人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岂不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上帝吗?这个上帝果真是上帝吗?假若上帝是可疑的,那么,有关上帝的产物,即所谓希望也就是可疑的。如果上帝的希望是可疑的,那么人类的希望就变得有可能了,只是这个希望也许并不那么乐观。这就是伊格尔顿所说的“不乐观的希望”。
克尔凯郭尔是指引卡夫卡的一颗闪亮的明星。1917年10月,卡夫卡在给奥斯卡·鲍姆的信中写道:“克尔恺郭尔是照耀在我几乎不可企及的地区上空的一颗明星。”[11]2401918年3月卡夫卡在致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继续写道:“我大概是在克尔恺郭尔那里迷了路。……婚姻是他的主要问题……这是我在《非此即彼》、《恐惧与颤栗》中读到的。……现在克尔恺郭尔老是出现在我的头脑中,无论我在什么地方干别的什么事,总是不能够完全脱离与他的联系。……在性情上,我同他有些相似,《克尔恺郭尔和她》那本书写得很明白。克尔恺郭尔是和我同住一屋的邻居,他变成了一颗闪亮的明星。对此,我不仅有赞叹之意,而且也有一丝淡淡的同情……。克尔恺郭尔对普通的人视而不见,而是在云彩上画起了一幅阿伯拉罕的像。”[11]295-296(3)译文根据英译本略有改动。1849年,克尔凯郭尔出版了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致死的疾病》。在书中,克尔凯郭尔提出“致死的疾病”就是绝望。在绝望中要成为自身,就是违抗绝望或反抗绝望。克尔凯郭尔违抗绝望的方式直接影响了卡夫卡。
亚伯拉罕“燔祭献子”的故事表明了亚伯拉罕无条件服从上帝的虔诚性格。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中这样评价亚伯拉罕:“他没有怀疑,没有痛苦的左顾右盼,没有用他的祷告去向上天挑战。他深知正是上帝这全智全能者在考验他。他深知这是能向他要求的最艰难的献身,但他也深知当上帝提出要求之时就不会有什么献身是过分艰难的——于是他拔出了刀子。”在克尔凯郭尔看来,真正的信仰是信仰骑士的信仰,而真正的信仰骑士是这样的:“他饮尽深植在无边弃绝中生活的悲哀,他知道无限者的幸福,他感受到了抛弃一切、抛弃那世上最珍贵的东西的痛苦……。他永恒地放弃了一切,却依靠荒诞又重新赢回了一切。”[12]克尔凯郭尔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一切,他赢得了他的信仰;卡夫卡也最终抛弃了一切,他选择了创作。克尔郭凯尔和卡夫卡拥有了最后的希望。
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表达或透露出这种“不乐观的希望”,长篇小说《城堡》可谓最为典型。这是一部有关荒诞、绝望和希望的小说。加缪说:“卡夫卡同他的上帝争执道德上的伟大、启示、善与一致性——但只是为了更热切地投入他的怀抱。荒诞被认识了并被承认了,人只有听其自然,我们从这一刹那知道,它不再是荒诞了。”[4]111在加缪看来,荒诞一旦被认识并被超越,人们也就超越了荒诞。人类的希望也就在这里。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说:“我们还不完全明白,我们为什么感觉到他的作品是对我们个人的关怀。福克纳,以及所有其他的作家,给我们讲的都是遥远的故事;卡夫卡给我们讲的却是我们自己的事。他给我们揭示了我们自己的问题,面对着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我们的得救已危在旦夕。”[13]卡夫卡讲述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已经深陷灾难之中,危在旦夕,但并不是不可能得救。萨特(Jean-Paul Sartre)说:“卡夫卡成功地揭示了世界的苦难的本质,表现了挣扎在生活的旋涡中的人类,对于希望和自由的无限渴望和追求以及这一追求的最后的幻灭。”[14]人类在苦难中挣扎,对希望无限渴望,在追求中幻灭,在幻灭中追求,周而复始,以至于无穷。如果将法国著名意识流作家普鲁斯特与卡夫卡相比,“普鲁斯特已经表现了最低限度的希望,低于这种限度的希望是不存在的。但是卡夫卡却往下走得更远,远了很多;然而还闪烁着一线希望,那就是只要他在,就还不是完全的黑暗”[15]。只要人类社会不是完全黑暗,就总会有一丝希望。
三、“高度把握自己的死亡”
莫里斯·布朗肖在《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中,分析了卡夫卡与其所处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导致死亡,甚至自杀。布朗肖写道:“卡夫卡深深地感到艺术是对死亡的感受,因为死亡是那种极端,谁能把握住死亡,谁就能高度地把握自己。”[16]死亡是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终点,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终极的问题。正是死亡显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谁能把握住死亡,谁就能高度地把握自己”,把握自己就是把握自己的死亡。
法国著名作家加缪认为,哲学的根本就是判断人生是否值得经历的问题。如果世界和人生是荒诞的,那就根本不值得经历;如果人生是有价值和意义的,那就不是荒诞的,因而是值得经历的。但是,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呢?人生没有先验的价值和意义,否则就是“本质先于存在”;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人走完自己的一生之后方可获得,这就是“存在先于本质”。“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其他问题——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都是次要的,不过是些游戏而已;首先应该做的是回答问题……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是诸问题中最急需回答的问题。”[17]自杀还是不自杀?活着还是死亡?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生命的意义的问题也就是人的存在的终极的问题。
201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维克多·布朗伯特教授出版了《死亡滑过指尖》(MusingsonMortality:FromTolstoytoPrimoLevi)一书,论述了八位西方现当代作家对死亡的描述和思考。在第三章“卡夫卡:在永恒的当下的死亡之旅”中,布朗伯特写道:“他(卡夫卡)的作品始终在揭示人类的弱点,向读者展示生活中死亡是多么倔强。此外,这些作品在死亡与写作之间建立了一种必要的联系……这些幻想反映了人们生活的疾苦、无尽的愧疚、深深的挫败感和自杀的冲动。死亡反而成了期待中的解脱,现实则让这些主人公在走向死亡的旅程总饱受磨难。”[18]11卡夫卡的作品总是纠缠在死亡与自杀这些致命的问题上,正如卡夫卡也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深陷其中一样。
卡夫卡认为,“死亡不是时间概念上的结束,不是会很快到来的‘消逝’,而是一直存在于当下的永恒痛苦——不是真正的死亡,而是一种永恒的垂死状态。死神的驳船无情地游弋在日常琐碎生活的大海上。格拉库斯身上体现了卡夫卡最深沉的恐惧——永恒的垂死的痛苦。”[18]61-62这里提到的格拉库斯是卡夫卡短篇小说《猎人格拉库斯》(TheHunterGracchus)中的同名主人公。
该小说写于1917年。一只小船驶入码头,两条汉子从船上抬下一副躺着一个人的担架。在船主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一幢三层的黄楼前,走了进去。一位头戴饰有黑纱的大礼帽的绅士模样的男子来到门前,敲门进去。在二楼的房间里,担架上“躺着一个男人,头发和胡子像野地里的杂草一样,乱糟糟地长在了一起,皮肤黝黑,看上去像个猎人。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紧闭双目,似乎毫无气息”。那位先生走向担架,跪下来祈祷,在众人离开房间后,担架上人睁开眼睛问道:“你是谁?”来人答道:“里瓦市市长(The mayor of Riva)。”躺在担架上人说:“我就是猎人格拉库斯。”猎人说,许多年以前,他在德国的黑森林里追捕一只羚羊,从悬崖上摔死了。不过,“在一定程度上我还活着。我的死神之舟迷了航……我的小船却从此航行在尘世的河流上。就这样,原来只想生活在山区的我,死后竟然周游世界各国。”死后的猎人躺在船上本来是要去彼岸世界的,但船迷了航,这究竟是谁的错呢?大声呼救是没有用的。猎人并不想继续呆在里瓦市,“我的小船没有舵,只能随着从冥府最深处吹来的风行驶。”[19]
20世纪美国著名文学与社会文化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说:“任何读过这篇小说的人几乎都会说,或许心烦意乱地大声抱怨,‘它究竟在说什么?这奇怪的叙述究竟想要向我们传达什么?’”[20]118迷惘之后一定觉得,这篇小说一定是有意味的,它与人的精神和命运有关。它使我们想起某些广为人知的古代神话。譬如古希腊阿多尼斯的神话、古埃及“死亡之舟”的神话、奥西里斯(Osiris)的神话等。在宗教研究领域,阿多尼斯和奥西里斯常常被视为耶稣的前身。但是,“卡夫卡小说中已死的猎人可被看做一个绝望的耶稣,他没有重生,不论是‘另一个世界’的掌管者,还是这个世界的人类,都永远不会‘接受’他”。当然,猎人也许是耶稣,也许就是人类自身,也许就是卡夫卡自己。读者阅读小说后会产生这样一种效果:“使我们有一种囚禁在平庸和烦琐之中的无助感。但,如果我们也曾体验过人生的空虚和无意义,如果我们也曾遭受胁迫之痛,也就是我们的意志不是我们自己的,或意志终止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几乎无法抵挡卡夫卡对人之存在的可怕想象的力量。”[20]122
猎人格拉库斯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幽灵四处飘荡,很长时间都无法进入天堂或到达彼岸世界,然而他深知,死神无论早晚都会降临。格拉库斯在走向死亡,他等于在慢性自杀,他在死亡的航程中漫游。死亡航程的长度意味着人的有限性的长度,而在这有限的长度中自杀者亦能选择自主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作为“有限的主体”的人必然会面对个体生命的终结,但他可以选择终结的方式,甚至可以选择终结的时间。这种选择就是自杀。“人类行为中还有什么比自杀更特殊的呢?”[21]在卡夫卡看来,“一个人只能扔掉他确确实实占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把自杀看作是过分到荒唐程度的利己主义,一种自以为有权动用上帝权力的利己主义,而实际上却根本谈不上任何权力,因为这里原本就没有力量。自杀者只是由于无能而自杀。他什么能力也没有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他现在去拿他占有的最后一点东西”[3]337。
像卡夫卡笔下的猎人格拉库斯一样,卡夫卡经常想象自己的死亡,并萌生自杀的念头。卡夫卡甚至认为,那些最有意义的书就是一些关于自杀的书。1904年卡夫卡在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中写道:“我们需要的书是那种对我们产生的效果有如遇到一种不幸,这种不幸要能使我们非常痛苦,就像一个我们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的死亡一样,就像我们被驱赶到了大森林里,远离所有的人一样,就像一种自杀一样,一本书必须是一把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7]26自此以后,卡夫卡在日记和书信里经常提及自杀。1911年卡夫卡因为家族石棉厂的问题与家庭发生矛盾,随后矛盾逐渐升级,卡夫卡一度想到了自杀。1912年3月卡夫卡写道:“前天由于工厂的事受到指责。一个小时后躺在长沙发上想着从——窗户——跳出去。”[7]2141912年10月7日,卡夫卡在一封给布罗德的信中,再次表达了自杀的想法:
我清楚地意识到,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在大家入睡以后从窗口跳出去;要么在以后的两周内每天去工厂,去妹夫的办公室……我没有跳窗,诱惑我写这封抉别信的力量也并不太强……同时我也想到,比起我继续活下去,我的死亡对中断我的写作更具有决定性意义[11]132-133。
卡夫卡不仅自己想到自杀,他的小说中的人物也常常以自杀结束生命。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在流放地》《饥饿艺术家》等深刻地反映了卡夫卡的自杀想象与自杀冲动,从而完成了卡夫卡对死亡问题及终极关怀的想象和思考。当然,卡夫卡的自杀臆想并不能等同于卡夫卡笔下的自杀者形象。“卡夫卡笔下的自杀者虽有卡夫卡的影子,但并不完全是他的复制,因为他们无一例外都没有获得‘书写的拯救’。正是心怀‘做有意义之事’的终极信念,卡夫卡才未以自杀彻底终结他的书写进程——因为那无异于另一种自杀。如若书写者无法在现实中与世界达成妥协,那就只能通过与自己笔下的生命最彻底的分崩离析来达成与他人、与世界的最后妥协。因而,书写使卡夫卡离死亡更近也使他离死亡更远——作为忠实的书写者,卡夫卡转而成为自杀的反抗者。”[22]自杀者因为思考人生之终极问题而自杀,随后又因为思考这一问题而反抗自杀,最后成为卓越的文学写作者。
总之,解读和阐释卡夫卡具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而对于卡夫卡的当下意义的探讨就更是如此。因为每一种阅读和阐释都有道理,而一种阐释与另一种阐释不仅不尽相同,甚至完全可能是矛盾对立的。这既是阐释卡夫卡的困境,也正是卡夫卡的魅力所在。“卡夫卡的著作使评论家们陷入了矛盾甚至是对其作品的过度解读中。这些解读包括从严格的病理学解读到代表着无尽的精神追求的断言。根据评论家的猜测,这种压力可能来自内疚、自我惩罚、噩梦般的恐惧,或是欧洲中部犹太人的异化感,从而在卡夫卡的著作中寻找救赎。最推崇的文本是互相排斥的,忽视了卡夫卡激进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性情,呼吁反对观点的共存,它是一种包括而不是选择,只是一种意义到另一种意义的瞬时通道,并不存在他们之间真正交流前景。”[18]40本文对卡夫卡当代意义的解读也只能算是众多的解读之一,提供了又一种阐释的可能性,但这种阐释并不排斥或拒绝对话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