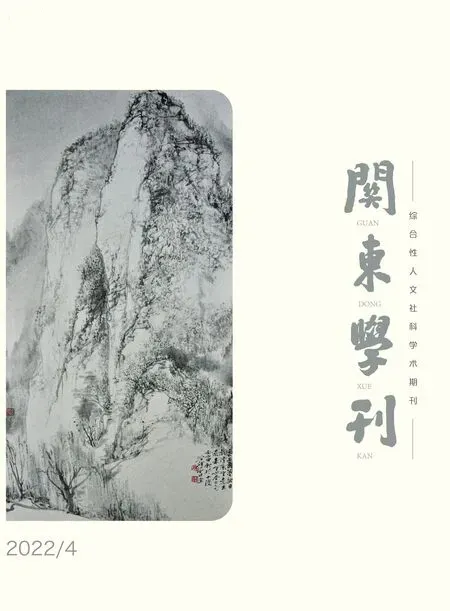清末民初文学中的疾病与诊疗叙事
曹晓华
清末民初文学对各种“病症”和医治过程的铺陈与描绘,成为动荡年代特殊的文字“诊疗”。对此,学界的相关研究大致按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围绕“疾病”隐喻的修辞分析,包括对医疗题材、医者形象以及相关作品叙事手法的讨论,常借用福柯“生命政治”和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的理论视域;二是将相关作品中的疾病与诊疗叙事视为尚在进行中的现代性表征,将其提升至医疗话语层面做进一步的探讨。
实际上,创作者对疾病的“再发现”不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或文学表征,还关联着中西医的攻守进退,其中隐含着探寻国族“富强”的不同路径,是考察清末民初文学的另一种视角。包括医界小说在内的文学创作对国民个体到国族群体的“病”“症”剖析,除了从具体到抽象的文本“诊疗”行为之外,作为医文互通传统的延伸,还折射出中西医对话的早期语境。在进化论和优生学的交替影响下,国人对“疗救”的反思投射在了更多“个人/集体”的文学文本对峙中。本文将在文学史和医疗史的双重视角中,解读清末民初作品中的“病”“症”二分对疾病的“再发现”乃至“富国强种”叙事的由来。
一、“病”与“症”的文学“诊断”
五四运动前夕,鲁迅笔下的华小栓,吃完了人血馒头。不久,华家的茶馆热闹起来,满脸横肉的康大叔,也到店铺里来邀功了——“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面对康大叔的嚷嚷,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1)鲁迅:《药》,《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8页。《药》中的华小栓满头大汗,咳嗽不止,瘦得脱了形。《黄帝内经》所谓“咳,脱形,身热,脉小以疾”,(2)郝易整理:《灵枢 玉版第六十》,《黄帝内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31页。是中医认为的肺痨之症,五逆之一。但在病症如此明显的情况下,华大妈依然对康大叔这样公开嚷出“肺痨”两字而心生不满。
《药》在《新青年》发表,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华大妈对康大叔的不满,是辛亥革命前后直至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普通民众对疾病和诊疗认知的缩影。《药》作为恰好在“五四”时间节点上的创作,不仅是鲁迅个人创作生涯中的重要作品,与清末以来的文学景观和社会心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借以考察中西医“病”“症”话语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发生。
解读小说《药》,自然要提到弃医从文的鲁迅从关注肉体病痛转向“精神的疗救”,他从社会痼疾的“横截面”中挖掘出国民性的病根。1903年,赴日不久的鲁迅应许寿裳的稿约在《浙江潮》上发表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讲述了一位斯巴达妇女因为丈夫苟且偷生没有和三百战友战死沙场而自刎的故事。此时的鲁迅,还是在弘文书院学习日文的青年,尚未正式学医。此时正值拒俄运动,小说中斯巴达勇士三百人战波斯三百万敌军,最后全军壮烈牺牲,文字间以命相搏的强力和勇气背后是爱国青年鲁迅的赤诚之心。《斯巴达之魂》受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民丛报》的《斯巴达小志》影响,(3)鲁迅《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斯巴达小志》之间的关联,参见高旭东:《鲁迅:从〈斯巴达之魂〉到民族之魂——〈斯巴达之魂〉的命意、文体及注释研究》,《文学评论》2015年第5期。而此时的梁启超已开始倡导国人体育,中国学人对西人所谓“东亚病夫”的反思从政体弊端的探讨逐渐延伸到提升国人身体机能的讨论。(4)近代学人对“东亚病夫”的认识,经历了从提升“国力”到提升“族力”的转变,参见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5年第23期。1896年10月17日的《字林西报》,转载了外报评论《中国现状》(The Condition of China),同年末《时务报》登载了该文的中译版,“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5)张坤德:《英文报译中国实情》,《时务报》1896年第10期。事实上外刊的原文着重对无能的清政府进行抨击,并没有涉及具体中国人的身体素质。然而在当时学人的解读和翻译中,“东方之病夫”承载了国人病痛和政治之弊的双重重负。以斯巴达人的尚武精神注入国民教育的想法,可视为对“东方之病夫”的回应,带着革命理想化的色彩。然而鲁迅后来也发现这剂梁启超认为的“良药”,并不对“症”——“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他依然留下了这学医前的旧作——“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6)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可以想象学医期间的幻灯片事件,对带着“无谋”的“天真”的鲁迅,造成了何种强烈的战栗和震动。但即便“弃医从文”,鲁迅个人对疾病的体验和感知融进了学医生涯积累的专业知识,又与他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相结合,渗透进长期的文学实践中。鲁迅对国民性的“诊疗”,逐渐褪去了《斯巴达之魂》那样一往无前的豪迈热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思熟虑后沉重又锐利的笔风。
《药》中的“诊疗”过程,首先对应的是公开的疾病“命名”行为。华大妈抗拒康大叔将华小栓的病“确诊”为“肺痨”,即便她和丈夫还是在按照治疗“痨病”的偏方给小栓寻药。对疾病的命名意味着确诊,在此之前却是折磨病患的药方试探。现实中,鲁迅的父亲至死也没有被中医诊断出明确的疾病,而成年后的鲁迅对那些奇怪的药引还记忆犹新,从河边现掘的芦根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从原配的蟋蟀到老弗大,然后便是那陈年破鼓皮做成的“败鼓皮丸”,但是对于一日日水肿起来的父亲都没效果,黔驴技穷的大夫暗示没有找到前世的“冤愆”。(7)鲁迅:《父亲的病》,《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296页。和华小栓抑制不住的咳嗽一样,鲁迅父亲的病也只有日益严重的水肿和喘气,对于病症发作和病人受苦的情形,鲁迅着墨甚多。有关病痛的细节越来越丰富,但疾病的诊断却一直悬而未决,这种文本中的延宕也体现出鲁迅对传统医方的怀疑,进而开始思索具体疾病以外的病因。无论是人血馒头的偏方和中医开的药方,都只是对“症”下药,对于病因的追索只停留在应对季节“以气感气”的“六气”“六化”,再进一步便是“冤愆”,玄论中没有半点病菌的影子。传统中医缺乏实证也给华大妈对儿子疾病的幻想留了可乘之机,这在早期的鲁迅看来,是老大中国“瞒”和“骗”的又一重要证据。如果我们继续将视线转向中西医刚开始“交锋”时的“病”“症”二分,还可以给清末民初文学的疾病和诊疗叙事添加另外的解读线索。
比较中西医的诊疗模式,中医着重的是病症和发病过程,而西医着重的是引起病症的本源,与西方现代医学发现的细菌、病毒、寄生虫等不同,中医眼中的病症因人而异,而药方也各不相同。倾听病人的诉说,依照不同体质下药,这本是中医的优势和特长,但这种特长在西医东渐中受到挑战。“病”“症”二分首先给清末民初医学名词的翻译审定带来了麻烦,高似兰等人“医务传道”时便发现了“病”与“症”的矛盾。1908年,高似兰编撰的《高氏医学辞汇》(Cousland’s Medical Lexicon:an English-Chinese Lexicon of Medical Terms)出版,这是经过名词委员会认定的成果。在出版说明中,高似兰特别提到了合信编纂并在1858年出版的《医学英华字释》(A 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合信在书中列举的1829个医学条目,经过管嗣复的帮助,试图将西医理念与古雅的中国文言结合起来。(8)孙琢:《近代医学术语的创立——以合信及其〈医学英华字释〉为中心》,《自然科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而高似兰和博医会名词委员会的同仁,延续了合信中西兼采的翻译方式。在1908年初版的《高氏医学辞汇》(时名《医学辞汇:汉英对照》)的凡例中,高似兰试图对disease的内涵进行说明,“‘病’与‘症’的区别很随意,前者是所有疾病的泛称,既可以是具体的疾病也可以是疾病的症状;后者则仅限于具体的疾病,比如腹水(ascites)是‘病’,天花(small-pox)是‘症’”。(9)P.B.Cousland:《医学辞汇:汉英对照》,上海:中国博医会,1908年。但是高似兰在1930年第五、六版的辞汇序言中承认,编纂辞典时为了方便起见,将“病”“症”二者区分开来,“‘病’指的是明确的疾病,而‘症’指的是症状,但实际上二者很难区分”。(10)P.B.Cousland,“Extracts from Prefaces to Fifth and Sixth Editions”,鲁德馨、孟合理编:A Cousland’s Medical Lexicon(Ninth Editon),中华医学会出版委员会,1939年。在西方医学定义的“疾病”进入中国之前,中医对各类疾病已经有了相应的指称,并有关于病症的描述性语句。事实上对于某一种疾病的命名,在一开始只是围绕这种疾病的发病症状,对于引起这种疾病的病原(如细菌或者病毒)缺乏科学的甄别,这意味着高似兰等人进行术语翻译时必须进行中西结合的考辩。吴章(Bridie J.Andrews)分析肺结核与细菌学说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在地化时,指出在细菌学说流行起来之前,包括合信在内的传教士在翻译“肺结核”时依然沿用中医的指称——“痨”,一个来自于“传尸痨”与“痨虫”的词。(11)吴章:《肺结核与细菌学说在中国的在地化(1895-1937)》,余新忠、杜丽红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4-229页。
高似兰等人的困境部分来自中医中说不清、道不明的玄学部分,这种不同于西医通过实证确诊病因的诊疗过程,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部分国人价值观念的迟滞。随着西医抗菌体系的成型和东传,1910年已有报纸登载“卫生歌”:“肺不运动叶渐缩,细菌寄生肺痨伏;肺若运动叶舒张,细菌祛除空气足”,(12)佚名:《肺之养生歌》,《女学生》1910年第20期。虽有“细菌”的概念,但依然使用“肺痨”之名。而鲁迅笔下受看不见的“痨虫”侵扰的华小栓一家,还没有结核菌的概念,华大妈对“痨病”二字的排斥,也并非对疾病有自己的见解,而是一种“自欺欺人”,似乎只要病名不定,无论现时“症状”几何,华小栓吃下去的人血馒头定能带来病愈的希望,而这种“确诊”的“延宕”带来的“治愈”“虚妄”还不如鲁迅所说的“绝望”。(13)鲁迅:《希望》,《鲁迅全集》第二卷,第182页。小说结尾处,在夏瑜的坟前,夏瑜母亲对害死儿子的人发出诅咒,希望乌鸦飞上坟顶“显灵”,鲁迅让夏瑜母亲的“希望”落了空,而华大妈“似乎卸下了一挑重担”。(14)鲁迅:《药》,《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72页。华大妈一定是庆幸老天没有“显灵”,使这恶毒的诅咒无处应验。其实她此时卸下重担的心态,如同当时对康大叔嚷出“痨病”不高兴一样,似乎只要不点破、不说破、不显灵,一切可安之若素,可见无论是儿子的死还是夏瑜的死,都未能真正推动华大妈对革命的观念产生变化。
围绕“人血馒头”展现出的形形色色的“症”,华小栓突起如八字的肩胛骨印出“吃人社会”驯化出的麻木和愚昧,在鲁迅眼中就是那个经过实证和临床观察发现的侵蚀国人精神的病菌。通过鲁迅留日期间的医学笔记可以了解到他系统学习过《解剖学》《血管学》《组织学》《有机化学》《五官学》《病变学》等课程。(15)杨燕丽:《关于鲁迅的“医学笔记”》,《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期。早在1899年,还在矿务学堂的鲁迅已经接触到了一些基本的西医知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16)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38页。回看鲁迅追索国人精神痼疾的过程,从呈现传统中医辨证的各种“症”入手,最后在民族的比较间找出了国民蒙昧麻木的“病因”,其中析微察异、剖析病情的思路,又偏重于西医观照下的“病”和引起“病”的“菌体”。
二、“疾病”的文学“发现”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疾病”和“诊疗”并非孤例,中国文坛素有“医文互通”的传统。借着显微镜,清末民初作家重新发现了“病态”与“病体”。刘鹗、陆士谔、郁闻尧等人的作品,通过主人公行医的过程揭示社会的顽疾。柄谷行人在分析日本前现代文学时,曾经提出一种“风景的发现”,也就是“发现”原本并不存在的事物,并使之成为不证自明的存在。(17)[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9-12页。这种认识论上的“颠倒”也可以在清末民初文学的疾病叙事中发现,在中西医疗观念的碰撞中,创作者“发现”了新的“风景”。清末一则笔记小说,写一医者自警,墙上挂了一幅图,图中除了捣药老翁,还有一只突兀的狐狸,观者看了题跋才知道,只因狐狸“善假且谲,而当时之医专喜偷窃古人陈说,用以欺人,毫无新颖知识,龌龊险诈,其去狐也几希”。(18)佚名:《狐耶医耶》,《医药学报》1909年第1期。观者一开始不解其意,看了题跋后恍然大悟,明白了狐狸和庸医之间的相通之处。文学中的疾病“发现”和“诊治”,常开始于“正本清源”的精神自救(暗示这不是“真正的”中医),但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揭露,纵使真正的行医高人也“黔驴技穷”,这其中又透露着作者的无奈。
刘鹗《老残游记》中的老残,未能走科举之路,而是和道士学了几个行医口诀,做了云游四方的江湖郎中。出身医学世家的刘鹗,在小说中展示了丰富的中医诊疗细节,小说第三回便写了他如何医喉疾:“这病本不甚重,原起只是一点火气,被医家用苦寒药一逼,火不得发,兼之平常肝气易动,抑郁而成。目下只须吃两剂辛凉发散药就好了。”(19)刘鹗:《老残游记》,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第15页。老残开了“加味甘桔汤”药方,治好了高老爷的小妾,但刘鹗在小说中详细开出的药方,却只是导向社会病态的药引。引药归经,老残的医术经过高老爷的宣传,很快人尽皆知,不久他便上了高档的宴席,就在宴席上,曹州知府玉贤的故事传了出来。在这个“清官”的治理下,曹州不仅没有了强盗,百姓也“路不拾遗”,玉贤由此还得到了嘉奖。然而他的政绩只是不问黑白、滥施酷刑的结果,曹州的匪患看似已平,实际老百姓却迎来了更大的祸患,即“清官误国”。老残的药方引出了更加严重的国祸,玉贤并未将曹州“治”好,政绩掩盖下的暴虐和酷烈,在江湖郎中眼里也成了害人害国的“重症”——“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由此看来,请教还是有才的做官害大,还是无才的做官害大呢?倘若他也像我,摇蚌串铃子混混,正经病,人家不要他治;些小病痛,也死不了人。即使他一年医死一个,历一万年,还抵不上他一任曹州府害的人数呢!”(20)刘鹗:《老残游记》,第38页。旧疾新病,满目疮痍,刘鹗在给黄葆年的信中写到,“弟固未尝知天,弟固未尝不信天。惟其不能知天,故竟以天下为己任。天下之安危,匹夫与有责焉。今日国之大病,在民失其养。”(21)刘德隆、朱禧、刘德平:《刘鹗及老残游记资料》,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页。因为兴办实业而受到太谷学派同仁压力的刘鹗,向当时的学派领袖表明心志,《老残游记》中“抱残守缺”的残棋隐喻,不仅是老残的名号由来,还埋有扭转残局、治疗“国族之病”的“暗线”。
如果说《老残游记》类似一部失败医案的合集,那么颇具影响力的“医学小说”《医界镜》就是一部“医场现形记”。该作可视为奇方异术和黑幕小说的结合体,于1908年出版,署名“儒林医隐”,正是作者郁闻尧根据自己在1906年出版的旧作《医界现形记》改编重印的。“医界镜”,取的是传统小说中常见的“照妖镜”比喻,对晚清医界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就小说的创作来看,无外乎才子佳人、官场黑幕、房中秘术的杂糅,贝氏父子行医经历看似贯穿期间,实际上还是各种医界形象的堆砌。《医界镜》将华洋杂处时国人对中西医的态度,以及部分学人意识到的中西医优劣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呈现。小说中的中医,多是借迷信或是借西医画皮招摇撞骗,偶有一两个真正精通医道的中医,俨然是不可多得的清流。小说发现的“疾病”,与其说是书中录入的各种疑难杂症,不如说是人心浮荡加上时运不济导致的中国传统医道和医术的崩坏,作者接着又从这种崩坏反思中医的劣势。作者借书中人物之口道出,“苟能采取西法,洞明全体,习化学而明西药,知其然且明其所以然,官为考取,设局施医,从此精益求精,将至于完全不难也”。(22)儒林医隐:《医界镜》,嘉兴:同源祥书庄,1908年,第171页。小说一方面用了诸如“微生物”、“养气”之类的舶来术语,但另一方面,因果报应不爽的叙事讨论又无时无刻不提醒着读者,即便有科学的术语,若是没有科学思想的启蒙,也只能发现个体之病,罗列医界乱象并不能深入到国族之病的根本。《医界镜》的序言中提到,“爰作《医界镜》四卷,俾平人阅之可预先稔知医生之高下,一旦有病或不为庸庸者所误;医家阅之可以警惕深造而勉为良医,而与卫生之道尤时时致意焉”。(23)儒林医隐:《序·医界镜》,第1页。小说就像是嬉笑怒骂的“打假指南”,庸医横行,丑态毕现,但隐藏在游戏文章之中的作者态度隐而不显。前半部分的主人公贝仲英用烛油和身上污垢和成“浊垢丸”,因为前世福佑歪打正着治好了赵家公子,而赵家老爷精晓“卫生之道”,竟然也并未对疗法有任何怀疑。其中叙事,旧疾依旧,但诊疗之法新旧掺杂。由此可见,郁闻尧虽然对庸医极尽讽刺之能事,但对传统中医未曾有过怀疑,他只是希望通过对“庸医”的“发现”,唤起医生和病家的警惕,遏制中医界的乱象。这也不难理解《医界镜》一度被认为出自陆士谔之手。民国期间废止中医案中力主中医的陆士谔,曾著有《寒魔自述记》《环游人身记》等医界小说。《寒魔自述记》和《环游人身记》连载于《金刚钻》报纸上,都用拟人化的手法展开叙述。(24)《寒魔自述记》见《金刚钻》1924年4月14、21、24日三期,《环游人身记》见《金刚钻》1925年1月1、3、6日。《寒魔自述记》中,风、寒、暑、湿、燥、火六魔,由外侵入人体,人体内四魔酒、色、财、气,若人破卫生之法,便会迎接六魔共游。而《环游人身记》的内容和《寒魔自述记》大同小异,多了肾水、经脉等中医术语。陆士谔在小说中所谓的“卫生”和《医界镜》一样,沿用的是中医“保卫生命”的养生之意,和西医提倡的“卫生”不同。
“寡人有疾”的叙事由来已久,只不过随着时代的沿革有了全新的版本。小说中主人公开的药方,只能医治个体,但对牵扯出的病入膏肓的群体却束手无策。在文学实践的场域内外,注重个体养生的传统医方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追名逐利的庸医使中医的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梁启超曾以“疾病”的“诊治”论洋务运动的弊病:“今有病者,其治之也,则必涤其滞积,养其荣卫,培其元气,使之与无病人等,然后可以及它事,此不易之理也。今授以甲胄,予之以戈戟,而曰尔盍从事焉,吾见其舞蹈不终日,而死期已至矣。彼西人之练兵也,其犹壮士之披甲胄而执戈鋋也。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25)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梁启超全集》第一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6页。国本未固,“病夫”披“甲胄”,洋务不能医国,这与庸医用和缓的方子行骗一样,只会贻误病情。有想要“正本清源”的小说,却无意间揭示了当时的中医“弊病”。1909年有报纸登载《医林外史正传》,希望能借小儿学医的故事为中医正名,但是小儿出游前父亲一番苦口婆心的劝告,却将中医界的乱象揭出:“如今有种医生,卖弄手段,不肯问人,不管好歹,胡乱用药……高抬身价,神乎其神,那晓得见了重症,无非写了一张不关痛痒的药方,以为服药之后,一时不死,可以卸却干系,病家反讲他用药平稳,见识老成……”(26)佚名:《医林外史正传》,《绍兴医药学报》1909年第16期。庸医“药不对症”的拖延战术,梁启超对此十分清楚。他改学制、育新民的宣传,本就脱胎于“病体(病国)”的分析,其《新中国未来记》直接借李去病之口提倡西医峻急的“疗法”,用上“雷霆霹雳手段,做那西医治瘟疫虫的方法”,将中国的病虫“铲到干干净净”。(27)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1902年第2期。
道光年间的学者兼医者陆以湉,看了合信的《西医略论》颇有感触:“西国医士合信氏《西医略论》,略内症而详外症,其割肉锯骨等法,皆中国医人所不敢用者……其诊脉至数验以时表,取其旋运有准,谓华人用鼻息呼吸,恐有迟速长短,不如时表之准也。”(28)陆以湉:《今书》,《冷庐医话》,吕志连校,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9页。虽对西医内治之法难以苟同,但陆以湉还是赞赏时表诊脉的有效性,殊不知这“时表”后来成为“雷霆霹雳手段”的隐喻,表针移动,疾病凸显,在国族危亡境中主攻“辩证”的中医危机加剧。
三、“医人”“医国”与“造人”
清末民初文坛对中医的贬低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逐渐演变为当时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杨念群指出,“‘中医’没有资格成为现代社会医学的最重要的理由是,中医总是呈分散状态面向每个病人个体,而现代的‘社会医学’应以群体体魄的改造为基本职能,最终指向保国与保种以及民族国家建设的终极目标”。(29)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9页。“发现疾病”的小说中,已暗含从“医人”到“医国”的转变。清末民国时期文学文本,掺杂着对中西医攻守的回应,“疼痛”“畸形”和“残缺”的个体上升为蒙昧落后的国族象征。
俞樾在《废医论·去疾篇》中认为,“夫人之病,由心生也;心者,气之帅也;气者,人之所以生者也。善养生者,长善心而消恶心……不善养生者,消善心而长恶心”。(30)俞樾:《废医论》,《俞楼杂纂》卷四十五,《春在堂全书》第三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755页。可是俞樾并不懂医,他只是将修身之道套用在了“卫生”之道上,并将朝政之上君子与小人的进退与“卫生”之道类比。亦有人提出“小医医一人,大医医一国;小医而自病矣,人将谁医之?大医又自病矣,国将谁医之?”(31)马世杰:《医国篇》,《新世界学报》1903年第13期。跳出中西医论争,清末民初学人能够达成共识的是,国体“病入膏肓”显然不能“讳疾忌医”,这疾病不限于个体肌理,更在于种族弱势和朝政衰败导致的国民的精神病态。
清末民初文学的“诊断”从个体延及群体。笔记小说《医皮》讲述外国人售卖“能使黑奴变白”的香皂,作者灵机一动,想到看到消息说国外医生已有技术可变肤色,无需香皂即可让人由黑变白,至于黄种人变肤色就更加方便了,然而“我黄种人之大病,又不专在于皮之黄而实在于皮之厚,忝然面目,固有针之,全无点血,炙之不损一毛者,不识该医生亦能别出心裁,以疗此恶疾否?”(32)佚名:《医皮》,《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第6期。作者戏谑的笔触背后,是对恬不知耻的国人的鞭挞,而开玩笑间将治愈的希望寄托在了据说掌握变肤色技术的西人医生身上,种族的耻感被压抑在了肤色变化的笑料中。游戏文章批驳族群之恶,名为医治,实为挞伐。无独有偶,小说《医意》也用幽默的笔调写了一出“治病救人”的“闹剧”,小学徒在师傅不在的时候擅自给病人开方,建议向难产的产妇投掷钱币,老医生得知后大发雷霆,不料家属却上门道谢,称照着“神医”医嘱,产妇顺利生产。讶异之余,老医生询问徒弟为何开此方,反遭徒弟嘲笑:“何师之愚也!今世之中国,孰是见钱而不出攫者哉?”(33)武:《医意》,《月月小说》1907年第7期。未出世的婴孩也“见钱眼开”,看见钱币便呱呱坠地,联系小说数次重复的中医“医者意也”,讽刺极为辛辣。小说《刘医》则将矛头对准了上海一些唯利是图的医生,有某老爷为了占有继女,拜托刘医毒死继女病重的未婚夫,刘医趁机敲诈了老爷一笔巨款,反而将病人治愈,并拿这笔钱促成了两位年轻人的婚事,老爷得知后暴跳如雷却又无可奈何。这篇小说出现在《医话丛存续编》里,收入丁福保主编的《丁氏医学丛书》,小说结尾处写道:“沪上医家,惯做其前半段”,(34)佚名:《医话丛存续编:刘医》,《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3期。小说以坊间花边新闻为背景,对刘医侠义行为的赞许带上了对上海医界怪象的批判。小说《医界镜》中也揭露不学无术之人中西医通吃,以洋商招牌兜售“救贫戒烟丸”,“广请通人,做了许多浅近俚俗的歌词,登在报纸,使人人皆易明白,又请人做了保证书,各处招摇,使各州各县的生意人,皆替他行销,报上登的告白,每说要富国先强种,要强种先戒烟,本社以救济同胞为心,故创这良药……”(35)儒林医隐:《医界镜》,第124页。这个卖假药宣传的情节有多处值得玩味。首先买的是丸散,却要借用洋招牌,可见当时西医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其次登载浅近歌词宣传,此处的歌词应指类似于歌本、时令小调之类的过渡文体,本是启蒙的重要环节,却在小说中成为招摇撞骗的工具。再次便是戒烟与富国强种的联系,戒烟丸成了国民药方,加入了“诊疗”体系,戒烟由此不再是个人行为,而是强国保种的重要途径。可以看到,医人/医国的主线凸显出来,同时以西方为标杆的现代文明想象又强化了文人启蒙大众时对自身传统的反思。只是这种叙述和黑幕小说一样,在“猎奇”的过程中削弱了揭露黑暗的深度和力度。
要想扫除旧“疾”,除了肃清社会制度的弊端,还有一部分文人开始了“强国保种”框架内的“改造”叙事。早在1897年,浙江名医陈虬已作《保种首当习医论》,他认为保种救世应号召全民学医,“夫医也者,不独其能疗疾卫生延年也,人类之藩道昌而运隆,罔不基此”。(36)陈虬:《保种首当习医论》,《利济学堂报》1897年第4期。然而在陈虬看来,人类是地球万物之首,其中又以中国人最为聪颖,但当时面对西方民族的崛起,华族处处受制。陈虬提出的保种习医,虽也涉及中西交流,甚至论及婚嫁优生,但归根结底对华族的信心仍在,而他所提倡的医学,也是传统中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昔日如陈虬这样的民族自信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对种族改造的想象。严复《天演论》带来的“物竞天择”,给原本判定国族“体弱多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人种进化的线索。经过翻译和再阐释的“东方之病夫”犹如民族耻辱的烙印,想要摆脱它,原本的“医治”成为“替代”,“雷霆霹雳”的西医手段变成西方科学家造出“新人”。
鲁迅在1906年的《女子世界》上以“索子”为笔名,刊发了名为《造人术》的译作。日本学者发现《造人术》是按照日译本翻译的,原文是Louise J.Strong发表在Cosmopolitan杂志1903年1月号上的An Unscientific Story(《一个非科幻小说》)。(37)[日]神田一三:《鲁迅〈造人术〉的原作·补遗——英文原作的秘密》,许昌福译,《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无独有偶,包天笑也翻译了这篇《造人术》,登载在1906年4月26日的《时报》上。有学者认为鲁迅的《造人术》通过日本词组和英文词组“life-germ”之间的对译,为晚清文学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将不同的生物种类,不论是人,还是植物,都统一在‘人’‘芽’一体的细胞概念之中,而这个概念,体现的正是现代生物学有关生命起源的理论”。(38)[美]刘禾:《鲁迅生命观中的科学与宗教(上)》,孟庆澍译,《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3期。事实上,包天笑和鲁迅翻译《造人术》的时间很相近,且包译版本也用了“人芽”这个词。对于鲁迅《造人术》的具体刊发日期,学界尚有争论。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注明鲁迅《造人术》刊于《女子世界》第二年第4、5期合刊,即1905年。但据宋声泉和夏晓虹考证,《女子世界》第二年第4、5期合刊应出版于1906年。(39)宋声泉:《鲁迅译〈造人术〉刊载时间新探——兼及新版〈鲁迅全集〉的相关讹误》,《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5期。对于生物学的接受是晚清学人的普遍现象,但面对同样的文本,鲁译和包译风格迥异,按语立意也各不相同。鲁迅和包天笑都翻译了原小说的开头部分,大致说的是科学家伊尼他氏苦心经营数年,终于创造出“人芽”,可以视为现代科学中人工胚胎的原型,只不过对于“人芽”的诞生过程并无生理化学细节描述。两人的译文在科学家成功创造出“人芽”后都戛然而止。其实小说之后的情节发展是“人芽”变成怪物,引发了科学灾难。更有学者考证,小说原作者是根据黑人和中国人的形象创造了怪物的外观。(40)王家平:《鲁迅译作〈造人术〉的英语原著、翻译情况及文本解读》,《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12期。撇去两人翻译风格的差异不谈,两个译本都侧重于激动人心的“新造物主”诞生部分。鲁译版本后,周作人(萍云)按语认为“世界之女子,负国民母人之格,为祖国诞育强壮之男儿……新造物主之称号,乃不能不移之以赠我女子”。(41)索子:《造人术》,《女子世界》1906年第4、5期。丁初我则补充道,“铸造国民者,视国民母之原质,铸造国民母者,乃视教育之材料”。(42)索子:《造人术》,《女子世界》1906年第4、5期。无论是鲁迅和包天笑笔下造物主的“大欢喜”,还是周作人和丁初我强调的女子“造物主”,都离不开对国家人种改造的想象,“人芽”狂想是当时文人在小说中进行“改造种族”的缩影。
“新造物主”的诞生之所以激动人心,不仅是科学幻想的感染力,背后还有“进化论”和“优生学”影响下的“治愈”期许。清末民初兴女学、复女权都离不开对女性生育能力的强调,女性作为“造物主”,承担着繁衍优等“国民”的责任,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解读直接涉及国族人种的改良。19世纪末弗朗西斯·高尔登(Francis Galton,1822-1911)正式创建优生学(Eugenics),该学科与进化论紧密相关,是“研究所有能够改善人种先天素质(the inborn qualities of a race)”(43)Charles Benedict Davenport,Heredity in Relation to Eugenics,New York:Holt,1923,p.1.的科学。人种先天素质的差异可以后天弥补,似乎为急于找到“治病良方”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加速国族“现代化”的灵感,除了周氏兄弟三人,严复、章太炎、陈独秀、胡适、陈长蘅等人都发表过优生优育以实现人种改良的言论。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人种进化”“疾病治愈”的“黄金未来”心驰神往。值得一提的是,比起鲁译后按语对“人芽”的接受,包译版本后自加的按语则态度微妙。“发明造人术后,更当发明造魂术,不然,是蠕蠕者纵能运动,世界亦奚用此行尸走肉为?”(44)笑:《造人术》,《时报》,1904年4月26日。即便人种完成了“新陈代谢”,后来者若是没有精神世界的革新,便也是无用的行尸走肉,这是对科学幻想中“少年中国”的警示。1910年,包天笑译作《新造人术》在《小说时报》面世,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已然全新的世界。有一博士造出脑力体力均优于人类的超级物种,不料实验品从实验室逃出,躲藏在一位作家家中。作家见其打字迅捷,博学多才,便也默许这只半人半羊的物种留下,帮他一起写历史小说。但是博士终究找到作家,用电击胁迫实验品回到实验室,作家斥责博士残酷至极,却也被电击威胁。包天笑译罢,叹曰:“呜呼!创造生物,创造生物,果人间社会之幸乎?”(45)笑:《造人术》,《时报》,1904年4月26日。其实包天笑前后两次翻译不同的“造人术”,他的态度并未改变,病态中孕育出的新生命,不一定是治病良方,可能是恶劣“原质”的延伸,何来“治愈”的功用?
清末民初文学实践场域中,隐藏在文本之下的“疾病”自指已经成为苏珊·桑塔格所说的“疾病的隐喻”,“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疾病隐喻的夸张透露出一种惩罚性的观念:这并不是说疾病是一种惩罚,而是疾病被当作了邪恶的标志,某种将被惩罚的东西的标志”。(46)[美]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89页。古老的国度及其子民在肉体和精神上被发现的“疾病”,变成一种虚弱的疲态,一种现代化过程中落后于他国的内在原因。原本天人合一的个体养生观念,终究被民族“疾病”“诊疗”的话语实践取代。而无论是中西医论争映射在作品中的困顿,抑或是新生“人芽”的狂想,都试图在文字中“治愈”“顽疾”,让积贫积弱的中国在象征层面“焕然一新”。从“医人”到“医国”乃至“造人”,疾病隐喻引发的“疗救焦虑”,最终成为一种“寻求富强”的现代性探索。清末民初的文学实践场域,见证了“国族之病”的发现与疗救,也见证了“进化论”与“优生学”在科幻叙述中完成的“人种改良”。人文传统与科学话语的交织并行,共同构成了“五四”文学的先声。在“救亡”与“启蒙”的延长线上,注定伴随着矫枉过正式的文字“猛药”,清末民初文学只记录下一部分时代转型的阵痛,而相关的探索、阐释与反思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