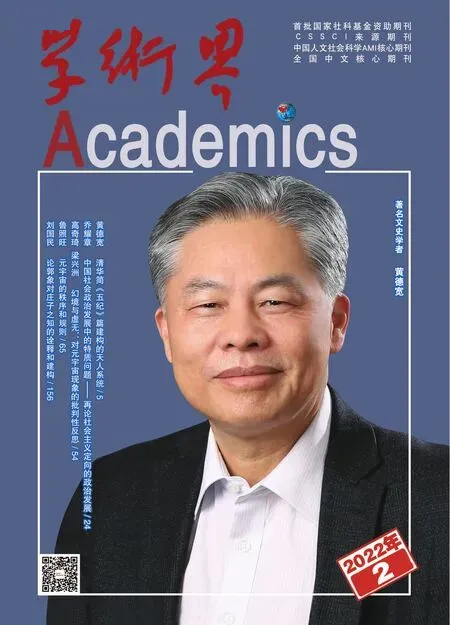从生命需要看人之存在之谜
——我们如何存在与何以存在
蔡 昱
(云南财经大学 金融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221)
存在与非存在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存在学包括三个领域:实在论、观念论和指称论。〔1〕存在的实在论以巴门尼德为代表。巴门尼德处于古希腊哲学的发轫期,当时的人们热切追问的是:超越时间变化的万物始基是什么?〔2〕由此,超越性的维度成了巴门尼德的实在论的基本特征。在他那里,存在被定义为永恒生成之力,〔3〕是天地、自然和人作为实存的存在之源。同时,“存在”是完整、单一、不动、完满的;(它)既非曾经存在,也非将要存在,因为(它)现在作为整体存在,是一体的、连续的,〔4〕从各个方面看都像是浑圆的球体。〔5〕显然,这种外在超越的存在观隔离了超越与经验,同时,人和人之实践也成了受外在支配的结果;以概念为基础的观念存在论的存在之生成是根据概念先天的确定性,以康德哲学为代表。它以先验性代替了超越性,使存在的问题成了主体性的问题。以概念为基础的观念存在论导致了生命存在的概念化从而无力又空疏,如尼采所描述的“冰冷的理性”“苍白的真理”“空洞的‘存在’”,〔6〕产生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以体验为基础的观念存在论以海德格尔为代表。他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7〕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自我存在,人应当尊重自己的存在,按照自我意识自由选择,自我造就。〔8〕其理论具有虚无的倾向,一方面,它反对普遍的道德原则对个体性的抹杀,强调在主观体验中把握关系与存在,认为人之选择的基础就在于他/她的自由,然而,个人的主观自由的无限选择必然滑向茫然与虚无。〔9〕另一方面,“虚无主义的将死观笼罩着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思想”,那里,死亡成了庇护虚无最可靠的“殿堂”;〔10〕指称存在论认为存在只是思维图像之间形成的相互指称,即存在即语言和思维系统,也就是说,存在与非存在并不以实存系统为参照。〔11〕
显然,经由存在作为存在是天地、自然和人作为实存的本源,到存在作为存在是概念先天的确定性,再到存在作为存在是此在日常生活的展演,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被不断地人化,即人不断地摆脱了上帝和概念的束缚,〔12〕而另一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地抛弃了实存和超越性,也变得越来越狭窄与片面。同时,“当存在即语言和思维系统遇到人工智能技术,存在的逻辑化和机械化就会愈演愈烈”。〔13〕
雅斯贝尔斯认为克尔凯郭尔与尼采作为独立思考的先行者,察知到了当时与存有脱节了的时代意识的唯我主义所带来的虚无主义,从而对人类的未来充满着不安的预感,即自我的存在走向虚无,结束就是毁灭,时代意识在虚无中栽了跟斗。〔14〕当前,时代精神显然更加严重地滑向了虚无的深渊,我们急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自由与自觉的特殊的生命,人如何以及何以克服虚无而在感性世界中‘为其所是’(即存在)”,显然,上述思想没能提供给我们恰当的普遍性的知识。
从古至今,无论哲学家还是心理学家都对人之需要从不同视角进行了丰富的讨论: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外在诸善有其阈限,超出其阈限就必然变得有害或无用;〔15〕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望和性本能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原动力;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人有生理、安全、爱、归属及自我实现的需要;〔16〕奥尔德弗则将人的需要分为生存、相互关系和成长发展的需要;〔17〕麦克里兰发现在最基本的生理需要被满足之后,人的基本需要有三种,即权力、亲和与成就;〔18〕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以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和使命,从不同角度(如历史发展和社会现状的视角、〔19〕人的需要发展层次的视角、〔20〕需要层次的不同划分方式〔21〕等)广泛讨论了人之需要;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区分了“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22〕弗洛姆认为人除了物质需要,还有交往、情感、归属、认同、献身、爱、超越等有别于动物本能的高级需要。〔23〕
上述对人之需要的讨论极大地推进了人对自身的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大多缺失了将人的感性需要这种活的力量与人的存在相结合的视角。同时,因没能辨认出作为最深层次的人性的人之弱点的生存性恐惧这一人之自由、道德和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现实化的障碍,它们也都无法揭示与人之自由、道德和存在如何现实化相关的超越生存性恐惧的需要。
揭示人如何以及何以克服虚无而“为其所是”(即存在)是哲学的根本任务。然而,前人因为没能给出恰当的存在依据,也没能辨认出生存性恐惧这一人之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现实化的障碍,“人如何以及何以克服虚无而在感性世界中存在”便成了“人之存在之谜”。本文尝试将人的需要和人之存在结合起来,直接从“人之生命的本质性(即作为存在依据的)需要”的视角讨论人的需要和揭示“人之存在之谜”。由此,对生命需要的探讨必须阐明的是作为一种特殊生命的人,其自由自觉的“为其所是”的“存在”的内容和方式是什么(即人如何存在),同时,还需要回答“人何以存在(即人之存在如何在感性世界中现实化)?”。显然,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答,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即原子式的经验性的个体性)哲学所带来的普遍虚无才可能消散。
一、人的生命需要——我们如何存在
所谓“人之生命的本质性需要”,简称“人的本质需要”或“人的生命需要”,是指对于作为一种特殊生命的人来说的,作为其存在根据的那些需要。显然,人之生命需要所推动的对其自身进行满足的生命实践可以使人克服虚无而本真地存在,即此生命实践是生命需要的表达,同时,它与生命需要是因果一体的。由此,因果一体的人之生命需要—人之本真的生命实践就是人的存在依据。
(一)一般性的生命需要及其内蕴的生命的永恒性的面向
亚里士多德曾经讨论事物的“运动”,当然,这里的“运动”是指潜能的事物(作为潜能者)的实现即是运动,〔24〕而并不是纯物理性的活动。显然,此“运动”的本义“是在揭示运动本身的存在性质”,〔25〕也就是说,此种从潜在状态到现实状态的“运动”就是“为其所是”,即“存在”。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深受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影响,却没能真正解决理念论的严重缺陷,即理念与实存之间存在着裂隙。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发现对生命来说,“为其所是”的“运动”并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有其特定的结构,即此“运动”必须遵循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故其理论是失败的。我们将从生命需要和其基础上的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这种内在的感性的活的力量,及生命需要所内含的具有超越性结构的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出发来讨论生命的“为其所是”的生命活动,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存在意义上的)“运动”。显然,当我们以因果一体的感性的生命需要及其所推动的感性的生命活动作为存在依据(即本质),便既克服了柏拉图主义的理念性的本质主义的“无力症”,又赋予了超越性以内在性,赋予了应然性以本然性,赋予了生命的存在以其特有的超越性的结构和感性世界中的现实化。同时,生命需要及其基础上的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和其所推动的生命活动的因果一体性使得生命的此种“运动”摆脱了前因后果式的因果链而获得了自由。 具体而言,对于无生命之物的运动来说,其动力是外在的,目的也是外在的,如对于桌子被推到阴凉地这一运动,其动力是人的推动力,目的则是为了人不被晒着,或者桌子不被晒坏以免破费桌子主人的钱财。与之相反,对于生命来说,在其“为其所是”或“成为自己”(即“存在”)的生命活动(如橡树的种子长成橡树)中,其动力是生命的本质性的需要和其基础上的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其目的也是内在的,即“为其所是”或“成为自己”。我们将生命的此种在其内在的固有的本质驱动力下的“为其所是”或“成为自己”的本质性的生命活动称为“创生”,它是生命需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自然中的所有生命的本真的存在方式是“自在(即‘为其所是’)与共在并存”意义上的“和谐共生”,即生命既“为其所是”地成为自己,又处于整体关联之中,它们组成了相互联系、相互成全又相互影响的整体的有机系统。因此,生命的创生并非封闭地孤立地进行,而是处于“自在(即‘为其所是’)与共在并存”式的开放的整体关联之中,即遵循“和谐共生”的生命的本真的存在方式这种整全性的超越性的结构。由此,生命的创生方式是一体两面的“自我创生”和“相互(协同)创生”。也就是说,生命是在相互(协同)创生中自我创生的,即可将这种相互创生或协同创生看作是自我创生的实现方式,我们称这种遵循生命本真的存在方式而进行的生命的创生活动为“生—生式的自我创生与相互(协同)创生”,简称“生—生”。如蝴蝶依靠花蜜维持生命,而花朵依靠蝴蝶授粉结出果实;土壤供给蚯蚓以枯叶和朽根,而蚯蚓则以其分解的无机物反馈给土壤。
显然,“生—生”的生命活动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的存在依据,体现了生命的本质性的需要(即生命需要),是“生命之道”,它既表达了生命的本真存在的内容(即创生),又表达了生命的本真存在的方式这种整全性的超越性的结构。进而,我们可以将“生—生”的生命活动描述为生命被其生命需要及其基础上的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推动的,遵循生命的本真的存在方式的,即以相互创生的方式所达成的生命的“为其所是”(即存在)意义上的内在目的之实现的生命活动,它是生命之所以被称之为生命的根本原因。 由于生命需要和其基础上的生命的本真驱动力推动下的“生—生”的生命活动是开放的,它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扩展便将生命连接成超越时间的永恒的“生命共同体”,这就使得处于“整体关联之在”中的生命具有了永恒性的面向。显然,从根本上说,生命的这种永恒性的面向的根源就在于内在于生命需要和其基础上的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的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所具有的整全性的超越性的结构。
综上,生命的本真存在的内容是创生,生命的本真存在的方式是“自在与共在并存”意义上的和谐共生,因此,生命的本真存在的需要(即生命需要)便是在相互创生中自我创生,即“生—生”的需要。进而,因果一体的“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需要基础上的)生命的本真驱动力—“生—生”的生命活动是生命的存在根据。同时,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所具有的内在的整全性的超越性赋予了生命以超越性,即永恒性的面向。
(二)人之生命的独特性
毋庸置疑,进化使得人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生命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表现为:
首先,与其他生命“仅仅作为种群成员”而分享种群的意义并仅仅服务于“种群延续”这一“种群大体”的目的(如对于蜜蜂或土拨鼠来说,有意义的生或死,或有意义的关联仅指种群,而任何一只蜜蜂或一只土拨鼠作为个体本身都是无意义的)不同,人具有个体化自我的需要,即人的意识、自我意识、理智和从生到死的生命故事和自觉的生命意义使得他/她可以从群体中凸显出来,即他(她)有需要也有能力个体化自我,从而使自己作为个体本身而有意义。
其次,与其他生命不同,人因拥有足够清晰的意识、自我意识与理智而摆脱了与生命活动直接融为一体的规定性,即他/她有能力从事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实践(如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繁衍)。
再次,由于人进化出了足够清晰的意识、自我意识和理智,使得他/她可以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有死性,即发展出了个体的死亡意识,这是进化出了个体化自我的能力和需要的人所需付出的必然代价。进而,人便有了超越死亡所带来的虚无的超越意识和超越的需要,即以有限之身追求无限的需要,这是人的终极需要。
最后,如前所述,人具有个体化自我的需要与能力,而对于人之外的生命来说,有意义的关联仅指种群,因此,在生命的整体关联中,人是以个体身份参与“生—生”的,而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则是以种群身份参与“生—生”的。由此可见,作为“常识”的“动物弱肉强食”的观点是片面地着眼于对动物个体的观察而导致的偏见,进而,以“弱肉强食”来类推人的本质必然走向荒谬。
(三)人的生命需要的独特性
由上可知,人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他/她因具有足够清晰的意识、自我意识、理智、死亡意识、超越意识、个体化自我的需要与能力、从事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实践的能力和“以有限之身追求无限”的终极需要等而区别于其他生命。因此,与其他生命相比,在其作为存在依据的因果一体的“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需要基础上的)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生命需要和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所推动的)“生—生”的生命活动方面,便具有了如下几个方面的独特性。
首先,人之“生—生”的本质性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实践。具体而言,对于人之外的其他生命来说,“为其所是”或“成为自己”的创生是无意识的、自动而非自觉的,而对于有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自由意志的人来说,这种自我实现意义上的创生是通过“选择自己的自我”的有意识的自由与自觉的生命实践来达成的。也就是说,人摆脱了与其生命活动直接融为一体的规定性,也便担负了使自己存在与自由的责任。进而,人要实现“生—生”,或遵循“生—生之道”,需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是自为的。正因为如此,人也存在被异化和自我异化的可能性,而异化在人之外的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如橡树不可能开出梨花,除非人为干预。在笔者之前的系列论文〔26〕中,将人的这种自由自觉的本真的(即非异化的)本质性的(即作为存在依据的)生命实践称为“互慈和创”。其中,“慈”便是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这种驱动力肯定、成全与创化生命。它既指向整合,又指向创造,即在整合中创造,在创造中整合,在整全与创造中超越。“互慈和创”则是由“慈”推动的人与人之间肯定、成全与扩展双方自我,肯定、成全与扩展双方生命的,协同创生的有意识的生命实践活动。显然,“互慈和创”是人之生命的本真存在的实现和表达。
其次,在“互慈和创”中,人之存在与人之自由与道德得以一体实现,或者说,在人之存在中,人之自由的现实化与道德的现实化得以统一。具体而言,对于人,因果一体的“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即“慈”)—互慈和创的生命实践不仅表达了“选择自己的自我”的自我实现意义上的自由的需要与个体化自我的需要(即通过有意识的自由与自觉的生命实践而发展自己的本质力量、天赋和潜能从而肯定自己的存在,肯定自己的生命),还表达了作为其实现方式(即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的和谐共生中的“生—生式的关系”中的道德需要。具体而言,在这种遵循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的关系中,双方的人格都被承认,双方都被允许“如其说是”地存在与行动。也就是说,每个人都不把对方当作观察、研究与利用的客体或对象,更不把对方视为可操纵的工具,同时,各方都通过将对方的需要当作自己的需要而形成的开放的“我们”而超越了“原子式个体”的“严格的私人性”,从而在和谐共创的活动中舒展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共同扩展与实现着双方的生命。显然,这种“生—生式的关系”是互为目的的,因此,它是一种道德关系。同时,互慈和创这种实现道德关系的本真的生命实践也便是道德实践。
再次,在人的“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即“慈”)—互慈和创中,人实现了个体性和整全性的统一。具体而言,对于人类个体而言,其“整体关联之在”,即“生—生”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扩展而成的开放的“人类生命共同体”是超越时间的,是永恒的,而其中的每一个节点(即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可被看作是“永恒的人类生命共同体”的一环,即“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也就是说,人类个体既是个体化的她/他自己,又是“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永恒的大我”,即她/他处于个体性与整全性的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之中。例如,我们每个个体的物质创造或精神创造不仅是与同代人合作的结果,还是以前人的物质和精神创造的结果为前提的,同时,我们所创造的成果又会作为未来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创造的前提。显然,对于人来说,“我是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是可以被自觉认识的,进而,他/她对此的确认会带给他/她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和由此获得的勇气、力量感所形塑的整全性的人格(即“大我”人格)基础上的精神维度指导下的生命态度、行为方式和本真的生命实践。
复次,在因果一体的“生—生”的生命需要—慈—互慈和创中,人实现了有死性和当下永恒的统一。我们已知,人是个体性和整全性的统一,即一方面,人具有个体性,而人之个体(包括个体的身体、作为个体的身体的抽象物的个体的名字、作为个体的身体的延伸物的个体的灵魂)和附着于人之个体之上的那些东西(如金钱、权力、珠宝、房屋、地位、声名、荣誉、死后的个体灵魂的“待遇”等)都是落入时间中的。由于时间的特征是“成—住—坏—空”过程中的能量的耗散性(这是熵增定律所决定的),因此,上述落入时间意义上的“时间之物”是有死的、有限的和虚无的。〔27〕另一方面,人又具有整全性的面向,即她/他又处于永恒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开放的“整体关联”之中,也即她/他又是“潜在的人类生命共同体”这一“大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永恒在时间中投影于每一个当下,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当下永恒”;第二,永恒在每个人类个体身上投影为“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和由此获得的勇气、力量感所形塑的整全性的人格基础上的精神维度指导下的生命态度、行为方式和生命实践;第三,由上可知,有死的人类个体是在每个当下通过生命意义、大我的人格及其生命实践而契入永恒的(即契入永恒的人类生命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由此,达成了个体性和整全性的统一,有死性(有限性)与当下永恒性(无限性)的统一。因此,永恒性与超越性并不脱离于感性生活和感性实践。
最后,人之生命需要和终极需要是一体实现的。我们已知,人之生命需要内蕴的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所具有的整全性的超越性的结构赋予了人之生命以永恒性,同时,人具有以有限之身追求无限的终极需要。因此,对生命需要的满足就是对人之终极需要的满足,也就是说,人之生命需要和终极需要可以在互慈和创中一体实现。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便可以回答“人是如何存在的?”这一问题。在因果一体的人之“生—生”的生命需要—慈—互慈和创中,人之存在、人之自由和人之道德得以一体实现,人也实现了个体性与整全性的统一和有死性与当下永恒的统一。同时,这里的永恒的超越性的根源是内在于活生生的人之生命需要—生命的本真驱动力(即“慈”)—本真的生命实践(即“互慈和创”)中的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这种超越性的结构,即它是一种基于感性世界和感性实践的内在超越。
二、我们何以存在——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的生命面向的翻转
(一)生存性需要及其与生命需要的关系
显然,人还有生存性需要,它是指人的自我保存的需要,即一方面,人是生物性存在,需要一定的与身体相关的物性需要以维持生存;另一方面,人是社会性存在,需要与他人在物质、情感和精神上形成关联,不可孤立地生存。生存性需要作为生命需要的基础和前提理应内含于并服务于生命需要(即生存性需要理应指向并服务于生—生的内在目的,而非“仅仅为了活着”),由此体现的是人之需要的全面性、整体性与一致性。与之相反,如果出现了生存性需要的片面发展,人便会被禁锢于“(盲目追逐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仅仅为了活着的目的”和“严格的私人性”(即片面的个体性),表现为需要的萎缩、退化和片面化,甚至可能趋近动物的需要,即失落存在而陷入虚无(这既体现为自由的失落,又体现为道德的失落)。此时,人便发生了异化。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们陷入片面的生存性需要或片面的个体性?或者说,是什么遮蔽了人的生命需要?又或者说,什么是人之存在和自由与道德的现实化的障碍?其答案便是下文中将要论述的作为人之弱点的生存性恐惧。
(二)生存性恐惧
本人在之前的系列论文〔28〕中论述了作为最深层次的人性的人之弱点,即“生存性恐惧”,这里将对它作进一步的细化讨论。
人具有急切的自我保存的需要,即生存必须性的需要,正是生存必须性的需要所具有的急迫性,使得生存必须性及其所引发的“生存性恐惧”,即“对(生存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的恐惧”,成了对人之自由的内在胁迫,即生存必须性的胁迫。“生存性恐惧”是人之弱点,如果被它摄住,人们常会盲目追求生存性的安全感,从而将生命力虚耗在偏离自我实现(这一内在目的)的外在目的上,即处于盲目和不自由的状态。总的来说,人的“生存性恐惧”包括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物性的生存性恐惧又可细化为三个方面。具体而言:
一方面,人具有对(生存安全感意义上的)物性匮乏的恐惧。如果某种机制制造了虚假的物性匮乏而引发了匮乏感,便会迫使人们盲目追逐匮乏感所指向的对象,从而挟持了人的目的。概言之,“对物性匮乏的恐惧”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建立于对个体身体死亡的恐惧之上的,对扎根于个体身体的物性的那些东西(如房产、首饰、金钱、豪车等)的(生存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的恐惧。在消费主义喧嚣的当代社会,此种恐惧可能来自真实的匮乏,但绝大多数则是被他人或社会通过广告等欲望生产机制制造的虚假的匮乏。〔29〕第二,是建立于对个体身体的抽象物(即个体名字)死亡的恐惧之上的,对扎根于个体名字的声望、名誉等的(生存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的恐惧。如西方封建时代的骑士精神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英雄主义激情便是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目的而通过制造“对名声和荣誉的匮乏感”,并以作为人之弱点的“对个体名字死亡的恐惧”为中介而塑造的对名声或荣誉的盲目追逐的人性。第三,是建立于对个体身体的延伸物(即个体灵魂)死亡的恐惧之上的,对扎根于个体灵魂的那些东西(如宗教恐怖主义组织许诺给执行自杀式恐怖袭击者的死后“待遇”)的匮乏的恐惧。这些恐怖袭击者的残忍性是宗教恐怖主义组织通过制造“对个体灵魂死后‘待遇’的匮乏感”,并以作为人之弱点的“对个体灵魂死亡的恐惧”为中介而制造的。
另一方面,人具有“对社会性(生存安全感意义上的)匮乏的恐惧”,也即“对不被他人或社会认同的恐惧”。如果某种机制制造了“孤立感”,则会引发此种匮乏感和恐惧感,它会使人以窒息本真自我和牺牲内在自由为代价与他人关联以追求虚假的安全。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人泛化成标准的人性,自利和竞争也泛化成标准的人际关系模式,这使得人们感觉被丢到了一个相互敌对的世界而孤立地存在,进而,被认同的神经症性需要使他们机械地与外界关联而被周围吞噬。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认为的,工业社会中的人之个体如同机器中的螺丝钉,成了“群众”,即无明显差异的因处于同样情绪压力下而融为一体的一群人。〔30〕显然,雅斯贝尔斯没有辨认出这些情绪压力的根底正是生存性恐惧。
综上,对于人之个体自身而言,不能超越生存性恐惧(即不具备超越生存性恐惧的勇气)从而陷入“片面的生存性需要”是其弱小恐惧、盲目追逐和盲目屈从的原因;对于关系而言,不能超越生存性恐惧从而陷入“片面的生存性需要”是人们相互疏离与相互斗争的原因。也就是说,生存性恐惧既是人之自由的现实化的障碍,也是人之道德的现实化的障碍,总之,是人之存在的现实化的障碍。因此,超越生存性恐惧的需要也可以看作是生命需要的一个方面。
(三)非此即彼——人的两重生活境况
本人在之前的系列论文中根据是否超越生存性恐惧将人之个体的生活境况分为被生存性恐惧摄住的“片面的生存性境况”和超越了生存性恐惧的“生命性境况”。显然,对于人类个体来说,他/她的具体的生活境况是非此即彼的。
具体而言,所谓“片面的生存性境况”是指人如果不能超越“生存性恐惧”,就会被“匮乏感”和“恐惧感”封闭在(盲目追逐生存性安全感意义上的)“仅仅为了活着的目的”和“严格的私人性”(即对小我的有用性或狭隘的私利)中。其中,“仅仅为了活着的目的”表现为盲目追逐匮乏感所指向之对象(如卖肾以盲目追逐广告所制造的对苹果手机的虚假的需要),或盲目屈从于异化的社会力量(如阿伦特在对纳粹恶行的反思中所揭示“无名之人”所犯下平庸之恶),从而丧失“选择自己的自我”的独立能力而成为“萎缩者”;“严格的私人性”则表现为失去了相互通达的能力而陷入“原子式个体”的片面的个体性的状态,即对其所遭遇的所有事物,包括他人的言行,都反射性地机械性地用“对生存性小我的有用性/狭隘的私利”来衡量与歪曲,便失去了相互间有效沟通的可能性。由此,在对片面的生存性需要的盲目追逐中,这些作为原子式个体的萎缩者既丧失了独立性和使自由现实化的能力,也丧失了相互结成生—生式的道德关系的使道德现实化的能力。总之,在此境况中,生存性恐惧遮蔽了生命需要而使生存性需要片面地发展,从而导致“片面的个体性的个体”失去了使自己本真存在的能力,即陷入了虚无。
所谓“生命性境况”是指人之超越了生存性恐惧从而摆脱了匮乏感和恐惧感的状态,其中的个体是既有能力通达他人又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自我”的“超个体的个体”(也可称此种个体为“跨主体性的个体”〔31〕或“超自我的个体”)。也就是说,“超个体的个体”既具有使自由现实化的能力,又具有使道德现实化的能力,总之,是具有使自己存在的能力。本质上,生命性境况就是生存性需要服务于生命性需要的境况,也即去除了生存性恐惧的遮蔽而使因果一体的人之生命需要—慈—互慈和创得以呈现的状态,于其中,人之存在、自由和道德得以一体实现。
(四)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的生命面向的翻转——存在或虚无
对人来说,他/她的具体的生活境况是非此即彼的,即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人或是处于生命性境况(即存在)而使“超个体的个体”显现,或是处于片面的生存性境况(即虚无)而使“原子式的个体”(即具片面的个体性的个体)显现。我们可以将上述机制描述为“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的生命面向的翻转”,即“成勇以成人”。
实际上,生命面向的翻转和“超个体的个体”的诞生在很多的个体和很多的当下不断地发生着、被见证着,却因之前没有形成关于超越生存性恐惧和生命面向翻转的普遍性的知识,它们的意义被忽略了。如那些为新中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那些孔繁森和焦裕禄式的怀着真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员,那些在火灾、洪灾、地震中勇敢救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人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生命面向的翻转和“超个体的个体”的呈现体现于每个当下的人之个体的生命意义、大我人格和生命实践,但对生存性恐惧的四个层次的超越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因此,即使是行于这条感性实践基础上的精神之路上的人,在生命面向稳定于生命境况之前,他/她也常会出现“原子式个体”和“超个体的个体”反复交替出现的情形。因此,这是一个认识与再认识和实践与再实践的过程,但绝不是无法达成的。与此同时,由于相关的普遍性的知识已经被揭示出来,相较于人类之前的隐性知识的路径,它是更容易达成的。
与此同时,在很多情境下,当生存性恐惧被某些原因遮挡,也会发生生命面向的翻转。如在孟子所讲的“乍见孺子入井”的故事中,因“乍见”而生存性恐惧尚未升起,因此,救人者在救人时处于生命性境况;当人们被自然的大美和艺术的大美震撼而“忘我”时,或处于极度专注的状态而“忘我”时,生存性恐惧同样未能升起,人们同样处于生命性境况。在上述情境下人们所体验到的安宁与喜悦便是生命需要得以满足和人之存在得以显现的有力证明。当然,如果没有超越生存性恐惧的自觉,当人们回归日常生活时,有可能时常处于原子式个体的“萎缩”状态。由此可见,即使在无超越生存性恐惧的自觉的情况下,人也可能在其一生中随着是否受制于生存性恐惧而不断变换着生活境况。〔32〕
由上,通过揭示“生存性恐惧”这一人之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现实化的障碍,我们回答了“人何以在感性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即通过“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的生命面向的翻转”,人才能从虚无跃入存在,也即“成勇以成人”。
三、生命需要与生存性恐惧对“人之存在之谜”的揭示
(一)之前理论的缺陷
揭示人如何以及何以克服虚无而在感性世界中“为其所是”(即存在)是哲学的根本任务。然而,无论前人的外在超越的实在论的存在观、以概念为基础的观念存在论、以体验为基础的观念存在论还是指称存在论,都没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其原因在于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没能确认恰当的人之存在根据,由此便不能回答“人如何在感性世界中存在?”,也即“感性世界中的人之存在的内容和人之存在的方式是什么?”。显然,人在感性世界中的存在依据必须具备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只有当此存在依据具有内在性的超越性时,才能赋予有限和有死的人之个体以永恒性和自由性。第二,只有当此存在依据具有因果一体性时,人之自由才可能实现,即人仅因其生命的本质的必然性而存在,也即人之行为摆脱了内在与外在的他性之力的奴役与支配而仅由其自身来决定。第三,只有当此因果一体的存在依据处于超越时间的当下时,人之存在才能既摆脱时间中的前因—后果的因果链而获得自由,又能获得永恒性这一“真无限”。〔33〕第四,只有当此存在依据具有整全性的超越性时,人之存在才可能既超越片面的个体性的有限性和有死性,又可达成道德与自由的一体实现。同时,只有当这种整全性的超越性具有内在性时,才能为道德和政治提供本然性的应然性的依据,即才使得自律性的道德和“作为自由的政治”成为可能。第五,只有当此存在依据内蕴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的结构时,其内在的整全性的超越性才有可能。第六,只有当此存在依据是人的感性需要时,才能为人之存在提供使其现实化的内在动力,即它是一种活的力量。显然,之前的理论都不能提供具有上述特征的人之存在的终极根据。
另一方面,是没能揭示人之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现实化的障碍(即从虚无跃入存在的障碍),也即前文论述的生存性恐惧,由此,它们就无法以普遍性的知识(即非隐性知识)回答“人何以克服虚无而在感性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例如,为了应对近代的主体性哲学的失败而引发的道德危机,胡塞尔开启了“主体间性”的研究视域,后经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的努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但由于没有发现生存性恐惧,他们分别将“主体间性”禁锢在思维、体验和关于如何有效地对话与协商的知识中,从而不能使主体间性和基于主体间性的自由与道德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34〕也即人之本真存在不能在客观世界中现实化。由此,人依然被囚禁于虚无的洞穴中。
(二)生命需要与生存性恐惧对“人如何以及何以存在”的揭示
我们已知,由于前人没能给出恰当的(即具有内在的整全性的超越性和活的力量的因果一体的)人之存在依据,便不能回答“人如何克服虚无而在客观世界中存在?”;同时,由于没能揭示生存性恐惧这一人之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现实化的障碍,便无法回答“人何以克服虚无而在感性世界中存在?”。总之,人之存在的普遍知识仍在幽暗之中。
通过本文前几部分的讨论,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
1.对于一般的生命来说,生命的本真存在(即“为其所是”)的内容是创生,生命的本真存在的方式是“自在与共在并存”意义上的和谐共生。因此,生命的本质性的(即作为存在依据的)需要,也即生命需要,便是在相互创生中自我创生,即“生—生”,它是生命之所以称之为生命的根本原因。
2.人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他/她因具有足够清晰的意识、自我意识、理智、死亡意识、超越意识、个体化自我的需要与能力、从事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实践的能力和“以有限之身追求无限”的终极需要而区别于其他生命。因此,与其他生命相比,在其作为存在依据的因果一体的“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需要基础上的)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生命需要和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所推动的)“生—生”的生命活动方面,便具有了独特性。
3.通过对一般的和人之特殊的生命需要的讨论,我们可以回答“人是如何存在的?”这一问题。简单地说,在因果一体的作为人之存在依据的人之“生—生”的生命需要—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即“慈”)—自由自觉的本真的生命实践(即“互慈和创”)中,人之存在、自由和道德得以一体实现,人之生命需要与人之终极需要也得以一体实现。同时,此具有活的力量的存在依据所内蕴的内在的整全性的超越性也赋予人以个体性与整全性的统一和有死性与永恒性的统一。其中,永恒存在于当下,存在于与永恒相关的生命意义,及其所带来的勇气和力量感所形塑的整全性的人格基础上的精神维度指导下的生命态度、行为方式和生命实践中。同时,这里的永恒的超越性的根源就内在于活生生的人之生命需要—生命的本真驱动力—本真的生命实践中的人之生命的本真存在方式这种超越性的结构中,即它是一种扎根于感性世界和感性实践的内在超越。
4.作为人之弱点的生存性恐惧是生命需要被遮蔽的原因,它既是人之自由现实化的障碍,也是道德现实化的障碍,总之,是人之存在现实化(即克服虚无而在感性世界中存在)的障碍。进而,对人来说,他/她的具体的生活境况是非此即彼的,即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人或是处于生命性境况(即克服虚无而存在)而使“超个体的个体”(即“跨主体性的个体”或“超自我的个体”)显现,或是处于片面的生存性境况(即失落存在而陷入虚无)而使片面的个体性的个体(即作为“萎缩者”的原子式个体)显现。我们可以将上述机制描述为“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的生命面向的翻转”。由此,我们便回答了“人何以在感性世界中存在?”的问题。
5.“生—生”的生命需要是人之存在的基础和根据,也便是人之真正的价值的基础与根据。与此同时,对于人类个体来说,生命需要是作为自由的道德(即自律的道德)的基础;对于社会来说,生命需要是作为自由的政治(包括法律和制度等)的合理性的依据。在此坚实的基础上,我们才能驱散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所带来的虚无的迷雾。也就是说,“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35〕
综上,通过对人之存在依据(即“生—生”的生命需要—慈—互慈和创)、作为人之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现实化的障碍的“生存性恐惧”和“以超越生存性恐惧为枢纽的生命面向的翻转”的揭示,我们发现困扰人类的“存在还是虚无”的问题本质上就转化为如何体验、认知、激发与强化人之生命需要和如何超越生存性恐惧而发生生命面向翻转的问题。
(三)前人的作为隐性知识的生命需要
生命需要和其基础上的生命固有的本真驱动力是一种活的力量,因此,在不受制于生存性恐惧的情形下,这股活的力量就会被人感知到。由于没有对它的普遍性的知识,前人对它的处理方法有两种:其一,是将它外在化,如在它之上设置象征性的神或上帝,或如巴门尼德一样将它设置成外在超越的本原;其二,是形成各种关于内在超越的隐性的知识,如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格物致知”、印度文化中的“梵我合一”、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斯多亚学派的把握性印象、克尔凯郭尔的信仰的跳跃、基督教中的圣灵的力量等,但它们都没能形成普遍性的知识,因而不能被常人所理解。同时,由于没有辨认出生存性恐惧这一内在超越的障碍,对于“内在超越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同样没有形成普遍性的知识,如儒家无法以普遍性的知识确切地说明“格物致知”何以可能;奥古斯丁、叔本华、胡塞尔等无法以普遍性的知识确切地说明内在直观、感性直观、本质直观何以可能;同样地,尼采呼唤意志的高贵和强壮,却没能回答意志何以高贵和强壮。然而,无论如何,这种隐性知识在人类历史上不断地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是生命需要不断地冲破生存性恐惧的遮蔽而自我表达的有力证明。
近代以来,西方的启蒙理性和主体性哲学的根本缺陷是没有恰当的存在论基础,也即缺乏恰当的人之存在的依据,这使得理性只服务于主体性(即原子式的经验性的个体性)的个体的盲目的生存性需要,由此,带来了普遍的虚无和道德危机。笔者的系列文章〔36〕分别揭示了近代以来作为西方哲学前提的“原子式的个体”不具有使道德、自由、民主、主体间性、人类健康共同体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有效防疫现实化的能力。由此,人类文明需要再启蒙。再启蒙的宗旨是使人回归人之生命需要和生命的本真驱动力,也即促进生命面向的翻转,从而使人从虚无跃入存在,使作为“大我”人格的实践主体的“超个体的个体”(即“跨主体性的个体”或“超自我的个体”)的“新人”诞生。于当代,再启蒙除了对真正的人类文明的建构意义之外,还在破解“市场失灵”和“政府介入可能发生腐败”的两难处境、破解对负有更高道德责任的医师的医德培养的困境、破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有效防疫的困境、破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困境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不再赘述。
注释:
〔1〕〔3〕〔11〕〔12〕〔13〕陈中雨:《巴门尼德的存在之路及其现代意义》,《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2〕〔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册,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0页。
〔4〕〔5〕〔古希腊〕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著作残篇》,李静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2-83、90页。
〔6〕〔德〕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7〕〔8〕〔10〕张宇:《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思想研究》,吉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9〕宫瑜:《交往理性与道德共识——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14〕〔30〕黄藿:《从精神医学到存在哲学——论雅斯贝尔斯的〈时代的精神处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15〕颜一编:《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6页。
〔16〕〔美〕亚伯拉罕·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7〕Alderfer C P.,“An empirical test of a new theory of human needs”,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1969,4(2),pp.142-175.
〔18〕冯蕾、郭亚锋:《基于麦克里兰三重需要理论的高校高素质教师培养问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20年第21期。
〔19〕姚顺良:《论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的理论——兼论马克思同弗洛伊德和马斯洛的关系》,《东南学术》2008年第2期。
〔20〕刘世昱:《马克思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21〕张积家、陈栩茜:《马克思的需要心理学思想》,《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2〕〔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
〔23〕〔美〕埃里希·弗洛姆著、黄颂杰主编:《弗洛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2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58页。
〔25〕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
〔26〕之前的系列文章参见蔡昱、龚刚:《论“人性”和“人之本性”——兼论中国文化激励下的“最美逆行者”》,《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蔡昱、龚刚:《守护人之本性——再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和人类文明再启蒙》,《南开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蔡昱、龚刚:《从“畏死的恐惧”看西方民主的前提错误——兼论民主能力及勇气》,《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27〕〔32〕〔33〕蔡昱:《有死性与当下永恒的统一对生存性恐惧的超越——作为践行性医德培养路径的生死教育》,《中国医学伦理学》2021年第12期。
〔28〕之前的系列文章参见蔡昱:《从生存性恐惧看道德如何现实化》,《道德与文明》2021年第4期;蔡昱、龚刚:《“看不见的手”与中国增长奇迹:激励机制还是资源配置机制?》,《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蔡昱、龚刚:《从畏死的恐惧看人的境况——三论节制欲望的共产主义和人类文明再启蒙》,《学术界》2019年第6期。
〔29〕蔡昱:《资本逻辑下的欲望异化及人类的自我奴役》,《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31〕“跨主体性的个体”参见蔡昱:《跨主体性的能力——从“畏死的恐惧”看跨主体性何以可能》,《学术界》2021年第2期;蔡昱:《医患共同决策何以可能——兼论“跨主体性的能力”与“参与式教育”》,《医学与哲学》2021年第12期。
〔34〕蔡昱:《跨主体性的能力——从“畏死的恐惧”看跨主体性何以可能》,《学术界》2021年第2期。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1页。
〔36〕参见蔡昱:《当代美德伦理学的缺陷和医德培养的关键》,《医学与哲学》2021年第13期;蔡昱:《跨主体性的能力——从“畏死的恐惧”看跨主体性何以可能》,《学术界》2021年第2期;蔡昱:《论作为公共卫生伦理基础的“超个体的个体”和“人类生命共同体”——兼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前提错误》,《中国医学伦理学》2020年第4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