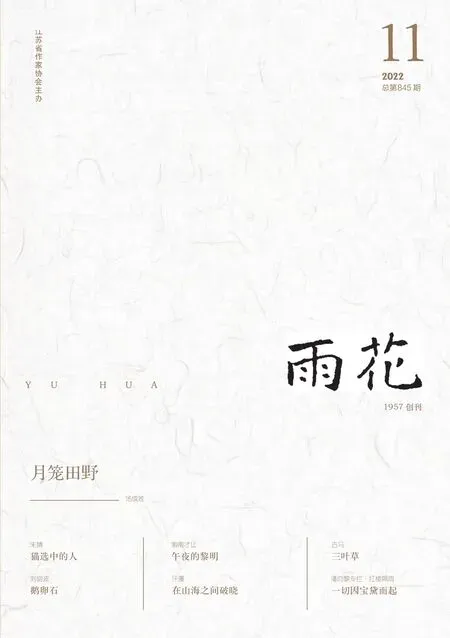在怕与爱中成长
张月芳
水草稞里的水獭猫
小花家的三间土基墙的茅草屋在我家斜对过,门前朝南有一大块空旷的平地,平地缓缓的下坡处是一条清澈的小河,玉带一样。河边高低不平的大小石块,是村人踩踏的码头坡子。庄上附近的人都喜欢到这条河边来。他们淘米、打水、汰衣服、刮锅。人多的时候,我们小孩儿也一窝蜂地来起哄。调皮的男孩子在空地上打仗、斗鸡、打水漂。我们小姑娘蹲在紧靠河岸的小石头上,看小鱼游动,夏天赤脚踩在水里,让小鱼亲吻我们的小腿,痒舒舒的。长满青苔的石头根部爬满了螺蛳,它们顶起它们圆形的小门,伸出头偷瞧我们,又立即缩进了螺眼里。我们把它们一个个拾下来,放进淘篓里,回家用水养着,等待母亲的红烧螺蛳,或螺蛳肉炒韭菜。有时候我们也能拾到大大的贝壳,父母们叫它“歪歪”,就像母亲擦脸的“歪歪”油。它们一张一翕,弧形的两扇银门反射着白光,里面带嘴唇的白肉慢慢朝外吐着,厚实肥美。我从没有捡到过里面有珍珠的河蚌,小花捡到过,她把她捡到的大河蚌扒给我们看,在河蚌肉根部靠蒂的地方,两颗大珍珠圆圆的,晶莹透亮。
石头缝里、螺蛳壳里藏满了我们的爱,而河东面的那片水草丛里,芦苇与茭白杂生的一大片领域,是水獭猫和白胡子老爷爷出没的地方。我怕!农忙的时候,父母去田里割稻了,哥哥姐姐也帮着去捆稻。爸爸说,“你就在家看猪,吆鸡,猪不要拱了圈门,溜出猪圈,鸡不要到西山屋后,啄了菜叶,天要黑的时候,就先淘米煮饭。你已经九岁了。”爸爸的大眼睛看着我,严肃中也有疼爱,妈妈用手揩了一把我的鼻涕,他们匆忙地下田了。
是的,我已经九岁了,我要做事。猪吃饱了躺在圈里睡了,老母鸡卧在草垛边准备下蛋,大太阳还热辣辣的时候,我就去淘米了。小花家的门紧锁着,河边空荡荡的。我踩着石头试探着朝河边水更清的地方挪动,左脸旁就是那水草丛。水獭猫就潜伏在那里,人少的时候它就会出来,小霞就是被它们拖进去吃掉的。还有夜摸子,夜里从这里飞出来,飞到哪家,摸一下孩子的鼻子,孩子就死了。小云的弟弟就是被夜摸子摸死的。秋香的奶奶说,有时候白胡子老爷爷也会从里面出来,拄着拐杖,拎着一个大白布袋,不听话的孩子都装进去带走。我扭头看看身后,没有白胡子老爷爷,一只癞蛤蟆蹦进草丛里,乱草一阵骚动,吓得我把米只浸了一下水,就赶忙朝家溜。
荸荠塘里的狐仙
八岁时,我在柘垛镇中心小学上一年级,离家三里路。有一年冬天,放学后我留下打扫卫生,回家时,天已经黑透了。
柘垛镇到我们村,中间隔着个湾址村。从湾址村的庄台上走,我不怕,路两边都是人家。有两户人家的小孩比我小,天天看我从他们家门前经过,还给我起了外号,一个叫我“烂苹果”,因为一到冬天,我脸颊上就会生两个大冻疮。还有一个叫我“小裙子”,那时候,农村穿裙子的孩子不多,我的裙子都是舅母从上海寄来的,很洋气。我至今还记得这两个孩子的样子,其中一个瘪嘴的小姑娘现在居然跟我生活在一个小区。
他们叫我外号的时候,我一点也不生气,反倒有一种他们在给我壮胆的开心。可是这个胆最多只能壮我走一百米路。走过有人的村庄,拐过弯,还有一段长长的路,两边都是农田,大片大片的,看不到边。北面一块农田的顶头,有一个四方的小小的荸荠塘,枯萎的荸荠叶黄黄的,瘫软在地上,像一地稻草。白天我听小云子说,春来有一天晚上经过这里,解了一个小便,后来就在这里打圈,走到天亮也没能走出去。大人们说,他是被狐仙缠身了。春来后来就一直在家里,我没有看他出来过。他说话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像女人一样。小云子还说,巧珍有一次也是,蹲下来小解以后,一直血流不止……
我越想越害怕,把屁股后面一颠一颠的黄书包按到面前,一边走一边哭。忽然,我听到妈妈叫我的声音,“大双子哎,大双子啊……”看到妈妈手里电筒的亮光,我瞬间停住了哭,朝亮光飞奔过去。
田里的鬼风
夏天的一个黄昏,妈妈扛着长柄的水舀,给田头边自留地里的瓜秧浇水。第二天早上,妈妈便下不了床了。腿疼得她哼了一夜。
庄上的老八太说妈妈中了鬼风了,她家的大娘子(老大的老婆)就是到河边挑水时,被鬼风一吹,嘴歪了,腿也瘸了。我去庄上打酱油时见过她家的大娘子,四赖子的老婆,拄着一根拐杖,嘴歪得靠近了耳朵根,流着口水,斜着眼看人,目光呆滞,嘴里“喔喔”的一句也听不清。她家的那条巷子,狭长阴森,一直连到河边,四赖子的老婆靠着墙往家挪。
隔壁邻居小矮子说,东角墩有一个大仙很灵,一看就好。爸爸把妈妈抱进了船舱,二叔撑船。我和哥哥也跟了去。到了大仙家的码头旁,二叔先跳下船,将扣船的粗麻绳套在了码头桩上。妈妈被抱下了船,放在大仙家的堂屋正中间。大仙家的堂柜上,点着高高的两对大蜡烛,观音菩萨像前,摆满了供果。大仙是个矮个子的小老太婆,她围着妈妈又是唱又是跳,“天灵灵,地灵灵……我看你哪里逃?……”大仙一剑劈下来,又继续唱跳,左劈右斩。天已经很黑了,我困了,爸爸让哥哥带着我走路先回去。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怕极了!东角墩到我们村中间有大片坟地。惨白的月光照着一个个坟头,高一个,低一个,有戴着土帽子的坟头,有掉了帽子的坟头,像人被砍了头,帽子斜倒在地上,七零八落,风吹着树叶发着“沙啦啦”的声音,不时还有乌鸦的惨叫,我吓得不敢落脚。走过了两个坟头,我实在不敢走了,瘫在坟之间的空地上哇哇大哭,说肚子疼得不能动。哥哥没有办法,驮着我往前跑。
夜里,爸爸妈妈回来了。
天亮的时候,爸爸在老爷柜前烧香,我看到他拿出几张真钱在香炉里烧,再把烟灰用纸撮起来。那天早上,爸爸喂妈妈口服了那烟灰,可妈妈还是疼得牙紧紧咬着,之后两个月没能下床。她已经瘦得没了人形,我常常倚坐在大门口的土墙上,听着屋里妈妈的呻吟声流泪。我很害怕,想着要是妈妈没了,我就跟她一起走。
后来,爸爸带着妈妈去柘垛镇上看了医生,医生说是风湿性关节炎,开了药并交代了护理方法。晚上,爸爸开始用加中药煮的一大锅热水替母亲熏腿,十天不到,妈妈的腿就好了。我们全家脸上又有了笑容。
睡在棺材板上
我有很多小人书,都是从舅舅家带回来的。安徒生的童话《豌豆公主》给童年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床榻上二十张床垫上面又铺了二十床鸭绒被,压在最下面的一颗小豌豆公主居然也能感觉到?甚至弄得她全身发紫,整夜都没有合上眼,太不可思议了。再想想我和姐姐睡的那张床,两张长板凳,上面铺了几块木板,都是外面捡来的,还有两块是棺材板,上面铺的是稻草,稻草上面铺了一层破棉絮,不要说一个豌豆,就是大石头藏在下面我也感觉不到,照样睡得香。事实也真是这样,冬天捂脚的盐水瓶经常滚到腰下,却也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看来我们连灰姑娘都不如啊。
我和姐姐从小就睡在这张拾来的棺材板铺成的床上。妈妈给我们织了一顶老夏布帐子,不白,有点发灰。我和姐姐常常在帐子里别上川英、栀子花,帐子里总是香香的。有时候,我们会把掏来的知了一个个放在帐子里,它们躬腰驼背,像穿着土褐色马甲的地主婆。早上一睁眼,知了不见了,只留下它们的盔甲还挂在帐子上,薄脆,闪着金光,中间裂开一道长缝,像一件连体的开衫,又像一个透明的小睡袋,小巧透亮。“知了呢?”我揉着惺忪的睡眼问姐姐。“肯定飞走了呗。”“怎么会呢?昨晚帐子门是关紧的。”“你夜里起来小便,帐子门压到席子下面去了吗?”我们一起看向帐子门,帐子垂垂地挂着。我们身子一动,它也跟着掀动两下,似乎在告诉我们,蜕了壳的知了就是从这里逃走的。我们小心翼翼地取下知了蜕下的壳,放在空的鞋盒里。等挑糖担子的进村,铜锣敲起,我们就取出鞋盒,用里面积攒的牙膏皮、鸡肫皮、知了壳去换糖吃……
小村庄里,我们既怕着,又爱着,我们爱着,又怕着。爱是能看到的,金黄的麦浪,碧清的河水,袅袅的炊烟,父母的呼唤……怕是看不到的,它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在怕与爱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