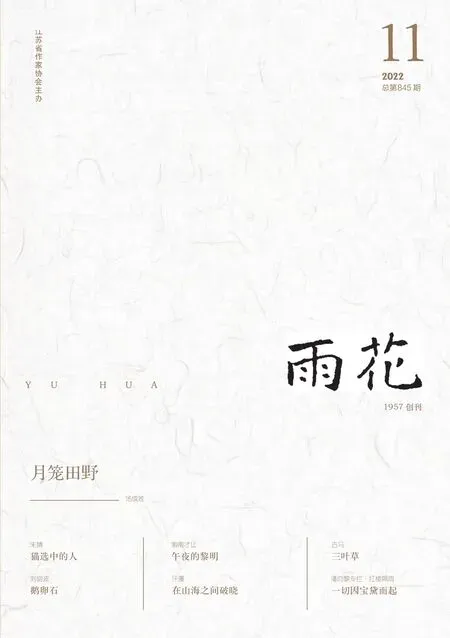静观和细语
——朱婧小说读札
韩松刚
如果以强弱来划分小说,有一种是恃强的,还有一种则是示弱的。恃强的小说,睥睨一切,却往往也目中无人,而示弱的小说则相反,时时都会保持打量的眼光,就像一只警觉的猫,于是,也便有了一种静观的视野。
朱婧的小说就是这样一种示弱的、静观的小说。因此,《猫选中的人》中的第一句——“阳台上的那只猫是妻子先发现的”既是叙事的开端,也是小说的方法。小说从写一只猫开始,围绕着猫这一明亮的主线,将“他”和妻子、父母亲两条或隐或显的感情线索编织得细密而有条理。
朱婧的小说,精于故事的设计,却从来不急于讲述故事,因为那些困在生活中的人就是故事本身。朱婧所设想的故事等同于一段生活、一段生命,甚至等同于一个谦卑而虚无的希望。以此来看《细路秘径》开篇所引的弗里德里希·尼采《阿里阿德涅的哀怨》,便不会觉得是一种虚张声势或小题大做。阿里阿德涅的被爱、被遗弃,以及她选择的永远离开,照见了《细路秘径》中一切普通人的爱的可能和命运。生活就像迷宫,而爱从来不是一把钥匙,它只是幻想的人在迷宫中的自我跋涉。
和《猫选中的人》一样,《细路秘径》同样是复调的叙事。水清和现实、和T(回忆)、和父母亲之间的交织,预示了朱婧对多重叙事线索的投入,并展示出一种丰富性的形式回归。但你也不要就此以为,朱婧有构建宏大情节结构的雄心,相反,它呈现出来的还是线条和图像,那些被仔仔细细地计算的时间,不过是一种想象,以及受此影响的我们对故事的看法。甚至于,很多时候,朱婧就是让我们在这一时间的往复中,去体验叙事的梦魇,去摆脱生活的重轭。
《猫选中的人》《细路秘径》基本上延续了朱婧小说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爱情、生活,以及与此相关的失落的、软弱的人。朱婧的小说,没有张爱玲笔下那种对人的内心黑暗的深刻剖析,那种绝望的有些残酷的灵魂审视,也没有萧红眼中那种种无所不在的痛感和麻木,那种带着生命的热力的挣脱和突围,相较于朱婧的细弱,这两个女作家着实太强悍了,而她只能是自己,以一种弱者的静观,对人生的困顿、无名的困惑、莫名的忧伤予以感同身受的体察。爱与恨,善与恶,悲与喜,一切的无奈与茫然,都在她静默的目光里。
朱婧的小说以细见长,细微、细小的事物,细致、细心的观察,细腻、细弱的感觉,叙事形态相关的绵绵细语。这一特征在她的小说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尤其是在遣词造句上,更是细到了一种极致。比如《猫选中的人》的结尾部分:“纸箱内有两只小猫,细小柔弱的身体依偎着,鼓鼓的脑袋互相触碰着,它们的眼睛微睁成细缝,时不时张开粉红色的嘴巴,露出轻软的舌头和几颗精巧的牙齿——这些牙齿让他想起他随身带着的,女儿换牙时掉落的细小的乳牙。”短短几句中,只“细”字就出现了三次,而其描述的精微和细致,更是有种不请自来的精妙。对此,何平曾评价说:“她写生活的枝枝叶叶,以及那些枝叶上或清晰或模糊的脉络,而不太愿意去理会那些摄人的花草香,她总是能在那些无关紧要的精神闲荡处,让你无时不觉出生活中一切细小东西的重要。”而我想,一个作家有意识、有耐心、有能力去书写微小的事物、微观的世界、微妙的情感,是不是也是一种成熟的标志呢?
细小即真实。相反,宏大则容易失真。朱婧的小说是一种“真的目光”的聚集,是喧嚣的世界背后,一个人静默的喘息和沉思,而这宁静里有人间百态和人生万象。小说就是生活,就是迷宫,让人猜不透,让人走不出,而朱婧并不急于甚至并不想猜透、走出。朱婧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小说观,那或许就是给生活的无奈以诗意的呈现,给那虚妄的混乱以理解的宽容。
朱婧的小说,少有精神上的炫耀,也没有笔法上的炫技,更不执拗于晦涩的智慧求索和固执的人性拷问,而只是执着于描写生活、想象生活,执意于完成对周边世界的自我陈述和表达。这表达里,有她对自己和世人的哀戚,有对生活(爱和生命)的不确定性的哀矜和叹息,由此便实现了一种审美的超越,显示出智性的高度和迷人的色彩。
朱婧的小说,因了这细的功夫,而少有一种情绪的激荡和情节的剧烈冲荡,一切的叙事和描写都显得缓慢而沉静。不管是在其早期的小说中,还是在《譬若檐滴》等小说中,朱婧对于剧烈的冲突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疏松,她始终以一种平静的眼光审视周遭的世界。即使是面对灰暗和不幸,朱婧也总能保持一种善的判断和美的感觉。
好似这复杂的世界与己无关,但其实确是事事关己。只不过,对于朱婧来说,她更喜欢或者说擅长以一种纯粹的审美来静观、细说和自身、他者密切相关的人生故事。她的隐秘的孤独感和天生的丰富内觉,使得她的小说远离外部世界过于政治化和社会化的时代语序。因此,在朱婧的小说中,你试图去捕捉时代的镜像几乎是徒劳的。
朱婧笔下的人是柔软的,与此相关的,她笔下的爱情也显得柔弱。对于人生、对于生活、对于他者,多的是同情的理解,而少有蛮横和不讲理。于是,爱了就是爱了,散了也便是散了。就像《猫选中的人》中的小猫们,“它们既不会要求,也不会抱怨,以为这逼仄、饥饿和匮乏是世间平常的事情”。
朱婧的小说清新而唯美,甚至流露出一种六朝的清寂,古典的忧郁和隐秘的忧思,在她幽微的小说世界里,纷至沓来。就像《细路秘径》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水清的名字一样,朱婧的小说在色调上也是冷的。古语说,水至清则无鱼。意思是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就像爱情,过于纯粹,并不见得能够存在。因此,当爱的空中楼阁消失的时候,在杂乱而真实的道具房里,另一种新的情感诞生了。
朱婧的小说以平静开始,也往往以平静结束。仿佛生活的原旨就是对喧嚣的反抗,从而实现一种精神的万籁俱静。那在笔尖流走的,似乎是朱婧发自内心深处的灵魂细语。朱婧的小说,有音乐般的质感和节奏,像如歌的柔板,是悲伤之情的慢舞,这低沉而柔软的情绪里,涌动着对于爱情、生活的孤独的隐忍和肃穆的哀悼。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发现朱婧小说对生活的呈现,那还不够,事实上,朱婧的小说内部有一种“重建”的冲动和执念——重建生活,重建自我,重建生命,重建爱情,重建一种健康的关系。比如在小说《猫选中的人》中:“他给过往生活的缺憾一一画上句点,他尝试探出一种可能去与一个真实具体的人,建立强烈的联系,从而去连结自己的未来,这是他没有机会从早逝的母亲那里学来的,人生绝无仅有的经验。”在小说《细路秘径》中:“她尊重他在权力结构里的位置,却也丝毫不为才华迷惑。爱才可以自己学,她早已获得了自由,因此无需将自由投射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当男女之间恢复了平等的精神状态,跨越层级的浪漫爱情就如最普通的白日梦一般消逝。”理想大相径庭,现实左右为难,但小说能够通过重构、重建来实现某种自由。
朱婧的小说,语言低调而内敛,叙事从容而舒缓,展现出她作为一位单纯的小说家所理解的斑斓世界。而她的小说艺术,就建立在她对生活的诗意理解之上和深度同情之中,她把灵魂的静默刻在了词语之间。由此,即便是在平静之中,朱婧的小说,也展现出灿烂的意象,据此和周遭世界的强力相对峙。
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说:“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懦弱往往要比勇敢更为有趣,正如失败要比成功更为精彩。”小说于朱婧来说,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夹带着一些莫名的寂寥和说不清的惆怅,因此,也便显得沉闷了许多。朱婧的温和,以及热烈的缺失,却也导致她对生活的表现,有时难免会偏于简单和简化。但是,在一片众生喧哗中,这忠实于自我的真切而内觉的调子,不是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吗?
我小时候被狗咬过、被猫抓过,对猫狗之类,着实没有太大好感。但一个好的作家可能就像猫一样,生性孤独,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它于生活不经意间的碰碰、摸摸、闻闻,就有了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