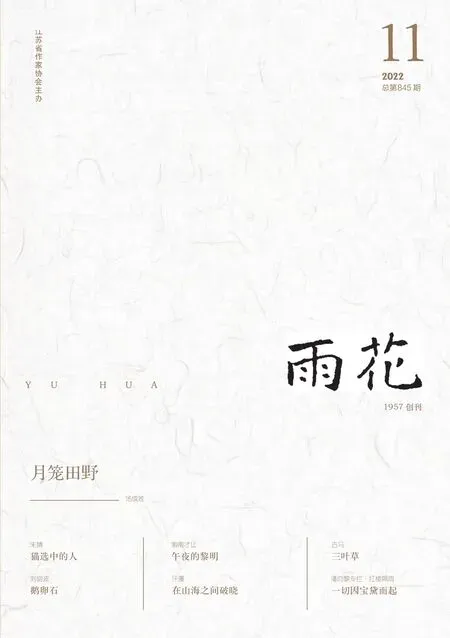祖宗树
姜 桦
滩涂地,一只苍鹰在头顶上盘旋,宽大的翅膀一直和大地保持平行。那条名叫阿黄的土狗在我身边跳来跳去,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仿佛永远不知疲倦。
手臂挥舞,一把柄长七尺的钩镰左冲右突,一路砍伐,一簇簇纠缠丛生的荆棘和杂树应声倒下,穿过那一大片望不到边的棉花田和湿气氤氲的芦苇荡,顺势爬上一个低矮的土坡,一座巨大的城堡出现在我眼前。那是一棵树,一棵比我先人的墓碑更古老的银杏树。此刻,它更像一座气势磅礴的深色山峰,顺着阳光,阔大的树影被一路送出去很远。满身的树皮粗糙如鳞,一棵经历了650年岁月的古老的银杏树,站在那里,更像一个经历过太多风霜的满脸皱纹的老人。
一棵树,我的祖宗树。
盐城市射阳县特庸镇码头村,黄海岸边一座向阳临水的古老村庄。一条破旧的木船系在早已荒废的码头上。岸边凸起一座高高的黄土墩,一棵四人合围的银杏树站立在巨大的影子里。
这是一个古老的遗址,又是一个神秘而不可知的时光密码。
中国东部沿海,由长江与黄河夹带的泥沙淤积成的滩涂地。一堆堆泥土,一颗颗砂砾,今年掩埋了去年,今年又会被明年覆盖。按照成陆年份计算,仅仅依靠一粒一粒泥沙的堆垒,脚下这片土地的形成起码应该有上万年的历史,但仅仅在近1000年以前,沿着当年范仲淹带领4 万民工修筑的范公堤,这片地域以东的地区,那闪着亮光的远方还是一片苍茫大海,脚下这片潮湿的土地还是一大片涨潮时沉没、退潮时露出的万顷滩涂。千年沧海桑田,伴随着大海的潮涨潮落,海水一寸一寸向东撤退。泥土慢慢高耸,波浪的踪迹渐渐远去,这片叫作盐城的土地留下,最终成为一片辽阔的滨海平原。时间在推移,咸涩的土地上开始生出稀稀拉拉的碱蓬和野茅草,渐渐地又生出了大片大片茂密的芦苇。树也有了,但都是一些杂树,那些树的种子,全靠一只只野鸟的粪便带来,天上地下,随意抛落。
时间回到1368年(农历戊申年,猴年),作为被称作“淮夷人”的原住民,我的十六世太祖公(以下简称太祖公)正带领一群民夫船工,沿着大海边狭窄的滩涂河道,一边“嘿哟嘿哟”地喊着号子,一边拉着沉重的运盐船。自远古时期起,地处中国东部的盐城沿海已经有人晒海煎盐了,至西汉,今盐城一带“煮海利兴,穿渠通运”,既是海滨的渔业集散地,又是淮东的盐产、盐政中心。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置盐渎县(渎:沟渠)。至元明两代,沿海的十三大盐场,因为一条串场河彼此连接,沿河两岸,白花花的盐廪高耸,蔚为壮观。
我的太祖公站在船头上。因为自小在白花花的盐池边长大,太祖公和那些与他年龄相仿的人一样,早已成了一个煎盐制盐的好把式。只不过此时,经过多年的辛苦奋斗,太祖公已经能够丢下淋卤煎盐的工具,成了专门在大海边押解运盐船的镖客。湍急的潮水中,趁着中午涨潮的高水位,我的太祖公和一群船工护送着一条条运盐船在海边狭窄的河道里缓慢前行。海边的滩涂地“十里不见坡”,平展展没有任何可资比对的参照物,因此,判断一条运盐船的运行路线和方向往往只能依靠平时日积月累的经验。大海正在涨潮,浑浊的海浪迎面扑来,凶猛而危险,在海边运盐,连船带人被巨浪卷走的事情经常发生,至于吃水很深的运盐船陷入淤浅的泥滩,最终使一船原盐沉没,化成一片海水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但只要有我的太祖公在,那一船船海盐和整个船队基本上都能成功地走出迷宫般的河槽,通过新辟出的盐运河顺利抵达邻近的伍佑场和新兴场,还会送到串场河的北起点庙湾场,交到那些来自安徽或者山西的大盐商手中。然后,他再领着一条条空船回到海边,等着几天以后的又一次航行。
那天上午,太祖公和船工们运盐归来,空空的木船穿过狭窄的河道,顺着寂静的水流缓缓漂向高墩上的那一座水码头。时令已过清明,一轮黄花大太阳晒得人浑身暖洋洋的,除了偶尔有几只鸟儿从头顶上飞过,偌大的世界毫无动静。躺在滩涂地上的太祖公有些百无聊赖,突然,平日寂静无声的大地有了响动。他抬起头远远望去,那座高高的土墩南侧,一株旗杆一般的小树站立起来。太祖公和伙计们翻身跳起,风一样地飞奔向那片黄土墩。就在那迅疾而短暂的跑动中,很快,他们看见了那株小树旁边又立起了一座泥墙草顶的丁头小舍(草庐),小屋的门前还围起了一圈刚刚扎好的芦苇篱笆。一群群鸟儿也飞过来了。燕子们在那座土坯草屋的檐下筑巢,两只喜鹊在渐渐长大的树枝上垒窝。一棵树,一座丁头舍的土坯小屋,一户人家,院子前面一圈低矮的芦苇篱笆。在1368年的这个乍暖还寒的春天,一株说着吴侬软语的小小的银杏树和它的主人,一副生动的场景,完成了一群人从未有过的想象。
而这场景的出现,发端于400 公里外的苏州阊门。
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统治近百年的元朝宣告结束。申猴一跃,大明开国,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年号洪武,长达276年的大明王朝开启。史书上说,朱元璋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四做了皇帝的。那一天,整个江南江北都在下雪,江河湖海、群山平原都被裹在厚厚的雪里。大雪酷寒,比这场大雪更为寒冷的是朱元璋突然颁布的一纸诏书。为了报复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一带拥戴张士诚的王府绅民,刚刚登基三个月的朱元璋以移民垦荒为由,将大批江南人丁经由苏州的阊门驱赶到江北。作为一段历史公案的“洪武赶散”自此开始。
“前后历经76年,40 余万人被逐出苏州城。”“洪武赶散”无疑是历史上苏北地区最早也是最大的一次移民运动。据《苏州府志》记载,第一批被赶散的人一部分迁往安徽北部,更多的则流落到了苏北沿江沿运河的扬州、淮安地区,后来则扩散到更大范围,其中主要包括更为偏僻贫穷的盐城、连云港赣榆直至鲁西南等地。在如今的盐城、宿迁、沭阳等地,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洪武赶散”的移民,都是从苏州的阊门来的。
在苏北的滩涂地上栽下那株银杏树苗、用芦苇搭成一座小屋的张太宗,正是遭遇“洪武赶散”流落到苏北沿海的苏州阊门移民。至于张太宗具体何时离开阊门,从哪条道一路去往苏北,最终如何落脚在了盐城海滨,落脚到了仅有一座破旧码头的蛮荒的滩涂地,无确凿证据可考。但确切的是,跟随着“洪武赶散”的人流,张太宗和他的族人从苏州阊门涉江北上,朝着这片偏僻的“淮夷之地”,一路乞讨着走来了。挑着担子,牵着耕牛,手持蟹钩,竹箩里插着两株刚刚刨起的银杏树苗,张太宗原本打算在泰州或者姜堰一带落脚,无奈被赶出来的人实在太多,没办法,为了活命,他只能跟着移民潮继续北上,最终来到了地处黄海边的这片穷乡僻壤。
一轮巨大的太阳在天空滚动,早晨在东边,傍晚在西边。一路风雨缠着一群人的裤管。那株从老家门前挖过来的银杏树苗被一条破麻袋捆扎得严严实实。一路的颠簸劳顿,一路的风尘仆仆,从姑苏城内带到江北带到盐城,树苗的叶子和枝条已经完全被风干,好在由于一把稻草的牢牢捆扎,那些泥土并未脱落。在盐城北洋岸(新洋港古称)东北的一片空地上,放下破旧的行李和锅碗瓢盆,张太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了一块邻水的高亢地,栽下了这棵银杏树。“洪武赶散”,数十万人颠沛流离。作为故乡的江南注定是回不去了的,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家园,去往一个新的地方,山水不再,乡音不再,无根的人们需要一个念想,因此,来自故乡故土的这株银杏树成了这些江南移民乡情乡思的最终寄托。一棵普通的银杏树成了“承受不了”的最后的乡愁。据《张氏宗谱·百忍堂》记载:最初来到苏北黄海岸边的这片白花花的滩涂地,张太宗是带了两棵银杏树苗来的,但由于地处盐碱地,土地碱分太重,两棵树苗最终只成活了一棵。也正因如此,这棵树苗成了张太宗一家最钟爱的宝贝。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孙一样,张太宗对这棵银杏树苗爱护有加。一年年悉心呵护,一代代托付相传。如今,历经650 余年时光,虽饱经风霜,那株银杏树依然站立在当初落脚的地方,站在汪洋大海的边缘,站在日月下风雨中。
一木独秀,一木成林。在黄海岸边这片成陆还不过三千余年的滩涂,这株已经活了650 余岁的银杏树称得上是一株充满奇幻色彩的“神树”,是一段古老历史的“活体”标本。它所讲述的,是一段悲壮、甚至凄美的传奇。银杏树是普通的落叶乔木,在南方的城市乡村,到处都可以见到,没有半点稀罕。巨大的树冠上长着形似鸭掌的叶子,故又名“鸭脚树”。又因为其果实形似小杏,核呈白色,被人们叫作“白果树”。欧阳修写有《和圣俞李侯家鸭脚子》,诗云:“绛囊因入贡,银杏贵中州。”而我似乎更喜欢梅尧臣的“鸭脚类绿李,其名因叶高”。我之所以更喜欢梅尧臣的这句诗,是因为我面对的这株已经有650多年历史的银杏树乃雄性植株,枝干虽无比高大,却有叶无果,而那叶子真的酷似一只只略显笨拙又憨态可掬的“鸭脚”。
2021年1月,一个冬日暖阳的下午,我正坐在家中的书房里。我的住所是处于市中心的一个花园小区,良木嘉荫,书房东边正对着一个小广场,一排巨大的银杏树的枝条一直送到窗前。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的一棵棵高大的银杏树,遥想千年沧海桑田,眼前忽然就出现了那一株生长在海边平原上的古老的银杏树——正是张太宗当年栽下的那株。神思飞驰,漫步于历史长河的堤岸,我看见张太宗正抚着一绺银须,坐在燃着牛粪火的灶门口,昏花的眼睛里奔腾着一片土黄的潮水。张太宗最初来到北洋岸,这里的海潮还没有完全退去,站在潭洋河边的那座水码头上,一脚就可以踏向远处的滔天巨浪。恶劣的生存环境一度让这群江南人想半途而废,打道回府或者另择他处谋生。但严苛的移民政策终究阻拦住了这群江南移民,纵然心中有再多的不甘,他们也只能委身于这片荒寂的盐碱地。张太宗劝他的那些江南老乡,本来就是来避难讨生活的,已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走到此地此境,干脆就一条道走到黑,落脚于此吧。天下之大,哪一片黄土不埋人,又有哪一条河水不养人?既然去哪里都是为了生存,那就安营扎寨,心无旁骛地住下来,靠一双大手活命,栽一棵大树乘凉,这片连兔子都不拉屎的盐碱滩,这片天地相接、宽广无边的土地,或许注定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张太宗和他的家人最终留下来了。
离开桃花盛开的江南,落脚于蛮荒贫瘠的海滨滩涂地,生存总是第一位的。环境极度恶劣,移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就是这里的气候。靠近大海,滩涂潮湿阴冷,冰雪的严冬自不用说,即使是到了春天,四月,这苏北大地似乎还一直躲在寒冷的冬季,江南的桃花早已经盛开,杨柳早已爆绿,可是在苏北,那种阴冷依然藏在骨头深处。
再一个问题是饮水。喝惯了故乡那清澈甘甜的山泉水,如今面对的竟是这又咸又涩的老海水,“一碗清水半碗沙”,一碗水刚喝到一半,下面就沉了半碗泥脚子,让人忍不住要一口吐出来。最初的半年,这些来自江南、来自苏州阊门的移民,不少人一直在拉肚子,几乎每个人的喉咙里都曾经喝出过泡来。
最艰辛的还是劳动。从前,在江南,这些移民世世代代都是靠种植水稻油菜为生的,来到这里,土地连青草都长不起来,开了一小块地,第二天就被白花花的盐碱覆盖。庄稼是种不成的,唯一能生存下去的方法就是向当地的盐夫灶民学习晒盐。于是,移民们拜本场人为师,从最简单的平田整地开始,一步一步,慢慢学会引水晒盐。用一把铁锹将咸涩的海水引进盐池,然后顶着烈日,一次次戽水、淋卤、曝晒。一年一年,一代一代。好几代人过去了,终于,脚下荒草不生的咸土地被逐步改良爽碱,慢慢地种植下枸杞、苜蓿、藜麦、高粱和向日葵等耐盐耐碱植物。从1368年至今,时间过去了650 余年。如果按20年一代计算,已经经历了三十几代人。三十多代人,仅仅是张太宗一系,一代代传承至今,也应该有大几千人。巨浪滔天的黄海拍打着咸土地,一户户来自南方的移民,他们布满伤口的双脚在裸露的海滩上一步步挪移,红色的血印留在了苦难的大地。凭借随身携带的一把铁锹一把蟹钩,这些移民在这块滩涂地上晒盐挖蛏,捕鱼摸虾,开荒耕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存繁衍。曾经杳无人迹的滩涂地最终成为他们的栖居之所,一片养育生命的家园。
大海一寸一寸退向远方。跟随着自己的主人,那棵从江南来的纤弱的银杏树,经年历代,终于在这片土地上顽强地扎下根来,并且越长越高大,越长越茂盛。春天,新生的叶子新嫩、鲜亮、透明,挂着细密的雨水;夏日,巨大的树冠笼盖着脚下宽阔的土地,整个土墩都堆积在一片茂盛的树荫里;秋天,金黄的银杏叶随风飘动,落在地上时带起的一阵阵绵软的声响,像极了那位来自江南、习惯微笑着说着一口吴方言的张太宗。
一株银杏树种在海边,立于乡野,在一片滩涂地上安身立命。最早的银杏树或许只是用来拴系捕捞船只的船桩,后来成了故乡和江南人的影子。子孙海站在面前,祖宗树立在身边。生活在大银杏树下的人,很多年后依然还会被称作“海里人”或者“东海人”。“东海”并非习惯上所称的东海,而是巨浪翻卷的滔滔黄海。“海里人”则大多是江南移民,这“海里人”似乎成了南方移民的代名词。移民们的性格颇似这一株银杏树,数百年来,昂首挺过无数次的自然灾害,一回回免遭兵燹之厄,霜雪压不倒,雨水淹不死,坚韧挺拔,堂堂正正,逆风而立,踏浪而歌,一路陪伴着这片土地的形成与生长,经历着沧海变成桑田。古银杏地处高土墩,每逢汛期发大水,附近其他地方都一片汪洋,唯有这棵银杏树一直高出水面。
一棵银杏,一座土墩。环绕在这棵大树下的子民,早已适应了这里平静简朴的生活。来自南方的人们,到了滩涂就是这里的柳树和芦苇,拼着命终于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张太宗用泥土垒砌的房子被命名为“阊门小筑”,那棵银杏树被称作“祖宗树”。张太宗对子孙提出要求,一代一代,无论何时,这幢宅子的名字不得更改,穷死饿死,那一棵银杏树不能采伐更不能变卖丢弃。在张家人的心里,那是张家人的祖宗,是一代代阊门移民的祖宗。
大地是树木的母亲,古老的大树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祖宗。今天,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这棵大树或许应该有一番特别的意义。这群从南方辗转来苏北的移民,是海滨大地上的另一种树木。傍依着这棵银杏树,附近有张码头和张各庄。一直到今天,张姓都是当地的望族。从海边平原走出来的人,只要说自己是大银杏树下来的,一准是张姓族人。作为一个温情的原点和坐标,在辽远的滩涂,来自远方的人们会凭着这片树荫寻找到同乡和亲人。清明磕头祭祖,过年杀猪宰羊,这片树荫成了更多人聚会与告别的驿站。日日生长的大树,春天时遮风挡雨,夏天里消暑遮阳,冬天里抵御那一阵阵的寒风与暴雪。秋夜,大树底下铺一张草席,面朝南方,仰望星空,那宁静的梦里,是桂花飘香的江南,是金橘满树的故乡。
黄海岸边的古银杏,卧着是一座城堡,举起来是一只手臂。因为一棵大树,天空有了支撑。
对于这棵老树,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内心都对它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这是当地渔民们走向大海的出发地,返回家园的导航台,是闪耀在茫茫大海边的神灯。当年,从这里的大码头出海,穿过黄沙港,一望无际的海面上,波浪与天空相接,四周没有任何参照物,大家一回头就能看见家的方向。出海归来,渔船满载渔获,远远地,看见海水托着的这棵银杏树越来越近,渐渐地看见那片高土墩,看见那座水边的码头,看见那岸边明亮的灯火;即便是将要在大雾中迷失,那些运盐船也会凭借这棵树确定自己的位置,找到回家的路。
老银杏下流传着“救命树”的传说。村里尚且健在的百岁老人张水海就是因为爬上了银杏树而免于一难的。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大水(海啸),十米高的狂浪从射阳河海口一路冲到了大码头,六岁的张水海就是爬上银杏树才保住了性命。银杏树,是他们脚下永远不会沉落的土地,是留住生命的“幸运山”与“生死岭”。
还有那个“消息树”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场震动苏北的盐阜区“九里墩——大码头伏击战”。1941年9月30日凌晨,日军一个中队从盐城经北洋小街一路追捕新四军枪械所“枪机连”,爬上大树顶上放哨的民兵发现后立即报警,得到消息的村民迅速钻进大码头外的芦苇荡。扑了空的鬼子兵气急败坏,倒上汽油试图焚烧这棵银杏树。此时,他们遭到隐蔽在海边芦荡里的新四军的伏击,一个中队的鬼子死了大半。可在那片高高的土墩上,那被烧焦的树身,第二年春天依旧爆出了嫩芽,生出了更加蓬勃的新叶,巍巍老树,葱茏一片。
一声声呼唤像一根潮湿的鞭子抽打着远去的海水。最后一个故事与我的家族有关。那年冬天,我远房的四姑太,那个叫作秀巧的姑娘,因为不愿意给盐霸孙大麻子做小(妾),趁着黑夜,拎着一条白绫来到了大银杏树下,但在大树底下坐了半天,秀巧姑娘还是没将自己挂上去。从小就知道这棵大银杏树下是全村人欢乐聚集的场所,因此,即使再悲伤,再走投无路,她也不能将那条白绫拴在那棵树上。
最终,美丽可怜的秀巧穿过开阔的滩涂地,一步步走向了远方那冰冷彻骨的大海……
一棵树就是一座山,一棵树就是一片海。这高山可能是喷薄的火山,这大海可能是无尽的深渊,但我面对的这棵大树,似乎一直是以一棵树的形象出现的。它站在明亮的太阳下,以葱郁的树荫笼盖大地,枝干挺拔,树根深入下扎;枝叶包容,为生活铺满绿荫。承载,寄托,给道路指出方向,给思念留下归宿,从不拒绝一切嘱咐,连风中的言语也变得生动。站立在海边大地,一棵古老的银杏树,它的巍然屹立,它的昂扬向上,这是平原的骨骼和大地的轮廓,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才会有的气度和力量。
忍受住贫瘠,经历过苦痛,辽阔的海滨平原,不断生长的滩涂大地,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明亮的梦!人活着,或许就是为了说出所有的梦幻与理想,说出自己爱这个世界的理由!
一棵树,一个已经六百五十多岁的老人,他注视着我,目光温暖,明亮,充满了爱。我认定他是我的祖先。
屹立在海边的古老的银杏树,我的祖宗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