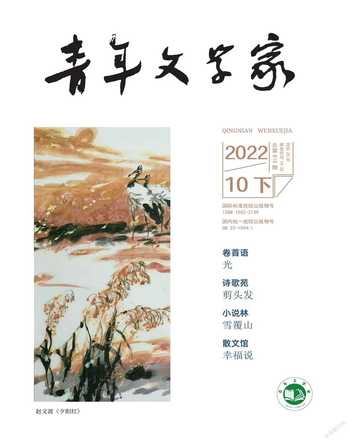重估刘熙载文艺美学思想之当代价值
肖蓉欣

一、刘熙载文艺美学思想形成原因
(一)时代背景
刘熙载生于晚清末期,一生经历五朝帝王。晚清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可能是刘熙载一生大部分时光都投入到教育事业的原因。刘熙载经世致用的思想,不仅是受儒家影响,同样也离不开晚清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他的这一思想也正好迎合了当时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救亡图存的社会潮流。在刘熙载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他一直在上海龙门书院担任主讲,培养了一大批为中国现代化效力的经世致用之才。刘熙载的众多学生,如祁兆熙、张焕纶、胡传、袁昶、范当世、葛士濬、姚文栋、李平书等近代知识分子,他们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含晚清的边防、教育、外交等多类事务。故要论刘熙载的个人成就,他远不止作为文艺美学思想家而已。
(二)思想渊源
对刘熙载思想形成造成影响的可以分为内外两个方面:
首先,是内部的传统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思想方面,儒、释、道思想在刘熙载身上均有体现,但就笔者看来,刘熙载的根本立场还是代表了正统美学,是对唐以来“文以载道”的观念的强化。不过,刘熙载在晚年说过:“余之少也,学不知道,虽从事于六经,然颇好周秦间诸子,又泛滥仙释书。”又说:“忆余自始学以来,知圣贤之道不易明,欲从他道参验之,至如阴阳道释之言,苟有明之者,竭诚以问,不惮再三焉。”从他的自述来看,他说自己虽然事于六经,但是也爱好众多,周秦诸子,阴阳道释均为他所重。可以看出,刘熙载的思想是以儒家为主,但也兼通释、道。《艺概》站在内外学术思潮激烈碰撞的时期,可以代表古典正统美学对文学进行的一次回望和总结。刘熙载对六经最为推崇,重视作者人品,重视作品的教化功能。但同时刘熙载又吸收了道、释两家的思想精华与思维方式,多种思想的碰撞使他有丰厚的思想基础,他的《艺概》能流传后世饱受称赞,脱离了儒、释、道哪一家恐怕都会减色不少。
其次,是外部的时代文化思潮。在时代文化思潮方面,“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人物志》中曾记载:“熙载治经,无汉、宋门户之见,其论格物,兼取郑义。”汉学盛行于东汉期间的古文经学,治学方式讲究“实事求是”,崇尚原始儒学、汉儒,同时又重训诂、考据;而宋学,指的是宋明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清人的宋学主要是指程朱理学,治学方式讲究使经学理学化、以理贯经。清代时,汉学盛行,清代儒士们推崇汉儒,对宋儒那种空洞注经的毛病不屑一顾,于是呼之为“宋学”,以此与“汉学”相区别。但到了晚清时期,因为此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这一时期哪怕是再封建的知识分子,不管原来他们是宗汉儒还是宗宋儒,在这种急需救亡图存的时代形势下,都开始尽力汲取对方之长,以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融会贯通思想和经世致用思想是这个时代文化思潮的主流,所以综合言之,晚清时期的儒学主流是一个汉宋调和的过程,是故云,“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徐世昌《清儒学案》)。这种兼取众家、融会贯通、经世致用的思想同样对刘熙载的影响巨大。
二、是粹然儒者,也是实践者
刘熙载说:“为学不专在读书伦常之地,日用行习之间,事事准情酌理而行,便是真实学问。”又说:“礼乐、兵刑、天文、地理、农田、水利,皆有专书,皆为有用之学。能专习一种,自有一長,泛泛涉猎,无当于学也。”
从这可以看出,在思想上刘熙载是重视各种专门的实用性的学问的,并不像传统意义上保守的儒生那般看不起实用技艺。刘熙载注重实用主义,不唯书,敢于突破程朱理学的藩篱,用辩证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在实践中发挥最大的作用,这是刘熙载在思想上传授给弟子们的宝贵财富。重视对学生专门技艺的培养,因材施教,真正开发出学生的兴趣,使他们在某一领域刻苦钻研,学有所成,这是刘熙载思想上经世致用,力图从人才教育上挽救国家之危机的重要体现。
此外,在行动上刘熙载也是以身作则。他熟悉六经典籍没错,但他对算术、地理知识、音乐、文字学、天文学等非传统儒家的学科也有研究。刘熙载能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予以指导,离不开他本人广泛的知识经验。胡传的儿子胡适曾经提到,说他父亲在上海龙门书院当学生时,养成了对中国地理的兴趣,尤其是对边疆地理的兴趣。正因为刘熙载本人也对地理有所了解,所以他在知道弟子胡传对地理有兴趣时才能及时给他具体的指导。胡传后来在地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刘熙载的细心栽培。
有的学者说:“刘熙载生在一个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文化学术急剧变革的时代,却采取了一种不介入、不趋时、不偏倚的态度。”笔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根据杨抱朴先生著的年谱记载,刘熙载在上海龙门书院担任主讲十四年,实乃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龙门书院在刘熙载的严格要求下,培养出了一大批讲究实干的杰出人才。在刘熙载的弟子中,袁希涛、沈恩孚、张焕纶等学生在中国近代教育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李平书、姚文栋、胡传对边疆舆地之学的研究作出了不少贡献,使得中国近代的边防外交、城市建设工作取得很大进步;另外还有文学家范当世、数学家刘彝程等人,均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其实,刘熙载顺应救亡图存、经世致用的时代潮流办学,为龙门书院培养出了一大批为中国近代实业发展效力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刘熙载选择的一种介入社会、改变社会的方式。刘熙载注重实学、强调躬行实践、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上海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在龙门书院这所特殊的学院内,存在着严密的契合。
通过对刘熙载任教龙门书院期间,于教书育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的考察,我们可以知道,他绝不仅仅是一位曾经被皇帝夸奖过的“粹然儒者”,也不仅仅是一位知识丰富、对各门类知识不存门户之见的教育家,他更是一位通变务实、思想先进、关心国家发展的伟大实践家,只不过他介入社会、改变社会都是通过教书育人这一途径达成的。
三、刘熙载文艺理论之创新:“镜喻”“灯喻”与“日喻”
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序言中说:“本书的书名把两个常见而相对的用来形容心灵的隐喻放到了一起: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发光体,认为心灵也是它所感知的事物的一部分。前者概括了从柏拉图到18世纪的主要思维特征,后者则代表了浪漫主义关于诗人心灵的主导观念。”
自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的“模仿说”就对西方文艺理论界产生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古罗马的普罗提诺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补充,认为艺术不仅可以模仿感性世界,还可以模仿理念世界。至此,西方的“模仿说”沿着两条路发展:一条是将文艺创作视作对外界环境真实反映的现实主义表达,一条是“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的浪漫主义表达。艾布拉姆斯分别用“镜”与“灯”对此作出了形象的概括。
刘熙载文论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没有拘泥于传统的“镜”与“灯”的比喻中,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日喻说”:“镜能照外而不能照内,能照有形而不能照无形,能照目前、现在,而不能照万里之外、亿载之后。乃知以镜喻圣人之用心,殊未之尽。”又说:“人之本心喻以镜,不如喻以日,日能长养万物,镜但能照而已。”
刘熙载在《艺概》中说:“文,心学也。”他十分重视作者情感对作品起到的根本性作用,认为作者的情感和意志会对文学艺术作品起到根本性影响。不过,刘熙载认为,以“镜”喻人心不如以“日”喻人心,因为“镜”只是外在地、平面地、客观地反映事物,而“日”则是内在地、立体地、能动地表现事物。“镜喻说”主要突出了是文艺的社会功用,而“灯喻说”“日喻说”则是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刘熙载觉得,以“灯”喻文艺作品之效用不如以“日”喻之,因为灯照一时,日照古今;灯照一隅,日照千里。灯只是照亮,日却能滋养万物;灯需要依靠外在能源,而且会有熄灭的时候,日却与宇宙同生,恒久发光。“日”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与被照之物一同为宇宙的组成部分。刘熙载的高明之处可见一斑。
四、是继承者,也是发扬者
有人评价刘熙载:“他這种人生与治学态度,决定了他在理论上恪守儒家传统教条,不可能有站在时代前列的、激动人心的创新独白。”笔者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相反觉得刘熙载在文艺美学理论上的建树被学术界大大低估了。刘熙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一次总结没错,但绝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全盘西化的未必就是好的,古典美学里也未必就找不出创新意识。之所以现在很多人有这样的偏见,是由于当代文学界缺乏对古典文艺理论的重视,未能深挖我国古典文论中精彩之处而导致的民族文化自信的缺失。因而我们立足于当下,对刘熙载文艺美学思想进行当代思考是很有必要的。
从刘熙载的《艺概》中,可以见他的文艺美学思想有以下特点:
一是刘熙载对古典文艺美学的总结,实则暗含了他的现代意识。首先,刘熙载说道:“文,心学也。”他认为文艺创作归根结底是靠创作者的心声,外在的其他条件只是次要因素。刘熙载对文艺是“心学”的强调,体现了在那个时代他对作者个性的肯定、对文艺作品表达自我的肯定。刘熙载充分鼓励作家表现在言论著作中的个人意识,正所谓“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其次,这种现代意识也表现为他对古典文艺美学的总结。刘熙载剖析各类文艺现象,以艺术辩证法论之。例如,刘熙载在自己的著述中就运用了阴与阳、丑与美、正与变、工与不工、是与异等两两相对的范畴。这些范畴,包含了文艺的形式、内容、风格等各个方面,不管是在内涵还是在外延上,它们既各自可以独立论证,又相互交叉关联,形成了一个既有逻辑规律,又有充满变化的纷繁复杂的网络。虽然这些相对的范畴有不少在前人的文论中已有论述,但刘熙载作为集大成者,其自觉性、全面性、系统性和深刻性方面,实在超过前人不少。
二是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是带着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刘熙载论述中国古典文艺美学,从思维方式到话语系统,都具有中国古代文论之独有特色:不是抽象论证,而是结合具体实例进行具体分析;表达形式上也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特有的那种语录体,多比喻,形象生动。比如,刘熙载对杜甫诗歌的评价是“高、大、深”,对苏轼诗歌的评价则是“打通后壁说话”。我国学者朱良志指出:“《艺概》是一部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美学著作,这个‘概可以说是中国美学精神之‘概,不仅在形式上反映了中国美学的特点,在精神气质上也体现了中国美学的内脉。”
就实际情况来看,刘熙载之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一直处在“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的状态,更像是“西方文艺美学在中国”而非真正的“中国文艺美学”。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由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缺乏自信,西方的各种文化观点、文化思潮都在中国留下足迹,这使得中国学界充斥了广泛但混杂的声音。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研究却被很大程度地忽视了。我们站在今天重新审视刘熙载的文艺美学思想之精彩处、创新处,重温他关于“艺者道之形”的文学作品论,“文之道,时为大”的作品与时代关系的文艺发展论,“论词莫先于品”的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接受论等文艺美学观点,对我们接续中国文艺美学传统,弘扬中国文艺美学精神,建构既兼具中国传统特点,又具有现代意义的文艺理论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