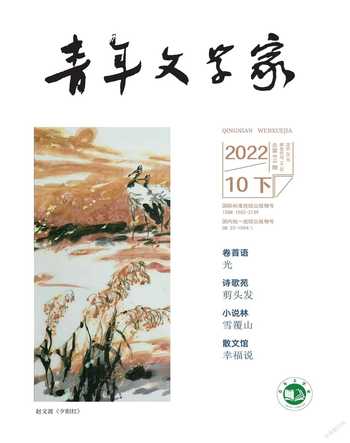浅析庄子思想与魏晋诗歌的关系
鲍晨
庄子和老子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的思想倾向于政治层面,在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其实阐述了如何更好地治理一个国家的主张,无为的背后是有为,而庄子的思想表现出更加彻底的无为,远离尘嚣。庄子的思想与老子有着很大的关联,但是他的思想不是针对浩瀚的天地宇宙而探究其来源与构成,而是开始注意现实的生活,关注世人的苦难,探究解脱苦难的方法。对宇宙本体的形成,老子有一套感悟的、直觉的而非逻辑实证的推演,庄子对此不感兴趣,以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庄子开始观望并体验自然天地的存在状态和表现形态,并且对其进行审美观照和评述。庄子的思想不仅迥异于当时的百家,还对以后的中国文学,尤其对魏晋时期诗人的影响,要远远深刻于其他诸子。
一、天地之美与山水诗
与儒家思想相比,庄子的哲学更加关注自然,关注天地和自然界的大美。在《知北游》中,庄子提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天地承载万物,四季不息运行。大自然以其纯真自然、博大无限的胸怀,向人们展示了它的曼妙和多彩。在自然的造物主面前,我们只有安心的敬畏与静静的观赏。庄子对天地自然的态度还不是将天地作为独立的审美观照来看待,而只是将天地作为道的体认和道的诠释。天地自然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审美对象出现,是在魏晋的山水诗歌兴起之后,但是,魏晋时期的诗人们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追本溯源,就会发现,庄子有着开启风气之功劳。
庄子亲和自然的美学理想在魏晋时期有了勃发,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审美观照产生了深刻影响。永嘉之乱以后,晋室南渡,虽然当时中原仍然战祸不断,偏安东南一隅,不得不说是一种可悲的窘境,然而毕竟东南一带是比较安乐的所在,比起北方的战乱,这里的境况要好得多。因此,诸多的士大夫并不追求如何建功立业,而是走向自然山水,把自己置身于自然山水之中,远离尘世,在人与宇宙自然的和谐融合中成就其艺术的人生。这种在宇宙自然中体察人生的全新视角,促进了自然美的觉醒。这种对自然之美的体认发展到魏晋,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和展开,表现在文學上,就是山水诗的产生。
山水诗歌的产生是与玄言诗的兴起分不开的。东晋的玄言诗是为了体道,是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一种诗歌形式。正是玄言诗中理趣的存在,为山水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玄言诗借助山水风景说明理趣,借山水抒情,到了东晋之后,山水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而存在,因此出现了不少描写山水的佳句,并且出现了山水诗歌的集大成者谢灵运。谢灵运是六朝时代一位有着多方面才能和素养的悲剧性诗人。谢灵运的诗歌开始关注自然造化之美,喜欢描写山水名胜,善于刻画自然景物,并力图用语言来描绘所见的大美。因此,在谢灵运的笔下,自然天地之美怀于胸中,发自笔下,奔泻而出。他用细致的观察和生动的文笔细致刻画了山水自然的绚丽多姿,创作了一大批吟咏山水美景的诗歌,并由此开创了将山水风景纳入文学审美对象的诗歌创作角度,奠定了中国山水诗发展的雏形。自此以后,山水诗成为一个诗歌的流派,并在唐代发展为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
谢灵运在创作的时候,采用移步换景的手法,将所看到的风景用文字进行精细的描绘,几乎是让文字发挥画笔的作用,如《过始宁墅》中的“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连”,《登池上楼》中的“池塘生春草,柳园变鸣禽”,《初去郡》中的“野旷河岸净,天高秋月明”。“由于诗人在政治上不得意,转而从山水中寻求精神寄托,在湖光水色中他曾经领悟到了淡泊寡欲,以及山水自适的道家哲理。”(孙明君《庄子与古代山水诗》)
而到了谢朓,他则把山水诗由客观的外在的描写,进一步发展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层次,不再追求“外无遗物”的表现形式,而首先以感情切入景物。这对以后的中国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魏晋的山水诗保留了庄子思想的灵魂。山水诗的渊源,既有着庄子对道的体悟,又有对天地之美的关怀。庄子思想中的自然精神是魏晋山水诗的全部精神和灵魂内涵。魏晋的山水诗,就是庄子思想的外化形式。庄子打破了儒家学派对人生的责任和义务的强调,而着重强调自由的、艺术化的人生。这种主张在魏晋南北朝时候被玄学家们进一步发掘,并最终促成了山水诗的产生。
二、隐逸思想与田园诗
隐逸文学一向是中国文学的重头戏。隐逸的思想在《庄子》一书中有着深广的体现,如《庄子·外篇·刻意》曰:“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这里就提到了避世隐居的江湖之士。再如《庄子·外篇·秋水》,“(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而庄子最后却拒绝了楚王的请求,因为庄子“宁生而曳尾涂中”。再比如《庄子·杂篇·让王》,“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庄子》中所表现的隐逸思想或是贤者避世,或是对抗社会。这种隐士思想本是庄子在战国那样一个连性命都难以保全的时代提出的一种消极的应对策略。然而,这种思想却在魏晋时代放出异彩,赢得了这个时代人们的心灵需求和渴望。
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评价徐干时说道:“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瑀崇尚隐逸的追求则更为突出。曹操为了自己的经国大业,四处搜寻人才,他听说阮瑀有才华,就想找阮瑀出来做官。阮瑀不应,最后竟到逃进深山的地步。阮瑀的归隐是对当时政治的一种逃避,可能也有他自己的个人志向在其中。
正始时期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学更加带有明显的隐逸倾向。阮籍便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受庄子的影响十分明显。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像许由、巢夫那样隐居起来。《咏怀诗》其三十二中的“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和《咏怀诗》其七十四中的“巢由抗高节,从此适河滨”让我们看到了阮籍功名利禄背后潜藏的危险,因此他有着保全自身的个人追求。
魏晋时期的陶渊明,这位被《诗品》尊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大诗人,在他辞官回乡之后,创作了很多描述田园生活的诗歌。这些诗文语言质朴,辞藻清雅,却能够体现陶渊明完全看透自己的人生追求之后的超脱心态。他所写的诗歌,不是为了传世或者被人欣赏夸奖,而只是抒写一己之怀。陶渊明的诗歌,以他躬耕自织的隐居生活为创作基础,以他自己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思想为创作的精神根基。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受老子、庄子的影响非常明显。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说:“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庄子认为:在现实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人为物役;在人自身,形与心(神)的关系是心为形役。人要摆脱这两者,才可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陶渊明对自己过去的这种认识,显然是受了庄子思想的影响。”(宗明华《庄子与魏晋文学中的隐逸思想》)这是陶渊明在切实看到自己的性情与官场格格不入之后的感悟体验,深切喊出了自己对简朴的田园生活的向往,说明自己在有限的生命历程内,不该让自己“心为形役”,应该追求自己的快乐。为了追求自己身体和精神上的自由,他甘愿抛弃世俗人所热衷的功名富贵。他所发出的“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的感慨,完全可以从庄子的文中找到精神渊源。《庄子·杂篇·盗跖》中说:“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庄子以为人的寿命是短暂的,与其被外物所累,不如顺从内心,与天地万物逍遥。所以,陶渊明又写到“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富贵不是陶渊明想追求的,成仙得道这些虚幻之事也徒耗心力。他只是希望自己可以和自然相融合,乐天知命,安命顺处。这种精神追求和庄子的精神自由有着某些共通之处。庄子只是把这种自由放在虚幻的头脑与驰骋的想象中,通过一种激情飘荡的想象来暂时的超脱现实,暂时摆脱现实的不快。而陶淵明却在现实生活层面践行着这种理想的境界,试图让自己的生活充满诗化的艺术色彩。最终,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完美实现了这种融合,他所写的田园诗,成为后人不可超越的经典范本。这些诗歌平淡自然,冲合超脱,带来了全新的艺术境界。他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入诗,“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这些诗句表现出他从容自得的心情和安贫乐道的情怀,真正实现了庄子笔下的“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的理想生活。这种艺术化了的人生,也解释了庄子笔下的“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的道理。
三、逍遥无待与游仙诗
追求绝对的逍遥无待的自由是庄子笔下透露出的理想。庄子笔下的“至人”“神人”超越了普通层面的存在,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逍遥游》云:“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外篇·田子方》说:“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这些人从现实生活的羁绊和困扰中解脱出来,实现了真正的身心自由,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大解放。他所说的“至人无己”,是去掉外在的形骸躯壳之类,让自己的精神与万物接通。“神人”“质人”是一种无所羁绊、逍遥无待的存在,不惧水火,不怕酷暑严寒,“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这些“神人”“至人”,他们是一种绝对的精神逍遥。
虽然实现像“神人”的逍遥,庄子没有给出具体的途径和应该有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观念本身已经是一种令人向往的存在,这种描写和幻想可以将人们带入到一种暂时摆脱现实困扰的理想世界。因此,它首先成为一种不被抛弃的美好幻景。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和灾祸的蔓延,它逐渐变成了一种信仰,并最终为游仙诗的出现提供了基础,“神人”“至人”的存在对魏晋士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自东汉末的战乱以来,“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忧艰常早至,欢会常苦晚”的感叹不绝于耳。为了摆脱现实生活对生命的威胁,为了给不自在的生命找一个宣泄的出口,人们不得不通过想象彼岸世界的美好来寻找精神安慰。这样,自秦汉以来就有寻求海外灵药、寻求长生、寻求升仙的思想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并逐步把神仙世界作为一个超尘脱俗的精神栖息地。例如,郭璞的《游仙诗》其二:“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翘迹企颖阳,临河思洗耳。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诗人在诗中表达了一种否定仕途的心态,对隐居的道士大加赞美。隐逸所处之地,在青溪山上,环境清幽,安静自在,隐者凝神闭目,天地与我合一,物我两忘,表现出纯粹的精神自由。诗人在歌颂隐士的同时,读者不难体会到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的苦闷。诗歌所表现的已经不是纯粹的迷信神仙和依赖神仙,而是依照庄子设计的精神世界,创造了一个精神乌托邦。
庄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十分深远,《庄子》一书中奇幻迷离的情节和驰骋的想象,进一步推衍为一种艺术境界,激发文人在创作中的主观想象力,使魏晋文学蒙上了带有理性的浪漫色彩,促进了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也直接影响到了文学理论的形成。庄子摒弃人间功名富贵,排斥功利,尊重个性的思想倾向,也对后人的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提供了思想支撑。《庄子》不仅促进了魏晋文艺的繁荣,还丰富了中国古代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