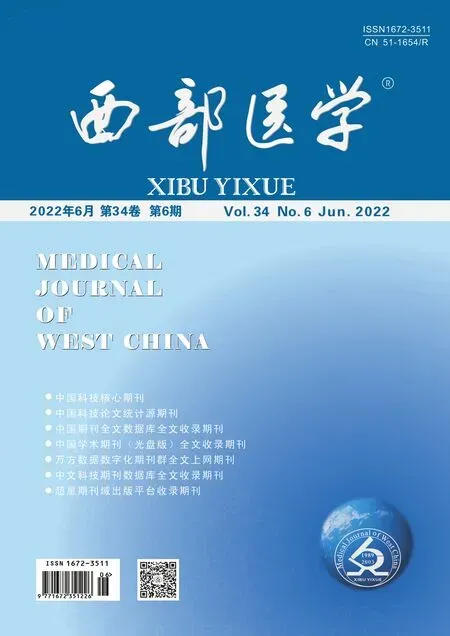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中的研究进展*
曹青 综述 岑瑛 陈俊杰 审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美容整形烧伤科,四川 成都 610041)
皮肤癌是白种人中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占所有诊断癌症的4%~5%,并且有上升趋势[1]。皮肤癌大致分为两类:非黑色素瘤皮肤癌(Non melanoma skin Cancer,NMSC)和黑色素瘤。最常见的NMSC是基底细胞癌(Basal cell carcinoma,BCC) 、鳞状细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SCC)和光化性角化病(Actinic Keratosis,AK)[2],其中BCC和SCC分别占NMSC的70%和25%[3],在早期诊断并积极治疗情况下NMSC的预后良好,通常来说BCC恶性程度较低,局部侵袭、组织破坏和复发的能力有限;CSCC更容易发生转移,转移率为0.1%~9.9%,占 NMSC 死亡人数的 75%[4]。目前随着肿瘤微环境研究深入,“种子”与“土壤”学说为人们认识肿瘤发生发展提供新的视角,因此研究肿瘤微环境中重要组成部分之肿瘤相关巨噬细胞以及巨噬细胞在肿瘤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1 巨噬细胞的起源、分化及招募
巨噬细胞(Macrophages)源于单核细胞,是一种位于组织内的白血球[5]。属于单核吞噬系统(Mononuclear Phagocytic system,MPS)的一部分,是一组发挥作用的终末分化细胞,巨噬细胞在维持组织稳态,抵抗炎症和抗感染中起关键作用。在经典的巨噬细胞发育模型中,骨髓内的造血干细胞产生髓系祖细胞,通过循序渐进的分化最终成为循环的单核细胞。单核细胞有两种亚型,炎症单核细胞介导血管外炎症反应,巡逻单核细胞负责清除血管内受损细胞和碎片。单核细胞经内皮外渗进入组织后,可分化为巨噬细胞[6]。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umour-associated macrophages,TAMs)则是指在肿瘤微环境中,经由肿瘤细胞相关因子的刺激促使单核细胞形成与肿瘤发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的巨噬细胞,它在肿瘤微环境中具有相对较为复杂的功能,可以借助分泌相关因子抑制免疫应答;还能够依靠淋巴管和肿瘤血管生成方式的不同去影响肿瘤的侵袭、增殖、转移和转归等能力。正因如此,临床对其在肿瘤免疫中的作用得到临床越来越多的重视[7-8]。经相关临床实验证实,TAMs在肿瘤发生和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促癌作用也逐渐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9]。巨噬细胞极易被肿瘤细胞招募至此种炎症系统中演变成TAMs,并参与肿瘤发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可将其视为肿瘤微环境的特殊组成部分,同时凭借其特定的调节方式参与细胞的侵袭、增殖和转移[10-11]。TAMs能在不同的肿瘤微环境条件下极化为两种功能不同的亚型[12],例如在IFN-γ、微生物产物(如脂多糖)或GM-CSF激活条件下分化为M1巨噬细胞,M1巨噬细胞能抑制肿瘤[13],同时能分泌高水平的促炎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12 (IL-12),IL-1,IL-23,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和基质细胞来源因子1α (SDF1α)[14 ]。相反,在IL-4、IL-13、IL-10和M-CSF/CSF-1激活条件下分化为M2巨噬细胞,M2巨噬细胞产生IL-1β、IL10、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转化生长因子β (TGF-β)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肿瘤微环境中,M2型TAM具有促进肿瘤血管及周围淋巴管形成生成,促进机体组织重建和损伤修复,以及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等功能[15]。因此TAMs倾向认为是M2样表型,相关研究表明,TAMs是由多个具有重叠特征的不同极化状态巨噬细胞群体组成[16-17],并且两者在不同的刺激条件下彼此的表型和功能又可以相互转化[18]。因此,为了进一步区分巨噬细胞的不同极化状态,也有人将M2巨噬细胞分为M2a(由IL-4或IL-13诱导)、M2b(由免疫复合物结合IL-1b或LPS诱导)、M2c(由IL-10、TGFb或糖皮质激素诱导)和M2d(传统的M2巨噬细胞,发挥免疫抑制作用)[19-20]。
2 巨噬细胞在肿瘤中的作用机制
2.1 M1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抑制肿瘤机制 一般认为,M1型巨噬细胞具有促炎抗肿瘤作用,M1型巨噬细胞能够识别肿瘤细胞并通过免疫机制杀死肿瘤细胞,研究发现M1型巨噬细胞是通过以下两种机制来杀伤肿瘤细胞:M1型巨噬细胞直接介导细胞毒性杀死肿瘤细胞,相关研究表明,巨噬细胞释放活性氧(ROS)和NO等杀伤肿瘤分子,对肿瘤细胞具有细胞毒性作用[21]。另一种机制是抗体依赖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杀死肿瘤细胞[22]。
2.2 M2巨噬细胞促进血管生成 经研究发现[23],血管的生成是实体瘤生长的基础,不仅存在于肿瘤生长的每个时期,还可以通过新生的血管达到远处转移的目的。血管生成是癌症和癌症间质细胞作为转移性疾病的先决条件[24]。它需要基底膜的降解以及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TAMs广泛参与血管生成过程的每个步骤:通过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和组织蛋白酶的产生来降解基底膜[25];促血管生成生长因子如VEGF、PDGF、碱性FGF (bFGF)和趋化因子CCL2和CXCL8的分泌,这些因子不仅提供维持癌细胞生长所需的血管网络,而且促进肿瘤的传播[26]。此外,基质金属蛋白酶降解肿瘤细胞周围的组织基质,释放肝素结合生长因子,如VEGF-A,以进一步支持血管生成。最后,VEGFA和CCL2也作为单核细胞募集的强趋化因子,它们的表达与人浸润性导管乳腺癌中TAMs的增加和肿瘤血管化水平高呈正相关[27]。因此,TAMs是癌细胞扩增血管生成的一种间接机制,与肿瘤来源的血管生成因子共同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形成。
2.3 TAMs促进肿瘤转移 肿瘤的转移主要是指肿瘤细胞由原发部位逃逸后,经过淋巴管道、体腔或血液循环等方式在其他部位继续生长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由原发部位脱落—脉管内的入侵或外渗—转移区域的适应性生长[28]。经研究证实[29],在上述的每个阶段TAMs均参与其中。目前相关研究表明,肿瘤转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肿瘤组织内皮细胞基底膜的降解和损伤。临床上肿瘤转移也是肿瘤治疗预后不良的重要表现。有报道称活化的TAMs通过产生可溶性因子直接促进肿瘤转移[30]。M2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肿瘤微环境中能有效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组织蛋白酶、丝氨酸蛋白酶酶类因子,它们能破坏内皮细胞的基质膜并且分解细胞外基质中的各种胶原蛋白等成分,从而帮助肿瘤细胞和肿瘤间质细胞迁徙转移[31-32]。上皮-间充质转化(EMT)也是肿瘤转移侵袭的基础[33]。这一转化过程赋予了肿瘤细胞的干细胞特性,并使肿瘤获得了迁移侵袭的能力[34]。此外,肿瘤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也能有效影响TAMs的分化状态,从而在EMT与TAMs之间形成正反馈回路[35]。何楠等[36]研究发现,TAMs对胃癌患患者肿瘤细胞的侵袭和转移,可直接通过激活TGF-β/BMPs、TNF-α/Wnt、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和IL-6/STAT3/IRF4等多条信号通路来完成。
2.4 M2巨噬细胞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 肿瘤细胞增殖与TAMs浸润密切相关。肿瘤微环境中的蛋白酶主要来源于TAMs的产生,其破坏细胞外基质促进肿瘤侵袭。随着TAMs衍生表皮生长因子(EGF)的激活,乳腺癌中癌细胞侵袭形成和基质降解增加[37]。研究表明,TAMs可以表达多种刺激肿瘤细胞增殖和有利于肿瘤细胞存活的细胞因子,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包括上皮生长因子(EGF)、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PDGF)、TGF-b1和因子受体家族上皮生长配体(EGFR)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38]。总之,TAMs是肿瘤组织中EGF分泌的重要细胞来源[39]。研究还表明,TAMs与肌成纤维细胞之间构成CCL5和CCL18的正反馈回路,驱动叶状肿瘤(PT)的恶性侵袭。CCL5与CCR5结合,激活AKT信号来招募和重新极化TAMs。TAMs释放CCL18,通过将间充质成纤维细胞分化为肌成纤维细胞,进一步诱导恶性PTs侵袭,导致PTs恶性[40]。
2.5 TAMs的免疫调节 TAMs可调节T细胞和NK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M1巨噬细胞增加了纤维化肝中总NK细胞和活化NK细胞的数量,释放凋亡诱导配体(TRAIL),诱导HSC凋亡[41]。此外TAMs还可以通过精氨酸酶1、iNOS、氧自由基或氮类代谢l -精氨酸来直接抑制CD8+ T细胞增殖[42-44]。此外,TAMs通过CCL22招募Treg,进一步抑制T细胞的抗肿瘤免疫反应[45]。条件性TAMs消融术通过降低异种移植小鼠的CCL20水平,阻断Treg细胞募集并抑制肿瘤生长[46]。肿瘤部位的炎症反应可以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进展,炎症和免疫逃避被认为是癌症的特征。据报道,TAMs还可促进癌症相关炎症,通过炎症性Th亚群(如TFH)的产生导致肿瘤发生[47]。
3 巨噬细胞在皮肤鳞状细胞癌中的相关研究
在肿瘤发生发展中,TAMs释放多种有利于癌变的因子,如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C、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特别是MMP9、MMP10和MMP11。肿瘤炎性浸润中大量巨噬细胞促进促炎细胞的表达,促炎细胞释放刺激肿瘤生长和血管生成的细胞因子[48-49]。相关研究表明,M2型TAMs密集浸润到淋巴结转移,提示巨噬细胞可能通过吸引肿瘤细胞参与SCC转移[50-51]。最近研究表明,TAMs的炎症浸润可能与更晚期的头颈部鳞状细胞癌(HNSCC)相关,并且是淋巴结是否发生转移的一个有效判断因子[52]。SCC中一般都可以检测到TAM高表达的精氨酸酶1,在肿瘤微环境中,精氨酸酶1可使L-精氨酸分解为L-鸟氨酸和尿素,从而导致肿瘤微环境中的L-精氨酸缺乏,并且通过降低T细胞抗原受体介导的CD3-z&链的表达,从而抑制T细胞活性[53-54]。在头颈鳞状细胞癌中,TAMs衍生的EGF上调癌细胞CCL2的表达,进而招募更多炎症单核细胞,诱导它们成为M2样巨噬细胞,从而在头颈鳞状细胞癌中形成正反馈旁分泌环[55]。HNSCC可通过TGF-β1/TβRII/Smad3信号通路诱导TAMs产生VEGF,从而形成癌细胞与TAMs之间的正反馈循环[56]。巨噬细胞的消融抑制了头颈部鳞状细胞癌肿瘤细胞的侵袭、血管生成和转移[57-58]。口腔鳞状细胞癌(OSCC)与TAMs研究中,Hu等人使用了CD68(一种泛巨噬细胞标记物)和CD163(一种m2型巨噬细胞标记物)标记物进行实验检测,结果提示TAMs丰富的浸润与(OSCC)不良预后相关[59]。在冯稳等[60]的研究也发现,TAMs在食管癌患者临床病理过程中,其浸润数量与临床分期、浸润深度以及淋巴转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夏易曼娜等[61]研究发现,TAMs与上皮性卵巢癌的发展、疗效以及预后情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吴奇勇等[62]研究中,采用免疫组化方法分析肺癌组织中巨噬细胞浸润情况,分别采用CCK-8法和Transwell法检测单核巨噬细胞系THP-1对肺癌细胞系A549细胞影响时发现TAMs在肺癌组织中的浸润数多于癌旁组织,可通过激活诱导的TAMs细胞促进A549细胞的增殖和侵袭,故而可用TAMs浸润深度预测患者的预后情况。
4 巨噬细胞在皮肤基底细胞癌中的相关研究
在动物模型中,Konig等[63]用clodrolip(一种吞噬细胞抑制剂)治疗BCC小鼠,并报道皮肤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数量的减少促进肿瘤生长。成纤维细胞密度也较低,这可以通过巨噬细胞数量减少来解释,巨噬细胞在成纤维细胞增殖中起作用。Tjiu等[64]在BCC相关实验中报道了TAMs的数量与肿瘤厚度、血管生成和COX-2表达呈正相关,BCC细胞与M2 TAMs共培养导致BCC细胞中COX-2表达增加,导致肿瘤进展和侵袭。然而,Kaiser等[65]的研究表明,TAMs的数量及其特异性亚型与BCC的浸润行为无关。Padoveze等[66]分析了术后复发性基底细胞癌和非复发性基底细胞癌的TAMs值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无相关性。
5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靶向治疗
5.1 抑制TAMs向肿瘤组织的招募 TAM 可以产生趋化因子,将免疫抑制细胞直接募集到肿瘤微环境中。 其中,CC趋化因子2(CCL2)是一种促进单核细胞募集到肿瘤组织中的细胞因子。 它存在于 CCL2 阳性黑色素瘤中,分子抑制剂 Bindarit 可以显着抑制巨噬细胞募集和肿瘤生长[67]。Young 等[68]报道 TAM 分泌的 IL-1β 刺激成纤维细胞产生 CXC 趋化因子受体 (CXCR2) 配体,该配体将骨髓来源的抑制细胞募集到肿瘤部位并起关键作用。
5.2 阻断M2型TAMs极化及M2型向M1型TAMs再极化 研究表明,体内外的许多因素能有效诱导或者抑制巨噬细胞向M1型或M2型方向极化。通过利用相关的条件定向地诱导巨噬细胞的极化,可以为肿瘤等疾病的治疗和预防提供新的思路。在一定浓度的IL-23处理后,模型的各种指标均显示M2型巨噬细胞向M1型巨噬细胞极化,此干预措施能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浸润和转移[69]。猪苓多糖属于多糖类物质,能够使M2型巨噬细胞逆转为M1型巨噬细胞,提高巨噬细胞的肿瘤免疫功能,主要是因为猪苓多糖能够提高CD206、CD16/32的阳性表达率和相关炎性分子的表达[70]。
6 小结与展望
本文主要对TAMs在皮肤鳞状细胞癌及基底细胞癌中的作用机制以及靶向治疗进行相关综述。以更好认识巨噬细胞在皮肤鳞状细胞癌及基底细胞癌中的发生发展规律,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理论依据。然而目前对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研究不够深入,相关促进血管形成及肿瘤转移机制不完全明确,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能够更深刻认识皮肤鳞状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与巨噬细胞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指导临床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