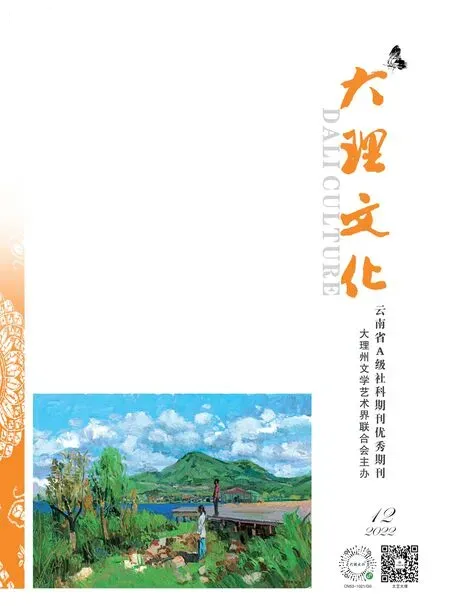书事
●疏雨
雨天纸墨明润,尤其使人心安。若手中有一本心仪的纸质书,纸页绵密,指尖触处便有了一种自然的、隐匿的情愫在悄然洇漫。
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大理师范读书,当时对阅览室的眷恋,因为书,也因为人。
学校的阅览室设在电教馆内,从我们住的女生院到电教馆可以穿过常青园,抄近道。阅览室每天晚饭后开放一小时,许多同学都会提前去等着开门。我通常会带着笔记本和速写本,提前半小时离开宿舍,在去完成阅览室读书的这个主旋律之前,给自己先来上一个小乐段——完成一幅速写。这个乐段通常是在常青园悄然进行。
常青园的南面是一幢黄墙青瓦的老苏式楼房,当时美术班的画室就设在里面,它斑驳的墙身便是常青园南面的围墙。园子东、西、北三面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常见的半人高的砖墙和上半部分的钢筋围栏,三面各留了一道月亮门。围栏上面爬满了爬山虎,大片大片的青绿,阳光明媚的时候,光影绰绰,层次丰富。常青园因常青而得名,除了葳蕤浩荡的爬山虎,不大的园内还有七八棵梨树。每到春来,梨花便铺天盖地地开着,有时会看到有人在树下吹笛子,花瓣簌簌落下,我怀疑是被那袅袅的笛声颤落的。那笛声不但颤落了梨花,还颤动了我同窗好友的芳心,她的校园恋情几经波折,在毕业三年后终于修成了正果,这是后话。北门边有一个花架,是用来支撑一棵古老的紫藤,它藤茎遒劲,如书法中笔走龙蛇的行草。梨花开的时候,紫藤也一串串竞相开了,每天路过这里,我都会围着余晖中的藤蔓、花叶,选一个角度,在阅览室开门前五分钟完成一幅速写,一边沙沙地画,一边听花瓣偶尔落下的声音。这个园子,这个时节,可入画的还有小路旁花坛中的杜鹃,白杜鹃白而清透,纤尘不染;粉杜鹃如云似霞,温柔烂漫,洇染着画纸,也洇染着花季女孩的心事。杜鹃花旁有一棵四季常青的老柏树,像一位智者驻立在那儿,风吹则清扬,风平则静安。
有时这个乐段也会在电教馆进行。阅览室对面有一棵法桐,主干需两人合抱,枝叶繁茂,特别是秋天,掌状的叶片在风中俯仰,翻飞出深深浅浅的青绿橙黄,映着湛蓝的天,煞是迷人。阅览室外等待的人们会先拿出自己手中的书看着,我会走走停停,选取最佳的角度,给法桐来一个速写,或画全貌,或画一枝。后来,我翻开速写本,发现除紫藤、杜鹃、柳树、石桌石椅外,画得最多的还是那棵法桐。每年十月底,法桐开始陆陆续续落叶,我便每天捡一片夹在笔记本中,这些叶子一片片由青黄、明黄到橘黄、枯黄过渡着,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黄色系色卡。每片叶子上我都写上日期,偶尔也写上一句“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所有的开放都浸透着忧伤,芬芳和美丽从来都脆弱易碎”“惜春春去,几点催花雨”等诸如此类伤春悲秋、“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句子。速写本、笔记本在我手中随机切换,当时的我始终确信,对于眼前那些方寸的美好,我能用画笔将它描绘出来,画不出来的亦可以用文字表述出来,到了光阴知味的年纪,愈发怀念少年时那青涩莽撞、不谙世事的自信和勇气。
待到阅览室开门,便随众人蜂拥进去,选好自己要读的书,把学生证交给管理员摆在那本书的位置上,便可以接过书找个空位坐下来。读自己的书可以在上面写写画画,读借阅的书就不能这样任性了,见到心仪的句子连忙抄到笔记本上,待回去以后细读细品,感觉唇齿留香,兴之所至,还会在旁边即兴地写写画画。让人倍感纠结的是,正抄到酣畅淋漓处,“叮——”阅览室关门的铃声响起,如刚刚到口的佳肴,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收拾好笔记,换回学生证出了阅览室,一路牵肠挂肚,当晚,连睡觉都不踏实。第二天必定早早去等着,一开门直奔那本书,急切又小心地翻到昨天那页,如获失而复得的宝贝,畅快地抄起来。如果有事耽搁了,迟到一步,书被别人先借去,就会觉得一个晚上都没着没落的,特别沮丧。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读《名作欣赏》,有中外名作赏析,还有书法和绘画作品的品鉴,我会反过来去找文中提到的书或文章来读,这种以书找书的方式,短时间内扩大了我的阅读量,我很享受这样亦读亦赏、亦赏亦读的状态。阅览室的管理员是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眉眼娟秀、有着书卷气的小姐姐。有几次我在书架上找不到《名作欣赏》的时候,发现她手中正是这本书,原来她也喜欢读这个。她抬起头来,看到我,会顺手把书递给我,我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便说:“我找别的书看看。”她笑笑说:“没事,等你们上课去了,我再读。”到后来,只要看到我进门,她都会事先把书拿下来放好在桌子上。这样的默契,让我感到一种秘而不宣的温暖。
除了《名作欣赏》,《美术》月刊也让我很着迷。里面会有画坛的动态,一些绘画作品的欣赏、技法,还有画家的故事。有一位高我们一届的师兄,他是美术专业班的翘楚。他们班经常以常青园东面的外墙做“展厅”,在饭点的时候展出他们的作品:素描、水彩、水粉、油画、静物、人物、风景。打饭路过的师生们各自端着碗一边吃,一边看,站的站,蹲的蹲,有的还用舀饭的勺子或是穿着馒头的筷子“指点江山”,而这位师兄的作品总是会被一眼认出,辨识度很高。我看过他们班在常青园写生,模特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脸部和五官的轮廓硬朗有型。其他学生画完模特后都是以实景为背景,或是一面爬山虎,或是一段斑驳的老墙,或是那棵紫藤,都因自己写生的角度而定。唯有他的背景是东升的旭日和山崖上一块沐着橘色晨光的磐石。就是屡屡画出这样“惊世”之作的师兄,他来阅览室也是直奔《美术》月刊来的,可每本杂志只有一本,彼时他刚毕业留校,在他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和闺蜜也和他们打饭菜拼餐过,所以我还是会有“他是学长”的思维定势,并不拿他当老师来畏着,心里还偷偷地想:我要早去阅览室拿下那本书,他是老师,老师是可以借回去看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穿过常青园,奔向电教馆时我便一路小跑。一边跑,一边透过北边围栏上枝蔓间的空隙看向主干道,看看他那辆斑马自行车有没有倏忽闪过。听说,他的自行车变“斑马”是有来由的。那一段时间,偷自行车的特别猖獗,他也不可避免地丢了好几辆,后来他索性弄来点白油漆一条一条画上道道,俨然是一匹精瘦有型的斑马,从此,江湖任我行,再没丢过。好几次从围栏绿植的缝隙间看到那斑纹穿花度柳一闪而过,心里一激灵,不好,又迟一步,果然,到了阅览室门口,那漂亮、不羁的小斑马,已然在一众黑色普通的自行车中清新脱俗地小憩着了。就是在跑不过“斑马”的时候,我又开拓了新的“领域”,读起《散文》月刊来。在其中一期的借阅卡上,我发现了我们舞蹈老师的名字,记忆中的她很美,白皙、知性、优雅,从未大声说过一句话。
当然,关于《美术》月刊的借阅,我也享受过一次“教师待遇”,也是仅有的一次。不记得是哪一期了,里面有许世虎先生的水彩作品欣赏,其中有一幅画的是窗边书桌上的玻璃花瓶里插着一束菊花,橘黄的、暗红的、浅绿的、素白的,背景是透着光的淡紫色的窗帘,流动的色彩和光影让人感觉阳光也是柔软的。写实与写意悄然融合,水色迷离、花影摇曳。他笔下的玻璃花瓶分外清透,花朵氤氲的气氛又是那么恰到好处。尤其是色彩之间的对比和过渡尤为绝妙,在仿佛油画般的浓郁渲染中,飘溢着水彩画特有的透明轻盈的质感。这种清水洗尘、温婉和煦的美一下子让我心旌荡漾,我要把它画下来!当时就暗暗下了决心,也不知道我这个非美术专业的“票友”,哪来那么大的勇气。那天,管理员小姐姐不在,听说她考研去了,是学校一位教《文选》的刘老师先来顶岗几天。我又激动,又有些不安地等到关门的铃声响起,看书的人陆陆续续离开后,来到书架前,跟刘老师说,我想把这本书借回宿舍。他听了有些诧异,我翻开那幅画给他看:“我想把它画下来。”他看看书,又扭头看了看我的学生证,面露难色。“我一定尽快画完,保证爱护好。”他听了随和地笑笑:“没事,你慢慢画。”“谢谢!”我抱着书高兴地飞奔回宿舍。

接下来的几天,逼仄的宿舍里,三分之一的空间成了我的画室。我不知晨昏地画,画到酣畅处,浓墨重彩,水色淋漓;画到瓶颈处,无从下笔,就看着天上的蓝天流云和窗外的柳树发呆。同窗、舍友习惯于看着我的背影偷偷关注我,在我洗完调色盘的时候,我的饭盆已被悄悄扣上了碗,里面的饭菜还有余温。在我外出读书或写生回来的时候,舍友们正悄悄欣赏我的作品,为我收拾没有彻底清除的颜料,多年以后,我才由衷感动——感谢那些年她们能那么悦纳一个有些清冷,又有些一意孤行的女孩。记得一周后,我将书交还刘老师手里,并把我临摹的画也偷偷给他看,他看看书上的,又看看我画的,慈蔼地笑着,朝我竖起了大拇指,如今刘老师已过世多年,他温厚的笑容却清晰如昨。
二
读师范时遇到教我们《文选》的左老师亦是莫大的幸运,他博览群书、才情飞扬。《文选》课上得慷慨激昂、回肠荡气,特别是上古典文学的时候,他会不时地开怀大笑,笑得极爽朗,让我一度想到:这么清癯嶙峋的他,竟会笑成京剧中豪气冲天的铜锤花脸!吟到诗词的时候他时而铿锵,时而低回,兴之所至,他会微眯着眼睛摇头晃脑地唱起来,然后习惯性地用右手将额前的头发往左边一捋——那叫一个酷!满脸陶醉的笑意。真是腹有诗文气自“狂”!这样的课堂,如正在酿造一坛清冽、芳香的美酒,我们的青涩、懵懂、求知、感悟、愉悦和老师的博学、睿智、洒脱、孜孜不倦……一股脑儿酿入其中,历久弥香,回味悠长。课堂上的他旁征博引,融汇古今,他所给予我们的远远超出了教材,我们都以能找到他引用的诗词典故为荣。
他爱书,熏陶得我们也爱读书,每个人每周有一次到学校图书室借书的机会。图书室先是在学校那一排琴房尽头的一幢苏式建筑的一楼,周围树木掩映,就像西方油画中的林中小屋。里面空间狭小昏暗,一进门就有书味,是那种新书、旧书很多书混合的味道,和那木制的老书架、苏式的老屋很是契合。在里面寻书,就像在一本巨大的老书中寻宝。从图书室借来的书,舍友们一个传一个,巧妙“错峰”,人人都有得读,有时,还和其他宿舍的交换读。大多都是被子里面打电筒,废寝忘食也要一本不落地读完。当然,也有人等宿管走后,点蜡烛读的,读得入迷,蚊帐烧了一个大窟窿,整个宿舍一夜惊魂未定。《包法利夫人》《简爱》《茶花女》《文化苦旅》《平凡的世界》……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本接一本排队读完的。记得读到《穆斯林的葬礼》的时候,一个个被楚雁潮和新月感动得稀里哗啦,无限感慨,能遇见这么美好这么长情的爱,死了也值。
有一次,我从学校图书室借来一本《宋词纵谈》,这本书真正为我打开了宋词这扇窗。富有乐感的长短句、唯美的表达形式,赋予了宋词极强的画面感和极富韵律的节奏感。我为“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儿女柔情、“大江东去浪淘尽”的风云豪情、“怎一个愁字了得”的富贵闲情着迷。它的美感,不仅仅是能够表现精致的细节,打动人心,它还可以表现浩瀚的气魄,穷尽山河。也许真正美好的艺术大抵如此,当它摆在你的眼前,透过远古的尘埃,你真正能够看懂其中多少的美妙意蕴,就在于你的眼、你的心。它似闪烁着美之光芒的春波,倒映着翩鸿般的古典情怀,让我彻底沉醉其间。我跑遍全城大大小小的书店,想买到这本书自己收藏,反复玩味,可惜都一次次无功而返。不得已以遗失图书处理,给图书室交了三倍罚金,才如愿以偿。后来又花“巨资”买下了《唐宋词鉴赏辞典》,“大快朵颐”。
当时左老师教两个班,每学期开学他都会给每班买十本书让我们传阅,到学期结束,各班《文选》科目前十名的同学就有幸去挑选自己钟爱的书。那可是我们最崇拜的老师给买的,何等殊荣啊!按当时的书价,二十本书大约在两三百元,老师的工资并不高,可他每个学期都买,雷打不动,令我们甚是感动,更重要的是他及时地让豆蔻年华的我们浸润在书香里,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多年以后读到了一句话才了悟:他固守着孤独和清贫,却是用生命来提携学生。
记得有一次,左老师通知前十名的学生到他那儿去挑选书,按名次先后挑,考得越好挑的余地就越大。当时我和另外一名同学恰好不在学校,老师就帮我们一人挑了一本,当我们回校去取的时候,我发现另外那个同学的《杨贵妃秘史》封面艳丽好看,而我的封面是灰灰的水墨画,上面写着《美的神游——从老子到王国维》。我有些不高兴,为什么我的不是那本漂亮的呢?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原来,老师是懂我的。
左老师是慷慨的,但也有吝啬的时候。记得当时他有好几架子书,每架书都用布帘遮好,我们很难一睹“芳容”。有一次我去交作业,老师正在读书,布帘是拉开的,露出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却无缘一读的书。于是,我壮着胆轻声说:“左老师,我想,我想借本书……”看着他面露难色,我有些后悔我的冒失了,可说出的话收不回了。只见他沉思片刻,伸出三个指头,一个一个掰:“第一,不许弄丢了;第二,不许弄坏了;第三,不许有折痕。”为了读书我只好忍受他的“再三刁难”,然后挑了一本遇赦似的飞奔回宿舍,封上书壳如饥似渴地读起来。记得书名是《凝重与飞动》,讲的是中国的雕塑和书法,书里说:“雕塑是凝固的音乐,书法是纸上的舞蹈。”作者试图去探寻“为什么我们民族的艺术那般空灵,历史却那般沉重”。我细细品读,琢磨,又找了一些关于雕塑、书法的书来读,还找了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来对照赏读,受益良深。
我们毕业后,左老师考上复旦大学的研究生,离开了师范学校,只身赴上海硕博连读。毕业后辗转了几个城市,如今,回到了大理,在山环水抱的大理大学安定了下来,每日授课、读书,居于苍山脚下,樱花深处。每年初春,这里的樱花缤纷开落,他就在这书香中和花香中,时而疏狂,时而简静。每次放假回巍山,他都会送给我许多书,少则十来本,多则三四十本,他总会说:“有些是我做研究用过的,有些是买重了的,你随便看看。”这些“随便看”的书中有《我们仨》《顾随诗词讲记》《献芹集》《芳园筑向帝城西》……年逾不惑的我,还如期接受近三十年前老师的馈赠,接受这份精神投喂,真是倍感温暖和幸福。
三
遥想当年,学校图书室和阅览室的那些书,是满足不了全校师生这么大的阅读量的。当时的我们正值囊中羞涩的年纪,除了泡阅览室、泡图书馆,最期盼的是卖旧书的来校园里的树荫下摆摊,一来,四角钱一公斤的废报纸可以练好长一段时间的书法;二来,可以五毛、一元地淘上几本诸如《李义山诗笺注》《读者文摘》《散文诗》一类的小册子来读。除淘旧书外,还经常到大大小小的书店书屋去蹭书看,如今想来这“蹭书”真是一件最忐忑不安又快意无限的事。走进一家书店,在林立的书架间漫行,自带的搜书雷达此时会飞快运转,少顷,目光落处便是锁定的目标。当然,有时是来续“蹭”的,也不能轻车熟路直扑目标而去,还是要按耐着内心的雀跃,淡定又若无其事地走过它,又折回来驻足,余光快速扫瞄店主,若没被发现便飞快取下,一头扎进书里,随之沦陷在字里行间,先前的忐忑悄然销声匿迹。直到脚麻了才会动动,抬起头,瞬间清醒自己的处境,若是与店主的目光撞个正着,那份不安也瞬间归位,遇到宽容的店主,他会很快把目光移开,假装是不经意一瞥。遇到洞悉你的小把戏,又按耐不住心中不快的店主,只能在他犀利的目光中,默默把书放回原位,当然不忘飞快扫一下页码,以期到下一个书店接着读。这样的桥段和林海音的《窃读记》差不多,都有着隐秘的忐忑和欢喜。
如今想来,在风城大大小小的书店里都留下了我们窃读的蛛丝马迹,很多店主的宽容满足了当时还是穷学生的我们对阅读的渴求。也许因为他们自己也是读书人,从而生出一种同心相惜,让我们收获了一份心照不宣的感动。当然,在书店里也会遇见别样的不期而遇的温暖。
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又和闺蜜去学校附近的一个书店蹭书看。艺术书架上的《马奈莫奈画风》不经意地跃入眼帘,我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迫不及待地抽下来翻看,那天光云影、那柳丝缱绻、那袅袅婷婷的莲影,让人心动神摇,欲罢不能……

第一次看到这本画册是在一位友人的画室里。春日的午后,阳光透过淡蓝的窗帘斜斜洒进来,案头的陶罐里是一束淡紫的雏菊,翻看着那本莫奈的画册,和着淡淡的调色油的清香,莫奈的睡莲是那样猝不及防地击中我,那种不谙世事的不染,莞尔在浅粉淡蓝的如沦如漾的梦幻中,温婉轻敛,一下子摄住我的心,那颤动的笔触和闪烁、跳跃的色彩,让我分不清哪里是水面,哪里是水底,哪里是倒影。这种写意的手法用在油画中竟然那么悠远静谧,犹若沐浴着江南的杏花春雨。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于那古典曼妙的画境中,能自己拥有那本画册成了时时萦绕我的愿望。
不想在这儿和它不期而遇,甚是欣喜!但是一看书价:四十元!当时,普通人的工资也不过百十元。四十元,接近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我摩挲着,反复翻看了许久。当我轻轻放回书架的时候,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轻声问我:“很喜欢那本书,是吗?”我有些惊讶,慌张而木讷地点点头。他微笑着拿下那本书,并拢他手中的另两本书朝收银台去了,不一会,他拿着书折回来,把那本画册递给我:“给。”我怔怔地站着,不敢接他手中的书,他笑了笑,轻轻地将书放在我身旁的一叠书上,转身走了。我愣了一会儿,拿起书飞奔出去,想还给他,可当我追出去的时候,穿梭的人影中已不见他的踪影。手中握着画册的我忐忑地立着,不知所措。
我的闺蜜看到心满意足,带着一脸的惬意找到我:“走了!”“我……”看着我不安的样子,听完我简单支吾地叙述,她的娃娃脸笑开了花;“呵呵,傻啊,有人给你买书还不敢要,要是我呀,乐死了!来,你不敢拿,我帮你拿着!”往回走的路上,我紧张地张望,生怕那个买书人会在某个角落出现,脸上带着狡黠的笑意……后来以至于我不敢翻动那本书,直到多年以后,当然也从未邂逅那位买书人……
二十几年后的我,已过不惑之年,特别是当了母亲之后心也逐渐柔软,也懂了当年那位买书人,他不过是看到一个爱书却买不起的孩子,生了恻隐之心,而那个年纪的青涩懵懂却让自己怀揣了多少自以为有道理的“心眼儿”,如今想来,我若遇到类似的情景也会欣然满足一个陌生孩子的愿望。几十年了,这本画册依然放在我的书架上。在整个书房三面顶天立地的书架上,它已然淹没在书丛中,只是我依然清晰而准确地记得它的位置,偶尔会抽出来翻翻,去触摸那摇曳在时光流里的莲。
因为它依然温暖着我,温暖着我对书的记忆。所以逛书店、买书,依然是令人愉悦的事情,青年书店、三人书店……都是最好的去处,后来又有了新知图书城,看书买书的领域随之扩大。
初识新知,是1998年2月,我到云南师范大学去读函授。一个微雨的夜晚,春城的冬日依旧华灯闪烁,流光溢彩。我独自漫步在街上,沿街的霓虹闪耀着漠然的光辉,雨丝滑落在地上,映着灯光游丝浮动。一个个艳丽如霓虹的陌生面孔也如霓虹般漠然地和我擦肩而过,心里涌动着一种淡淡的孤寂。
走到建设路的一个街口,一幅巨大的商场广告吸引了我:玫红的底板上,一条黑色的飘带矫若游龙,设计简单,却令人难忘。原来这是百汇商场的标志,就在这时,我意外地发现标志的旁边竖着一个不大的灯箱,写着“昆明新知图书城”几个字。在这个商业味十足的商场里居然有一个图书城,这大概就是“知识经济”的最好诠释吧,我有些调侃地想。随着电梯徐徐上升,我来到了新知图书城。在这里,我真正领略了“书城”的内涵:宽展延伸的空间、林立的书架、云集的读者,让我既惊喜又兴奋。特别是墙上的话令我非常动容——“为读者找书”。一种久违的亲切感随即弥漫开来,让人蓦然间找到一种归属感。“为书找读者”,赋予了书以生命和灵性,只为知音者赏,其价值的内涵已升华到精神的空间,折射着一种人文的气息。私以为,经营书店不能是一种纯商业的行为,更应该是经营一项文化事业,经营一种操守,书店本身也应该是一方滋养文化的沃土。因为这俯俯仰仰的人群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们正在或即将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从此,来这儿读书,成了我的心理日程,好像与它有一个重要的约定。在各个书城间流连,书架透视成无限延伸的空间,一直到视线的尽头,心中升腾着一种磅礴的感觉,这是一个精神自由徜徉的所在,灵魂在这里得到了彻底的放松。这里弥漫着互不相识又浑然一体的气氛,相互间有一种自然的默契:手伸向同一本书时的谦让;踮着脚也够不着书时,一只大手帮助取下来时的惬意;对书中某一个细节轻声讨论后会心的笑容。在这儿,总能和许许多多素不相识的人不期而遇,相互间无言的亲和力让人感动:读者之间是不设防的。
我与新知的约定依然继续。不知有多少次,抱着从各个书店挑选来的书,坐在供读者休憩的椅子上不得不重新筛选——在外求学的我总不能随心所欲地买吧,怎么弄回去呢,当时还没有快递这一说。可还是有好几次拎着一大堆书徒步返校。记得每次抱着书来到验书处,这里的服务生总是看着桌上的一堆书微笑着说:“要章吗?”“要。”我总是不假思索——这是与新知每一次约定的轨迹。
每一次的约定,我都能更深切地感受新知。在读者群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都是学生模样,有的蹲在书架前,有的坐在椅子上,都在专注地读书,翻看书页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的,看得出他们手中的书没有一丝折痕。服务员们已开始用餐,人们也陆续散去,他们掏出兜里的食物——或馒头、或面包,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完后,把手擦干净,又继续读书。不知过了多久,人又陆续多起来,学生中有人看看表,小声招呼自己的伙伴,孩子们依依不舍地放下手中的书,再回头反复确认是哪本书的哪一个页码,哪本书在哪一个书架。触景生情,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一边读书得一边观察店主的脸色,若发现苗头不对,赶紧把书放回,带着对书中文字的牵挂和对店主的歉意,怅然地离开书店。不过,也感受过书店老板的宽容,不知多年以后这些好读的学子们是否也会对这里心怀感激。
想起一位叫萧轶的作者在《依旧有味是青苑》中所说:“一个书店的灵魂,不仅仅是靠书的熏陶,更是源于读书的种子的每一次流连忘返。城市的灵魂,也就在书店的艰难前进中慢慢得到培养和熏陶。”所以书店又不仅仅是书店,对于读书人来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份精神姿态,一段成长记忆。
与新知相约总是在微雨的时候——每年的2月和8月,正是冬雨纷纷、秋雨绵绵的时节,也正是我赴昆读函授之际。就这样与之走过了三个秋冬,以书为友,不离不弃。将自己埋进书丛,置身于淡淡的书香之中,就会感到久违的生命的静谧,隔绝了外界的纷扰嘈杂,也使置身于纷繁生活中的自己,在一次又一次尘埃落定时,反复审视生命的厚度。
2000年8月,我的中文函授毕业了,恰好当年的10月1日,昆明新知(大理)图书城开业了,与新知的相约又得以继续。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畅游书城,挑选钟爱的书,验书处的服务生笑容依旧:“要章吗?”“要。”我依然不假思索——我们相约的轨迹既然已“保持连接”,当然要让它继续。书架上《倾城之恋》《长恨歌》《额尔古纳河右岸》《温一壶月光下酒》《行者无疆》……一册册充实着我自己的书架,充盈着我的内心。我也开始在绿色格子稿纸上写文章,手写,颇具仪式感,投稿要邮寄,贴上好看的邮票,投进邮箱的一刹那就升腾起一种牵系,一种希望。
四
从未想过,多年以后,我自己也会出书,一本关于戏曲的散文集。
一个人对于文字、戏曲或其他领域的热爱,有的是电光石火的一瞬,便开始深深迷恋,比如白先勇先生对昆曲的热爱,早在他幼年时就埋下了种子。当时不到十岁的白先勇,由母亲带着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看了梅兰芳先生《牡丹亭》中的一折《游园惊梦》。那是他第一次遇到昆曲,美妙的音乐和戏词却悄然沁入脑海。确实,世间的许多事情,一旦起心动念,就有了因果。因孩提时代的惊鸿一瞥,就有了后来青春版的《牡丹亭》。
而我对戏曲的喜爱又是因为耳濡目染,一点点的渗透和浸润的。在我幼年时,巍山古城有过一个滇剧团,我的小姨便是这个剧团的大青衣。上了妆的她,就像是从古画中走下来的,美得惊心动魄。我经常跟着她,在后台化妆、背台词、候戏。我六岁的时候就有了第一次跑龙套的经历。为了那一句两句台词插得恰到好处,小姨教我熟悉念白和唱词。这样的幼年在同龄人中是一个异数,在同龄孩子追着母鸡满院子疯跑的时候,我手中是一张薄薄的信笺,上面是用蓝黑墨水写的唱词,俊逸的楷书,煞是好看:“贾宝玉进潇湘泪如雨洒,西风起见叶落满径黄花,那壁厢破芭蕉空造雨打,这一旁只剩下几树山茶……”还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牡丹亭》剧本,不大懂,但读着“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感觉美得不行。后来读《红楼梦》,发现黛玉听了这段唱词,也是“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对于我来说,或许当年背下来的那些唱词就是最早的文学启蒙。
那些丝丝拉拉的胡琴声和点点滴滴的司鼓声已经浸润了我的整个童年,直至成年以后听戏、看戏已成为一种日常。从青衣婀娜委婉、大气端然,到老生的沉沉苍苍、黄沙漫漫。听马连良、余叔岩、周信芳,听梅派、尚派、程派、荀派,最先让我意惹情牵的是程派,“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那唱腔,断而后续,若断若虚,丝丝绕绕,婉转缠绵,欲罢不能。梅派是华美的,是盛唐女子,是云做的衣裳、花做的容,不由得你不喜欢,但又不是可以太亲近的那种喜欢。尚派几近失传,留存剧目不多,寒山瘦水,大漠孤烟,但总有一股浩气在,有一种人见犹怜的悲壮。荀派是花旦,真正的花旦,很娇俏地带着那种花枝斜插的艳,袅袅婷婷,如水如花红妆。
想起早些年的时候,我是羞于谈自己喜欢戏曲的,听戏的时候怕人听见:“喜欢听戏?没搞错吧,你有那么老吗?”后来,读了《合肥四姐妹》才知道四小姐张充和八十多岁还唱昆曲呢。直到近百岁,她仍旧吹笛子唱昆曲,到老来不见衰朽,愈发好看,有着昆曲雅韵深深浸润过的淡远、清朗。人们称她为“最后的闺秀”。羡慕她被书法、昆曲、诗词浸润的一生,多么幸运、芬芳。张爱玲倾城的文采也和戏曲根脉相连,她很多次在文章里讲述自己看戏经历和体会,她说:“为什么我三句离不了京剧呢?因为我对京剧是个感到浓厚兴趣的外行。”写《韭菜花》的汪曾祺会吹笛子,唱昆曲。年少时,跟着父亲的胡琴唱老生,也唱青衣。以前读他的《人间草木》《寻常茶话》,只觉得其中的文字干净质朴之外有着乐感和韵律,后来才知道他是国家京剧院的编剧。他在《人间有戏》中流露着的对伶人的悲悯:“我听得耳熟,他唱得悲凉。京剧伶人身怀绝技,头顶星辰,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粉墨人生,风流云散,由伶人身世,看尽世情悲欢。”

这些被戏曲浸染的有趣灵魂感染了从小泡在戏里的我,戏曲已然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它贯穿于我的成长和喜好中,我一边听戏,一边写文章,用文字表达自己。2010年的时候,我开始在新浪网上写博客,写的也都是一些零星的经历和感受,或长或短,和自己对话,表达自己,安放自己。后来,我开始写戏曲散文,写方寸舞台,阅世情悲欢。书写这些故事和感悟,也是在梳理自己成长淬炼的过程。同时也从戏曲舞台上了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披甲上阵的前台,也该有卸下盔甲,让心灵小憩的身心清宁的后台。前台是粉墨登场的所在,回到后台,悦纳自己的优雅从容,亦悦纳自己卸妆后疲惫的容颜,甚至是戏装上的泥渍,在这里,不用妆容精致,不用发丝不乱,偶尔的脆弱可以在这里安然释放。当我们一次次体面地转身于前台的满堂华彩的时候,我们也有梳理自己、安抚自己、沉淀自己的后台。于我而言,阅读、写作就是这个后台,我在这里和自己和解,与生活言欢。所以,读书、写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个人秘密幸福的一部分,我不想让这一切带有一丝强迫性和表演性。
随着戏曲散文在报刊杂志上的陆续发表,我也能更舒展地表达我对戏曲的迷恋,书写着自己和戏有关的幼年。
年幼时戏在心里是单纯的,就是小姨咿咿呀呀粉墨登场的样子。从小生长的巍山古城,在记忆中如老照片一样,灰蒙蒙的,又像轮廓不甚清晰的版画,或是黑白变幻的电影胶片。惟戏是清晰的,浓墨重彩的,那锣鼓笙箫、丝竹胡琴,如水墨画中的“破色”,而台下平日灰蒙蒙的众生,一旦登台亮相,便让这色破到绝妙之处,惊艳无比,仿佛跨越时空过着另一种人生。
小姨便是这样,生活中一样柴米油盐过日子,一旦上了妆,上了戏台,便成了跨越千古的绝美青衣。她是滇剧团的角儿,她到哪儿都带着我,我便成了她的“小跟班”。我陪她在后台化妆、候场。因不知在镜中看了多少回,那场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如绘:化妆师取过肉色的彩底,挤在掌心,均匀地一点一点往她脸上、脖子上、手上抹,然后,调眉,包头,戴头套,用黑色眼彩勾眉眼,蘸胭脂轻染,点上绛红的唇彩,艳若丹寇,服装师为她披上水衣。那时的她是云鬓珠花、水袖盈风的嫦娥;是一花不与众花同的白蛇仙子。
妆成之后,她便背过身默戏去了,每次有演出她都要早早到场,为的就是默戏。这个时候,谁也不敢惊扰她,连我这个“小跟班”也不能黏着她了。她要进入另一种人生,悲喜都是那个人生的,现实中的她被那个人生一点一点渗透,浸成戏中的那个人,没有了自己一丝的痕迹。
待小姨默完戏,转过身来候戏时,她眼里已经没有我,没有周遭,恍惚间让人感觉天地虚无,神智不知落在哪个朝代没回来,已然是戏中人了。只听侧台一声:“苏三,上。”有人把那“出将”的帘子掀开,“苦哇——”小姨便出去了,“好——好——”每场都是这样“掀帘彩”。她是名角,她的身段、行腔、唱念做打,特别是那戏的灵魂精魄和这“掀帘彩”匹配得丝丝入扣。灯光盏盏照在戏台上,有一种特别的繁华和隆重。我早已溜出去趴在前台,看她绣花鞋尖上顶着的朱红毛绒球颤颤悠悠,她则步步生莲地走圆场。满场翻飞的裙裾,花飞蝶舞,像刮过了一整落花风。
记不清多少个夜晚,不谙世事的我陪着她,演绎着别人的悲欢离合,喜着自己的喜,悲着自己的悲。她清透的嗓音乍破银瓶一般穿透礼堂,穿过城楼,在月明星稀的夜空萦绕,有一种旷然清新、耳目一明的感觉。这样的冰雪嗓音配上这样的清风明月,真是广寒宫里嫦娥展袖,天上人间共此一曲。待她回到后台,摘了行头,卸了妆,带我去吃宵夜的时候,她已魂归原位又是我亲切、贴心的姨了。看着她和其他叔叔伯伯我就觉得戏好神奇,它能把我身边这么亲近熟悉的人,用粉墨,用行头,用程式,用功夫,用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转瞬之间变成跨越千古的英雄美人;而卸了妆,又是“洗尽铅华呈素姿”了,花栽泥里,云浮天上,各归其位,妥当安稳。
长大后的我没有学戏,但随身带着一把胡琴,这两根弦一张弓,颤动的是我心底的余音,是姨的姣好身影和那眼底化不开的忧怨。戏,是我心上的刺青,我浸润于它的幼年,悄然成了我人生的底色,在心底寻我前尘的余音——那浅吟低唱已消散在喧嚣和匆忙中,有时,我觉得自己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拽着,不知方向地往前赶,再往前赶。只有在夜深人静,心的深处又响起那唱腔和唱词的铺陈的时候,心才有了归属,脚才踩到了土地,我已然是一株悄然生长于斯的作物,我的生命有意无意间摇曳的是她的芳华。我坐在电脑前,拉平时间的褶皱,一点一点地码字,写下这些芳华、这些吉光片羽、这些金粉金沙的艳。
2019年伊始,我便开始整理这些关于戏曲的文字,准备结集出书。此时的纸质书和戏曲一样,已经式微,且一叠书稿到一本书的蜕变,要经历多少个回合,亦是可以想见的。但是,我愿意。因为我深爱的文字、深爱的戏曲,更何况,这是一本关于戏曲的文字。或许,这也是当年在图书室、阅览室、书店一排一排静谧安详的书架间穿行流连时,悄然种下的青春的梦想。岁月杳然,回顾所来径,梦想的嫩叶新枝在不知不觉中已吐新芽,默默生长。从稿子的筛选、修改、内容的三审三校,到纸张的挑选和装帧风格的甄别、选择,再到封面和插图的设计、手绘效果的N次修改,确实是一个漫长而繁复的过程,每一个细节都得仔细推敲,耐心协调,带着“书为阅己者容”的期许,或者说有无“阅己者”、有多少“阅己者”都已经不重要了。我、编辑、设计师都带着对书的敬畏和坚持,将戏曲的那些翩若惊鸿的身段、百转千回的声腔,那些沉敛妩媚,那些气冲霄汉,那些忠贞大义,那些繁华苍凉,牢牢焊入纸页中。
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本有故事的书,人和书的每一次相遇都开启一段新的旅程;人和书、人和人的相遇相知又形成了每个人的人生故事。人成了书,书成了人。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书卷是读书人的心底山河,那纸页散发出的淡淡书香,那翻页时簌簌作响的纸张,那一个个饱满整齐的汉字,哪一个不能触发人的无限情感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