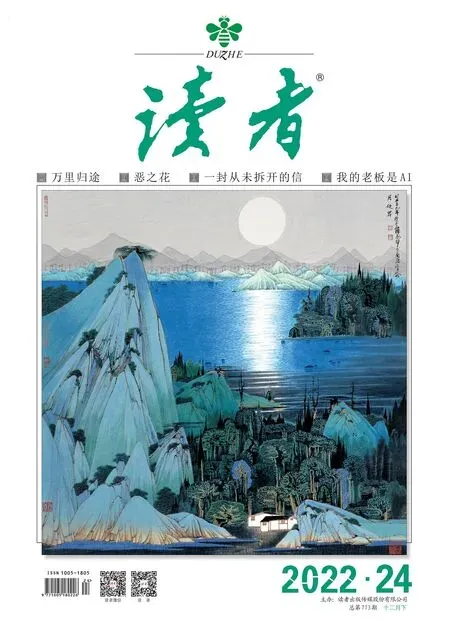熬鱼
☉铁 鱼

每逢周末,只要老陈给我打电话,说弄到了三四斤的大鳎目,我就立刻启程,从北京去天津一饱口福。
老陈今年七十多岁了,比我爸还大十几岁,我喊他“大爷”,他却喊我“兄弟”。他开了一辈子饭馆,也没发财。我曾建议他扩大经营规模——以他的手艺,执掌一个二三十桌的饭店,应该问题不大——可他总守着这个三五张桌子的小店。
他熬的鱼是一绝,无论是鳎目还是平鱼,先煎后熬,用长鱼盘一盛,卖相绝佳——薄薄一层红亮酱汁,盖着下面的鱼,一筷子挑开鱼皮,鱼肉仿佛白玉。鱼盘里没有一点儿多余的油,鱼身下隐隐有一层汤。最绝的是炸成虎皮的蒜子儿,跟鱼一起炖一番,别有滋味儿。把鱼肉往白米饭上一铺,再来一勺鱼汤,如果说“朋友”二字有具体的味道,那一定是熬鱼拌大米饭的香味——不必推心置腹,但总是相谈甚欢,天南海北、世间万物,好不快活。
每次我去,他总会陪我喝一杯直沽高粱,喝多了他就连串儿地迸天津俏皮话,我跟着学了不少。
他父亲九十四岁,身体硬朗,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巡店,拄着一根铁拐棍儿——我偷偷拎过,倍儿压手。父亲见了他就骂“你个倒霉孩子”,看他百般不顺眼。
他有时候被骂急眼了也发点儿脾气,摔摔打打的,但是依然给老爷子熬鱼、烫酒。只是做给老爷子的鱼都是小鱼,几条小杂鱼,都是事先烧好了的。老爷子一边骂一边吃,吃完了就自己拄着铁拐棍儿回家,也不用扶。
我有一次遇到了就取笑他:“爷爷脾气可够大的,这骂人的劲头!”
“我七十三了。”他抽了一口烟,“还能有人骂我两句倒霉孩子……”后面的话他没说下去,我也懂。
“他以前在街面儿上也是有一号的,年轻的时候在海河上跑船,你看他那根铁拐棍儿,以前里面藏着剑呢。
“他这一辈子就爱吃熬鱼。好嘛,以前他熬鱼,那大鳎目,十来斤。现在可没有啦,有也吃不起。”他比画着说,“我没什么本事,这辈子也就跟他学了个熬鱼,他的其他本事我不爱学,也学不会。他也看不上我,我呢也这把年纪了,除了开饭馆,什么也不会。”他有一句没一句地抱怨着,可面儿上笑嘻嘻的。
后来他的饭馆停业了一阵子,我才知道他父亲得阿尔兹海默病了,卧床了很久,他索性把饭馆关了,去照顾父亲。春节我给他打电话拜年,他很惊喜,说:“兄弟,你哪天来,趁过年,来咱家,我给你熬鱼。”
我问起老爷子的情况,他说:“唉,人都有这一天,伺候着呗。”
我说:“过几天我从山东路过天津,去您那拐个弯儿。”
他说:“好嘞兄弟,我等着你。”
可一直到了夏天,我才因公去了一次天津。顺便路过他的小店,一看竟然开着门。
他头发白了很多,正在收拾一条四五斤的大鳎目,我喊了一声“大爷”。他猛地转过身来,看着我,憋了好半天才说:“你来了?”
我说:“来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您。”
他说:“好,还想着我这个老哥哥。”
“我不想您,也得想您的熬鱼啊。”我看着那条大鱼直流口水,“我这还赶上了。”
他摇摇头:“兄弟,今儿这鱼你吃不上了。”
我说:“怎么的,被人订了?”
他摇摇头,指了指里屋。
那九十多岁的老爷子,一身长袍马褂,戴着礼帽,手持铁拐棍儿,端坐着,面前摆着一桌子菜。他看到我来,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我吃惊地问老陈:“这……老爷子好了?”
老陈摇摇头,说:“他早上突然从床上起来,说要吃熬鱼。自己换了衣裳,点了菜,一路走过来。”
我心里迸出四个字——回光返照,但是我们都没说出口。
他说:“儿孙都在外地,也都通知到了。不知道赶不赶得上。”
“倒霉孩子!熬鱼呢?”老爷子在屋里骂了一句,我跟老陈赶紧进去。
老爷子招招手让老陈过去,老陈把熬鳎目鱼摆在桌上,弯腰蹲在他跟前。他吃了一筷子鱼,伸手摸了摸老陈的头,叹了一口气,说:“宝贝儿,你是个好孩子。”
我眼看着七十五岁的老陈眼泪不要钱似的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