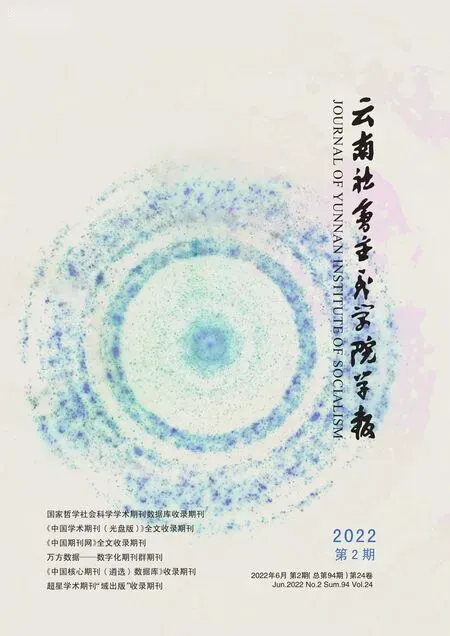以微显宏: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
——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
罗夏梓平,孙俊烈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名人故居的核心要素是已故历史名人和所居住过的场所。“名人”一般是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发挥过较大作用且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故居”则是名人曾经居住过的场所。它既包括名人出生地及其自有居所,也包括其他与名人人生、社会重要阶段相关的住所。因此,结合前述界定名人故居,应注重历史名人的人生经历与居住场所的关系及其社会价值而定。
名人故居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空间,与历史建筑旧址、工业遗产旧址等归属于旧址博物馆。①单霁翔:《实现保护性再利用的旧址博物馆》,《东方博物》2011年第1期,第4页,第5—21页。三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纪念的对象不同。历史建筑旧址侧重于展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历史事件等承载某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建筑;工业遗产旧址则侧重于展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为生产活动而建设的各类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两者主要是通过纪念旧址建筑还原历史风貌和获取历史文化知识。而名人故居旧址主要纪念特定的历史人物及其与之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相关的历史贡献与社会价值。作为一种微观人物史,它所体现的精神文化价值成为跨越时空的社会影响。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历史名人的一生依托物质性的建筑景观展示转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
现阶段国内学界关于名人故居的相关研究主要以保护和开发两种路径为主。比如,丁超、张秀娟从理论上提出了名人故居的认定和保护原则;①丁超、张秀娟:《北京名人故居的三重属性及其认定与保护原则》,《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第3—39页。常青、王云峰从建筑学的角度探讨名人故居的保护,提出了“谦卑”修景的观念;②常青、王云峰:《梅溪实验——陈芳故居保护与利用设计研究》, 《建筑学报》2002第4期,第22—25页,第68页。刘敏从建筑遗产的公众参与机制出发,探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保护路径;③刘敏:《天津建筑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与实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21年。唐德彪、方磊利用加权合成法评价名人故居的旅游开发;④唐德彪、方磊: 《名人故居旅游开发的综合评价:方法与实证》, 《怀化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20—24页。沈实现、李春梅、徐华用系统考证、实测的方法对杭州名人故居进行分类评价,提出了名人故居景观、文化与经济系统发展的原则;⑤沈实现,李春梅,徐华:《地域景观·城市记忆——杭城名人故居的景观特质与保护开发》,《城市规划》2005第9期,第55—59页。黄林、张建华、郭安禧运用IPA等方法进行游客满意度调查,从而提出名人故居四种旅游发展策略。⑥黄林、张建华、郭安禧:《上海名人故居游客满意度分析——以上海鲁迅故居为例》,《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73—80页。总体来看,学界对名人故居的研究较为统一,较少出现国家层面对名人故居的叙事研究。基于此,本论文将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探讨名人故居如何从物质实体转化为符合国家叙事的精神文化。
一、名人故居与国家叙事的关系
叙事,就是“讲故事”,是对发生之事的重述。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叙事强调的是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历史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把握和理解的语言结构,并赋予意义。⑦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6第3期,第23—38页,第189页。由此来说,叙事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及其意义结构。
国家叙事是基于特定国家构建的一种话语模式,它支撑着国家的存在,并推动着社会的运行。日本心理学者岸田秀认为,国家叙事在于囊括大多数国民的情绪以保持一致性,并对内给予国民荣耀与价值观的支持,对外得到别国的认可。这样,国家叙事才能在认知上实现连续性。⑧[日]岸田秀:《ものぐさ精神分析》,东京:青土社,1977年,第27页。笔者认为,国家叙事的内容应该注重历史的“人文关怀”。这一叙事思想在于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以最大限度获得国民的共鸣与成就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叙事的历史积淀性。叙事内容应承载着国民整体的历史记忆,体现集体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国家叙事的“人文关怀”。叙事内容要贴近民众的生活,让民众真切感受到叙事的“真实”,也就是要有“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的叙事思维。因此,具有历史“人文关怀”的国家叙事不仅构建一种民族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还成为独特文化魅力的对外展示。
名人故居记录的是历史人物的生平及其与时代发展的关系,属于一种微观人物史。将其居所置于国家叙事中,采用一种“同在性”取代“时序性”的话语模式,将历史人物的私人空间进行公共空间移位。名人故居得以成为一种叙事文本,具有明显的后现代叙事手法。西摩·查特曼区分了“故事空间”与“话语空间”,认为前者是故事或行为发生的当时环境,往往具有故事中人物的视角。后者是叙述者的空间,是叙述者的视角或物理位置。两者组成了叙事文本的“指示中心”,即叙事时空分别指向了有机本原与出发点。“视角”和“聚焦”是查特曼叙事模式的核心。①David Hermanetal.: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552.由此看来,从普通民居旧址到名人故居的“标签化”,所呈现的是“故事空间”到“话语空间”的不同空间指向,以形成微观人物史与宏观的国家叙事的关系。因此,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是基于具体的历史人物及其居所作为媒介的叙事策略。
名人故居作为具有纪念意义的旧址博物馆,在国家叙事中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莫里斯·哈布瓦赫将记忆视为一种社会产物,个人记忆被圈定在一种“现实感”的集体记忆框架中。他认为:“社会思想本质上是一种记忆,它的全部内容仅由集体回忆或记忆构成。这其中只有那些在每一个时期的社会中存在,并仍然在其现在的框架当中运作的回忆才能得以重构。”②[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正如名人故居叙事空间的转变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和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具体要求,在新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机制中,国家叙事的建构策略赋予了名人故居新的“话语空间”,从而渗透到社会观念系统中成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而作为一种记忆场,名人故居依托物质化的空间展示,表达着特定的国家叙事“知识”。从视觉的印象到思想的内化,这种集体记忆模式就更具有稳定性,也得以实现跨时空的共存。
二、聂耳故居国家叙事文本的建构路径
聂耳故居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甬道街73、74号。其始建于光绪十年(1884年),系重檐店铺房。光绪三十年(1905年),聂耳的父母从玉溪来到昆明,租住于此并开设了一个小医馆,取名“成春堂”。1912年2月14日,聂耳出生于此,他的童年基本在这里度过。1986年7月,聂耳故居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12月18日,升级为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聂耳故居进行修复;2011年,成立昆明聂耳故居纪念馆;2012年,聂耳故居挂牌设立为云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
聂耳故居的历史考证、资料整理、建筑修缮等都与国家叙事文本的建构路径紧密相关。它展现的是这个时代国家的“话语空间”与集体记忆。聂耳谱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不断激发爱祖国、爱人民、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情感和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自豪感。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赋予宪法地位。③吴北光:《几度沧桑话国歌》,《人民日报》2004年3月31日,第9版。聂耳的形象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一样,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在国家叙事文本的建构中,聂耳故居承载的是民族精神与进步文化。
聂耳故居采取史料实证的历史叙事与民俗叙事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历史考证、文献查阅、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行国家叙事文本的建构。最终,聂耳故居呈现出物质景观叙事文本、语言文字叙事文本、仪式行为叙事文本三种。
(一)聂耳故居的物质景观叙事文本
聂耳故居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一样,强调的是“人”与“物”的关系。“物”在博物馆的展示空间中被构建成景观叙事文本。简·塞特斯怀特根据杰克逊的设计提案《JacksonStreet:EngagingtheNarrativeLandscape》提出了“叙事景观”一词,用以表达景观中的记忆、视觉参考与体验三层意义。①陆邵明:《浅议景观叙事的内涵、理论与价值》,《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年第3期,第59—67页,第209页。意味着,名人故居中的景观叙事文本是将历史故事浓缩于物态的景观设计中,以“讲故事”的形式述说过去,以拉近时空距离,唤起集体记忆。因此,时间在空间中的物质化是国家叙事的首要方式,也是体现名人故居各要素的主要手段。实际上,“景观”既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角色,又是一个综合的叙事系统。从聂耳故居的景观设计来看,主要呈现历史建筑、馆藏民俗文物和图片两类。
1.历史建筑景观叙事
自2004年以来,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多次对聂耳故居的历史状况进行了详尽考证,并制定了《聂耳故居修缮方案》。2007年5月,云南省文物局同意《聂耳故居修缮方案》。修复后的聂耳故居复原了1912年时的原貌,被开辟成聂耳故居陈列馆,并于2011年6月23日重新对广大市民游客开放。
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这是一个“符号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景观堆积的颠倒时代。②[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7页。聂耳故居从最初商住两用的木结构生活居所发展成为当下具有博物馆、旅游、教育等功能为一体的景观建筑,其本身已经改变了建筑的叙事方式。基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需要,相关部门充分利用建筑的日常生活“故事空间”进行国家“话语空间”的改造,将具有国家叙事特点的学术知识、文化知识融入其中,并结合昆明老街的商业、旅游开发,以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重文化功能诉求。就此,聂耳故居作为文物被修缮、保护,不仅成为民族精神和集体记忆的象征符号,还构建出具有建筑美学价值的区域性经济发展模式。
聂耳故居作为一种景观叙事的“物的语言”,在集体参与中成为不同民众身临其境的“人的语言”。在从微观的日常生活建筑到宏观的名人故居的界定,国家叙事为其提供了新的定位,使之以媒介的形式在“集体凝视”中引导思想、表达情感,从而创造出新的话语符号。
聂耳故居既是一座传统民居又是一座小型博物馆。其无论以什么身份呈现,都具有“容器”的功能。虽然在容纳个人日常生活和历史建筑景观时有着不同的叙事指向,但它都与不同时代产生着紧密的联系,并内蕴具有民族精神的“家国同构”的国家叙事思想。
2.馆藏民俗文物和图片的景观叙事
聂耳故居中的民俗文物和图片内容展现的是特定时期民间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其“物”的表征下隐藏着深刻的民俗文化内涵及其新的文化指向。关昕认为:“民俗器物被嵌入不同时期的公共文化结构里,体现了对传统日常生活差异性的文化转译。”③关昕:《从生活日用到文物藏品——民俗器物博物馆化的话语表征与意指实践》,《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4期,第45—52页。因此,当历史遗物及图片背后应有的活态“故事真实”成为博物馆中的静态“话语真实”时,它所赋予的是当代社会共有的价值与意义。聂耳故居中的“物”不再是民俗意义上的认知重塑,聂耳的生活与社会的关系所体现出的民族精神被肯定、凝练、强化于国家叙事中,成为一种新的景观叙事。
聂耳故居中所展示的民俗文物和图片采用的是博物馆中常见的“陈列语言”模式,也就是通过模型、图片、雕塑、照片等实物向观众交流思想的工具。④张翊华:《博物馆陈列语言的探讨——文字说明在陈列语言中的地位和作用》,《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4期,第52—55页。聂耳故居中收藏了聂耳和家人生前使用过的家具、日用品、乐器等富有生活气息的器物以及大量的人物图画、照片等生活图片。一楼入口厅房的左侧是聂耳父亲聂鸿仪的医馆,里面摆设了行医需要的桌椅板凳等器物。医馆正上方二楼是聂耳父母的卧室,里面摆设了睡柜、桌凳、箱子、梯子等日常家具、用具。一楼入口的厅房和右侧房间及其对应二楼的两房间主要展示了聂耳和家人的大量生活图片。同时,展柜中还放置了一些聂耳生前使用过的各类乐器、日记本、创作歌曲手稿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虽然不是历史的真实,但它们起到辅助展览,并帮助参观者理解的作用。在故居院子中,放置了一个石头水缸和一些盆栽植物,这些实物景观设计旨在还原民居中的样貌和体现生活气息,以丰富景观叙事内容。
聂耳故居中的民俗文物和图片建构出可视化的国家叙事符号。从聂耳吹小号、弹钢琴、参加求实小学乐队等与音乐相关的活动图片展示,到聂耳使用过的笛子、小提琴等器物展示,都是围绕“人民音乐家”这一主线展开叙事。这些物质景观所体现出的“生活真实”被归指向聂耳最为朴实的艺术人生与爱国情怀。国家叙事的符号化与生活化,从视觉上构筑起了历史与当下的生活联结,致使参与者在体验式的叙事交流中产生情感共鸣。
(二)聂耳故居的语言文字叙事文本
聂耳故居的语言文字叙事文本主要来自于文献史料和口述史记录,两者都属于“历史记忆”的范畴。王明珂认为,历史记忆包括“社会情境” (社会群体的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它与相关的族群、性别或阶级认同与区分)和“历史心性”(遵循的材料与叙述模式)。①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第5期,第136—147页,第191页。聂耳故居基于国家在场的影响,将凌乱、片断、无体系的文献史料和口述历史进行再次组织、选择与综合,形成新的国家叙事方式,用以构建一套符合当代国家价值体系的“故事线”,并在新的“社会情境”和“历史心性”中赋予聂耳故居新的社会认同体系。
聂耳故居正门入口的厅房前挂着一幅巨型的聂耳头像照,照片中的聂耳西装革履,是旧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装扮。照片上方写着“人民音乐家”五个大字,这与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着共通性。两者所体现出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形成互构,这为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奠定了基调。由此,在以“人民音乐家”为中心的叙事中,通过《义勇军进行曲》由抗日战歌到国歌的形成、发展,来诠释聂耳的人生轨迹与中国革命及其国歌创作的关系。
聂耳的生平叙事依次分为“诞生与童年”“不朽的乐章”“生命的绝响”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叙事内容都与音乐紧密相关,并串联成一条“故事线”。“诞生与童年”侧重叙述了聂耳的家庭与出生;慈母的言传身教对聂耳思想品德的形成;母亲讲故事融入民族音乐玉溪花灯对聂耳音乐爱好的启蒙;聂耳求学阶段不仅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还参加各种音乐活动,学习各类乐器。这些叙事内容为之后聂耳投身革命,谱写革命歌曲埋下了伏笔。“不朽的乐章”叙述了聂耳离开昆明前往上海工作的经历,侧重描述了聂耳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及其如何投身革命,并自觉地将自己在音乐上的发展与革命进步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同期,聂耳走进群众中间,去体验和熟悉生活,创作了大量进步歌曲。《义勇军进行曲》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之一。这些内容虽然叙述了聂耳的革命事业与音乐的关系,但其中蕴涵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生命的绝唱”主要叙述了聂耳人生最后的作品《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过程及其在日本鹄沼海滨不幸罹难,其骨灰安葬于昆明西山。同时,罗列出了聂耳1932—1935年期间创作的35首歌曲和4首器乐曲。这些乐曲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揭露了社会的矛盾,唱出了大众的心声,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是我国音乐史上不朽的乐章。总体来看,三个部分对应着“(出生)成长—成熟—死亡”三种人生阶段。无论从叙事内容还是思想内涵来看,都呈现层层递进的关系。
聂耳故居的语言文字叙事材料所遵循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共同性原则。这是从微观到宏观的国家叙事策略,目的在于将较为局限性、私人化的历史文献和口述历史转化为公共性资源分享,以在国家叙事中构建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
(三)聂耳故居的仪式行为叙事文本
聂耳故居作为一种特殊的意义空间,与当时的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我们只有在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人和真实的事物,它们构成一种相关联的框架。①[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58页。由此来看,聂耳故居的时空框架,凝聚着这个时代人们的共同主题与思想,并伴生出各种人类仪式活动。罗兰·巴尔特认为,空间的隐喻方法要比抽象定义更为重要。其作为特殊的容器,本身并无定义,但通过选择、排列、充实化来决定其意义。②[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8页。这意味着,物质空间的表征背后隐藏着人类意义的本身。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造就了建筑本身由微观“人间烟火”向宏观“象征符号”的功能转变。聂耳故居的空间设置体现出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建构,从而通过其空间设置凝练出“聂耳精神”的国家话语隐喻。正如日本建筑理论家香山寿夫所言:“场所就是在不断迭加的过程中,各种事情都在那里发生的地方,是一个将人类集团统合为一体的地方。场所是共同体的依靠和支柱。”③[日]香山寿夫:《建筑意匠十二讲》,宁晶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因此,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旨在构建公共的文化教育场所,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聂耳故居的仪式行为叙事主要通过纪念性活动和各类主题文化活动来实现。
第一,纪念性活动。聂耳故居承载着记忆过去、缅怀历史、启迪当下、开创未来的多重社会责任。作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聂耳故居但逢相关的纪念时间节点,便会迎来各类社会群体的纪念行为。比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民众参观聂耳故居,通过对聂耳生平和国歌诞生的了解强化了对历史的记忆,实现了自我的革命精神洗礼和对国家和先烈的崇敬;国庆日,由各县、区退休文艺工作者组成的聂耳故居音乐组通过演奏聂耳身前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弘扬聂耳文化、传承聂耳精神,同时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国际博物馆日,省、市、区相关文旅部门打造的博物馆旅游活动,将聂耳故居纪念馆融入其中,不仅探寻昆明历史街区的风貌,还回顾了云南革命的历程。这些围绕聂耳故居开展的纪念性活动强化了人们对“聂耳精神”的记忆,通过政府的引导和民间社会的自发组织,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各类纪念活动,进而在追忆历史的同时完成了民族精神的传承、个人道德的教化以及国家构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二,主题文化活动。聂耳故居作为物质遗产和史料记忆场,在国家叙事中成为思想道德教育实践基地。依托主题讲座、专题宣讲、青年团校等形式,充分挖掘聂耳故居的红色文化资源。社会各界群体、机构单位每年都会开展各式各样的党建、团建等主题活动。比如,聂耳故居所在的昆明老街区建立了党群活动服务中心,打造了“党建+红色旅游”为主题的品牌,将老街的历史文化与红色基因融入到区域的经济发展中,在传承“聂耳精神”“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中构建诚信道德的良好公共秩序。同时,昆明市五华区制定了《关于“党建引领、红色文创、爱党爱国”项目的实施方案》,以构建独具特色的党性教育品牌。五华区的长春小学作为聂耳的母校联合聂耳故居打造昆明市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建成“聂耳精神教育基地——壮志摇篮”主题景观与“聂耳文化走廊”两项文化设施。以聂耳故居为中心开展的各项主题文化活动,成为“聂耳精神”新时代的传承方式。
三、聂耳故居的文化实践
国家叙事语境下的名人故居是以“记忆”的方式来重塑历史。作为一种记忆性的理性活动,在“回忆过去”时,往往以现实社会的国家价值体系为取舍标准对历史人物及其事件去芜存菁。英国心理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认为,当我们回忆并重述一段历史故事时,我们是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心理构图”上重新建构这个故事。①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Remembering:AStudy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pp.199-202.意味着,我们所重塑的故事是基于叙事者心理倾向的意义生产。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正是国家话语体系中的一种文化实践,其所建构的是国家意义的“记忆之场”。一般而言,社会记忆是人类维系文化传承的基础,而任何一种社会记忆都是不断被重新建构的。②王晓葵:《记忆论与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第2期,第28—40页。这种重新建构的过程正是一个时代的文化之需,也是国家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实践之路。
聂耳故居的文化实践是一个生产的过程。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概念。人类生产包括三个层面:即物质生产(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人类自身的生产(种的繁衍)、精神生产(文化生活的需求)。这三种生产分别对应了“个人的生命的生产”、“他人生命的生产”、“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③李益蓀:《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研究》,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第96页。聂耳故居正是国家对个人生活史的再生产过程及结果,使之体现国家的意识形态。当地政府通过“生产”的概念将历史和时间统一到具体的空间中,以形成国家的意义生产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的文化空间。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④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asil BlackwellLtd,1991,p.26.用以说明文化空间是人类主体的有意识的活动产物。聂耳故居的空间生产具有历史性,它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实践、知识、概念的构造及其结果,并在社会的变迁中扮演着某种社会化的角色。聂耳故居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的文化生产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民族精神的建构,二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实践。
(一)聂耳故居的民族精神建构
1951年10月,国家文化部颁布了《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并提出博物馆是进行革命的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博物馆让人民大众正确认识历史,认识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⑤单霁翔:《关于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中国文化遗产》第1期,第6页,第8—25页。这为新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奠定了教育发展之路。不仅如此,早在1895年,世界最大博物馆机构的创始人詹姆士·史密森也强调,博物馆的使命在于研究其专题,并以此来教育人。⑥[美]乔治·埃利斯·博寇:《新博物馆学手册》,张云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因此,名人故居作为博物馆的一类,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纪念,而纪念是为了实现宣教的目的。
聂耳故居作为公立性质的纪念馆,采取的是地方文物行政部门的管理体制。这为聂耳故居的文化生产及其社会运作建立起了正当性基础。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以聂耳“人民音乐家”的形象为中心而展开,隐含着国家话语体系的“道德原则”,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国家叙事通过一个微观的人物史来表现宏观的革命服务精神,由此上升到中华民族精神的道德标准。而当地政府针对聂耳故居进行的故居修缮、文献查阅、民俗文物收集、口述史记录、专家论证等“输入”性的文化建构,才得以“生产”出具有爱国主义教育价值的文化空间。由此,聂耳故居在构建国家叙事主体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一种“会意空间”,以达成人民大众对国家叙事内容的理解。这一空间的叙事从聂耳的音乐之路到革命之路的发展过程,凝结出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的乐章—— 《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文化生产方式取材于人民大众耳熟能详的国歌,才得以将最为个人化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了公共叙事资源和公共话语的一部分。①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社会学研究》2018第2期,第164—188页,第245页。这是一个国家为弘扬民族精神,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必须具有的共同历史与文化基因。
(二)聂耳故居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文化实践
聂耳故居作为国家叙事的静态物象,在不同社会群体中构成多重话语的文化实践,从而共同指向聂耳及其精神的认同。“认同”一词源于心理学,由弗洛伊德最先提出,意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和心理上的趋同过程。②陈国验主编:《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认同具有社会性,它是形成文化互动的基础。国家重塑聂耳及其人物精神的文化空间,旨在形成具象化的民族精神符号,从而成为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信仰和情感的分享,以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在凝聚力。
与此同时,聂耳故居将不同的社会群体与事件以某种方式组合起来,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关系结构。作为云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聂耳故居不仅仅局限于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它还将这一文化空间扩展到游客的参与体验,民间的纪念活动,社团、组织的爱国主义精神宣讲,聂耳音乐作品的传唱等多元化的文化实践。这些多重话语便构成了差异性的叙事文本,以进一步丰富了聂耳故居国家叙事的内容。因此,聂耳故居和不同社会群体在共同的历史记忆“生产”中不断强化民间大众对聂耳及其人物精神的认同,以丰富时代的内涵。
四、结语
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的目的在于保护历史文物和弘扬民族精神,这是具有文化传承和凝聚民族共同体精神的双重意义的文化事业。实际上,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在于将个人生活史转化为国家层面的话语结构,以构建具有公共性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同时,个人的生活实践进入国家的话语体系中,表现为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的互构,呈现一种国家与个人的时空对话方式。
同时,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还应注重国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以形成一种交流式的文化实践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聂耳故居自我生存、发展的空间和环境,也才是文物保护和民族精神传承的最好方法。由此,国家话语体系中的聂耳故居的保护与利用,有助于将物质性的遗产转化成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以新的叙事方式实现新的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