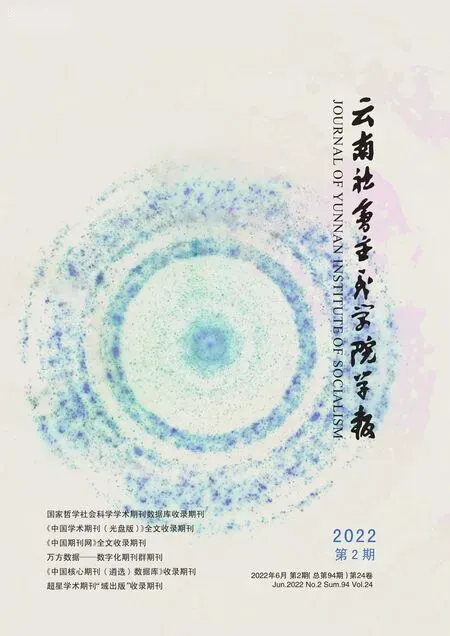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研究
马宜果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与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紧密相连。西南地区从秦汉时期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南地区的各民族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融入中华民族。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进程,是由以汉族形成的凝聚核心为外部动因、以西南民族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认同为内部动因以及经过秦汉时期历时性的长时段建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程,从地区、政治、文化等方面与各民族一同融入中华民族的发展构成,研究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路径、内生动力等问题对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秦汉历代王朝对西南的治理与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
秦统一全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分全国为36郡,在少数民族地区设道,于西南地区设置巴郡和蜀郡。西南地区是最早进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地区之一。公元前214年,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略定南方百越,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以适遣戍”①《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253页。,岭南地区正式纳入到秦王朝的统治。秦朝不仅向南扩张,还对西部地区进行延伸,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②《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2993页。《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3046页。秦朝在今滇东北及川西南部进行经略并曾设郡县进行管辖,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曾在僰道积薪烧崖以开成都县两江,疏通岷江并入长江的通道。“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檄。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①《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页。秦国曾沿民间小道修筑“五尺道”,经过秦国百年的建设发展,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且通过商贸的繁荣发展也带来了华夏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播,由此巴蜀地区的富饶也给汉朝灭秦提供物质支撑。秦末,萧何主张入蜀:“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②《汉书·萧何曹参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2006—2007页。刘邦听取萧何意见,进入巴蜀地区,之后巴蜀成为了刘邦平定中原的大后方,并为其征战中原提供了物质帮助。
西汉建立以后,对西南民族的治理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发展。自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至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先后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巂郡、益州郡,将大部分西南地区纳入统治范围。但由于西南地区的民族生计方式不同,有从事农业、游牧还有渔猎的民族,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所以,虽然汉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郡县,但是想要将中原地区的模式照搬到西南地区非常困难。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汉王朝在郡县制的体系下并行羁縻制度,“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9页。即保持西南地区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在依托汉朝派遣的汉族官吏管理的基础上,分封各部落首领为王侯,通过调度本地区的上层贵族,达到对西南地区的统治目的。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两百年间里,汉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巂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同时东汉王朝借助哀牢王率众内属的时机,在西汉经营的基础上设立永昌郡,并派遣了许多的汉族官吏进行管理,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将西南地区纳入到王朝体系中。《后汉书·百官志》载:“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④《后汉书·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3633页。从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分封层级来看,这些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正式地从体制上纳入到封建国家的政权体系中,部落首领经济上需要纳贡,政治上需要听从汉王朝的调遣,但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仍然保有原来的社会组织和自己的管理体系。虽然需要向汉王朝纳赋,从都尉郑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一斛,以为常赋”⑤《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第2851页。来看,西南地区相较于中原地区赋税较轻。
汉武帝最初开拓西南的原因是为了利用夜郎攻打南越,但当时“西南夷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⑥《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7页。并且正值“朔方以据河逐胡”,公孙弘与巴蜀百姓极力反对,汉武帝便放弃对西南夷地区的开拓活动。元狩年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建议“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遣王然宇等人“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开始第二次通西南夷。然后被滇王留下并帮助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最终被昆明王所阻。此行虽未达身毒国(即今天的印度),但与滇王建立联系,“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为西南夷的最终属蜀郡创造了条件。汉武帝在元鼎元封之际对西南夷全面发动战争的契机是,南越谋反时汉朝本欲发南夷兵攻打南越,而南夷人却趁机杀使者即犍为郡太守。于是,汉朝发兵击破南夷,后又破南越。南夷夜郎侯本倚仗南越,在此形势下只有入朝受封夜郎王。而滇国直到元封二年王然宇破南越入滇时才属蜀郡,置益州郡。至此,汉武帝才完成了在西南地区设郡置吏的统一大业,自此西南地区纳入到汉王朝的版图中,并且由官方承认西南地区的身份地位“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三月,益州、昆明反,汉武帝派遣拔胡将军郭昌还击昆明,《史记·大宛列传》载:“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①《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第3170页。从建元到元封经历三十多年,发动经略西南夷,设置郡县,纳入汉朝版图。
两汉对西南的移民屯田政策促使西南民族融入到王朝统治之下。汉王朝想要进一步经营西南地区,首要措施是修筑道路。“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②《史记·平淮书》,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1421页。但终因“数岁道不通”,开发南夷道后,又对西夷道进行开发,“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越南夷。”③《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3046—3047页。于是,通零关道,招徕西夷,豪民进入西南地区开垦必然大量汉民随之进入,汉族移民进入西南地区,直接开发了西南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具。牛耕、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和灌溉技术也相继传入。值得注意的是,汉武帝反复开拓西南的深层原因根植于自秦统一六国以来,在各族文化长期以来互相融入的基础上,以中原农耕型的周秦文化为基本模式向全国进行推广,农业生产是秦汉政权的根基,因此在秦汉王朝开拓领土之前首要考虑因素就是当地的农业条件是否可以生产足够养活当地居民的粮食,这成为了秦汉及以后历代王朝开拓经营的标准。④葛剑雄:《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兼论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虽然羁縻政策使得西南地区各民族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但是汉民族与西南民族共同开发建设西南地区这是不争的事实。王莽时期,益州郡太守文齐在任犍为南部都尉时“造起陂池,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增加粮食产量,“降集群夷,甚得其和”⑤《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46页。。文齐为益州太守时,在益州郡历经天凤至地皇年间的战事之后,依托汉初以来的屯守政策,召集这部分汉人进行农业生产开发,这部分汉人中包括了派遣至西南地区的官吏、原先的屯户、一些散兵和遣而未归的士卒,将他们结合到一起,重新建立统治基础。为了开发生产,大量制造先进的生产工具,并且“降集群夷”,让当地的部族加入到生产活动中,太守文齐与当地民族共同建设西南地区,也为其后抵抗公孙述提供后备力量。与文齐同时期的牂牁郡郡吏谢暹也团结当地夷帅及汉族大姓共同抵御公孙述的割据,与东汉保持臣属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 “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功曹谢暹保境为汉。”⑥《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45页。大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享有朝廷承认的权力,在西汉末年时已形成大姓势力,谢暹在任期间团结地方大姓势力并且对公孙述的侵扰进行抵御。这些与内地类似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在西南地区施行,使得汉文化在西南夷地区传播,处在交通沿线的民族逐步接受汉族先进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与此同时西南民族的思想观念也受到影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上层开始了汉化进程。
东汉桓帝时,牂牁郡任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仪,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西南地区文化事业由此开启,到汉章帝时汉文化的传播更深入到滇中的大部分地区,王追为蜀郡太守期间“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在南中地区建立学校,以其诚信的作风,治理教化的并行信服当地夷人,“蛮夷犷悍,不知礼义,喜即从服,少拂意称兵相向,迄无定岁,非儒教不克驯之。而自汉置郡以来,为政者沿习夷俗,故滇人犹未知书。今王追实开其始”。滇人尹珍从汝南许慎学成归还乡里,并“劝谕蛮夷,昌兴诗礼”,对此明人诸葛元声按语:“滇人之从儒教,自叶榆张叔学于司马相如,归授乡人……今尹道真学于许、应二公,传授乡里。况有太守如王追者劝学兴礼……以故文治彬彬,家弦歌,户诵读,人人衣冠礼让,喜谈先王。”①[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47—60页。以少数民族的代表和汉王朝的官吏两者对汉文化的传播施教,使得西南地区的文化得到进步,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明也逐渐与中原汉文化融合。可以看出,汉王朝对于融入到其封建国家统治体系的西南民族社会并未强制要求其与内地施行同样的社会制度,也没有要求立刻接受其文明,而从承认王朝的主权开始,在民族社会中建立象征中央王朝的统治权,并且中央王朝承认地方上层统治的权利,来实行间接统治。这样的观念促使周边民族集团主动融入到中华民族之中,在中央王朝占主导地位的时期里,这样的方式既可以维护王朝统治的稳固,还可以使周边民族集团的利益受到保护,保障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性。在这些正面政治措施的影响下,众多边民对地方官员民族政策执行表示认同,对有利于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的汉族官员尊敬认同,“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②《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51页。,并主动表现出归属的愿望,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③《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54—2855页。
总体来说,秦汉王朝在西南地区开拓与设置郡县等客观举措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内地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同时拓展了封建王朝统治的版图,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对西南民族来说,纳入到封建王朝统治当中有利于本地区的开发,同时在内地的经济文化影响之下,边疆民族可以较快地走上封建化的道路。从以上的分析来看,西南各民族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西南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统治者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略,因此在西南民族融入到秦汉王朝统治的过程中,许多西南民族发展出与自身生态、经济背景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秦汉时期出现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局面正是来源于内地与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各民族内部独立发展的同时,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生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对中央王朝具有强烈的向心力。④王文光等:《中国西南民族通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页。
二、秦汉时期西南民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内生动力
《史记》《汉书》《后汉书》既记载了作为华夏典范的两汉王朝的历史,而且它们的史学撰述方法本身也成为后世修史的典范。正是这种对异族渊源的叙述手法,不仅在华夏知识世界建立起复杂的夷狄谱系树,而且最终影响了非华夏族群对自身历史的认知,以及他们借以凝聚族群的认同方向。⑤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9页。《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⑥《汉书·百官公卿表 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742页。边疆郡县称为道,以道作为周边民族的行政区单位。当边疆民族集团内属王朝以后,其集团的首领从王朝得到官位,获得官方认同,成为王朝臣民的一分子,那么该集团首领所辖民众向王朝纳赋,其原本的政治领土成为王朝版图的一部分。“至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7年),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蛮夷王侯,王侯受诏,已复相攻,轻易汉使,不惮国威,其效可见。”⑦《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3843—3844页。在此之前,汉武帝时期“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入朝”⑧《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66页。,并且受封夜郎王,也就表明西南少数民族进入到郡县制度的统治后,少数民族集团首领受封为王的同时,该地区具有了双重身份。主动归附内属意味着认同,汉王朝采用的是一种通过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集团首领间接统治的方式,给予了当地的上层统治阶层相当大的权力,但王朝始终持有对郡县管辖的实权,形成了政治制度上的双轨制。
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哀牢王贤粟攻打鹿茤,但遇“震雷疾雨,南风飘起,水为逆流,翻涌二百余里,箪船沉没,哀牢之众,溺死数千人。……中国其有圣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①《后汉书·南蛮西夷列传》,第2848—2857页。于是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 “贤粟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巂太守郑鸿降,请内属。光武封贤粟等为君长。自是岁来朝贡”,哀牢王内属汉王朝后,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并置哀牢、博南,割益州郡西部都尉统领六县,合为永昌郡。至永元六年(公元94年),永昌郡外孰忍乙王莫延感慕汉义,“遣使译献犀牛、大象”,永元九年(公元97年),“永昌郡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昌郡的设立,将今天云南省西南部在公元69年纳入了东汉王朝的版图,永昌郡内的民族与境外的民族大多属同一民族,其境内外民族的联系交往也促进了东汉王朝与境外民族的交往。元初三年(公元116年),越巂郡外夷大羊等同样“慕义内属”,正值郡县“赋敛烦数”。元初四年,永昌、益州及蜀郡的夷人皆起反叛,攻坏二十余县,杀长吏,侵掠百姓,益州刺史张乔率杨竦大战封离并取胜,并且将侵犯蛮夷的九十名长吏上奏处置,此后张翕之子张湍继为太守,“夷人欢喜,奉迎道路”。永平年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在任期间宣教汉朝德化,在西南地区颇有盛名。汶山郡以西的地区未曾与汉王朝交流,但该地区的民族,如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举种奉贡,称为臣仆”,朱辅向汉王朝上奏这些部落向汉朝进歌三首,表达对汉朝的慕化归义,“蛮夷所处……慕义向化……不远万里,去俗归德,心归慈母”,“吏译传风,大汉安乐,……传告种人,长愿臣仆”。建武初年,白马氐隗嚣族人隗茂叛乱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钟留与郡丞孔奋共同击杀隗茂,之后时有为寇之人,郡县内都协同作战。可见在西南夷地区,不同的民族群体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接触,为了获取土地或资源,他们彼此之间既战争又联合、通婚,民族融合自然发生,西南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
西南民族对汉王朝的认同不仅仅体现在对汉王朝正统性的拥护,还体现在对汉文化以及其汉朝臣民身份的认同。诸葛元声《滇史》记载:“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滇王献白雉于朝。时王莽窃柄,潜移汉祚……然滇久置郡邑,立汉官,又何重译哉?如此举动通朝附和,恬不知耻,反为远夷所笑。未几莽篡汉而益州蛮夷终不肯服从,宜矣!”②[明]诸葛元声撰,刘亚朝校点:《滇史》,第47—60页。时值王莽篡政,意图利用滇王诈称越裳氏献雉,以“白雉之瑞”来证明自己的功德高尚比肩周公,但“滇久置郡邑,立汉官”又何来“重译”之说,反而成为了“远夷”所不齿的闹剧。汉承秦制以来,原本受秦所封或者纳入到统治势力范围内的西南地区都已独立,汉朝建立之初与各国关系不紧密,还属于“外臣”的范围,直到派遣使节从西夷西出寻找通往身毒国的道路,经过滇国后返回朝廷复命才使得汉朝统治者注意到滇国,也才有了之后开拓经营西南地区的史事。汉王朝对待“外臣”之国的做法是,在承认其统治者的王位并保护它不受外来侵略的同时,要求它“称臣”“奉贡职”“遣使入朝”,汉王朝所规定与外臣之间的关系,虽带有君臣关系的性质,但并非是单向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同时规定了双方相互具有义务的关系。③[日]王柯: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6页。如在《史记·南越列传》记载,“愿长为藩臣,奉贡职”“称臣,使人朝请”“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①《史记·南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970页。与西南地区不同,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发兵击灭劳浸、靡莫,到滇国时“滇王始首善……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印,复长其民”②《史记·西南夷列传》,第2997页。。王莽建国四年(公元12年),西南夷杀牂牁大尹,“更易汉制曰‘汉氏诸侯或称王,四夷亦如此,违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王号有皆更为侯’”,使得句町王王邯怨恨,形成了“三边蛮夷愁扰尽反”的局面,至天凤元年(公元14年),滇王再次击杀益州尹程隆,王莽派遣平蛮将军冯茂攻打益州,滇王率诸蛮大败冯茂,三年后,王莽发兵攻打夜郎蛮但未攻克,激发了西南地区的周边兄弟民族的不满情绪,于建武三年(公元27年),西南地区的豪杰以诛王莽为名号奋起反抗。王莽时期,西南民族成为了与“华”对立的“夷”,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西南民族进行压迫并且不承认西南民族与中原民族的共存性,激发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情绪,而西南民族的上层统治者对于自身以及中央王朝的身份互认业已形成,西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早已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自汉族形成之后,其凝聚力向周围各族辐射,促使各族人民与汉民族从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融入,并且形成了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华民族实体。
中国最初的民族思想,是以生活、生产方式为基础形成的文明方式。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对于西南地区人群的记述来看,其实质是内地对于周边民族的认识和概括,称这些民族集团为“蛮”“夷”是从其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划分,本身不存在歧视含义。并且,中国所具有的多民族性质和中华民族本身的多民族来源共同组成了多民族共存的中华民族实体,众多的部族和民族集团通过“华夏化”形成了一个文明共同体。秦朝采取了众多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措施,如大规模地移民实边,行郡县制度,统一文字等方面,重新整合成了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文字、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在这四个要素下,各民族间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并在实际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形成了物质到精神的转换,产生共同的意识,西南民族融入到中华民族并共同生活,都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产者之一。西南民族与中华民族相互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民族来源当中的一元,具有共同的利益安危,强烈的体认感情意识,西南民族与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一致,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体认,使其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的符号。
三、小结
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结束了华夏族的分裂状态,加强了其内部各方面的联系。虽然国家与民族是不同的社会范畴,有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两者在发展过程中是紧密相连的。国家政治的统一和因此带来的民族内部联系的加强,对民族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秦汉政治的统一,使华夏族(汉族)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逐步趋于平衡,从而也就加强了经济生活的一致性。在民族意识上,汉族的观念日益增强,特别是在与其他民族的关系中,这种共同的观念,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③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自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纳入到中央王朝的统治后,西南民族开始与中华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的祖国、共同开拓了祖国疆域、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共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