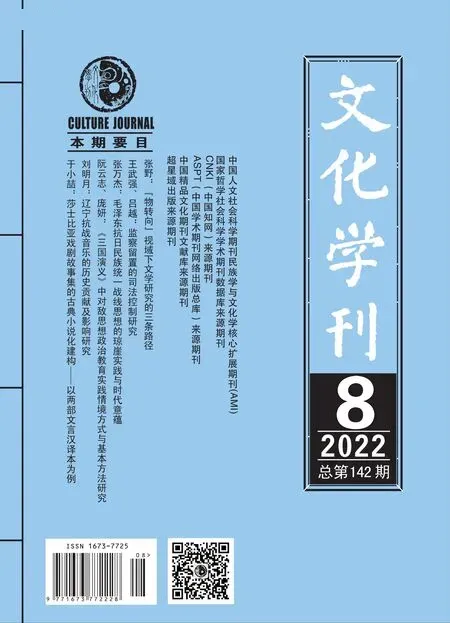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女性独立走向失败的原因
王姣姣
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被看作是“理解美国文学传统的核心”[1]。这部作品以其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爵士时代的喧嚣与浮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各国的研究学者从各种批评理论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解读,比较常见的为心理分析、叙事理论、结构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在女性主义分析中,主要聚焦当时社会对现代女性产生的厌女心态,以及在男权社会下,作为附属的女性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不得不依靠男性的无奈境况。本文依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研究小说中三位女主人公是如何在新时代的舞台上演绎新女性的角色,并探索新女性的觉醒之路到底应该如何前行。
一、沫特尔——为了“爱情”,背叛婚姻
处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下层阶级的沫特尔的主要身份是情人,而不是一个妻子。确切地说,她更认可自己是汤姆·布坎南的情妇这个身份。谈及丈夫的时候,沫特尔是鄙夷的,不爱丈夫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结婚的礼服都是跟别人借的”[2]35。而爱上汤姆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对方身着打扮是上层阶级的样子。由此可见,沫特尔进入婚姻和背叛婚姻的本质原因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只是她并没有靠美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勤劳和诚实的品质为自己谋求想要的生活,而是想通过婚姻和男人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当她发现婚姻并没有带来她想要的生活和财富后,她抓住机会,义无反顾背叛了婚姻。为了合理化她的行为,她不断对自己说“人生苦短”[2]36。
看似沫特尔在主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在新时代的熏陶下表现出大胆、无畏的特质,但事实上,她恰恰是因为懒惰而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又因为虚荣造成了婚姻的不幸,更是因为贪得无厌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哪怕获得了布坎南一时的关注,得到了金钱和激情带来的短暂的快乐,但也牺牲了沫特尔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当她展现出对黛西的嫉妒,大声在布坎南面前叫她的名字时,得到的是一记恶狠狠的耳光。连沫特尔鄙夷的丈夫,都可以随时把她控制在屋内,不准她外出。沫特尔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一个上流社会的玩物。在婚姻中,她得不到想要的丈夫的温情,在婚姻外也得不到情人的尊重。她对命运的反抗就像她的结局那样,注定是惨烈的。
二、乔丹——建立在欺骗上的独立和自由
乔丹是菲茨杰拉德塑造的一位具有男性特色的女性角色。首先乔丹的名字是男性化的体现,其次,小说中提到“她是个苗条的平胸少女,昂首挺胸地站着,姿势很像年轻的军校学生”[2]13,以及“她穿晚礼服,无论什么衣服,都像穿运动服”[2]49。桑德森指出,菲茨杰拉德对待新时代的时尚女性反映了现代主义中传统男性面对流行化的女性形象时的态度:菲氏作品中的女性有着雌雄同体的表现[1]178。乔丹是小说里唯一一个靠自己的能力混迹在上流社会的女性。乔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性,不仅靠自己养活自己,还曾获得高尔夫球赛的冠军,而她真正的愿想是成为上流社会中的一员。所以当黛西想和她说话的时候,她感到“受宠若惊”[2]72,因为她从小就非常崇拜黛西。事实上乔丹真正崇拜的是黛西作为上流社会的身份,以及这种身份所加持的光环带来的罗曼蒂克。在告诉尼克盖茨比和黛西的过去时,她提到“那军官如痴如醉地看着她,每个女孩儿都希望有人这样仰慕自己。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罗曼蒂克的”[2]72。乔丹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菲茨杰拉德对新时代女性的理解:敢于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及想要属于自己罗曼蒂克般的爱情。这样的乔丹在令人感到敬佩的同时,也有着属于她的独特魅力。以至于尼克有她的陪伴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原因是“因为她拿过高尔夫球赛冠军”[2]55,乔丹也是小说中唯一一位因为自己的成就而令他人刮目相看的角色。如果这是乔丹的所有故事的话,那么除了性情冷漠,偶尔撒谎以外,这个独立女性的角色似乎无可指摘。但事实是乔丹曾在高尔夫球大奖赛中做过手脚。而喜欢尼克的原因也是因为她认为跟尼克这样诚实的人在一起并不会受到束缚。而作者对现代女性的偏见也在尼克的自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不诚实得不可救药。她无法忍受落人下风,我想正是由于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导致她从小就学会了各种骗人的花招,这样她才能对世人摆出冷漠而倨傲的笑脸,却还能满足她那漂亮结实的身体的各种需求”[2]56。
如果说乔丹的冷漠、不诚信、不诚实是菲茨杰拉德对新时代女性表达的不满,那么乔丹事业中的投机取巧、感情中的锱铢必较,充分地显示了她独立外表下的羸弱和安全感的缺失。尼克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后,乔丹很快声称自己已经订婚了。这种不甘示弱的态度夹杂着对恋爱对象的情感报复看似倔强,但其实只是用逞强来掩盖内心的受伤。乔丹努力通过自己的努力挤入上流社会,但因为破坏规则而受人诟病;想要寻找一个诚实可靠的男人,却因为自己的不诚实而被甩。独立强大的乔丹到最后也只能在上流社会的边缘游走,在情感失意中落寞。新时代女性所追求的独立和自由在乔丹的事业感情失意中宣告失败。
三、黛西——充满诱惑之路
黛西最鲜明的特色就是跟随着自身的欲望去思考和行动。出身显贵的她和盖茨比陷入爱河时并没有考虑到他们之间门不当户不对的问题,爱上了就沉溺其中。但当盖茨比离去,她又感受到了精神的空虚。金钱或者爱情,她必须拥有一样,或者更好,两者兼得,这不仅反映了她精神的虚无,更体现了她本性的贪婪。黛西就像无根浮萍,不知道何去何从,像一个寄生虫,必须在宿主上才能生存。从本质上来讲,黛西和沫特尔是一样的,她们都贪婪、虚荣、自私,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不同的是,见多识广的黛西来自上层阶级,拥有与生俱来的金钱和地位优势,再加上美丽的皮囊和充满魅力的声音,她可以用外表的光鲜去遮掩内在的龌龊,也能在撞死人后,轻易脱罪,逃之夭夭。黛西当然爱过盖茨比,否则不会在嫁给布坎南的前夜醉得不成样子,要归还价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项链,但黛西的爱就像六月的天那样,说变就变。她在和汤姆·布坎南度蜜月的那段时间就爱上了他,确切地说,是依恋。“如果他有片刻不在房间里,黛西就会心绪不宁地到处找,并说:‘汤姆去哪里了啊?’而且会满脸失魂落魄的神色,直到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2]74。黛西对布坎南的依附还表现在婚姻中的隐忍上。她明知丈夫已经背叛了自己,依然选择息事宁人,可见婚姻的忠诚对她而言不是必不可少的,这也可以解释当盖茨比再次出现后,她毫不纠结地选择了再续前缘。稳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才是黛西最在乎的,其他都可以妥协。盖茨比对于黛西来说,只是无聊婚姻的消遣,也掺杂对布坎南婚内不忠的报复。
黛西深情得让人无法抗拒,也冷漠得令人措手不及。黛西象征着她所处的势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轻歌曼舞尽日不息,声色犬马终年无休”[2]146,也只有这样的纸醉金迷的世界能够暂时吸引黛西的注意力,给她短暂的活力。她无法长久地等待爱人,也不能为了一晌贪欢抛弃现有的地位。她深知自己无力改变这个世界,于是面对不忠的伴侣,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面对昔日爱人,选择及时行乐;面对自己的女儿,她希望对方是个“美丽的小傻瓜”[2]19。黛西不仅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还合理化了这种论调。哪怕她从头到尾都是新女性的装扮,但却自动放弃了主动去创造生活的力量,沦为了周围环境的囚徒。波伏娃指出,女人命运时刻受着选择更容易走的道路的诱惑,她从来不被鼓励要像男人一样披荆斩棘走自己的路,而是被告诉要放弃自己的力量,去接受命运的安排,就能获得想要的快乐。当她醒悟过来后,一切已经晚了,她已经在圈养中彻底失去独自行走的力量[3]。被耗尽力量的黛西披着新时代女性的外壳,如行尸走肉般继续前行。
四、盖茨比——“了不起”中的局限
盖茨比无疑是整部小说的核心人物,他出身贫苦家庭,靠着自律和异于常人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混迹于上流社会。只是哪怕是整个小说中对爱情最执着的人,也很难说他是女性真正的拥护者。诚然,盖茨比对黛西的感情无疑是真挚的。哪怕已经过去五年,他对黛西的感情依旧如故,为了见黛西,他不惜重金租下黛西家对面的公馆,夜夜笙歌,只是为了有一天黛西能够光临他为她准备的城堡;煞费苦心地接近尼克,只是为了能够见黛西一面;在黛西撞死了人之后,他没有选择为自己争辩,而是代替黛西承担了命案,一心只想和黛西远走高飞。但事实上,他的这些行为与其说是对爱情的执着,不如说是对黛西所代表的那个阶层的向往,更是一种对梦想一致性的强迫性追求。当他在分离五年后再次见到了黛西,和其相处一下午后,就已经知道一切都已经变了。他知道黛西是一个声音“充满了金钱”[2]116的拜金主义者,也了解黛西事实上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完美。哪怕梦想已经呈现出令人失望的原形,盖茨比依然要自欺欺人,竭力配合自己的虚妄,让一切朝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这也体现出了他另一个致命的缺陷——一意孤行的偏执。财富和周围人的崇拜让原本清醒的盖茨比也失去了对自我的正确认知,觉得自己可以实现一切梦想,这一点从他对黛西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想见黛西,请求尼克为他们安排“偶遇”[2]77,根本不管黛西是否同样也想见他,因为他“不想让她知道”[2]78;当他终于如愿见到了黛西,相处之后,他又开始苦恼,觉得他很难让对方明白他的想法,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让黛西对布坎南说不爱他,并要求黛西和自己远走高飞。盖茨比一直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他爱的是代表着上流社会的奢华和财富的黛西,而不是浅薄无知、拜金虚伪的个体。盖茨比的自我从他对待其他女人的方式也可以看出:“这些女人很宠爱他,反倒惹他看不起,因为年轻的少女太无知,成熟的女人则常常因为他做了某事变得歇斯底里——而在只顾自己感受的他来看,他做哪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正是盖茨比的这种自我英雄主义蒙蔽了他看清现实的双眼,同时他也没有把黛西当作一个和他平等的个体去对待,对他来说,黛西是他要实现的梦想,得不到黛西就是追梦的失败,结果他看不到黛西作为一个人的需要,否定了黛西的自由意志,最终只能得到一个破碎了的梦。
五、尼克——不公平的讲述者
作为讲述着,尼克从一开始就竭力证明自己是公正的。他说道:“不去评判别人就是对别人怀有无限的希望”[2]5。然而之后他又强调“我的宽厚也有个限度”“一旦过分到某种程度,我也就不管背后的原因了”[2]5。事实上,尼克从故事的开始,就已经不断在评判了。到了纽约拜访了黛西后,就认为她应该抱着自己的孩子逃离自己的生活;当知道乔丹在比赛中作弊后,就给对方贴上 “不诚实得无可救药”[2]56的标签;在最后一次见盖茨比的时候,更是否定了除了盖茨比以外的所有人。小说中处处充斥着尼克对黛西和布坎南一类人的厌恶和鄙夷,连同在他们身边的乔丹也毫无例外最终被尼克排斥。感情上,尼克在来纽约前已经有一位女朋友,但仍然和乔丹暧昧不清;想置身事外,成为一个时代的局外人,但也享受这个城市的纸醉金迷。尼克这个角色充满了矛盾,正是他的偏见和言行不一,减少了他对小说中女性的批判的权威性。他和盖茨比的亲密友谊可以说一部分是基于对黛西所代表的女性的偏见。他认为黛西拜金,乔丹虚伪,几乎没有什么优秀品质可言。相反,在描写汤姆——自大无知的婚姻背叛者时,他突出了汤姆在处理情人沫特尔被撞死一事表现出来的镇定和克制,以及后来冷静地和黛西一同商定计划嫁祸给盖茨比的思维清晰。两者相比,尼克对新时代女性的不满一目了然。
六、结语
进入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时代的美国就像获得新世界入场券的年轻人,对一切新奇的事物都跃跃欲试,在纸醉金迷和物欲横流中错把金钱和权力当作幸福的目的地,而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女性的力量开始复苏,但远远还不够。处在上流社会的黛西精神空虚、缺乏意志力,渴望罗曼蒂克的爱情,但却最终纶为他人巩固财富地位的手段,也失去了真正的爱情;处在底层的沫特尔妄想通过婚姻获得财富,失望落空后,又和汤姆纠缠在一起,企图实现阶级跳跃,最终以死亡告终;乔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自己的路,也选择了看起来实诚的尼克作为伴侣,但也因比赛中的作弊而受到指责,也在没有做错什么的前提下被男友甩了。这三位女性角色都意识到了自己的渴望,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去追寻想要的东西,不管是爱情,阶级跨越,还是成功的事业,但她们的追求手段要么是通过婚姻和男人,要么是在比赛中做手脚,既不勇敢,也不诚实。她们只想享受新时代下女性获得的特权,却没有想过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自己的现状,甚至她们中的大部分还是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到他人身上,当发现是一场徒劳后,要么飞蛾扑火,要么完全放弃反抗,沦为他人意志的阶下囚。她们只有意识到想要拥有多大的自由和权力,就要付出相应的责任,才能真正收获属于她们的幸福。同时,女性真正的觉醒不仅仅要靠个人去努力,更需要时代的推波助澜,也需要男性放下对女性特质的偏见,开始关注女性的成就而非历史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女性想要平等地和男性对话,需要完全放弃自己的依附心理,把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才能真正开始自我追寻之路,而这一切的改变,虽然漫长,但却是女性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