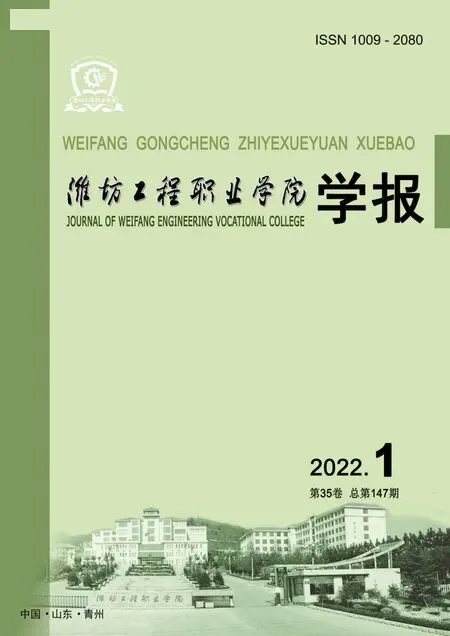日本学者下定雅弘的《长恨歌》研究
朱 霞,邱美琼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昆明 650500)
下定雅弘(1947-),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文学博士,现为冈山大学名誉教授,专攻中国六朝文学和唐诗,在各大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出版著作《白乐天的世界》《中唐文学研究论集》等,是海外汉学的重要学者。在下定雅弘的中国古典诗学研究中,白居易研究占据了非常大的部分,而作为白居易的代表作的《长恨歌》自然也成为下定雅弘重点涉猎的部分。下定雅弘的《长恨歌》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长恨歌》主题的探讨,对《长恨歌》与《李夫人》的比较,对《长恨歌》《长恨歌传》、《长恨歌序》关系的讨论等方面,通过文本细读,作品比较,历史回溯等方法,对《长恨歌》的深层内核进行追问与思考。
一、《长恨歌》主题的探讨
《长恨歌》主题的探讨一直是国内外热议的话题,关于《长恨歌》的主题,中国学术界一般有三种解释:一为讽喻说,二是爱情说,三是双重意蕴说。近年来还另外出现了一些别的解释,但大致绕不开这三个观点。
下定雅弘也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研究现状,他指出:“中国的讽喻说有着很强的理论基础,在漫长的世间内(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中国以政治作为基准来思考文艺作品价值的传统,便有这方面的影响。”[1](P81)总体来说,讽喻说都是中国学术界占据优势地位的一种观点,讽喻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寅恪、张中宇等。诗的讽喻功能自古至今都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从孔子“兴观群怨”之说到新中国建立以来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政治一直是考量艺术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而一部描写玄宗皇帝沉迷女色疏于朝政导致王朝衰败故事的《长恨歌》自然被当作劝谏君王,讽刺政治的最佳代表。此外,陈鸿的《长恨歌传》一般被学者界用来作为“讽喻说”的最有力证据,《长恨歌传》末端“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2](P238),近人陈寅恪先生指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3](P45)“惩尤物,窒乱阶”便一直被看作是《长恨歌》的主题。最后,《长恨歌》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的诗句与主张“首句标其目”的新乐府诗歌不谋而合,于是这便成为“讽喻说”成立的又一有力证据,支撑着“讽喻说”成为今天中国学术界关于《长恨歌》主题最重要的解释。
但在日本学术界,情况却大有不同,《长恨歌》的主题的解释似乎没有那么复杂,下定雅弘在《白乐天的世界》一书中指出“在战后日本学者受到中国议论的影响也有赞成讽喻说的人,但最近认为是‘爱情’的主题成为了日本学术界的共同理解”[1](P81),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近藤春雄在《论长恨歌》一文中认为,《长恨歌》吟咏的是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世界,其主题是玄宗思慕贵妃而悲伤谢世的长恨[1](P81),丸山清子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以悲剧告终的爱情,是对“失去的爱情”所抱的长恨;西村富美子的《长恨歌管见》认为白居易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类,表明他作《长恨歌》的目的不在于讽喻[1](P85)。近藤春雄、丸山清子、西村富美子都是日本研究白居易的重要学者,在日本主张“爱情说”几乎占据了主导。
在著作《白乐天的世界》一书中,下定雅弘用了很大的篇幅对《长恨歌》主题进行分析。首先,下定雅弘和多数日本学者一样,主张“爱情说”,但他所主张的爱情,又不仅仅是单纯的男女之情,而是“吟咏玄宗皇帝对杨贵妃的爱之深和失去贵妃的痛之切”,他将这种爱情,提高到整个人类精神的高度,指出这种爱情,是“人类整体所不能脱离的深刻而有力的宣言”[1](P81)。之后,下定雅弘对《长恨歌》进行了分段式的分析,他将《长恨歌》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到“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歌颂的是人间世界中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后半部分“临邛方士鸿都客,能以精魂致魂魄”到最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讲述的是玄宗派遣方士至仙界寻找贵妃未果最终郁郁而终的故事。通过对整篇文章的把握,下定雅弘对全诗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
正如第1、2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和第15、16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第19句—32句“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下足”所说,如果只看这些内容,玄宗沉溺女色疏于朝政而招至唐王朝的衰败是应该被批判的,但是,这其中的每一句都必须放在特定的文学脉络中,上面《长恨歌》的各段表现了什么内容,其中的叙述已有表明,这些句子都是玄宗宠爱贵妃,为表现玄宗成为爱情之虏段落中的句子,不是对政治和玄宗的批判[1](P86)。
在这一段论述中,下定雅弘用了“如果……但是……”这组具有递进意义的关联词来表现他的情感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在下定雅弘看来,看似在批判玄宗的诗句,其实应该结合整体的文本,而体会出表现伟大爱情的主题,而不是对玄宗的批判。下定雅弘在以一个异邦人的身份打量《长恨歌》主题的时候,没有受到中国长期以来的政治影响,而是深耕于文本之中,以最真挚的感情考察作品,蕴含丰富,为海内外的学者提供了思路,颇有引导后学之功书。
二、对《长恨歌》与《李夫人》的比较
《李夫人》是白居易收录在《新乐府》中的一首杂言诗,因为同为描写君王宠爱妃子而误国的事件而常常被拿来和《长恨歌》放在一起作对比,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早有阐述“盖此篇可以《长恨歌》著者自撰之笺注视之,而今世之知此义者不多矣”,谈《长恨歌》而不谈《李夫人》,未免得鱼忘筌。下定雅弘也充分重视到《李夫人》的研究价值,他认为将《李夫人》和《长恨歌》的异同进行比较研究,是明确《长恨歌》主题的重要资料,然而,实际上,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就作品的主题与其表现进行比较也并不多,这就是一件十分值得惋惜的事情了。
在日本,新间一美在其《论源氏物语的结局——长恨歌与李夫人》一文中,从物语构成的视点进行比较,认为《长恨歌》由于有方士与贵妃的对话以及“失去所爱女性之悲的男性立场”和“在仙界思念下届的女性立场”的对话的存在作为最大的不同与《李夫人》而区别开来[1](P87)。另外,矢羽野隆在其《长恨歌》的主题和构成——《李夫人》与悼亡诗的比较研究中,对《长恨歌》和《李夫人》两种不同的“恨”的原因进行比较和研究,揭示《长恨歌》中的“恨”是一种男性普遍的痛恨[1](P87)。
在中国,这样的比较研究也不是很多,关于《李夫人》更多的研究还是把它放在汉武帝的那段历史中作为文献进行研究,偶有几篇论文和专著进行了专门的比较,金性尧在《炉边诗话》一书中将“杨贵妃”与“李夫人”两位提出来进行创作上的比较,认为《李夫人》作于《长恨歌》之后,是为《长恨歌》之补充,但金性尧显然是讽喻说的支持者,所以这种比较不如说是一种辅证讽喻说的工具罢了[4](P87)。另外,林雪娇在《长恨歌与李夫人的对比研究》一文中,从创作背景、故事主人公、内容、主题、艺术特征几个方面对《李夫人》和《长恨歌》进行了全面的比较,颇有借鉴价值[5]。
综上所述,《长恨歌》与《李夫人》两个作品之间的比较是十分有必要的,下定雅弘充分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下定雅弘发扬了日本学者一贯对待学术严谨踏实的态度,首先对《李夫人》一诗也进行了全篇的阅读和分析,其次对于序言中的“鉴嬖惑也”,下定雅弘也做出了解释,他联系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的新乐府序,认为《李夫人》的创作目的正是对君王、大臣、老百姓“不可接近美女”的警示。其后,下定雅弘几乎是一边逐句解释一边与《长恨歌》进行比较,最后下定雅弘得出结论:《长恨歌》所表达的,是一位挚爱女人的男人的真实深切之悲,这与《李夫人》一诗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有根本不同[1](P92)。在下定雅弘眼中,《长恨歌》与《李夫人》的主题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他认为《长恨歌》的主题是歌颂爱情,李夫人的主题是讽喻,而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李夫人》中常用的“苦”“惑”等词语,这便把《李夫人》和《长恨歌》有力地区分开来。并且从诗歌内容的角度来讲,白居易诗歌讽喻诗的主旨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但《长恨歌》的结尾“长恨”却只是表达爱而不得的痛苦而非唐玄宗的昏庸无道,这与《李夫人》中“尤物惑人忘不得”显然是不同的,明白了这一点,《长恨歌》与《李夫人》的不同自然是不言而喻了。下定雅弘创造性地将两首诗歌放在一起进行把握和比较,不仅填充了两个作品比较研究的空白残缺,更为下定雅弘论证《长恨歌》爱情主题说又提供了一项有利的依据。
三、对同题材作品《长恨歌》、《长恨歌传》、《长恨歌序》关系的探讨
下定雅弘的《长恨歌》研究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便是对于同题材作品《长恨歌》《长恨歌传》《长恨歌序》之间的讨论,为了方便,下定雅弘在这部分研究中将《长恨歌》简称为《歌》,《长恨歌传》简称为《传》,《长恨歌序》简称为《序》,笔者在这部分内容中也沿用,以求行文的简洁。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这首诗是白居易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故事而创作的。根据陈鸿《长恨歌传》结尾“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所云可知,《传》作于《歌》之后,《传》的前半部分主要叙述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故事,后半部分叙述方士到仙界寻找贵妃的故事,内容与《歌》相似,但《传》明显批判了玄宗对贵妃的过分宠爱,批判性与讽刺性很强。“传”一般有注释、传记之意,所以《传》一般被看作是《歌》的注释之作,被当作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歌传结合,而被众多学者所研究。
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唐人小说例以二人合成之,一人用散文作传,一人以歌行咏其事,如陈鸿作《长恨歌传》,白居易作《长恨歌》,元稹作《莺莺传》,李绅作《莺莺歌》,白行简作《李娃传》,元稹作《李娃行》。白行简作《崔徽传》,元稹作《崔徽歌》,此唐代小说体例之原则也”,他这样评价这种现象“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那么,《歌》与《传》真如陈寅恪所说“不可分离吗”[3](P44),也有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陈寅恪发表这篇文章不久,夏承焘先生就发表了《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文章对于歌传一体提出质疑,最终得出结论:《歌》与《传》之可以分离独立,此即为最自然、最了当之解答。元和间人虽好为小说,然白氏此《歌》,只是一篇故事诗而已。陈君必牵率以入小说之林,又强绳以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过深,反成失实,是亦不可以乎?[6](P178)此外,周相录先生在《〈长恨歌〉研究》一书中,也得出“歌、传一体之说,诚不可取”的结论[7](P57),这些论证都说明,“歌传一体”的观点值得质疑,那么,下定雅弘是怎样看待《歌》与《传》之间的关系呢?
在《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一文中,下定雅弘明显表示出《传》因为其极具批判性的结尾成为《歌》主题是批判君王沉迷女色的最大证据,然而,《歌》的主题却没必要按照《传》来描写。主题不同是《歌》与《传》最大的区别。作者创作出与陈鸿《传》同素材,异主题的作品,使《传》能在爱情诗开始发展的唐朝能起到一种缓冲的作用,读者再读《歌》时,就相对更加容易接受,当然这种想法是基于《传》是《白氏文集》卷十二的版本之上的,关于《传》的版本,下定雅弘引日本竹村则行先生的观点,也就是认为《传》目前有三个版本,原收录在《文苑英华》卷七百九十四附载的《丽情集》经白居易修改作为自己的作品放在《白氏文集》卷十二中,既是白居易自己承认的作品,下定雅弘依据此前提进行推理,并不是没有证据和道理。《传》承担了讽喻的功能,而《歌》没必要按照《传》的主题写下去,而是抒写爱情,描写人类普遍的感情,亦为一得之见。
《序》在下定雅弘的研究中主要是指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长恨歌》早期在日本流传,有多种抄本,前面都有序,但中国本土流行的抄本却没有序,这些序,是哪里来的呢?下定雅弘认为,这些“序”可能是日本人所写[1](P100)。
在日本流传的《序》中,杨贵妃的形象与中国流传的杨贵妃形象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中国,杨贵妃被看作是坏女人,而在日本,杨贵妃则是一位“可爱的女主公”,对玄宗挚爱不尽的杨贵妃,事实上,日本人对杨贵妃是是非常喜爱的,在日本有杨贵妃的墓,观音像等,在日本传统表演型式“能”中也有专门的《杨贵妃》瑶曲,这与中国人眼中那个祸乱朝政的红颜祸水杨贵妃形象有很大的差别,对于这种不同,下定雅弘分析了两个原因:
其一,《诗经》本是爱情诗的源头,然而汉代的《毛传》规范了《诗经》的解释,直到白居易元稹活跃的中唐时期,爱情诗才逐渐成为文学的主题,这与日本从《万叶集》发行的古代就将爱情作为文学的中心主题不同,爱情一直都作为最主要的题材流行着,也正是因为这样,表现男女之爱的《长恨歌》才在日本有这方面阅读基础和土壤。
第二,中国的天子被赋予了最高的权力,同时也有对天下负责的义务,人们对天子是有一种人格的要求,当天子沉迷声色,懈怠朝政,人们自然会对他产生批判的情绪,但在日本,天皇并没有统治的实权,日本人无法站在中国“道德”的立场上对玄宗进行批评,而是把它当作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用直观的感觉去体会[1](P104-105)。
下定雅弘的论述充分考虑到中日两国在政治环境、文化心理,文学发展史上的不同,切中肯綮,致力于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颇有不同凡响的启发引导意义。使《歌》《传》《序》的研究成为一个具有中心理论的系统,这个中心的理论便使下定雅弘所坚持的主题爱情说,《歌》作为一部描写抒发爱情的伟大诗歌著作,《传》便是同素材,异主题的具有批判意义和缓冲作用的传奇,《序》便是日本感动于李、杨爱情具有反映日本愿望功用的序言。三部作品都有各自的特色和意义。
四、下定雅弘研究的特点
下定雅弘关于《长恨歌》的主题、与《李夫人》的比较以及《长恨歌》、《长恨歌传》《长恨歌序》的讨论已如上文所见,分析下定雅弘对于《长恨歌》的研究方法和特点,对我国的本土研究也是颇有裨益的。
1.视野开阔
下定雅弘在研究《长恨歌》时,充分发掘研究材料和文献,视野开阔,不拘泥于研究对象主题,他的论说方式也独具特点,注重纵横穿贯与比较辩识,善于从横向将研究的主题与相关的作品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并且从纵向上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时代、政治、文化等因素,注重不同研究内容间的融合贯通,并与研究主题相结合,大大加强了论证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始终将研究建立自一个牢固可靠的基础之上,在对杨贵妃形容进行探讨时,下定雅弘结合中日两国皇帝的不同的功能以及古代的文化心理,独具特点,极具启发意义。
2.回归文本
下定雅弘在研究过程中,充分重视文本的重要性,立足于文本进行分析,不仅在分析《长恨歌》时是这样,在对《长恨歌》相关文献《李夫人》进行分析时,也是从文本展开,字句分析,语言推敲,情节比较一个不落,也正是因为下定雅弘有这样回归本文,吃透材料的精神,下定雅弘所做出的论断,才是充分值得信任的。
3.善于比较
跨文化视阈下的学术研究,有一大忌,便是不懂比较,将研究对象作为孤立的材料进行研究,下定雅弘深谙此道,在他的研究中,时刻注重比较研究,他在论证《长恨歌》主题时,充分注重到中国主流的讽刺说与日本主流的爱情说的差异,并且,对于这种差异,下定雅弘还积极的思考其成因,指出这与中国的文化土壤有关,在研究中,下定雅弘贯彻着求新求变的精神,致力于在充分把握两国研究差异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论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论,下定雅弘在研究《长恨歌》时,注重细密的材料考证和文本分析,又充分关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发展脉络之间的关联,还善于将之与相关的作品进行比较和讨论,形成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思想内涵,但正如下定雅弘所说:“关于长恨歌的研究,争议长存”[1](P105), 在研究长河中不断挖掘,不断进步,方为学无止境之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