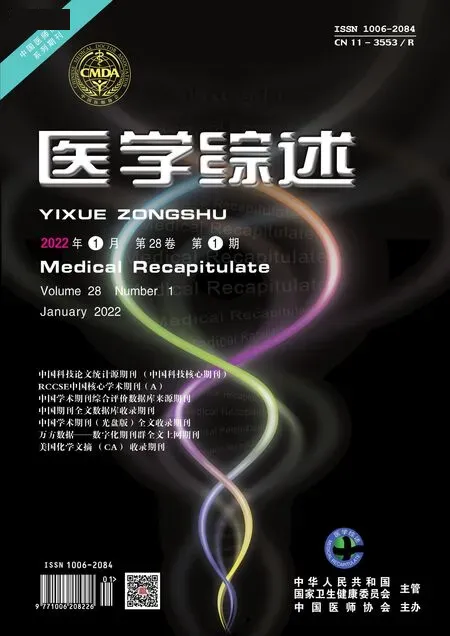一过性食管下括约肌松弛的影响因素
雷霞,张耀平,冯洁,黄晓俊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兰州 730030)
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指胃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的不适症状和(或)并发症,分为伴食管黏膜损伤的糜烂性GERD和仅有症状的非糜烂性GERD。GERD的发生与多种危险因素相关,包括肥胖、吸烟、幽门螺杆菌感染等[1]。RomeⅣ标准将非糜烂性GERD定义为存在异常酸暴露,有阳性或阴性反流相关症状,将反流性超敏反应归为功能性食管病[2]。近年来,GERD的发病率逐渐升高,专家共识推荐使用质子泵抑制剂以及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治疗[3],但是大多数患者表现为用药时症状缓解,停药后再次出现反酸、胃灼热症状,上述症状长期反复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GERD发病机制主要包括抗反流屏障功能障碍、一过性食管下括约肌松弛(transient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 relaxation,TLESR)和酸清除障碍等[4]。胃食管反流常发生在餐后,表现为短暂性食管下括约肌(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LES)松弛,即TLESR[5],且大多数患者的LES压力正常。因此,目前GERD的治疗以控制TLESR的发生为主。TLESR的影响因素较多,针对性地控制其影响因素可降低胃食管反流的发生频率、减少患者的不适症状、降低Barrett食管的发生率,提供治疗GERD新的方法[6]。现对TLESR的发病机制及影响因素予以综述,以期对未来GERD的药物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 TLESR的定义及发病机制
TLESR是指非吞咽情况下LES和脚膈肌同时发生自发性松弛,持续时间>10 s[7],并常伴有胃食管反流,可由进食及胃扩张触发,在睡眠、麻醉及迷走神经阻滞后终止。TLESR的特征为:①TLESR不是由吞咽引起,而是由于LES压力突然降低到胃内压力水平,食管体部缺乏蠕动收缩,进而导致反流发生;②TLESR的发生与脚膈肌抑制相关;③TLESR松弛时限差异性较大,在最大松弛80%的情况下,由吞咽引起的LES松弛持续时间仅6~8 s,而TLESR明显更长,几乎总是超过10 s;④TLESR有一种独特的运动模式——食管远端纵行肌收缩(longitudinal muscle contraction,LMC),LMC导致的轴向拉伸引起食管强烈的逆行性收缩、缩短[8]。
TLESR只发生在清醒状态下,胃扩张是TLESR的一种有效刺激,且迷走神经调控、咽刺激、膈肌抑制均参与了TLESR的发生。胃扩张时发生的TLESR与犬和人类的呃逆有关,其可防止过多的气体积聚在胃内或进入十二指肠,被认为是餐后排气的主要机制。近端胃,尤其是胃底贲门区的牵张感受器可通过机械刺激诱发迷走-迷走反射进而调控TLESR产生。TLESR的神经调控机制通过迷走神经通路介导,由胃机械感受器的扩张激活所启动的运动模式组成。感觉信号通过迷走神经的传入纤维投射到孤束核,来自孤束核的信号被传送至迷走神经背侧运动核,运动功能信号从迷走神经背侧运动核通过迷走神经传出投射到LES和膈肌,这些信号再传递到肌间神经丛,分布在整个食管体和LES。吞咽时咽刺激通过迷走神经的传入纤维传递到脑干的孤束核,进而引发TLESR。此外,TLESR的发生也常伴有膈肌选择性抑制,由于脚膈肌不仅受传出迷走神经终末支配,还由膈神经支配,而呼吸调节中枢的兴奋与膈肌运动神经元活动相关,因此吞咽时出现呼吸抑制,导致膈肌被选择性抑制,引发TLESR。
2 影响因素
影响TLESR发生的影响因素众多,如姿势与睡眠、胃扩张与咽刺激以及其他因素。对于胃扩张与咽刺激,选择性地激动或抑制迷走神经通路中的受体和递质,可影响TLESR的发生。针对上述受体和神经递质研发出对应的靶向治疗的药物,可有效地缓解患者症状。
2.1姿势与睡眠 健康人群一般不会在睡眠中发生胃食管反流,但夜间反酸、失眠或睡眠质量差是门诊报告的常见症状[9]。Eastwood等[10]研究发现,LES的功能不受睡眠和姿势的影响,清醒直立位和睡眠期间的反流大多与TLESR有关。在GERD患者中,仰卧位TLESR的发生率明显低于直立位[11],其原因可能是仰卧位时胃内的空气分布较均匀,对位于胃底的机械感受器的刺激兴奋较少,使TLESR的发生率下降。另外,TLESR的发生率受到大脑皮质的调控,深睡眠时TLESR的发生率降低,在夜间稳定睡眠时则不会出现TLESR,只有从睡眠中短暂觉醒或完全清醒时才会出现。
一般情况下,直立位的胃食管反流发作频率高于仰卧位,但仰卧位的胃食管反流往往较直立位更严重。食管炎分为Ⅰ级(黏膜红斑)、Ⅱ级(食管溃疡)、Ⅲ级(食管纤维性狭窄)。Demeester等[12]的研究表明,仰卧位者多发生Ⅲ级食管炎,而直立位胃食管反流患者仅出现Ⅰ级食管炎,其主要原因是仰卧位时无效蠕动的发生和唾液产量的减少导致食管酸清除时间较直立位明显延长,胃酸及胃反流物在食管内的停留时间较长,对食管黏膜的损伤比较大。
仰卧位时胃食管反流发作频率低,但对食管的伤害更大,Person等[13]提出了一种更佳的睡眠姿势——左侧向下卧位。当左侧俯卧时,液体胃内容物位于胃体部,在食管胃交界处只有气体反流进入食管;此外,健康人群左侧向下卧位时发生TLESR的可能性低于右侧向下卧位[14]。综上所述,简单的改善睡眠姿势(如抬高枕头、左侧向下卧位)即可以在不使用药物或其他侵入性抗反流治疗的情况下降低夜间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率,改善患者症状。
2.2胃扩张与咽刺激 TLESR由迷走神经通路介导,由胃机械感受器的扩张激活所启动的运动模式组成,吞咽时的咽刺激亦可通过迷走神经的传入纤维引发TLESR。而孤束核和迷走神经背核是重要的迷走神经感觉和运动核团,在TLESR的神经传导通路上存在许多受体与神经递质,如大麻素受体(cannabinoid receptor,CBR)、γ-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 acid,GABA)受体、谷氨酸受体(metabotropic glutamate receptor,mGluR)、一氧化氮递质、胆囊收缩素(cholecystokinin,CCK)受体和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PG)E1受体。通过控制影响神经传导通路中的受体和神经递质减少胃扩张与咽刺激,进而减少TLESR的发生。
2.2.1CBR激动剂 CBR属于G蛋白偶联受体超家族,主要包括CB1和CB2,CB1主要表达于包括肠神经系统在内的中枢和外周神经元,而CB2主要表达于炎症/免疫细胞[15]。Lehmann等[16]探讨大麻素对TLESR和胃迷走神经机械敏感传入放电的影响发现,CB1可能作用于脑干,而不是由胃迷走神经传入至外周介导。CBR激动剂可以抑制自发性吞咽,降低TLESR的发生率。同时,自发性吞咽和反流清除减少,并产生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因此,使用选择性靶向外周CB1激动剂进行靶向治疗十分必要。Van Sickle等[17]发现,内源性大麻素能够同时激活CB2、CB1,而这两种受体可共同激活局部脑区,从而减少CB1激动剂引起的精神性不良反应。因此,通过提高释放的内源性大麻素水平靶向特定的局部CBR也是一种治疗策略,不仅可通过影响TLESR的神经传导通路减少TLESR的发生,还可以减少中枢作用类药物的精神性不良反应。
2.2.2GABA受体激动剂 GABA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广泛存在于中枢孤束核神经细胞,其可通过影响迷走神经的机械感受器改变迷走神经传出冲动,影响TLESR的发生[18]。目前与GABA受体有关的治疗GERD的方法有巴氯芬药物治疗和针刺足三里治疗。
巴氯芬是一种选择性GABA受体激动剂,其作用机制一部分依赖于抑制外周机械敏感的胃迷走神经传入,提高动作电位的放电阈值;一部分依赖于抑制中枢迷走神经传入,导致递质释放减少。Lehmann等[19]报道,GABA受体激动剂巴氯芬在高剂量水平下几乎能够完全抑制犬LES的短暂松弛。随后,Cossentino等[20]研究表明,使用巴氯芬后,直立位胃食管反流的发生率明显低于仰卧位者,且LES压力正常GERD患者最明显,呃逆、反胃和GERD总体症状评分显著改善。孙旻[21]的研究表明,巴氯芬联合奥美拉唑和莫沙必利可缓解老年GERD患者的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其临床疗效优于单纯应用奥美拉唑和莫沙必利,且安全性较高。巴氯芬能提高LES的静息压力和综合松弛压力,且对控制原发性食管蠕动的食管传出通路没有或仅有有限的影响,这有助于维持LES抗胃酸回流的能力,减少反流的发生[22]。巴氯芬由于中枢不良反应较大而应用受到限制,但GABA受体激动剂可作为一种新的治疗方式减少TLESR的发生。中枢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他克林可逆转针刺足三里对TLESR的抑制作用,而一氧化氮前体L-精氨酸对其无作用,表明针刺足三里对TLESR的抑制作用可能与乙酰胆碱通路有关[23]。陈宏达等[24]研究表明,阻断胆碱能M受体后,针刺的干预效果明显减弱,但仍可使LES压力恢复至正常水平,可见针刺可通过迷走神经的胆碱能受体以及其他途径对LES发挥干预效应,表明电针足三里可能通过激动孤束核中的GABA受体影响迷走神经-食管中枢调控机制,进而恢复LES的正常生理功能,减少TLESR发生并降低胃食管反流的发生频率。
2.2.3mGluR拮抗剂和一氧化氮合酶抑制剂 mGluR和一氧化氮合酶大量存在于迷走神经传入神经上,是介导TLESR触发的反射弧中的重要因素之一。LES肌间神经丛含兴奋性、抑制性神经元和神经纤维,兴奋性神经主要是胆碱能神经,抑制性神经包括氮能神经和含血管活性肠肽的神经。而一氧化氮是非肾上腺素能非胆碱能神经的神经递质,也是胃肠运动抑制性递质,能够引起LES松弛。近年来,mGluR和一氧化氮合酶影响TLESR的相关研究较少。既往研究表明,mGluR5受体拮抗剂可降低胃胀的机械敏感性、降低犬TLESR的发生率、减少中重度GERD患者的胃食管反流发作频率[25]。同样,一氧化氮合酶抑制剂也能显著降低TLESR的发生率,通过降低胃扩张刺激减少TLESR的发生[26];通过抑制中枢内孤束核和迷走神经背核的一氧化氮合酶实现抑制TLESR的作用,此作用可通过电针内关穴实现[27]。因此,一氧化氮合酶抑制剂和mGluR5受体拮抗剂对GERD患者的潜在临床益处较大,特别是对于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后仍有持续症状的患者,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治疗GERD的新型药物。
2.2.4CCK受体拮抗剂 CCK对LES的压力有兴奋和抑制两种。一方面,CCK可通过与sling纤维和clasps纤维的CCK受体的差异性结合来调节、诱导LES收缩;另一方面,CCK可通过胆碱能途径增加胃机械感受器的自发性放电,从而使TLESR的发生率升高。而CCK-A受体刺激sling纤维收缩的作用较CCK-B受体更强[28],在胃扩张过程中,输注CCK可增加TLESR的发生率[29]。
不同动物CCK水平对维持LES兴奋性和抑制性机制的平衡存在差异,无论CCK的兴奋作用是直接作用于肌肉还是通过胆碱能途径,CCK对LES的抑制作用始终覆盖所有的兴奋作用[30],而CCK受体可作为治疗GERD的理想靶点。
2.3其他因素 LMC是TLESR的一种独特的运动模式,其导致的轴向拉伸引起食管强烈的逆行性收缩、缩短。刺激PGE1受体[31]和CCK受体[32]均可诱导正常人发生LMC,诱发TLESR。目前,PGE1受体在人食管中的分布尚不清楚,但PGE1受体拮抗剂可抑制TLESR,并且可以在不改变健康受试者平均LES压力的情况下,使TLESR的发生率降低20%[33]。此外,低剂量PG对GERD有保护作用;而高剂量PG呈剂量依赖性地刺激胃蛋白酶的分泌,对GERD产生有害作用[34],上述两种作用均通过激活PGE1受体介导。因此,应用PGE1受体拮抗剂不仅可减轻健康受试者酸灌注诱导产生的胃灼热[35],改善酸反流症状,还可作为一种新的治疗靶点,抑制TLESR的发生。
3 小 结
目前,除使用质子泵抑制剂以及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进行抑酸治疗外,还可通过调控TLESR治疗GERD,如CBR激动剂、GABA受体激动剂、mGluR拮抗剂、一氧化氮合酶抑制剂、PGE1受体拮抗剂均可直接或间接抑制TLESR,减少GERD的发生。此外,抬高枕头、左侧向下卧位、中医针刺足三里和内关穴、调节食管的LMC也可减少TLESR的发生。深入研究TLESR的神经通路的介导机制和受体种类,对研发控制TLESR的高效药物以有效减少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