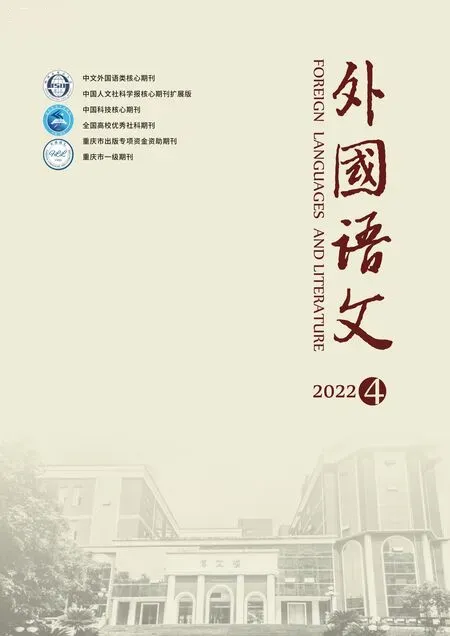村上春树《镜子》中的恐怖书写
贾庆超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东北电力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2)
0 前言
《镜子》①《镜子》最初发表于日本伊势丹百货公司主办的会员杂志《特莱富尔》(Trefle)1983年2月号,同年9月被编入短篇集《袋鼠佳日》(平凡社,1983),之后被收入《村上全作品1979—1989⑤短篇集Ⅱ》(1991)和《最初的文学》(2006)。在中国《镜子》被为收录于短篇集《遇到百分百的女孩》(2002),是依据《袋鼠佳日》版本翻译而来。村上在《全作品》版本中对《镜子》进行了多处修改,而中国关于《镜子》的翻译版本却一直并未随之修订。木村功在比较不同版本后分析指出《全作品》版本更加有意识地表现“恐怖”,比如添加了“我去了走廊那里。那里烟头还在,木刀也掉在地上。但是没有镜子”、“对人类而言,这个世上恐怕没有什么比自己更令人感到恐怖的吧”等部分,认为《全作品》版的恐怖效果最成功,日本学界关于《镜子》的相关研究也大多采用此版本,本文也将使用《全作品》版本。参阅木村功「教科書教材を読みなおす(8)村上春樹「鏡」論:本文·鏡·鏡像体験をめぐって」、『岡山大学国語研究』2018年第32期、第6頁。本文中所引用的日文文献,如未特别提示,均为笔者自行翻译。创作于1983年,通篇不足5 000字,村上对这部作品极为喜爱,不仅曾在多个场合朗读,还将其收入精选集《最初的文学》(村上春樹,2006)之中。作品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大家聚在一起依次分享自己的怪异体验,作为主人的“我”讲述的是自己年轻时在中学做夜警的经历。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在走廊发现一面镜子,“我”意识到“镜中我”似乎并不是“我”,甚至想要支配“我”;“我”用木刀把镜子击碎后落荒而逃,翌日清晨返回原地发现木刀还在,但根本没有镜子。此部作品在中国并未引起重视,但在日本享有重大知名度,自1993年以来被陆续收入东京书籍(1993)、尚学图书(1995)、大修馆书店(2003)、明治书院(2013)出版的高中国语教材之中,成为村上所有作品中被录入教材次数最多的一篇。
关于《镜子》村上(2006:261)曾这样说道:“我那时曾一度想试着创作类似于‘怪谈’一类的东西。我对于如何能在文章中切实表现心中的‘恐怖’很感兴趣,因此作为尝试写了这个篇幅不长、类似于怪谈一类的东西。”由此可知,《镜子》是采用类似怪谈手法、以表现心中的恐怖为目的的作品。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教材角度以及关于“我”和“镜中我”形象的探讨,对于作品中的怪谈手法较少涉及,只有西田谷洋(2008:31)、善塔正志(2014:56)、原善(2020:68)指出《镜子》体现了怪谈的“百物语”①百物语原本是怪谈的讲述形式之一,也被称为“怪谈会”,兴起于江户时期,不少怪谈作品集直接以“百物语”命名。的结构。对于作品中的“恐怖”,坂田达纪认为该作品的恐怖之处在于“我”自认为过着正确的生活,但是在他者眼中却令人憎恶(2015:47),山田伸代(2016:84)指出“我”经历了这一事件后依然未有任何改变,之后仍然过着四处游荡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恐怖。目前的研究对于《镜子》具体何处体现了怪谈色彩、如何通过怪谈营造了恐怖效果、营造的恐怖效果又与村上所指的“心中的恐怖”有何关联等问题缺乏深入探讨,笔者将结合怪谈的特点以及作品的创作背景对以上问题展开论述。
1 《镜子》中的怪谈色彩
“怪谈”是日本传统的恐怖文学形式,《日本国语大辞典》(第二卷)将其定义为“不可思议的故事,奇怪的故事。特别是有关妖怪、幽灵的故事”(日本大辞典刊行会,1979:983)。怪谈产生于江户时期,其发展形成受中国明清时期白话小说影响颇深,该时期上田秋成创作的《雨月物语》(1776)、《春雨物语》(1808)被誉为“怪谈文学的巅峰之作”。怪谈在江户时期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这一状况一直到明治后期才得以改观,“随着江户风潮的回归,欧美神秘主义哲学和心灵学的传入,作家迎来了解除怪谈禁欲的时代”(三浦正雄,2012:303)。
泉镜花是明治时期的知名怪谈作家,创作风格对上田秋成多有借鉴,在《高野圣僧》(1900)等作品中塑造了鬼怪出没、离奇恐怖的文学世界。以上两人恰恰是为数不多获得村上青睐的日本作家,内田树和平川克美(2015)曾指出“村上春树和上田秋成、泉镜花处于同一谱系上”。村上小学时期就被上田秋成吸引,成年后重新阅读依旧十分喜爱,山爱美(2019:179-180)指出上田秋成“此岸的世界/生的世界”同“彼岸的世界/死的世界”的界限并不明确的世界观对村上有着深远影响。村上对泉镜花也有着深刻理解,曾声称思考小说中虚幻和真实的关系时就会想起他,认为现在人们之所以又开始关注并重新评价泉镜花,可能是由于泉镜花文学是创作虚拟和现实并不分明的文学世界的最后作品了(河和隼雄 等,2011:96)。村上文学的突出特点为构筑了处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异界”,幽灵、夜鬼、吸血鬼、僵尸、小小人等令人毛骨悚然的超自然意象往往由异界进入现实世界并引发强烈的恐怖感。包括《报纸》②该作品被收录于東雅夫『文豪てのひら怪談』,東京:ポプラ文庫,2008年。(1986)、《第七位男士》(1996)在内的多部作品都弥漫着怪谈色彩,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镜子》。
《镜子》讲述了“我”在学校走廊发现一面镜子并遭遇“镜中我”想要控制自己的恐怖体验,“镜子”是怪谈中的常见要素,作为故事发生地的学校与走廊也是怪谈的经典舞台③与镜有关的怪谈有小泉八云的《镜与钟》、森鸥外的《不可思议之镜》等诸多作品。1980年以后日本兴起了以学校为舞台的怪谈故事,统称为“学校怪谈”,目前已成为日本怪谈的重要门类,走廊又是学校怪谈中出现灵异现象的常见场所之一。,很明显该作品采用了百物语的叙述形式。杉浦日向子(2007:142)曾在《一日江户人》(小学馆文库,1998)中通过漫画展现了“百物语”的进行方式,简单而言就是大家在漆黑之夜轮流讲恐怖故事,一直到第99个才停止。百物语采用讲述者对听众述说的形式,内容既可以是虚构,也可以是亲身经历——即实话(実話),此类怪谈被称为“实话怪谈”。
在《镜子》中,夜晚大家围坐在一起轮流讲恐怖故事,作为主人的“我”最后出场,虽然一再声称自己的体验平淡无奇不值一提,其实他有着高超的讲述技巧:不仅通过“要是现在,当然是抱头鼠窜”“走廊地布是绿色的,现在都还记得”(村上春樹,1991:75-77)等与听众积极互动,同时情节张弛有度,让听众乃至读者都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九点巡视时平安无事”(松)——“三点铃响时,我总觉得很不对”(紧)——“校舍没有什么不正常,一如平日”(松)——“黑暗中好像有什么一闪。腋下一阵发凉。”(紧)——“是镜子!虚惊一场。”(松)“我突然注意到一件怪事:镜中的形象不是我!”(紧)——“对了,你们注意到我家里一面镜子也没有了吧?不照镜子而能刮须,做到这一步可相当花时间的哟,不骗你。”(松)(村上春樹,1991:76-79)
原善(2020:59)认为在该作品中“因为作为主人要在最后讲故事,所以为了吓唬听众而做手脚”,即应将《镜子》中遇到镜子的体验理解为只是“我”为了娱乐大众而创作的虚构故事而已,作为读者只需要理解其虚构的魅力即可。这一观点旨在批判教材指导书中的刻板解读方法,强调故事的趣味性,但这种解读无疑大大削减了作品的恐怖氛围,与村上提出的希望通过《镜子》表现心中的恐怖的目的并不相符。在笔者看来,应将作品理解为实话怪谈。实话怪谈强调自己的体验是真实的,往往采取“我遇到了这么个怪事儿”开场,并没有明确的起承转合结构,大多凭借采用开放性结尾或结局的缺失以延续恐怖诡异气氛。更重要的是,实话怪谈营造了故事就发生在身边且随时可能发生的氛围。《镜子》的情节也并不完整,“镜中我”到底是什么,在遇到“镜中我”后“我”又经历了何种人生体验,对于此类问题作品都没有明确交代。结尾处的“对了,你们注意到我家里一面镜子也没有了吧?不照镜子而能刮须,做到这一步可相当花时间的哟,不骗你”(村上春樹,1991:75),更近一步渲染了故事的真实性,以此烘托“你也可能会遇到”的恐怖效果。
2 《镜子》中的怪谈式恐怖
恐怖是人类最原始的情绪,人类最原始的恐怖是对超自然事物的恐怖,结合恐怖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表现对超自然的恐怖(supernatural horror)也成为恐怖小说最原始、最经典的手法,作为西方恐怖小说源头的哥特小说和日本怪谈往往采用吸血鬼、僵尸、幽灵等意象表现超自然恐怖。河合隼雄(2006:81)将恐怖定义为:“人类持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或体系生活,使其人生观、价值观或体系在某处发生动摇的就是恐怖。”近代人一直接受“世间本无鬼怪”的理性主义熏陶,对于生灵、幽灵并非完全相信,突然遭遇此类超自然意象无疑超越了以往的认知体系范畴并由此引发强烈的恐怖感。虽然同为表现超自然恐怖,日本知名怪谈研究学者吉田悠轨(吉田悠軌)(2018)认为欧美恐怖小说和日本怪谈具有明显区别:前者往往表现突然遭受怪物袭击的恐怖且危及生命,而后者的恐怖并不像欧美恐怖小说那样显露,往往是由想象力造成;比起性命攸关,大多是突然接触到来自异界事物这一事件本身的恐怖。表现来自异界的“生灵”作祟的恐怖,则是日本怪谈独有的。
自古以来日本人就相信活人的灵魂可以从身体脱离并作祟,离体之物被称为“生灵”(生き霊)。黄健香(2018:116)指出生灵是日本特有的“物怪”(もののけ),具有怨灵的属性并往往作祟于人。日本人对生灵作祟这一构思情有独钟,平安时代以来尤其是近世怪异小说频繁借助这一表现来烘托恐怖的氛围,在小泉八云的《生灵》、上田秋成的《吉备津之釜》等诸多怪谈作品都有生灵出现,这是在欧美恐怖小说以及中国怪异小说中难以看到的①中国怪异小说中虽然也有生魂出现,但大多只是离体并未作祟。比如在收录于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中的《生魂离体》,讲述了沧州长官王某的女儿病重,临死前生魂离体站到树荫下看月亮,不久后就死去;唐代陈玄祐《离魂记》中的张倩娘为了和表兄王宙生活而生魂离体,均未作祟。。村上也有着强烈的“生灵意识”,他在《刺杀骑士团长》(2017:53)中设置本应在疗养院的雨田具彦突然深夜出现于画室,之后借叙述者之口感慨“现在如此目睹的即是他的幽灵。但据我所知,他尚未去世。因此准确说来应称为 ‘生灵’才对”。在《斯普特尼克的恋人》(讲谈社,1999)、《奇鸟形状录》(新潮社,1994—1995)、《1Q84》(新潮社,2009—2010)等作品中也均有生灵出现。但以上作品中的生灵更接近于汉语中“生魂”的内涵,即只是止于脱离肉体并未作祟,在《镜子》之中,村上则是借用生灵作祟营造了强烈的恐怖氛围。作品中的“镜中我”与“我”外表完全一致,却又是“我以外的我”,而且“打心眼里憎恨我,谁都无药可医的憎恨”“在他的盯视下我的身体像被铁丝绑住一样动弹不得”(村上春樹,1991:78)。西田谷洋(2008:32)认为“镜中我”是亡灵,但“我”反复强调“虽然我已经活了三十多年了,但一次也没看到过幽灵”“我没见到什么幽灵”(村上春樹,1991:73,79)。幽灵属于死灵,与亡灵同义,可见西田谷洋的这一说法并不成立。笔者认为“我”之所以否定曾看到幽灵,是因为“我”所看到的是“生灵”而非“幽灵”。
从时间上而言,“我”在深夜三点发现镜子,这正是恐怖小说中鬼怪频繁出没的时间段;从空间上而言,镜子位于正对大门走廊的正中央,大门是学校内外的连接点,走廊往往在村上作品中承担着此界和异界的纽带作用,镜面又是镜内空间和镜外空间的分界,可以说在“我”发现镜子时正处于此界和异界的临界点上,这都符合“生灵”产生的时空条件。“镜中我”与我容貌毫无二致,可以视为脱离肉体后的“我”的灵魂;同时“镜中我”又对“我”怀有极度憎恨甚至想要支配“我”,“我”动弹不得且又无法反抗,这正是“作祟”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怪谈中的“生灵”大多是作祟于他人,极少作祟于自己,这也应该是村上将作品称为“类似于怪谈的东西”(怪談らしいもの)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怪谈”的缘由。这一特殊的设定又进一步加深了恐怖氛围:遭遇他人的生灵尚且有逃跑的可能性,但面对另一个“自己”的作祟却难以逃脱,相比之下更能让人毛骨悚然,时隔多年再次提及时依然心有余悸,感慨“唯独那天夜里尝到的恐怖滋味至今也不能忘掉”(村上春樹,1991:79)。
3 “怪谈式恐怖”与“内心的恐怖”
村上提及《镜子》是为了表现“心中的恐怖”而创作,至于这种“心中的恐怖”有何具体内涵,则需要结合村上的自身经历和创作背景分析。村上1968年进入早稻田大学时适逢“全共斗”①“全共斗”为“全国共斗会议”的简称。1968—1969年大学纷争时,各大学结成的新左翼和或无党派学生组织领导了当时的全日本学生运动,在大学校园设立路障堡垒与校方对峙。1970年前后运动走向溃败和解体。运动爆发,村上也曾参与其中。黑古一夫(1993:182)将此段经历视为村上文学创作的原体验,指出“村上春树和同时代作家的内心深处, 都打上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所谓(青春=革命+恋爱)的烙印。他们以各自受到的精神打击为原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最初的“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都是对学生运动的整理,作品中始终弥漫着空虚迷茫的氛围;在创作《镜子》的1983年,村上依然处于此阶段,《镜子》即是以“全共斗”运动为背景展开,在作品中明确提及“我高中毕业的六十年代末发生了一系列纷争,动不动就要砸烂体制的时代”(村上春樹,1991:74)。
《广辞苑》将“体制”(「体制」)定义为“政治支配的形式,特别是既存的支配势力”(新村出,2012:1686)。1968年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旨在反抗体制的学生革命运动风潮,这一风潮也波及日本,日本的“全共斗”呈现出与法国“五月风暴”(1968)等西方学生革命运动的同时代性。日本1960年代早期的反体制运动尚且与“反安保斗争”这一特殊历史语境相关,但1968年的学生运动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为了打破而打破,大多参与运动的学生只是在风潮裹挟下自然而然走上街头,曾参与其中的内田树(2010:33)认为“全共斗运动在政治史上而言,也是不太明白其意义的事件”,上野千鹤子(2015:237)也尖锐地指出“没有具体的目标,是空中楼阁的运动”。这种目标的模糊性导致反体制一方内部争权夺利,后期甚至发生了“浅间山庄事件”(1972)等过激行为。这让崇尚个体自由的村上倍感失望,他深刻意识到学生运动中所谓的“反体制”只是“对于蛮不讲理做法的纯粹愤怒的发泄,很快变成了政治运动(movement)和政治运动的战斗、数量和数量的战斗、党派和党派的战斗、表层话语和话语的战斗那样的东西。那样一来,个人想法什么的就被整个弃之不顾,被彻底卷入战斗这一行为之中”(2019:57),即“反体制”一方非但没能撼动体制内部结构,甚至在“反体制”一方也衍生出否认和压制个体的“体制”。
村上曾和川上未映子(2019:57)探讨“恶”的存在形式,川上谈道“同‘恶’战斗,同时也是和自己心中的‘恶’发生冲突”时,突然毫无征兆地提及《镜子》,指出镜子里的形象“虽然那是照在镜子里的本人模样,却是‘恶’本身的形象……在黑暗中看见‘恶’的化身那样的东西,可是照在镜子里的是自己的嘴脸”。之后又对“恶”做出明确定义:“不过眼下我视为最大的‘恶’的,仍是体制(system)。”(2019:231)即在村上看来,外部的体制与人内心的“恶”存在呼应关系,即便是自以为站在“善”和“反体制”一方,在特定条件下也会作“恶”,这种善恶边界的模糊性正是村上所要表现的“内心的恐怖”。
村上写作《镜子》时仍处于创作风格的早期实验阶段,从怪谈的恐怖特点而言,在《镜子》中作为尝试而采用了类似于怪谈的手法,这其实与要表达的内心恐怖相吻合。生灵往往因嫉妒和憎恨作恶,例如《源氏物语》中的六条御息所原本德才兼备高贵典雅,最终在遭受冷落后生灵出窍迫害夕颜和葵之上,但本人发觉后也对此内疚自责,可以说生灵正是灵魂挣脱理智控制形成“恶”的化身。村上正是通过生灵这种超自然意象,将无形的内心恐怖以有形的方式更为直观地呈现出来,由此表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此外,故事又以百物语的形式讲述,呈现出“讲话人”对“听众”讲故事的模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往往形成“读者”=“听众”和“作者”(村上本人)=“讲话人”的感受,也更能与故事产生共鸣。村上(1991:79)在《全作品》版本中特意加上“对于人类而言,恐怕没有什么比自己更恐怖的了吧。你们不这么认为吗?”这里的“人类”(「人間」)“你们”(「君たち」)具有泛指意义,即不仅存在于“我”自己身上,在其他人身上也普遍存在。通过这种讲述方式,更容易把这种恐怖一般化,并传递到每个人身上且引起反思。
4 结语
村上春树对怪谈这一日本独特恐怖文学类型持有浓厚兴趣,《镜子》就是作为尝试采用类似于怪谈的手法创作而成,但村上并未止步于表现传统怪谈中遭遇鬼怪的超自然恐怖,而是利用这种超自然恐怖形象地表现善恶界限并不明确的内心恐怖,体现出高超的叙述技巧。这部作品篇幅短小,却对之后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作品中镜子、生灵等意象以及针对恐怖、体制和反体制、善恶的探讨也频繁出现于此后的作品之中,可以说针对此部作品的研究对整体把握村上春树的文学特色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