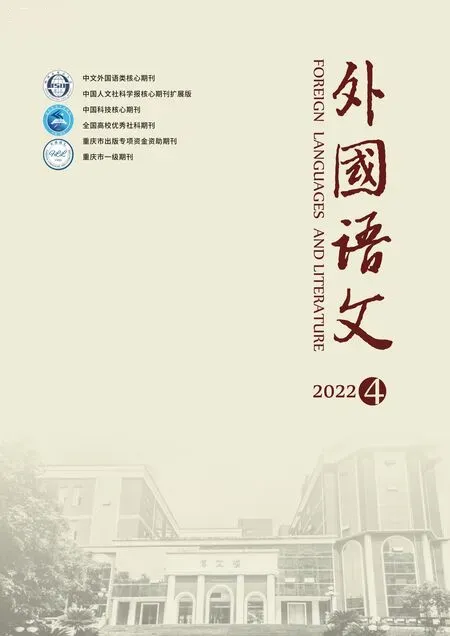美国符号学纲要
吕红周
(湖州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0 引言
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得到的科学分类,如目前较通行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人们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对特定的研究对象开展研究,不断积累某一领域的知识宽度和深度,在人才培养方面,学科还具有强力性质的规范和塑造涵义。学科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不断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生存方式,体现着人类对世界的最新认知状况,“符号学的终极关怀指向的是人,不管是研究符号系统还是解释各种意义,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吕红周,2016:7)。
就符号学而言,一般将法国学者巴特(Barthes)《符号学原理》①《符号学原理》法语版1964年出版,1967年英译版出版。对于该著作评价不一,如科布利(2013:8-9)指出:“为了让符号学得到拓展,超越语言符号,巴特对索绪尔的一处口误大肆发挥,表示‘能指也能够被某种东西中转……能指的实质始终是物质性的(声音、物体、形象等)’。巴特对这种非索绪尔式的断语不以为羞:有了如此断语,所有关于符号的事情,包括混合体系中的那些,就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思考了。”的出版视为学科独立的标志,学界通常将20世纪50年代视为符号学学科化与制度化的开端。在符号学70年的学科化进程中,符号学思想史的研究还不尽人意,到目前为止依然缺乏关于符号学史的专题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符号学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和学科交叉性。在符号学研究史上有太多伟大的学者,他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为符号学的形成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思想。艾柯(Eco,1984:80)为撰写符号学史提出了一个基本建议:重新阅读整部哲学史,或者还需要一并阅读其他许多学科史。迪利(Deely,2001)做了这样的努力,他的《理解的四个时期》重新审视了从古代到21世纪转向的哲学史,将其分为发现现实性的古代哲学时期、存在哲学的拉丁时期、现代哲学时期和后现代哲学时期,其中在后现代哲学时期论述了皮尔斯、索绪尔、艾柯等学者的符号学思想。
遗憾的是,受学识和视野所限,我们无力书写完整的美国符号学学科史。虽然我们同意艾柯“当前任何一位作者都难以独立完成论述符号学史的重任”的论断(Sebeok,1991:1),但我们仍试图以一种极简方式去管窥百年来美国符号学的发生与发展历程,而且原意承受挂一漏万的风险以及可能由此而带来的批评,因为符号与人和人类文明的关系是一个最为复杂和基本的问题,去回顾与分享那些充满智慧的发现是一种巨大的诱惑,而将这些伟大智慧拼出相对完整的符号学版图无疑是一项令人激动的事业。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分别从语言学和哲学进入符号学研究,引领了现代符号学的两个发展方向。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后,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学成为符号学发展的主流路径,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因其理论广博、术语驳杂、语言晦涩而发展迟滞,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与接受。赵毅衡(2014:1)在“回到皮尔斯”中指出:“中国符号学运动在索绪尔的影子中已经徘徊了几十年,早就应该走出来,却始终没有一本走出丛林的指南……今天,我们的努力有个明确目标:回到皮尔斯,是为了走向符号学运动更加广阔的前景。”在符号学经历了70年学科化发展的今天,符号的生产与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对符号以及符号学的认知更加成熟和理性,重新审视美国符号学发展的阶段,思考基于传统与史实的符号学思想史,对于把握和预测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赵毅衡(2012)把20世纪的符号学分为20世纪上半期的模式奠定和解释阶段、20世纪60—70年代的索绪尔模式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发展阶段。美国符号学符合这一总体发展特点,尤其以多元化为典型特征,如哲学和逻辑学、行为主义、结构主义、生物主义、认知科学等,这正是西比奥克(Sebeok,2001)一生为之努力的“全球符号学”图景。“西比奥克把符号学喻为拼图,学者们对采用哪些符号碎片进行组合以及不同成分的位置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关于符号学版图的设想一方面是让人激动的,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误导。”(王铭玉 等,2021:171)所以,我们在此所给出的发展阶段区分以及由此而提及的符号学代表人物也存在西比奥克已经指出的潜在风险。我们在此的考虑基于西比奥克给符号学的定义:符号学是使用符号区分现实与幻象的学问(Sebeok,1991:2)。这一观点体现了皮尔斯符号学的认知倾向,“皮尔斯符号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认知过程的机制问题”(Nesher,1990:44,1)。思维通过符号来实现,思维与心智的运行机制在本质上具有符号性。在美国甚至世界符号学发展史上,皮尔斯是一个关键人物,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皮尔斯描绘了一般符号学的蓝图。因此,我们尝试选取另一种视角和维度来梳理美国符号学的思想史:皮尔斯之前的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以及皮尔斯之后的符号学。
1 皮尔斯之前的符号学
人们对自然符号的认知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时期,他们已经使用自然符号开展了占卜活动,这不同于索绪尔语言符号模式下的对等模式,而是类似于命题形式的推理,如果P则Q。威尔金斯(Wilkins)的《秘密的和流动的信使》被誉为第一部密码学著作,开启了秘密交际研究的进程。人们对自然符号的关注与使用具有久远的历史,如人类根据动物留下脚印、粪便等开展的狩猎、追踪,根据自然界的云的形状与颜色、风向等预测天气变化,以及决定人类和动植物遗传与发展的基因等,被称之为自然之书。劳赫(Rauch)是符号学的先锋之一,他指出术语semeiotic来源于希腊语中的semeia,提出符号具有意向性,符号的价值取决于意指等卓有远见的观点,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提出symbolical/emlematical/semeiotical三分①Symbolical指对象与它所表征思想的同质性,如生命之光与火把之光是同质的,熄灭的火把和死去的人之间具有类比性;想象产生的是emlematical,此时形式与内容之间是异质关系或不充分关系,比如饭店门口标志上的茶杯不是渴的象征,而是一种指示或索引。想象的工作机制是符号学的,形式总是倾向于表征特定的内容,而不是表征与其相似与表征不同于自身的东西。符号如果不用于意指或失去了意指的内容,符号便失去了它自身的价值(参见:王铭玉等《符号学思想论》,2021:173-174)。,为皮尔斯著名的icon/index/symbol提供了启示。约翰逊(Johnson,1947:40)的观点特别需要注意,“我致力于将语言从属于自然,自然是语言的解释者,而不是相反。如果我成功了,那么在知识的每一个领域都将会出现一个伟大的革命”。约翰逊对自然与语言的这一认识无疑突破了语言中心进而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既然不是语言言说世界,那么,人类必须寻求新的表征方式与中介,自然世界具有符号性质,世界通过符号实现自我表征,世界的内在运行机制是符号活动。惠特尼(Whitney)所主编的24卷本《世纪大辞典》中有众多词条出自皮尔斯,可见惠特尼与皮尔斯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从索绪尔对惠特尼的直接引用情况可以清晰地看到惠特尼的语言制度观、符号的社会性以及系统性等观点对索绪尔产生的直接影响(吕红周,2010:58)。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惠特尼间接影响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从而推动了符号学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因为他的《世纪大辞典》收录了皮尔斯关于“符号学”①在惠特尼《世纪大辞典》(1889)之前出版的《帝国英语词典》(1883)中已经有了关于“符号学”的词条:(1)关于符号的科学或学说;符号语言;(2)在病理学上,指人健康或疾病状态下的身体症状;症候学;符号学(Ogilvie,1883,IV:27)。也就是说,在皮尔斯为《世纪大辞典》撰写“符号学”词条之前,就已经有semiotics这一词形。的词条。
2 皮尔斯符号学
皮尔斯被公认为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他在美国享有更高盛誉,如“皮尔斯不仅完全掌握了他那个时代的数学和科学发展,而且还有科学和哲学史”(Russell,1959:277)、“美国最具原创性思维的人” (Nagel,1982:303)、“美国复兴的亚里士多德”(Lowe,1990:2)等。皮尔斯的自我评价也充分说明了他对于符号学的偏爱:我从来没有能力学习任何东西,数学、伦理学、形而上学、万有引力、热力学、光学、化学、比较解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音学、经济学、科学史、惠斯特、男人与女人、葡萄酒、计量学,符号学研究除外(Hardwick,1977:85-86)。皮尔斯反对心理主义,推崇科学、实验室、实证的研究方法,认为数学研究假设事态,从可能性、假设、想象中推导出必然性结论,最大限度降低随意性,而不考虑它们是否与实际事物有关。皮尔斯努力将形而上学科学化,同时提倡知识可错论,皮尔斯寻求将宗教和科学相统一的知识体系,能够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我想要创造像亚里士多德哲学那样的一种哲学,即创建这样一种综合理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管是哪个哲学流派或类别,不管是数学、心理学、物理学、历史、社会学或其他任何学科,整个的人类思维,都是我理论的组成部分。”(Peirce,1931:3-4)
关于皮尔斯符号学的理论全景是一个无比宏大的课题,1946年美国成立了皮尔斯研究会,普渡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宾州大学设有皮尔斯研究中心,在加拿大、巴西、芬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都已经建立了专门的皮尔斯研究机构,皮尔斯研究专刊Transaction也已经出版50多年,目前关于皮尔斯的集中研究成果是1931—195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的八卷本《皮尔斯文选》(TheCollectedPapersofCharlesSandersPeirce)以及《皮尔斯历年文稿》(WritingsofCharlesS.Peirce)、《皮尔斯精粹》(TheEssentialPeirce)、《皮尔斯:编年版》(CharlesS.Peirce:AChronologicalEdition)等。
关于皮尔斯符号学理论形成的阶段,根据可追溯的文献来看,皮尔斯对符号学理论的思考和学科体系的建构先后持续了54年,其标志性事件是从1865年的哈佛大学讲座开始到1911年与维尔比夫人的通信结束。从已经出版的著作来看,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并没有一个界限清晰的分期,但大致可根据三个时期的标志性文献来把握。第一阶段。1865年皮尔斯在哈佛大学关于“科学的逻辑”系列讲座开启符号学研究,1867年“一个新的范畴目录”体现皮尔斯关于符号学理论体系的思考,皮尔斯找到了自己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方法和起点,他从对康德范畴的批判开始,提出了新的三类范畴:品质(quality)、关系(relation)和再现(representation),即从数学中得到了一级范畴(firstness)、二级范畴(secondness)、三级范畴(thirdness),这时的皮尔斯主要关注符号的再现以及再现的分类、符号的形式等问题, 从而为一系列三元划分奠定了基础: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语法/修辞/逻辑、术语(term)/命题(proposition)/结论(argument)、归纳/演绎/溯因等。第二阶段。1877—1878年,皮尔斯的“澄清概念”“确定信念”代表了他这一时期对实用主义的思考。1905—1906年发表的“什么是实效主义”“实效主义”“实效主义序言”三篇论文阐释了他的实效主义哲学观。皮尔斯反对心理主义,不同于实证主义之处在于,他努力将形而上学科学化;他不是纯粹的唯心主义,但他发展了进化宇宙论,认为宇宙是一个从完全混沌状态向一个绝对有规则状态的发展过程,遵循机会(opportunity)→发生(occurrence)→习惯(habit)发展路径,得出宇宙中一切都具有“心智”(mind),绝对规则状态是死亡了的心智状态,也就是一种习惯状态。库尔(Kalevi Kull) 对皮尔斯的“习惯”提出了不同的解读方式,认为物质世界中的规律并非“习惯”,但生命发展起来的规则可以是“习惯”,由此,深入发展了生物符号学。第三阶段。1903—1911年间皮尔斯和维尔比夫人间的书信往来中包含了皮尔斯生命后期对符号学的集中思考。
我们对符号的探究方向不应是功利主义的,不是寻求符号权力的最大化,而应是探究真理,即经过无限符号活动之后,无限的趋向事实,终极解释项即真理。皮尔斯发展的是一门科学符号学,想通过符号学的术语体系重构我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最终重构人类的知识体系,所以皮尔斯把符号学视为一门基础性科学,符号学借助现象学和数学发展科学知识,澄清概念、固定信念、消除人们不断产生的怀疑,使人们能处于一种有信念的满足状态。“任何事物至少在原则上都是可以被完全探究的,那么这样一个共同的探究将会最终克服无知和根除错误,个体的片面性,它将获得真理。”(瓦尔,2003:52)理论上,通过无限的符号活动和符号生长,整个宇宙将充满符号,符号活动的终极目标必将实现,即达到最后的意见(final opinion)或真理(truth)。
3 皮尔斯之后的符号学
事实上,符号学在美国的接受和传播不是始于皮尔斯,1938年莫里斯“符号学基础”一文在《统一科学百科词典》上的发表,符号学才正式进入大众视野,“从一战爆发到1931年米德逝世,符号学在美国处于低谷期。作为符号学家的皮尔斯甚至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直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皮尔斯文选》的出版逐渐被发现”(Sebeok,1991:67)。美国符号学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协会和研究中心,如皮尔斯研究协会(1946年成立)、国际符号学研究会(1969年)、美国符号学会(1976年)、印第安纳大学语言和符号学研究中心等,符号学研究丛书,如《符号学研究方法》(ApproachestoSemiotics)、《符号学进展》(AdvancesinSemiotics)、《当代符号学论题》(TopicsinContemporarySemiotics)、《符号学网络》(TheSemioticWeb)、《符号学域》(TheSemioticSphere),杂志如《符号学》(Semiotica)、《美国符号学研究》(AmericanJournalofSemiotics)等。
应该承认,米德和莫里斯对于皮尔斯符号学兴起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米德对身势符号的分析以及他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成为莫里斯行为主义符号学说的重要来源。莫里斯继承皮尔斯逻辑学是基于一般符号理论的科学观点,但他符构学、符义学和符用学的三分将符号学重新限制在了语言学范畴,而并没有像他所预想的那样使得符号学成为一门元科学。关于符号学的分类问题,莫里斯将符号学分为纯符号学、描写符号学和应用符号学,纯符号学即元符号学,应用符号学即把符号学当作工具(Morris,1946:220)或使用符号完成不同目的(Morris,1946:353)。很显然,莫里斯给出的应用符号学定义过于宽泛,据此定义,市场营销、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病理语言学以及国家语言政策规划等都属于应用符号学的范畴。20世纪50年代在统一科学运动中,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为代表的不同领域的学者为符号学的跨学科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如“控制论: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循环、因果和反馈机制”系列会议,引发了当今符号学工作者强烈关注的一系列问题,如语言结构与信息、交际结构、动物交际、催眠等(Sebeok,1991:71-72)。
西比奥克以自己的符号学理论贡献和学术组织与实践活动推动了符号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他在回顾1962年美国符号学会议时,提出了五个主题:文化人类学、教育学、语言学、精神病学、心理学(Sebeok,1991:21)。虽然雅各布森的诸多作品中没有直接论述符号学的内容,但他却是符号学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除了他的语言六功能模式以及“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等,“他自己的一生是探究符号学的鲜活榜样”(Eco,1987:111-113)。雅各布森的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更是为翻译学与符号学融合发展提供了启示。1986年美国符号学年会的主题是“符号学与各行业”,这一方面体现了符号学交叉学科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符号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发展的前景,之后的符号学运动证明了西比奥克预言的正确性,符号学出现了多元化发展。概而观之,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科学,其发展领域存在不均衡性,尤以语言符号研究最为成熟与发达,进而向非语言符号领域拓展,以全球符号学为发展趋势。
语言符号学与非语言交际符号学。虽然我们将索绪尔符号学视为语言符号学的起点,但在美国符号学界也有众多学者为语言符号学的发展贡献了智慧。语言学是符号学的重要理论来源,1976年美国符号学会成立以来,多位语言学家曾担任会长,如我们前文提及的劳赫。此外,持语言学是符号学一部分,或从事符号行为科学研究的语言学家们,还有萨丕尔(Sapir)、赵元任、兰姆(Lamb)等,“语言学家都是符号学家,但符号学家不一定是语言学家”(Sebeok,1991:28)。雅可布森(Jakobson)、韦勒克(Wellek)以及里法泰尔(Riffaterre)等人从诗学进入符号学研究,认为诗学特征不仅是属于语言学研究,而且属于普通符号学。派克(Pike)被西比奥克称为密码符号学家(Sebeok,1988:259),尝试符号学理论用于社会事件的分析,发掘其中具有复现性的模型,如教堂礼仪、足球赛等的符号学分析。绍米扬(Shaumyan,1987)在其《语言的符号理论》(ASemioticTheoryofLangauge)以及《符号,心灵与现实》(Signs,Mind,andReatity)(2006)中直接把语言学定义为符号学中研究自然符号系统的部分。瓦特(Watt)对字母符号学的研究独树一帜,字母作为符号具有广泛的认同性,但字母系统表意方式却不同于自然语言。奈达(Nida)在对圣经的翻译实践中发展了社会符号学的翻译理论,成为今日翻译符号学的重要理论来源。西比奥克(Sebeok et al.,2000)在洛特曼二级符号系统基础上提出了三级模式化系统,从而将语言的功能从意指、指示、象征、交际等进入模式化维度,对语言形式化、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理论的推进做出了贡献。广义上任何关于世界的阐释都是一种符号系统,提供了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埃夫隆(Efron)在博阿斯指导下开展了非语言交际研究,通过对比美国的意大利和犹太人的身势语,他认为身势语受种族和文化的影响,他的《身势语,种族和文化》(Gesture,RaceandCulture)(1941)成为非语言交际的奠基性著作。20世纪50年代以后,非语言交际研究一度蓬勃发展,出现了空间关系学研究(Hall,1968)、人体动作学(Birdwhistell,1970)、《非语言有声行为研究》(Mahl,1987)等,成立了非语言交际研究协会,创办了杂志《非语言交际研究》。非语言交际是语言交际的补充形式,以语言为因素为主要表意载体,如面部表情、语调、眼神、身体动物等,但不具有语言的结构复杂性、离散性等本质属性。
全球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西比奥克2001年出版了《全球符号学》,从而将医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生物学、伦理学全部纳入符号学领域的宏观计划。医学是符号学的重要起源,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被誉为符号学之父,因为他把研究内在疾病与身体的外在表现联系的学科称之为症候学。贝尔(E. Baer)《医学符号学》(1988)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作品,聚焦症候概念,以及梳理皮尔斯、布勒、弗洛伊德以及图尔·乌克斯库尔对医学符号学的贡献,发展了“生命逻辑”(logic of life)概念,生命个体发生阶段遵循医学符号学的基本原则(Sebeok,1991:46)。西比奥克也曾经专注于生命符号现象研究,1985年为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作了系列讲座,这也直接影响了西比奥克对内符号学和外符号学概念的形成。耶茨(Yates)创造了“药学符号学”(pharmacosemiotics)这一术语,推动了医学符号学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认知科学的发展,语言、心理、认知便成为不可分割的要素获得深入探究,而皮尔斯创建的符号活动(semiosis)概念的认知意义逐渐凸显,一门认知符号学逐渐形成。心理学是研究语言外因素的重要维度,麦克尼尔(McNeill,1979)受维果茨基和皮尔斯符号学影响,在《语言的概念基础》中发展了“符号学拓展”(semiotic extension)的概念,他提出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融合假设,认为符号拓展是从空间到时间以及其他经验领域。贝尔(Baer,1988)从符号学角度研究心理疗法,基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阐释强调了交际过程对心理的重要影响,论述了交际的普遍存在,如口头的、姿势的、礼仪、政治的以及宗教的等,而西尔弗曼(Silverman,1983)则在其《符号学对象》(TheSubjectofsemiotics)中主要分析了拉康理论与符号学的联系,此外,还有《肉体符号》(Rancour-Laferriere,1985)。
以乌克斯库尔(Uexküll)、西比奥克(Sebeok)、霍夫梅耶(Hoffmeyer)、库尔(Kull)等持符号活动是生命本质的观点,每一个有机体在生命之初就开始使用符号建构自己的主观环境界(Umwelt),在符号学与生命科学间建立起了内在关联,发展了人类符号学,“真正的现实不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的科学发现,而是通过符号来自我揭示。只有这些符号是真正的现实,符号和符号活动所遵循的规则和法则是唯一真正的自然法则”(Uexküll,1982:3)。西比奥克在1976年创造了内符号活动(endosemiosis)和外符号活动(exosemiosis)这对术语,将身体器官、组织、细胞、内分泌、基因代码、神经符码、新陈代谢等视为内部符号活动,逐步发展了动物符号学、植物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细菌符号学等分支学科,推动了重新符号化运动,深度发掘和阐释自然界的符号活动模式,体现了更加充分与自觉的符号意识。“生命通过符号活动来改变宇宙,从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Sebeok,1991:135),生物符号学把符号活动视为生命的基本特征,认为所有生物的基本特征在于携带目的性的存在(teleonomy)。受“人本质上是符号动物”(卡西尔,2004:37)的影响,要理解人类就要发展一门系统的符号理论。在皮尔斯将生物的繁殖和生长视为一种符号生长(sign growth),一个新符号的出现只能源于其他符号,皮尔斯的这一断言受到菲尔绍(Virchow)格言“所有细胞都是细胞”的启发。在生物符号学视域下,意指与交际成为更广阔研究领域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心理-神经-免疫融合发展的趋势,佩特丽莉(Petrilli)和庞奇奥(Ponzio)提出伦理符号学,把人是符号动物发展为符号伦理动物,在全球符号学语境下,人作为唯一有意识的符号动物为整个地球生态中所有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科布利,2013:351)。
4 结语
国际符号学学会副会长、巴黎符号学学会会长安娜·埃诺(Hénault)在谈及《符号学思想论》(王铭玉 等,2021)时指出:“这样的一项事业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各个国家和学派有关符号学的丰富性、多样性和互补性,而不同的符号学研究则分享了有关意义世界、意指系统、传播系统和各种唯理研究的广大领域。”这样的评价和鼓励无疑是中肯的,关于世界符号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的介绍与考察将推动各学派间的交流与互动,逐渐呈现出符号学的整体样貌,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国别与区域研究以及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是符号学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方向。法国符号学界已经启动了这样的工作,《符号学问题》便是这一努力的成果,他们对索绪尔传统的法国符号学与皮尔斯传统的美国符号学做了比较研究,而且尤其观照符号学的多样性应用,如以戏剧、文学、报刊等为代表的语言符号,以建筑、绘画、音乐、电影等为代表的视听符号,以及以烹饪、时装等为代表的感知符号,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对比与分析了法国与美国符号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与实践诸领域的异同,并预示了未来的可能研究方向。
20世纪的美国符号学史上的众多学者具有不同的成长、受教育与工作经历,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各自的原因汇集美国,把他们作为美国符号学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准确的。西比奥克在《美国符号学》(1991)一书中,也论述了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符号学家们在美国符号学传播与可能性影响,如英国的奥格登与瑞恰慈(Ogden & Richards),法国的巴特(Barthes)、麦茨(Metz)、托多罗夫(Todorov)等,意大利的艾柯(Eco),德国的卡西尔(Caser)、雅各布·乌克斯库尔(Uexküll)、图尔·乌克斯库尔(Uexküll)以及作为群体的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等。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学术交流与传播,他们的各种思想与学说影响了不同地区的年轻学者,可以说,这种辐射的范围和影响将会是巨大的和持续的,符号学正逐渐超出国别的界限而向全球符号学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