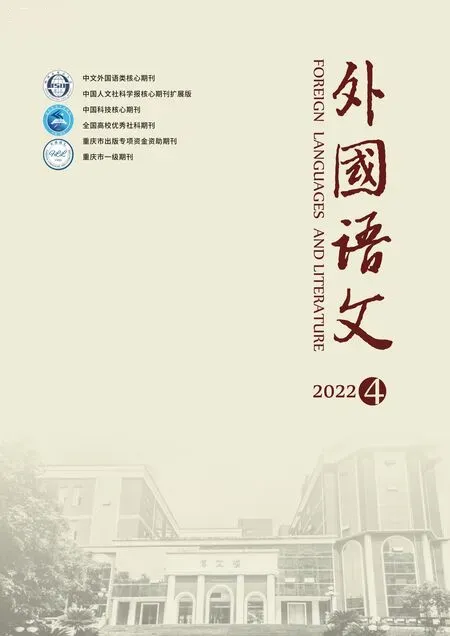毛姆《彩色的面纱》的跨国现代主义解读
黄丽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89)
0 引言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865)是20世纪较早游历和书写中国的英国作家,曾分别于1919和1921年与美国男友杰拉尔德·哈克斯顿(Gerald Haxton)一起旅行东南亚,取道上海、北京、沈阳等地,并创作了中国题材三部曲:写实游记《中国画屏上》(OnaChineseScreen, 1922)、虚构小说《彩色的面纱》(ThePaintedVeil, 1925)和短篇戏剧《苏伊士以东》(EastofSuez, 1922)。《彩色的面纱》是其中一部最有创意和争议的作品①小说最初以连载形式在杂志《纳什》(Nash)上刊出不久,一位雷恩先生(Lane)提出诉讼,因小说主人公名字为雷恩,最后出版社以250英镑平息此事,主人公的名字由此易为费恩(Fane)。但小说出版后,又受到香港政府官员的抗议,因为小说涉及女主人公与香港殖民地辅政司助理的私通丑闻,毛姆虽在前言中解释“这是一部取材于故事,而不是取材于人物的小说”,但为此引来的麻烦却令他始料不及,再版时他将香港改为虚构地点“清阴市”。本文所参考的版本为未经修改版。。国内评论界对毛姆这部作品的关注已有10余年,知网收录20多篇论文,大多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视角解读该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中国形象和中国观。但是,毛姆一向以冷傲孤寂、离群索居著称,“任何情况下毛姆都不是兴趣完全地集中,他为杂志撰稿,看中的是商业创作的金钱价值……很可能毛姆就是为了创造性地书写欧洲,这一点从结尾(主人公)回到伦敦即可判定”(Brander, 1963: 72)。另外,根据这部小说的序跋,素材取自毛姆1894年在意大利旅行期间,房东女儿给他讲述的《神曲》中一则炼狱故事——皮娅的丈夫因忌妒而把她毒死。毛姆听后久久难以释怀,将其构想为一个现代故事,但是一直苦于无法找到故事发生的场景,“直到在中国进行了一个漫长的旅行,我才找到”(Maugham, 1949:ⅹ)。最终小说于1925年付梓。综上两点,与其说毛姆旨在贬低或“东方化”中国,不如说毛姆更多地是以中国作为叙事场景,思考和关注的是欧洲或西方的问题。
20世纪初的欧洲文明出现危机,正如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中所言,战后的欧洲“以非常遍及的、集体的、难以治愈的炮弹恐惧为特点”(Miller, 1999: 24),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T. S. 艾略特(T.S. Eliot)等感时忧世,采用新的实验手法展示现代人的困境,被奉为经典文学现代主义。这种在文学艺术上兴起的批判启蒙现代性的表达即为审美现代性,又称文化现代性,较早出现在浪漫主义文学和艺术中,表现为反对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有逆反、无政府、创世论、贵族式自我流放等多种方式 (Calinescu, 1987: 42)。 20世纪出现的先锋派、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都是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主义的实践形式,也就是说文学现代主义的形式也是复杂多样的,而不仅有经典现代主义一种。
除了时间纵轴上的多种现代主义,还有空间横轴上的跨国现代主义,都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启蒙现代性工程的恶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量英国作家跨国旅行,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启程前往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wood)去了柏林和加利福尼亚,W.H.奥登(W.H.Auden)去往纽约,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到了中国和俄国,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到过法国的里维埃拉、奥斯波特·西特维尔(Osbert Sitwell)到了意大利、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和I.A.理查兹(I.A.Richards)在北京、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任教武汉大学、威廉·燕卜逊(William Empson)到了东京和北京,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利比里亚半岛之旅,他们为西方文明寻找出路。毛姆身处英国文化场域,在《彩色的面纱》中采用跨国现代主义嘲讽“西方的没落”。通过深入分析《彩色的面纱》中现代英国女性凯蒂(Kitty Garstin)在梅潭府的觉醒和救赎之旅,本文认为毛姆并非真正地丑化中国,而是借用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跨文化再现策略和认知模式,即跨国现代主义,批判启蒙现代性以来中产阶级庸俗的婚姻观、实证理性和清教伦理。跨国现代主义展示了西方知识分子向异域的“他者”文化寻求改变欧洲衰败倒退之方的人道主义情怀。
1 在梅潭府的原始景观中复苏直觉意识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具有主体性,但同时也是社会文化的表征和缩影。作为现代女性,凯蒂从小生长在伦敦一个家境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长相出众,周围不乏追求者。但流连于家庭舞会的凯蒂无意之中错过了最佳的择偶年龄,无奈地嫁给了呆板木讷的香港细菌学家沃尔特·费恩(Walter Fane)。在《彩色的面纱》中,毛姆为我们揭示了20世纪伦敦中产阶级趋利实用的婚姻理念。“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在遵守维多利亚时期政治制度的管理,赞颂帝国这一谨慎的形象,尤其是严肃内敛、缄默无声和虚伪矫饰的性态,直到今天仍然受其思想控制。”(Foucault, 1978:3)正如福柯指出,在17世纪以前性实践行为并没有被编码,那个时期身体可以充分展示自身,但随着启蒙现代性的步伐,“性态受到严格规范限制,被转到家庭领域,婚姻家庭监控性态,将之纳入严肃的生殖功能之内”(Foucault, 1978: 3)。虽然福柯在《性史》中探讨的是西方的“性压抑”史,但揭露了实用主义为原则的中产阶级婚姻制度对人性直觉和欲望的禁锢。在《彩色的面纱》中,女主人公凯蒂转眼“到了25岁仍然未嫁出去”(Maugham, 1949: 22),这对于凯蒂和她父母而言,不啻为奇耻大辱。因而,当名不见经传的香港细菌学家沃尔特·费恩出现并求婚时,韶华已逝的凯蒂仿若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如果嫁给他,她将和他一道(去中国香港),不然出现在妹妹多丽丝的婚礼当伴娘将不会那么有趣,她宁愿逃离那里”(32)。可以看出,凯蒂的婚姻选择出于无奈。
就像一部侦探剧,《彩色的面纱》初始的场景设置在女主人公凯蒂在香港的卧房,时间为炎热的中午,凯蒂与情夫偷情的一幕被窥视,二人诚惶诚恐,凯蒂担心被丈夫沃尔特·费恩发现。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读者通过凯蒂的回忆,了解到新婚后的凯蒂经常随夫出入香港大小宴会,她对自己的生活非常满意,“非常欢愉快乐,她愿意每天说个不停,很容易开心大笑”(35-36),而她的丈夫却不苟言笑,喜欢独处。当她发现在香港“她的社会地位是由丈夫的职位决定……而作为政府细菌学家妻子的身份甚微,这令她气愤”(11)。这种秩序由职位决定,并决定着生活各个方面。比如她的新房位于“幸福谷”的小山边,能看到蓝色的海洋和熙熙攘攘的船只往来的港湾。相比之下,殖民地辅政司秘书查理·汤森德(Charles Townsend)夫妇居住在“尖峰”别墅。那里临海,景色别致,受人尊敬。于是她被前程似锦、激情四射的查理·汤森德吸引,坠入爱河。如果说在文明社会,功利世故的价值观筑造了她“无奈”的婚姻选择、禁锢了她的欲望,那么在香港凯蒂以女性身体僭越婚姻和伦理秩序,这也注定她会成为白人男性社会的“他者”而被丈夫惩罚,被迫与丈夫一同前往瘟疫肆虐的中国内陆城市梅潭府。
与凯蒂成长的秩序井然、庸常俗套、虚伪矫饰的伦敦和香港不同,小说中的梅潭府“无序”“奇怪”“神奇”。刚到梅潭府,凯蒂神情恍惚,深陷旧情,这从她多次经历的梦境可窥一斑。经过乘船和人力车的长途跋涉后,凯蒂梦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环境,周围人都驻足嘲笑她,这时情夫查理来到她面前,“把她抱在怀中,把她从椅子上拉起来,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她感到他吻她嘴唇,她悲喜交加……突然听到粗鲁急促的喊声,他们分开,一群苦力急忙而无声地从他们中间穿过,穿着破旧的蓝色衣服,抬着一个棺材”(109-110)。 “梦”往往是无意识的体现,是人在现实世界中受压抑、未实现的梦想的回返。凯蒂虽然痛恨二人事情败露后汤森德的自私无情,但她仍深陷情网无法自拔。
凯蒂的第一次觉醒发生在她到达梅潭府后的一个清晨,异域生疏的自然风景带给她全新的生命体验,将她从文明社会的记忆中抽离出来。清早起床,她透过窗户看到河中的帆船“成百上千,宁静而神秘地停靠河上,光怪陆离的光线中,令人感觉那水手有着某种魔力,帆船也仿佛并没有停息,有某种奇怪可怕的东西令这一切如此寂静无声”(110)。这景观抚慰了她汹涌起伏、矛盾复杂的内心情感。在文明社会中,人们期许和渴望的是美满婚姻、崇高的社会地位与身体的愉悦。而这种景观的浪漫之美和宁静的神秘感不仅从身体上而且从灵魂上唤醒了她的直觉生命。她放眼清晨的江上景色,开始用心灵之眼体味异域的自然风景:
太阳透过薄雾,白色光芒仿佛隐伏在暗星上的雪白幽灵。尽管河水明亮,可以隐约看到拥挤的舢板的轮廓和排排桅杆,再远处是眼睛无法穿透的刺眼厚壁。突然,从那朵白云后闪现高耸的、阴冷而巨大的一座堡垒。似乎不仅在无处不在的太阳光下呈现,而是由神奇魔杖下骤然出现。残酷野蛮种族的要塞高高耸立江上。但魔术师陡然变化,彩色围墙装点堡垒。一会儿,薄雾后面是绽放黄色光芒的巨大太阳,照射着一行行黄绿相间的屋顶,错落有致,忽又消失。出乎意料地,放肆地,难以想象地神奇。这不是堡垒,也不是庙宇,却是天帝的神奇宫殿,没人能进。它虚幻空灵、变幻莫测、无影无形,不是出自人工之手;而是梦境的造物。(110-111)
梅潭府自然风景的宁静壮观和原始的神秘无序,开启了凯蒂久违的“浪漫之美”的体验之旅,她开始挣脱情欲的困扰。其实,她看到的不过是城墙外的庙宇,但由于这个迷狂的体验,异域自然风景直观地唤起她的感受,她惊叹于“自然之神奇,即使还有秩序,你也无从找到。毫无方向、放肆无度、超出寻常的丰富多彩”(111)。这种体验是在貌似秩序井然却物欲横流的白人世界不曾有的。在这梦幻般的直觉体验中,她激动地落下眼泪,心情从未如此轻松愉快,感到身体与灵魂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截然分开的两部分,感慨道:“仿佛身体是个空壳,落在脚下,自己是灵魂。”(111)这暗示凯蒂从伦敦物欲横流、理性约束的社会脱身,从香港等级尊卑有序的氛围离开,在梅潭府的自然景观中觉醒,她的灵魂如同受到超脱净化一般,与她融为一处,物质性的身体不过是虚假的外壳,只有灵魂具有超越性。在梅潭府,原始的自然景观唤起她久已麻痹的直觉感性,为她摆脱身体的污秽罪恶、走向精神超脱铺垫了序曲。
2 在瘟疫肆虐的梅潭府找回智识情感
小说中的梅潭府不仅被再现为原始的场所,还是一个瘟疫肆虐、危险丛生、充满死亡威胁的炼狱空间。费恩心怀怨恨带着凯蒂置身于异域空间,犹如天外来客。作为细菌学家,费恩理性、冷酷、不苟言笑,是科学的化身和理性的代言人,代表受文明洗礼的西方现代人。到了梅潭府,费恩仿佛救世主一样投入瘟疫防控事业。他不禁令人想到大航海时代以来远征东方的商人、传教士与外交官,他们都反映了启蒙工程所秉持的科学精神和解放事业。但正如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所言,“启蒙被视为最大意义上的思想进步,解放人类,以远离(愚昧造成的)恐惧,以将人塑造为主人为目标。但整个被启蒙的大地却笼罩在凯歌高奏的灾难中”(Horkheimer et al.,2002: 1)。如果说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一语道破了启蒙的“神话”,认为科技“无法亦不能产出观念和图像,更毋庸说赋予人以理解的欢愉,而它只关注方法,利用他人的劳动获取资本”(Horkheimer et al., 2002: 2),那么费恩正是这种把工具理性当作社会主导逻辑的产物,受困于以计算或量化看待各种事物和事件思维惯性,失去对实际性质、行为苦难和存在意义的思考能力。与费恩不同,妻子凯蒂在梅潭府死亡威胁的状况下,放眼周遭,心生同情,灵性生命被唤起,发生了第二次蜕变。二者不同的遭遇与结局,体现了毛姆对科学和理性的嘲讽与批判。
首先,梅潭府的死亡威胁唤起凯蒂对道德伦理与生命意义的感悟。在前往梅潭府的住处的路上,映入凯蒂眼帘的是牌坊,“她知道那是为了纪念某个德高望重的学者或贤德良姝的寡妇……在太阳西下的暮霭中,牌坊显得更加神奇和美丽”(101-102)。牌坊是中国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建筑,为歌功颂德或纪念贞节烈妇,体现着高度的道德感。她看到“到处是绿色的山包,一个紧挨一个”(102),她知道这是墓地,“四个农民快速而沉默地走过去,抬着一个新的棺材,未喷漆,新木板在黑暗中闪着白光……她恐怖的心跳到脊梁深处”(103)。如果说贞节牌坊与墓地、棺材令凯蒂震撼、羞愧、恐惧的话,目睹死尸令她思考生命与伦理道德的意义,“院子的墙脚躺着一个人,面朝天,两腿张开,胳膊蒙着头。穿着补丁的蓝色破旧衣衫,头发凌乱披散,就像中国乞丐”,“凯蒂身体剧烈地颤抖,无法移动”(122)。我们不要忘了凯蒂是受英国的世俗社会熏染、纵情声色、遭受流放的浅薄女性。再次见到尸首,她对死亡的理解已经超越时空:“死亡很可怕,任何其他事情在死亡面前都显得那么微小。那尸首看起来并不像人,你看他,真难以相信他曾经活着,更难想到就在不久的几年前,他还是一个小男孩,曾经手中拿着风筝疾跑下山。”(128)在异域遍布的死亡威胁面前,凯蒂发生从肤浅到深邃的精神蜕变,开始意识到人的渺小、道德的崇高和生命的过去与现在。
其次,死亡威胁的生命体验令凯蒂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丈夫与婚姻的真谛。当初丈夫为了惩罚她的偷情行为而将她带到瘟疫肆虐的梅潭府,令她心生怨恨,但到了梅潭府她得以从他人的评价中审视丈夫。海关官员瓦丁顿(Waddington)告诉她对丈夫的评价:“我尊敬他,他有头脑,人品好,这两点是超乎寻常的品质……他在救死扶伤,清理城市,整治河道。他不计较去哪、做什么,每天冒死数次,他令于上校俯首称臣……修道院的女尼也听他派遣。”(125-126)她发生转变,认识到丈夫是个英雄,对他由原来的厌恶之情变得肃然起敬。当她听到女尼说:“你不知道你丈夫对我们多么善良友爱。他是上帝派送给我们的……你一定替我们照顾好他。”(142)她勇敢地忏悔“我对你非常不好,我不忠”(149),并感叹道“我为你骄傲,沃尔特”(150),这言谈令沃尔特吃惊。
凯蒂在智识上的改变最终上升到具有悲悯、宽恕的情感。对于自己不光彩的过去,她对丈夫说道:“我不想让你原谅我,不求你像以前那样爱我,但是我们能不能成为朋友?人们在我们周围成千上万地在死去,还有那些修道院的女尼。”(150)凯蒂希望丈夫能从痛苦中解脱,学会宽恕:“我不禁感到,为一个愚蠢、对你不忠的女人而灰心沮丧,是多么荒谬与不值,我对你而言不值也不重要,不要在乎我。”(150)忏悔不能令丈夫饶恕,凯蒂更进一步认识到丈夫的爱恨根源并不在她,而是他自己内心理想的破灭,“因为他给一个木偶穿上漂亮外套,把她放到神殿膜拜,然后发现木偶不过是木屑内瓤,他无法原谅她和自己,他的心碎了”(154)。凯蒂认识到这才是丈夫不愿饶恕自己,宁愿深陷复仇深渊的缘由,她不禁感叹:“他为什么没有意识到她刚刚体会到的,在死亡威胁阴影和她所看到威严的美丽风景中,他们自己的事情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如果一个愚蠢的女子犯下了乱伦之罪,为什么她的丈夫每日面对崇高还要对此放不下难以释怀呢?那有什么意义呢?”(154)因此,她感慨道:“事实上,是他自己无法原谅他自己。”(154)
小说中的凯蒂是一个圆形人物,她不仅体验到个体生命的灵性回归,还拥有了奉献精神和正义感。她自愿到修道院义务服务,在奉献中体味从未有过的满足。当沃尔特得知凯蒂身怀有孕,满怀期待地问她那个孩子是否是他的,在这个可以如愿改变他们僵化关系的关键时刻,凯蒂战胜私心杂念,在正义感和良心的驱使下,她说“不知道”,将二人之间本来可缓解的感情推到难以复合的境地。也许费恩无法面对蜕变的凯蒂,也许无法面对自己婚姻选择的失败,他最终身染霍乱。他临死前借用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挽歌》的最后一句“是狗死了”来映射自己心碎的一生(227),嘲讽自己像狗一样被理性社会异化,毫无自我。凯蒂清醒地认识到“沃尔特死于心碎”(236)。如果说毛姆《彩色的面纱》的小说素材来自但丁《神曲》的皮娅故事,但小说结局却是有意戏仿——女主人公凯蒂并没有死,反而是沃尔特染病身亡,作者仿佛在用沃尔特的死讽刺科学理性的荒谬和现代人的卑微。
3 在梅潭府受精神洗礼后超脱重生
启蒙运动以来,科学压倒宗教、知识压倒迷信,宗教作为科学知识的对立面不断被批判,但在西方社会却从来没有退场。16世纪宗教改革后,新教宣扬的世俗理性取代天主教的神学理性,在启蒙现代性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神性让位于人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深入地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共生关系,认为宗教改革改变了基督教的伦理模式。与天主教修道院的理想——超越世俗存在——的需求不同,清教提倡现世苦修,承担责任与义务,这令宗教行为具有了现世的关怀,成为伦理道德的最高形式;与此同时,加尔文主义的“预定论”宣扬那些尘世行为的“良好行为”,一些人会因此受到嘉赏而成为上帝的选民,免于责难,会因财富积累、冷静节俭在道德上受到上帝的嘉奖,只有财富被用作沉迷奢华的生活时才受谴责。由此,“新教的道德责任是财富积累,这成为新教徒的人生观和自我道德约束”(Giddens, 2002: xiii)。新教的这种伦理观带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一路高歌猛进,成为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而英国是新教国家也是欧洲工业化最早的国家。在《彩色的面纱》中,毛姆充分肯定的并不是启蒙现代性的新教伦理,而是异域古老的宗教道德——中国道教和法国天主教——对凯蒂的救赎作用,受到古老的天主教和中国道教的灵魂洗礼后,她最终彻底发生精神蜕变。
小说中对异域中国的宗教没有明显描述,而是借助与凯蒂深交的瓦丁顿这个人物,毛姆令英语世界读者领略到中国道教超验的神秘性以及带给西方现代人的超凡脱俗感受。瓦丁顿是英国海关副税务长,虽然其貌不扬,但精明有趣,“充满怪念头和奇闻逸事、直率坦白”(119)。他在中国20多年,受中国文化熏染,汉语流利,娶满族公主,讲中国历史故事,“他以玩笑的态度看待生活,尖酸地取笑香港殖民地,而且嘲笑梅潭府的中国官员,嘲笑肆虐城市的瘟疫。任何悲剧故事或者英雄故事,他讲起来都有一丝荒谬可笑”(119)。在瘟疫肆虐的梅潭府,他有着一种诙谐豁达的人生态度,在凯蒂看来,他已经开始采用中国人的视野,视欧洲人为野蛮人,“在中国才有可能使明智的人体会一种现实。这里有令人反思的土壤,从前凯蒂总听说中国人堕落、肮脏、无法交流。而今,仿佛窗帘的一角偶然被拉开,她窥视到一个充满色彩、如此重要的世界”(120)。在她看来,是中国的宗教精神改变了瓦丁顿的人生信念,小说中有一段对话揭露中国道家的道:
道是大道和行大道者。是永久的道,所有人都用道,但道没有制造者,因为道本身就是道,是每件事物又不是什么事物。从它衍生万物,万物遵从它,万物返归它。道是无棱之角,无声之声,无形之相。如一张大网,浩瀚如海,却空无一物。道为万物所依,但又无所在,无需向外看,就能看到它。它教人:欲所不欲,自然无为。委曲求全,曲中求直,败乃胜所依,胜乃败所伏。无人知晓何时为转点?道柔弱如孩童,柔能制胜,柔能安全。胜己为强者。(234)
瓦丁顿的言行个性、所受的中国道教思想的熏染可以说是对凯蒂世俗观念的冲击、洗礼和净化。
其次,古老守旧的法国天主教徒的无私奉献进一步令凯蒂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梅潭府的修道院与伦敦和香港的世俗奢华环境截然不同,院长嬷嬷和修女们的慈爱奉献又与势利虚伪的英国人形成对比,这使凯蒂在功利与奉献、世俗与脱俗中幡然醒悟。修道院内静穆而安宁,令人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超越空间与时间。空空的屋子,白色走廊,肃穆而简单,似乎有着某种遥远和神秘的精神。白色教堂简陋而粗朴,透着凄凉;它有着染色玻璃和壁画装饰的大教堂所缺乏的东西,它很卑微;但是有信仰装点它,有爱滋养它,这个教堂充盈着心灵之美”(143-144)。简陋的修道院与瘟疫横行的外部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它仿佛是炼狱中的避难神庙,救助染上霍乱的士兵、居民以及被遗弃的女婴和儿童的生命,在死亡之界焕发着光芒。
如果说修道院是神圣的避难之所,那么天主教嬷嬷和修女们的慈爱与勇敢令凯蒂认识到天主教赋予的人性光芒。她眼中的院长嬷嬷“是个美丽女性,她的美来自性格,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增长……她有着基督教慈爱赋予的威严气质”,凯蒂“模糊地感到在她身上有某种气质难以形容”(136),无形中,她感到似乎自己在院长嬷嬷面前像个小女生。她看到院长嬷嬷受到中国孩子的爱戴:
当院长嬷嬷进门,长着黑色中国眼睛、黑色头发的两三岁的小孩子马上围着她。他们抓住她的手,藏在她的大裙子里。喜悦的笑容点亮她严肃的面庞,她爱抚着他们……她(凯蒂)打了个冷战,因为他们穿着一样的服装,蜡黄皮肤,矮小,扁平鼻子,在她看来他们根本不像人类。他们令人作呕。但是院长嬷嬷站在他们中间,就像慈爱的化身。(138)
天主教的仁慈和普爱精神感染着她,领悟到“……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肉欲中,在俗世还是在修道院,人都找不到平静,平静只能在自己的灵魂中找到”(161)。“凯蒂奇怪地感觉自己在成长……她开始重振勇气,感到越来越美好而坚强。”(171)她由浅薄、世俗、浮躁的英国白人女性转变为充实、独立、宁静的女性。院长嬷嬷一语道破:心灵的钥匙乃是爱的义务,“当爱与义务合而为一,人也就气度优雅,会感受世人难以理解的幸福”(245)。她不仅忘记了情夫查理,而且原谅了丈夫的死亡惩罚,开始对生活充满信心,她焕发出一种美,与中国孩子一起玩耍,“她流波闪烁的眼睛放着光芒,美丽的头发凌乱铺开,可爱的笑容绽放脸上”(173)。
凯蒂终于完成了最后的蜕变,对生命有了哲思和领悟。如果说梅潭府的霍乱、死亡、贞节牌坊乃至沐浴清晨中的自然之美令凯蒂体验到崇高之情,那么修道院、院长嬷嬷、修女和救助中国孩童让凯蒂重获心灵宁静和幸福真谛,“唯一令我们这个世界值得不厌烦地生活下去的是美,人们不时地从混乱中创造的美……所有美的丰富形式中,最美的是美丽生活,是完美的艺术品”(233)。她感叹人世转瞬即逝,“……人类就像河流中的水滴,水滴流淌,每个水滴彼此紧邻,却又分隔甚远,(每个生命)是一条无声的洪水,奔向大海”(176)。她将自己和丈夫沃尔特看作两个水滴,彼此个性不一,却完全没有意义,彼此折磨憎恶,“生命很奇怪,我感到自己像一个在鸭子池塘过了一生却突然进入大海一样。我透不过气,却欢欣鼓舞。我不想死,我想活下去。我感到全新的勇气。感觉自己像个老水手,即将扬帆驶往未知海域,我的灵魂向往一切未知”(180)。瓦丁顿认为她所寻找的是道,“我们有些人在鸦片中找到它,有些人在上帝那里(找到),一些人在威士忌中(找到),一些在爱中(找到)”(203)。她也从最初的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肤浅女子,蜕变成一个拥有直觉判断、智性能力,精神独立的女性,“她自由了,自由,她几乎抑制不住地大笑起来”,感到自己“被治愈”(172)。
4 结语
综上所述,《彩色的面纱》中凯蒂这个英国现代女性的成长经历在文本中体现为:受伦敦代表的文明世界的规范而嫁给细菌学家,前往香港僭越婚姻而失足,在异域中国的梅潭府重获新生,返回香港,返归伦敦。凯蒂返回香港后令人失望地与查理私会,重蹈覆辙。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是毛姆在小说中的败笔,但笔者认为这符合毛姆对西方社会的批判逻辑,这个情节似乎在影射任何人进入社会大染缸,都难以逃脱污秽,难以保持清纯。最终凯蒂回到伦敦,与父亲团聚,忏悔从前对父亲的冷漠,开始全新的生活。可以说小说结局既表达了毛姆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也寄托着他对未来的希望。但重要的是,在凯蒂重获新生的成长经历中,梅潭府是中间站,是个跨国的原始空间和前现代的存在。经过梅潭府这个异域时空的洗礼,凯蒂重获新生。
自启蒙时期以来,异域他者一直在文学作品中作为欧洲的对立面存在,如《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殖民地安提瓜岛、《德伯家的苔丝》中的殖民地巴西、《黑暗的中心》里的非洲,都是需要白人前往开垦拓荒、拯救的场所。但“从1907到1935年间,出现了一场运动,现代性主体对种族他者的人物和文本在认识论的地理版图上进行了重新解读和阐释,重新认知种族属性,在定义和书写方式上进行了巨大改变,可以认定为一场文化原始主义浪潮……”(Sweeney, 2004: 2),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代的焦虑颠倒了贬低的方式,将他们变成救世主特点”(Johnson, 1973: 95)。毛姆在《彩色的面纱》中呈现出异域拯救西方现代主体的特点,这是跨国现代主义的表达,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神话世界,异域成为一个未经现代性洗礼、未曾沉沦的“他处”,代表着一种新的跨文化审美形式,被赋予了修复和批判一战后受挫的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使命,成为开拓主体性过程的场所。因此,毛姆在《彩色的面纱》中再现的原始中国虽然基于他的旅华见闻,但更多的是融入了他的想象、批判和期许,正如雪莱(Percy Shelley)在诗中表达的一样:“别揭开这彩色的面纱:呵,人们称之为生活,虽然画上没有真像;而只是仿制我们意愿的事物……”(1970: 569)异域中国的前现代、无序状况表达着现代作家对“那逝去的美好岁月”怀旧的浪漫情怀以及对启蒙现代性渊薮的批判。跨国现代主义体现了西方知识分子向原始异域的“他者”文化寻求改变欧洲衰败倒退之方的人道主义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