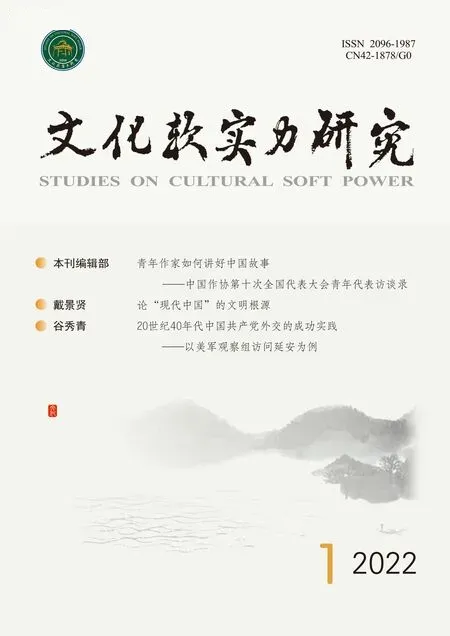从政治文化传统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侯文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所,四川成都 610072)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针对时代需要和国家发展需要提出的。尽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提出的新概念,但却始终隐含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在中华文明历程中,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有机整体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各民族关系尽管有时冲突,但更多的是相互融合、相互认同。这既是由于中华民族居住的地理条件以及经济上互补共存的现实原因造就,更是由于中华民族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文化传统。这就是齐其政、修其教、因其俗。这三点出自《礼记·王制》,文中讲:“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食火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食火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1]正因为中国与蛮夷戎狄的习性各有不同,所以,“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1]对于这些“殊异”,在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必须齐其政、修其教,来加以管理。其中,齐其政,是政治前提;修其教,是文化根脉;因其俗,是治理策略。古代有识之士从这三方面努力,促进了中华民族从松散联盟向有机整体逐步牢固的进程。对今天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齐其政
齐其政,是说政令刑法划一。在古代,就是要承认以天子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相应的政策法令法规,就是要在行动上确保大一统政治的稳定。任何要触犯大一统、破坏大一统的行为或人事都是不被允许的。这是因为“大一统”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1918,是源于天地之本源,古今之共性,拥有天道、历史的根据,因此大一统具有至高无上性、神圣性、不可动摇性。在中华文明史上,真正实现大一统是在秦汉之际,而在这之前,关于天下一统的论证多见于诸子的论述中。
《论语·宪问》中,子贡问孔子:“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3]151子路对管仲辅佐齐桓公之事有微辞,认为管仲所为“非仁”,而孔子则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3]151孔子赞扬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做法使民众得到了好处。同样的问题孔子学生子路也问过,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3]151在孔子看来,管仲辅佐齐桓公后所成就的事业,能使诸侯罢战,人民得到安宁,是值得夸赞的,他的行为就是仁者的行为。从孔子的夸赞中,可以看到,在孔子思想中,天下应该统一,这样民众才能得到好处,能使天下统一、有秩序的行为,就是仁德的极好体现。
孟子政治思想中,也主张天下要统一。《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谒见梁襄王,梁襄王问:“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4]12就是说,天下要想安定,必须要统一。孟子认为,天下要想统一,必须行“仁政”,用王道,如此,人心归顺、天下安服。孟子说:“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4]190只有以良好的道德来熏陶教养人民,天下才能归服,人心才能归顺,离开了善德,而想称王天下,是从来没有的事。
到了荀子之时,天下统一的大势日益明朗,荀子预见到这一趋势,因此最为明确地提出了“一天下”的主张。在《荀子》一书中,多次提到了“一天下”。例如,在《荀子·王制》篇中,荀子描述了当时小农经济、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水陆交通的便利,以及诸侯国之间经济贸易往来的不断加强,正在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5]102的局面,因此,荀子明确提出:“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5]108荀子将“一天下”看做是天王之事,给予很高的期望,并从士农工商、君臣父子、礼乐政刑多方面加以阐述,荀子不仅强调了天下统一的政治、伦理、经济等的一体化的必要,还注重思想统一的必要,在《荀子·非十二子》篇中,荀子对当时显明的各家,像墨家、名家、思孟等六家学说,共十二人的主张作了批判。荀子主张:“六说者立息,十二子者迁化。”[5]61强调了思想上统一的必要性,如此,才能“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5]61同样,处于战国后期为即将建立的秦帝国政治服务的《吕氏春秋》也强调:“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摶之也,一则治,两则乱。”[6]1132“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6]
先秦诸子强调的天下统一,到董仲舒时阐发的最为明确。他指出,大一统,可以改变“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2]1918的局面。董仲舒还进一步阐述到:“《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来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也。”[2]1904从此,以大一统为模式的王道政治成为实现天下统一、民族发展的政治文化理想目标和主流价值取向。而无论是“定于一”还是“一天下”,这个大一统,都包含着“诸夷”与“夷狄”。正像《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时讲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7]意思是说,这样的大一统,是包括了“诸夏”与“夷狄”的,不是讲天下有内外,而是讲治政的由近及远。
从春秋战国分裂到秦汉大一统之后,历代王朝,无论是统一还是分裂时期,崇尚政治上的统一、反对分裂,始终是一以贯之的主旋律,既体现在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度主体并无大的变化,还体现在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始终牢固运行上。
在多民族大一统发展历程中,秦汉、唐代、元明清三个时期,是多民族大一统发展的高峰时期。通过有意识的制度设计,使四方之民归附中央,成为中央集权制度下的一份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戌。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8]秦始皇通过设立桂林群、象郡、南海群,以及诸多县,确保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在政治上的一致性、统一性。比之秦始皇,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更是在更广范围实现了“海内一统”[9]:“在东北边疆安抚朝鲜,设置了乐浪郡、临屯郡、玄菟郡、真番郡;在北方不断发动对匈奴的反击;南抚诸越;开西南夷,设置了益州郡;等等。”[10]160
通过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格局。像秦汉时期边疆少数民族设置特别行政区“道”;唐朝设置边郡、边州;元朝形成了土司制度。清朝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区采取的“改土归流”政策。此外,像唐代为了维护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在边疆设置了安西大都护府、北庭大都护府、安东都护府、安南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等,对吐蕃、南诏、渤海等民族则以多种方式建立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有联系的政治关系,例如册封松赞干布为驸马都尉、西海郡王,册封南诏,册封渤海,等等。”[11]164
通过这些措施,从政治制度、政治体制、职官设置多层面构筑了一个以天子为核心、以中央集权制度为主体的政治网络,保证了大一统的政令通畅、统治有效,成为构筑多民族有机整体重要的前提。
二、修其教
修其教,是说要实施礼仪教化。古人认识到,要形成多民族共同体,除了政治上的安排,还需要文化上的引导,只有文化才能从根脉上柔化人心、凝聚人心。礼仪教化说的是用以儒家德治、仁爱等为主要内容的礼义道德规范去教育、涵化各民族。从历史上看,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1]5-6尧早在上古时代就以美好的德行使各邦族之间团结和睦、亲如一家。这说明,在上古时代处理氏族、部落关系主要是通过道德的力量使人们团结起来、和睦起来的。而西周时期,在反思殷商灭亡的过程中,周公意识到 “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12]224,一个政权的合法性、长久性并不来自于天命鬼神,而是来自于“敬德”。周公对德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刑罚的运用中,有感于殷商刑罚苛严、不得人心,主张“明德慎罚”[12]181、以德为先,不滥用刑罚、伤害百姓。这些主张成为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主张的思想渊源。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11他认为,为政者要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就可以赢得民众的归顺与拥护,就像繁星围绕北极星一样。如此,就可以实现良善政治。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治主张,主张以仁政、王道统一天下,反对以武力、霸道政治统一天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4]74,这是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做不到的。
在《吕氏春秋·十二纪·异用》中还讲了商汤网开三面、德及禽兽的故事:“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罹)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12]560君王宽厚仁德已经广及禽兽,此举使四十国感化而归附。正因如此,古人提倡以以德为先、先德后武的原则处理民族关系。古人认为,人心、人性是相通的,“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一也。”[6]1293-1294不同民族、不同风俗,但人之性、人之欲是相通的,人们的心理是相通的。以德化人可以起到攻伐战陈起不到的作用,能够赢得人心。在《吕氏春秋》中还讲了禹服三苗的故事:“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周明堂,金在其后,有以见先德后武也。”[6]1256以德为先、先德后武,成为处理民族关系重要的政治文化经验。
汉初,面对匈奴“挠边疆,扰中国,数行不义,为我狡猾”[13]的局面,贾谊上提出“三表五饵”之策。提出:“今汉帝中国,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13]也是主张行仁德,以服四方。董仲舒则更进一步强调“王者爱及四夷”[14],主张对遵守儒家礼义的少数民族要以仁爱之心相待。
不止于以仁爱、仁德去感化少数民族,古人还从礼义教化等方面用力,以促进文化沟通与文化融合。孔子曾言:“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言导民,以刑禁之。”[15]孔子主张应首先以德教、礼治,即礼义道德之“教”来化育人民,反对以刑罚为主的治民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只能在礼义教化不起作用的时候,才能使用。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也重视礼义道德教化的作用,强调要在民众安居乐业的同时,“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4]17荀子则说:“不教无以理民性”[5]328这些主张都成为古人强调以礼义道德教化少数民族的思想渊源。其典型就是兴办各种礼义教化学校,以礼义道德教育、引导不同民族,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认同。例如,“唐太宗击破突厥颉利可汗之后,依彦博之策,‘救其死亡,授以生业,教之礼义’,欲其“数年之后,悉为吾民”。盛唐时代,在国子学中广泛招收四方子弟,教以‘中国之学’。宋则在熙州、广州等地设‘蕃学’,以‘中国文字’和佛经等教授‘蕃人’。明代,与土司制度配合,‘谕其部众,有子弟皆令入国学’,接受儒家教育,并在土司地区设立学校,‘宣慰、安抚等土官,俱设儒学’。清朝实行的则是针对不同民族的教育政策:八旗以‘骑射’为根本,亦重儒学;南方土司地区以‘文教为先’,在其地设义学、社学、书院等,广招土司子弟入府州县学,并在学校科举中专设土司名额。”[16]通过这些措施,使少数民族接受儒家文化熏陶,掌握儒家思想、学会儒家礼义道德,为实现文化融合进而促进民族融合打下了基础。
三、因其俗
因其俗,就是顺因其习俗进行治理。即在承认天子统治的前提下,中央允许少数民族实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治,保留其本民族的一些制度、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对边疆地区的因俗而治最早可上溯到西周早期。齐国治理东部边疆东夷时采用了因俗而治的政策,《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17]因其俗,从观念上讲,关键在“贵因”。因,就是因循、顺应、依据的意思;贵因,就是在治国理政中要注重因循之道。老子最早以无为之道论述了治国的方针,《管子·心术上》中则将老子无为思想做了吸收和发展,“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18]强调要遵循事物本性、客观规律治理的道理。古人认为:“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13]925只有依据客观情况,发挥主观能动性,事情才能取得成功。 “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13]927“因”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治国理政应该因人情、因人性、因民心、因民俗等,如此,事业才能成功。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朝在与匈奴的关系上,就经过了长期的探讨,最后制定出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班固在《汉书·匈奴传》开篇就对匈奴的历史、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等做了介绍,“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苟利所在,不知礼义”[19]。班固还指出,自先秦开始,华夏族就以本民族为中心制定了相应的策略:“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页。”[19]2830从华夏族立场看,“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略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19]2830班固尽管从华夏族优越的立场出发,但是,其所阐述的夷狄之性以及由此而制定相应的羁縻政策,却反映了因俗而治、不拘一格的道理。
从最高政治统治上看,一方面,边疆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离中原统治中心遥远的边塞,不好控制与管理;另一方面边远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不论在发展程度上,还是在风俗习惯等方面,与汉地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果强行将汉地制度移用到民族地区,只会徒增压力,而且很难奏效。因此,历代王朝在确保最高尊荣和主权的情况下,往往对民族聚集地区实行比较特殊的管辖制度。例如,“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平定突厥,突厥愿意归附,唐太宗除将突厥十万互内迁到中原地区之外,又在突厥原所在地设置羁縻府州。在行政管辖方面,任命该族各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县令,责令他们统率原来的部众,允许保留本部族原有的治理形式,保持半独立状态。……羁縻府州虽然有较大的自治权力,都督、刺史也多由原部族首领担任并且可以世袭,但这些都督、刺史都必须由中央任命,同时还取消了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原有的 ‘可汗’称号,说明他们仅仅是大唐属下的特殊民族自治区。”[20]
因俗而治,因具有怀柔的特点,成为历代王朝治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重要的政治方针和文化政策。即使对于犯法者,亦有因俗而治的规定。《唐律疏议·名例》 中“化外人相犯”规定为:“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在解释这段规定时指出:“化外人,谓蕃夷治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同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21]因俗而治的方针因为切合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中央利益与边疆地区利益,既顺应了民情民俗,又因势利导使之成为巩固王朝统治、维护政权的有利方式。
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借鉴古人政治智慧,而齐其政、修其教、因其俗就是古代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治理、民族关系协调的主要政治文化传统。现在来看,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现在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共同体,同时,由于时代及观念的进步,对于存在的民族矛盾更多从法治上着眼、从发展上想办法,比之古代,有了更大的进步。
(一)政治认同是前提
在古代处理多民族关系时,齐其政是前提,要求承认中央王朝统治,保证政治上的一致性。这一前提,为实现多民族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延续至今的重要政治因素。在当代,齐其政,就是要达到政治上的认同。
具体而言,这一认同体现为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等的认同。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从具体政治制度而言,就是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了国家团结统一,又实现了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是“统一”和自治相结合。首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22]。无论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政治看,保持大一统下的各民族团结一致是各民族发展、稳定、繁荣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族区域自治。其次,民族区域自治必须在确保国家政治、法令一统的前提下,依法自治。各民族都要自觉遵守法律,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
(二)文化认同是根脉
在古代处理多民族关系时,修其教是主要的文化原则与措施,其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文化融合,进而达到文化涵化。这是凝聚人心、促进民族稳定、民族团结的重要经验。在当代,这一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23]“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2]157为此,要将“多”与“一”有机结合起来。
首先,既要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特色,又要促进文化交流和文化沟通,推进中华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此基础上,还要搞好各民族地区各类各级教育,不断提高各民族科学文化素质,通过文化交流、融合,夯实民族团结的基础;对于影响民族团结的思想,如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都要加以反对。
(三)发展是总钥匙
古代多民族关系治理,因其俗而治。从政治上看,更多的是权宜之计,是在王朝控制力有限的情况下产生的政治策略,难以从根本上实现民族团结与民族地区稳定。而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通过发展,发展经济、发展文化、提升各民族的生活水平等等。
故而,要制定适宜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方案,应多作顺民意、惠民生的实事,如保障就业、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同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22]147。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前提下,尊重差异、交流沟通、和合共处,共同维护多民族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只有各民族都发展起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有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