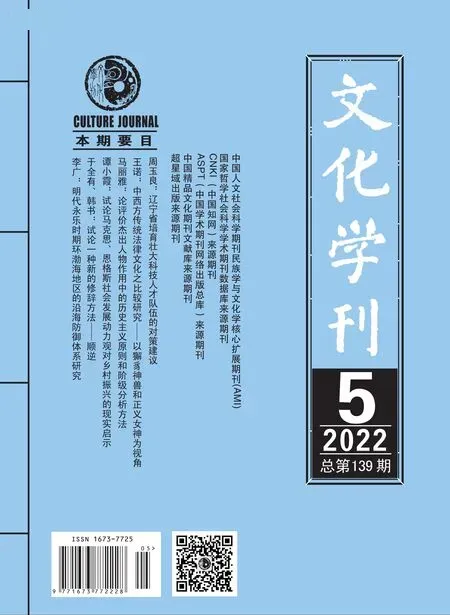文化“居间”的境象寓言辨析
——评严歌苓小说《寄居者》
何燕娜
一、文化“居间”的寓言
作为现今颇具锋芒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霍米·巴巴在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对民族和文化身份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阐述,这一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混杂文化”理论。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看来,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社会中的移民和过去历史中的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处境有着某种超越时空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样置身于一个“文化之间”的世界,他们同时是此和彼,又同时非此非彼,身陷于变动不居的文化翻译(文化既是跨境的又是翻译的——霍米·巴巴语)过程之中[1]。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恰恰正是通过这种充满再生再造可能性的“混杂”文化环境,这些“移民”赢得了弥足珍贵的后殖民视角,他们得以将自己放置于文化的“第三空间”,从而拥有了一种新奇宽阔的叙述视野。严歌苓,作为新移民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凭借其女性独特的叙事视角加持身处东西方文化双重交织文化环境的生命体验塑造一系列多元文化混杂中的“边缘人”形象,不断为新移民文学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寄居者》便是其中的典型作品之一。小说中严歌苓主要是通过三种“境象”的建构来描绘自身关于世界流散者这一群体的文化想象的,并且这些“境象”都具有后殖民理论视阈内的“间性”特征。
“间性”存在的前提是“间隙”的存在,在探讨跨文化交流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与社群的文化身份问题时,霍米·巴巴认为最能充分凸显文化身份差异的地方正是不同文化相交的“间隙”[2]。“间隙”一词本义上来讲是表示方位、指示空间存在的名词,而霍米巴巴所提出的这个文化混杂视域下“间隙”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换句话说,霍米·巴巴实际上是将空间化的思维方式引入了对移民者身份问题的思考。西方理论学者苏珊·斯坦福·弗里曼德在拓展女性主义理论边界的时候曾提出“永远空间化”的论断,她认为无论是身份认同还是文化知识都是位置性的产品[3]。在这种空间化思维下,移民者所身处的多元文化状态其实是东西方文化相互协商与交融的“第三空间”中达到的一种新的文化结果,它不属于所在国文化,又不属于故国文化,而是一种新的“第三文化”。
以此为理论前提,《寄居者》整个文本可以说是这种文化论断的巨大境象隐喻。“境”和“间隙”同样充满空间意味,《寄居者》正是通过充满“居间”意味的文化语境、人物处境、生存意境将文化“边缘人”时代体验、生存体验和身份想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她在小说中努力地标志出人物在社会中特定的文化位置并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作者自身的文化身份思考,为新移民文学的书写加上了极具创新意味的一笔。
二、文本“境”象
《寄居者》可以说是严歌苓新移民文化观书写中颇为直率坦诚的一次表达。从文本的表层来看,文化身份的寓言甚至直接被“裸露”在小说篇名中,“寄居”二字似乎已经将移民者“居间”的文化位置明示了出来,这在严歌苓系列新移民文学创作中实在少见,与她早期同类型的作品《少女小渔》一对比便可印证这个观点。从文本的内理来看,小说中移民者的“居间”的身份寓言其实是在层层推进的“境”象中逐渐揭示的,男女主人公所处的文化语境、“居间”窘境下的生存体验、身为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寻找都以“境”的形式层层隐喻在文本中。
(一)“居间”下的文化语境
作为小说的背景,《寄居者》主要有两个时空设置,一是处于商业经济飞速发展时期的美国和“孤岛”时期的上海,其中又以“孤岛”上海为主背景。
从时代背景上来看,上海“孤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战争历史的“间隙”,是一个被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书写所无法容纳的时间断层。在这种断层里,上海不仅仅是战争风云中的孤岛,更是文化记忆里的孤岛。一方面英、美的殖民文化以高姿态入侵到上海生活的肌理,另一方面革命党人新文化思想也在这里占有一席之地。两种文化的冲击之下,几千年顽固生长的地方文化依然生生不息地留存于老上海人的记忆里。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的文化性格和生活姿态不断产生冲突,又在冲突中相互妥协和成就,上海人、苏北人、客家人的衣食住行在市井生活中嘈杂碰撞,平民百姓、上层权贵、外来流亡者经由严歌苓的笔聚集在一个故事中,多元文化“混杂”的情形在这样的文本语境中被真实地呈现出来。而这种文化混杂气息最为浓厚的便是生活于其间的文化人,因为对于文化身份的寻找与思考在这一类人身上显得尤为迫切。
“文化人”一般意义上是对知识分子的统称,在更通俗的意义上我们将有学识、懂艺术和研究艺术的人都称之为文化人。从这一点来看,严歌苓在《寄居者》中塑造了一批处于“文化间隙”中文化人群像。女主人公玫正是在这种历史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混杂的文化空间中巧妙地游离着。一方面,父亲给予她的文化基因不仅仅体现在一张显而易见的东方面孔,更重要的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文化记忆,据此她可以轻而易举地逃脱父亲的庇护迅速融入上海市井生活;另一方面,在美国文化下成长的她又可以适应上海中西方文化混杂的生活方式。男主人公彼得,是一个在典型犹太文化中成长的犹太人,即使在物质已经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的母亲仍然最大限度保护了他接受精英教育的机会;杰克布是混迹于美国底层在自由主义文明中成长的非典型犹太人,但同时他又是充满文化气息的人。作为普遍意义的“文化人”,三个主人公在一种时空下跨越着国界,有力印证着上海特殊多重文化空间共存下的文化生态。在这里,严歌苓一改从前,将新移民游离挣扎的背景从异国他乡迁移到祖国大陆——沦陷时期的孤岛上海,将主题从展现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在异质文化时空中的身份迷思置换为展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化人”在我们母国特殊时期的“混杂”文化环境中的种种挣扎,以此来验证新移民在世界范围内经历身份离散与文化痛症。
(二)“居间”里的人物处境
从严歌苓以往的小说来看,她笔下最为人惊叹的是对世界“边缘人”心理危机的细致描摹。严歌苓在《寄居者》中一反从前以中国人在异质文化中艰难求生的叙事主题,将书写的笔端指向异族新移民者在中国特殊历史文化场域的生存境遇,关注“双重边缘”人物群。努力用亲身的异族体验去塑造“活”的异族人物,努力将“间性”书写的笔触由中国的流散者扩展到世界的流散者。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彼得是典型的犹太人,在母亲的严格培育下,他有着令人艳羡的职业,外表俊逸,谈吐优雅,是世人眼中“天之骄子”。但他却因为民族身份问题被自己的国家赶尽杀绝,即使他们母子二人千方百计来到上海,当种族战争蔓延的时候,这座以包容性闻名的现代都市也一样容不下他们。女主人公玫也是在哪儿都格格不入的边缘人,在美国的时候,母亲严格的管教将她的童年束缚在琴凳上、马背上、舞蹈把杆上,为了让她在成年后能杀出唐人街。但到了上海,她只能用异国的身份勉强护自己周全,民族国家沦落至此,个人命运也只能任人摆布。男主人公杰克布的处境就更加复杂,他来自柏林却是个美籍犹太人,他的美国护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是足以保自己周全的护身符,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护照已经远远比不上一口流利的德语更管用,世界边缘人的处境清晰可见。就是这样原本相隔万里的三个人,因为玫的爱情阴谋被牢固地绑在一起,作者几乎抓住一切的细枝末节来展现他们作为“寄居者”“飘忽不定”的处境,从而揭示他们“身份”的游离。
除了对边缘人群像的塑造以外,严歌苓以“重复”的动作由现在连接过去让人的物化情境反反复复出现,将“寄居者”在身份认同找寻过程的“边缘位置”在世界范围内触目惊心地标记并勾连起来。文中存在了一种重复式的情境模式。“船一靠岸,日本兵便会戴着防毒面具,用刺刀拨拉开上海本地犹太人的迎接队伍,冲进底舱,把杀虱子、跳蚤,以及种种已知未知微生物的药粉慷慨扬撒。刹那间,一片黑的人饼就成了一片雪白”[4]2。这是女主人公玫在犹太难民登入上海时所看到的画面,这与她曾祖父初次踏入美国领土的场面如出一辙。除此之外,犹太难民在日本人的迫害下求生无门的场景与玫的祖辈们在美国的排华法案中所遭遇的欺压和践踏也是对应的情境;无家无国的寄居者和有国有家的寄居者之间的境遇也没有显著的差别,对处于沦陷区的孤岛上海而言,有国有家的上海人也在“寄居”,日本兵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意凌辱中国人,细长的军刀就像猎杀动物般砍向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时,任人宰割的中国人有时不得不为一桶柴油付出生命的代价。世界离散者们在不同时空中的边缘处境在小说中以电影蒙太奇般的形式得到了展演。这种展演不禁让人产生这样的思考:世界范围内的离散民族的境遇都有共通之处,不同的人生境遇下是相似的边缘处境,一代又一代的移民者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不惜离开生养的故土流浪漂泊到异国他乡,在忍受了骨肉分离的苦痛之余克服了种种心理上的分崩离析,当他们带着对新生活的渴望和憧憬踏进这片陌生的土地时,感受到的却是人性至暗的冷漠与疏远,这种情感上和文化上的双重剥离,使他们彻底成为孤独的“他者”。
(三)“居间”下的边缘意境
边缘者的处境是孤独寂寞的,但应该知道“边缘”也有其珍贵之处。就写作者而言,新移民文学在文化“间隙”中定位为自己赢得了一种特定的“边缘”视角,“边缘”的珍贵之处在于能逃离任一主流文化的牵制而以真切的生命体悟理解生命与世界,以独立自由的精神与世界对话。其中作为新移民作家的严歌苓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自觉,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就像流淌在她血液中的基因符码一样坚定不移。因此,在中西方文化的“间隙”中,她一方面固执地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发掘出了符合现代理想的精神,另一方面严歌苓也不拒绝从异质文明中汲取养分,从而显示出“世界公民”的视野和胸怀,即对生命的本质和人类的终极关怀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在严歌苓的作品中感受到强烈的济世情怀和载道意愿。《扶桑》中对华人内在的生命韧性的全力表现,《金陵十三钗》中对人类现代性的反思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寄居者》虽然以爱情为底本铺展整体的叙事,但是作者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虚构一个庸常世俗的三角恋故事,而是意在通过三个主人公在爱情、国族、文化三者之间的犹疑和抉择来展示“世界边缘人”在特定语境中的困顿与挣扎。但是,和严歌苓其他作品所不同的是《寄居者》在对少数族裔漂泊宿命的展现中作为“寄居者”积极的生存态度被强有力地凸显了出来。
小说中处于同一文化语境下的三个主人公显示出文化混杂语境下不同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态度,他们典型代表了三种不同文化主导下的人格成长。在中国文化为主导下成长起来的女主人公玫、在典型的犹太文化下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彼得、以美国文化为主导成长起来的犹太人杰克布,三个人在不同的文化性格主导下在上海这个“熔炉”中重生再造,产生了迥然相异的人生轨迹。其中,光辉的人性和积极的生存态度集中在杰克布身上,在小说的一开始他便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不坐把人变成牲口的交通工具。在生活中他更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去包容这边缘处境中的艰难与愤懑。美国文化中长大的他,看似胸无大志却在战火中醒悟战争的本质,从日本人的欺压和凌辱中反省出抗争的意义,在犹太难民的宗教仪式和社团活动中找到真正安身立命的所在——文化归属与认同,从沦陷区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中看到了正义的光辉。他在多元文化混杂的孤岛上海真正找到了自我,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一名光荣而正确的英雄。我们可以看到,跨越国境不仅仅是一种现实中的行动,更是一种自我的选择,或曰自我认同的找寻,在这一找寻的过程中“寄居者”们能获得信仰的力量。小说中,严歌苓也以玫的身份作了这样一番省思:“谁才是真正的‘寄居者’。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单。我是个哪里都融化不了的个体,我是个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而寄居在这里的彼得、杰克布、罗恩伯格却不是真正的寄居者。他们定居在这片雄浑的声音里,这片能把他们熔炼成一体的声音。……人信着什么多好,没有国土也没关系,信仰是他们流动的疆土,嗡嗡的诵读缓缓砌筑,一个城郭圈起来了,不可视,不可触,而正因为它的不可视和不可触,谁也击不溃它。”[4]152可见,文化信仰是“寄居者”们在边缘处境中唯一可以抓住的支点,只有找到了这个支点才能在嘈杂的文化语境中获得自我认同。
就像严歌苓自己说的,在自己真实的移民体验中,移民就像把自己从原有的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文化生命的剥离使得她的全部生命神经彻底裸露,正是这种裸露造就了她对新移民议题惊人的敏感,这一点在《寄居者》中有了深刻的诠释。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比起严歌苓的其他创作,《寄居者》者中对于新移民“寄居”情境的呈现和“居间”文化的寓言中,带着有意远离新移民血肉征战的现实沙场的意图,这不可避免地使作品距离生活的源头愈来愈远,其文字的热力也因此而有明显的减弱。此外,在《寄居者》中,我们也能发现严歌苓在驾驭长篇宏制的结构冲突上显得有些散乱,小说语言也存在精致有余,雕饰过度的嫌疑,整体而言不如她的短篇写得那么玲珑剔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