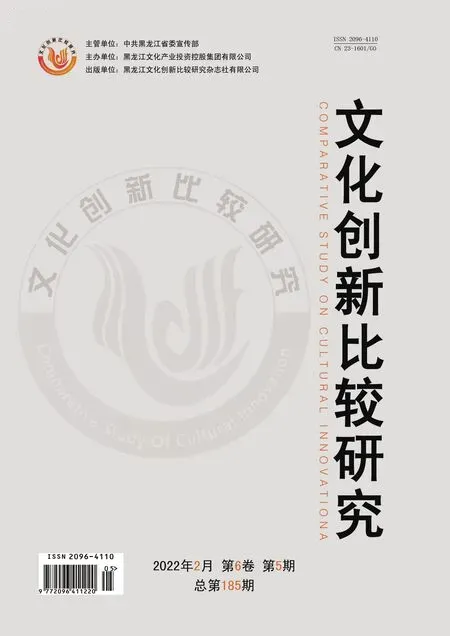符号与互动:“粉丝群体”的集体认同建构
徐振祥,郭鑫
(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岳阳 414000)
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认为单个个体的亲身在场可以使情感能量拥有一个及时的反馈效果,在一个团体中每个成员必须进行充分的身体接触,为其提供共享的关注与情感,然后迸发出群体意识以及成员之间的尊重感。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实时的情感表达不再局限于面对面才能实现,虚拟网络空间使“身体不在场”的信息交流成为可能。技术的普及使人人都能够在网络“外衣”的隐藏下进行交流互动,也就是说网络的匿名性为粉丝提供了互动的安全网,虚拟在场的技术提供了粉丝交流的平台,使粉丝拥有对群体的认同以及归属,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粉丝群体的团结,赋予粉丝成长的价值观意义, 进而推动粉丝之间互动链条的良性运转。网络技术的“虚拟共在”打破了以往的“身体共在”,使身处不同空间和地域的粉丝有了一个交流互动的“虚拟”场所。相比以往的亲身“在场”,虚拟的网络使粉丝的交流互动变得更加及时便捷。
1 符号与互动的相关概述
符号与互动理论,既被叫作符号互动论,又被许多研究者称为是象征互动论。作为一种通过关注个人的生活自然环境,去进一步研究人们群体生活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符号互动论最先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提出并形成,从某种角度上而言,符号也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就一般情况来看, 符号互动论认为事件对于个人之间产生的社交行为影响,并不在于事件自身所产生的内涵与功能,而主要在于事件自身相对于个人所产生的社会意义。而与此同时,由于事件的意义主要来源于个人和社会其他人之间的互动,而这种的互动又主要包含了文化方面的互动、 语言方面的互动以及社会制度方面的互动等各种因素, 当个人在应对其所面临的社会事件时,也会尝试着运用自己的解释去运用事物并修改事物对其的含义。
关于符号与互动这一理论,其思想奠基人米德坚持探究个体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的关系,并且,运用社会行为去解释个体意识,米德主要吸收了实用主义哲学关乎于真理的经验关联性以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客观意识研究方法,最终认同,根据个人的行为, 特别是可以让别人观察到的行动去研究个人经验的行为主义方法。与此同时,将理解个人的行为与经历作为整体的社会背景,并由此发展出了社会行为主义方法。
2 符号编码促成粉丝社群的生成逻辑
根据鲍德里亚所言,在现代消费社会,一个物品既是符号,也是消费对象,被消费的正是该物品的个性和差异[1]。偶像借助自身的“人格符号”能够获得粉丝的理解和喜爱。粉丝从一开始的路人变为××明星的“fans”,这中间需要一个对偶像的认知了解的过程。身材“高大”、形象“帅气”、“少年感氛围”等都作为明星偶像的气质符号,以此获得粉丝的特定认知与理解。偶像完美的身形音貌以及在专业领域的地位是他拥有粉丝的第一步。而饭圈作为粉丝共同体,个体成员“饭”上爱豆的基础源于对自己偶像的认可,例如明星的外形气质、价值观、成长经历、演艺成就、生活习惯等。根据“粉丝”群体思想观念调查报告显示,明星是否敬业是粉丝们选择偶像的重要标准[2]。
同时新媒体的发展为各种媒介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开放平台,互联网组织迎合了“受众细分”的发展趋势,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并区分为各自的群体组织[3]。互动仪式通过个体的相似关注,对于不属于群体的“局外人”进行设限,通过这种限制,使参与其中的人能够依据个体身份认同机制明确辨明内部群体成员。粉丝能否加入组织,会根据相应的准入机制判别申请人是否契合“粉籍”(即粉丝身份),进而使群体拥有一个风朗气清的内部环境。在互动仪式启动之初,由于个体粉丝拥有统一的关注焦点聚集形成了互动群体,当群体成员参与具体的互动时,在获得情感体验的同时其归属感也逐渐增强,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命名标准的群体符号也因此得以产生、传播和使用。同时这种符号也作为区分成员非成员的一种标准来对粉丝进行区隔。例如,微博粉丝群设置了一系列关于明星的问题来测试申请进群者对偶像的熟悉程度,以此来判断申请人是否具有粉丝身份,是否拥有对偶像的忠诚度。粉丝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准入机制是只有群体成员才了解的黑话(即行话)[4]。作为非粉丝的路人,在网上经常会看到看不懂的缩写如zqsg(真情实感)、awsl(啊我死了)、zfwb(转发微博)等,以及空瓶、捞、断层等粉丝专属用语,都是粉丝群体专有的话语符号表达体系。
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其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共同关注的焦点,只有当受众对相同的人或事物产生兴趣,才能根据这一相同的关注点产生思考和交流[5],进而出现更深层次的互动行为,引起更大范围内的互动传播。粉丝拥有共同关注的偶像,通过个体情感表达找到组织并汇聚在一起,同时利用即时通信技术和社交媒体的传播, 在错位的时间和空间中交流,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展开互动。在这种虚拟环境中, 人们的形象和举止往往有所隐藏,呈现出来的只是符号语言和画面。情感的传递方式不再是面对面,而是介于相应的媒介环境,化解时间和空间的弊端,即使身处不同空间地区的参与者同样可以在互动中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6]。
3 情感参与下粉丝自我投射与群体互动
柯林斯用“情感能量”来讨论情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认为短期的情绪可以通过互动仪式转化为一种追求群体成员身份和获得群体归属感的长期情感[7]。粉丝是指甘愿为他们的偶像明星付出时间、 精力和金钱的热爱者。他们通过对偶像的理解和认同激发情感,从产生自我认同到群体性认同。
弗洛伊德认为能够在别人身上产生自己情感的心理就是“投射”。粉丝对于偶像的感情来源之一就是如此。处于粉丝群体中的每个人在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产生自信时,都希望自己的形象完美,能够获得别人的喜爱。而当这个愿望无法快速实现时,他们就会把理想中的自我投射到偶像身上,从而产生情感来源,自发成为偶像的粉丝并加入他的粉丝组织。柯林斯强调,在群体互动的过程中,个体产生丰富的情感能量,且情感能量能够累计成为长久的情感积累。随着偶像的成功,或是说“出圈”,即被广大网友路人称赞,粉丝们往往也会视其为自己的成功,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群体间的仪式互动是群体成员所产生的个人情感的表现,个人情感在成员间传递形成群体感情,成为群体凝聚力的核心。
粉丝在日常生活中,在使用媒介时能够展现出不同的自我形象,偶像对于粉丝是理想自我的镜像投射,粉丝从而将自己的情感赋予在偶像身上,随着偶像的发展成长,粉丝也逐渐建构出一个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统一的身份。粉丝群体在群体内的交往不仅是因为共同的明星关注和情感汇聚在一起进行日常的聊天问好。群体内的成员有着各自不同的任务以及身份特征。在虚拟粉丝群体中,每个人既能获得信息,也会分享自己得到的信息,这样循环往复,才使得粉丝群体间的互动行为得以建构,保证群体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8]。詹金斯在《文本盗猎者》中曾提出盗猎者的概念,即粉丝通过对原作品的二次加工再造为新的内容[9]。在网络时代,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多,粉丝可以搜寻明星的图片或者截取影视剧片段来生产自制的明星表情包,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从事文字工作者的粉丝,抑或是有着剪辑爱好的粉丝会依据自己内心的剧本,对明星所有动态物料进行主观能动的再次加工生产[10]。
基于积累的情感能量,粉丝们会更为忠诚地为偶像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同时,粉丝又是消费群体,其消费行为一是体现在粉丝对明星表情包的使用,对明星参演电视剧、电影、综艺的收看与分享,对明星所发布微博的转发评论点赞等行为,二是体现在粉丝群体的消费行为,粉丝为了支持自家爱豆,往往会产生购买明星所代言的商品的行为,并会在群体内呼吁,尽自己最大努力为爱豆的价值做贡献[11]。而偶像的出圈增强了群体成员的满足感,情感能量也随着互动的增加而不断累积,群体成员的团结感和归属感促使群体成员更加积极地加入仪式互动中,形成循环往复的互动仪式链闭环。
4 情感积累凝结群体互动的价值
群体信任是粉丝互动的催化剂,表露互惠是群体互动的动力,社会性情感能量是其互动的根本诉求, 社群管理员和节目运营方构成了互动仪式的权力分层,由此形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基于此,粉丝群体得以形成。在群体内部,粉丝们的交流互动也促发了更进一步的情感,从而产生更深入的交流,并循环往复。
因共同的关注和专一的情感而进行的互动仪式,能够形成一种群体性符号[12]。涂尔干认为,仪式能加强社会个体对集体的认同感,保持对集体的顺从归属观念,从而使共同体得以继续维持下去[13]。群体成员身份认同得到强化后,同时也增强了成员的归属感和团结感,仪式随着互动不断推进,个体间传递的情感能量越来越强,推动互动仪式持续进行,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感也随之加强,进而形成循环往复的互动仪式闭环。
粉丝一方面把偶像当成自己“完美形象”的具身化形象,另一方面也被偶像身上具备的品质所影响。具体表现在偶像对粉丝群体的榜样作用,以及价值观引导。偶像是粉丝现实生活中对理想自我的投射,反映出每个人对自己的美好期望,粉丝通过对偶像的欣赏和模仿,可以实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青少年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就能带来示范作用,引导粉丝文化朝着正确的主流价值观方向发展[14]。例如,由粉丝汇集而成的“易烊千玺V 公益”组织并发起了多场公益活动,通过创办品牌公益项目“千玺林”,累计捐赠100 多万元的善款。易烊千玺18 岁生日时,其粉丝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湖南省桂东县第一中学设立“易烊千玺·新长城高中生自强班”,对50 名学生提供助学帮助。
对粉丝群体来说,消费与偶像相关的产品同样也被赋予文化意义。在产生消费的过程中,粉丝通过购买行为表达对偶像的情感认同,以此强化偶像的符号意义或赋予偶像符号更加丰富的所指意义[15],进而实现自己粉丝身份的意义。饭圈内部会组织许多集体应援活动,激发群体性情感,产生对偶像共同认同以及支持。例如,易烊千玺在2021 跨年夜有新电影上映,粉丝会纷纷对其电影进行宣传,或预售时购入电影票,并且有粉丝群会分配成员任务,以此种交流互动的仪式来激发认同并强化群体,进而产生更大情感能量。
5 结语
在粉丝群体中,共同的关注焦点使个体的情感凝聚成群体中的情感能量累积,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同时满足了自身的情感需求,提升自我效能感,积极学习偶像身上的优秀品质,朝着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方向努力,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情感积累的基础上也为偶像的事业资源以及关注度做出了贡献,并在不断循环的互动仪式中进行生产消费,包括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以此促成了粉丝经济的产生。